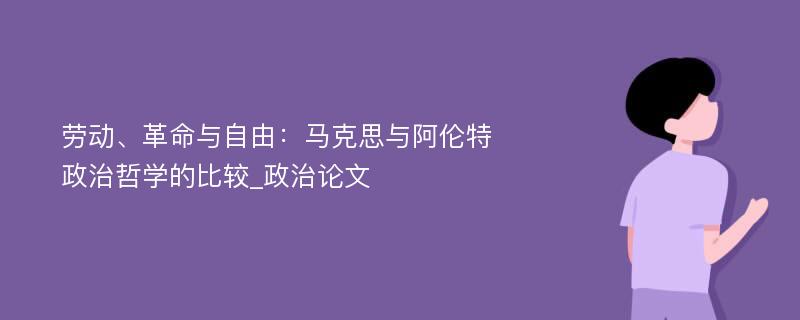
劳动、革命与自由——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伦论文,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黑暗时代的一盏明灯”①,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在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的渊源中,有个“巍然耸立的马克思形象”②。可以说,马克思对阿伦特的影响最大,因为:第一,马克思不能忍受沉思内省,他迫切希望运用资本主义所创造出的强大生产力来“改变世界”,从而明确地跟西方主流传统相决裂;第二,马克思是最明确地认识到传统之价值的人,同样,与其说阿伦特对西方思想准则持反对态度,不如说她更关心传统在社会生活中的歪曲表现;第三,唯有马克思使政治成为谋求更完美人生的手段,对他来说,行动的世界胜于思想的世界。③在此基础上,阿伦特本人十分重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西方政治传统的理论,“马克思哲学不仅颠覆了黑格尔,而且颠覆了思想与行动、沉思与劳作、哲学与政治的传统等级秩序”④。阿伦特的《人的境况》一书被视为她与马克思的直接“对话”,而后她又有专门论述《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讲稿问世。但阿伦特本人又对马克思存在诸多误解。这种误解主要集中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和“支配他者的人不能获得自由”三个方面。⑤这实际体现了马克思和阿伦特在“劳动”、“革命”和“自由”三大问题上的根本差异。在此,本文仅就这三个问题来具体阐述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的联系与差别。
一、劳动:“自由的”还是“必然的”
马克思与阿伦特都很关注劳动问题。劳动这种人类特有的活动,正是在传统中最受轻视的人类活动。而在马克思这里,不是上帝而是劳动创造了人,人之所以胜过动物,正是因为他通过劳动创造了自身。在马克思看来,人不是理性的动物,而是劳动的动物,将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不是理性而是劳动,劳动是人的自由本质的自我确证:“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劳动的动物,有意识的劳动正是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直接体现,而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在马克思之前的国民经济学家虽然也看到了“劳动创造财富”的意义,但他们所理解的“劳动”,还只是抽象的被异化了的劳动,所以马克思批评“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⑦。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强调:马克思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是以“生产”概念取代了“反思”概念,以“劳动”概念取代了“自我意识”⑧;金里卡也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在政治进步中居于中心地位”⑨;而恩格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⑩。因此阿伦特承认马克思真正反传统的一个侧面主要是对“劳动的赞美”,“马克思是19世纪唯一的使用哲学用语真挚地叙说了19世纪的重要事件——劳动的解放的思想家”(11)。但马克思在赞美劳动的同时,也最为充分和自觉地认识到和揭示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还存在着“异化”:“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2)所以马克思为了“拯救劳动”,将劳动进行了二分:必要劳动和自由劳动,主张通过从必要劳动走向自由劳动的“劳动解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尽管如此,阿伦特还是无视马克思对劳动所做的区分,一直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只是“为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一种“人类营生活动”,是一种受必然性强制的活动,属于私人领域。而在阿伦特看来,劳动是前人类行为,与其他种类动物的行为有共同之处,劳动只是政治的“前政治”的条件,只能停留在政治的外面。(13)在劳动行为中,不存在任何显示个体性和差别的可能性。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观存在着内在矛盾:马克思从1844年《手稿》到《资本论》都坚持劳动创造人,这是完全混淆了劳动和生产。马克思以为人类的解放取决于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的进化,这是模糊了人造的自由领域(政治领域)和自然决定的必然领域(经济领域)之间极为重要的界线,这就有可能导致以后者来代替前者。在阿伦特看来,虽然马克思从未想要与自由为敌,但他却抵挡不住必然性的诱惑,因为他犯了一个关键性的错误:模糊了工作与劳动的界限。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对“积极生活”(vita activa)所包含的各种活动进行了三分: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劳动与单纯的生存本能相联系,这使它成为一种无休止的重复性活动,但它确保了个体生存和类生命的延续;工作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生命自然环境的人造物的外部世界,为有死者的生活赋予了一种持久长存的尺度;与之相比,行动并不带来外在的结果,它致力于政治体的创建和维护,为历史创造条件,是最出色的政治活动。(14)在阿伦特看来,劳动、工作和行动三者都根植于诞生性,但行动与人的诞生性境况最为紧密,行动就是“开始的能力”,去行动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就是去创新、去开始,因而人在根本上就是一个“开始者”。行动显示行动者本人,而劳动和工作都不显示活动者本人,都需要从更高一级的活动中获得拯救,所以只有行动才是其中最高的活动,体现了人的自由本性。人作为“劳动动物”需要“工作”把他从无休止的生命循环中拯救出来;在工作中,人是作为“技艺人”的制造者,制造出工具,工具的制造不仅减轻了劳动的痛苦,而且使劳动者获得了一个相对持久稳固的世界,但工作遵循的是手段—目的模式,在一个由手段—目的模式所决定的世界中,所有的价值都会自行贬值,而且在工作的过程中,难免还要带进暴力;行动之所以不同于工作,就在于其脱离了手段—目的这一模式,因此,作为目的本身的行动就具有创造性和开端启新之功能。并且在阿伦特看来,相对这种沉默无言的劳动和工作而言,行动往往伴随着言说,或者说,言说即行动。(15)只有言说和行动这一以自身为目的的自我显示的活动,才能把制造者从无意义性中拯救出来,人才能获得自由。尽管劳动、工作和行动同属“积极生活”,都是人生在世必不可少的基本活动,但行动还是与其他两种活动不一样,劳动和工作是属于前政治的,而行动则特别地与政治生活相关,是最出色的政治活动。在此意义上,阿伦特认可“人是政治的动物”。但在阿伦特这里,投身于行动的只是自由人,广大奴隶和工匠被排除在外,这就使得她的“行动创建和维护自由”大打折扣。
阿伦特利用三分法对马克思劳动观的批评,虽说独辟蹊径,却颇有争议。阿伦特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的劳动观对促进她所特别关心的政治自由行动之可能性的愿望:“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6)阿伦特没有认识到:第一,马克思的初衷是把劳动价值论的运用范围严格限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第二,马克思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只是与这种劳动是否有助于产生剩余价值交换问题相关;第三,马克思的著作清楚地表明,阿伦特所说的“劳动”在马克思那里被归为“异化劳动”,它是社会生产组织的一种特殊历史形式,正是马克思要超越的。(17)马克思其实早就认识到,正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导致了“劳动”由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变成了仅仅是“维持生存的手段”。阿伦特建构“行动”理论的努力,由于过分重视“行动”的重要性,夸大其与劳动和工作的对立性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密切相关性,甚至以此区分来否定和批判马克思的劳动观,体现出她的一种“行动本体论”情结,在根本上走向了“行动唯我论”。因此,阿伦特反而不无讽刺地与她所反对的“正统的”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到了一起。(18)
二、革命:“解放”还是“暴力”
应该说,马克思是“暴力革命”的倡导者,但并不能因此说马克思就是暴力或极权主义的始作俑者。马克思所生活和亲身体验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就是“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对立性和个性”(19)的社会。马克思的理想,就是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现实的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从而实现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这只有通过“革命”——推翻现存的统治权力和消除旧的环境的政治行为,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使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而建立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在马克思看来,“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20)。所以,“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1)。要是没有革命运动,共产主义制度就不可能产生。因此马克思强调,自己“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22)。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深刻认识到:要根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资本统治人的弊病,仅仅改变这种制度中的规则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彻底废除这种制度本身。所以,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进而“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23)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4),也就说通过“暴力革命”实际地推翻产生资本主义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来实现——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25)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共产党人从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共产党人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革命理想中确实有暴力的成分,但暴力只是达到非暴力的革命的手段,而决不是目的本身。因为在革命中,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所以,马克思只是运用“暴力”概念作为他描述卷入伟大的社会与经济变革的强制词汇表的一个常规部分。(26)
在阿伦特看来,“革命”(revolution)一词原来是个天文学范畴,指的是星体有规律的运转,而革命的原义就是“复辟”,是旧政权的恢复。但近代以来发生的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却意味着社会的根本性变化:为的是令无知者启蒙,令全人类中的受奴役者解放。所以,创新性、开端和暴力这一切因素,都与革命概念息息相关。(27)因此,革命首先包含这样一种历史观念,即历史会突然开启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进程,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但并非所有的政治剧变都是革命,有没有革命就要看有没有在历史存在中开创未来,缔造社会的新生。“只有发生了新开端意义上的变迁,并且暴力被用来构建一个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缔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体,从压迫中解放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那才称得上革命。”(28)所以,革命就是在政治世界进行的开新行动。革命这一开新行动的核心内容是创造一个自由的公共领域,而阿伦特认为,人类有能力在任何逆境下“重新开始、自由行动、创造真正的公共领域”(29)。但革命要确立的“公共领域”,却不仅是另一个“政治秩序”,而是另一种“社会秩序”:“对于革命者来说,更重要的是改变社会的结构,而不是政治领域的结构。”(30)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对自由的渴望。极权主义的肆虐让阿伦特看到了与人的自由初衷完全违背的新专制压迫形式,它造就了现代政治的空前危机,这样的“革命”是坏死的革命,因为它糟蹋了革命的创新承诺。但阿伦特认为,建立一种与自由相一致的政治权威,最终的希望仍然在革命。革命必须建立一个维持政治自由行动的公共空间,“没有公共自由和公共幸福的原则,革命就无从发生”(31)。唯有如此,它开始的那种政治自由行动才有可能是一个有意义的革命承诺,否则,即使它的开始时刻有政治自由行动,也只是革命“暧昧复杂”性的一部分。
阿伦特认为,革命就是关于行动的个体、显现的空间、真正的权力和自由。以此为标准,在《论革命》中,阿伦特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的区别。在法国大革命中,革命的暴力并没有解决大众的贫困问题,反而使民众陷入了更大的恐怖,最终葬送了个人的自由;而对于美国独立战争的暴力革命而言,革命者在革命后迅速制定了一部能够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限的出色宪法,从而避免和压制了暴力革命的肆无忌惮的特性,保持了美国优秀的革命传统。法国革命是一场导向极权主义的失败的革命,而美国革命则由于建立了自由宪政而成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同样以此为标准,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革命理想在颠覆和超越西方政治理论传统的过程中“颂扬了暴行”(32),所以马克思的革命理想也与法国革命一样,走向了自己反面——革命变成了暴力——极权主义。但实际上,马克思的革命的目的在解放人——在“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的意义上,他与阿伦特“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是一致的。马克思强调暴力只是实现非暴力的手段,特别是在革命的初期: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做的。但马克思暴力革命的最终目的,却不是要建立新的暴力,而是要消灭暴力,以至于消灭阶级和国家——革命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在革命后的社会里,革命将被“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33)所替代。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马克思对于大众有组织的社会暴力——“社会力量”,即人们凭借协作性实践所产生的力量——的强调也许是在暗示,社会力量所依靠的是压力或说服力,而不是暴力或暴行。(34)
三、自由:“个性的”还是“公共的”
自由是马克思和阿伦特都重点关注的核心问题。在马克思这里,自由是人的一种特别的生活或生存状态,即自由生活或生存的状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的自由实现的历程概括为三大阶段:最初的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而人的自由真正实现的是“第三阶段”,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35)马克思的自由追求的是每个人都作为完全独立的自由个体,拥有和享受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从而获得“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也即马克思所强调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因而“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6)自由既是人的个性的全面实现,也是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专门用一个非常形象和贴切的比喻作了说明:“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7)这才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追求和向往的人的自由个性真正解放的“自由王国”。但“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而它的根本条件就是“工作日的缩短”。(38)对此,马克思强调:“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也即“个性得到自由发展”。(39)苏联学者也指出,马克思全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中心思想就是人的“自由思想”:把人和人类从压迫他们的种种势力的支配下解放出来的思想,对自身命运和全人类命运负责的个性的形成的思想。(40)
在阿伦特看来,“自由是一种在世界中的实在,表现为可以被听见的词语,可以被看见的行动,以及在其最终融入人类历史的伟大的故事整体之前被人们谈论、记忆和编成故事的事件”(41),所以自由既与行动有关,又与政治和公共领域有关。在劳动中,人完全受生命必然性制约;在工作中,人作为制造者虽然有一定的自由,但是由于受到制作对象和制作工具等物质手段的制约,还不是完全自由的;只有在行动中,人只和人相互作用,不受任何物质因素的制约,才是完全自由的。因而阿伦特把行动看成是自由的体现,与政治生活最为相关:自由本身就是人们共同生活在政治组织中的理由,没有自由,政治生活将是没有意义的;政治存在的理由就是自由,而它的经验领域是行动。(42)这一方面表明,在阿伦特那里,自由与行动密不可分,自由与行动实际上是一回事,只有在行动中才能真正获得自由,这种只能在行动中获得的自由才是政治的真谛。另一方面又表明了阿伦特独特的公共自由观,即自由离不开一定的公共政治领域。“自由是一种政治的或公有社会的现象,而行动则是真正政治的核心”(43)。但这种自由不会因为解放的行动而自然地到来,除了单纯的解放之外,还有赖于其他同样解放了的人,以及一个对所有人都是公共的空间,没有这样的公共空间,就没有自由可言:“没有一个政治上有保障的公共领域,自由缺少得以在其中出现的一个真正的现世的空间。”所以,真正的自由源于政治领域,“需要一个组织起来的政治性的世界,以便每一个自由的人都可以通过词语或行动使自己加入到这个世界之中”。(44)在阿伦特这里,自由、公共领域与行动是三位一体的。人类的最终目的是要获得自由,而自由只能在公共领域的行动中获得,它与私人领域中的一切活动无关,只有摆脱了家庭生活、生产劳动的必然性领域,“完全从生存必需性和生存必需性所从出的关系中摆脱出来”(45),进入绝对平等的公民身份的领域,政治自由才能实现。“唯有存在一种公共领域,才会出现一种不仅仅是人统治人的政治”(46)。在此意义上,阿伦特视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为实现政治自由的典范。
但阿伦特的自由观捍卫的是政治共同体里的自由,而不是个体反抗共同体的自由。在此意义上,阿伦特与马克思的自由是根本不同的两种自由:马克思反对和批判的是“虚假的共同体”里的形式自由,追求的是“真正的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实际自由,即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全面而自由发展(47);而阿伦特虽也认为自由属于公共领域,自由存在于一个组织起来的政治性的世界里,但她看重的还是古希腊城邦制的自由:城邦是所有政体中最健谈的,因而也是最自由的空间。(48)在阿伦特这里,政治和自由总与城邦共存。但古希腊城邦制的政治和自由只属于“城邦之内”,“城墙之外”实际上既无“政治”也无“自由”。(49)所以,阿伦特的自由观只是达到了形式的“精神和自由的概念”,还远没有达到马克思“自由个性”的实践水平。说到底,阿伦特对自由的阐述尽管关注现实,但却根本上源自希腊古典时代,因而更多的是对现实自由的一种理论想象——一种公共政治领域的乌托邦。
注释:
①[美]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②③(17)(18)(29)(43)(46)[加]菲利普·汉森:《历史、政治与公民权:阿伦特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5、35、235、65、75页。
④[美]汉娜·阿伦特:《传统与现代》,载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8页。
⑤(11)(13)参见[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2、13—15页。
⑥⑦(12)(16)(19)(20)(21)(24)(36)(37)(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179、158、162—163、46、232、539、66、189和185、537、571页。
⑧参见[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⑨[加]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6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14)(15)(45)(48)参见[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6、5、1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1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
(25)(3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1、874页。
(26)(34)[美]谢尔登·沃林:《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0、510页。
(27)(28)(30)(31)[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5、23、14、218页。
(32)Hannah Arendt,Between Past and Future:Six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1,p.23.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第104页。
(3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9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下)第218—219页。
(40)[苏]罗森塔尔主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6页。
(41)(42)(44)[美]汉娜·阿伦特:《什么是自由》,载《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9、370、372—373页。
(49)许章润:《城墙之外无政治》,载《读书》201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