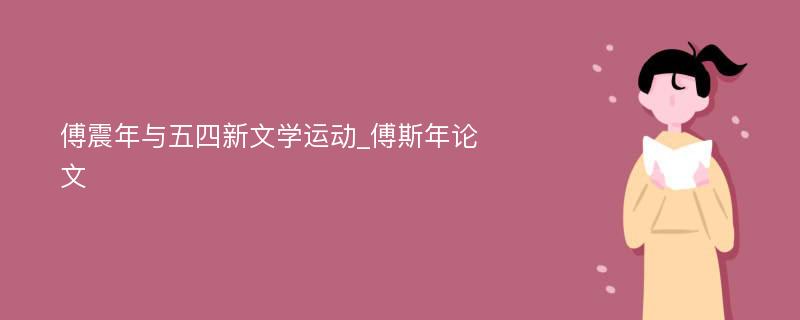
傅斯年和五四新文学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新论文,文学论文,傅斯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动的向封建主义进攻的思想启蒙运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除胡适外,其他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象傅斯年、罗家伦”等(毛泽东语,见斯诺《西行漫记》),都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因此,依据历史事实,研究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社会活动和思想活动,恰当地评述他们的历史地位,将会开阔我们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视野。本文即是这一尝试。
一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件事。接着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宣布了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的三大主义。这两篇文章,成了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发难宣言。但这发难者的先声,似乎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反响,“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先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注:《〈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当时守旧派们对高雅的文言有着极强的信念,认为主张白话者只是“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注:严复著:《书札六十四》,《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甚至讥笑他们以白话藏拙。新文学运动若想取得发难的成功,必须有更多的同盟者和追随者,特别需要那些国学根底深,文言文写得好的人站出来拥护白话文学。
傅斯年服膺胡适应用科学方法以研究学术后,就常去胡适家中讨教,而“适之先生甚惊异孟真先生中国文学之博与精。”(注:罗家伦著:《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一期。)在当时北京大学师生中,“文言文写得不通或不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多,文言文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注:傅乐成著:《傅孟真先生年谱》,台湾传记文学社,1969年。)正是在胡适的引导下,有“徘徊崎路的资格”的傅斯年走到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下。因而罗家伦说:“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崎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中。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注:罗家伦著:《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一期。)
1918年1月,《新青年》刊出了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议》。这篇看似只是普通读者来稿,实则经胡适亲自校阅,被列为“要目”而推出的万字长文,充分显示了新文学论者的良苦用心和寄以傅斯年的厚望。傅斯年在文章的一开始,便首先表明了自己拥护文学革命的立场。但同时他认为,由于传统的极大惰性和历史的深厚积淀作用,国内对文学革命持怀疑、反对态度的人很多,而象陈、胡发难者那样单纯列举文言文的弊病,武断地宣判文言文的死刑,是没有说服力的。因此文学革命论者应该更多地去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和系统、科学的论证工作。《文学革新申议》首先从理论上就文学性质上立论,认为文学和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一样,皆“群类精神上之出产品,”它应当同政治等一起,随时势的变迁而变化。而且文学的作用,在于“宣达心意”,而心意又是一个人对于政治等一切心外景象所起的心理上的反映,既然政治等一切心外景象都随时变化,那么今人的心意,自然不能与古人相同。如果再用古人的文学来表达今日的心意,自然是困难和不可能的。另外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从六诗、楚辞的“全本性情,直抒胸臆”到明清的“复古”,可以说,纵观楚汉至今二千年中国文学发展的轨迹,凡因循守旧者必成文弊,自身无多少存在的价值,而不因袭古人、自我创造者都能大开风流,独领风骚。再从当时的社会现实看,西方科学文化输入中国,近代社会剧烈的新陈代谢,也必能促进新文学的诞生。正是他看到了历史的大势所趋,从而对文学革命表达了强烈的信念,认为文学革命自是“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逆从者。”(注:《文学革新申议》《傅孟真先生集》第一册“论学类”。)
傅斯年在《文学革新申议》中积极响应陈、胡的文学革命主张,从理论、历史、现实三个方面论证了旧文学之当废,新文学之当兴的历史必然趋势。他的论述,具有浓厚的理性色彩和逻辑力量,是自文学革命以来革命阵营对革命对象进行的第一次系统的批判。从此傅斯年一发而不可收,连续撰写多篇文章,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名的“文艺理论者”(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作家小传”)。二
在文言文雄踞社会的各个阶层,古典文学霸占文坛的情况下,发难者在文学革命之初,大都倾全力于破坏,还无暇顾及新文学的建设问题。而傅斯年参加文学运动之初,便正确地认识到破坏(旧文学)与建设(新文学)的工作应同时进行,而且建设远比破坏更重要。正是这种立足于建设的指导思想,使傅斯年得以在新文学运动中贡献出自己颇有见地的建设性意见和主张。
(一)关于“文言合一”的观点。“文言合一”是白话文运动中的根本主张。但在这一根本主张下如何“废文言而用白话”,实现文言合一,新文学革命论者意见是不一致的。胡适主张白话文学“不避俗字俗语”(注:胡适编:《文学改良刍议》,《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钱玄同则赞成“纯为白描,不用一典”,主张“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注:《寄陈独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刘半农的见解也许更正确一些,他认为文言白话各有所长,不能偏废,两者应相互取长补短,“于文言一方面,则力求其浅显使与白话相近;于白话一方面,除竭力发达其固有之优点外,更当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优点,至文言之优点尽为白话所具,则文言必归于淘汰”。(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但刘半农的这一见解,只是文章诸多观点中的一个,匆促中并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述。受此启发,傅斯年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于1918年2月《新青年》上发表了《文言合一草议》一文,就“文言合一”问题作了具体而详尽的论述。在这篇文章里,傅斯年首先阐述了自己关于“文言合一”的观点,他认为不能把“文言合一”简单地理解为废文言而用白话。原因在于,文言尽管有种种缺点,但毕竟历经二千年的发展进化,内容丰富;而白话虽行于当世,但内容贫乏,表达力弱。正因为文言、白话各有自己的优缺点,所以对文言不能全盘抛弃,而应扬弃;用白话也不是照搬当时的口语,而应加以改进。“文言合一”应该是“以白话为本,而取文词所特有者,补苴罅漏,以成统一之器”。这样,取材于语言者,取其质,取其简,取其切合人情,取其活泼饶有兴趣。取材于文词者,取其文,取其繁,取其名词剖析毫厘,取其静状充盈物量”。(注:《文言合一草议》,《傅孟真先生集》第一册“论学类”(本部分未注引文均出此)。)这一辩证的观点,无疑比刘半农的看法更为具体,更为系统和全面一些。
正确的原则是行动的基本保障,但仅仅停留在原则上是不够的,傅斯年认为必须将这个原则划为具体的方法与措施。他的具体观点是:①语言中代名词、介词、位词、感叹词、助词、应全取白话,如用“你”“我”“他”代替“吾”“尔”“汝”“若”,用“拉”“了”“麽”“呀”代替“焉”“哉”“乎”“也”,用“哀呀”代替“呜呼”等,就显然亲切而容易理解。②白话的不足,在于名词和形容词的贫乏与直朴,而文言中的此类词,往往具有审美的价值和“画龙点睛”的艺术表达力和感染力,因此应当有选择地吸收。③中国的文字,一字一音,一音一义,而且同音字极多,容易造成听者理解的困难。对此傅斯年主张用“单不足以喻则兼”的原则予以解决,即尽量少用单词,多用复语,“故白话用一字,文词用二字者,从文词。白话用二字,文词用一字者,从白话”。这样文言中的“今”“往”就被白话中的“现在”“过去”代替了。当然对于成语,如“今不如夕”,因是约定俗成,就没有改正的必要了。④重视俗语,傅斯年认为,许多描写事物与表达感情的俗语,非常传神,表现力极强,因此无论雅俗,都应该尽量兼采。⑤遵循“出词贵简”“贵次天然”的原则评判文言与白话,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应力求简洁、明了,这是一个根本原则。
(二)关于“欧化的白话文”的观点。1918年4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总结了一年来文学革命发难后的理论成果,文中把文学革命的目的化整为零,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这标志着文学革命发难期重心的转移,即从对封建文学的批判破坏而发展到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实际发展。但在白话文学进入实践阶段的初期,只有理论的倡导无现成的楷模;虽然有《水浒传》、《红楼梦》等旧白话小说,但与新文学的要求亦有相当距离;在文言书海里成长起来的新文学论者要改变自己思维和实践的习惯,无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初期的白话文,“有许多很不可看的,很没文学组织的…‘你’‘我’‘尔’‘汝’随便写去,又犯了曹雪芹的告诫,拿那‘最可厌的之、乎、者、也’一齐用来,成就了半文半白、不文不白、不清不白的一片”,自己扎不下阵角,更遭保守派的讥笑。这引起了傅斯年忧虑,认为当务之急是研究白话文的做法。他根据自己做白话文的经验,撰写了《怎样做白话文》一文,提出了做白话文的两大原则:“一、留心说话。二、直用西洋句法”(注:《怎样做白话文》,《傅孟真先生集》第一册“论学类”(本部分未注引文均出此)。)。
关于“留心说话”──“留心自己的说话,留心听别人的说话”。傅斯年认为,语言和文章,在文言分离的时代,是两样东西的,不会做文章的人,可能善于说话,不善说话的人,可能做得好文章。但“言文合一”以后,文章语言便是一回事,国语文学就是文学国语。这样想做好白话文,便需要把语言的精神,当作文章的内在素质,从而必须善于说话并留心自己和别人的说话。
关于“直用西洋句法”。留心说话,把说话当作白话文的凭籍,这固然是重要的,但仅有此又是不够的。因为文言分离二千年之后,白话由于缺乏修饰与改进,变得越来越苍白、直露,在文典学、言语学、修辞学上都有着若干致命的缺陷,因此中国国语文学的发展,必须于“乞灵说话之外,再找出一宗高等凭借物”,那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即使国语“欧化”,成一种“欧化的白话文”。白话文为什么需要欧化呢?傅斯年认为,在句法上,近代西方文章都是一层层叠进,思想意思一层层显出,逻辑性很强,“层次分明”是西洋文的一大特征。而中国的文章则相反,复句少,单句多,一个问题层层分析的句调与文章,就更没有了。傅斯年认为这是中国人思想简单、逻辑性不强的表现。显然,他并没有将国语欧化仅仅视为一个语言问题,而是将语言问题与思想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身体力行,《怎样做白话文》本身即是一篇在力去原来的简单,力求层次的发展,摹仿西文语法的运用方面体现较明显、较成功的白话论说文。
傅斯年还从“移人情”这一文学的根本功能的角度分析欧化白话文的必要性。他认为,文学的职业,只是普通的“移人情”,文学的根本,只是“人化”。按照这一观点,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旧文学是不足以借鉴的,只有文艺复兴以后体现人文主义精神的西方近代文学才符合“人化”的这一标准。中国文学只要效法西方近代文学,受它的感化与影响,也一定能达到“人化”的境界。由此傅斯年提出了“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的观点,这种全盘欧化的观点,当然是错误的,显示了“五四”一代青年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的幼稚。但应看到,傅斯年实际上在这里注重了文学的思想性,主张文学应反映、表现人性,是人的文学、人化的文学,已经包含着“文学即人学”这一根本的文学观,这是难能可贵的。
《怎样做白话文》提出的创作白话文的两条凭藉,无论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十几年后,胡适在综述中国新文学的成绩时曾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白话文建设中提出的“两条最重要的修正案”。并为此论述到:“近年白话文学的倾向是一面大胆的欧化,一面又大胆地方言化,就使白话文更丰富了。傅先生指出的两个方向,可以说是都开始实现了”。(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24页。)
(三)关于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观点。废文言、兴白话的白话文运动兴起之后,表现文言的中国汉字的存废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虽然新文化论者一般地赞成废汉字而行用拼音文化,但如何具体处理,陈独秀、胡适等自认为是:言语学的门外汉,不配说话了”(注:《答<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46页。)。因此能够系统论述汉字拼音化问题的,只有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
文字是语言的工具和载体,傅斯年首先从工具应力求简便的角度分析了“汉字当废”的道理。中国的文字,字数虽少,却是个个独立,所以学习中国汉字,只能一个个去记忆、去掌握,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难识的词汇,因而应当废除而行用拼音文字。但同时傅斯年又极力反对当时许多人主张的引进外国语作中国的语言。这样他便把全力注重在汉语上,替汉语造一个拼音文字。他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汉语虽是单节,却不是纯粹单音了,这样就可以“拿词(word)做单位,不拿字(charactor)或音(syllable)做单位”(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傅孟真先生集》第一册“论学类”。)。汉字里可以废除单音,拼音文字施行的困难就去了一大半。
在阐述了汉语应当而且可能改用拼音文字之后,他又就制作拼音文字的基本规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第一是字母选用问题,因为罗马字母在世界上影响最大,傅斯年主张选用罗马字母。但中国汉语的声韵比罗马音多,罗马字母是不够代表汉音的,对罗马字母还须加以变通,不能照搬,由此他提出了具体制作的几条原则。第二是字音选定问题,拼音文字应该选用“蓝青官话”的字音,因为它已经占了统一的国语的地位。第三是文字结构的题,这是制作拼音文字的重点和难点,傅斯年就此提出了几项原则:①在具体和抽象名词、形容词、代名词、动词、位词、介词、感叹词中,凡一个以上的汉字,联合起来作为一个词时,拼音文字即认为是一字;②数词的离合在德文里有固定的规律,但没有限定的次数,傅斯年认为应当仿效德文,无论若干数词,只是表明一个数,都应当连接成一字;③汲取英语的经验,一切的语首根(prefix)和语后根(suffix)皆不独立;④力避单音字,努力多造二音以上的字。
语言和文字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最基本特征,具有长期的稳定性。随着一个民族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它的衍变只能是一个漫长而自然的过程。而新文化运动中汉字拼音化的主旨,却是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将汉字改成拼音文字,作根本、彻底的改造,这自然是不现实的。汉字拼音化以后,单音虽然很少,但仍然是存在的,而且独立的单音中有许多同音字,如何在拼音文字中分别呢?傅斯年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认为应当“制造若干辨别用的符号”,这些符号,“就性质上论来,差不多可以说是汉字的遗迹(survival)”。这样他的汉字拼音化方案下制造出来的拼音文字,竟可以说是“三分不像的拼音文字”,傅斯年亦感到了这一点,但他已无能为力了。这种无可奈何实际上已昭示了汉字拼音化运动的失败。十六年后,胡适对此还表示了遗憾,他指出:“在文学革命的初期提出的那些个别的问题之中,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得着充分的注意,也没有多大的进展,──那就是废汉字改用音标文字的问题(看钱玄同先生《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和傅斯年先生的《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两篇)。我在上文已说过,拼音文字只可以拼活的白话,不能拼古文;在那个古文学权威没有丝毫动摇的时代,大家看不起白话,更没有用拼音文字的决心,所以音标文字的运动不会有成功的希望。”(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32页。)
但遗憾本身即是对这一主张的最大肯定。虽然傅斯年的汉语拼音化方案并没有实现,但提出的问题却是客观的,汉字的难学,难识,难记,早已引起许多人的注意。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汉字拼音化将是必然的趋势。当中国文学革命的这一问题取得突破时,傅斯年的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没。
(四)关于白话文学与心理改革相联系的观点。“五四”时期,我国正处于急剧变化的大动荡时代,新思潮如汹涌的波涛冲击着文化思想界,出现了我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的思想大解放。要表现新思想,反映新时代,歌颂新生活,那些陈旧的僵死的文言、八股、骈体格律等形式,已经成了严重的桎梏,不彻底打破旧形式,不仅影响着新文学运动的开展,而且阻碍着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虽然胡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的发难宣言中都曾触及到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两方面的革新问题,但新文学运动中最先受关注和关心的还是语言的形式问题,所以便有了从“文的形式”入手进行文学革命的白话文运动,这是符合五四新文学运动特定历史条件的。傅斯年前期所关心的,也还主要是文学的语言形式的革新,如文言合一问题,做白话文问题,汉语拼音化问题,无不是强调语言形式的改革。但是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在文学革命中也出现了一种片面热衷于语言形式改革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思想内容革命的偏向。这引起了傅斯年的关注和忧虑:“觉得这白话文学的主义,不久定要风行,然而这白话文学主义的真价值,或者为着速效弄糟了,──这真可虑的很”(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傅孟真先生集》第一册“论学类”(本部分未注引文均出此)。)。1919年3月,周作人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思想革命》一文,对文学的内容革命与形式变革的相互关系,作出了具体的论述,明确指出:“文学革命上,文学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注:《思想革命》,《每周评论》第11号)。傅斯年受这篇文章的感动与启发而发表了《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全面阐发了他对文学革命中应当重视内容改革的观点。
首先傅斯年对周作人关于文学革命中思想改革的意见表示赞同。他认为真的白话文学,应该用白话作材料、有精工的技术和公正的主义,其中尤其强调思想内容的重要性。原因在于中国人普遍缺乏对人生的觉悟,大都醉生梦死,结果就是中国人的思想,虽经形式上的无数变化,但骨了里本质的内容依然如故,“用曾子曰‘每日三省吾身’做题目去作八股,和用‘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做题目去作八股是一种性格的两面”,仍然超不过“高为讲章白话文”的境界。因此,思想的革命在白话文学建设中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傅孟真先生集》第一册“论学类”(本部分未注引文均出此)。)思想之外,还有感情。思想的革命之外,还有感情的发展。思想是一种理性认识,是认识的最后阶段,因而力量比较的薄弱,因为无论在历史在现实中,“思想尽管高明,文章尽管卑劣”的例子比比皆是。而感情是一种感性认识,处于认识的初级阶段,因而对人的刺激力量比较强。他认为伟大文学作品的问世,有赖于中国人深沉挚爱的感情的投入。由此他觉得在文学革命中,单说思想革命,似乎不如说感情与思想的心理改革全面些。看到了感情在文学革命中产生革命文学的巨大创造力量,这是傅斯年的过人之处。
傅斯年不仅看到了感情在文学革命中的作用,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了感情具有巨大的社会作用,从而将文学革命提高到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他指出,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中华民国,之所以在政治上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方,就是因为政体变了,而人们的思想未变,所以才有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思想革命”的萌芽。但思想革命的成功,仅靠思想启蒙和理论宣传是不够的,还“必须以新思想夹在新文学里,刺激大家,感动大家,因而使大家恍然大悟了;徒使大家理解是枉然的,必须唤起大家的感情;徒用言语晓喻是无甚效力的,必须用文学的感动力。”所以傅斯年的结论便是:“真正的中华民国必须建设在新思想的上面,新思想必须放在新文学里面”,从而“未来的中华民国的长成,得靠着文学革命的培养”。将文学革命视为创造新政治和国民性改造的唯一主要手段,这无疑过分地夸大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作用提高到了一个不适当的地位,自然是不正确和唯心主义的。但在五四“物质的革命失败了,政治的革命失败了,现在有思想革命的萌芽了”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思想革命对新文学发出了强烈的呼唤,要求新文学为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鸣锣开道,摇旗呐喊,这是时代赋予新文学重任,也是五四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作为“现代型”新文学的特征之一。傅斯年清楚地认识到了五四新文学在思想革命时代的独特历史作用,将它与解放人性,启封建之蒙,唤醒人的觉悟,肯定人的价值,从而使中华民族觉醒起来,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联系起来,这无疑又是值得肯定和富有远见的。
(五)关于戏剧革命中新剧主义的观点。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中国文字繁难,学界不兴,下流社会,能识字阅报者,千不获一”(注:《论开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戏本为先》(箸夫著),转引自《中国五四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586页。)。教育不能普及,传统戏剧(指京剧、昆曲和各种地方戏曲)便以其通俗和活泼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担负了教化的功能。要在思想革命中改变人们的传统思想,就要首先改善担任教育功能的传统戏剧。所以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戏剧革命作为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一个方面军也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引起了社会上越来越多人的关注。1918年6月《新青年》在胡适的主持下,出版了“易卜生专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傅斯年的《戏剧改良各面观》和《再论戏剧改良》等多篇文章,此后周作人、钱玄同《论中国旧戏之应废》的通信也在下一期刊出。这些文章和通信,形成了戏剧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傅斯年在文章中,首先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系统论述了旧戏当废的道理。从内容上看,戏剧是人类精神的体现,因而应是“近人情”的,而旧戏却“全以不近人情为贵”,它所体现的不过是玩“百纳体”把戏的精神(注:《戏剧改良各面观》,《傅孟真先生集》第一册“论学类”。)。这是因为旧戏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而中国的历史社会,按照傅斯年的看法,“自从秦政到了现在,直可缩短成一天看。人物是独夫、宦官、宫妾、权臣、奸雄、谋士、佞幸;事迹是篡位、争国、割据、吞并、宴乐、流离”(注:《再论戏剧改良》,《傅孟真先生集》第一册“论学类”。),戏剧的内容便是这两样东西的写照。因此作为旧社会教育机关的旧戏不能不推翻,新戏作为新社会的急先锋便不能不创造。从旧戏的形式看,无论它的唱工、声音、服饰及意态动作和音乐,都毫无美学价值可言;就戏文而论,傅斯年认为从词句、结构和体裁三方面看,也难入文学之列。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傅斯年都认为旧戏一无可取,应在否定之列。因而他主张戏剧革命,反对戏剧改良。
傅斯年主张戏剧革命,要求创造新剧,但他不同意胡适赶快翻译西洋剧作为新话剧的意见。因为西洋剧本是以西方社会为背景的,中西社会区别极大,中国人不一定能够理解与欣赏西洋剧。因此应该主要取它的精神,弄来和中国的人情、国情相合,“直译的剧本,不能适用,变化的形式,存留精神的改造本,却是大好。”(注:《戏剧改良各面观》,《傅孟真先生集》第一册“论学类”。)这种“拿来主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戏剧革命中对待西方文化的形而上学倾向。新剧的创造,关键是编制新剧本,为此他提出了六条具体原则:①剧本的材料,应当在现实社会里寻找,断不可再做历史剧;②注重悲剧的作用,反对中国旧剧结尾大团圆的通病;③剧本的事迹,应当是日常生活;④剧本的人物,须是平凡人,反对旧戏里多为王侯将相、才子佳人;⑤剧本的观点,善恶分明的说教性不能太强,注意艺术性;⑥编剧要注意思想性。这些积极的创作理论,实际上为新话剧的编写提出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特别触及到剧中人物的典型化、主题思想的含蓄深蕴等重要问题,比胡适的主张更富有建设性意义。
三
傅斯年不仅是文学革命的热心倡导者,也是积极的实践者。自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了真正显示文学实绩并为新文学发展奠定坚实基石的白语小说《狂人日记》以后,白话文的各种题材大都得到了社会不同程度的承认。唯独白话新诗,遭到了最多的异议。这一方面是由于诗的体裁、格式的独特;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旧体诗的高度发达(诗歌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因而人们对用白话能否写出比旧体诗更好的诗来表示怀疑。如果攻不下这座“诗的壁垒”,所有新文学的理论就不能算是完全正确的,白话文运动也不能算是成功了。所以,尽管傅斯年擅长的是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但还是拿起笔,“要作先锋去试作白话诗。”(注:胡适著:《逼上梁山》,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1919年上半年,傅斯年陆续发表了八首白话新体诗,按照他自己的诗歌分类法,八首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与山遇”的诗,计有《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老头子和小孩子》、《咱们一伙儿》、《阴历九月十五日夜登东昌城》。这类诗象工笔画,寥寥数笔就勾划出一个静谧、旷远的大自然之美意境。但因为纯粹写景,没有多少思想内容。后来他自己都有悔意,觉得应该多创作另一类“人与人遇”的诗,这包括《前倨后恭》、《心悸》、《心不悸了》、《自然》四首。这类诗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或者揭露黑暗丑恶的社会现实,呼唤独立人格精神,或者表现个人在社会大潮中的追求与彷徨的思想感情。这类诗虽然有较强的思想性,却显得直白浅露,艺术性不高,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新诗的创作流行色和通病。尽管傅斯年的白话新诗带着初创时的种种痕迹,但是毕竟是有意识地进行诗体解放的尝试,在破除旧诗词的声韵、格律、骈偶、典故等凝固化的旧体式的束缚方面做出了一定努力。他以白话语言为利器,采取自由新体,表现新的思想感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精神,透露出或浓或淡的新的生活气息。
四
在北大学生中,傅斯年不但第一个公开发表文章响应五四新文学运动,而且从1918年1月到10月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陆续在《新青年》上刊出《文学革新申议》、《文学合一草议》、《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戏剧改良各面观》、《再论戏剧改良》这五篇都很有份量的万字长文,以其突出的文学理论建设,大大壮了新文学运动的声威。傅斯年的才华,不仅得到了胡适的赏识,而且得到了《新青年》其他同仁的重视。1918年10月,《新青年》编委会决定吸收傅斯年参加明年的分期编辑工作,这是《新青年》编辑部里唯一的一名学生,也是最为年轻的。傅斯年能够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兄弟等共同轮流编辑《新青年》,充分说明了傅斯年已跻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行列中,成长为一名思想成熟,能够独当一面的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先锋。[按:1919年《新青年》原定出十二期,后因五四运动发生而未果(只出了六期),所以傅斯年极有可能未独立编辑《新青年》,但他成为编辑部成员,参与编辑了《新青年》,当无疑议。可参见《陈独秀年谱》第92页附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