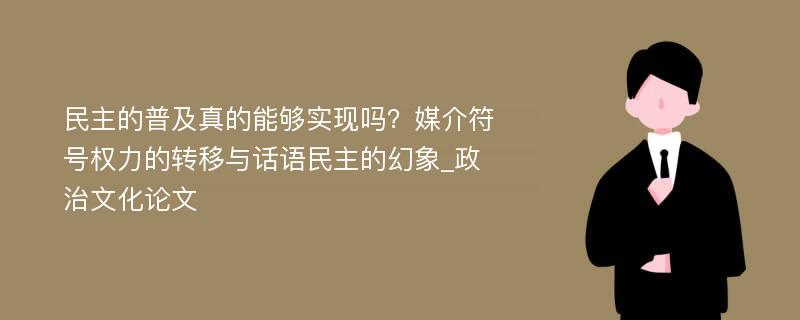
传播民主真的能够实现吗?——媒介象征性权力的转移与话语民主的幻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幻象论文,象征性论文,媒介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象征性权力的涵义及表现形式
权力有许多种形式。在制度化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强制权力之外,约翰·B.汤普森还特别提出一种象征性权力。即“运用象征性形式干预事件进程的能力,影响他人行为而创造事件的能力,采用的手段是象征性形式的生产和传播”①。在这里,象征性形式主要指通过印刷、照片、电影、视听或数码等技术复制和传递的人类交际的内容。
汤普森认为,“日常生活中,人人都可以创造性地利用象征性权力,帮助个人和群体应付、适应、创造和改变经济政治力量和强迫性影响所构成的环境。”②但事实上,在制度化的力量作用下,媒介组织及其产品因此成为象征性权力的持有者,并为社会政治经济精英的利益服务。象征性权力成为一种媒介权力。在今天这种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的时代,象征性权力因此也具有了民主意义而备受关注。
在日常生活中,象征性权力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1.口号、标语
口号、标语言简意赅,简短有力,好读易记,是政党、组织或个人宣传其观点主张的有力工具。因而,口号标语也成为反映意识形态和权力意志最为明显的文本。布尔迪厄认为,“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形的方式表现出来。”言语行为涉及到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种权威的受众之间的权力关系。所以,我们常常看见暴力和强制色彩在标语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彰显了执法者的权威和力量。
中国是一个标语大国。日常生活中,街道、公园、机关、广场、社区等各个地方随处可以看见标语,在一些集会、庆典等仪式性场合也常常会打着标语、呼喊口号。标语口号作为一种反映时代变迁的语言,反映了一种赋予的权力关系,体现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对语言的控制和干预权力,因而也被称为“时代的标签”。标语口号体现的是一种话语权。廖广莉从语言角度对暴力标语口号进行评价,对其背后所包含的权力意识和社会环境进行了分析。指出标语口号作为一种语言手段并不具有权力和暴力,但是它反映了一种社会规约和政治规约,体现了口号标语发布者的权威和对受众的威慑力,体现了执政者的话语强势和支配控制力量。③
2.新闻联播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新闻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独立。它总是要受到权力有形或是无形的操控。它所发出的声音,其背后的机制都是“权力在发言”。在电视控制机制上,布尔迪厄提出“新闻场”的概念。他认为所有的文化生产场都受制于新闻场的结构,而不是受制于某个记者或是电视台的台长。这一控制力在所有场中都施加着极为相似的系统影响。
借鉴这种思路来分析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栏目,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新闻联播》可能是目前中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栏目。作为最能凸显中国意识形态和民族精神的新闻栏目,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国家权威和政治秩序的象征,成为“国家的代码”④。而在其具体运作过程中,由于“‘集体记者’和‘全国联播’制度的建立,不但使新闻联播占据国内电视新闻节目中的核心地位,连同它庄严大气、权威严肃的‘联播’风格已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言人,而它上情下达的‘喉舌’角色和及时准确的信息播报也成为国家政治秩序的重要象征。”⑤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化仪式,《新闻联播》在建构国家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国家象征的《新闻联播》已深深地介入到现代普通人的生活中,而它的意义亦超越了任何意识形态和再现所扮演的角色。它最重要的作用是将一套思想体系、一种价值观、一种行为方式、一种对国家的热爱、一种对执政党的信任,通过每天看电视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植入到每个中国人心中。”⑥《新闻联播》作为一项重要的电视仪式镶嵌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其政治生活和民族认同的重要内容,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新闻联播》已经成为一项“国家的仪式”(张兵娟语)。通过新闻共同体的建构,《新闻联播》完成了对国家与民族等“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它“构成了一个民族国家认同、意义、合法性、信心、权力和希望的来源”⑦。它的语言风格、播报形式、新闻组合方式乃至主持人的装扮都是以国家的面貌出现的,旨在树立一种庄严、权威的国家形象,确立一种权威秩序,“使现存的政治秩序和权力关系合法化”。《新闻联播》因而成为中国最典型的政治符号与权力象征。
3.报纸社论、头条新闻、专题报道及新闻出版
新闻是一种特殊的叙事。它迥然有别于日常谈话、文字读物和神话故事。报纸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类型,其社论、头条新闻、专题报道及各种专栏,都是为了界定和建构外部世界并使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合法化。他们演绎、辩解、解释、证明当下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为之提供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证明和辩护。根据梵迪克关于“新闻图式”(即报纸新闻的常规形式和常规范畴)的理论,新闻记者在新闻收集、新闻写作和读者在运用已有认知重新建构新闻事实的过程中,新闻价值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使新闻话语的生产完全成为一种社会性实践,更成为一个建构意义和权力的过程。正如塔尔德所言,“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想象,报纸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个人的谈话,既使之丰富多样,又抹平其差异,使人们的谈话在空间上整合、在时间上多样化;即使不读报但和读报者的交谈的人也会受到影响,也不得不追随他们借用的思想,一支笔足以启动上百万的舌头交谈。”⑧新闻报道扩大了公众参与政治的范围、规模和质量,放大了社会事务的影响,使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原子化生存”的个人感受到团结和集体的认同,重新凝聚为一个社会整体。权力在这种体认和认同的过程中产生和实现,并在社会网络中进行传递。政治精英和民众的权力博弈也在此基础上展开。罗森布拉姆曾经这样描述新闻话语的力量:不论国外大事,还是国内事务,如果没有充分知情的选民,民主制度难以奏效,外交政策不可能不由华盛顿的精英、专家或利益攸关的院外活动集团进行最后拍板。如果能够及时预见,某些世界政治危机就完全可以避免。但如果没有可靠的国外报道,公民将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即便众多的美国人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只要有了记者和编辑们——纽约人的疯子——就能够使他们确信这一点。⑨在中国,新闻话语更多的是强调国家和政府的权威。公共权力具体体现为政治权力,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
报纸的社会作用之一是实现社会整合。报纸语言及其所承载和体现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和道德理想趋于统一,使个人、民族、国家之间连接为一个整体。但是,语言也成为社会分化和民族分隔的界线。一方面,报纸语言的使用和理解,使得庄重、雅致的书面语和日常对话所使用的口头语截然有别,造成了经常读报的社会上层精英和几乎不读书看报的社会底层人群的阶层分化。尤其是中国报纸的行政级别,也在读者中造成了阶层和身份的差别。看一个人经常读什么报纸,看什么电视节目,就能大致判断出他的社会身份。新闻也因之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报纸新闻也正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划定界线和挑起争端。语言的同化和净化之争,往小了说是民族文化之争,往大里说就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相连。“在有些国家里,语言之争和民族之争是一回事。其原因是,新闻业使民族感情复活;报纸真正有效的影响,止步在报纸使用的语言的边界线上。”⑩多语言的新闻出版事业与其说是一种文化政策,倒不如说是出于某种政治策略。
4.现场直播
早期的电视直播强调提供事实,但在重大报道中,电视直播不仅要提供事实,更像是一种媒介仪式。电视直播的优势在于“现场感”、“真实性”,但是已有许多研究者指出现场直播并不等于事件/真实本身。“‘现场’往往是经过精心挑选、加工、组织和编排,再通过电视镜头传递给观众,即便有记者声称自己的摄像机式是完全随意的,‘镜头’所展现的也只是实践的某一个部分。”(11)也即是说,所谓“事实”背后其实隐含着各种权力话语。正是种种权力话语决定了“事实”的呈现方式(12)。
电视新闻的一大优势,就是再现现场。这也是构成其真实性的重要基石。但是镜头下的现场,只能是一种“想象的现场”。即使是对于那些突发性事件的报道,我们看到所有的媒体一拥而上,似乎都在宣称自己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可是根据实际报道的情况来看,这种“现场”都是不完整的,而且呈现高度的同质化;另外在报道立场上也毫无例外地表现出“主流化”的倾向。以汶川地震为例,从报道来看,最先到达震中地区,在现场观察和报道灾情的媒体就是搭乘温家宝总理专机到场的中央电视台记者了。实事求是地讲,中央电视台在汶川地震中的报道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国外媒体同行中也获得了肯定和好评。摄像机的镜头拍下了北川、映秀、什邡、都江堰等受灾最为惨重的几个震区的场景,残垣断壁,瓦砾遍地,灾民沉痛的面孔,时时袭来的余震等等,使每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心灵上受到极大震撼。但是,即使尽可能详尽的报道仍然有无法克服的弱点,即现场的“碎片化”和“同质化”。
在布尔迪厄对电视新闻的祛魅分析中,他就深刻地指出,电视新闻“以显而隐”的操作原则对于电视民主及新闻真实性实际上是一种戕害。“如本该属于其职责范围的事,亦即提供信息,展现的东西,电视却不展现,或者虽然展现了本该展现的东西,但其采用的方法却是展而不示,让其变得微不足道,或者重新加以组合编造,使其具有与现实毫不相符的意义。”(13)究其原因,他认为是“记者们有着特殊的‘眼镜’,他们运用这些眼镜看见某些东西,但对某些东西却视而不见;同时又以某种方式,见他们所见的东西。他们进行某种选择,并对所选择的进行建构”(14)。那么由此可以推知,依据这种原则,经过这种选择而“组装”、建构出来的现实,离真实其实有着不小的距离。在现场直播中,新闻价值其实只是无关紧要,或者是不那么重要的一个因素,权力关系的考量决定了新闻呈现的面貌、顺序和重要程度。
电视新闻,尤其是电视直播还具有一种仪式功能。尤其是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中,电视直播建构了一种观众参与的媒介仪式。“媒介仪式是指广大电视观众通过电视媒介符号的传播,被邀请参与到某些重要显著的共同性活动或者某些盛大事件,最终呈现的一种象征性和表演性的文化实践过程和行为。”(15)电视直播对媒介仪式的呈现,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塑造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于是,个体通过参与这项仪式,其身份归属和情感归属得到确认,作为单独的个体被整合到集体之中。
5.广告
广告日渐侵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操控了我们的观念和知识体系。广告中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商业利益和经济权力的隐晦表现。它所使用的方式,就是通过重新建构知识话语,并以真理的方式占据人们的头脑,从而置换或改变人们的原有认知。广告体现的不仅仅是经济话语,还有政治话语、文化话语和性别话语。话语体现并展示了权力。我们从形形色色的广告中,可以看到不同品牌的同一种商品,出于竞争的目的夸大自身功效,诋毁对手产品,于是各种说法离奇夸张而又自相矛盾,有些说法甚至是违背常识。在这里,经济利益操纵了知识表达,知识是可以随意建构和改写的,即使违背常识也在所不惜。假国医、假大师张悟本的绿豆养生学说,在全国掀起了茄子、绿豆热,并成为导致绿豆价格暴涨的幕后推手。民众在这种满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广告以及讲座形式的营销中一次次受到愚弄和欺骗。
广告中的政治话语主要体现在公益广告和一些特定的广告事件中。如为下岗工人所作的广告,明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利益被剥夺者,承担了巨大的改革成本,生活遭遇了巨大的不幸。但是在这则广告中,却被轻描淡写为个人生活中的一个小小挫折,“只不过是重头再来”,导致个人不幸的社会原因被完全掩盖了,相反是要求个人对其负责并采取实际行动。无可否认,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但改革的设计初衷本是按照帕累托改进的原则,使更多的人从改革中受益。中国现在远远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而在社会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却不断扩大,这一群体恰恰是被认为是社会基石的普通民众。在中国,社会底层的范围大大扩大了,他们有一个特定的称谓——社会弱势群体。作为无权无势的人群,他们应该是最需要关爱的群体,但是我们在广告中却难觅其身影。而所谓精英人士、成功人士和上流社会的形象却比比皆是。作为商业利益的代表,广告无疑是势利的,但社会如果也变得势利就是国家的悲哀了。权力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化会加深社会分离的趋势。人们应该对这种趋势引起警惕。
关于广告中所体现的文化资源和性别权力失衡的现象,相关的论述很多,在此不再赘述。
二、象征性权力的生产和传递
1.象征性权力与话语权力
与权力的物质载体如警察、军队、法院、监狱等不同的是,象征性权力体现的是一种思想权力,一种观念的权力。与福柯所谓的微观权力相类似。在福柯那里,权力与话语相连。通过建构知识和话语,并通过对知识及话语的真理化,使之获得了权力。象征性权力的载体即媒介产品,其内涵往往涉及意义的生产。由于这种意义往往又影响到社会的价值认同和权力的构成,因此,话语也常常被视作一种权力,并具备建构社会的能力。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话语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世界的意义。如此一来,媒介话语建构和传递的过程也影响并再现了社会权力建构和传递的进程。
2.象征性权力的转移与话语传递(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
象征性权力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强化社会结构,塑造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方式。但另一方面,象征性权力也可以被用来发动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战争,对抗权力集团。象征性权力具有流动性和扩张性,因而它能够在不同阶层和社会组织间发生转移,并因此而改变传统的社会权力形式,并形成新的文化景观。
在中国,象征性权力的转移可以大致勾勒出如下路径:国家控制——媒介控制——大众参与(电子政务、电子民主、电子动员等)。以下详述之。
改革开放前中国大致上属于“总体性社会”(16),在社会资源上体现为高度集权化,媒介组织只是社会主义政权组织中的一个部门,一个螺丝钉,一个宣传和动员机器而已。市场化改革启动后,大势所趋,传媒业也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有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国家—社会二元分立的社会格局逐渐形成,社会的力量开始壮大,媒介在整合社会意识、建构社会公共领域、推动社会民主发展等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媒介在传递信息、进行大众教育、开展舆论监督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甚至被寄望于成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国家领导人也公开阐明,舆论导向与人民利益祸福相依。上至政府,下至百姓,“有事找媒体”,呼吁重视“媒治”。大众媒介在施加象征性权力方面既具有了权威性又俨然具备了合理性。
市场化时代,出于影响力和商业利益的考虑,讲求收视率为王,发行至上,受众的地位大大提高。媒介对于受众市场的调查与反馈极为重视。同时为吸引大众参与,媒介也逐渐向大众开放。民生新闻、方言新闻、平民选秀、大众相亲和真人秀节目纷纷走红。而网络更是为平民大众提供了畅所欲言、表情达意的平台,网络舆论群情涌动,在某些事件当中甚至左右和改变了决策者的态度,这些事件被归结为“民意的胜利”。如“周老虎”案的水落石出,厦门PX事件尘埃落定等等。而政府对此的态度也逐渐松动。于是我们看到,既有汹涌高涨的网民“网络论政”的热情,又有政府纡尊降贵、“网络问计”的谦恭姿态,这似乎成为中国民主进步的标志。从其言论开放自由的进步性而言,数量众多的网民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公共领域的再造和书写。这似乎也回归了象征性权力的本来涵义,即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象征性权力的使用者和创造者。
对于目下中国的网络政治和网络民主,杜骏飞认为其拓宽了中国政治民主的空间,提供了政治与社会治理的新理念。“以政府上网为标志展开的电子政务、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选民沟通为标志展开的电子民主、以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开展社会运动为标志展开的电子动员,等等,都是互联网的政治应用中出现的形式,丰富了转型中国的媒介形式和传播方式,为各种社会力量提供了新的参与渠道和博弈空间。”(17)“网络问政”、“网络监督”、“政府发言人”等变化给中国的政治生态和舆论生态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这是对于全能政府的政治治理模式的反拨与调整。尽管这种制度设计的变化带有被动色彩,但是毕竟也是一种民主的进步。
三、话语民主的幻象
正如狂欢过后,一切都要重新归入日常生活,接受既有秩序的评判和审视。当我们在欢呼网络赋予我们表达自由和平等话语后,也不无遗憾地发现,网络的优点并不较之其负面影响为多。时下为人所诟病的网络暴力,如话语暴力、网络审判、人肉搜索、煽动和教唆、信息欺诈和广告垃圾等等,也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烦恼。虚假消息、情绪化、非理性、网络色情、网络犯罪、信息泛滥、隐私和名誉侵害等被列为网络的“七宗罪”。面对这些失控的问题,网络民主面临更加严峻的拷问。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公众的力量是可怕的,他们可以推动社会和政治进步,但是公众的狂热有时也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公众反过来影响起初煽动他们、现在却不能控制他们的人,他们召唤评论员惟命是从的疯狂,评论员笔端流出的是疯狂,是滚滚而来的抒情或诅咒、奉承或诋毁、乌托邦错乱或血腥的疯狂——评论员是昔日的主子,如今却成为惟命是从的奴隶。”(18)当遭遇网络民族主义猖獗,网络暴力和网络舆论审判盛行时,我们不禁要问:网络时代的人民真的可以从此幸免不良的社会政治吗?
杜骏飞肯定了网络民主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也同样提出质疑——当这种互联网时代的群体力量是以数值优势呈现时,那些一边倒的网络舆论是否始终有统计学的谬误?如果没有,那么,有时的网络舆论是否可以作为政治或奢华理性的存在而受尊重?应该受多大程度的尊重?当它与国家意志抗衡时,我们的人类群体智性将如何选择、如何自处?(19)
面对这样尖锐和沉重的问题,恐怕我们是很难作答的。
即令是对于“媒介治理”、“媒介执政”这样的提法,我们也很难保持乐观。因为从根本上而言,它既不具备合法性基础,也缺乏合理性的依据。如陈力丹所指出的,媒体只是一类意见的载体,它不拥有以暴力作为背景的“权力”,仅仅通过反映舆论来体现它的社会功能。将媒介归入到权力体制,这是对媒介职能的误解,在实践上也做不到。它并不具有司法和行政的权力,也不具备司法和行政的效力。而超越自身权限和职能归属的媒介审判更是一种角色和功能的错位,应当是媒介力戒的。所以,媒治从根本上来说与当前倡导的依法治国的法治精神相违背的。即使是受到提倡的舆论监督,也只能成为社会监督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能真正成为一项社会治理技术。(20)
媒体的权力仅仅是一种象征性权力,不具备任何强制性,它仅仅是一种软性的、无形的权力,是从改变人的观念认识入手,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作为民主的表征内容,媒体的开放程度体现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民主水平。但是单纯的传播民主不可能独立存在,它只能是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有助于促进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但是也要警惕它可能造成的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分裂和混乱。塔尔德看到了这把双刃剑的危险一面:新近的民主制度造成的危险在于,善于思考的人要逃避混乱和执着越来越难了。(21)因此他发出严重的告诫:“知识分子要谨防各自为政、各奔东西的倾向啊!”(22)过往的经验也证明,过于自由放任的“大众民主”或许会在某种狂热的、非理性的感情驱使下成为放诞、专横、偏执和残暴的“乌合之众”,因为人多势众而产生的力量感,在某种情况下,“很容易干出最恶劣的勾当”(古斯塔夫·勒庞语)。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指出群众政治有走向独裁的危险。寄望于完全不受约束的“大众民主”,会从根本上铲除个人自由的基础,最终可能使其驯服权力的愿望完全落空。这也是我们看穿传播的民主幻象的一记沉重警钟。
小结
对于媒介象征性权力的意义和功能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媒介给社会带来的标示作用。当我们不只是在权力束缚、经济制约和技术掣肘中寻找答案的话,我们会发现,注重真相与舆论平衡的媒介话语的确立,会给媒介生存、民主发展以及社会政治生态带来怎样的意义。
注释:
①Thompson.J.B.The Media and Modernity,Cambridge,UK:Polity Pres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②[美]詹姆斯·罗尔著:《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董洪川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6页。
③廖广莉:《暴力标语口号的语言评价》,《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7期。
④详述参见徐敏:《国家的代码:论“新闻联播”》,载汪民安主编:《生产——新尼采主义》(第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5页。
⑤⑥⑦张兵娟:《国家的仪式——新闻联播的传播文化学解读》,《现代传播》,2010年第8期。
⑧⑩(18)(21)(22)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著,特里·N.克拉克主编:《传播与社会影响》,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226、227页。
⑨转引自[荷]托伊恩·A.梵·迪克著:《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1)(12)(15)曾一果:《媒介仪式与大众娱乐——关于现场直播的媒介分析》,《当代传播》,2010年第5期。
(13)(14)[法]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16)关于总体性社会的概念,参见社会学家孙立平著《断裂》中的相关论述。
(17)(19)杜骏飞:《网络政治中的问题与主义——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译序》,《当代传播》,2010年第3期。
(20)陈力丹:《质疑“媒治”》,《当代传播》,201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