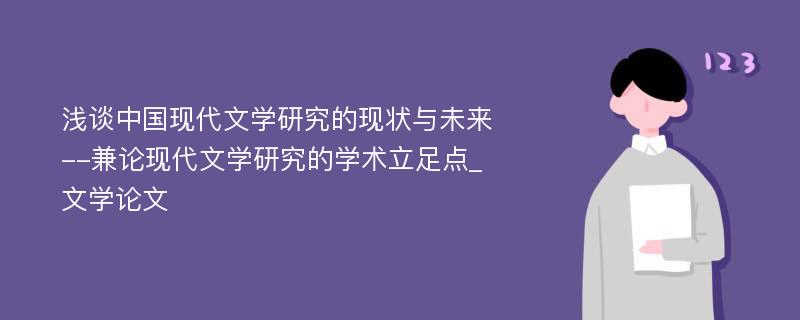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与前途笔谈——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立足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笔谈论文,立足点论文,中国论文,前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1996年5月9日至12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石家庄举行第七届理事会,河北师院中文系、河北师大中文系、河北大学中文系和河北省社科院文研所联合承办了这次会议,河北师院中文系承担了会议组织工作。来自全国的数十位著名学者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途进行了热烈研讨,有共识,有争鸣,新见迭出。本刊摘发几篇论文,以飨读者。
一个从事研究而不能寻找到学术立足点的人,是非常可悲的。因为学术立足点本身便包含着发现,既发现自己的研究个性、研究视野,又发现这种个性视野与时代的学术文化潮流的结合点。也就是说,学术立足点的寻找,乃是研究工作中的一种文化战略的选择。我们自然不必像西方某位科学家持有那么大的口气,宣称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搬动整个地球,但学术立足点或支点的确定,无疑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记得不久前,出版社要我编选一部《唐弢书话》,就给我出了一个小小的选择学术立足点的难题。由于唐先生生前已经以书话文体开拓者和学问家的身份,编集过《书话》和《晦庵书话》,如果不能发现我作为编选者的新的学术立足点,所作的就只能是一些徒劳无功的重复性劳动。寻找立足点的程序,第一步就是切切实实地返回到研究对象的本然状态。我不仅读了唐先生的书话集,而且通读了他的十卷文集和一些佚文,终于发现唐先生写书话,是读一本书写一篇的,而我却是把他的书话和类书话的文字作为一个整体透视的。一旦确定了“唐弢读书,我读唐弢”这个立足点,编选起来就势如破竹, 就能够从“品书会心”、“考镜源流”、“书坛掌故”、“序跋甘苦”、“装帧学问”和“书城纵横”六个层面,以“唐弢书话六境界说”来规划新的编选体制。加上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自文集其余部分,这使得已有《晦庵书话》的读者,还有购买这个学术选本的价值了。
以小窥大,尽管颇有些同行喟叹现代文学三十年,拥挤着三千研究和教学的人马,文学史也写过二百种,但只要能够发现一些具有文化战略价值的新的学术立足点,辅以返回研究对象之本然状态的功力,还是可以开拓出许多新鲜的学术空间的。我今天想强调的是,我们正面临着从实质意义上更新学术视野和立足点的重要历史契机,这将给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拓展出开阔的英雄用武之地。中国文学自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尤其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发生了具有历史阶段意义、或社会整体规模的转型,对外来文化和文学的输入,经过严复、林纾的拟古翻译,五四时期的直译,四五十年代的经典迻译, 以及近十几年的多元翻译和追踪最新思潮的翻译,已经走到了一个可以中西互参、择善而从、重新整合、立足创造的新的文化建设的门坎。如果借用哲学术语,把中国传统文化称为“正题”,五四文化称为“反题”,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合题”的历史阶段。“合题”既是对“正题”、“反题”的超越,又是对“正题”、“反题”智慧的集大成。它将为我们提供新的学术立足点,使我们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文化台阶上,增强对现代文学进行历史理性审视的科学性,使整个学科形成博大精深的气象。
现代文学以五四为发端,形成了反传统的文化思维定势。它引入西方自文艺复兴到20世纪的文化和文学思潮,冲击民族文化数千年的沉积,使中国文学出现了转换格局、革新文体和重铸气质的生机。陈独秀宣布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胡适揭起白话文运动的旗帜,鲁迅等人开创了新文学的形态,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新文学世纪的有声有色的开端。这是中国文学转向现代发展进程的必不可免的一步,但是当我们站在文化“合题”的新的立足点上重新审视它的时候,其间的正偏是非、成败得失和盛衰荣辱,是可以再度分析和商量的,并非都是可以垂训百世的文化宝典。
能够再度分析、比较和商量,既说明了研究对象的丰富性,也说明了研究主体的成熟和博大。处在20世纪末叶的这一代学者不比五四那代人愚蠢,也许有些地方还要高明。这倒不是要比历史地位,那是存在着许多不可比因素的;也不是比读书多少,有些他们读过的书我们没有读,有些我们读过的书他们岂都读了?这主要指的是我们和他们之间存在着80年的历史时间距离,他们当年提出的一些文化和文学主张的是非得失已在80 年间受到历史的严峻的检验, 我们拥有了他们不可能拥有的80年的历史教训。这一点比任何东西都更有说服力地使我们变得聪明,使我们作为新的历史主体和他们进行心灵对话,从而形成“继承五四”和“走出五四”的双构性思维。比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在20年代曾经产生过轰动效应,被视为一时思想学术的典范。但是他如果拿前者参加今日的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委员肯定会提出不少实质性的质疑。后者把李白、杜甫诗称为白话文学,论杜甫只及《北征》、《羌村》、“三吏三别”而排斥其律诗,这样的杜甫是要大打折扣的。至于可以推崇“老妪能解”的白居易,不能读解扑朔迷离的李商隐,就更暴露了他以文白标准判断文学之死活的偏离文学本质的缺陷了。
此外可议之处尚多。比如胡适在古典小说的历史考证,尤其是《红楼梦》作者身世考证上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开创了“新红学派”。但他把《红楼梦》视为作者自传,实际上未能跳出晚清人把小说当作政治书(如蔡元培),五四人把小说当作自传书的局限。《红楼梦》既是“人书”、又是“天书”的复合审美品格,使它的作者即便以“自传”始,终归要以“反自传”终。如果他始终固守自传家数,写出来的充其量也只能是《浮生六记》一类作品。固守这种自传说,胡适晚年就抓住太虚幻境和公子衔玉而生这些反自传、非写实之处,说《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不及《儒林外史》和《海上花列传》了。在《红楼梦》的文本意义研究上,胡适也许不及他的反对派吴宓以“并非一切文学都是自传性质”的尺度,“比较曹雪芹之假贾真甄及太虚幻境之义解”来得高明,尽管吴宓的学者生涯远比胡适寂寞。这些分析并不说明我们在《红楼梦》研究上的贡献比胡适大,但由于我把学术立足点定位在文化“合题”之上,就可以改变当时人的“追星心态”,还文学史研究以科学性的原本。依此类推,是可以使我们的学科建设趋于博大精深的。
我不无感慨:20世纪世界文学思潮发展的一大遗憾,在于具有数千年历史,因此堪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智慧,未能以平等姿态参与前沿思潮的对话和创造,致使多元共构的世界文化张力未能充分发挥,而前锋思潮趋于偏执与乖戾。其间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品格。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并非没有民族文化“寻根”的倾向。比如新文学运动开始不久,即有“整理国故”主张的提出,胡适以白话、文言定优劣的尺子权衡古今,认为白话文学运动是禅门语录、理学语录、白话诗词曲子、白话小说的复兴;周作人以言志、载道当尺子来衡量文学史思潮,把现代文学看作晚明公安派一类文学在新历史条件下的重演;梁实秋则以人性为尺子,扬弃文学进化论,把孔门伦理和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庸视为楷模。此类议论虽然各有建树,但都羁于“我执”,未能原原本本地返回中国文化的原点,都这样或那样地偏离中国文学的本原。因而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化的充分深刻的现代化阐释和转化,还是一个未了的历史命题。
那么是否应该走向“新儒家”?“新儒家”的名目是偏离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诸子百家文化,是儒佛道交融互补,民间文化和文人文化、中原文化和边地文化多轨并进的文化系统。儒术独尊所形成的“中心——边缘”文化结构,对中国人丰富多彩的、包括科学技术方面的智慧的箝制和压抑功能,难道还有必要重复吗?不是出自现代文学学者的偏爱,而是出自现代文化意识,我们不能不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了“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古老法则,为中国文化的新生、也为我们科学地认识孔子的伟大,提供了真正的历史契机。在文化合题的学术立足点上,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相适应,我们的学科将形成双构性的文化思维:对外来文化实行平等的更高程度的开放,对民族传统文化实行充分的更深层面的现代化转化,从而使我们的学科在现代意识和民族特色上都取得新的进展。
由于我们选择了新的学术立足点,在学科研究上,我们便拥有一个新的学术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