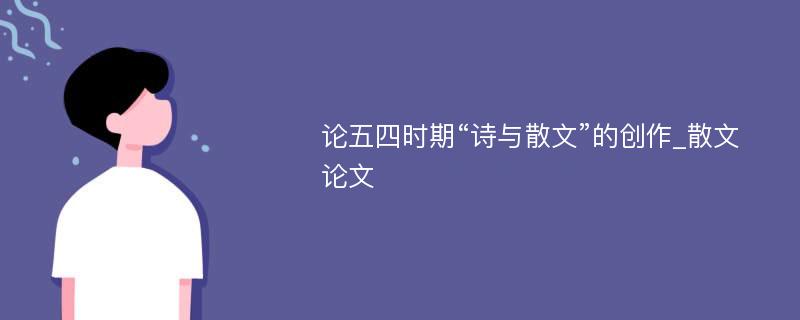
论“五四”时期“诗散文”的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时期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诗的散文”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看来,散文使用白话是古已有之,韵文使用白话则需重新创造。以胡适为代表对新诗的语言进行了最初的“白话”的“尝试”,力图用精炼的语言与分行的形式完成诗与散文的分离。但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第一、在当时“作诗如作文”、“作文如说话”的文学观念的影响下,许多诗作的语言徘徊在诗与散文之间,形成散文与诗歌语言的交融;第二、由于缺乏“白话诗”的借鉴,作者对诗歌的形式因素知之甚少,多数作品的分行实属不必要,只是徒具诗歌表面的形式,而未摆脱散文语言的束缚。所以,新文化运动初期的许多白话诗,实为“诗的散文”的雏型。
“诗的散文”指那些具有诗的内核(“情绪”与“想象”),篇幅较长(比之于诗歌),不分行的无韵律的文章。1922年1月,郑振铎在总结新文化运动初期的“诗散文”创作后,指出:“有一种论文或叙述文,偶然带了些诗意,我们就称它做‘诗的散文’。”①1932年,冰心在她的《全集·自序》中也说:“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连带着说一说《繁星》、《春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后来,她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一文里,谈到印度诗人泰戈尔将他的孟加拉文的诗歌译成英文的时候,“如要保存诗的内容就不采取诗的分行的有韵律的形式,而译成‘诗的散文’。”可见,郑振铎与冰心的看法是一致的,“诗的散文”即指那些富有诗意的、不分行的、无韵律的散文。
但是,“诗的散文”长期被人们称为“散文诗”。其实,二者是有些微区别的。虽然,二者都需要“诗核”,但“散文诗”的中心词是“诗”,一般要求有韵律,语言更精炼,形式更短小,主观抒情性更强。而“诗的散文”的中心词是“散文”,它不要求押韵,比之于“散文诗”,篇幅更长,其内容可描述为繁杂的事物和心理。也许,有人认为“诗与散文的分别在精神而不在有韵与否的形式。”这种看法,表面上是拓宽诗的自由度,实际上因宽泛而降低了诗的品格,甚至取消了诗。美国康纳尔大学M’H’阿伯拉姆教授对“散文诗”的解释是:“散文诗是用一连串没有行间间断写成的作品。它们简洁紧凑,韵律明显,读起来响亮动听。”②仍然强调“韵律”。其实,“韵律”就是情感表达的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和语言的音乐性。所以,明确“散文诗”的韵律,是对“散文诗”审美特征的维护。
那么,是否“诗的散文”比“散文诗”低劣而属“下品”呢?否!高尔基在《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一文里指出:“写散文吧——我还没有下决心,在我看来散文要比诗还难,它需要特别敏锐的眼力,需要有洞察力,要能看到和发现别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还需要有某种文字上的异常严密而有力的词句,但是我终于开始尝试写散文了,可是当我发现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写普通的散文时,我就选定了‘有韵律的散文’。”③这“有韵律的散文”就是“散文诗”。可见“诗的散文”写作的难度大于普通散文,更大于散文诗。也就是说,“诗的散文”的审美品格并不低于“散文诗”,故把带诗意的非韵的“诗的散文”说成“散文诗”,是大可不必的。
“诗的散文”最早的译介者和开拓者是刘半农。1918年,他将两年前(1916)在美国《Vinity Fair》月刊上看到的印度歌者Sripa RamaHbNsa的《我行雪中》(为歌者拉坦·德维——Raten Devi——所唱)翻译出来,在《新青年》4卷5号(1918年5月)发表,并在“导言”中说明翻译之经过:“尝以诗赋歌词各体试译,均苦为格调所限,不能竟事。今略师前人译经笔法写成之,取其曲折微妙处,易于直达。”《我行雪中》描写了一位歌者过曼赫旦,入一室后,在猎伯兰画前的幻觉,表达了对“诸原本物,悉归真纯”,“一切事物,悉归天然”,“是美亦是爱”的渺渺人生的向往与追求,有浓厚的如佛思想。《我行雪中》“结撰精密”,是我国译介的第一篇“诗的散文”。
不久,刘半农又翻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Sir 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的《恶邮差》和《著作资格》两篇“无韵诗”(“诗的散文”),刊于《新青年》5卷2号(1918年8月)。《恶邮差》叙述了一个小孩眼见母亲“不快乐”,便以为是邮差将他父亲的信“留去自己看了”,为了安慰母亲,表示自己给母亲写一封“和父亲一样好”的信,表现了一颗真纯的童心。《著作资格》也从儿童心理写一位小孩希望母亲能理解他的写字、画画、折纸船。因为这如同他父亲的写作一样,具有“著作资格”!接着,他又在《新青年》5卷3号(1918年9月)发表了《译诗十九首》,其中泰戈尔的《海滨》(五则)、《同情》(二则);印度女诗人乃朵(Sarojini Naidu,1879-1949)的《村歌》(二则)、《海德辣跋市》(五则)、《倚楼》(三则);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1818-1883)的《狗》、《访员》。这些“诗的散文”,有的写孩子们汇集在无尽世界的“海滨”上与海的嬉戏、玩耍(《海滨》);有的写孩子对挨饿的小狗和被锁的绿鹦鹉的深深同情(《同情》);有的写一位少年,远远地去端瓮水,在回家的路上,忽听舟子之歌而迟疑不走。不料天黑了,狂风大雨,他想起家里弟弟和母亲对他的思念,心里十分难受,于是发出“Rám re Rām!我其死乎”的慨叹,表现了印度一些农村饮水的艰难(《村歌》);有的写市场商品之繁富(《海德辣跋市》);有的写对所爱者的尽心奉献(《倚楼》);有的写对生命的珍惜和对死亡的“恐慌”(《狗》)……,强烈的生命意识在这些作品里若隐若现,给人以心灵的震撼!
《新青年》6卷2号(1919年2月)还刊载了一篇“诗的散文”:《蜡烛》。作者是俄国作家索洛古勃(Sologub1863-1927),他出身贫寒,1882年毕业于师范学院,曾为数学教师。1884年开始诗作,属于“老一辈”象征主义派,其诗作多隐晦,主张抒真情,写“自我”。《蜡烛》描写一位智者在深夜里,在烛光下为人诵读“笔记”,传播知识与真理,可是“风吹来”,“他们发抖”。与此同时,一个女人在微弱的烛光下熬着寒冷,“坐着缝纫”,直至天明。后来,智者死了。女人哭着。但已有“几个人拿着书读”,并且“一群人到来”,唱歌,散发香烟。虽然棺木扛走了,“蜡烛被吹熄”,“一切仍如从前了”。但书声、歌声却扩散开了。此文以忧郁的笔调抒写了寒冷的俄国社会生活中的微弱的灯火,暗示了知识和真理始终不会泯灭的。
虽然,“诗的散文”的译介在“五四”前不是太多,但不久便有人翻译波特莱尔、王尔德、屠格涅夫、泰戈尔的“诗的散文”,在《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1920年6月,《晨报·副刊》将屠格涅夫的50篇“诗的散文”介绍给中国读者,引起不小的震动。这些“诗的散文”的评价、引进、对我国“诗的散文”的创作起了借鉴与催生的作用。
二
我国现代散文史上,“诗散文”的创作开始于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号刊载了沈尹默的《鸽子》、《人力车夫》和胡适的《人力车夫》、《一念》。5月,刘半农在《新青年》4卷5号上发表了《卖萝卜人》,在“题记”中注明:“这是半农做‘无韵诗’的初次尝试。”“无韵诗”者,“诗的散文”也。1919年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6卷2号上发表《小河》,也在“题记”中说:“有人问,我这诗是什么体,连自己也回答不出。法国波特莱尔(Baudelaire)提倡起来的散文诗,略略相像。不过,他是用散文格式,现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写了。内容大致仿欧洲的俗歌;俗歌本来最要押韵,现在却无韵。或者算不得诗,也未可知;但这是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波特莱尔提倡的是“诗的散文”。他在《巴黎的忧郁》出版后,寄给阿尔塞纳·胡赛的“信”中说;“在这怀着雄心壮志的日子里,我们哪一个不曾梦想创造一个奇迹—写—篇充满诗意的、乐曲般的、没有节律没有韵脚的散文:几分柔和,几分坚硬,正谐和于心灵的激情、梦幻的波涛和良心的惊厥?”周作人以此为鉴,自觉进行“诗散文”的创作,说明这一文体已经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和兴趣。事实上,《新青年》从1918年1月到1920年1月,据不精确的统计,在两年时间里的20期刊物上,共发表“诗的散文”51篇。其中:沈尹默15篇,刘半农8篇,周作人6篇,沈兼士5篇,唐俟(鲁迅)4篇,胡适4篇,俞平伯2篇,夬庵2篇,常惠1篇,陈衡哲1篇,李剑农1篇,陈子诚1篇,陈独秀1篇。同一时期,鲁迅在1919年8月19日—9月9日的《国民公报·新文艺》栏发表了一组“诗散文”,总题为:《自言自语》,共七篇:《序》、《火的冰》、《古城》、《螃蟹》、《波儿》、《我的父亲》、《我的兄弟》,将“诗散文”的创作推向一个新阶段。
在“诗的散文”的作家群中,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是先驱者或具有突出贡献者。沈尹默的“诗散文”内容厚实,充满对现实的愤懑和对美好事物的希冀。他的《除夕》写随着年岁的增长,儿时的天真烂漫逐渐减少,生活的艰难逐渐增多,故“乐既非从前的所有,苦也为从前所无。”反映了人事的沧桑,人生的苦难。《小妹》写一位辞别红尘出家为尼的小妹的眷恋,表现出对尘世的不满。《赤裸裸》谴责现实世界使洁白的人不得不紧裹着自己。他的“诗散文”中还有一些篇什表现出对受扼杀、受践踏的弱小者的同情,如《鸽子》、《羊》、《落叶》等;对沉睡的人们觉醒的希望,如《白杨树》、《三弦》;对傲风斗雪的不屈精神和蓬勃生命力的赞美,如《秋》、《生机》等。刘半农是“诗散文”的倡导者和先驱者,他不仅引进外国的“诗散文”,且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来丰富“诗散文”的画廊。他在《新青年》上共发表8篇“诗散文”,这些作品大量地反映了社会人生的苦难与不平。《学徒苦》以复沓反复的语调,历数学徒在店主家一年四季牛马不如的苦难生活,发出了“生我者,亦父母”的悲惨呼号,揭示了阶级压迫与社会的不平。《卖萝卜人》写一卖萝卜者被警察赶出破庙,反映了劳苦大众“脚无立锥之地”的悲惨命运。《无聊》写暮春天气里,花瓣纷谢,大院子里“却开着一棚紫藤花”,“铜铃叮叮当当,响个不住”,充满了生的气息。《晓》展现了晓行的火车窗外的两幅画面:车窗外——朝霞满天,平原上薄雾朦胧,绿树丛丛,远山淡淡,炊烟袅袅。车窗内——人们东横西斜,脸色死灰式似的干——枯——黄——白。唯有一个3岁的女孩,“笑迷迷的,两颊像苹果,映着朝阳。”表示了对新生、对未来的希望。们的“诗散文”直指社会人生,更热烈,更直捷,更具社会性,更富现实主义精神。周作人是“诗散文”的自觉实践者,他的6篇“诗散文”中,以《小河》、《两个扫雪的人》、《北风》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小河》是篇寓言式的“诗散文”,作者借农夫筑土堤、修石堰,河水被阻,只得在堰前乱转、呻吟、挣扎,堰外的稻、桑树、小草和哈蟆面临干涸的威胁,一方面希望小河象从前一样缓慢而曲折地流动,一方面又担心小河善良、美好的品性被扭曲,成为“不认识从前的朋友”的凶狠的河。《小河》是“普通人”的象征,它的重重被禁锢的命运是生活中普通人悲惨命运的写真。作者以物喻人,谴责了现实世界里扼杀人性的重重“堤”、“堰”!这些“诗散文”较为含蓄、深沉,但有些篇章较为浅薄,意蕴不够厚实。
三
综观“五四”时期“诗散文”的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表现出明显的审美特征,主要是:
(1)浓郁的现实主义精神。大量的“诗散文”作品,来自生活的真切感受,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值得一提的是沈尹默和胡适的同题“诗散文”《人力车夫》(《新青年》4卷1号,1918年1月15日),沈尹默以淡淡的笔墨,勾勒出了车上车下对比强烈的“街市小图景”:车上,“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车下,“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下堕。”揭示了贫富的差异和对立,给人以沉重的回味与思索。胡适则写一个年仅16却已拉车3年,“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的凄惨景况,虽有暴露,但更多的是怜悯,力图以富人对穷人的“同情”去调和社会矛盾,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刘半农的《车毯》(《新青年》4卷2号,1918年2月15日),写人力车夫为了多得“老爷”“两三铜子”,宁愿受寒,也不愿拉车毯“披一披”,因为“恐身上衣服脏,保了身子,坏了毯子。”反映了劳动者的凄惨生活。这些作品直面人生,针砭社会,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
(2)意象丰饶,哲理性强。意象是经由作者内心的造型和思维,进一步透过文学的媒介、语言的转义借喻等产生的一种形象。所以,“意象是以心象为基础,以各种譬喻手法为表现程序的一种语言图象——转义、象征、隐喻、类比,正是构成意象的几个主要修辞途径。”④“诗的散文”中,作者大量使用“意象”笔法,意象丰饶而哲理隽永。鲁迅《自言自语》中《火的冰》写“流动的火”,“遇着说不出的冷”,成了冰,但仍是“火的冰”,借火的变化与遭遇来象征如“火的冰的人”——先觉者的形象,表现了一种热烈而倔强的精神。鲁迅以唐俟的笔名发表的《梦》、《爱之神》、《桃花》(《新青年》4卷5号,1918年5月15日),也都意象奇特,哲理性强。《梦》写黄昏的“梦”,相互起哄、挤压,但都是“墨一般黑”的颜色,看不见出路,隐喻社会的黑暗。《爱之神》借小天使之口,说明一个人要敢爱敢憎。《桃花》写“我”到桃李花开的园中,不偏不倚地赞叹一句:“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不料惹得桃花“气红了面孔”,形象地批评了中庸之道。可见,“诗散文”的作者使用的是象征、暗示、隐喻、类比等手法,将自己对现实的深层次思考浓缩于独特的意象之中,以寄寓其强烈的爱憎情感。
(3)直白的语言,散文的节奏。“诗的散文”毫无例外地一律使用白话,甚至生活中的口语,直白的语言使文意显豁,思想明朗。自然,由于古代文化的深厚积淀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一些“诗散文”作品中常常夹杂个别的古文词语和外来语。如沈兼士的《寄生虫》:
Distome!⑤你寄生在我肚子,十多年了。我精神强的时候,你就弱些。
你精神强的时候,我就弱些。
弱之又弱,万一至于死,不知你那时候还能够独活吗?(《新青年》6卷6号,1919年11月1日)
这篇短文直白如话,夹用外语,在看似冷静的责问中,对害人的“寄生虫”表示了强烈的谴责。散文的节奏,指“诗散文”在语言上表现为白话的节奏。较之诗歌,它更侧重于语言的连贯性和序列化,有明显的口语结构,在句与句的连结上不象诗歌语言那样具有较大的跳跃性。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散文语言,注重事实的记叙和描写,为了适应主观抒情的需要,它的语言更精炼、更灵动。因此,这种语言节奏体现为口语的节奏,既舒徐连贯,又跳宕短促。如沈尹默的《月》(《新青年》5卷1号,1918年7月15日):“明白干净的月亮,我不曾招呼他,他却有时来照着我;我不曾拒绝他,他却慢慢的离开了我。我和他有什么情分?”叙述句的舒缓与独立句的急促,构成了强弱和谐的旋律,较好地表达了作者对“月”这一美好事物的依恋之情。
注释:
①郑振铎:《论散文诗》,《文学旬刊》24期,1922年1月。
②[美]阿伯拉姆:《简明外国文学辞典》,27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高尔基论文学》1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④郑明娳:《现代散文构成论》71-72页,台湾大安出版社,1989年版。
⑤Distome:双盘吸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