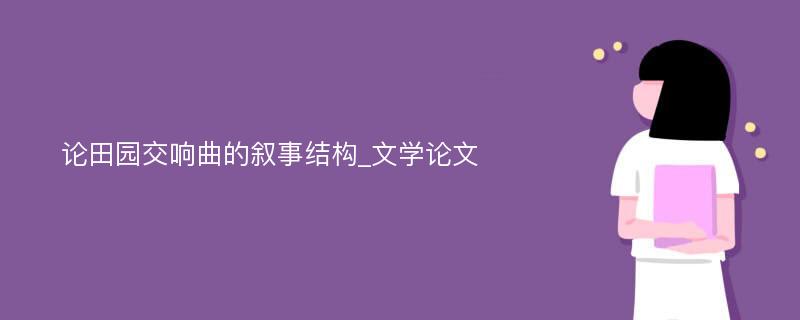
论《田园交响乐》的叙述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交响乐论文,田园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评论家塔迪埃在评论普鲁斯特的小说时指出:“小说既是空间结构也是时间结构。说它是空间结构,是因为在它并排展开的书页中出现了在我们的目光下静止不动的形式、组织和体系;说它是时间结构,是因为不存在瞬间阅读,因为一生的经历总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注:塔迪埃《普鲁斯特和小说》,桂裕芳、王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224页。)当然,文学作品的结构相对于自然科学中的结构而言有其特色。文学作品既不是一堆杂乱的唠叨,也不是千篇一律的信息罗列,它依赖于叙述人即作者的技巧和才能,并经过作者精心的安排和艺术的加工。“叙事作品与其他叙事作品共同具有一个可资分析的结构,不管陈述这种结构需要多大的耐心。因为复杂的胡乱堆砌和最简单的组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不依据一套潜在的单位和规则,谁也不能组织成(生产出)一部叙事作品。”(注: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裕禾译,见《符号学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9页。)那么这个结构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试图参照当代若干有关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理论,对法国作家纪德的《田园交响乐》作一些分析,以证明这种结构的存在及其文学价值。
一
任何完美的艺术作品,都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存在着一种多维的、多方位的、非线性的布局。在这些作品中,可以说“没有一个笔触是孤立的,每一部分都能从其他部分获得存在的理由,并把自己的存在强加给它们。”(注:普鲁斯特《盖尔芒特家那边》,潘丽珍、许渊冲译,《追忆似水年华》中卷,译林出版社,1994年,第313页。)而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说,这种布局就是文学作品中存在的叙述层次。罗朗·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一文中将叙事作品分为功能层、行动层和叙述层三个层次,每个层次都有各自的结构和意义。如功能层可分为功能和标志两个单位,而功能又可再分为核心和催化两个更小的单位,标志也可再分为标志和信息两个更小的单位,正是这些小单位和由它们组合起来的大单位构成了叙事作品的整体。行动层实际上就是人物层。世界上没有一部叙事作品是没有“人物”的,或没有“行动主体”的。如普洛普把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压缩成简单的类型:授以法宝者、助手、坏人等。(注:普洛普《民间故事形态学》,巴黎索伊出版社,1970年,第51页。另见张智庭(怀宇)译《法国文学评论史》第384页注释②,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根据人物的行动可以对它们进行描述和划分,把为数众多的人物纳入若干个行动范围,每个人物在自己的行动范围中就是主人公。不过,行动主体通常并不限于一个。叙事作品类似于某些比赛结构,有时会有两个平等的对手“争夺裁判发出的球”。在作品中,人物也是叙述单位,并且通过人称来表达,我们可以总结一套人称的语法,不过语法范畴只能按话语的主体而不能按实际的主体来划定。叙述层就是交际层。叙事作品内部存在一个交际模式,有个叙事作品的授与者,还有个接收者,即叙述者和读者(或听众)。“我”通常是叙述者的符号,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叙述同语言一样,只有两个符号体系:人称体系和非人称体系,如“我”和“他”等。同时,叙述作品也有语境问题。一般说来,叙述不能从使用它的外界取得意义,如同语言学研究到句子为止一样,叙事作品的分析到话语为止。然而,叙述层有一种模棱两可的作用,它通过一些语境编码与外界相连,与其他一些体系(社会的、经济的、思想意识的体系)相连。当然,叙事作品的语境一般被作者有意无意地掩盖起来,作者虚构了一个合情合理的情景,使读者不易察觉语境的存在。
文学作品中这种布局和层次成了某种结构,即帮助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叙述结构。菲力浦·阿蒙在分析莫泊桑中篇小说《奥尔拉》的描写结构时发现,文学作品中存在着某些要素,存在着某些类同的单位,可以根据它们的功能和连贯方式进行分门归类。如在文学话语中,通过相同成分的重复可以构成一种A-A[']结构:A代表第一个相同成分,A[']代表第二个相同成分,二者构成话语中的切分界标。在两者之间和两边放置X、Y和Z三个切分成分(Segment),构成类似于立论——驳论——综论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可以从最大的切分成分开始,直到最小的不能再分的切分成分为止,以便确定各切分成分之间的关系及其地位,并且与语言的各层次(语言的、词汇的、语法的、语义的)相结合。(注:阿蒙《结构描写论》,载法国《文学》杂志专辑:《文学作品的语义学》,1971年12月第4期,第31页。)这么一来,语言学中的大部分关键性概念似乎都适用于文学话语的分析,如描述层次、可变项、功能、互补式分布、转换、系统、纵组合项(paradigme)、横组合项(syntagme)等。我们可以建立一门结构语义学来分析文学话语,因为文学话语是一个预先划定的和谐的体系,其中的各个成分,表面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实际上都是相互关联着的。每个成分将由它与该话语总集的关系来确定,而不取决于话语外的参照对象(真实的、传记的、历史的、心理的等),即巴特所说的叙事作品的“语境”。文学话语的每个成分在逻辑上和语义上都具有功能性,没有一个成分游离于话语之外。
诚然,文学话语是一个不断复述的整体,它在不同的层次上复述同样的成分,复现等值的两个内容或两个形象。这种二重组合引导人们像分析其他任何话语一样去分析文学话语(语义、语境、文体、结构等)。我们可以像分析语言那样,从非复述成分中筛选出复述成分,仅仅抓住那些具有同质的成分(重复、等值)和具有差异的成分(分离、相反概念或自相矛盾)。文学话语的意义并不是词汇或句子在线性排列上的意义累加,而来自于互相关联的意义在表达层次上总体合成的效果。话语有自己的赋义方式,隶属另一种语义学,它与语符的赋义方式迥然不同。这就意味着需要建立若干个话语模式:表层模式和深层模式,顺时模式和非顺时模式,结构模式和统计模式等。文学话语擅长于在话语集的连续性和合成性上做文章(语段、章节、段落、插曲)。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找出大量的话语集,即在语义上或功能上都等值的话语集。把不同长度、不同形式的句段看作等值的话语集,这与话语特有的运作方式是相符合的,如各种不同的替代手段便是话语从语义上进行类同化的要素。“我们也可以设想,文学话语也像语句本身一样运作,它使用大量的套语、成语、复合词和习惯成自然的横组合项,词序相对固定,韵律比较明显,从而组合成庞大的话语空间。”(注:阿蒙《结构描写论》,载法国《文学》杂志专辑:《文学作品的语义学》,1971年12月第4期,第34页。)
托多罗夫在《文学叙事作品分类学》一文中也对文学作品的话语功能及其叙述逻辑作了探讨。他认为,“从总体上讲,文学作品有两个方面:它是一个故事,同时又是一个话语。说它是故事,因为它回述了某种现实,某些业已过去的事件,一些过去的、但与现实生活混为一体的人物……。但作品同时也是一个话语:有一个叙述者在叙述故事,在他的面前还有一位听众(读者)在倾听。从这个角度来说,重要的倒不是所要报道的事件,而是叙述者向我们讲述故事的方法。”(注:托多罗夫《文学叙事作品分类学》,载法国《交际》杂志1996年第8期,第132页。)作为故事,叙事作品有两个层次:动作逻辑层次和人物关系层次。叙述通常通过重复、渐进、类推法等手段建立一种动作逻辑关系,使作品的各个叙述段能相互呼应,相互粘连。例如,作品中存在一种三元叙述模式,即整部叙事作品由许多小叙事作品相互连接和镶嵌而成,而每个小叙事作品又由三个(有时为两个)要素组成。所有作品都由这种小叙事作品组成,其结构相对稳固,功能相当于生活中的小情景,如“欺骗”、“约定”、“保护”等。人物意义则完全取决于他与其他人物的关系,即三种最基本的关系,这就是欲望、交际和参与。欲望在所有人物身上几乎都能看到,其最常见的形式是“爱情”;交流则造就一种“守密”关系;参与则导致“帮助”关系。在这三个基本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对立规则和被动规则衍生出十二个不同的关系。如爱情的对立面是仇恨,守密的对立面是泄密,帮助的对立面是阻挠。再如欲望有主动去爱别人和被别人爱,恨别人也被别人所恨;交流中守密可以是向朋友透露消息也可以是朋友的知情者,泄密可以是泄漏别人的秘密也可以是自己的秘密被人知晓;参与中帮助可以是帮助别人也可以是得到别人的帮助,阻挠行动可以是阻挠别人或受到别人的阻挠等。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叙述作品中十二种不同的关系,我们借助三个基本谓语(关系)和两条衍生规则对它们进行了描述。必须指出,这两条规则的功能并不完全相同,对立规则用于引出无法用别的方法表达的句子;被动规则用于显示业已存在的两个句子之间的亲属关系。”(注:托多罗夫《文学叙事作品分类学》,载法国《交际》杂志1996年第8期,第140页。)
作为话语,叙事作品是叙述者向读者发送的话语和言语,而发送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托多罗夫总结出三组话语程序:叙事作品的时间(即故事时间与话语时间的关系)、叙事作品的视角(即叙述者感知故事的方法)和叙事作品的方式(叙述者讲述故事的方式)。在叙事作品中表现时间一直是个难题,因为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是不相同的。话语的时间是线性的,故事的时间是多维的(即数个故事同时发生),而话语又必须将多个故事一个接着一个地叙述出来。要这样做,就必须打破故事的“自然”时序,重排时间。在数个故事同时发生时,叙述必须采用连接或镶嵌的方法。连接就是将数个故事并列起来,讲完一个再讲另一个。如三位兄弟外出寻宝,每个人的旅行便是一个故事,可以并列叙述;镶嵌就是大故事里套小故事,如《一千零一夜》里有许多这样的镶嵌叙述。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组合法很像语法中两种基本句法关系:并列从句和从属从句。叙事作品的视角则反映了叙述者与人物在作品中的地位问题。传统小说中有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叙述者,他可以看到密封屋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知道人物脑子里所想的东西。因此,人物处于从属地位。而在现代小说特别是卡夫卡的小说中,叙事者与人物的能力对等,前者不比后者知道得更多。第三种情况是叙述者比任何一个人物知道的都要少,他只能描述人物所看到的或听到的,而没有自己的意识。叙述作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再现与叙述。它们相当于从前的编年史和正剧之间的关系,编年史的作者仅仅报道事件,人物不用说话,是纯粹的叙述;而正剧中的故事是在观众眼前展开的,叙述不用叙述者来完成,而包含在角色的话白和动作之中。再现通过人物的言语、人物的行动和客观的言语活动来实现,而叙述则通过叙述者的言语、叙述者的形象和主观的言语活动来完成。
可以看出,巴特有三个叙述层次,阿蒙的话语集语法,托多罗夫的叙述形态分类等,其目的都是试图勾画出文学作品的叙述结构,抓取作品中的某种“秩序”。那么这些思考是否合理呢?他们的方法是否行之有效呢?我们不妨以纪德的中篇小说《田园交响乐》(注:Gide,La Symphonie Pastorale,中译本有丽尼译《田园交响乐》,上海美术生活社,1935年,转译自英译本;有穆木天译《牧歌交响曲》,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有施宣华译《田园交响乐》,上海启明书局,1938年。)作为应用对象,分析一下这部作品的叙述结构,检验一下这些理论的可行性和局限性,看看要建立一门文学叙事作品类型学是异想天开,还是切实可行。
二
《田园交响乐》(以下简称《田园》)是一部日记式小说,讲述了一位乡村教师收养、教育并爱上一个失明女孩的故事。小说中的日记分一、二两册,第一册包括七篇日记,篇幅都较长,第二册有15篇日记,但大部分篇幅较短。日记是按日期顺序写的。每一篇日记都有准确的日期,长短不一,似乎被分成一段段组合着单一性功能的中断组织,像连环画那样以一幅幅画面出现。巴特把这种中断组织称作序列(sequence)。小说中22篇日记可能看成22个序列。从第一册第一篇日记开始,依次为相遇、收养、启蒙、情窦初开、情敌、嫉妒、倾诉等;第二册依次为分离、彷徨、希望、复原、再次求爱、失落、吻别、求助、复明、焦虑、回避、等待、意外、吐露真情、永别等。每个序列又由两个相互补充的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故事”,即小说中叙述的过去的事情;另一部分是“话语”,即小说中交待的作者写书时的情况。例如在第一篇日记中,小说以叙述者的话语开始:“大雪不停地下了三天,积雪堵塞了道路。我没能去成R镇……。我利用大雪封路给我的空闲时间回忆一下过去的事,讲讲我是怎样照料杰尔特吕德的。”(注:纪德《田园交响乐》,巴黎伽利玛出版社《袖珍丛书》6,1970年版第9页。)第八篇日记也以叙述话语开始:“我不得不将日记搁置了一些时间。积雪终于融化了……。昨天夜里,我重读了先前所写的一切……,说真的,当我再次读到以前所说的话时才懂得……。”(注:纪德《田园交响乐》,巴黎伽利玛出版社《袖珍丛书》6,1970年版第103-105页。)在总共22篇日记中,用叙述话语开始的日记占多数。所以,故事与话语的安排清晰可见。其实在作品中,故事的时序是符合实际的。如在3月8日(第一册第五篇)日记中,叙述者说:“八月上旬的一天,距今大约六个月……”(注:纪德《田园交响乐》,巴黎伽利玛出版社《袖珍丛书》6,1970年版第28页。)根据推算,3月8日写日记,六个月前确实是上一年八月份。小说中多处有此类情况,如3月18日日记中,“去年夏天的谈话”,3月10日日记中“复活节那天”等。但是话语的时序往往与实际不完全吻合,这表现在日记时间与叙述时间的差别上。例如在2月27日(第一册第二篇)日记中,叙述者说:“我利用(积雪堵路)的机会继续讲述我昨天开始讲的故事。”(注:纪德《田园交响乐》,巴黎伽利玛出版社《袖珍丛书》6,1970年版第70页。)若按日期推算,故事中的“昨天”应该是2月26日,昨天的故事应该是第一篇日记中讲的故事。然而,第一篇日记的日期却是2月10日,二者相差16天。由此可见,遵守不遵守时序是作者有意安排的。作为故事,应该有一个时间上的逻辑性,前后必须一致;而作为叙述,更注重话语的紧凑性,把十多天以前说成“昨天”,无疑给话语在时间上的连接增加了粘合剂,同时也使叙述话语更为自由,更能适应于表达内容,拼组叙述序列。
那么,上述序列是怎样组合成作品的呢?我们不妨借助阿蒙的A-A[']结构来考察一下《田园》的结构,牧师把盲女带回家来,牧师的家是第一个切分界标,即A;后来又把盲女寄托给M小姐,M小姐的家成为第二个切分界标,即A[']。在A和A[']的中间和两边,安排了三个切分成分:故事开始的情况、杰尔特吕德在牧师家的日子、杰尔特吕德离开牧师家后的日子。故事开始的情况被安插在2月10日日记(第一册第一篇)中,算第一个切分成分;盲女在牧师家的日子构成第二个切分成分,与第一册日记(7篇)基本对应;盲女离开牧师家的日子为第三个切分成分,与第二册日记(15篇)相对应。这样就构成了《田园》的整体结构:
山腰茅屋 牧师家 M小姐家 回归(永别)
I- - - - - - -I- - - -I- - - -I- - -
序曲 和谐的田园曲 起伏的田园曲 终曲
作品伊始,叙述者描绘了法国东部汝拉山区的景色:“我认出两公里外一个神秘的小湖,金色的晚霞抹红了湖面,我认出了它,似曾相识于梦中……。从小湖泻出一条小溪,削去林海的一侧,沿着一块沼泽逶迤向前……。太阳已经下山,我们沿着溪边小道走着,夜幕已经降临……在一座小山的腰际,有一座似乎无人居住的茅屋,看不到一丝炊烟,在黑暗中蓝影绰绰,屋顶染着些许天空的金光。”(注:纪德《田园交响乐》,巴黎伽利玛出版社《袖珍丛书》6,1970年版第11页。)这一段描写在叙述结构中起着划界的作用。卷首描写的功能是向读者展示故事的背景和人物的环境,如巴尔扎克《高老头》中对伏盖公寓的描写,司汤达《红与黑》中对维璃叶镇的描写,莫泊桑中篇小说《奥尔拉》中对鲁昂市的描写等。不过,《田园》中的卷首描写除了上述功能外,还对叙述进行划界。因为汝拉山的山区风貌和居民的活动本身就“带有社会学特征,可以称之为划界的底片”。(注:阿蒙《结构描写论》,载法国《文学》杂志专辑:《文学作品的语义学》,1971年12月第4期,第36页。)卷首描写虽然不长,但独自成为叙述的第一个切分成分,为整部作品划定了叙述框架:时间为19世纪90年代,地点地法国汝拉山区的一个小镇,人物是“我”和“这个虔诚的灵魂”,情节为“这个虔诚灵魂的教育和发展”,“我觉得我把她从黑暗中拯救出来,就是为了热爱她,就是为了爱情。感谢我主赋予我这一使命。”(注:纪德《田园交响乐》,巴黎伽利玛出版社《袖珍丛书》6,1970年版第10页。)这一部分相当于音乐《田园交响曲》的序曲,是叙述者将读者引入叙述天地的入口。
第二和第三切分成分是作品的主体,在总体结构上两者都较“等值”。如在写景方面,两者都以雪开始。雪在本作品中是叙述结构的核心单位,因为屋外在下雪,牧师无法外出,所以才有时间写日记,换言之,下雪给了“叙述者安静的状态”。处于这一状态时,叙述者有两种选择,他可以写或不写日记,这样就把故事和叙述引向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在人物的行动方面,两册日记中都有静和动的对比,有相似的接近与远离。前者是大雪封路不能出门,是被动的静,后者是因发生精神危机而闭门思过,是主动的静;开始时牧师主动接近杰尔特吕德,去教化这位“迷途羔羊”,后因产生爱情有悖教义与伦理,于是主动疏远她,把她托付给M小姐照料。然而肉体的远离更加强了精神上的接近。在第二册日记中,他们相处的时间虽然不多,但心理的沟通已经处于最佳状态。复明可被看作一种接近,但是复明使杰尔特吕德看到了他们“原罪”,决定与牧师永远分离——自杀。在话语方面,两册日记中有许多相同的词句。如“我利用空闲时间……”(第9页),“我利用不能出门……”(第28页),“我得从头说起……”(第48页),“我不得不停下日记”(第103页)等;有很多处使用“主啊!”(第10、35、117、136等页);还有“复活节时”(第106、114页);“谷仓”(第125、136、144等页);另有重复出现的不定的专有名词:雅克的朋友T(第73页)、到R地方去(第9页)、M小姐(第88页)等。这些复述成分组成了较小的界标,用以标出各个序列的叙述切分点,同时又使前后两册日记形成某种对等的叙述结构。不过就前后日记的篇幅和篇数而言,差别是很大的,这里我们仅指出两者在话语方面的对等。不对等的方面则说明《田园》的叙述结构中还有其它一些因素,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从总体结构看,《田园》属A-A[']结构。不过,从作品的内容结构来说,也存在巴特所说的层次结构特征。就功能层而言,雪就是一个核心功能,这个词在小说中先后出现过许多次,而且都处在叙述结构的重要分节处。如卷首、2月27日日记中(第28、44页)、第二册日记开始处(第103页)等。尤其是在第二册开始处,叙述者说:“积雪终于融化了……”,这样,思维逻辑让人自然想起冬去春来的结论,于是,叙述得以继续。当然,雪也是一个比喻,它暗喻着盲女那洁白无暇的心灵,暗示她那白纸一张的精神天地正等待牧师去教化。同时,雪也许还表明,叙述者的作品这时也是一张白纸,正等待叙述者来构建。马拉美曾经提到过“空白纸的洁白禁止着……”,不让作者写作,禁止他与读者交流,正如大雪阻止牧师去布道一样。像雪这样的核心功能单位在作品中有许多,如老女人的死、盲女、带盲女回家、听《田园交响曲》、儿子雅克、医生马丁、盲女复明等。再如第89页提到牧师的妻子忧心忡忡。妻子的忧愁为后面的叙述埋下伏笔,谜底到129页方才揭示:牧师和盲女双双堕入爱河。这些核心功能组成了叙述的主线。在这些核心单位周围,聚合了一些催化功能。它们与各个核心功能发生关系,其功能性较弱,是核心功能的外围和寄生物。核心功能维系着叙述的命脉,从逻辑上聚合作品,而催化功能是些“细枝末节”,在功能分布中起着“较弱的”聚合作用。如果说雪在《田园》中是核心功能,那么,太阳、小山、河湖等便是催化功能,描述它们不是主要的,而是为了衬托大雪。再如在发现盲女的时候,她像“一个不定形的东西蜷缩在壁炉边,似乎睡着了,厚厚的一堆头发几乎完全遮住了她的脸。”(注:纪德《田园交响乐》,巴黎伽利玛出版社《袖珍丛书》6,1970年版第13页。)盲女的眼瞎、不具人形等细节就是催化功能,为的是描述盲女当时的悲惨境况。标志和信息是填充作品骨胳的肉,如作品中提到牧师没能去做圣事,表示他是神职人员;“我把迷途羔羊带回来了”,表示他是一位虔诚的、乐善好施的牧师,这些都是标志性叙述单位。信息类叙述单位则有地名、人名(如瑞士城市洛桑、法国的汝拉山等)、天气等,在此不一一列举。
作品的行动层也有一些特色,探讨一下将得出有趣的结论。我们可以从叙述者的行动、普洛普的功能分析法、行动的逻辑层次和人物关系着手。关于托多罗夫的逻辑层次和人物关系法,我们将在下文讨论。现在先看一看《田园》中的叙述主体问题。小说中的叙述者是个匿名人物,他一直以“我”的口吻讲述故事,交待写作的过程;他无名无姓,妻子阿梅称呼他“我的朋友”,盲女杰尔特吕德起先叫他“牧师”,到死前也叫他“我的朋友”,儿子雅克称他“我的父亲”或“您”等。其实,这个人物是双重的,他既是叙述者,也是一个主体人物。说他是人物,因为他在故事中自始至终参与行动:把盲女接回家、安顿、启蒙、送医等;说他是叙述者,因为作品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他叙述的。在这两个身份中,叙述者的身份似乎更强一些,人物的身份则要弱一些。作为叙述者,他轻车熟路地驾驭着小说的进程,展现着所有人物(包括作为人物的自己)和他们的行动;而作为人物,他只是故事中的行动主体之一。可以说,“我”是一个单数的人称行动主体,更是一个单数的人称叙述主体。
现在我们再看一看《田园》的叙述形态,即叙述层上的情况,看一看普洛普的功能分析法是否也适应于它。普洛普把民间故事分成31个叙述单位,统称为功能(注:普洛普《民间故事形态学》,巴黎索伊出版社,1970年,第35-80页。另见张智庭(怀宇)译《法国文学评论史》第384页注释②,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它们是(功能后字母为代号):1) 离家β、2) 禁止γ、3) 违禁δ、4) 询问ε、5) 信息ζ、6) 欺骗η、7) 阴谋θ、8) 坏事A、9) 劝说B、10) 不听劝告C、11) 出发↑、12) 捐赠者D、13) 考验E、14) 接受捐赠F、15) 旅行G、16) 战斗H、17) 印记I、18) 胜利J、19) 如愿K、20) 凯旋↓、21) 追踪Pr、22) 救援Rs、23) 微服还乡O、24) 冒功L、25) 艰巨任务M、26) 完成任务N、27) 公认Q、28) 揭露Ex、29) 变形T、30) 惩罚U、31)婚配Wo。在这31个功能中,D、E、F为三个主要功能,即捐赠者、接受考验和接受捐赠。从《田园》来看,这三个功能似乎倒也适用。对牧师来说,当他外出布道时,遇到孤苦伶仃的盲女,出于怜悯和对上帝的虔诚,他把盲女带回家中收养,使盲女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长大成人。这里的捐赠者是借助盲女来体现的上帝;面对盲女作何选择是对牧师的考验;教化成功、盲女复明、牧师灵魂得到锤炼就是上帝的捐赠。对盲女来说,姑妈去世迫使她离家,牧师则是捐赠者;学习生活、皈依教义是对她的考验;获得两个男人的爱(牧师及其儿子)和灵魂的拯救是上帝的馈赠。可见,作为叙述形态的主要功能,《田园》中多少能找出一些,另外一些非主要功能也不乏其例。不过就整个作品而言,《田园》并不十分遵循这种形态,所以用民间故事的形态分析法来硬套确实有些牵强附会。
三
作品的话语界标和叙述功能构成作品的形式结构,把握它们对认识作家的创作过程、动机、特点等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样一个故事,叙述方法不同,其美学效果也截然不同。不过,借用多托罗夫的逻辑层次和人物关系概念对作品进行补充分析,则会得出另一些结论,使我们对作品的逻辑结构有所认识。从行动的逻辑层次看,《田园》的各篇日记相当于一个行动,每个行动中包含着一个小叙事作品。如2月10日(第一册第一篇)日记展现了“闯入、敌意、接纳”的内部结构,即当牧师将一个陌生人(杰尔特吕德)带回家时,受到全体家庭成员的冷遇,但杰尔特吕德最终得到家庭的认可,住了下来;再如2月27日(第一册第三篇)日记描述了杰尔特吕德“学习、进步、好学”的进程,即牧师在儿子的帮助下教盲女认读盲文,盲女从被动学习变得勤学好问(如怎样用声音来理解颜色);5月10日(第二册第四篇)日记反映出一种对立的内部结构:“顺从、对抗”。牧师的儿子雅克表面上同意不和杰尔特吕德接触,实际上偷偷地见她并给她读《圣经》,并且挑选与父亲观点相反的章节,以改变杰尔特吕德对《圣经》的理解。妻子阿梅丽虽然对盲女照顾周到,热情接待,但赌气说,“老天没让我生来就是瞎子”。在日记与日记之间也有一种逻辑关系,各个行动(从叙述角度说为序列)根据某种逻辑相互结合,或并列、或对立、或镶嵌。如相遇与收养、爱情与嫉妒、收养与分离、彷徨与再次示爱、希望与失落、吐露真情与永别等。各篇日记内部和日记之间通过重复、渐进、类推等手段建立起行动逻辑关系,使作品的各个部分相互呼应,相互连接。
从人物关系看,“欲望、交际、参与”的关系在《田园》中也比较明显。牧师的欲望最初是挽救生灵,体现的是上帝的爱,后来转变成了性爱。他的行动开始是主动的(收养盲女、教育、用上帝的爱教化她等)后来变得被动了(他不能解答盲女提出的问题,没能阻止盲女选择自杀等);杰尔特吕德对雅克的爱先是被动的,后来成为主动的。在牧师和盲女之间,在盲女和雅克之间,在盲女和牧师妻子之间,都存在一种“守密”关系。“帮助”则更为复杂,分别分布在数个层面上,如表面的与背后的、主动的与被动的、体力的与智力的、生理的和心理的、世俗的与宗教的等等。不过,《田园》中人物关系上的逻辑主要是爱情与嫉妒、合作与对抗的关系。请看书中发生矛盾冲突的四个主要人物的情况:牧师、阿梅丽、雅克和杰尔特吕德。他们四人构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关系:牧师是不该爱,却爱上了杰尔特吕德;阿梅丽是该被爱的,却受到了冷落;雅克应该去爱杰尔特吕德,却被禁止不让爱;杰尔特吕德对父子俩都爱,但这种爱是盲目的,后来演变成在精神上与牧师心心相印,而在肉体上更仰慕雅克。从法律和传统的角度看,牧师与阿梅丽已经是夫妇,因而不能再去爱别人;雅克和杰尔特吕德都是年轻人,是可以相爱并结合的。然而牧师爱上杰尔特吕德就树起了两个情敌;妻子产生嫉妒,视杰尔特吕德为情敌;雅克也产生仇视,以父亲为情敌。牧师的做法显然有悖于伦理道德,但他却从教义中寻找借口,并将这种观念灌输给杰尔特吕德。他故意将一张卡片留在她房间里,上面写作“不吃饭的人不要审判吃饭的人,因为上帝接待了吃饭的人”(出自《圣经》第16章《罗马人》)。(注:纪德《田园交响乐》,巴黎伽利玛出版社《袖珍丛书》6,1970年版第115-116页。)他想以此让盲女认识到,他们的爱情不是原罪。然而,他们的爱情却以悲剧结束,原因是牧师背离了教义。他没有向杰尔特吕德全面地传授教义,而是根据自己的感情需要去片面地解释《圣经》,这种断章取义的做法非常危险。这也正是纪德在作品中刻意要表现的批评态度。
阿梅丽是一个贤妻良母,在这场冲突中她完全是个受害者。盲女进入家门,她就感到不祥的预兆。她最初的冷淡表面上是由于“家里的人已经够多的了”,更深层的是出于对外来女性的本能的排斥。“这种事我早就看出来了。但你们男人就是注意不到。”“我一直在想,留着她将后患无穷”。(注:纪德《田园交响乐》,巴黎伽利玛出版社《袖珍丛书》6,1970年版第87页。)但出于对丈夫的忠诚和对家庭的责任感,她忍辱负重,协助丈夫照看好盲女和自己的五个孩子。雅克虽然年轻,但在精神世界里却比他父亲更为成熟。他对杰尔特吕德产生了爱情,但在父亲的劝告下,他表示“好,父亲,我听您的”,离开杰尔特吕德去度假。不过,他有时也来点阳奉阴违,私下里去医院看望做复明手术的盲女,还给她念保罗福音书:“从前因为没有戒规,所以我活着;而当戒规来临时,原罪复活,而我就该死去,”(注:纪德《田园交响乐》,巴黎伽利玛出版社《袖珍丛书》6,1970年版第153页。)以此诱导杰尔特吕德,使她明白她与牧师的爱情是原罪。当然,他自己也感到某种负罪感,即与父亲争夺同一个女人,所以自己皈依天主教。杰尔特吕德则从一无所知的“东西”成长为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从对牧师的依附到对牧师产生爱情,一切都是在无知和牧师的误导中发生的,她是无辜的。她经历了生理的成长和心理的成熟,经历了躯体的完善和灵魂的升华。当她复明后,看到了她与牧师的错误和原罪,看到了阿梅丽的忧愁,发现她所爱的是雅克:“当我看到雅克时,我突然明白我爱的不是您,而是雅克。他的脸庞与您的完全一样……”(注:纪德《田园交响乐》,巴黎伽利玛出版社《袖珍丛书》6,1970年版第154页。)绝望中,她投河自尽,死前向牧师坦白说,雅克已经使她皈依了天主教,她得到了真正的永生。
人物之间的对抗关系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教义理解上的分歧,特别是纪德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态度。作者通过作品结构的安排,通过作品形式的对立、类比和人物、行动等逻辑关系上的对立,多方位地烘托出这种深层的对立——精神世界的论争。书名及书中描述听交响乐的情节暗喻了一种人生旋律:杰尔特吕德从纯洁无暇的盲女,经过坎坷成长为坚定的信徒,本身就是一首美丽的田园诗,一部激动人心的交响曲。提起田园曲,人们自然会想到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该曲五个乐章分别表现了不同的情景。《初到乡村时的快乐感受》反映出大自然的景色:在鸟语花香的田野里,阳光透出了薄云,微风吹拂着大地:《溪边景色》写了人们在潺潺流水的小溪旁沉思默想;《乡民欢乐的集会》表现出乡民朴素的民风和活泼豪爽的性格;《暴风雨》再现了大自然摧枯拉朽的力量及对大地的洗礼;《牧人之歌》表现了农民在暴风雨过后幸福和感激的情绪。(注:薛金炎《音乐博览会》,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36-38页。)读者隐约可以在纪德的小说中“听”到贝多芬这首交响曲。牧师在布道途中看到山区的田野风景,感受到造物主给他的子民营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一个放牧的广阔天地;在旅行中,牧师遇上了“迷途羔羊”杰尔特吕德,于是担负起了教化她的神圣使命;家庭成员及朋友的态度使他对家庭责任和神职义务作出思考和选择;感情纠葛和冲突像是一场暴风雨,也可以说是大浪淘沙;经过风雨的洗礼,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在至高无上的主面前达到和谐,奏出一曲感人的生存之歌,一曲拯救灵魂的“牧歌”。这大概就是《田园》的最深层的逻辑结构。
《田园》的结局值得我们再探讨一下。如果说小说到此显示出一种内种结构,一种形式结构,那么在结尾时则反映了一种外部结构,一种本体论的结构。杰尔特吕德自杀,雅克进入神职界,妻子心灰意冷,牧师本人则“心比沙漠还荒凉”,这些行动已经不是叙述形式,而是将小说和社会伦理道德连接起来的“公分母”。叙述结构到这里必须有个出口,即面向现实生活的出口。“这样,‘生活’变成了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是一个根本要素,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以便更好地理解叙事作品的结构。只有到了这时社会方面的干预才有其理由,而且完全是必要的。作品可以到此为止,因为它已经在现实中建立了秩序。”(注:托多罗夫《文学叙事作品分类学》,载法国《交际》杂志1996年第8期,第156页。)一部作品虽然自成体系,但决不是完全封闭的体系,就连托多罗夫也认为作品有两个秩序:作品的叙述秩序和作品的社会语境秩序。应该说,《田园》中的叙述秩序是清晰可见的,但也不是处处都遵守。语境秩序(生活秩序)在多数情况下从属于并服务于叙述秩序,但有时也占据首位,如小说结尾处就是这种情况。从叙述重新进入生活的做法,托多罗夫称之为“违犯”,违犯也是结构要素之一,是叙述秩序与生活秩序的转折点和连接点,是将小说与生活对接起来的途径。读者可以从《田园》中看到一种精神世界的论争,看到圣保罗教派的罪孽学说和耶稣教的普爱学说的对立,这也正是纪德本人所经历过的精神冲突。牧师的悲惨结局揭示了“自由解释《圣经》”的危险。纪德一直想写一本《反基督的基督教》,但没有写成,对牧师与杰尔特吕德关系的批评,实际上是对他自己与另一位少年关系的批评。这样就把小说与作者、读者、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另外,《田园》的写作开始于1918年春,后来因纪德去英国一度中断,回国后,他费了很大劲才完稿;同时,从前后两册日记的篇幅来看,后一册写得比较仓促,特别是后几篇日记缺乏精心的设计,有草草了结之感。
综上所述,《田园》中确实存在一种结构,一种标示叙述的形式结构,同时也存在一种反映社会生活和伦理道德的逻辑结构,只是前者比后者更突出一些。作者无疑在小说中追求一种文本效果,即试图冲破传统小说的结构框架,使作品成为语言创造的体验活动;作品中的能指被无限地放纵,千变万化的能指装扮着所指,使所指常常处于似是而非的境地,给作者创作及读者赏析留下宽广的自由空间;作者既不是作品的源头,也非本文的终极,他只是“造访”文本,使作品向读者开放,读者既是作者的合作者,又是作品的消费者,读者参与作品意义的创造;作品是一种可阅读成分的组合,“是一个万花筒,满是五颜六色的纸片,稍稍转动一个角度又会排成一个新的组合。由此,读者不断地被作者(或者说把自己)抛入新的视角,永远处于一种‘散点透视’的惶惶之中。”(注:汪耀进《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译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页。)然而,恰恰由于这种惶恐和迷茫,读者能够在文本中获得无限的阅读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