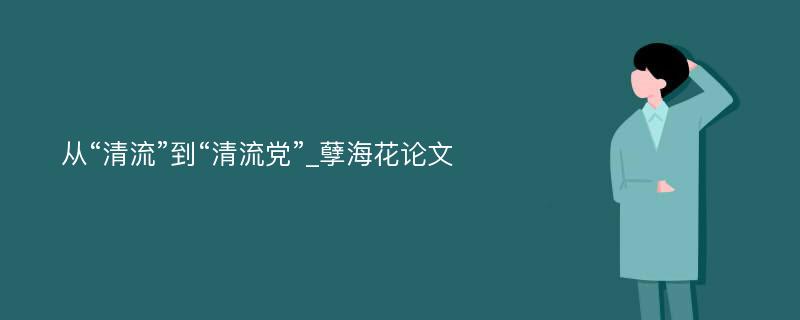
从“清流”到“清流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6)01-0028-09
有些事件历时愈久,愈是引发出人们谈论的兴致。而此类事件喧腾人口的过程,恰好也是其称谓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时候。比如中法战争前后盛行一时的“清流”称谓,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被人一劈为二,变成了两个称谓:1880年代的建言者和他们的活动被称为“前清流”,1890年代的则被称为“后清流”;而一入民国,“清流”不再分辨前后,合而为一,被换上了“清流党”的新标签。从晚清的“清流”到民国的“清流党”称谓演变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呢?
一 《孽海花》里的“清流党”
中法战争前后那场热热闹闹的建言活动,在当事人的日记、笔记和书信里,使用的都是“清流”或“清议”,有时用来指奏折议论,有时指建言之人。建言活动的参与者、反对者和旁观者莫不如此。①在进入20世纪之后,“清流”一下子被置换为“清流党”这一新称谓:
今日参督抚,明日参藩臬,这回劾六部,那回劾九卿,笔下又来得,说的话锋利无比,动人听闻。枢廷里有敬王和高扬藻、龚平,暗中提倡,上头竟说一句听一句起来,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惊心,他到处屁也不敢放一个。……还有庄寿香、黄叔兰、祝宝廷、何珏斋、陈森葆一班人跟着起哄,京里叫做“清流党”的“六君子”,朝一个封奏,晚一个密折,闹得鸡犬不宁,烟云缭绕,总算得言路大开,直臣遍地,好一派圣明景象,话且不表。却说有一日黄叔兰丁了内艰,设幕开吊,叔兰也是清流党人,京官自大学士起,哪一个敢不来吊奠!衣冠车马,热闹非常!②
这是小说《孽海花》里第五回的一段“热闹非常”兼冷嘲热讽的描写。其作者是当时积极参与反清活动、与章太炎共组爱国学社的金松岑,曾朴是从第七回起续写的。文中提到的厉害的笔杆子“庄仑樵”,影射的是张佩纶。翻一翻《孽海花》书后附录的人物索隐表便知晓:“敬王”指的是奕訢,“高扬藻”指李鸿藻,“龚平”指翁同龢;其余依次为张之洞、黄体芳、宝廷、吴大澂和陈宝琛。该小说是在留日学生强烈反清的背景下出现的,金松岑是经历了言论自由后返国的带有政治激情的年轻人,他的“清流”故事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在当时的日本留学生界,结党结社如同家常便饭,给“清流”加个“党”自然符合现实语境。
今天的历史学家很容易找到此段文字中的破绽:恭亲王奕訢与李、翁不是同路人,他和李鸿章一起,常常是被“清流”攻击的对象,不可能是“清流”的后台老板;中法战争时,一封白简将他赶出军机处的正是著名的“清流”人物盛昱;“六君子”之说也不知从何说起,从来没有人称呼“清流”是“六君子”,只有郭嵩焘对“清流”有过“松筠十君子”的说法。③或许这一称谓脱胎于 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的“六君子”称谓。如果是这样,倒是可以反过来证明作者是以后来的语境来套写前人的故事。上述引文让人觉得不可理解的第三点是,黄体芳已经被算作是“清流党”的“六君子”之一,紧接着又重复说他是“清流党人”。这些破绽显露了作者对半个多世纪发生的故事不够熟悉。
无所谓,反正“醉翁之意”不在复原历史。如果说晚清同时代人笔记、日记和书信里的“清流”故事多是掌故,那么,《孽海花》里的“清流党”故事矛头所向,则是当代政治。这一点,《孽海花》前六回的作者金松岑从来就不曾掩饰过:
此书乃余为江苏留日学生所编之《江苏》而作。当时各省留日学生颇有刊物,如《浙江潮》等,而《江苏》所需余之作品,乃论著与叫小说,余以中国方注意于俄罗斯之外交,各地有对俄同志会之组织,故以使俄之洪文卿为主角,以赛金花为配角,盖有时代为背景,非随意拉凑也。④
这里的“非随意拉凑”,只能理解为作者精心选择写作角度和剪裁历史事件,来为反俄的现实政治服务。但政治上的“非随意”,却导致了历史事实上的“随意拉凑”。如果说金松岑不熟悉“清流”故事还情有可原,为了政治宣传而演义历史也无可厚非,那么,小说的续写者曾朴完全有条件纠正金松岑的失误。因为在民国初年的小说家和报刊发行人中,恐怕没有人比曾朴更熟悉“清流”故事。
他是江苏常熟人,翁同龢的同乡,吴大澂的外甥,李慈铭的熟人。与“清流”人物相比,他虽是后辈,没有赶上中法战争前后翰詹名士热热闹闹的建言局面,但凭借着父亲在京城的关系,19岁的曾朴(1891年)一到京城,就得以与李文田、文廷式、江标和洪钧等名士交往,还成了翁同龢的忘年交,他获取的“清流”资料应该是第一手的。尽管中法战后“清流”人物已经黯然退场,但他们所倡导的时髦学术在90年代余韵犹存,曾朴本人还确实跟了一阵风,于元史、西北地理和吉金之学多有涉猎。⑤他不仅熟悉“清流”故事本身,而且了解这段历史的背景。但曾朴如金松岑一样,恰恰在这两点上用历史为现实服务。换句话说,他将自己看作是宣传家和小说家,而非历史学家。
他是金松岑的好友,两人又一同商量过第六回之后的章节写法,所以金松岑的写作动机和目的不可能不贯穿在曾朴的1905年的小说林社的版本中。到了事过境迁的1928年,《孽海花》出了修改本,曾朴想冲淡一下小说的政治动机,特别强调了该小说记录历史的功能:
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想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一幕一幕的展现,⑥
这里曾朴是在强调自己的作品的纪实性,但同时又没有否认其中多有想象。小说有想象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以想象的历史小说来抨击现实政治就异乎寻常,鲁迅发现了此类小说的异乎寻常之处,将其归类到“谴责小说”的范畴:
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予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⑦
鲁迅明白无误地点出了“谴责小说”的强烈政治色彩,研究晚清小说的名家阿英先生也认为曾朴的《孽海花》“表现了一种很强的革命性”。⑧这就是说,曾朴创作的原动力是为了政治。曾朴本人政治态度比较激进,是立宪政体的支持者。那个时代搞政治的人常呈狂态,头脑一热,难免就不太顾及事实。而不太顾及事实的原因,除了“革命性”外,还有“时人嗜好”的诱惑。虽然曾朴一再强调该小说的“历史”功能,但事实上他也难以免俗。这里有20世纪文坛掌故老手郑逸梅的话为证:
常熟曾孟朴撰了一部《孽海花》,轰动一时,可是没有完笔,同乡燕谷老人,因有《续孽海花》之作,这书的真实性,更较曾氏所作为强,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小说。⑨
其实最早指出《孽海花》小说真实性有问题的不是别人,正是曾朴自己。1934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
余作《孽海花》第一册既竟,岳父沈梅孙见之,因内容俱系先辈及友人佚事,恐余开罪亲友,乃藏之不允出版,但余因此乃余心血之结晶,不甘使之埋没,乃乘隙偷出印行,时光绪三十二年也。⑩
确实,曾朴有写作《孽海花》的本钱,但同时也有禁忌。所涉及的都是自己的长辈和朋友,要记实谈何容易,更遑论别人的解读?曾朴的人品是有目共睹的,蔡元培、郁达夫和胡适等人的悼念文字都是明证。他为什么宁愿得罪人也要出这部小说?其真正的动机,恐怕还是为了政治,所谓“不甘使之埋没”只是托词而已。看透这一层的,是日后反白话文的林纾,他在《孽海花》出版的第二年(即1906年)评论道:
昨得《孽海花》读之,乃叹为奇绝。《孽海花》非小说也,鼓荡国民英气之书也。其中描写名士之狂态,语气投我心坎。嗟夫!名士不过如此耳。特兼及俄事,则大有微旨。(11)
林纾所点的是曾朴的两个“要穴”:一是说“《孽海花》非小说也”,那它到底是什么?所谓“鼓荡国民英气之书”,那岂不是与早两年出版的《革命军》是同等的革命宣传品吗?另一点是说该小说“大有微旨”,并在文中一再强调傅彩云非小说的主线和主角。两个要点,一个中心,都是强调《孽海花》的政治特性。有趣的是,曾朴在日后接受了林纾的这一解读,并认为这是对他小说的“无量的推许”。(12)
愿意将《孽海花》看作是政治小说的不仅是林纾一人。辜鸿铭,这位慈禧太后的崇拜者,在《孽海花》行世后的第三年,即1910年,用英文撰写了《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 (汉语译为《清流传》),并在上海出版。老夫子摆出一副誓死捍卫大清帝国的架势,对领导洋务的李鸿章痛恨至极,同时对批评和攻击李氏的“清流”翰林好话说尽。他不仅将曾朴含有嘲讽意味的“清流党”标签全盘接受下来,而且将“清流党”看作是一个党派:
北京的翰林院是中国的牛津,是全国贵族知识分子精华之地。于是,翰林院就成了我所谓的中国牛津运动的总部所在。参与并支持过这个中国牛津运动的翰林们,被叫做清流党,就是致力于使民族精神净化的党派。(13)
《孽海花》犯有谴责小说“张大其词”(14)的通病,这点鲁迅先生早已指出。但与《清流传》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如果说,小说允许虚构和夸张,曾朴的“清流党”故事还不算离谱,那么,辜鸿铭则不顾事实,将“清流”描绘成为一个以复兴儒家教义、反对李鸿章的西方自由化路线的现代政党。(15)
从“清流”到“清流党”的标签更换,不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无论是“清流”的揶揄者还是同情者,无论是小说家还是政治家,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愿意借历史之老酒,浇现实之块垒。 (利用小说反点什么,并不是1949年后才有的发明。)此时的“党”,已不再局限在传统意义上的朋党范畴之内,而是从西方和日本传过来的多党制的政党。随着“清流党”称谓的出现,“清流”故事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它有时指朋党,有时指政党,有时两者兼而有之。使用者的心态和目的,决定着该称谓的内涵。
二 商业报刊与炒作“清流党”
甲午战后,清政府不得不容忍的一个现实是公众舆论(16)的狂飙突起,其表征之一是报刊杂志的大量涌现。除了带有政治和党派倾向的报刊外,商业报刊也应运而生。商业报刊最受大众欢迎的栏目是连载小说,而连载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晚清历史演义,它们的内容介于虚拟和真实之间,既给读者解气,又给读者留下猜测想象的空间。精明的商业报刊发行人把握住了市场脉搏,大量推出此类的政治消遣小说。这是20世纪头10年“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流行的商业背景和大众阅读心理背景。
那是一个政治狂热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在一个突然兴起的从舆论严控向舆论自由的转换过程中,商业利益及其操作方式对文人墨客的观念冲击是非常大的,哪怕是具有政治理想和操行的商业弄潮儿,也不得不遵守商业运行的规则,更不能超越“为稻粱谋”的生存现实。当时文人下海多集中在出版界,写手和作坊主,往往一身而二任,既是老板,又是雇员。仅从生存的角度说,压力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谴责“谴责小说”的大写手李伯元“应商人之托”而作《官场现形记》,也大可不必揭穿吴趼人领了商家的300块钱而构思《还我灵魂记》,为中法大药房的“艾罗补脑汁”大做特做广告。(17)一个人做事的动机并非都是单一直线的,没有理想和赚钱的双重驱动,或许也就不会有此类小说的高产繁荣。过去我们的文学史家似乎太专注于谴责小说政治意义的评估,而忽略了对其商业运作一面的考察。
这一时期的小说作者喜欢用笔名,如“南亭亭长”、“我佛山人”、“洪都百炼生”、“东亚病夫”、“古沪警梦痴仙戏墨”等等,当今网络时代的博客能够想到的笔名,那时都有了,而且二者使用笔名的心理状态也很相似:在一个有着千年文字狱传统的国度里,文人们对刚刚到手的舆论自由,既激动不已,又忐忑不安,谁也不清楚,这一自由是否有走到尽头的一天。同时,乐于广泛传播自己的文字,又很清楚自己写得东西很随意,在这种时候,让自己的文字顶着一个虚拟的名字流行,既安全,又惬意。至于为什么要把笔名起得别出心裁,可能也是因为“产品”如同流水线,要混“脸熟”、显个性,只好打笔名的主意了。
谴责小说的作者多是科举不太顺利的南方读书人,走仕途无望,攀洋务无门,能够自恃的,就是自小炼就的制艺和诗赋工夫了。文人心情不好的时候,看着台上操持权柄的人,气就不打一处来。甲午战后,上海成为中国新闻出版业的中心,这些失意读书人这才发现“天生我才”的用武之地,纷纷聚集沪上,或做自由撰稿人,吃百家饭,如吴趼人;或自立门户当老板,开作坊式的报刊杂志社,自弹自唱,自产自销,如李伯元和曾朴。由此构成“海派”文人下海经商的一景,年轻的小说家沈从文后来从内地到上海时也看到了这一景,他将这一景总结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18)
所谓“商业竞卖”,就是要把文字变成钱,这是对“君子不言利”的传统文人做人准则的挑战。从鲁迅所提到的三大“谴责小说家”来看,他们都顺利度过了这一难关,迎合“时人嗜好”,并不构成他们写作的心理障碍。他们既是自由撰稿人,同时也是商人,李伯元就是在商言商的行家,他直接委托有实力的商人推销自己的著作:
拙作《官场现形记》初编、续编各一部,祈赐教为幸。另初、续各编各个五部,《夺嫡奇冤》十册,寄存尊处,倘同人中有欲阅者,便乞销去。琐琐奉渎,不安之至。(19)
吴趼人的手法更直截了当,以自己有影响的笔,直接给商家写广告小说,当然容易被人误会、受人谴责。其实当时很多写手都接做类似的“订单”,“同时日报主笔如病鸳、云水、玉声诸君,且受庸药肆剧场,专事歌颂”。(20)
这样比较下来,曾朴的文人气最重,哪怕是身在商海之中,也得保持文人的脸面,所以他的策略是以小说的内容取胜。以他的经历,写翰林院名流的故事最得心应手;以他对法国历史和文学的熟悉,将“清流”与西方的政党挂上钩,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此时国内政坛初具政党形态的各种名目的“学会”蜂涌而起,“党”更是个时髦的字眼,给“清流”换上“清流党”的标签,自然是一种很应时的选题策略。(21)
曾朴《孽海花》出版的效应,除了前面提到的林纾和辜鸿铭,还有众多的私人笔记作家。那个时代,“谏书”和“御史”最能歆动读者的神经,而晚清有关“谏书”和“御史”的最精彩篇章就是“清流”。因为笔记的“纪实”特征,其销路后来居上,出版社不失时机地大力推出笔记作品,心急处,根本顾不上历史事实。民国著名报人和掌故家徐一士曾在报纸上揭露过一家发行小说的杂志社匆忙炒作晚清笔记的事情:
《归里清谈》著者为山东潍县陈氏。……惟其名为何,尚有疑问。书由上海小说报社印行。封面标题‘谏书稀庵笔记’并署‘清御史陈庆淮著’。盖欲藉‘谏书’‘御史’字样,号召读者,而于其名似未及审。(22)
《谏书稀庵笔记》的作者实际上是陈恒庆,其前言中署名为“谏书稀庵主人”,这是那个时代平常而典型的一个笔名。该书完成于1917年,这正是笔记体的晚清故事被炒作得昏天黑地的年代。陈氏光绪后期在翰林院任职,本人没有什么名气,也不见得自己要炒晚清逸事谋取名利。文人习性,晚年总要留下点文字。既然是东拉西扯的笔记,所以老老实实地取名为《归里清谈》,名副其实。但出版商要哗众取宠,不仅改人家的书名,还要包装作者的身份,匆忙之中,将作者名字也搞错了。
出版商的策略其实很简单:哪怕扯不上“清流”这一话题,至少也要搭上词臣台谏的边。只是那时出版商、编辑的胆子和想象力都还不够大,否则早就给这类笔记挂上“纪实”、“隐秘”之类的幌子了。到了民国时期,新闻出版行业已经催生出了相当数量的、类似当代社会的“自由撰稿人”和“专栏作家”,他们是爬格子的专业报人,是靠稿酬养家糊口的。(23)他们比曾朴一辈更加具有商业化的眼光,反过来说,他们也更加缺少政治倾向。从民国20年代起到40年代,报刊出版业内出现几位明星大腕级的掌故家和专栏作家:
比如胡思敬,江西新昌人,曾在宣统和张勋复辟的清朝里做过御史,入民国后,虽有遗老的味道,但终究是掌故家。他在1911年写道:
江西人向无党援。道、咸之交,陈孚恩、万青藜、胡家玉同时在高位,皆被人挤陷,一仆不再振。青藜既长六卿,与户部尚书董恂皆有协揆之望。李鸿藻后起而秉枢政,忌两人资望在先,嗾清流党攻之。(24)
这是一江西版的“清流党”场景:时间、人物、缘由都与光绪中期翰林才子的事情风马牛不相及。仅仅是因为民国时期大家都在讲“清流”,于是这位出身江西的胡老夫子大笔一挥,就想象出了这出江西人遭“清流党”攻击而一蹶不振的故事。在同一部书里,胡氏还给出了其他版本的“清流党”图景,容稍后再叙。
比如刘体仁,安徽庐江人,淮军重要将领刘秉璋之子。兄弟四人中,唯他淡泊于名利,民国时期拒绝与袁世凯合作,弃官回家闲居。他写书是为了排遣时间,与炒作无关,但他也使用“清流党”的标签。估计该书在1916年前后面世,因为书中有犯忌之处,出版时有所涂删。如同该书名所揭示的,作者描述的“清流”场景的确令人惊“异”:
相传公子霭卿部郎清流党人也。
张霭青观察南城谓之清流靴子,讥其比之于腿犹隔一层也。又谓为捐班清流,而乃翁靖达为诰封。清流以善与诸名士交而有是称。
有张某为之奔走传观者,呼为清流腿,其依草附木者,则以清流靴子呼之,意谓较之于腿犹有间也。因而有赀者为捐班清流,有佳弟子者为诰封清流。由是互相标榜,以跻显贵。既有捷径,则人莫不趋,党徒之众,固其宜矣。
醇邸隐握朝纲,礼遇文士,以要时誉,开当时词臣言事,清流结党之风。(25)
这位霭卿公子是刘体仁的密友,大名张华奎,京城有名的“高干子弟”,其父乃淮系大名鼎鼎的张树声。张树声的出身与刘坤一相似,靠军功而得高位,在翰林名流面前比较心虚,需要“罗致清流”,但张树声的老辣之处在于,自己躲在幕后,让儿子鞍前马后地与“清流”人物套近乎。刘体仁虽不趟这混水,却从好友处听到了不少“清流”故事。他叙述的“清流”,实际上是张华奎的版本。他本人无意夸大捏造“清流”,但他却缺乏判断,罗列了不同的“清流”传说,而且他不能免民国出版界之俗,接受了“清流党”的标签。
比如徐珂,浙江杭州人,上海商务馆的编辑,既是学者,也是著名的专栏作家,20年代他在上海的报刊上写道:“比甲申之役,张佩纶等并得罪谴去,当时清流党大受掊击,几尽于绝。”(26)
比如徐一士,江苏宜兴人,原名徐仁钰,一士为笔名,其兄即笔名为凌霄的徐仁锦,两人都是民国时期专业的新闻从业者。士家大族出身,支持戊戌变法的徐致靖、徐仁铸父子分别为其叔父和堂兄,从1910到1940年,徐一士都是靠稿费维持生计。他写道:“光绪初年,(陈宝琛)与之洞及张佩纶宝廷等同为清班中最以敢言著者,……时称清流党焉。(27)
当时两位最好的掌故家和两位最好的专栏作家,都给“清流”贴上了“清流党”的标签,是不慎被骗,还是有意随俗?恐怕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以他们的阅历和学识,绝不会分不清“清流”和“清流党”的区别。而之所以随俗,原因也很简单,“和时人嗜好”、迎合读者而已。小说家和掌故家联手,用“清流党”的标签替换晚清时代的“清流”称谓。现代媒体初试锋芒,其最大的成功,似乎不是舆论的监督,而是商业的炒作。
三 清流党:朋党与政党
前面列举的辜鸿铭版的“清流党”标签说明,并不是所有的借“清流党”说事的人都是为了商业利益而炒作。清末民初现代政党的诞生,党派纷争而形成的南北对峙的格局,也刺激了一些衣食或无虞或有虞的官僚政客的写作兴趣。所谓借古讽今吧,这些人从晚清的“清流”故事里,不仅发现了党争,而且发现了党争的源头,即党派,而形成党派的源头呢,是地域,是乡党。于是,南人和北人,南党和北党,就成了“清流党”故事的主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晚清的“清流党”故事,而矛头所指,则是民国时期的党争现实。
前面提到的胡思敬,就在其1911年完成的笔记中两次详细演义了南北党格局下的“清流党”故事:
光绪初年,台谏词垣弹章迭上,号为清流,实皆鸿藻主之。……南皮张之洞、丰润张佩纶尤为鸿藻所器重。……鸿藻引拔多直隶同乡,世称为北党。迨翁同龢、潘祖荫出,南党稍稍盛,然视二张声气,不及远矣。
是时朝臣分南北两党,北党主驳,以李鸿藻为首,孙毓汶、张之万、张佩纶等附之。南党主准,以潘祖荫、翁同龢为首,孙家鼐、孙诒经、汪鸣銮、李文田、朱一新等附之。(28)
这一版本与前引江西版的“清流党”版本一样,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但耐人寻味的是胡氏演义“清流”故事的现实背景。胡思敬是南方人,自然心思向着南方人,李鸿藻的“北党”令人想到袁世凯的“北党”,北人的强势最终导致了清朝的灭亡,作为参与了张勋复辟的清朝遗老,胡思敬说的是晚清的“清流党”,而其锋芒所指,当然是民国的现实政治。
与此相映成趣的,还有另一个版本的“清流党”:
当时京师人士呼李鸿藻为青牛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29)
不用猜,该文的作者也是南方人,因为只有南方某些省份的人声母L和N不分,所以只有南方人会将“清流”化为“青牛”的谐音加以讥讽。作者刘成禺,湖北江夏人,早期兴中会成员,1904年奉孙中山之命,赴美国办报。民国后任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虽然他与胡思敬的政治倾向截然相反,他却有着与胡思敬相同的南方人的噩梦,那就是南北党争中南方人的失败。作为湖北人,作为孙中山的战友,这一惨痛是其它省份的革命者们无法比拟的。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刘成禺也喜欢从南方人北方人的角度演绎“清流”故事:
自同治末迄光绪初,此数年间,乃为南北清流发生最大摩擦之关键。闻之樊樊山曰:“南派以李莼客为魁首,北派以张之洞为领袖,南派推尊潘伯寅,北派推尊李鸿藻,实则潘李二人,未居党首,不过李越缦与张之洞私见不相洽,附和者遇事生风,演成此种局面耳。”(30)
除了南北党,就是“清流党”,民国一开始,“清流”故事的基调就确定下来了,而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故事的,多是南方人。比如易宗夔,湖南湘潭人,是追随梁启超的维新派人士,1898年在《湘报》上著文,主张西化,被昔日“清流”、时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斥为“杂种”。后公派赴日学习法政,与宋教仁过从甚密,民国时期先后担任省议员和法制局长。他眼中的“清流”是这样的:
同光之间,张香涛、张幼樵、邓铁香、刘博泉、盛伯熙、陈伯潜、宝竹坡等,直言敢谏,封奏联翩,京师目之为清流党。(31)
兼有官学双重身份的黄濬,福建侯官人,民国时期以文字得以交结梁启超,梁任财政总长时,黄为其秘书。后又得到汪精卫的赏识,被召往南京行政院担任秘书,1937年因涉嫌通日而被捕杀。这位才子的文名远远超过其政治声誉,因而受到同乡、“清流”前辈陈宝琛的器重,结为忘年之交。他最爱谈的晚清掌故就是“清流”:“四谏,即清流党,以光绪初年始盛。”(32)
还有以笔名小横香室主人写就的《清朝野史大观》:
吴县潘祖荫,宗室宝廷,南皮张之洞,丰润张佩纶,瑞安黄体芳,闽县陈宝琛,吴桥刘恩溥,镇平邓承修,尤激昂喜言事,号曰清流党。高阳李文正公当国实为之魁。(33)
还有小官吏耳食的更加稀奇的“清流党”版本,比如欧阳昱,江西宜黄人,没有进士头衔,也不曾在京师当过官,最高的官衔是个州判,他听到的“清流党”实际上是以在京师的居所划分的:
同治,光绪间,御史翰林参劾内外官,声名赫赫者,有陈启泰,孔宪谷,邓承修,张佩纶,陈宝琛五人,时称为“五把刀”,又加张之洞,周德润,何金寿,黄体芳,内尚有一人,予忘之。共五人,为十友。俱住南横街,人目为“南横党”。(34)
还有其他的说法,以致抄来抄去,民国时期的“清流党”故事多有相似雷同之处:比如恽毓鼎的“清流”版本与小横香室主人的说法如出一辙,夏仁虎重复着曾朴的“李慈铭故事”,还有许多笔记作者干脆将笔名叫做“佚名”,更加放心大胆地编造和抄袭“清流党”故事。(35)
除了政治影射和商业炒作,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出来澄清一下“清流”的真实情况?当然不是。就在曾朴发表其小说《孽海花》的同一年,就有人讲述没有丝毫“党”的影子的“清流”。这个人就是以满族贵族世家自诩的震钧,他庚子后为清廷县令,进入民国则蛰居南方,颇有遗老的风韵:“今夏伏处江干,日长无事,……追溯旧事,正不异玉堂天上之嗟。呜呼,昔日之笑歌,所以酿今朝之血泪也。”其中多处写到了“清流”:
方光绪初年,京师士夫以文史,书画,金石,古器相尚,……当时以潘文勤公,翁常熟为一代龙门,而以盛王二君为之厨。顾四方豪俊,上计春明,无不首诣之。即京师人士谈艺,下逮贾竖平准,亦无不以诸君为归宿。
当光绪甲申越南事起,枢臣多不主战。于是廷臣交章极谏,盛祭酒昱劾枢臣尤力,众知事必有变。
未几诸言臣蔚兴,人皆以名臣自期。及癸未张幼樵编修佩纶以庶子暑副都御史知贡举,而清议益重。后生初学,争以清流自励。(36)
对满清的感情不同,写书的目的不同,所展示的“清流”景象也迥然不同。震钧眼里的“清流”,只是一段词臣建言的普通历史,它不涉传统的“党议”,更无现代政党的踪迹,他所使用的“清议”和“清流”的字眼,也就不涉褒贬。
另一位蒙古族贵裔出身的崇彝也讲到“清流”。他是咸丰年间因科场案被杀头的大学士柏葰的孙子,光绪时期一直在户部和吏部做小官,默默无名,以致其去世的年月也无从考证。其笔记中记载到了民国16年的事情,故可断定该书的出版是在1927年以后。他眼里的“清流”是这样的:
东四南豹房,胡同内有一古刹,曰法华寺。其住持僧名德云,字静澜,本热河承德人。当咸丰末驻跸热河时,德公与肃顺交甚好。迨肃获罪,始遁入京师,住持此寺。能作大字,颇通文墨,喜交文士,与予兄星搓交最稔。当甲午以前,续筱泉邀八旗名流讲学此寺西偏海棠院,所邀之主要人,有震在廷,恩席臣,光裕如及星搓兄诸人,颇有清流之目。
荣文忠公,姓瓜尔佳氏。初为工部郎,后改道员,复用为京堂。同治初,设立神机营,恭醇二王以其将门之后,荐为管理大臣,不十年升工部尚书。当年有清流之目。(37)
这完全是另外一幅的“清流”人物图,确切地说,这是一幅纯粹的满族“清流”图。如同震钧一样,崇彝是以遗老的心态怀念失去的光荣和梦想,其落笔的重点是自然是本族的人与事。这里所罗列的满族“清流”名人,其实出道很晚,获得进士都在中法战争之后,他们根本就没赶上全盛时期的“清流”大戏。而毫无文学才情、靠镇压改良派而晋身的荣禄也被阑入到“清流”的行列,其理由,恐怕正如辜鸿铭说的,因为荣禄是“满族贵族中最后的人物”。(38)很可能是被民国时期“清流”出版热所触动,崇彝也要为贵族世家争取一点“清流”的光彩。尽管如此,他下笔还是有分寸的,那就是“清流”与“党”无关,不管这个“党”是传统意义上的“党援”还是民国时的政党。
同样是以遗老自居的汉族人,即使是讨厌翰詹名流,也有人实实在在地在追忆“清流”,比如陈夔龙:
吴江病逝,高阳柄政,意在延纳清流,以树羽翼。南皮张香涛阁学、丰润张幼樵侍讲、宗室宝竹坡学士、瑞安黄潄兰侍读,均以清流自居,慕东汉士风,……当时清流横甚,文正亦为所挟持,声望顿为之减。(39)
已经将“清流”与东汉的党祸相提并论了,但陈夔龙并没有把“清流”归置于朋党之列,更没有将其与现代政党混为一谈。这是尊重历史的态度,其内容的可信度,还可以晚清重臣王文韶的日记为佐证。光绪三年至八年(1877-1882)王文韶正好在京任兵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行走,他在此期间多次记到“清流”人物,他与李鸿藻和翁同龢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但他叙事平实,一字不涉“清流”。(40)与其说这反映了他的“琉璃蛋”政治操行,倒不如说表现了他的客观。只可惜他的《日记》一直躺在藏书楼里,否则倒是可以纠正民国谈论“清流”之偏。
想纠正民国时期谈论“清流”之偏的还有其他人。比如何刚德,1877年的进士,在北京当了19年的小京官。古稀之后,“退居无事”,从1916年起陆续写稿,分别于1922年完成了《春明梦录》, 1934年完成了《客座偶谈》,其中都涉及到“清流”:
光绪初年,翰林渐拥挤。而简放学政试差,军机大臣偏重门生,不无可议。而怀才不遇者积不能平,遂因法越开衅,归罪枢臣,交章指斥朝政,人目为之清流。
清流之起也,或云李文正与同值意见不合,恭邸不无左右袒,势孤无援,清流从而赞助之。
光绪甲申,法越肇衅。讲官张佩纶宝廷诸人,相约弹劾权贵,操纵朝政,时人目之为清流。
清流之起,人多疑其挟私意。然其激于义愤,志在救国者,往往而是。(41)
无论是震钧、崇彝,还是何刚德,他们在前朝都是芝麻官,“余生也晚”,没赶上亲睹“清流”的政治悲喜剧,虽然他们所叙述的“清流”故事也是耳食来的,但下笔尚属慎重,有一说一。其原因,除了遗民心态,还是他们的写作目的,不是为了赚稿费,也没有党派成见,而是为了“自成为一家言”,书成之后,友朋叫好,经不住怂恿,才“属诸手民”(42)的。可惜有他们这样心境的笔记作家太少,而他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又太小。在商业炒作和政治影射的双重夹击下,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了。而甚嚣尘上的,反而是不太严肃的演义式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写作抵不过历史编造,并不是当代文坛才有的现象。在一个缺乏公共空间和公众舆论传统而最不缺乏历史影射传统的国度里,不期而至的舆论自由带给人们的,恐怕更多的是“公开的私议”,而这种私议更容易修改历史、混淆视听。“清流”变为“清流党”的过程,便是一显著的例证。
注释:
①“清流”称谓变化过程的考证,请参见拙作《谁是“清流”?——晚清“清流”称谓考》,《史林》2005年第3期,第 8-14页。
②曾朴:《孽海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5-36页。
③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4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④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页。这一表白的时间是1934年。金松岑在1904年为自己的作品所撰写的广告中称《孽海花》为“政治小说”。见前引书,第134页。这说明他30年来的想法是一致的。参见郑逸梅:《梅庵谈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⑤参见时萌:《曾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⑥前引魏绍昌书,第131页。其实早在1905年小说林社第一次出版《孽海花》时,已经改称为“历史小说”了。参见前引书,第134页。
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页。
⑧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从这一点出发,阿英先生觉得《孽海花》的思想性超过了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⑨郑逸梅:《文苑花絮》,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2页。
⑩(11)(12)前引魏绍昌书,第142、135、129页。
(13)辜鸿铭著,语桥译《清流传》,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1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1页。
(15)辜鸿铭在1910年完成的另一本笔记体著作里反复以“清流党”来指称中法战前建言的翰林。见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157页。
(16)这里借用了欧洲“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概念,用来表述西方意义上的新闻报刊业在中国的发展。欧洲公众舆论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简言之,它的早期含义是“公开的”,“非秘密的”,如中世纪的司法审理过程。16世纪,它又带有“国家事物”的含义。17世纪,它被打上了“市民空间”的烙印,如英国的咖啡店和法国的沙龙。接着出现了早期的报纸,但它还只是商人们交流商业消息的载体。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开启了公众舆论的新纪元,卢梭说,任何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到19世纪中期,公众舆论在许多欧洲国家发展成为“第四种权力”,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现代公共舆论由此诞生。按照我的理解,欧洲19世纪中期以前的公众舆论,属于“前公众舆论”,即依附于国家权力之下的有限的言论表达自由。这种“公众舆论”在中国王朝体制下也是存在的,Stefan Maedje在这一框架下研究了南宋王朝的“公众舆论”。(参见他的博士论文《书院:朱熹学说和南宋时期的公众舆论》,Akademien,Die Zhu-Schule und die Oeffentlichkeit der Suedliehen Song-Zeit,Hamburger Sinologische Schriften,第5辑,2002年)Mary Backus Rankin在其研究晚清史的论文中借用了“公众舆论”概念,她认为,19世纪初,中国王朝体制内已经存在着“公众舆论”,到19世纪中叶,发展成为独立于体制外的现代意义上的公众舆论(参见她的《“公众舆论”和政治权力:十九世纪晚期中国的清议》,“Public Opioion”and Political Power:Qingyi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XLI,No.3,May 1982)。晚清正处在从“前公众舆论”向现代公众舆论的转变过程中。
(17)前引鲁迅书,第282和294页。“其实这类广告文章,吴趼人所作也非仅此一篇,在上一年(一九零九)吴已为南洋华兴公司出品的‘燕窝糖精’写过《食品小识》一文。”参见魏绍昌编《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18)转引自《徐懋庸杂文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82页。
(19)见郑逸梅:《清娱漫笔》,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2页。
(20)前引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第17页。
(21)这一时期政党之风起云涌以及政党与报社之关系,可参见宗方小太郎《辛壬日记》和《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收在章伯锋、顾亚主编的《近代稗海》丛书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2)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见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636号,文海出版社,第224页。徐一士在其《近代笔记过眼录》里考证出该书的作者为陈恒庆,书商之所以张冠李戴,是因为只知道“清末言官有陈庆桂,而又误桂为溎,遂漫为题署,未免可笑。”见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937号,文海出版社,第33页。
(23)比如著名作家徐凌霄就是靠稿费生活,而且生活得非常好。他的儿子回忆道:“父亲的稿酬很高,上海《时报》的稿费,每千字大洋十五元,连同其他收入,每月有五百元左右。”当时顶级教授的月薪为大洋400元,可以买一幢小洋楼。参见许姬传:《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5页。
(24)胡思敬:《国闻备乘》,收在《近代稗海》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
(25)刘体仁:《异辞录》卷2,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20、23、29-30、44页。
(26)徐珂:《清稗类钞》(3),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158页。
(27)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405页。
(28)胡思敬:《国闻备乘》,收在《近代稗海》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9-250、279页。
(29)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收见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从刊》第717号,台北文海出版社,第90页。
(30)前引刘成禺书,第95页。
(31)易宗夔:《新世说》,收在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从刊》第180号,台北文海出版社,第36页。
(32)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页。
(33)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第2辑卷(下),台湾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4页。
(34)欧阳昱:《见闻琐录》,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57页。
(35)参见车吉心主编《中华野史》第14卷,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2页;第15卷,第5087-5088页。
(36)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4、71、131、177页。
(37)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2、40页。
(38)辜鸿铭著,语桥译《清流传》,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39)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40)参见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2、449、451、462、469、473、498、517、537、 541页。
(41)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上,第8、9页及《客座偶谈》卷1,上海书店1983年合订影印本,第11、12页。
(42)何刚德:《平斋家言序》,上海书店1983年合订影印本,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