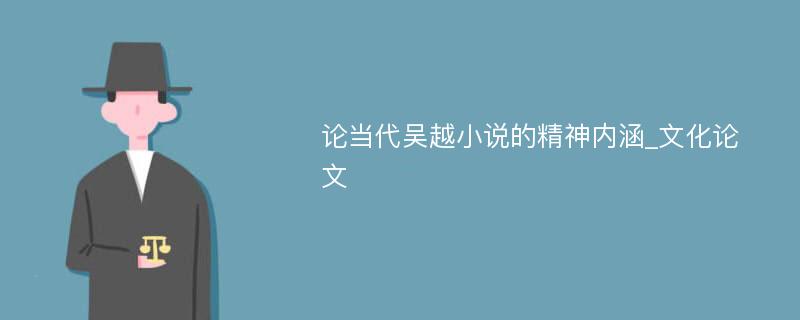
论当代吴越小说的精神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涵论文,当代论文,精神论文,小说论文,吴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对地域小说来说,仅写出地域的外在风貌特色,奇异独特的风俗习尚,是不能成其为大气象的。只有在时代发展中,努力去开掘特定的地域人心,写出构成特定时代地域文化特色的人的精神、灵魂和人格,也就是说,要去发掘民族文化精神的时代性地域性表现,思考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对于人的精神影响,并进而努力去开启能照亮人类心智的紧随时代发展的灵光。这样的作品,其主题内涵的开发,方能进入较高的精神文化品位。
无疑,有志于从事地域小说创作的写作人,不管是深入历史,还是审视现实,大都能以上述要求来作为自己的写作目标,以此去显示小说独到的精神文化追求。尤其是当这种独特视角的文化选择,一旦成为当AI写作作人有意为之的一种小说的精神意蕴的指向的时候,他们的笔触显然早已不满足于仅仅局限在对于政治、经济等社会文化学层面的思考,而常常是自觉去尝试从文化哲学、生命哲学,或人本哲学等新视角去观察和把握生活,创作中已明显地渗透着写作人自身的哲学观念和美学理想。正是这种特定内涵归向的文化开掘,使得新时期(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地域小说,较之以往的乡土小说、都市文化小说、市井风俗小说等在审美追求上有可能进入到一个更为深广的审美领域。
那么,作为我国地域小说中一种特定文体形态的吴越小说,其所包容的精神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吴越小说家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心态去开掘、思索和表达这些精神文化主题的呢?笔者以为,要而言之,当代吴越小说的精神文化主题开掘,主要是侧重在反映这一方域由古老的农业文明向先进的现代文明转化、融合、蜕变过程之中的种种人生情状,以及对于这种生存状态从各个角度的审视和反思。一些假托历史之作,其实也是从一种新的特定的立场对吴越文化传统的一种回视和审察。其中所透发的精神意蕴,常常是在对于理想家园的怀恋和追索,对于传统演化的情感态度,和对于人格精神的自度自审之中得以曲折地传递出来。这是一种通过写作人之笔的曲折传递,因而,在发掘、思索和评价吴越民人的人生情状和精神归趋之时,也流露出吴越写作人自身的精神归向和文化心态。
一 在家园怀恋中追索理想人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特定地域环境和文化传统之中成长起来的本土之子,对自己的故乡总怀有一种牵扯不断的依恋之情,尤其是当他们离乡背井寄居他乡,故乡之地就更是他们心中最值得挂怀之处。当然,这种怀恋,除了对乡土风情习尚的记忆外,更主要的还是无法忘怀故土的人情,以及由人情、风情、风光、习俗等所构筑起来的特殊的精神文化氛围。
在这样的文化情感背景之中去考察吴越小说创作中的一些怀想家园之作,我们看到的也就是与上面的表述大致相似的情况。
汪曾祺在小说集《孤蒲深处》一书中所收进的一批所谓“高邮系列”的“怀乡”小说,大都成文于80年代初期以及以后一段时间。当时,新时期文学尚沉浸于一片浓浓的“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氛围之中,而这批小说却透过对于高邮乡镇旧事的记忆,以一种恬淡平静、和谐温馨的“田园牧歌式”的抒情笔法,和“天国仙境般”的梦幻情调,抒发着他所追索的一种空灵闲适、清新超脱的儒雅境界和浸透着东方灵性之气的健康人性。虽然,乍一看来,这些作品和同期文学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似呈现着一定的离心倾向。但是,就在这样一种以雅致、灵动的笔触而艺术地写出家乡生活的往日情韵中,寄寓着作者对于人生和情操美好的理想追求。透过这些小说还可以进一步看到,作为长期生活在京都大城市的汪曾祺是把故乡民人那种淡泊自然超脱功利的生活境界,视为自己所要追索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的。可见,与城市文化相比,他还是比较愿意亲近故乡的那种特定形态的乡村民俗文化。而这种对于农业文明的依恋和认同,其实,也正是曲折地反映出了他对于喧嚣的快速变化着的城市文化的不适应和自觉逃离的倾向。再进一步看,这种倾向的出现,也可以看成是地域文化的历史积淀对作家的精神气质内在结构进行规约的一种表现。
“矮凳桥系列”是林斤澜在80年代回温州家乡探亲之后,记叙对故乡的印象、感觉的一组系列小说。从作品看,林斤澜感兴趣的显然并不在故乡现实的改革生活,而是情有独钟地发掘家乡生活中特有的种种情韵,写他在重游家乡时所发现的乡情和乡趣。正如有论者所说,在这一系列中,作者是以“情趣”取代了主题。这在《溪鳗》等小说的描写中是有着明显表露的。
如果说,汪曾祺和林斤澜在他们的怀乡之作中,主要是通过家乡民间文化的再现,来传达他们所追寻的理想人生的话,那么,在叶文玲的小说《长塘镇风情》和《浪漫的黄昏》等作品中,虽然也都是她思乡恋乡意绪的一种结集,也均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了她对于家乡社会民俗文化形态的认同和赞美,但在具体描写中,叶文玲则努力将时代气息和整个社会衍变的信息,融入到她的怀乡题材之中,借乡情的抒发,乡风的描绘,把家乡之地的人文精神作为她人生理想的一种参照,从而去完成她的求善、求美、务实的主题旨归。因此,在她的小说中,表现出了较强的现实功利性和理性思维色彩。但是,和汪、林两位共同的是,叶文玲所要寻觅的理想人生,依然没有跳出对于家乡乡镇生活中的一些美好的记忆,她在衡量真善美时所选择的标尺,仍然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精神要义。从小说中可以看到,她虽然有着要走出乡土而去寻求新的理想人生的热情和愿望,可是,她显然是并不习惯于都市的。
因此,无论是汪曾祺、林斤澜还是叶文玲,在小说中都是以巨大的热情在怀恋着自己的家园,并在对家园的记忆中追寻着各自的人生理想。尽管他们的追索各有侧重,追寻理想的抒情方式并不相同,在内涵掘向和外在表达上也各有特点,然而,有一点都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之所以对于“家园”有着不尽的怀恋和无限眷念,是因为在情感上都是基于对乡村情感的一种自觉的认同,对传统文化积淀的一种自觉认同。这也许正是吴越小说作家在创作上的一种内在趋动和旨归。
二 以感伤情怀面对尴尬的传统
从上面例举的汪曾祺、林斤澜、叶文玲们的创作情况中不难看到,当他们透过“家园”故事而去追寻各自的理想人生之时,他们写作中的内在情绪大都是乐观的。但吴越小说的创作并不都是在一种乐观、平静、充满期待的心态意绪之中行进的。在更多的时候,特别是当写作人的笔触指向传统的终结,深入历史的变革之时,由于传统文化在处于终结状态时所显现出来的种种尴尬相,由于历史文化在面临裂变的过程中所呈现的痛苦和艰窘,常常使得具有现代意识的当AI写作作人会在内在精神上显现出抉择的艰难和评价的困惑。
虽然,在现代目光的理智注视中,吴越写作人无疑是看到了处于终结状态的传统的尴尬和走出尴尬变革观念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然而,作为从传统文化的教育、薰陶之中“过渡”过来的本土文化之子,留落在他们身上传统文化的种种积淀,以及他们对于历史文化情怀的自觉参与和沟通,又使得他们在情感上对于处在尴尬状态的传统文化不无留恋和依从。因而在创作中会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不同程度的伤感情怀。即便在上述汪曾祺、林斤澜们的作品中,在温馨的感觉背后,仍然是可以读出隐于故事深处的某种悲凉和忧患意味的。只不过是生活的淡泊超脱,使他们在传达忧患之时,采取了一种较为隐蔽的方式而已,心灵上的某种忧伤和痛苦,常常是被一种精神的自娱所超越了。而事情到了年轻一代作家的手里,情况又有所不同了。在叶兆言、苏童那里,由于他们在参与历史文化情愫之中在心智能力上的种种默契,对于处于尴尬状态的历史传统的伤感情怀,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心理世界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实在就是一种历史伤感情怀的承受者和表述者。这一点无论在叶兆言以“幽默”笔调所描述的一组“江南名士”历史情状的“夜泊秦淮”系列中,还是在苏童的以“抒情”笔调所写出的“江南佳丽”群象的《妻妾成群》等一批小说之中,都是有着充分的表露的。当他们的笔触探向源远流长的江南士大夫文化之时,他们不愿看到但事与愿违地发生着濒临终结的历史传统的种种尴尬景况,于是,种种凭吊的心绪,伤感的情怀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油然而生。
但是,笔者以为,仅仅指出这种历史的感伤情调在叶兆言、苏童们作品中的存在,似乎还不足以揭示出他们“钟情”于“历史情状”的全部情感内涵。作为一代理智的当AI写作作人,当他们在传达对于历史文化情愫的心智体验之时,在他们以“挽歌”的格调所写出的旧时代文人充满“死亡”文化意味的“精神形象”中,以及对于江南旧女子寻求“死亡”生活的“本真韵致”的传递之中,其所包涵的精神内涵,显然不会仅仅是写“趣味”、写“情态”和传达“伤感”。在这里面,还有着另外一番思考与寄寓。其实,这种对于处在终结状态的传统的尴尬行状,以带有一定喜剧色彩的“挽歌”形式的“唱出”,在笔者看来,其本身就是包含对于酸腐、悖时、尴尬、错位的文化生态的一种批判和否定。当然,这种批判和否定又与留恋和依从掺杂在一起,因此,从中流露出的创作主体情感也并非单一,而是一种错杂浑和的感情。
较之于江南才子们面对历史文化的种种尴尬而表露出来的复杂的一言难尽的感伤忧郁意绪来说,有着山东血统的越地作家李杭育在评判处于变革之中民俗传统文化中的种种悖时行状时,他的心智归向,虽然也不无忧患和伤感,但显然较之前者要表现得理智得多。
应当说,从创作“葛川江”系列小说起,李杭育才开始具有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他后来的一系列创作实践,也证明了他就是要通过“葛川江”系列小说的创作,从张扬吴越民间文化的角度,来实现对于儒家规范文化价值观念的一种否弃,从而去寻找和铸造他所理解的中华民族的精魂。他在小说中创造出了一群“最后一个”的代表:“最后一个”渔佬儿、“最后一个”画屋师爹、“最后一个”弄潮儿等等。这些人都有过光荣的、值得自豪的过去,但是随着时代的变革,旧的生存手段失去了原有的效用,旧的价值观念逐渐遭到社会的遗弃,从前令人尊敬的人物如今却一个个沦为多余之人,受尽奚落和歧视。面对着“最后一个”们在逆境之中不消沉、不悲观、敢作敢为,敢以倔强的执着来证明自身价值的努力,李杭育的心情显然也是复杂而不平静的。他赞扬和同情他们的刚强和不屈,同时,也为他们不愿趋从变革的悖时和执拗感到惋惜和忧虑。作为一个理性的现代文化人,李杭育显然是赞同于变革的必要和合理的。在这个小说系列中,对应于“最后一个”的人物形象,他还满腔热情地创造了一组“最早一个”的人物群像就是一个证明。尽管对于“最早一个”们的“改革”(如“船长”的所作所为),他是运用了一种调侃的笔调,但是,看得出这是一种善意的讽喻,对于他们自觉地更新观念,他显然是表示赞同的。然而,李杭育确实又对于美好的“旧事物”的消亡而表露出怀恋和忧伤(这从几篇小说带有伤感情调的结尾中可以看出)。而这种复杂情感状态,在李杭育的小说中又似乎被一种中庸的立场掩盖起来了,从而使得情感的波动和理性的思索有机地交融在一起,能有效地激起更多持不同价值尺度的人们的共鸣。同样是面对着传统文化的尴尬行状,较之叶兆言苏童们以伤感情调掩盖了沉重的思索,在李杭育却表现出充满理性思索之中的忧伤情怀。
尽管在情感流露之中感性化和理性化的程度有所不同,可是有一点还是不难看出,那就是:无论在叶兆言苏童们所创造的历史图景之中,还是在李杭育所描绘的变革时代的现实情景之中;无论是在叶兆言苏童对于陈旧、颓败的“死亡”生活的追问里,还是在李杭育对于悖时或“创新”镜头的摄录之时,在作品之中无一例外都是流露着他们对于人类文化生存行状的一种关怀之情。他们都看到了尴尬的传统对于历史发展的阻碍作用,看到了变革是促进社会文化发展前进的一种必然。因而,尽管从情感上有着这样难以割舍的依恋和怀念,可是,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改变尴尬的行状,走出孤独的局限,改造社会的生态,始终是顺应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种顺应和改造是否能得以实现,其关键之点就在于每个人自己的身上。
相对于叶兆言、李杭育而言,像陆文夫、高晓声这样年长一辈的作家,尽管在气质上和这些年轻人还是有着较多共通之处的,然而,由于阅历和观念上的某种差异,决定了他们在面对传统尴尬之时,所采取的往往是和年轻人偏于感性化的写作态度有所区别的情感立场。他们的写作思路相对比较质朴和单纯,他们的创作旨意更多地会去关注文化表现中的某些社会现实层面。因此,无论是陆文夫的小巷故事,还是高晓声的农民故事,他们常常会以“客观”地“写实”而去隐匿主体情感的抒发,以理智的传达来抑制情感经验的表现。但是,由于创作主体内心趋从于既认同革新又难舍传统的双重情感愿望,所以仍然使这些“喜剧”故事中带出了一种苦涩和伤感的意味。而他们的理性批判意识,也就在情感的含蓄表露中得以巧妙地传达出来。
三 文化人格展示中的偏于自我迷醉
如果说,吴越作家通过对“家园”的眷念和怀恋而去追寻理想人生之时,在作品中主要是表现出压抑了悲剧意识的一种乐观意绪,而当他们面对着尴尬的传统时,不由自主地在意识到改造必要的同时,却又难免抒发出种种依恋和怀旧的忧伤情怀的话,那么,当他们通过作品去追怀和展示吴越文化熏陶下所形成的充满地域特色的文化人格精神的时候,他们在内在情绪上似乎是表现得充溢着抒情色彩的自我欣赏和自我迷醉有余,而客观冷静的理性自审则相对不足。
所谓地域的文化人格,当是指在地域文化积淀和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地域民人的群体和个体的精神特征。自然,由于地域文化积淀和影响中正面和负面的各种效应,所形成的地域性精神特征也应是优劣杂存好坏都有,并且并非一成不变的。就吴越地域来说,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积淀,加之历史上中原文化的多次入侵和揉合,以及湘楚、闽粤等文化旁敲侧击的种种影响,再又是现代文明对于地域性文化精神的巨大强烈的磨合作用,这些均使得吴越地域的文化人格精神既表现出一定的地域个性,同时也呈现着多元和复杂的色彩构成。在吴越小说中,有不少作品就成功地展现了这种独特地域的人文色彩。比如,陈军的《玩人三记》,就是通过对一个“半人半仙”式的“玩人”形象何梦的描写,通过对他参悟了世态炎凉、人间沧桑之后所采取的一种飘逸达观的人生态度的描绘,成功地显现出了从古老的吴越文化之中升华出来的一种超脱物役的文化人格。这种人格精神,根出于吴越之地的一些共有的精神特点,与吴越文化中某些逍遥快乐的精神物质相沟通。如果说,在《玩人三记》中,陈军对于吴越的逍遥飘逸精神一面,作了一次人文意义上的注释,那么,他在《清凉之河》、《禹风》等作品中,则是为至今尚流淌在现代越人血脉之中的坚韧、苍凉的古越精神的遗传因子,作了一种生动的阐发。陈军的努力,目的很显然,那就是要证明:尽管杭州作为越中之地,民风因经“南宋遗风”的侵扰而变得柔靡而奢侈,然而,代表着古越文化精神的刚毅、坚强的文化人格,依然未在这一方域完全灭绝,在建筑师张园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搏击、惨淡经营、献身进取、坚韧不拔等精神品格,正是古越文化人格在当代延续的一种体现。
成功地展示吴越之域文化人格的优秀之作,还可例举出王旭烽的《南方有嘉木》和叶文玲的《秋瑾》等。然而,相对于这类褒扬吴越优秀文化人格的作品,我们却很少能看到对于地域文化人格中某些劣质精神表现的深刻剖示。事实上,地域文化人格的形态表现是很复杂的,其精神内涵的构成也绝非单一。常常在不同的侧面上,有着其正负价值的不同体现。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其人格精神的体现,也可能是多层次多侧面的。而且审视目光和情感态度的不同,又可以对类同的人格形态表现方式,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因此,我们期望写作人要尽量跳出地域的和传统的某些情感局限,要能以一种清醒的理性立场去进行自审,这样创作主体才不致于看不到某些地域人格的负面效应,一味地沉缅于对地域文化人格自我迷醉和自我欣赏之中。我们在陈军的《东方闲情》和范小青、叶兆言等的某些作品中,似乎不同程度地看到了这种理性思索的暗寓。但是这类作品毕竟数量不多,而且对人格形态中劣质表现层面的批判的份量和深度,相对于写作人对于地方文化生存氛围的自醉和自赏来说,也显然是大为不如的。
因此,本土作家在创作中如果只局限在乡土情感的立场上,他就较难对本土文化提出深刻的批判。写作人如要对本土的文化生存在情感判断上持有一种冷静客观的理性态度,则首先必须要让自己的情感流向从地域性的影响和局限中摆脱出来。吴越小说在对本土文化人格形态的评价上,之所以自审意识相对缺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些写作人在情感归向上过多地对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甚至可以说是陷落于传统的阴影之中不能自拔。正是这样,在吴越小说的精神表现上,创作主体运用现代意识的观照和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是微妙地交杂在一起的。当现代文明以越来越快的节奏,一步步逼近当代人生的每一个方面的时候,为数不少的吴越小说却依然深情地驻足于往昔农业文明的记忆中流连忘返,对于传统文化的趋于终结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感伤的情怀,表现出一种保守的文化心态。当吴越写作人自以为是用现代目光去注视这片土地时,他们在实际上却还是常常以温情感伤,或者是自我陶醉来替代真正冷静理性的审视。
因此,吴越小说要克服小家子气,使其在精神内涵的开掘上,有一种更加恢宏深厚的拓展,作为创作主体来说:第一,必须要有一种从传统文化精神的局限中走出来的自觉性,更主动地实现从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的彻底转换;其次,要备有一付世界性的审察生活的目光,在审视和把握人生中从仅仅面对地域生存的窄小层中再跨出一大步,实现由狭隘的族意识思考方式向开阔宏大透视人类社会的类意识思考方式的转换。笔者以为,创作主体的精神状态只有处于这样的一种审美文化心态之中,才可以说是达到了开放自由的审美心态境界。
标签:文化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叶兆言论文; 汪曾祺论文; 李杭育论文; 叶文玲论文; 林斤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