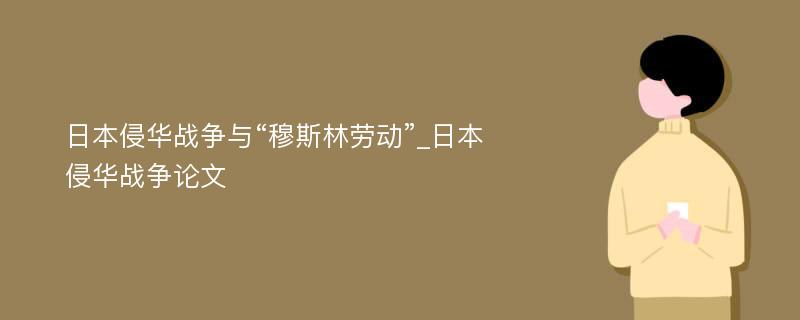
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教论文,日本论文,侵华战争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8年7月8日,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周年之际,日本政府“五相会议”①通过一份指导性纲领——《时局的发展与对支谋略》,确定了对华军事战略、政治攻势(如分化中国内部政治势力等)和加强在华经济掠夺以支援战争等加快侵略中国步伐的六条方针。其中的第四条为:“推进回教工作,在(中国——引者注)西北地区设立以回教徒为基础的防共地带。”②对于日本在战争时曾经推进“回教工作”一事,日本的历史学界几乎无人提及;而在中国的历史学界更是鲜为人知。然而,通过日本防卫研究所所藏战时日本陆军档案、日本外交史料馆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战时外交档案,可以清楚地看到:早在20世纪初,日本就已设想向中国的“回教徒”进行渗透,以为日后侵略中国所用。③而在发动侵华战争后,日本又具体制定并积极实施了“回教工作”。因此,搞清楚这一事实,不仅可以加深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本质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历届中国政府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过程中,尤其重视加强边疆地区居民以及有着其他历史文化背景的民族共同体之国民意识的原因。
一、日本关注中国“回教”的出发点
1890年代,有两三位在海外接触到伊斯兰教的日本人皈依伊斯兰教,尽管如此, 日本国内并不存在一个穆斯林群体。直到进入20世纪,日本才开始关注伊斯兰教。这种关注,与宗教信仰无关,完全是出于官方的,即外务省及军部的政治需要。1905年5月,一位名为樱井好孝的人,“接受外务省的秘密命令,到新疆至蒙古一带进行旅行和视察”,“行程约二万余千清里”。第二年12月回到日本以后,他就内蒙和新疆的地理位置、交通情况、居民成分、宗教信仰和商业等情况向外务省提交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④而从外务省于1906年1月16日向茨城县厅申请推迟对樱井好孝的征兵命令一事来看,樱井好孝应是日本外务省的属员。⑤另外,1910年,日本外务省的调查员中久喜信周,也对河南省的“回教徒”情况进行了调查。⑥
1913年, 日本关东都督府将其霸占地域划分为大连民政署管区、旅顺民政署管区、金州民政支署管区、瓦房店警务支署管区、大石桥警务支署管区、辽阳警务署管区、奉天警务署管区、抚顺警务支署管区、安东警务署管区,“按照神道、佛教、基督教、道教、回教之类”进行了详细的“宗教调查”。关东都督府为关东军的前身,担任其历任都督的都是现役大将或中将,但是从这项调查报告来看,在当时关东都督府所管辖的所有地域中,“回回教”的势力微弱,仅仅在金州民政支署管区内的“皮子窝所辖区内有一寺,几近毁灭状态”。⑦
1918年3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为有在库伦、新疆方面扩充情报网的必要”,于是使用“临时军事费”,⑧“在支那驻屯军谍报担任地域内分别设立谍报机关”,“在张家口方面,有该地三井洋行出张所员宫崎嘉一,虽无军事方面智识但却办事可靠;陕西西安方面,派遣军队司令部翻译吉田忠太郎前往;新疆迪化方面,派遣在乡军人下士佐田繁治前往,以宗教研究为目的,同时进行谍报活动;在外蒙古库伦方面,有居住在库伦的日本人驹田信夫,最近接受了进行谍报工作的委任”。⑨另外,还向“天津及其他驻屯地”、“西安或太原”“配备军官或其他能干的间谍”,并“预定向张家口派遣军官”。可以看出,这些被指定优先派遣的地区,多在中国西部、北部或边疆地区的中心城市。日本军部之所以扩充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情报网,其主要目的为:“随时局进展,侦探俄德设在支那西北边境的设施,以便及时采取共同行动阻止。”⑩但是,日本军部的行动,还隐藏着另外的目的。例如,佐田繁治在新疆“以宗教研究为目的,同时进行谍报活动”。因为新疆居住着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在这里进行“宗教研究”,重点当然只能是伊斯兰教。笔者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的内阁公文中发现,1873年7月15日出生于岛根县的在乡军人(即预备役)下士佐田繁治,在此之前是殖民地台湾警察,并非宗教研究家。(11)
可以看出,近代日本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关注,并非出于偶然。有日本学者指出, 日本对于“回教”的关注,原本就与侵略亚洲的目的有关。(12)其关注焦点所在,可以从大林一之所著刊行于1922年8月的《支那的回教问题》中看出。大林对中国伊斯兰教进行研究的目的,说到底是在研究“回教”在中国的统一与分裂问题上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所以,他在这本书的最后这样写道:“我认为,富于煽动性,并具有雷同性,在特殊地域里成为特殊潜在势力的支那回教,在现今的形势之下就是支那的癌症。但是,除非到了支那自身被解剖手术切开之时,是无法将其剔除出去的。而因其病情发展非常缓慢,若没有来自外部的冲击就不会发生急激的病变。”也就是说,大林的结论是,“回教”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的一个分裂因素,值得日本积极加以利用,他进而提出:“支那的回教,根据对它如何进行利用,可以使其在调整整个远东问题上发挥出一种有力的作用。”(13)大林一之的这本小册子由青岛守备军陆军参谋部刊行,出版后被分发给军部与政府各有关部门,而当时大林一之的身份为“军嘱记”(军方委托进行研究人员)。这说明,大林的调查、研究和研究成果的出版,都是遵从军部的意愿、使用军部的资金进行的。
1922年11月,外务省情报部购买了山冈光太郎于1909年出版的44本《回回教的神秘威力》,分发给外务省的局长、课长,以及向南美洲地区输出移民的各地方府县政府,并发出通知要求学习有关伊斯兰教的知识。(14)山冈光太郎被称为第一位到麦加进行朝觐的日本人。关于他到麦加进行朝觐的背景,有日本研究者指出:“与其说他是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进行了这次旅行,毋宁说这就好像是一次与宗教没有任何缘分的冒险旅行。说得更深刻一点儿,那甚至不是一位身贫如洗的青年自发的冒险旅行,而是接受了军部的指示进行的麦加朝觐。”⑤虽然目前还没有原始资料来证实这位日本研究者的指摘,但是通过日本军部的各种作为可以肯定,他们极其关注伊斯兰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田中逸平是第二位到麦加朝觐的日本人,他是在中国青岛的日本驻屯军中供职期间改信伊斯兰教的。“支那回教研究家”若林半,在他1935年向日本外务省提交的履历书中这样回忆道:“大正五年(即1916年——引者注)时,我去到青岛陆军访问翻译官、同志田中逸平氏(故人),共同谈起东亚的百年大计,我恳请他改宗为回教徒以研究支那回教。在促使该氏下定了决心,并互相约定顺从天意之后,我回了国。”若林半在吹嘘自己的功绩时甚至说,田中逸平之所以在1924、1935年两次去麦加朝觐,就是因为他的劝说。(16)田中逸平是作为日本陆军的翻译官随着“山东占领军”(又称“征胶军”)来到山东省的。之后他一边挂着东京国民新闻社特派员的头衔,一边从1917年开始在山东省筹备创办中文报纸《济南日报》,并担任该报主笔。
设立报社并非一件易事,不仅需要通过各种审批,而且需要大量设备和资金。但是,田中顺利地设立了报社,缘由是他得到了日本驻屯军的支持:“设备费由当时的军政长官吉村健藏氏出面,说明田中等为军政尽力之事,说服青岛鸦片局刘子山出资约一万元。”而田中逸平之所以能够得到占领军的信赖和支持,就是因为他办报的目的是在中国制造对日本有利的舆论,以支持日本的侵略政策顺利实施:“从经营山东的目的出发,操纵支那人,创立一个强有力的汉字报社”,以便“在解决山东问题乃至其后”的“帝国的北支那经营”(即如何将华北纳入日本势力范围的问题)上,“常常对时局问题直接产生影响”。(17)有日本研究者认为田中逸平之所以改信伊斯兰教,不是“企图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利用伊斯兰教”,而是“试图理解伊斯兰教的本质,在兴亚的理想基础上尝试与伊斯兰教进行交流”。(18)在没有看到以上田中逸平在青岛活动记录的情况下,这位研究者得出这样的结论,缺乏依据。
二、活跃在中国“回教”界的日本人
与田中逸乎有着亲密关系的“支那回教研究家”若林半,其在中国的活动也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1935年9月,若林半带领两名弟子,用了大约两个月时间,访问了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平、归化(呼和浩特)、太原、热河(承德)、奉天(沈阳)、新京(长春)、大连等地,这次旅行的名目为“调查中国的回教政策及情况,并与之进行联络”。而调查和联络活动所使用的经费,来自日本外务省支出的“补助费”(五百元)。(19)1939年1月10日,若林半以“日本名人”的名义,来到日本军占领下的北京,视察设立在此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并且进行了“训示”。(20)
战争初期,在被日本军队占领的许多地区,都先后出现了各种“回教徒”的团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团体的设立过程中,都能够看到日本人的身影。最初的“回教徒”团体,是1934年末设立的“满洲伊斯兰协会”,它在“伪满”各地共有166个分会。(21)该团体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强大的网络,就是因为日本侵略当局给予了极大支持。按照当时日本外务省调查部一位属员的报告,在该团体设立的过程中,“尽了最大努力的是一位名为川村狂堂的日本人”。川村狂堂(名为川村乙麿,狂堂为其号)被推为该协会的总裁,在他指挥下,这个会员达一万人以上的协会,积极支持了日本的殖民统治政策。例如,伪满洲国实施“帝制”时,协会“率先鼓吹宣扬王道立国与满洲建国的精神”,“赞扬友邦日本的仗义援助”。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穆斯林发出“抗日”号召后,该协会立即向各分会发出通知:“阐明发扬满洲建国精神、加强日满两国一德不可分关系之意义,以及不可反满抗日之理由和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教教义二者不可共容之道理,以此来引导在满回教徒。”当七七事变发生后,该协会又向“全满信徒”发出“谕告”,宣称日本的侵略行动,“不外是友邦日本为了维护东亚和平大义,而派出了正义之师”。(22)
据说,川村狂堂是受日本黑龙会的派遣来到中国的。从1910年代到1920年代,他一直活动在中国西北各地,大约是在北京或新疆改信了伊斯兰教,曾经在甘肃省因为与“穆斯林叛乱”有关而被当局当作“军事间谍”逮捕过。(23)事实说明,川村狂堂具有日本军部的背景。
1937年12月,日本外务省调查部举行第一次“回教研究会”报告会。会上,日本外务省欧亚一课“嘱讬”今冈十一郎(24)当着11位外务省官员、3位陆军省军官、4位海军省军官的面,就以上所言及的活跃在中国“回教”中的日本人,做了如下陈述:“人们都说,在我国人中的回教徒已经为数不少。而在我看来,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信徒,而是政策上的信徒。在这种人中间,从过去就有名的人大致如下:山冈光太郎(在印度接受了洗礼)、田中逸平(死亡)、中尾武男(现任驻土耳其大使馆嘱讬)、川村乙麿(号狂堂,在奉天,在回教徒中有权威)、波多野鸟峰(曾经在赤坂设立回教寺院)、冈本甚伍(跟从库利班加里接受洗礼,以世界旅行者而知名)、有贺文三郎(跟从神户的诺下姆古诺夫接受洗礼),之外年轻的还有小林(在爱资哈尔大学)、山本、铃木、乡等人。”“作为个人的行为,还有若林半在做支援输送青年去到麦加进行朝觐的活动。”(25)这些人“不是真正的信徒,而是政策上的信徒”,这句话真可谓入木三分,准确地道出了这些人进行伊斯兰教活动的本质。
在当时的察哈尔省府所在地张家口,1937年11月22日成立了“西北回教民族文化协会”。虽然名为“文化协会”,但是从7名一般干事均为各地清真寺的“教长”(伊玛目)这一点来看,该协会应该是一个由中国伊斯兰教信徒组成的宗教社会团体。而从12月18日日本驻张家口总领事代理松浦给广田外务大臣发出的机密电报可以看出,这个中国伊斯兰教信徒的团体一开始就是由日本人计划设立的。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透露:“本次事变爆发以来,军部为了防止苏联势力对从外蒙方面到内蒙及西北支那一带的渗透,在这一带遏制和排除共产主义的侵入而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正在进行中的对各地回教徒的怀柔,以及策划掀起排苏反共运动。上个月的十一月中旬,松林亮从奉天、山口从天津来张(家口),与特务机关取得联系,在当地纠合居民中的回教徒,于二十二日在本市市民大街清真寺召开了西北回教民族文化协会成立大会”,“特务机关、察南自治政府代表及顾问以及其他各机关的代表均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选举的5名协会顾问中,居然就有“松井特务机关长”、“金井蒙疆联合委员会顾问”和“田中察南政府代表”等4名日本人。(26)
在热河省省会承德,1938年5月7日成立了“防共回教徒同盟”。成立大会上,由“当地防共同盟本部首脑(日本人)”,即“同盟总裁”花田仲之助与“同盟长”张子文两人联名发表了“伊斯兰教教徒反共同盟宣言”。(27)同盟“网罗了鹤冈长太郎、重松又太郎、甘粕正彦、高桥水之助、十河信二、鲇川义介、土方宁、前田照城(驻承德五军宪兵队顾问、后备陆军大佐)、大川周明等与回教有关的知名人士”,来做同盟的顾问。(28)
在成立“防共回教徒同盟”的过程中,最为活跃的是“作为志士而闻名的退役中佐”花田仲之助(1860-1945)。(29)他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长期活动于中国东北。根据山名正二所著《日俄战争秘史 满洲义军》一书,1897年4月,时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军官的花田,为了搜集军事情报,曾受命扮作日本西本愿寺的僧侣潜入海参崴,以清水松月的假姓名潜伏了三年之久。花田归国之后被编入预备役,于1901年成立了以天皇“教育敕语”为基本理念的“报德会”,在日本各地广为宣扬“知恩报德·感恩报谢”精神。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花田接到征集命令,被任命为熊本步兵第二十三连队第一大队长,但在一个星期之后又被调往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被任命为“参谋本部属员”,受命组成一支在敌后收集情报和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别部队。在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的支援下,花田仲之助率领由他亲自选拔的8名步兵、工兵,加上7名玄洋社成员,组成了一支16人的“特别任务队”,进入中国东北辽东地区,(30)以“满洲义军”的名义纠集了“满洲马贼”,从背后对俄军反复进行攻击。有人说,“满洲义军”在日俄战争结束时,已经发展到1000人以上。(31)因为“满洲义军”劳苦功高,“义军总统”花田仲之助在战后受到日本军部的表彰。(32)
日俄战争以后,花田仲之助再次被编入预备役,(33)但依然与军部保持着密切联系。1936年5月和11月,花田仲之助作为报德会会长,两次搭乘日本军舰(乌苏里丸和扶桑丸)来到“满洲”进行视察。(34)在“满洲”,花田主要以“报德会”的名义进行活动,据说在各地受到热烈欢迎。(35)其中缘由,不仅是因为过去“满洲义军”时代的影响力,应该还与他和日本关东军以及情报机关关系密切有关。根据为《日俄战争秘史 满洲义军》一书执笔作序的大本营陆军报道部长、陆军大佐谷萩那华雄的回忆,花田来“满洲”时,他正在奉天特务机关作机关长土肥原少将(写作序言时已升为大将)的辅佐官,1936年秋的某一天,花田仲之助来到该机关,要求搭乘关东军的飞机。(36)1941年11月,“第十三届大阪府下报德会联合大会”召开之际,花田甚至打电报给当时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要求他给大会发贺电。这些事实证明,花田与日本军部之间有特殊的关系。(37)
三、驻屯日军的“特务机关”与“回教”团体
无论是“西北回教民族文化协会”,还是“防共回教徒同盟”,当时中国许多地方伊斯兰教团体的成立与运营,都与侵华日军的“特务机关”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9年1月13日, 日本驻张家口森冈总领事向有田外务大臣拍发绝密电报,提到“蒙疆”的“回教徒”有“五万至七万”之多,并进一步补充道:“为了操纵和指导这些回教徒,并以此为基础密切联络居住在西北五省的回民族,在蒙疆政权刚刚成立之初,已经根据军部的设想,前年十一月已经在张家口成立了西北回民族文化协会”,“对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回教青年进行精神训练,并在各地清真寺附属的阿拉伯语小学中增设了日语科目”;“上述各项工作由特务机关专门负责,(蒙疆)联合委员会只不过支出经费而已。”(38)
此外,日本驻承德草野代理领事在向广田外务大臣拍发的“绝对保密”的电报中,对于成立“防共回教徒同盟”的意义作了如下解说:“一,与满洲国的二百万回教徒保持联络”;“将该地作为回教徒的防共本部,并以此为中心,不仅与满洲国的而且与一千万支那回教徒进行团结,支援五马联盟,力图与中亚各国回教徒取得联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政治工作员(即义勇军)进行武装,首先支援五马联盟,使其从蒋政权中完全独立出来,然后进入中亚,促使该地区各国独立或排除第三国的影响,在皇国之慈光下完成东洋的皇道联盟”;“预定最近向新疆和阿富汗方面派遣工作员(日本人)”。(39)并补充道:“为了方便与参谋本部取得联络,该会干部渡边清茂和安田德助(均系教务会热河省本部职员)二人于八日由当地出发进京,为了与关东军取得联络,该地的特务机关长荒木大佐于九日出发前往新京。”(40)
对“同盟”的“第一次实施计划”,草野代理领事给予了高度评价:“据我观察,不仅内容上立意周到、组织具体,而且方针甚为精细。为了保证日本的大陆政策得以迅速顺利开展,不仅准备支援支那边境西域地区回教徒的反共政治独立运动,甚至还支持近东各国的民族解放和印度的独立运动。值得注目之点为:(一)实施要领规定:1,该项工作要始终与当地作战兵团的对回教工作保持一致;2,坚持不懈工作以强化和推动世界回教徒军的自发奋起,根据这一原则,重视回教徒揭竿而起,在表面上最大限度地避免军部进行指导(的印象);3,鉴于本项工作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要警惕不良分子进行策反,重视对人员的选择工作;4,关于本项工作的宣传活动,积极组织和利用民间的宣传网络,原则上排除官方宣传……(三)组建由回教徒独自参加的义勇军,编制为从第一军到第四军;(四)确保与我方大本营及内阁的秘密联络。”关于组建“义勇军”一事,“决定在承德特务机关的指导下”,第一次招收5000人;“关于派遣方法,遵照关东军的指示,另外单独做出计划,以期支援支那西域回教徒的独立”。最后特意强调“对于本项计划,承德特务机关长甚至牺牲自己的时间,始终给与了全力支持”。(41)
1938年2月7日,“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在北京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的日本方面职位最高者为“北支那方面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少将;就任联合会“最高指导者”的是北京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在“联合会最高指导及委员名系表”中,名列联合会主席之前的为茂川秀和特务机关长,以及主席顾问高垣信造。“联合会”开设了日语学校,根据茂川秀和特务机关长的指示,联合会于4月9日设立了“回教青年训练所”(回教青年团),第一年招生3期,共训练了47名伊斯兰青年。在毕业仪式上,有毕业生慷慨陈词:“组建回军,正值今日”,由此可以推测:对这些青年也进行了配合日军活动相关的训练。“联合会”得到日军的支援之后迅速扩张,一年之间设立了北京、天津、济南、太原、张家口、包头、河南等7个地区本部,成为一个拥有389个分会的庞大组织。(42)
“特务机关”是归属驻扎于各地的日本侵略军的组织。从很多现象可以看出,有关中国“回教”的问题,基本上就是由日本侵略军负责。例如,1938年9月至10月,由“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组织的“回教徒访日视察团”对日本进行了访问。团长虽然是由当地的“回教徒”担任,但两位“指导者”则均系日本人,其中一人还是“特务机关员”。引人注意的是,负责接待这次访问的并不是日本政府外务省,而是陆军省。此外,1939年“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回教徒代表团”出席“东亚回教徒恳亲大会”及“回教展览会”时,同样也是由日本陆军省负责接待。(43)根据“大日本帝国张家口大使馆事务所”提交的名单,1944年3月时“蒙古自治邦”中央机关在职和已经退职的日本职员共计236人。从该名单来看,这些日本职员以前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但是“回教委员会”的5名日本人顾问中,除了1名女性之外,全是现役军人。(44)
1938年4月,日本政府成立了以外务省为中心,陆军和海军相关人员组成的“回教及犹太教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制定“回教对策”为“急务”。(45)8月该委员会又向内阁总理大臣以及各大臣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回教对策的报告”,强调了“与分布在亚细亚大陆回教徒建立友好亲善关系,以确保从背后对支那进行牵制”的重要性。(46)当年9月,外务省情报部制定了《支那事变后情报宣传工作概要》,提出“作为外务省,在情报、宣传和谋略问题上不分对内对外”的方针,规定外务省搜集中国情报工作的目的为:“广泛收集情报,以至于了解支那的抵抗能力、各国的援助情况、人心动向。”并且做出下述具体决定:“由民间某团体开设研究所,以培养优秀的谍报人员”;在中国构筑“北支”、“中支”和“南支”三张情报网;在驻北京、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领事馆中增设情报主任、调查研究班和谍报工作班,其工作任务为:“侦查并粉碎(苏联和中共的)妄动”、“防止和镇压由国民政府进行的策反”、“监视政局和民众的动向”。(47)事实上,日本外务省在中国建设情报网的工作在此之前早已开始。如1922年5月, 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就已经雇佣了“一名支那人作为谍报人员”。(48)
总之,日本外务省不仅非常重视在中国开展“回教工作”,而且具有与“回教徒”打交道的能力。但是,通过以下各种实际活动可以看出,日本在中国的“回教工作”一直是由驻扎在当地的侵略日军负责。
1939年3月,在属于蒙疆联合委员会(实际上就是日本“驻蒙军”)的管理范围内的包头,发生了“文化学院”(内设“回教青年日语学校”以及附属夜校)由于接到“驻蒙军”“命令离开”的“谕示”而不得不停办的事件。这所学校的教员是森、菅沼两位日本人(档案中只有两人姓氏,未记全名——引者注)。按照日本驻张家口的森冈总领事的说法,这件事的起因为:文化学院由以“满洲国”的热河省为根据地的“防共回教徒同盟”经营,“其一部分经费由满洲国协和会本部支出,而且和回教同盟有密切的关系”,“他们违反了驻蒙军的方针进行工作”,“此外,当回教本部由承德迁往包头之际,他们没有与驻蒙军及蒙疆联合委员会联系,而直接与东京的中央军部进行联系等,事后被察觉”。(49)由此可知,在侵华日军中存在以下原则:即便是遵循日本政府“回教工作”方针开展的事业,与“回教”相关的一切事项均属于驻屯当地的日本军队的专管事务,必须接受他们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所以,当与“满洲国”方面有联系的回教机关进入“驻蒙军”的管辖地域时,尤其是他们绕过“驻蒙军”而直接与东京方面发生联系之事被发觉后,就遭到了“驻蒙军”的驱除。
四、“回教工作”中的“回教徒”军阀
在日本对中国“回教工作”的构想中,经常出现“五马联盟”一词,指以西北地区为根据地的五名“马”姓“回教徒军阀”的联盟,但是从这些关于“回教工作”的档案文书中至今没有发现一件日方所指“五马”究竟是哪五位“回教徒军阀”的文件。中国国内也有“五马”之说,但随着时代的不同,所指人物有所不同。民国初期的“五马”是指甘肃省督军马福祥、宁夏护军使马鸿宾、甘边宁夏镇守使马麒、凉州镇守使马襄廷和甘州镇守使马麟;而20世纪30年代的“五马”是指宁夏省主席马鸿逵、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以临河地区为中心的中央军新编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以凉州为根据地的中央军新编骑兵第五师师长马步青、活跃在甘肃西部的新编第三十五师师长马仲英。这些“回教徒军阀”虽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组成过一个政治联盟。此外,“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认为“中国回族中军事方面的实力派人物”为西北的马鸿逵、马鸿宾、马步青、马步芳、马麟,以及原籍桂林的白崇禧(国民军总参谋长)。(20)
1938年12月13日,日本驻厚和(呼和浩特)领事胜野敏夫在向外务大臣提交的报告中,对“回教军”进行了详尽分析:“虽然一般将其称为回教军或回教将领,但实际上却与分散驻扎在各地所谓的军阀之间并无太大差异,称他们为回教军阀也并不为过,他们当中并没有真正打算提高全体回民生活水平之人。因为当地居民经常受到他们的盘剥和压榨(对于汉族尤甚),所以并无一人一直全面得到当地居民(回民)的支持。”他还逐一评论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和马仲英的实力、人格和在民众中的声望:“1,马鸿逵:典型的军阀将领,只对保持自己的势力有兴趣,长期对当地居民进行残酷剥削,在回民和汉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声望……因此居民中的有识之士及其部下中的不满分子等私下均有欲排除马鸿逵的迹象。居住在厚和方面的天主教神父等也认为他为人反复无常,难以信任”;“2,马鸿宾:在当地居民中有相当声望(在外国人中也如此),而且得到部下深厚信赖”;“3,马步芳:推行仁政(虽然在青海那种地理条件下难以做到),以回民为首,在蒙古人中也有很高声望。我认为他是将来能成为西北回教徒领导人的唯一将领”;关于马步青,“具体不详”;关于马仲英,“目前客居苏联……行动不详”。(51)
虽然日本人对“回教徒军阀”的评价不高,但仍认为他们有利用价值。例如,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日高信六郎曾向广田外相做出过这种说明:“如果驯服了青海的马步芳,切断从哈密经兰州至西安的通道,并因此切断‘苏’联邦向汉口政府提供武器的道路,就掐住了汉口政府的命门。这件事不仅可以加快事变的解决,也可以阻止赤化势力依托这个通道东进,是一个十分切合实际的措施。”(52)回教圈考究所编撰的《回教圈史要》一书,对于“五马”的影响力做了如下断言:“很明显,居住在支那西北角受马姓军阀统治的回教徒,未必会倾听按照赤化音符吹奏出来的抗日笛声。其实与其这么说,还不如说他们对在马姓军阀的指挥下,采取独自行动充满了期望。”(53)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回教徒军阀”站在日本一边,与日本进行合作的话,战争局势就会变得对日本有利。
从当地日本领事馆向日本外务省提交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回教”团体积极地参与了对“五马”的劝降工作:“该反共同盟对五马联盟的联络,原来由在包头的高桥水之助(内蒙古军最高军事顾问)专门负责,该员最近将盟长晁悉文从奉天迎进包头,在协商了推行此项工作的方法之后,(晁悉文——引者注)已经于数日前由该地出发潜入宁夏方面。为了从当地通报其后的进展情况,一名同盟干部已于九日飞往包头”,“设在包头的‘穆斯林’同盟是该项工作的首脑总部,所需要的准备工作已悉数完成,首先进入五原,已经与当地秘密取得了联系。向马鸿宾(临河)、马义忠(陕西)派出了密使,同盟干部则从分散驻屯于五原周边的共产军的空隙中穿过,进入了临河”。(54)
事实上,这些“回教徒军阀”们从前在购入军火的时候,就已经与日本军方有过接触。比如,1930年11月,“马鸿逵通过上海的德商汉文洋行,与大仓洋行签订了购入二千支日本三八式步枪的协议”,“还希望将来能购入机关枪、平射炮或曲射炮”。(55)1936年12月马步芳、马步青通过驻扎在天津的日军,提出购买三八式步枪1000支、步枪子弹100万发(马步芳)、三八式步枪1000支(含刺刀及各种附件,马步青)。日军对此前卖给这两人的兵器用途进行了调查,并认为“考虑到在与额济纳机关等保持联系问题上,可以利用他们”,因此同意将武器卖给他们。(56)此外,1937年5月21日,马步芳通过日本的支那驻屯军购入了军刀2000把。(57)
虽然统称“五马”,但其中势力最强的是马步芳和马鸿逵。他们在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骑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1937年6月在蒋介石的严命之下,马步芳下令袭击在此之前已经存在,但他却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活动的“额济纳机关”,也就是日军设在尚未被占领的宁夏省额济纳旗的特务机关,逮捕了“江崎寿夫为首”的日本人特务机关员11人,其中10人“于10月11日在兰州被枪毙”。(58)剩下的一名“关东军间谍大迫武夫”,由于得到马步芳军第一旅旅长马步康的力保,说他是自己的知己,一个蒙古人而已,得到释放。此后,大迫武夫又一次进入青海,“活跃在西宁附近”,继续进行情报搜集活动。(59)
但是,根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日高信六郎于1938年3月25日向日本外务省提出的报告——《关于新疆及青海情况并马步芳对日态度的问题》,就在“额济纳机关”事件的翌年,马步芳放出想在印度孟买与日本方面进行协商的风声,并就前一年袭击“额济纳机关”、枪杀日本谍报员之事对日方进行了如下说明:“那是误中支那政府的奸计,而我本人对日本并没有任何敌意”,并且说明自己有在日本的援助和指导下反抗国民政府,驱逐赤化势力的决心,如果日军进军甘肃的话,“将立即将枪口对准汉口”,希望获得日本的理解。(60)
在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中,有一种“回教徒”先天地“极端厌恶共产主义,具有亲日感情”的说法。所以,他们认为,可以利用马步芳“阻挡经由新疆东渐的赤化势力”,“切断由哈密经兰州到西安的、苏联供给汉口政府武器的通道”;(61)“马鸿逵历来对日本抱有好感”。1938年5月16日,“驻蒙兵团参谋长”在向大本营参谋次长和外务省次官拍发的秘密电报中,传达了马鸿逵对日本的如下希望:“马鸿逵来信提出,每有关于回教工作(在京津地区)的新闻报道,就会刺激支那方面,增加他们对回教徒首脑阶层的戒心,也就更加加深对他们的压迫。因此应该绝对控制报纸报道。他的这一意见今后值得考虑。”(62)由此可见,其实马鸿逵也想与国民政府和日本两方面都保持良好的关系。
根据一份“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的报告可以得知,马麟于1938年11月派特使绕过中国军队防守线,从兰州跋涉一个月到达北京,向“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告了甘肃宁夏方面“回族军”的驻扎情况。马麟是马步芳的叔父,曾经担任过青海省省长,但在1935年的权力斗争中输给了马步芳,当时隐居在家乡甘肃省临夏。如果“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的这份报告属实的话,可以认为,马麟是想通过加强与日本军的关系重新夺回权力。
关于当时“五马”和“回教徒”团体的动向,日本人的评价有一定的出入。由大久保幸次担任所长的“回教圈考究所”认为: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支那的回教徒在理解防共主义大局的同时,为了保卫他们的宗教信仰权和生活权利,积极参加圣战和兴亚大业,是十分自然的事”。(63)但是佐久间贞次郎则一直坚持否定意见,警告不可夸大事实:“世人最近通过报纸宣传等得以屡次看到和听到西北支那回教军将领五马,即马步芳、马步青、马麟、马仲英、马鸿逵等(名字——引者注),由于事变(即卢沟桥事变——引者注)以来,这方面的工作进展也得到大力宣传,因而产生了应该与支那回教徒联合防共,而这项工作也正在进行的错觉。京津两地回教的那个什么会,尽管实际内容空洞,有名无实,但是宣传却做得玄乎其玄,未免过于夸大其辞。”(64)
五、战争目的下的“回教工作”
战争期间,日本建立了几个与“回教”问题有关的组织。丽泽大学教授大久保幸次(1887-1947)号称是日本最初的伊斯兰教研究者,但是从其曾积极参与在日塔塔尔人的内部争斗一事中,可以感觉出他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1938年3月,大久保幸次接受了德川家族的资金援助,成立了回教圈考究所(后改名为回教圈研究所)并一直担任所长。1938年5月考究所并入日本善邻协会系统,接受日本外务省的财政补贴,1938年7月开始出版月刊《回教圈》,并一直发行到1944年12月号。(65)
战争时期成立的另一个有关伊斯兰教的组织为“大日本回教协会”。该协会作为“调查和执行回教对策的专门机关”,(66)成立于1938年8月前后。值得注意的是,该协会的办公室人员中有5人为黑龙会成员,(67)协会的常务理事为“黑龙会”首领葛生能久。而协会的经费,除了一部分募捐之外,基本是由外务省全额负担。1938年10月,协会向外务省提交了一份总计1000万日元的《十年经费预算》。(68)并从第二年开始,每年按季度从外务省领取经费。(69)大日本回教协会从一开始就分为总务部、事业部和调查部3个部门。调查部的主要任务为:“有关回教的调查和研究”,“调查回教圈各地方的事情——民族、语言、政治、经济、产业、文化等”。(70)“回教及犹太问题委员会”在1938年8月提交给外务省《关于建立回教对策》报告中,如此定位“大日本回教协会”:“将大日本回教协会看作是民间的最高回教调查机关,给予支援和指导,令其主要从文化的方面实施各种对回教徒政策。”(71)从这些工作内容和经费渠道上可以看出,“大日本回教协会”不过是一个执行日本国策的机关。
“大日本回教协会”所做的最大工作,就是1939年11月在东京举办了“回教圈展览会”,利用这个机会,还召开了“世界回教徒大会”。这次大会作出了“今后每年召开回教徒大会”,以及“第二次大会定于东京召开”的决议。但是第二年四月,因为找不到出席者和担心遭到有关各国的指责而不得不决定停办。(72)
在回教圈研究所和大日本回教协会等所谓民间“回教”机关的背后,是由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有关人员组成的“回教研究会” (又称“三省回教研究会”或“三省回教问题研究会”)和决定“对回教政策”的“回教及犹太问题委员会”(简称“回教问题委员会”)。将中国的“回教”作为主要渗透目标,是这两个组织活动的共同特征。
“回教研究会”逐月召开,有时甚至每月召开两次。(73)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研究会上发表报告的是今冈十一郎,他的报告内容大量涉及中国伊斯兰教。他强调:“随着日支事变后的形势发展,今后我国将会实践从北支到内蒙,进而进入新疆,再进而进入中央亚细亚的大陆政策”,所以应该理解“回教”的重要意义。今冈尤其强调新疆的重要意义,为此使用了很大的篇幅。他说:“我认为新疆才是大亚细亚的心脏。正如有人所说:‘统治了新疆就是统治了亚细亚。’”“日本被称为是亚细亚的盟主。日本真要成为亚细亚的盟主,就不能不尽早掌握这个亚细亚的中心地带、亚细亚的心脏。”如果掌握了这个地域,就可以“从背后牵制支那,穿透苏联的脆弱部分的东部西伯利亚及中央亚细亚的腹部,从大英帝国的心脏即印度的背后进行牵制,摧毁被英印号称为防卫线上最后的金城汤池——新加坡军港的防御力量”,这是一个“可以一箭三鸟(英、俄、支)、非常有效的目标”。(74)
根据“回教研究会”的“研究成果”,1938年4月23日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就成立“回教(及犹太)问题委员会”达成了一致意见。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为:“设立由外务当局负责的回教及犹太委员会,分析探讨该问题的根本对策,外、陆、海三省及各派出机关之间经常保持联系,在统一的方针下处理有关回教及犹太教的问题。”(75)规定担任外务省的东亚局长、欧亚局长、美洲局长、调查部长、陆军省的军务部长、参谋本部的第二部长、海军省的军务部长、军令部的第三部长等与外交和军事有着直接关系职务者,出任“回教及犹太问题委员会”的干事。(76)
1938年8月,刚刚成立不久的“回教问题委员会”,在向内阁总理大臣及各大臣提交的《关于建立回教对策》的报告中指出:“帝国的回教对策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得回教徒最有力同情者的名分,以有益于对外经纶,尤其是帮助对英、对苏、对支国策的顺利实施”,在此基础上《关于建立回教对策》进一步指出:“(掌握——引者注)回教徒的分布状况、人口及其特性,是帝国在对外经纶上必须大力重视的地方,而从现实来看,它还是建立处理支那边境问题根本对策的火烧眉毛的紧急要务。”(77)很明显,这个委员会之所以成立,很大一部分是出于支援侵略中国战争的考虑。
为了“回教工作”顺利进展,不致发生“歧视回教的误解”,1939年3月日本还出现了修改《宗教团体法》的呼声,要求将第一条改为“宗教团体为神道、回教、佛教及基督教”,即明确加入“回教”一词。据说是因为担心这样做反而造成歧视其他宗教的印象,这一运动才慢慢平息。(78)以上种种事实说明,“回教”问题在日本被完全政治化了。而日本政府之所以使出了种种手法,从政治、财政、人力等各个方面大力支持有关“回教”的活动,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将“回教”变为支持其侵略战争的工具。
1938年10月4日,驻蒙军司令部制定了一份绝密文件——《暂行回教工作要领》。其中规定“回教工作”的第二个目标为:“促进以西北贸易为中心的经济工作以及加强与宁夏兰州方面的联系”,其目的除了通过贩卖日本商品构建对日本的经济依赖关系之外,还包括“利用回教徒在宁夏兰州方面实施谍报和宣传工作”,“进一步加强当前在包头实施的培养特别人员的工作,待条件成熟时将培养出来的特别人员混入以上(指宁夏兰州方面——引者注)商队,以建立与宁夏兰州方面进行联络的机关”;“现在要在灵活使用有联络的密探及建立和确保能与其他特殊人物进行直接或间接联络的手段上加大力度”。《暂行回教工作要领》规定的第三个目标为:“建立回教徒军”,“首先在蒙疆地区的回教徒中选拔胜任者,编成回教军(最初建立小规模部队作为实验),为将来实力雄厚的回教工作做准备。”为了能够实现这些目的,军部要提供“依托西北贸易商进行谍报及宣传工作的费用”、“培养和使用特别工作员的费用”和“在军司令部、特务机关等机关中充实有关回教工作事务人员的费用”等“特别工作费”。(79)
根据以上《暂行回教工作要领》,12月5日驻蒙军参谋部制定了《回教青年指导要纲》,其目的为“指导(回教青年——引者注)为建立西北地区防共亲日蒙政权工作而努力献身”。(80)驻蒙军司令部在翌年5月制定的《关于对蒙疆重要政策思想统一的问题》中再次明确提出:“蒙疆的回教徒工作,在于支援西北回教徒完成以亲日、防共为精神的独立复兴。”(81)同一时期,总部设于张家口的“西北回教民族文化协会”与总部设于厚和的“西北回教联合会”合并。(82)驻厚和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长山崎信彦在提交给上级的报告中说道:“该总部的工作,首先是对蒙疆回民青年实施精神教育,使防共亲日开花结果,最终建立西北独立国。”(83)总之,由日本军方直接指挥的“回教工作”,其目的不仅仅为维持占领区秩序,而且谋求随着战争的扩大最后建立由回教徒组成的独立亲日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回教徒”和“回教工作”,向中国西北部扩展日本的势力范围,绝非“驻蒙军”自己的想法。1937年11月, 日本大本营陆军参谋部第二部已经制定了一份“军事机密”文件——《关于支那进行长期抵抗的情势判断》,列举了数条“导致国民政府崩溃的方略”,其中包括:建立反共、反国民政府的政权;激化国民政府内部的矛盾;促使地方实力派抬头;煽动“反国民政府”的暴动和“对亲共容共分子进行‘恐怖’活动”;持续封锁海岸线;彻底轰炸中国的军事、政治、交通、经济设施等。其中第六条为:“致力于怀柔西部内蒙古及西北地区的回教徒,扶植亲日反共反国民政府势力,以阻止苏联经外蒙及新疆方面(向中国——引者注)输送兵器和军需物资。”(84)
“日本国际协会”也在1938年4月提出的《对支时局对策》中,以“推进怀柔边境民族及回教徒工作”为第六项对策。(85)本文最初已经提到,1938年7月8日,在开战一周年之际“五相会议”制定了指导性纲领——“随时局发展的对支谋略”,提出了以“在让敌人丧失抵抗能力的同时颠覆支那现中央政府,或者让蒋介石下野”为目的的六项“纲领”。其中包括:通过起用中国一流人物来软化中国民众的抵抗意识,怀柔杂牌军以分化瓦解和削弱中国军队战斗力,利用实力派人物树立反蒋、反共、反抗日政府,制造法币暴跌(此点以后被否定)等。同时作为第四点纲领被提出的是:“推进回教工作,在(中国——引者注)西北地方设立以回教徒为基础的防共地带。”(86)也就是说,从很早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军部就已经开始考虑通过内蒙古地区的“回教徒”,将其势力范围向西北部扩展。
中国的西北地区,在地理上与苏联接壤。因此,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前, 日本军部就已经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1935年12月2日,“支那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向陆军步兵少佐羽山喜郎发出一件绝密命令,将他的“负责谍报区域”设定为“绥远省、宁夏省、甘肃省、新疆省及蒙古”,同时又要求在绥远省的呼和浩特、察哈尔省的张家口、西索尼特、多伦和山西太原各地设立“特务机关”,并命令各“特务机关”:“准备并实施对蒙、对苏、对支的谍报工作,调查兵要地志(包括经济资源),收集并准备实施谋略所需要的资料。”(87)这份文件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实施谋略”所指何事,但明显意味着针对该地区的军事侵略行动。换言之,这份文件不仅可以证明日本军方至少在1935年底前已经具有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而且可以证明日本军方已经将这些边疆地区列入其军事侵略对象地域当中。
日本之所以想到利用该地区的“回教徒”,一是因为他们认为“回教徒”因其宗教信仰, “先天就是反共的”;二是因为他们认为“回教徒”在西北地区具有特别强大的实力。例如,1938年5月“防共回教徒同盟”成立大会发出的宣言——《伊斯兰教徒反共同盟宣言》,向西北的马姓军阀发出了如下呼吁:“位于支那边境西域的五马联盟应该与南方的土耳其遥相呼应,高举反共运动的烽火,切断苏联对支‘红色通道’,击破蒋介石容共政策的最后抗日据点。在此基础上,我等回教徒同志以神国日本为盟主,为了亚细亚文明的复兴,为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结成‘伊斯兰’教徒反共同盟。”(88)
由于日本“回教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援侵略战争,根本没有想要真正保护广大“回教徒”的利益,因此大政翼赞会在1943年4月提交给东条英机首相的《关于回教徒对策的调查报告书》中提出:“在我国,历来只有以回教工作为目的的、由各种国际社交团体和宣传机关进行活动,对外宣传中缺少一种能够从内心深处打动、振奋海外回教徒大众感情的东西。仅仅限于与一部分为政者之间搞好关系,反而会让更多的回教徒误以为(日本的回教团体——引者注)是伪装的信仰团体,到了后来知道不过如此时则大失所望,这种前例已经不少。”(89)前面述及与“五马联盟”联手的设想,当属此类。
一直与中国“回教”有关系的佐久间贞次郎,也看出日本为了战争利用“回教”,反而危害了中国“回教徒”的利益:“日本所谓大陆政策,必须要以文化和人道主义为基础。不能再是像他们在十九世纪中所做的那样一直坚持霸道的政治主义……就像日支事变那样,完全是由于支那一方的误解和错觉带来的恐日感,最后发展到排日、抗日,因思想倾向而想象为是一种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对立。结果使得支那大陆的三千余万回教徒,尸横遍野、气息奄奄,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境地。”(90)
说卢沟桥事变来自中国人对日本的误解,这当然是佐久间的一面之词。但他毕竟说出了一些事实真相:如果为侵略战争所利用,最后付出惨痛代价的,的确只能是“回教徒”自身。就像对外高喊着支持蒙古民族解放,私下里却千方百计阻止一样,(91)日本在战争期间之所以关心中国的“回教徒”,只是为了帮助推进侵略战争,丝毫没有帮助“回教徒”的目的,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六、结语
1938年7月,日本前驻外特命全权公使笠间杲雄在日本外交协会第266次例会上发表了《时局与回教》的演讲,他根据自己作为日本代表在土耳其、波斯、阿拉伯、埃及等国工作过的经验,针对当时日本国内的伊斯兰教热,就“回教工作”背后隐藏着的日本人以为自己才是伊斯兰教社会救星的想法,进行了严厉批评:“大家都以为不仅是支那的回教徒,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回教徒都在仰仗着日本人,希望得到一些什么帮助。而事实上,这些民族并没有仰望东方,借助日本的力量恢复民族独立的想法。都说日本是东洋的盟主, (日本——引者注)自己也确实有做盟主的心情,但是对方并没有请求(日本——引者注)一定担任这一角色。关于这一点,如不清楚认识,将来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之所以会成这样,完全是来自于日本人至今为止的傲慢。”(92)
其实,日本在中国的“回教工作”遇到了许多中国“回教徒”的抵制。但是为推进侵略战争, 日本军方发动宣传工具大肆鼓吹“回教工作”的成就,实是自欺欺人。例如,在“在北京茂川机关”的指导下为日本侵略战争摇旗呐喊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就被宣传为是一个极为活跃的“回教”团体。可事实上,在一位冷静的日本外交官眼里,那里不过是一片“门前罗雀的回教联合委员会”的景象。(93)
“回教工作”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帮助了日本的侵华战争?日本的关心究竟蒙蔽了多少“回教徒”,实在值得怀疑。然而,日本为什么会产生在侵略战争中利用“回教工作”的念头,却值得深思。毫无疑问,侵略者曾经认为,如果能够制造一个“共同的回教空间”,就能够覆盖住中国“回教徒”的“国家意识”;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让“回教徒”们以为日本理解、同情并且会保护“回教”和“回教徒”,他们就可以更加容易地跨越被侵略国家的门槛,并且达到占领或分裂中国的目的。但是,侵略者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广大伊斯兰教信众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向来都是反对外来侵略的,而他们自己在主动接触“回教”和“回教徒”时却明显地带着日本的国家色彩和侵略目的,因此,真正信任日本的中国“回教徒”并没有几人,“回教工作”在进入1940年代以后也渐趋式微。尽管如此,受到刺激的中国国民政府,也不得不针对边疆民族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集团,发起了又一轮确认近代国家主权范围、建设中华民族国家的运动。(94)
注释:
①由总理大臣(简称首相)、陆军大臣(简称后相)、海军大臣(简称海相)、大蔵大臣(简称蔵相)、外务大臣(简称外相)于1933年组成,主要就日本陆军和海军提出的所谓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军事问题决定大政方针。
②《時局ニ伴う対支謀略》,昭和十三年七月八日,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1類 帝国外交/1項対支那国/支那事変関係一件
第十四巻2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査询编码 B02030540000,立件名为《時局に伴う対支謀略》。
③本论文所使用的日本防卫研究所所藏战时日本陆军档案、日本外交史料馆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战时外交档案,虽有一部分为笔者过去直接査阅,但近年来随着日本档案公开工作的进行,大多可以通过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的档案査询阅览系统査阅到。因此,为了方便读者査询,本文在使用此类档案时全部统一为按照JACAR系统查询编码方法注明出处。
④桜井好孝:《蒙古視察復命書》,明治四十年一月,外務省記録/1門 政治/6類 諸外国内政/1項 亜細亜/蒙古辺境視察員派遣一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査询编码B03050331800。
⑤《公第一三四号 受第一三三四七号 現役兵証昼並二抽籤札領収昼廻送ノ件》,明治三十五年十月十日,外務省記録/5門 軍事/1類 国防/2項 兵役/本邦人徴兵関係雑纂 第十七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査询编码B07090106700,文件名为《桜井好孝、芝田辰治》。
⑥《中久喜信周調査 河南ノ回教徒》,明治四十三年十月,調書/調書/政務局。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査询编码B02130561800。
⑦《宗教ニ関スル一般ノ状況》,大正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外務省記録/1門 政治/5類 帝国内政/3項施政/関東都督府政況報告並雑報 第九巻4;《諸般政務施行成績 関東都督府》,大正二年度,8/第六。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査询编码B03041562800。
⑧《臨時軍事費使用ノ件》,大正七年四月,陸軍省大日記/欧受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JACAR系统査询编码C03024894800,立件名为《臨時軍事費使用の件》
⑨《諜報機関配置ノ件報告》,大正七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密大日記 4冊の内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JACAR系统査询编码C03022435700,文件名为《諜報機関配置の件報告》。
⑩《蒙古及新彊地方諜報機関配置ノ年》,大正七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密大日記 4冊の内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JACAR系统査询编码C03022436400,文件名为《蒙古及新彊地方諜報機関配置の件》。
(11)《台北県属滝九郎外三十一名召集免除ノ件》,明治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内閣公文雑纂/第二十五巻《台湾及庁府県ー》。国立公文書館蔵。JACAR系统査询编码A04010047100,文件名为《台北県属滝九郎。鳳山県巡査予備陸軍歩兵上等兵佐田繁治外十名。台北県弁務署主記後備陸軍砲兵一等軍曹門芳太郎外二名。台北県属後備陸軍一等書記加藤亮。台南県巡査後備陸軍…》。(省略号为原文所有——引者注)
(12)臼杵陽《植民地政策学から地域研究へ》(帝国主義と地域研究[報告一]),http://repository.tufs.ac.jp/bitstream/10108/26300/1/cdats-hub三.三.pdf.
(13)《印刷物送付之件通達》,大正十一年八月三十日,陸軍省大日記/欧受大日記《歐受大日記 自08月至09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JACAR系统査询编码C03025355100,文件名为《印刷物送付の件》。
(14)《山岡光太郎著〈回々教の神秘的威力〉購ノ/件》,大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外務省記録/1門政治/3類 宣伝/1項 帝国/宣伝関係雑件/嘱託及補助金支給宣伝者其他宣伝費支出関係/本邦人ノ部 第三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査询编码B3040728100,文件名为《山岡光太郎 回々教ノ神秘的威力 購入ノ件》。
(15)田中逸平在进行第二次朝觐时去向不明。坪内隆彦:《イスラーム先駆者田中逸平·試論》,http:// www.asia2020.jp/islam/tanaka_shiron.htm.
(16)《支那回教研究家 若林半、郡正三、細川將ノ三名ニ対シ北部支那及満洲国視察手當補給ニ關スル高裁案》,昭和十年九月十日起案,九月十一日決裁,外務省記録/H門 東方文化事業/6類 講演、視察及助成/本邦人満支視察旅行関係雑件/補助実施関係 第二巻3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統査询编码B05015680800,文件名为《支那回教研究家 若林半、郡正三、細川將 昭和十年九月十一日》。
(17)《漢字新聞 済南日報社内訌ニ就テ》,大正八年六月,外務省記録/1門 政治/3類 宣伝/1項 帝国/新聞雑誌操縦関係雑纂1/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査询编码B03040600500,文件名为《1/3 大正6年6月から大正9年5月12日》。
(18)坪内隆彦:《イスラーム先駆者田中逸平·試論》,http://www.asia2020.jp/islam/tanaka_shiron.htm.
(19)《支那回教研究家 若林半、郡正三、細川将ノ三名ニ対シ北部支那及満洲国視察手當補給ニ關スル高裁案》,昭和十年九月十日起案,九月十一日決裁,外務省記録/H門 東方文化事業/6類 講演、視察及助成/本邦人満支視察旅行関係雑件/補助実施関係 第二巻32。
(20)中国回教朕合会华北联合会总部编:《中国回教联合会第一年年报》,北京内部出版发行,1939年2月,第31-32、42、45-49、89、93页。
(21)回教圏考究所編:《回教圏史要》,東京:四海書房,1940年1月,第300頁。
(22)《満洲の回教》,昭和十三年二月七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 分割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33400。
(23)杨敬之:《日本的回教政策》,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23页;保坂修司:《アラビアの日本人日本のムジャーヒディーン》,《中東協カセンターニュース》,第45-49頁。http://www.jccme.or.jp/japanese/11/pdf/11-05/11-05-41.pdf#search.
(24)今冈十一郎(1888-1973),出生于日本岛根县,1914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語学校徳语专业,后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留学,1931年回到日本后,作为“嘱讬”进入日本外各省欧亚局一课,并担任“日本匈牙利文化交流协会理事”,成为当时日本推动图兰主义(Turanism,即提唱欧亚大陆各民族朕合)的主要人物,其关于匈牙利历史文化的著作颇丰。关于他在“日本匈牙利文化交流协会理事”的活动,参见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1類 文化、文化施設/本邦ニ於ケル協会友文化団体関係雑件/日洪文化連絡協議会関係2.第二回会議 (昭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424900。
(25)《回教研究会、外務省欧亜局第一課今岡嘱託報告》、《報告 (績)欧亜一課今岡嘱託》,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至十三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一巻 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33200。
(26)《西北回教民族文化協會ノ組織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1類 文化、文化施設/各国ニ於ケル協会友文化団体関係雑件/中国ノ部5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396100。
(27)《第一七号 (部外極秘)》,昭和十三年五月九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2.満洲国。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50300。
(28)《第一六号 (部外極秘)》,昭和十三年五月九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2.満洲国。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50300。
(29)《第一五号極秘》,昭和十三年五月七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2.満洲国。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4012550300。
(30)山名正二:《日露戦争秘史 満洲義軍》第六章第五節、第七章第一節,月刊満洲社東京出版部,1942年9月。
(31)于泾:《有关东北伪军的几个历史问题》,《文史长廊》2005年第5期。
(32)《勲労確認書》,明治三十七年六月四日,陸軍省大日記/日露戦役《勲労確認書等控綴 明治三七年五月以降 大本営陸軍副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C06041013000,文件名为《陸軍歩兵少佐 花田仲之助》。
(33)《召集解除人名別紙及通報候也》,明治三十九年二月,陸軍省大日記/日露戦役/《臨号書類綴 参謀本部副官管》。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C06041300300,文件名为《歩兵中佐花田仲之助外一名召集解除の通牒 陸軍省副官地》。
(34)《便乗許可ノ件》,昭和十年,陸軍省大日記/陸満機密·密·普大日記/陸満普大日記 《満受大日記(普)其52/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C04012142300,文件名为《便乗許可の件》。
(35)《報徳会幹事花田退役中佐離通二関スル件》,昭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外務省記録/Ⅰ門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4類 労働及社会問題/国民思想善導教化及団体関係雑件 第二巻3.報徳会関係。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3004800。
(36)谷萩那華雄:《日露戦争秘史 満洲義軍》,“序”。
(37)《祝電依頼之件》,昭和十七年,陸軍省大日記/壱大日記/《壱大日記第9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C04014965200,文件名为《祝電依頼の件》。
(38)《第六号ノ一(部外極秘)》,昭和十四年一月十三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波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3.中国分割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50400。
(39)《第二○号 (部外絶対極秘)》,昭和十三年五月十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2.満洲国。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50300。
(40)《第一六号(部外極秘)》,昭和十三年五月九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2.満洲国。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50300。
(41)《第一五号極秘》,昭和十三年五月七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2.満洲国。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50300。
(42)中国回教华北联合会总部:《中国回教联合会第一年年报》,第31-32、42、45-49、89、93页。
(43)《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主催回教徒訪日視察団ノ見学ノ件》,昭和十三年,陸軍省大日記/陸支機密·密·普大日記/陸支密大日記,5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C04120561300,文件名为《蒙古?盟自治政府主催回教徒訪日視察団の見学の件》。
(44)《昭和十九年三月現在 日系職員名簿》(其一),昭和十九年三月,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6類 諸外国内政/1項 支那国/満蒙政況関係雑纂/蒙古連合自治政府官吏録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2031793100。该名单扉页上题目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而名单每页上方第一页印着“蒙古自治政府”,因为后者为日文,本文使用前者。1937年10月成立蒙古朕盟自治政府,1939年9月成立蒙彊朕合自治政府,1941年8月再改名为蒙古自治邦。但日方记录中各处名称不一。
(45)《回教対策樹立ノ急務ニ就テ》,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33600。该文件未注明时间,但是从本文内容及同卷其地文书上来看,应该是昭和十三年四月至五月的档案。
(46)《回教対策樹立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三年八月,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33600。
(47)《支那事変ニ於ケル情報宣伝工作概要三》,昭和十三年九月,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1類 帝国外交/1項 対支那国/支那事変関係―件/輿論並新聞論調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2030585300。
(48)《張家口領事諜報者雇用ノ件》,大正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外務省記録/1門 政治/3類 宣伝/1項 帝国/宣伝関係雑件/嘱託及補助金支給宣伝者其他宣伝費支出関係/外国人ノ部 第八巻1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3040747200。
(49)《第七九号 (部外極秘)貴電第三五号ニ関シ(《イスラム》 同盟ニ関スル件),昭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3.中国 分割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50400。
(50)中国回教华北联合会总部:《中国回教朕合会第一年年报》,第10页。
(51)《西北地方ニ於ケル回教並一般情況等報告方ノ件》,昭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波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3.中国 分割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50400。
(52)《青海馬步芳利用方二関スル件》,昭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4類 労働及社会問題/各国ニ於ケル反共産主義運動関係雑件 第三巻3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4012985200。
(53)回教圏考究所編:《回教圏史要》,第293頁。
(54)《第五九号ノ一 至急 極秘》,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 第三巻 14.満洲国 (1)一般及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43400。
(55)《兵器払下ニ関スル件》,昭和六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昭和六年《密大日記》第1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C01003951700,文件名为《兵器払い下げに関する件》。
(56)《馬步青馬步芳ニ対スル兵器売渡ノ件》,昭和十二年,陸軍省大日记/密大日记/昭和十二年《密大日記》第7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C0l004340900,文件名为《馬步青馬步芳に対する兵器売渡の件》。
(57)《支那ニ兵器賣却ノ件》,昭和十二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昭和十二年 《密大日記》第8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C01004346900,文件名为《支那に兵器売却の件》。
(58)《額済納特務機関員ノ情況二関スル件》,昭和十三年,陸軍省大日記/陸満機密·密·普大日記/陸満密大日記/昭和十三年/昭和十三年 《満受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C01003367400,文件名为《額済納特務機関員の情況に関する件》。
(59)《額済納特務機関員ノ情況二関する件》,昭和十三年,陸軍省大日記/陸満機密·密·普大日記/陸満密大日記/昭和十三年 《満受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C01003367400。
(60)《新疆及青海事情並馬步芳/対日態度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3.中国 分割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50400。
(61)《青海馬步芳利用方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4類 労働及社会問題/各国ニ於ケル反共産主義運動関係雑件 第三巻3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985200。
(62)《蒙情電第二九七号》,昭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3.中国 分割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50400。
(63)回教圏考究所編:《回教圏史要》,第296頁。
(64)佐久間貞次郎:《回教の動き》,東京:春日書房,1938年,第230頁。
(65)《補助金使途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七年九月十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 分割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33700。
(66)《本邦二於ケル最近ノ回教問題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第二巻 分割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33500。
(67)《大日本回教協会創立費会計報告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三年十二月九日,外務省記録/Ⅰ門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波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33600。
(68)《大日本回教協会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五年四月十九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33600。
(69)《大日本回教協会ニ対スル補助金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五年七月十日起案、七月十六日裁決,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
分割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33700。
(70)《大日本回教協会本部業務分担表》,昭和十五年四月十九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33600。
(71)《回教対策樹立ニ関スル件》和《本邦ニ於ケル最近ノ回教問題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三年八月,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33600。
(72)《世界回教徒大会開催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五年五月十九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 分割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4012533700。
(73)研究会的报告内容,现在可知的有:《回教研究会,外務省欧亜局第一課今岡嘱託報告》、《報告 (續)欧亜一課今岡嘱託》,昭和十二年六、十三日(以上两文件参见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Ⅰ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一巻 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33200)。外務省東亜局第一課中田通訳官,《回教研究会研究報告》,昭和十三年一月十七日;外務省東亜局第三課牟田副領事官:《満洲の回教》,昭和十三年二月七日;外務省東亜局第三課白坂嘱託:《南洋回教徒ノ情勢》,昭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外務省調査部第三課田邊嘱託:《印度回教徒問題》,昭和十三年三月十七日;六月外務省調査部第三課:《伊大利ノ回教政策》(以上五文件参见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 分割1。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334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軍令部第三部犬塚大佐:《極東猶太財閥最近ノ動向ト之ガ対策二関スル研究》,昭和十三年四月 (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第二巻 分割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33500)。
(74)《回教研究会、外務省欧亜局第一課今岡嘱託報告》、《報告 (績)欧亜一課今岡嘱託》,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六、十三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一巻 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33200。
(75)《回教 (及猶太)問題委員会ノ設置及経過ノ件》,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该文件未注明时间,但是从本文内容及同巻其地文书上来看,应该是昭和十三年四月至五月间的档案。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33600。
(76)《回教及猶太教問題委員会内規》,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该文件未注明时间,但是从本文内容及问卷其他文书上来看,应该是昭和十三年四月至五月间的档案。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33600。
(77)《回教対策樹立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三年八月,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33600。
(78)《宗教団体法二関スル件》,昭和十四年四月―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33600。
(79)《文書返送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三年,陸軍省大日記/陸支機密·密·普大日記/《陸支密大日記 63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C04120639500,文件名为《文書返納に関する件》。
(80)《回教青年指導要綱》,昭和十三年,陸軍省大日記/陸支機密·密·普大日記/《陸支密大日記 73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C04120707300。
(81)《蒙疆重要政策ニ対スル思想統一二就テ》,昭和十四年五月三日,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1類帝国外交/1項 対支那国/支那事変関係一件 第十九巻28。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2030558900。
(82)《第七号、往電第六号ニ関シ》,昭和十四年一月十四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3.中国 分割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50400。
(83)《厚警高秘第二一四五号》,昭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3.中国 分割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50500。
(84)《六支那ガ長期抵抗ニ人ル場合ノ情勢判断》,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1類
帝国外交/1項
対支那国/支那事変関係一件 第十八巻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2030548200。
(85)《四重要国策関係 (支那事変中)/十六/対立時局対策》,昭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外務省記録/A門政治、外交/1類 帝国外交/1項 対支那国/支那事変関係一件 第四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2030524300。
(86)《時局ニ伴う対支謀略》,昭和十三年七月八日,《五相会議決定》,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1類帝国外交/1項 対支那国/支那事変関係一件 第十四巻2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2030540000。
(87)《支那駐屯軍司令官訓令ノ件通達》,昭和十一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记/昭和十一年《密大日記》第1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C01004134100,文件名为《支那駐屯軍司令官訓令の件》。
(88)《第一八号ノ一 (別電、部外極秘)》,昭和十三年五月九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2.満洲国。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50300。
(89)《調査会報告書〈大東亜建設基本方策ノ具現並二之二対スル圏内諸民族/協カヲ要スル事項及右確保万策 (乙 南方諸地域)〉上申ノ件》,昭和十八年五月十日,同《華僑対策》及同《〈回教徒対策〉上申ノ件》,内閣/公文雑纂·昭和十八年·第七巻·内閣七 (大政翼賛会関係二)。国立公文書館所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A04018704100,文件名为《調査会報告書 〈大東亜建設基本方策ノ具現並ニ之ニ対スル圏内諸民族ノ協カヲ要スル事項及右確保方策 (乙 南方諸地域)》、同《華僑対策》及同《〈回教徒対策〉上申ノ件…》。
(90)佐久間貞次郎:《回教の動き》,第85頁。
(91)《対蒙政策要綱》,昭和十三年十月一日,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1類 帝国外交/1項 対支那国/支那事変関係一件 第十八巻28。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2030550400。
(92)《時局と回教》,昭和十三年十月,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3類 宣伝/3項 啓発/本邦対内啓発関係雑件/講演関係/日本外交協会講演集 第五巻7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2030922100,文件名为《時局と回教 (前特命全権公使、笠間杲雄)》。
(93)《済南発閣下宛電報第五二号二関シ》,昭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外務省記録/Ⅰ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3.中国 分割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50500。
(94)《白崇禧ノ日本軍西北工作妨害》,内閣/各種情報資料/各種情報資料/各種情報資料·支那事変ニ関スル各国新聞論調概要。国立公文書館所蔵。JACAR系统查询编码A03024015400。(该文件未注明时间,但是从本文内容及同卷前店排列其他文书上来看,应该是昭和十三年五月间的档案——引者注)该资料在JACAR系统上件名为《米国 白崇禧/日本軍西北工作妨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