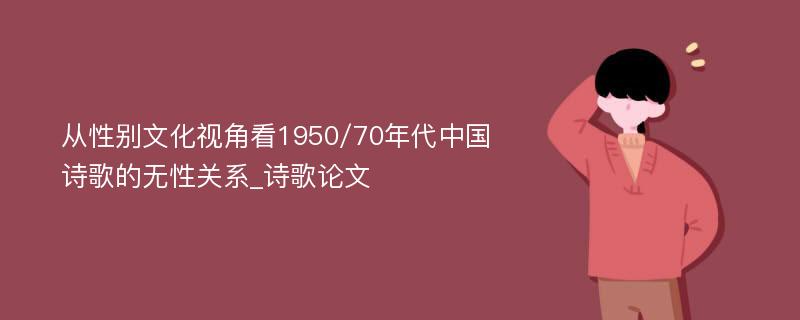
无性的两性关系:性别文化视野中的1950-1970年代中国诗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性关系论文,中国论文,诗歌论文,视野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5)01-0163-06
1950-1970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的中国诗歌,一般被认为缺少艺术审美性,没有 研究的价值。现在人们重新关注“文革”文学,其着眼点也是想在这种所谓“无价值” 的文学状态中寻找出新价值。所以,他们更关注如何发掘出有价值的作品——如对“白 洋淀”等文学社群为代表的“地下写作”(也有人将其称为“潜在写作”)的发现。我对 这样的“文学史重写”并不太感兴趣。我相信,每一个时代的书写都是这一时代话语的 鲜明而具体的历史性体现。
我感兴趣的是在1950-1970年代——这个特定时代的诗歌话语中,男女两性关系的存在 状态及其文化意义。我们都知道,中国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流行话语之一就是“妇女解放 ”、“男女平等”。我的着眼点是,将这个时期(社会已经解放,女性也被新政权赋予 了与男人平等的政治地位)的诗歌文本置于20世纪中国“妇女解放”的文化语境,通过 对其所想象和型塑的“女性形象”进行性别文化解读,力图真实地再现这一时期中国文 化中的性别图景。
(一)
“女性”作为文学描写和表现的形象始自文学的起源。人类通过文学这种言说方式将 自己的生活形态和生存处境再现和保留下来。在这个由男女两性共同构成的世界里,正 是他/她们的互动和参与,创造了人类最初的成就和辉煌,也创造了人类自身。按理说 ,男女两性共同创造的成就和辉煌,也应该由两性共同分享。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在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我们只见到男性的身影,听到男性的声音,女性被隐藏在男性 的身后,无声无息。男性化文明的这一缺陷,导致了人类在认识自我时的单一视野以及 由此带来的狭隘和偏见。因而,尽管女性人生作为人类生命形式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并 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文学的重要内容,例如在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最有生活气息 的“风”部分,共收十五国风,计160篇,据前人的考证和研究,其中关于女性问题的 就占85篇。[1]但是,在文学中,女性却没能与男性一起共同分享其创造世界的乐趣和 荣耀,她的世界已被限制在狭小的家庭范围之内。
综观自《诗经》始的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诗歌中被描述和表现出来的女性生活方式 及形象特征,也如现实的女性处境一样,实质上是一部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愿望和要求 史。这种愿望和要求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父权制社会基于保护家庭而对女性提出 的要求,即所谓“正夫妇”而表“妇德”,这在《诗经》开篇《关雎》的题解中可看出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诗经》只是当时 诗歌创作的一个编选本,虽然它没有明确的作者署名,难以确定其性别归宿,但从所选 诗歌表现的内容来看,已能看出编者的性别观念。因为,诗歌中女性形象及其生活已被 有意识地限制在恋爱、婚姻的题材内。这种阐释也开启了此后这类诗歌女性主题的题材 规范。另外,就是男性生理和心理对色欲的要求,这一要求因有悖于“妇德”的提倡而 转化成了一种潜意识。康正果先生在《风骚与艳情》一书中对此有很精当的分析。他用 “风骚”与“艳情”来概括中国古代诗歌中因这两种“要求”而伴生的两种对峙的诗歌 类型,同时也因这种“要求”而衍生出了两类主要的女性形象:一是有“妇德”的理想 的女性;另一类是那些靠色艺供男人娱乐的女性。[2]在几千年的超稳定的中国封建宗 法社会,女性就是以这两种形象生存在同样超稳定的封建意识形态结构——古代文学史 中。
历史证明,是父权制社会规定了女性的生存空间,是统一的男性中心文化在塑造女性 的形象、规定着她们的身份和生活场景。对两性来说,世界已经发生了倾斜,它属于男 性,女性只属于男人的家,因而没有权利与男性一起享受创造的快乐。
这两类女性形象在现代诗歌创作中有了新的发展。作为向封建宗法制反抗的一种策略 ,“革命”将女性纳入同盟军。第一次,中国女性走出狭隘的家庭和闺房,与男性一起 肩负改变社会的重任。这一历史性巨变表现在诗歌中,“色艺女性”的形象被逐渐清除 出诗歌,“理想女性”的形象进一步被强化。社会意识话语在几个方面强化着“理想女 性”的形象。
一方面,它在道德上强调一种具有传统意义的“女性美德”——实质上即传统“妇德 ”,如冰心笔下的仁厚、慈爱、无私、坚韧的母亲;如戴望舒笔下给人温暖和幸福的“ 天使”——妻、女:“我没有忘记,这是家,/妻如玉,女儿如花,/清晨的呼唤和灯下 的闲话,/想一想,会叫人发傻”(戴望舒《过旧居里》)。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强化 她们的不幸处境和命运,以引起人们认识社会政治的黑暗,较典型的如艾青的《大堰河 ,我的保姆》中的“大堰河”。另外,年轻女性的形象则充满了时代变革的气息,如丁 玲的《给我的爱》就洋溢着强烈的改造社会的英雄梦想:“我们不是诗人,/我们不会 讲到月亮,也不会讲到夜莺/还有那些所谓爱情,/我们只讲一种信仰,它固定着我们的 心。”白薇的《祖国,我回来了》更直接地表明献身国家的忠心:“祖国,我爱你,/ 我回来了,/我要投在你的怀抱里,做你忠实的女儿!为着祖国的解放,/尽我一份热情 。”响亮的“妇女解放”的性别话语连同“女性的声音”逐渐淹没在强大的国家、民族 解放的政治话语中。这一点在1950年代以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1949年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年。随着一个新的政权形式的建 立,女性终于获得了自“五四”开始努力追求的“解放”,取得了同男人平等的政治身 份。共和国政府颁布的第一部重要法律就是婚姻法,它首先确立了男女两性在婚姻关系 中的平等地位;1951年,政府又制定了“劳动保护条例”,规定了女工与男工享有同样 的劳动保护;1953年2月通过的“选举法”规定了男女公民都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特别是1954年颁布的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 生活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由“五四”开启的“妇女解放”的目标——“男女平 等”的性别理想终于成为现实。“男女平等”、“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 能顶半边天”等成为当时社会性别关系的主流话语。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取得了当然的地 位,不再被限定在封闭的家庭里,而是参与到了新时代的建设之中,并逐渐获得了在社 会上自食其力的经济能力。
女性的这种政治身份和经济地位是否在诗歌中得到体现?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诗歌 中具有怎样的形象特征?这样的形象特征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女性地位的这一“解 放”是否真正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别关系?如果女性真的获得了“解放”,何以在妇 女已经被“解放”了30年的80年代,“性别问题”突然又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 。80年代中期兴起的“女性诗歌”创作热潮就是它的一个反映。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自 50年代开始的“性别平等”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并认真加以审视。
(二)
一般说来,女性形象更集中地表现是在歌咏爱情和婚姻的诗作中,这也是传统的女性 生活题材。由于爱情、婚姻是连接男女两性最直接的桥梁,因而在一个时代的爱情、婚 姻关系中男女两性所处的地位最能反映这一时代的性别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应该 是我们检查并审视两性关系时最值得讨论的部分。
然而,当我仔细检索这一阶段有关爱情、婚姻的诗作时,才发现,要试图在这些诗中 探寻那个时代人们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是一种徒劳(这其中排除了林子等人写于此时但 发表于80年代的诗作)。这一时期表现爱情的诗作数量不多(特指公开发表的),且由50 年代到60、70年代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如同其他类型的诗歌,这时期的爱情诗无论是在 主题的确定,题材的选择,还是风格的倾向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单纯性,呈模式 化发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50年代成名的闻捷,他可以被称为这个时代的“声音”。
闻捷的组诗《吐鲁番情歌(三首)》因表现新时代的美好爱情名噪一时,其中《苹果树 下》、《舞会结束以后》等诗最具代表性,这些诗歌中的女性形象也较为鲜明。如在《 苹果树下》一诗中,对小伙子的大胆追求,姑娘先是惊慌、害羞,诗人写到:“苹果树 下那个小伙子,/你不要、不要再唱歌;/姑娘沿着水渠走来了;/年轻的心在胸中跳着 。/她的心为什么跳呵?/为什么跳得失去节拍?……”经过小伙子春天、夏天的不懈追求 ,到了秋天,姑娘终于动心了:“淡红的果子压弯绿枝,/秋天是一个成熟季节,/姑娘 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是不是挂念那树好苹果?/这些事小伙子应该明白,/她说:有句话 你怎么不说?”最后,姑娘内心终于接受了小伙子的追求:“说出那句真心的话吧!/种 下的爱情已该收获。”诗人通过一系列富有生活气息的场面,给我们描绘出一个情窦初 开的少女形象。与以前诗歌不同的是,这一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这似乎正 印证了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其实不然。这种爱情关系仍然具有很强的传统色彩,女性的形象仍未超越传统。诗人 用枝头未开放的“花苞”来喻指未嫁的少女,这个意象本身就具有明显的传统意蕴,如 《诗经》中就有很多用植物的生长(如《桃夭》)暗示女子长大成人、进入嫁娶的诗句, 《离骚》中也常以香草喻美人。在《风骚与艳情》一书中,康正果先生经分析考证,认 为这和古人的生育观念有关,中国古代文化极为重视生育,民间常有“多生贵子”、“ 早生贵子”之说,即指此意。因而,他们由植物生长的茂盛、开花、结果,联想到女性 承担的生育繁衍任务。[3]后来,意象的实用义——“生育繁衍”渐渐淡化,其审美性 增强,并逐渐扩大和凝固为泛指笼统的“女性美”,既有带“观赏性”的所谓“香草美 人、芙蓉出水”等,也有含贬损性的“杨柳风姿、水性扬花、残花败柳”等寓意。
对这种用“花苞”之类物象指代女性的隐喻,戴锦华曾有过很精辟的论述。她认为, “当女性外观被物化为芙蓉、弱柳或软玉、春葱、金莲之美时,其可摘之采之、攀之折 之、弃之把玩之的意味隐然可见。在这种人体取物品之美的转喻中,性欲或两性关系实 际上已经发生了一个微妙转变,它不仅表现或象征着一种对女性的欲望,而且借助物象 形式摈除了女性自身的欲望,它所表现的与其说是男性的欲望,不如说是男性的欲望权 。”[4]所以,从这首诗中“花苞”、“果子”、“采摘”等意象可以看出诗歌中所蕴 涵的男性立场。而在整个求爱阶段,这一立场就更鲜明:“姑娘”一直处于被动,“小 伙子”采取主动。诗人用了“小伙子”“去采摘”“成熟的果子”这个意象来表现男女 两性在婚恋嫁娶中的这种“主动和被动”关系。
这样的性别立场在闻捷的其他诗歌中处处可见,如《葡萄成熟了》一诗中,主动者也 是男性,女性成为男性“挑逗”和追求的对象:“小伙子们并排站在路边,/三弦琴挑 逗姑娘心弦”。这些意象明显地道出传统的两性观念,男性是恋爱的主体,女性是男性 追求的“对象”,是他要“采摘”的“果子”。这表明,尽管时代场景和女性的社会身 份改变了,但男性对女性性别的认知方式并未有多大改变。
这种传统爱情理念在当时的许多诗歌中不断得到确认,只是诗歌更加强调爱情的“忠 贞”品质,而且这种“忠贞”已经超越单纯的男女两性关系,其献身的对象已转换成以 工作、事业为名的“集体”。如在《舞会结束以后》一诗中,闻捷就试图歌颂一种新型 的建立在劳动关系上的忠贞爱情。诗人描绘到:舞会结束后的深夜,“琴师”和“鼓手 ”都争着送“土尔地汉”回家,实际上是“看上了她”,要追求她。对两人热烈的追求 ,“你到底是爱琴还是爱鼓?/你难道没有作过比较?”诗人让“土尔地汉”回答到:“ 去年的今天我就作了比较,/我的幸福也在那天决定了,/阿尔西已把我的心带走,带到 乌鲁木齐发电厂去了。”无论怎样的甜言蜜语也未能动摇“土尔地汉”对远方恋人的忠 贞。
当时表现同样主题的诗还较多,如李季的《黑眼睛》,在当时也是颇受欢迎之作。此 诗写于1954年。诗人用一双“温柔钟情”的眼睛来指代一个暗恋“我”的少女:“不论 是在图书馆里,/或者是蒸馏塔旁,/总有一对又黑又大的眼睛,/悄悄地对我张望。// 每逢我们超额完成了计划,/那双眼睛就显得分外明亮;/若是我们不小心出了事故,/ 它就像阴云密布的天空一样。//黑眼睛为什么那样温柔钟情,/黑眼睛为什么一直对我 张望——/是不是她也希望多出汽油,/还是看中了我的模范奖章?//亲爱的又亮又大的 黑眼睛呵,/请你再不要对我张望;/你若是真的爱着煤油、汽油,/我们欢迎你到炼油 厂;//假若你是喜欢那颗金色奖章,/真诚的劳动一定会得到报偿;/至于你要是为了别 的什么,/那么,请你听我说吧:/祁连山下,有一个放羊的姑娘……”但是,读到最后 ,我们才发现诗人并不是要表现“少女”处在“暗恋”中的复杂情感,也未看到“我” 的情感冲突,真正的“爱情”实际上已经消遁。将两首诗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舞会结 束以后》显得直截了当,而《黑眼睛》则要写得含蓄委婉些,而且两首诗的写作角度也 不一样,《黑眼睛》显然是一个男性主人公在叙说自己对“爱人”的忠贞,《舞会结束 以后》是第三人称,取中立立场。
但是,李季对闻捷并未有所超越,两首诗歌给我们投射出的都是鲜明的男性立场—— 只是这一立场被隐晦地潜藏于“发电厂”、“炼油厂”等等以“集体”形式出现的时代 语境中,因而,无论是“土尔地汉”还是“黑眼睛”所指代的姑娘,都成了诗人表达“ 忠贞”这一社会理念的语义代码,我们看不到爱和被爱者内心的情感波澜和生命体验。
这些诗歌传达了同样一个信息:道德的和高尚的爱是远离人的身体欲念的,爱情是劳 动生活的一部分,真正的爱情是和劳动、荣誉联系在一起的。诗人并不是要为表达青年 男女对爱情的真实体验和渴求,也不是要探讨新的人生处境中人们的情感变迁,因而, 私人性的表达消失了,我们只感受到一种单纯、明快的情绪,却无法进入丰富复杂的人 性世界。
然而,这一基调却很快地成为爱情诗的一个模本,同类型的诗作大肆流行,如田地的 《探望》、白堤的《收获期的情话(二首)》、纳-赛音朝克图的《蓝色软缎的“特尔力 克”》、包玉堂的《走坡组诗》、完忆萱的《在矮矮的灌木丛边》、忆明珠的《唱给蕃 瓜花的歌》等等。这种情爱观念成为社会的道德标准,最后甚至走到极端,像闻捷的《 种瓜姑娘》就直接要求对方拿“奖章”换“爱情”:“枣尔汗愿意满足你的愿望,/感 谢你火样激情的歌唱,/可是,要我嫁给你吗?/你衣襟上少着一枚奖章。”
最后,当爱劳动、忠贞逐渐成为社会对新时代“女性品质”的期待并被不断强化时, “爱情”从两性关系中退场,女性形象也就成为了诗人表达社会理想的一个“符号”。 不仅如此,作为人的人性内涵的个性特征也逐渐被强大的“集体”的力量所规训并剔除 。与两性关系的这种“人性”内涵一起丧失的还有诗歌作为艺术的魅力和审美价值。
苏金伞写于1963年的《吴琴的心》是一个典型的诗歌表现。诗歌正面描写了年轻寡妇 吴琴为丈夫守寡和尽孝的故事,而这也是传统的宣扬“妇德”的主流题材。在诗中,吴 琴忠贞、孝顺,更重要的是她还“爱党爱公社”。诗人这样写道:当丈夫抗美援朝牺牲 后,她对婆婆说,“妈,我永远留在你身边,/你指望儿子的我都一概承担!”在生产劳 动中,“——如果有人在队里干活偷懒,/看见吴琴就会羞愧得无地容身”。最后诗人 总结道,“爱吴琴就是爱党爱公社,/社员的脉搏都通着吴琴的心。”只是传统的对“ 丈夫、家族”的“贞洁柔顺”的“妇德”内涵已经扩大为对“集体、国家”的忠贞。诗 人力图给我们树立起一个“新时代”的模范女性形象。而这其中充溢着的男权化性别意 识卓然可见。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体现在这样的诗歌中的爱情、婚姻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它已从两性之间性和爱的吸引转移到对“对象”的道德品质和职业精神的要求和期待。 实质上,在这些女性形象(尤其是吴琴这一时代的模范女性)中,女性的外貌、身材、个 性、欲望等都已经消失,只剩下一个被抽象化了的女性品德。这种完全脱离了生命体验 和欲念的爱情,在今天看来真有点不可思议,但它却真实地表现出当时社会主流的爱情 观、性别观。这时期的“爱情”成了纯精神性的“冥想”,毫无“性”的内涵。两性关 系也就成了纯粹物质意义上的“生产合作”关系。同时,诗歌已经不再是诗歌——它丧 失了其艺术性而成为了作者表达其社会及人性理想的纯观念载体。
(三)
令人深思的是,在这一阶段,女性诗人则很少抒写爱情题材。而就在这少量的爱情诗 歌中,男女两性的角色期待以及两性关系的图景表现出与男性诗人极度的一致性。
典型的如黄雨的《我不知道怎样爱上他》:“我不知道怎样爱上他/当他为通红的炉火 所照亮/在一千八百度高温的旁边/凝视着沸腾的青蓝的钢水/我的眼光就一刻也离不开 他//当他机警地撬开密封的炉口/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从钢珠迸射中纵身跳出/对着激 荡奔泻的钢流微笑/我的眼光就一刻也离不开他//当他打开了‘黑色的冶金学’/像在黑 夜里探索崎岖的山路/艰难地探索着一字一句/要登上那科学的高峰/我的眼光就一刻也 离不开他//我不知道怎样爱上他/他说自己只是一块矿石/跟铁水一同在锻炼长成/他爱 钢胜过自己的生命/我爱他,像他爱钢一样忠诚”。“我”对“他”的爱和忠诚是因为 “他爱钢胜过自己的生命”,他的热爱“劳动”成为“我”爱“他”的唯一基础和标准 。同闻捷和李季的诗歌相比,我们并未发现这首诗在对爱情的表达和渴望上有什么不同 的因素。“钢铁”、“矿石”既是男性力量的象征,又是“集体”的权力标志。因而, 诗歌中的“女性形象”逐渐被诗人削去性别特征,从而被无性化、观念化。
消灭性别特征,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女性诗人的自觉选择。我认为根源在于“妇女解放 ”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引导。毛泽东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做得 到的事,女人也能做到”等话语成为新中国女性确立自我身份的标准。如张雅歌在《我 就是爱飞》一诗中所直接道出的:“我”“怎不爱飞呵,/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航向;/ 妇女能顶半边天,/在我们时代男女都一样!”“她们”真的成了新社会要求的“铁姑娘 ”。为了达到这样的与“男人”平等的标准,她们只好尽力去削去自己身上的性别特征 ,以达到新的社会对她们的身份认同。
这种选择体现在她们的诗歌中,就是“女性形象”的“无性别”色彩更加鲜明,“个 人自我”的声音更难以听到。如50年代比较活跃的女诗人杨星火,在其《山冈上的字迹 》、《金色的拉萨河谷》、《雪松》等代表作中,我们看不到女性的身影也听不到女性 的声音,甚至诗人常常化装成男性出场,有意识地抹掉性别特征。到70年代,这种倾向 更得到强化,女性完全消遁,诗歌中的性别话语一概笼罩在“男性化”的气氛中。如李 小雨的《我的阵地》,诗人将工作的岗位看成是战斗的阵地:“一间土屋——八平方米 ,/这小小化验室就是我的阵地。”而工作则“像空军战士查看每片云朵,/像海军战士 清点每座岛屿。//写下一份份闪光的报告——/是我献给党的最好战绩”,“虽然我身 边没有硝烟炮火,/可战斗却打得同样激剧。//日日夜夜,分分秒秒,/我和战友一起在 不同的战线冲锋杀敌。//虽说我的阵地只有八平方米,/却紧连着伟大祖国的千里万里! ”“我”的性别身份更难以辨认,其性别观念可见一斑。
由此看出,社会给予了女性同男性一样的政治地位,它也就用“平等”剥夺了男女各 自的自我主体身份,这是我们在审视这时期诗歌中性别关系时要特别注意的。
追根究底,诗歌中这种“无性化”倾向,早在50年代初期就有所萌芽。比较典型的有 梁上泉的《姑娘是藏族卫生员》和胡昭的《军帽底下的眼睛》。现举胡昭的《军帽底下 的眼睛》一诗为例,此诗写于1952年12月,与闻捷的《吐鲁番情歌》几乎同时。诗人描 绘了一个年轻的战士在被同样年轻的女卫生员救助时的心理活动:面对女卫生员“军帽 底下/闪动着的一对眼睛”,“我想起妹妹的眼睛/那么天真而明净,/我想起妈妈的眼 睛/那么温暖那么深……”,因而发誓,“我要保卫那对眼睛——/妹妹的眼睛,妈妈的 眼睛,/我亲爱的祖国的眼睛!”青年男女接触时,无性爱的冲动,而只想到自己的妹妹 和母亲,从这里,也可窥见当时的两性关系。
这种现象表明,新的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倾向于建立在——好女人,更应该说是好公民 ——这样的道德意义上的。这样的道德观念仍植根于以男性为本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中 。因而,它必然预示着女性在获得了“社会身份”的同时,也失去了她本该具有的某些 “身份”。所谓的“男女平等”,只不过是将女性变成男性的话语表达,通俗地说,就 是要求女性变成和男人一样,“男人能做得到的事,女人也能做到”。
然而,就是这样“纯洁”(毫无性别意义)的“爱情”,最后也被批判为写“不健康的 思想”,“小资情调”,而被迫退场。到“文革”时,发展到极致,所有的性别差异全 被取消,不光爱情、女人、男人、妻子、丈夫等带有“性爱”色彩的字词不能提,就连 大哥、大嫂、小姑娘这样的表性别差异的中性词也成为禁忌。有两个事例很有代表性。 一是郭小川的《林区三唱》,因写有“三个妇女,必谈丈夫”,被认为“出格”,在收 入诗选时被粗暴删去。[5]另一个是诗人张永枚对自己的诗作《骑马挂枪走天下》的修 改。此诗写于1954年,到了1973年,作者对它进行了大修改,由原来的34句诗改为19句 。如把“我们到珠江边上把营扎,/推船的大哥为我饮战马,/采茶的大嫂为我沏茉莉花 茶,/小姑娘为我把荔枝打”,修改为“我们到南海边把根扎,/乡亲们待我们胜过一家 。/阿妈为我们补军装,/阿爹帮我们饮战马”。[6]这样,诗歌语境中的两性关系完全 向“无性化”发展,作为具有“性征”特点的年轻女性(甚至最后也包括男性)从文本中 彻底消失,仅留下“母亲”(阿爹和阿妈)这一抽空了实际内涵的“语符”,女性形象最 终成为了一个“空洞的能指”。
1950-1970年代中国诗歌文本中的这一性别图景,真实地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化在对两性 关系的“平等”理想进行建构时存在某种缺失。它仍然是男性本位的,因而不能目的性 地服务于两个性别群体。“被解放了的女性”的现实处境与社会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存在 着巨大的差异性。女性主体自我并没有因为国家的解放、妇女的解放而诞生。相反,随 着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女性”完全消失、融会于一个中性的概念“人”,而此 “人”因其在文化历史中所涵盖的内涵必然使其指向传统的男权价值系统,在这个系统 中是不存在女性的。因而,“男女平等”就变成了单向度的女性向男性身份的认同,男 性身份也就成为女性建构自我的唯一参照标准。这一认识上的先天缺陷——女性本体的 意义缺失,最终导致女性主动参与的自我解放成为女性再次迷失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