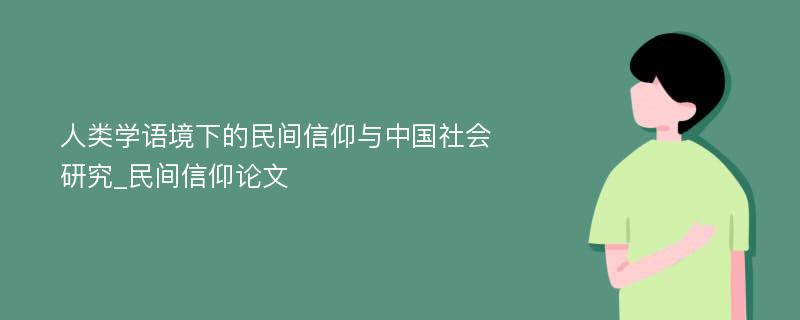
人类学语境中的“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语境论文,中国社会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随着30多年来各地掀起的“一场或许是历史上最大的地方宗教仪式传统的大规模复苏和重塑”运动①以及民间信仰合法化的最终实现②,正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③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纷纷将民间信仰纳入或重新纳入自己学科研究的视野和范畴,不同学科视野下的民间信仰研究有着各自不同的学术关怀和研究取向。
当我们审视中国民间信仰研究之时,不仅发现其成果丰硕,而且支脉庞杂繁多,观点各异,很难对相关研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文献综述。陈进国试图从民俗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的角度来反思上世纪以来中国大陆民间信仰研究的学术取向④,符平批判性地检讨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信仰事象范式、象征/文化范式和社会过程范式三种主体范式,指出了社会学超越目前主体范式的可能途径,⑤陈彬也谈到了“民间信仰的社会学研究论纲”问题⑥,吴真总结了近三十年来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对于中国民间信仰的不同表述和学术历程,以此回应以欧大年(Daniel Overmyer)为首的七位西方汉学家关于过去一个世纪海外汉学的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因缺乏中国同行的出色研究而无法得到应有的对话与矫正。⑦
本文主要在人类学语境中⑧,通过梳理“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学术成果,探讨前人研究如何透过民间信仰研究内容的拓展和研究范式的转换,推进民间信仰研究的学术进路,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寻找人类学语境中民间信仰研究的意义世界。
一、民间信仰:动态的概念界定和约定成俗的研究范畴
在现代学术研究中,概念或范畴是学术讨论的重要基础,民间信仰研究也不例外。自从上世纪中国引进并创建了现代学术体系之后,民间信仰研究便成为多个学科的关注对象。不过,在“民族—国家”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语境以及民族国家公共政策的左右下,加上中国民间信仰本身所具有的独特复杂性,近百年来“民间信仰”的话语,经历了诸如“封建迷信”、“俗信”、“民俗文化”、“民间文化”、“非制度化的宗教形态”、“民间宗教”、“民俗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宾词的价值界定,至今仍然是作为一个在被建构中的动态性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充满着不确定性,因而也富有开放性。⑨
很难指明和确定谁是最早对民间信仰下定义的人。从近年来学者们对民间信仰概念的界定来看,大多围绕着“信仰”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来阐释。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如何给“民间信仰”进行正确界定的学理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如何恰当定位和理性对待民间信仰的政策问题。归纳起来,这些定义可分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民间信仰不是宗教,而是一种信仰形态。1989年和1999年的彩图珍藏本《辞海》把民间信仰理解为“是对某种精神观念、某种有形物体信奉敬仰的心理和行为,”包括“民间普遍的俗信以至一般的迷信”,其思想基础是“万物有灵论”,“所体现的主要是唯心主义。”⑩实际上,把民间信仰排除在宗教的范畴之外,在上世纪之初就有此论断,而且出自许多名士鸿儒之著作。(11)1997年出版的《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民间信仰》的作者宋兆麟、乌丙安以及贾二强、赵匡为、王健、姜义镇、樱井德太郎、掘一郎等也持类似的观点。(12)此说意在强调民间信仰的自发性和民俗性,否定其宗教的本质属性。
第二种观点强调民间信仰具有对超自然力量的信奉和崇拜,因而民间信仰在本质上是宗教。此说以台湾学者李亦园为代表,他把民间信仰称之为“普化宗教”(diffused religion):
所谓普化宗教又称为扩散的宗教,亦即其信仰、仪式及宗教活动都与日常生活密切混合,而扩散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其教义也常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也就缺少有系统化的经典,更没有具体组织的教会系统(13)。
金泽、王铭铭、周星、渡边欣雄等也持这一观点。王铭铭等人甚至不采用“民间信仰”一词而代之以“民间宗教”,周星、韦思谛、康豹(Paul R.Katz)分别以“民俗宗教”(14)、“大众宗教”和“社区宗教”(15)等称谓来代称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属于宗教的意思表露无遗。此说强调民间信仰的本质属性及其草根性(非文本性),同时注意到与其他宗教、秘密宗教(教会)的区别和联系。(16)
第三种观点主张模糊民间信仰的概念界定,认为这样做还更有利于研究的进行。持此说以欧大年(Daniel Overmyer)、叶涛为代表。欧大年认为,中国古代在儒、释、道之外存在着第四种宗教,即民间宗教,而“民间宗教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派信仰的宗教,如白莲教、一贯道等;一是流传于民间的为普通民众所共同崇信和奉行的宗教戒律、仪式、境界及其多种信仰”(17)。在欧大年这里,民间宗教包括民间信仰。叶涛认为界定民间信仰可以“有一个偷懒的做法,就是正统宗教以外的都是可以拿进来,包括民间宗教、秘密教门、老百姓的习俗等”,并认为“模糊一点比精确一点好”(18)。
第四种观点认为民间信仰介于一般宗教和一般信仰形态之间,权且称民间信仰为“准宗教”也许比较准确些。此说可以认为是关于民间信仰模糊界定的另一种表述或深化,意在平衡概念定义上的某种争议。李天纲、林国平是此说代表。(19)林国平认为:
民间信仰是指信仰并崇拜某种或某些超自然力量(以万物有灵为基础,以鬼神信仰为主体),以祈福攘灾等现实利益为基本诉求,自发在民间流传的、非制度化、非组织化的准宗教。(20)
由此可见,关于民间信仰的定义,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民间信仰是不是宗教?民间信仰是否包括历史上被官方压制、拒绝甚至取缔的那些“秘密宗教”?前者反映出学者们在宗教本质属性和形态方面理解上的差异,也勾勒出中国宗教学术研究的西方模式;后者则涉及民间信仰的范畴问题。
尽管在界定民间信仰定义上有不同,但在目前的中国大陆或台湾地区,约定俗成的“民间信仰”范畴,通常指具有“宗教性”又有“民俗性”双重维度的信仰形态,用以指称那些与制度性的宗教形态(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宗教、新兴宗教或教派)相区别开来的混合性的信仰形态。从发生学的视角看,民间信仰一方面传承了各民族或族群的自然性宗教(自为生成)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传承了制度性宗教(有为建构)的传统,带有村社(村落和社区)混合宗教的典型特征,堪称“原生性”和“创生性”双性共存的复杂的信仰形态。作为一种中国民众(庶民和精英共享的)的生活方式、习俗传统、崇拜体系,民间信仰一直兼容了两种文化取向:一方面是礼仪化、人文化的取向,这种取向使得它和文化“大传统”或者说官方的正统(如敬天、法祖、尊贤)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观念形态上吸纳大量精英的知识和思想,在文化空间中允许大量建制性宗教的内生性仪式在场(如散居道士举办的仪式);另一面是数术化、巫术化的取向,这种取向使得它又同文化“小传统”有着密切的交集,吸纳了大量民俗性的成分,形成各类“依附性的宗教仪式”,如抽签、占卜等功利性的信仰形态。(21)
就研究对象而言,学者们所涉及到的,主要包括“流行在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中的神、祖先、鬼的信仰,庙祭、年度祭祀和生命周期的仪式,血缘性的家族和地域性庙宇的仪式组织,世界观和宇宙观的象征体系”(22),也涉及到流散在民间的各种形态的民间道教、民间佛教以及基于泛灵论的自然精灵崇拜和鬼魂崇拜等在内的种种信仰等等。可见,在当代中国社会人类学语境下,“民间信仰”实际上已等同于“民间宗教”,相当于与杨庆堃先生所说的与“制度化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不同的“扩散式宗教(diffused religion)”。
基于约定成俗的研究范畴,以下我们将要探讨的是,在人类学的语境中,将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勾连起来的,主要涉及以下三个相关议题:民间信仰与现代化、民间信仰领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的互构。
二、民间信仰与现代化:韦伯宗教研究的“中国命题”
民间信仰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它起因于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关于“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又因东亚工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突兴以及中国大陆地区改革开放后民间信仰的复兴而被热烈讨论。
韦伯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试图从东西方文化和历史比较研究角度,来探讨世界诸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新教伦理有关,这是西方文明形态的独特性。(23)作为佐证这一命题的间接证据,韦伯用同样的理论框架将中国的儒家伦理和道家传统与新教伦理进行了比较,他发现,儒家伦理和道家传统与新教伦理有着全然相反的特征,在新教伦理中,那些为资本主义做出巨大贡献的精神,儒家伦理和道教传统不仅没有具备,而且似乎处处与之相反。尽管中国拥有各种外在的有利于资本主义成立的条件,却无法抗衡家产制国家结构以及绵延不绝的大家族所造成的障碍,这些障碍因中国缺乏一种独特的宗教伦理作为必要的启动力量而强化,所以中国没有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24)言意之下,儒教和道教思想都不能像西方新教伦理那样促进现代化的实现;现代化这现代文明的产物,与儒家、道教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应当是无缘的。
由“韦伯命题”衍生而来的“中国命题”,以及中国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究竟如何,长久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得不指出,西方学者的宗教定义,往往以教团宗教为基础,表达为一种社会形式。韦伯如此强调,涂尔干亦然。(25)比较而言,中国宗教并不具备这样一种团体活动方式,缺乏自立自主的制度依托。它的宗教主体,或是宗族组织,或是官方的制度安排。因此,关于中国宗教的研究在许多学者那里就表现为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的现象:中国宗教现象既无处不在,又地位模糊。(26)
正是基于中国宗教地位的模糊性及争议性,华裔学者杨庆堃把中国宗教区分为两个结构:一类是教义和教会组织完备的“制度型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另一类是缺乏统一教义和组织系统的民间信仰,即扩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制度性宗教以佛教、道教为代表,具有独立的神学体系、崇拜仪式和组织结构,独立于其他世俗社会组织之外;扩散性宗教包括国家的祭天大典、家庭的祖先崇拜、宗祠祭祀、英雄崇拜以及各行业对其保护神的崇拜等。这种扩散性宗教,它的神学、仪式、组织,同世俗制度的概念与结构及社会秩序的其它方面紧密融合在一起,与世俗生活结合在一起,从而成为世俗制度的观念、仪式和结构的一部分。杨庆堃认为,中国社会宗教蓝图的基本特征,就是制度上难以独立自在,其教理、科仪、组织、神职人员,均与其它的世俗制度如宗法、族群、家庭、权力、国家等混杂为一体,并主要依附于世俗制度,甚至成为它的一个构成部分。他进一步解释说,在中国社会历史上,尽管宗教始终是非常重要的,但并没有如在欧洲或阿拉伯文化中那样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而存在,是因为在中国社会中,扩散性宗教占主导地位,而制度性宗教则相对薄弱。(27)由此,扩散性宗教概念的引入,揭示出中国宗教无处不在的事实,不仅直接驳斥了韦伯将中国民间信仰称之为“功能性神灵的大杂烩”轻蔑诠释,而且在“制度—扩散”的解释框架下,多元化的、芜杂的中国宗教现象变成了清晰和易于理解的宗教秩序。(28)
尽管杨庆堃的“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并不直接回答韦伯的“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理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问题,但却通过揭示在前近代中国社会中,中国宗教与普遍王权之间的关系本质、国家或政府以各种方式来实施或彰显这种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中国宗教的影响究竟如何等方面核心内容,首次展示了“宗教在中国社会及其组织方面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并以何种方式与社会秩序建立关联”的相关问题,建立了宗教与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关联。他的著作,既可以认为是从宽阔的社会学角度来证明中国宗教存在的形式、合理性以及历史传统,也称得上是从宗教的视角来观察从家庭、社会团体、社区一直到国家层次或结构的中国社会,确立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结构性地位,实质上还是为了响应韦伯那个著名的命题,曲线地解答宗教与社会进步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东亚经济的腾飞,人们开始热切地讨论儒家伦理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认为建立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构成了对韦伯的挑战。相关的研究很多,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余英时在其论著之中反复要论证、说明的就是韦伯所言之新教伦理,如入世苦行、勤劳、节俭、诚实、讲信用等新教美德,传统的中国儒教伦理、中国商人的行为与观念之中同样也包括了这些伦理美德,即认为中国儒家也有入世苦行的宗教伦理,也有理性主义。言意之下也很明了,中国近世(明、清)之所以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其“罪过”不在传统宗教伦理,而在于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对经济形态发生的决定性的阻碍作用。(29)
在这股“儒家文化圈”热的影响下,一些学者还通过民间信仰的观念世界寻找中国民间的“资本主义精神”。葛希芝(Hill Gates)通过对比中国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信仰里关于“钱”的概念和象征意义,证明中国民间存在资本主义的精神,只不过这种精神一直被压抑在“小传统”内,不能转变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而一当政府开放它的态度就会引起它的扩大发展。(30)赵世喻考察了华北庙会的迷信崇拜功能、文化娱乐功能、商品贸易功能,指出庙会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与传统社会中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密不可分。(31)他还进一步讨论了中国传统庙会及娱神活动中的狂欢精神,庙会狂欢具有心理调节器、社会控制安全阀以及维系社会组织、增进群体凝聚力的良性功能,反映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而质疑“中国人把非理性的情感因素压缩到最低限度”之说(32)。朱小田则通过对吴地庙会活动的研究后指出,庙会活动是神圣中有凡俗性,凡俗中有神圣性,两者混为一体,因此,庙会兼具神圣与凡俗的双重性。(33)
回过头来看,韦伯的论断深深地影响了其后的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杨庆堃是这样,后来研究者亦沿此路径,他们所做的工作几乎都是在回应韦伯的“中国命题”,努力证明中国宗教(包括民间信仰)含有促进资本主义的精神(ethos)和伦理(ethic),与现代化并行不悖。(34)今天,在观念层面上,尽管大多数人已不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是现代化的阻碍因素的观点(35),可是,在学术研究层面上,把一个现代化的问题转化为一个传统文化如何改造的工程,似乎都狭窄地理解了现代化和传统文化本身。等到1990年代后期,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人们又宣称“儒教文化圈”的理论不攻自破。那么,以儒教伦理来解释韦伯式“新教伦理论题”以解读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命题还能剩下多少学术价值呢?(36)可见,如果把这个问题给予还原,宗教现象就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关怀和伦理动力了。
三、民间信仰领域的国家与社会:权力、教化与国家的治理技术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许多学者意识到,“在讨论任何具体问题的时候,都不能忘记在他们的研究对象背后存在着一个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国家。”(37)因此他们将基层社会的民间信仰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典章制度及政府行为联系起来考察,探讨了民间信仰表达的关于国家、王朝与皇帝的乡土观念及其与官方意识的异同,国家正统信仰在民间的影响与变异,官方对民众所信神灵加以区别对待的政策,乡民、士绅、官员对某一或某类神灵之认知、态度的相同与差异。
信仰领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欧美学者与中国大陆学者的关注点略有不同。出于实际田野调查的困难,欧美人类学家多采用文献办法,将眼光投放到“过去”、“厚古薄今”,把民间信仰和仪式当作传统中国社会大系统之中的文化子系统,关注其特征、角色和功能,寻找象征体系与社会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力图在中国人的信仰、仪式和象征体系中发掘中国文明与社会构造的模式,阐明信仰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强调大众信仰的职能及系统特征。中国大陆学者则利用自身优势进行田野调查,更多是关心“现在”,探讨改革开放后在民间信仰和仪式的传统形式外表之内,如何融合或渗透进了当代的国家治理技术和权力关系:象征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
(一)欧美学者的关注:民间信仰在传统中国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
武雅士(Arthur Wolf)认为中国的民间信仰存在一个共同的象征体系:神、祖先和鬼。神是帝国官僚的化身,鬼是村落外部的“外人”和人们不喜欢的危险的陌生人的超自然的代表,祖先则是为给自己财产、社会地位和生命的力量源泉。武雅士认为中国民间信仰享有共同的神、祖先和鬼的崇拜,根源于农民的社会经历,表达的是农民对他们的社会世界的阶级划分。(38)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则指出,中国民间信仰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体系(整体性宗教),与中国人共享了一套关于宇宙和社会的解释体系——天命信仰与阴阳五行说有关,同时也是因为国家对宗教权威进行了成功的控制与整合。(39)与此相关的研究是,桑格瑞(P.Steven Sangren)同样认为中国民间信仰包含一种认知结构,即阴阳说。但是,在仪式实践中,这一认知结构与社会生活糅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有社会—文化意义的实践活动。宗教仪式是社会和个人辩证统一的逻辑,同时反映了人们活动空间的地理分布与宇宙观。据此,桑格瑞把“阴阳说”作为中国宗教共同的表现,重新思考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整合问题。(40)
自武雅士和弗里德曼之后,对于中国宗教尤其是民间宗教的研究,就具有了从“整体性”到“关联性”的研究取向。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基于台湾的田野经验,认为中国民间社会有着极强的模仿能力,烧冥币、香炉、灶神传说、城隍庙的崇拜等民俗生活,实际上背后隐含着帝国隐喻的逻辑(社区人士对王朝仪式的操演)。隐喻式模仿的逻辑,一直是中华帝国与民间社会之间能够进行沟通的主要途径。通过这种模仿的实践,帝国的运作逻辑得到了民间的认可并在民间发生了转化。在民间宗教(民间信仰)那里,帝国权威的隐喻逆转而成为民间社会对权力的再定义。换言之,在民间信仰的实践中,透过对帝国隐喻式的模仿实现了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勾连。(41)同样基于台湾的田野经验,戴德中(Alessandro Dell'Orto)认为土地公崇拜不仅是一个宗教社会现象,还是探索和分析台湾动态社会变迁的“合适的介质”(appropriatemedium),土地公的大众表征能够当作记录台湾人对地方、社区和认同的感觉的“晴雨表”(barometer)。(42)芮马丁(Emily Martin Ahern)则利用自己所搜集的文献和社区调查材料,认为中国民间仪式雷同于衙门的政治交流过程,是一种意识形态交流的手段,具有自己系统化的符号与程序。宗教祭拜仪式过程中的人神交流犹如百姓向衙门汇报案件:神即是官,祭拜者即是百姓或下级办事人员。中国社会中的仪式,因此是上下等级的构成以及等级间信息交流的演习,反映了政治对宗教仪式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民间对政治交流模式的创造。(43)
华琛(James L.Watson)关注的重点则是民间信仰是否能够作为一个文化因素使中国社会构成一个整体性社会的问题。在《神明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960-1960年)》一文中,他探讨了帝国国家和文化精英为接受并塑造像天后这样获得国家钦准的神的形象而有意识做出的努力,认为用这种方法有助于整合中国不同的地方文化。他认为,天后由福建沿海的一个影响不大的地方神上升为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主要的信仰对象,这一变化“没有国家的干预和鼓励不可能完成”。但是,国家并不是依靠强制手段,而是采用更巧妙的方式来控制普通百姓的宗教生活,表现为既引导大众又对民众的压力做出反应;既鼓励神灵信仰又把它们吸收进来。华琛认为,这是(传统)中国政府对文化整合做法的聪明之处:国家强加的是一个结构而不是内容;国家鼓励的是象征而不是信仰。它把庙里崇拜活动的组织工作交给了地方精英人物,而地方精英也通过遵守适当的形式,在建构一种全国文化的过程中与国家当局进行了合作,借以表明体面、“开化”、秩序和对国家的忠诚,这一做法足以让社会等级各层次上的人都可以建构他们自己对国家允准神灵的看法。中华传统帝国以这样的一种微妙的方式干预地方崇拜,就可以把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包容在一起,允许人们对于像天后这样由国家钦准的神的意义有多种多样不同的解释,但却可以使全国文化在表面上表现得相当一致。(44)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对关羽神话的“刻划标志”研究,注意到了标志变化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将国家、民众和民间信仰的关系做了更为复杂的解释。他首先发问,假如有关神的传说随着时间流逝而大大改变,而且对不同群体有不同含意,那么它们怎能发挥如华琛所说帝国国家要它们起到的作用,以确保文化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政治的合法性?他认为,答案就在于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当神话和形象随着时间而改变,各群体争相对神的作用及其主要形象做出自己的解释,新的解释并没有完全消除旧的解释,而是被“写上去(Written over)”,以致重要的东西仍延续了下来。这就是他所说的神话及其文化象征具有同时连续和不连续的特点。他提出,事实上保存并传播一种神话或其他重要的文化标志都是有必要的,其多重内涵仍保持不变,因为神话或神或标志的力量和适应性都取决于其诸多不同方面相互间的影响。不过,他同样承认,宗教形象的建构在维持帝国晚期国家的权威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甚至指出,由于对宗教机构的攻击,没有创造出一个有竞争性的代替关帝神话的东西,作为在国家和农民之间认同和沟通的标志性的框架,民国政权破坏了在中国社会中扩展其权威的真正手段。(45)
华琛和杜赞奇的研究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探讨了一些重要的、被广泛信仰、得到官方承认、被完全接纳进帝国的神谱中的神。然而,那些得不到国家和知识精英信任只是勉强被接受的神反映的可能是不同的历史进程和存在状况。因此,两人的作品引发了一些尚待全面应对的问题。比如,在宗教操作是如何标准化问题上,华琛提出了“基本符号的模糊性是在中国创造标准化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因素”的论点。显然,这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回答,因为文化的标准化并不一定是一个单一的进程,而是由诸多团体共存且互相作用而引起的多个进程。而在关于“什么人负责执行标准化这个过程”的问题上,华琛和杜赞奇都强调政府和地方中坚分子两大主要动力,但是这两大集团的代表在对地方层面上崇拜和操作的动机和重要性未必一致。这一点,在华琛作品中流露无遗。韩明士(Robert Hymes)关于三真君崇拜的研究证明国家的赞助并不足以使精英们长期信奉某个神明(46),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对碧霞元君的研究则表明,对碧霞元君的崇拜并不存在着成功的共生现象,尽管有某些超越不同群体的共同观念,但对碧霞元君的仪式和标志有分歧,而且这种分歧显而易见。“碧霞元君”这一共生体,从一开始形成后就裂变为分散且经常相互争执的各部分,有些精英甚至反对朝廷资助。(47)韩明士和彭慕兰的研究,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民间信仰领域更为复杂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二)中国学者的关注:信仰再造与当代国家的治理技术和权力关系
与欧美人类学关注“过去”的时段不同,中国学者更多关注民间信仰的当下实践。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内容很多,跨学科交叉研究成为一大亮点。(48)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在民间信仰的文献和田野寻找研究题目,同时也体验着不同学科在民间信仰的田野中所带来的独特经验。郭于华主编的《仪式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所收集的论文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郭于华将仪式与象征作为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和过程的途径。她把寺庙中的祈雨仪式归为“作为生存技术的仪式”,来与“作为权力技术的仪式”的“翻身”、“经济运动”、“政治象征符号”等政治运动做出对比,进而得出结论: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家仪式对社区仪式进行了一个取代,革命仪式形态对地方性话语进行了一个取代;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弱化与撤退,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正在复归和再建构。她的研究在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下,将仪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透镜,理解社会变迁与重组的机制,为我们展示了仪式中所呈现出来的国家权力与民间权力两者之间互动、互融的错综复杂关系。
刘晓春的研究增加了几个变量。他通过对同处一个客家乡镇的两个信仰——仪式中心的考察、比较和分析,展示了区域——仪式中心的变迁,以及仪式的兴衰演变与家庭、社区、国家及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复杂关联,论证了所谓传统的复兴与再造不过是国家权力、民间精英与权威、民众生活动力等各种因素互动与共谋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周大鸣分析了潮州凤凰村民间信仰和仪式复兴的过程和特点,探讨了传统复兴的多重动因:华侨资本的进入、宗族组织与村落领袖的关系、教育发展对宗教活动的影响、民众对于信仰的心理需求及传统生产方式的再度出现,乃至当前的商业活动和大众传媒的作用,共同构成民间信仰与仪式存在和演变的社会结构与氛围。
刘铁梁和高丙中则将田野调查的地点都放在了河北赵县范庄。刘铁梁通过对不同地域的几个村落仪式变迁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村落民众通过庙会仪式活动所建立的象征性生活世界和共同确认的社会秩序观念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关系。同时,村民在不断扩展的生活实践范围内,对传统进行新的解释和创新性运用,国家力量对地方社会的渗透以及地方对这种渗透的回应,也构成村落仪式复兴的真实动因。高丙中的相关研究则始终关注国家是如何“出现”在民间仪式中的问题,并确立“国家在社会中”这样一个命题,着重探讨民间社会、个人与国家权力的复杂互动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在不同的时代的存在状态。民间仪式在复兴时虽然强调其特色和身份,但同时又利用国家符号以获得更好发展。国家在民间仪式上事实上有着“治理”方式的演练。文化仪式的相互承认、互融及至共谋正是国家与地方民族传统、政府与民众之间新型关系的体现。
这些研究表明,在民间信仰和仪式的传统形式外表之内,已经融合或渗透进了当代的国家治理技术和权力关系。国家与民间信仰在仪式的实践中相互使对方“成为可能”,国家象征和权力存在于社会的仪式中,国家与社会相互形塑和渗透、各自的边界由此变得模糊。类似这样的论点实际上已经能够比较清晰地表达国家在民间信仰和仪式中的角色和所起到的作用,勾勒出信仰系统内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四、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互构:“权力的文化网络”
民间信仰是乡村社会文化与权力网络的一个重要环节。“以庙宇为中心的仪式场合更有利于明了在平常的生活场景下不易显露的社会分化与权力支配关系”(49)。多数学者注意到了民间信仰活动对村落社区的凝聚、整合作用,探讨了神庙祭祀组织与基层权力组织之间的关系及神庙祭祀仪式对不同群体权利、义务关系和村社规则、秩序的表达,以此说明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与运行秩序。
这方面的研究首推杜赞奇。他在研究中国华北农村时指出,民间信仰也是“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重要渠道,构成“权力的文化网络”的重要部分。进入20世纪后,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政权不再利用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力图斩断其同传统文化网络的联系,因而失去了乡村精英的支持,并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后果。(50)受杜氏著作之启发,不少学者尝试从这一角度重新检讨民间信仰与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关系。宋德剑考察了闽粤赣客家地区的民间信仰活动,发现在客家传统社会里,庙宇是得到官方的认同的民间处理地方事务的行政机构,是国家权力“话语”的地方化:“一方面,民间信仰体现出的象征与权威,有助于客家社会宗族聚居地的形成,这也成为客家地区宗族界限分明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透过民间信仰活动,可以发现不同社区内的族群之间的对立统一性,正是民间信仰使得客家传统社会维持着一种‘有序的无序’状态,推动了客家社会的进步,成为客家传统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所在”(51)。高丙中基于跨度9年的参与观察,叙述了河北范庄龙祖殿这个同时兼具博物馆和庙宇之名的建筑物从创意到启动再到完成的过程。他认为这个过程包含着学界的参与、村民的努力和政府机构的支持与通融,也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多种紧张关系在这个情境中被缓和、解决的过程。不过,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高丙中重新诠释了中国传统的双名制制度,认为范庄重建龙祖殿过程包含着中国传统的双名制被激活并被现实地运用的文化技巧,这种技巧表现在公共事务领域就成为一种政治艺术。(52)
王铭铭考察了改革开放后福建安溪溪村村民恢复和重建村神“法祖公”和“龙镇宫”过程,认为“龙镇宫”、家族祠堂、年度庆典构成了当地象征秩序的主体部分,这些不同的象征建筑与年度仪式构成了神、祖先、鬼三位一体的家族—社区空间符号。“龙镇宫”以及家族祠堂的重建既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溪村地方传统再造的体现,也是更宏观场景中所谓“民间宗教复兴”的组成部分。透过人类学研究者长期关注的“晚期中华帝国”民间传统在20世纪末期的文化动态,王铭铭着力反思了“现代化的主导意识形态”和带有偏见性的“文化遗产”概念。(53)
景军是国内较早运用社会记忆理论来理解村庄的历史是如何作用于作为村民生活一部分的孔庙毁灭及其重建的。在《神堂记忆》一书中,他以两个时间段为轴,叙述了从上世纪50年代直到90年代,大川人如何遭受迫害、中止庙会活动再到恢复重建孔庙的过程来析解这一疑问,指出这个神圣场所既纪念了远古以来的辉煌世系,更成为一个遭受了严重创伤的社区的近期历史的纪念碑。(54)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以布迪厄(P.Bourdieu)的“文化资本”为分析工具,提出仪式知识、文字技能、历史观念、政治意识等“知识”是构成庙宇重建过程的必不可少的一套资源,与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政治资源等同样重要。“知识”资源的安排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组织模式,另一方面取决于在组织限定内操作的特殊个体的策略。寺庙重建是社会组织的关键性领地,重建寺庙所需知识的提供者通常可以在社区之中获得相对较高的荣誉、声望与遵从,由此,寺庙重建就可能将普通的人际关系变成一种强大的社会组织力量。(55)
赵旭东试图透过寺庙重建及其庙会活动过程的考察来探讨“乡土社会的权力与公正”问题。他围绕河北赵县李村1989年重修起来的“张爷庙”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所举办的庙会过程,从食品准备、游神请神到开光守神、送神送鬼等进行了详细描述,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间宗教的复兴一方面表明寺庙在当地人生活中的实际功用,另一方面反映国家力量在乡村一元化支配格局的转变。村庙不仅是一个消除、预测风险以及调解纠纷的场所,而且再生产出了地域社会交往中的互惠原则。村庙中的观香仪式不仅是具有神判的功能,同时还是当地人宇宙观念的一种映射。(56)
范可结合布迪尔的象征资本概念和英国人类学家托马斯的“再地方化”理论,分析了闽南百崎这个福建唯一的回族自治乡近年来在建筑表现上有意塑造的伊斯兰风格,认为地方政府的“再地方化工程”,是试图通过对“地方”的个性化塑造,来强化地方给予外界的印象,是一种类似阿帕杜莱(A.Appadurai)所谓的“地方性”的生产(production of locality)。但是,地方政府的这一改造,并没有获得地方民众的认可,相反有时会成为当地某些民众“迁怒”的对象,由此可以反映地方政府行为与民意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不过,范可认为,这种紧张不一定只有负面的影响,因为它至少可以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种有益的警示,即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性(57)。
麻国庆在闽北樟湖镇调查后认为,通过民间信仰的仪式即“赛蛇神”与“游蛇灯”体现出的社会结合特性,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效地统一农民群体灵活多变的生存智慧。这种结合让人领悟和感受到“文化是如何被复制的”和“文化是如何被生产”的文化真谛(“文化+文化”模式)。(58)岳永逸注意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与河北C村娘娘庙会相关的起源传说发生的变化,认为在现今国家控制下的乡村社会,乡村庙会起源传说被仪式实践强化、再造,二者再在主流话语对乡村庙会的“民间文化——迷信”两可表述的裂缝间,共同形塑着地方社会,进行着地方社会的结构过程。由此可见,传说本身也是层累造成的。在不同的语境下,传说被添加了新的元素,并被赋予新的意义,每一次讲述有每一次的意义,原初的传说仅仅是“一张皮”(59)。
五、结论与讨论
就学术关怀而言,学者们通过近些年的努力,普遍认识到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民众日常信仰,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于普通民众的思维方式、社会关系及政治行为等都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多数学者越来越反对把中国民间信仰、仪式和象征看成没有体系的“迷信”或“原始巫术”的残余,而主张把这些社会—文化现象界定为一种宗教体系研究(60)。许多学者多年来一直为民间信仰正名而撰文呼吁,要求国家政策理性对待这一“影响力超过任何一种思想学说和宗教(制度化宗教)”的“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传统”(61)。对于研究民间信仰的意义,学者们意识到,作为一种草根文化的民间信仰,不仅可以提供一个考察中国社会基层文化的角度,而且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全貌也是很有意义的。学者们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如文化与权力、国家与社会、精英与民间乡土社会的整合和秩序、社区空间建构与发展、象征资本、社会记忆等方面对民间信仰问题进行审视,使民间信仰成为了考察中国地方社会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形成了一些关于民间信仰研究共同的关注领域和研究取向。或者说,我们不是为了研究民间信仰而研究民间信仰,而是希望藉此研究,将“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联系起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实践面相和丰富内涵。这表明,在人类学语境中,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已形成共同的问题、方法和学术取向,初具学术范式的意义。
尽管民间信仰已具有如此之多的共同的学术关注,民间信仰本身的发展也日益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可以充分利用的文化资本(62),但是民间信仰的学术研究如何进一步推进反而成为问题。其原因,是在“非遗”的话语下,民间信仰研究有逐步地被导向所谓“对策研究”和一些商业化考量的境地,以至于在“传统”与“发明”之间的学人选择问题成了问题。(63)赵世瑜也在第二届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会上发出了“非遗”之后民间信仰研究如何推进的担忧,并提出重新探讨华琛(Watson)关于“神明标准化”命题的重要意义。(64)按笔者的理解,这恐怕是部分学者担心学术研究被功利化,走向彻底的实用主义。
在“非遗”之后“民间信仰研究如何推进”这样的大问题有赖于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不过,按一般的理解,学术研究的推进最终还得靠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等各方面的拓展来实现。为此,笔者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要不断探索新的分析框架;二是深化问题意识。前者,符平透过分解“国家”,运用“国家—地方政府—地方民众”的三元分析框架代替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试图探得民间信仰空间生成的经验性社会过程及其机制的理解,以此来剖析民间信仰及信仰空间再造过程中所蕴涵和体现出来的当代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所呈现的相互制衡的“动势”,得出了与杜赞奇不一样的发现。(65)后者,张佩国考察了清代绩溪县登源汪公庙庙产和司马墓坟业的讼争中,如何集中呈现了地域崇拜、宗族认同、绅权治理、祭祀礼仪、司法实践、风水观念、地权纠纷等要素的整体性历史实践,指出“汪公信仰作为标志性民俗,呈现了徽州地域社会秩序场境中的整体动员机制”(66)。他的研究,将人们注意力关注到以下问题:在中国乡村社会中,常有作为双重身份(祖先崇拜和地域之神)的地方神明(灵),其地域信仰和地域空间秩序的结构化过程及其实现方式。
①丁荷生:《中国东南地方宗教仪式传统:对宗教定义和仪式理论的挑战》,载《从书斋到田野:宗教社会科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29页。
②萧放:《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民间信仰重建民间信仰的合法化》,《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5期。
③一般认为,民间信仰合法化,可以以2005年9月国家宗教事务局增设第四司和2008年6月民间信仰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两个事件为标志。此外,近年来学者撰文呼吁将民间信仰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呼声甚高。这些代表作有如下:刘锡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向柏松:《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高丙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课题的民间信仰》,《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2009年8月7—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召开的第七届全国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其主题就是“民间信仰与文化遗产”。参见刘晓春、王维娜:《第七届民间文化青年论坛——民间信仰与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化遗产》2010年第1期。
④陈进国:《民俗学抑或人类学?——中国大陆民间信仰研究的学术取向》,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Page=1&NewsID=49
⑤符平:《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主体范式与社会学的超越》,《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⑥陈彬:《民间信仰的社会学研究论纲》,《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⑦吴真:《民间信仰研究三十年》,《民俗研究》2008年第4期。
⑧关于“语境”一词以及民俗学、人类学关注语境的历史由来,刘晓春有过很好的诠解,认为“语境”包括时间、空间、传承人、受众、表演情境、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七个因素构成。参见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
⑨英文世界中的Folk Religion、Folk Belief、Popular Cult、Popular Religion、Communal Religion,都可能指涉所谓的“民间信仰”。该术语最早见于1892年的西方学术期刊,1897年日本学者姊崎正治亦正式用之。约在1920年代“民间的信仰”、“民众信仰”、“民间宗教”常见于中国学者的文章中。至1930年代“民间信仰”已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术语了。参见陈进国:《民俗学抑或人类学?——中国大陆民间信仰研究的学术取向》,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Page=1&NewsID=49
⑩《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4543页。
(11)例如,大学者梁启超曾说过:“中国是否是有宗教的国家,大可研究”,甚至说“做中国史把道教叙述上去,可以说是大羞耻”(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197—198页)。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则明确断言:“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参见胡适:“名教”,《胡适文存三集》第一卷。)大儒梁漱溟相对谨慎,指出:“世界上宗教最微弱的地方就是中国,最淡于宗教的是中国人……中国偶有宗教多出于低等动机……”(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198页。)哲学家钱穆也认为:“中国自身文化传统之大体系中无宗教”(参见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第17页)。
(12)宋兆麟、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民间信仰》,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
(13)李亦园:《文化的图像》(下卷),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180页。
(14)周星:《“民俗宗教”与国家的宗教政策》,《开放时代》2006年第4期。
(15)[美]康豹:《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社区宗教传统的主要动态》,李琼花译,陈进国校,《文史哲》2009年第1期。
(16)台湾学者郑志明认为,民间信仰具有“民众日常风俗习惯下的宗教传统”,但他认为民间宗教是指被官方所排斥与拒绝,甚至视为旁门左道或邪教的那些“秘密宗教”。不过,他同时认为,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关系极为密切、互为流动,民间宗教是依附在民间信仰的生态环境上。郑志明:《关于“民间信仰”、“民间宗教”与“新兴宗教”之我见》,《文史哲》2006年第1期。
(17)[美]欧大年:《解读辽宁民香,解读中国民众宗教意识》,选自侯杰、范丽珠:《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
(18)转引自路遥等:《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的若干学术视角》,载《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9)李天纲关于民间信仰是“准宗教”的界定,更多地是从民间信仰的存在状态来谈的,他认为相比“正式宗教”,民间信仰多为“散漫无组织状态”、“不太强势”,但是民间信仰的这种“泛宗教”的特色,反而使它更不容易消失。参见李天纲:《从“文化多样性”看民间宗教信仰的合法性》,《上海市社会科学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20)林国平:《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民俗研究》2007年第1期。
(21)钟敬文也指出,民俗信仰是指“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参见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22)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0页。
(2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龙婧译,群言出版社,2007年。
(24)[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韦伯作品集V》,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25)涂尔干也曾指出,宗教的社会本质就是一种群体的价值生活方式,将所有信奉者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并表达为一种卓然出众的社会形式。参见[法]埃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林宗锦、彭守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54、558页。
(26)中国民众见神就磕头、逢庙便烧香的多神信仰,是民间信仰区别于西方制度化宗教的主要面向,因而也是民间信仰最先被关注的部分。对于传统中国人宗教生活中的数教并奉、数神并崇现象,西方人常常会油然而生错愕惊异感,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就曾经将当时甚嚣尘上的三教合一思潮与实践看作是一身三首的妖怪。
(27)[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8)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杨庆堃本人并不认为“儒教”是宗教,而是将“儒教”视为一种具有宗教性的伦理政治思想。同样需要申明的是,杨氏关于整个中国宗教体系的分析都承袭了宗教与社会的功能性关系的思路。
(29)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载《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5—511页。
(30)Hill Gates,"Money for the Gods",Modern China,1987:No.3,Vol.13.
(31)赵世瑜:《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32)赵世瑜:《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33)朱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人民出版社,2002年。
(34)郭占锋、冯海英、李小云:《由中国民间信仰复兴现象反思现代化理论逻辑》,《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5)尽管从现实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性制度、民间信仰、民间组织和民间仪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恢复与重建,纷纷以一种“旧貌换新颜”的状态重新活跃于乡村之间,近几年又迅速扩展到部分城市,从而出现了萧凤霞(Helen Siu)所描述的“强化的仪式景观”。但是,人们对“现代”语境下“传统”的前途命运仍有不同的判断。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全面实施,乡村社会中传统因素的消亡将是不可避免的,所谓的传统复兴,不过是昙花一现,是特定时期的一种反弹现象,不可能持续下去。贺雪峰指出,“无论现代性论者如何坚持传统本身的合理性,大概不会有人认为当前农村社会传统的复兴已经达到了建国前的程度。在政治运动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冲击之下,当前乡村社区传统的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落,其主要表现在于:一、宗族组织和宗族经济的消失;二、民间信仰的影响式微;三、传统节日的日益衰落;四、人情世故的理性化倾向。”刘晓春甚至认为,民俗文化旅游的兴盛,既是“本土化的现代性”的一个表现,也是文化政治之暴力的一种表述,并不表明在中国当下的文化情境中,权力政治与资本已经平等地承认这些边缘话语。遵照这一逻辑,民俗传统文化在旅游的空间环境下要么“变质”,要么消失。请分别参见贺雪峰:《人际关系理性化中的资源因素:对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传统的一项评述》,《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刘晓春:《民俗旅游的意识形态》,《旅游学刊》2002年第1期。
(36)台湾学者叶仁昌认为,东亚经济奇迹背后的文化因素,是多种文化不同程度的综合体,它们以吊诡(paradoxical)的形式相互连结。此一综合体固然包括儒家伦理的成分,但绝非儒家伦理所可以涵蓋。以台湾而论,它还包括了不同程度的佛教伦理、威权文化、属于小传统的民间习俗与观念,以及大量的西方文化等成分。更重要的是,这些成分有许多甚至是与传统儒家背道而驰的。参见叶仁昌:《东亚经济伦理的澄清与辩思:韦伯、儒家与基督新教》,http://web.ntpu.edu.tw/~soloman/asiaeconomics.htm
(37)郑振满、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导言》,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38)Arthrur Wolf,Introduction: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Arthur Wolf e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1—18.
(39)转引自李向平:《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中国社会“信仰关系”的人类学分析》,http://1xp0711.blog.hexun.com/45964854_d.html
(40)P.Steven Sangren,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Traditional Chinese Corporations:Beyond Kinship Traditional Chinese Corporations:Beyond Kinship”,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4:No.3,Vol.
(41)[英]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42)转引自符平:《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主体范式与社会学的超越》,《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43)Emily Martin Ahern,Chinese Ritual an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44)[美]华琛:《神明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960-1960年)》,载韦思缔主编:《中国大众宗教》,陈仲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45)[美]华琛:《神明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960-1960年)》,载韦思缔主编:《中国大众宗教》,陈仲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46)[美]韩明士:《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皮庆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47)[美]彭慕兰:《泰山女神信仰中的权力、性别与多元文化》,载韦思缔主编:《中国大众宗教》,陈仲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48)跨学科交叉研究,大多采用“民俗整体研究”范式,在方法论上突破了中国民俗研究中的史学理路和“民俗事项研究”范式的局限,在引入历史与变迁的维度的同时,更关注现实中的人们如何进行信仰的实践活动。这一方法论上的突破,促发了民俗研究的人类学倾向,并招致大批民俗学者做了民俗学的“叛徒”。参见叶涛:《民俗学的叛徒》,《民俗研究》1999年第3期。
(49)郑振满、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导言》,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页。
(50)[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51)宋德剑:《国家控制与地方社会的整合:闽粤赣客家地区民间信仰研究的视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
(52)高丙中:《“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53)王铭铭:《溪村家族》,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54)Jun Jing ,The Temple of Memories:History,Power,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55)景军:《知识、组织与象征资本》,《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
(56)赵旭东:《权力与公正》,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77—203页。
(57)范可:《“再地方化”与象征资本:一个闽南回族社区近年来的若干建筑表现》,《开放时代》2005年第2期。
(58)麻国庆:《“全球化: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族群、地方社会与跨国文化圈”》,《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
(59)岳永逸:《传说、庙会与地方社会的互构——对河北C村娘娘庙会的民俗志研究》,《思想战线》2005年第3期。
(60)王铭铭:《中国民间宗教:国外人类学研究综述》,《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2期。
(61)朱海滨:《民间信仰——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传统》,《江汉论坛》2009年第3期。
(62)高长江:《民间信仰:和谐社会的文化资本》,《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
(63)刘惠萍等:《在“传统”与“发明”之间:当代民间文化研究的反思》,《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
(64)赵世瑜:《民间信仰研究如何推进?——对近期关于华琛“神明标准化”的讨论之反思》,http://book.sina.com.cn/cul/c/2009-09-21/1459260564.shtml
(65)符平:《“再造信仰空间——湘中两处三仙观(殿)的个案研究》,载《乡村中国评论》2008年第3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
(66)张佩国:《祖先与神明之间——清代绩溪司马墓“盗砍案”的历史民族志》,《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标签:民间信仰论文; 韦伯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信仰论文; 人类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宗教论文; 碧霞元君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