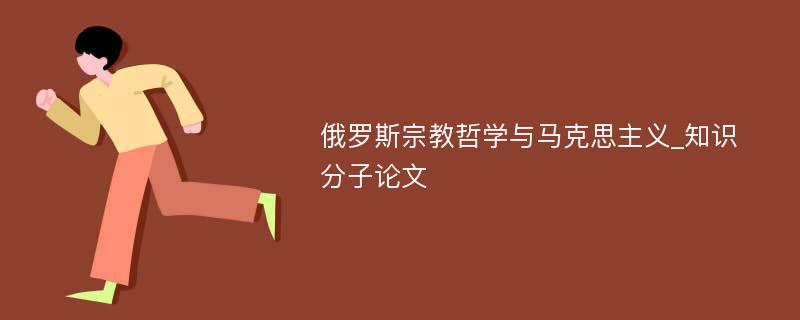
俄罗斯宗教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宗教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它与宗教哲学几乎是水火不相容。无论马克思早期的著作还是后来的著作,宗教都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而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发展延续了这一传统,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逐渐确立起来时,宗教便再也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一个人很难做到既信仰马克思主义又信仰宗教哲学。马克思主义以彻底的无神论自居,与宗教势不两立,也与以信仰为基础的俄国宗教哲学不能共存。不过颇为有趣的是,俄罗斯的一些宗教思想家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最著名的有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和弗兰克等,马克思主义在他们转向宗教哲学的思想历程中究竟起了桥梁的过渡作用还是作为需要批判的反面教材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一、宗教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批判
一般认为,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和弗兰克等人是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宗教哲学的,他们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在后来他们的思想发生了转向,转变成了基督教思想家。但是,仔细说来,宗教哲学家从来都不是正统的或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像通常那样,把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解为一种唯物主义或者辩证唯物主义的话(注:别尔嘉耶夫认为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在逻辑上是不相容的:“不可能有物质的辩证法,辩证法以逻各斯、意义为先决条件——唯一可能的辩证法是思想和精神的辩证法。”(Бердяев:Истог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низма,Paris:YMCA Press,1955,p.82.)),那么可以说,宗教哲学家从来就没有接受过这种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宗教哲学家即使在思想发生转向前,也很少在哲学上同情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和接受只限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马克思所构筑的共产主义理想。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宗教哲学家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还是批判,在很大程度上都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
应当说,多数宗教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熟悉的,他们中的不少人认真地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有的还曾试图作同情式的理解,理解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作过不少积极的肯定的评价,并为马克思主义高屋建瓴的历史观和宏大的视野所折服,他们认为俄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使俄国实现了真正的欧化,进入了世界历史。与马克思主义相比,俄罗斯以前的文化简直是地方性现象。不过,宗教哲学家基本的基督教立场使得他们永远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思想,苏联的革命实践使他们在看到其正义性一面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极权主义的隐忧。
1.进步理念的实质
宗教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明的产物,是深受西方思想传统的影响的,其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和核心内容是进步的理念。在实证哲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理解为一个由低级向高级渐次上升的过程,终点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的最终目标。在向这个目标的奋斗过程中,人类要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并且要作出巨大的牺牲。在宗教哲学家看来,马克思的这种历史观的后果和实质一是为历史上的恶辩护,二是把过去和现在看作是未来的手段,因而是不道德的。这种进步理念包含着神正论的因素,根据这种理念,就可以认为历史上的恶是发展过程中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步骤。只要是通向未来的理想王国的一环,只要它处于通往最终目标的路途上,只要它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前奏和准备,那么不管以往的、乃至现在的历史事实本身是善还是恶,它都是有价值的、进步的因素,因为它对“理想的”前景作出了贡献。
其实,反对在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进步理念不仅是宗教哲学的特点,也是整个俄罗斯哲学的显著特征。俄罗斯的哲学家们反对将一个世代贬抑为遥不可及的后世获取福祉的手段(赫尔岑),反对历史必然性的观念(米海洛夫斯基),反对理性的必然性(别林斯基),反对用无辜者的苦难换取未来的和谐(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把过去和现在当作未来的阶石(费奥德洛夫)。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们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个传统,他们把进步理论等同于社会主义,而把社会主义又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布尔加科夫就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上最重要和被最广泛接受的进步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当然是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他看来,如果为了进步,人类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的话,那么这样的进步宁可不要,他从根本上对把普遍的幸福作为历史的最终目的这一做法提出了质疑。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是不可替代和不可置换的,凭什么要在普遍性的幌子下,以未来的毫无保证的幸福作为允诺来牺牲个人和眼前的利益呢?纵然未来花团锦簇,前景妙不可言,也没有道理让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的无数代人用生命和苦难来铺路搭桥,何况这个允诺更可能是个陷阱呢?而在别尔嘉耶夫看来,进步的宗教是一种死的宗教,而不是生的宗教,它缺乏科学的、哲学的和道德的合理性,它是与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相敌对的,个体的人全然不在它的视野之内。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以历史的规律性和合目的性为前提的历史观是与人的自由格格不入的。历史本身是否有目的,有铁定的规律这是个大可怀疑的问题。“必然的历史进步的规律是没有的,这与人的自由是矛盾的,并且要以虚假的客观目的为前提。”(注: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第289页。)
把遥远的未来作为人们的全部希望所在,把人们的幸福托付和挂靠在看不见的彼岸,名义上是给予现实的苦难以灵魂的慰藉,实则是牺牲和扼杀现世的幸福。别尔嘉耶夫对这种进步理念可谓深恶痛绝:“相对于时间中的所有其他时刻而言,它是一个贪婪的吸血鬼,因为将来吞没了过去,是过去的杀手,进步的理念把它的希望建立在死亡之上,进步证明不是永生,不是复活,而是永恒的死亡,过去被将来永远抹去,前面的一代被下一代永远抹去。解决一切的天赐之福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会降临,将来的每个瞬间是分裂的和破碎的,它既是被吞没者,又是吞没者,吞没着过去而又被将来所吞没。这种时间中的矛盾使关于进步的整个理论成为不完美的和不适当的。”(注:Бердяев:
смысл истории.Опыт филосфии человеческо й
судъбы,Paris:YMCA Press,1969,p.228.)
2.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弥赛亚性质
宗教哲学家们把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相比(注:在西方世界,将马克思主义类比为宗教者亦大有人在。20世纪美国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保罗·蒂里希(Paul Tillich)就曾以“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为题论述过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和关于历史的概念与基督教的解释有着明显的一致性(见蒂里希《政治期望》,第121-129页)。),只不过这是一种无神的宗教。布尔加科夫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关于千年王国的学说,是关于尘世救赎的学说,是要在地上建立起上帝之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俄国有宗教倾向的无神论有吸引力,就是因为它有一个乌托邦的和末世论的维度。人类向共产主义的迈进,就是向自由王国的跃进。自由王国的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当中最诱人和最有价值的地方,丢掉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翅膀,就不再值得同情和联合。而伯恩斯坦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失去了翅膀的马克思主义,它的成功表明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反乌托邦和反末世论的倾向。布尔加科夫认为,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成功表明了实证科学与宗教精神的结合已经不再能够行得通了,科学已不再支持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因此,为了挽救信仰,有必要从根本上把科学与宗教分离开来。这种认识促使布尔加科夫转向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有神的宗教。
别尔嘉耶夫也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思想暴露出许多矛盾之处。一方面他有感于革命的暴力,他指出了千年王国梦想的异教性质,他宣称,基督教的末世论维度不应当被理解为在历史终点的赎救;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无政府主义者神权政体”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是朝向这个方向的正确一步,它的任务是将神的精神注入经济领域,从而为上帝王国提供经济基础。
另一位著名的宗教思想家诺夫哥罗特采夫也论述过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命运,他的主要思想体现在《论社会理想》(1917年)一书中,他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关于尘世救赎的最完美的宗教样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超越性的宗教,它来自于费尔巴哈的人身上固有的神性的概念。费尔巴哈把人神化,把人看作世界的中心,他一反传统的神学观点和基督教学说,认为人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相反,神是按照人的形象塑造出来的。这样,神人的宗教就变成了人神的宗教,人成了最高的存在,他不再需要有攀附的对象,因而也就不再有超越性。马克思虽然没有接受费尔巴哈把人神化的思想,但是在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主要是1833—1834年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有一个类似于宗教中的救赎的概念,这就是“人的根本解放”。“人的根本解放”就是指通过把人变成“类存在”或“公有的存在”,使人从“利己主义”中解放出来。马克思说:“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43页。)马克思尽管没有把人神化,但是他把人本身看作是人的根本,因而照布尔加科夫的看法,也是没有超越性的宗教。没有超越性的马克思主义就在集体中寻求救赎,它力图通过把个人与集体结合起来的办法,把个人上升到类的高度,使个人摆脱异化,回复到真正的人性中去。
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以集体性战胜个体性的做法也正是宗教哲学所极力反对的。以集体的方式消除异化寻求救赎势必要形成对集体的依赖,其结果是个性消融于集体中,集体对个人施暴,是前所未有的极权主义的到来。布尔加科夫以自己的语言对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作了如下概括:“只有当人们丧失了他们的个性,社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斯巴达,一个蚁丘,或一个蜂窝时——只有在那时人类解放的任务才能完成。”(注:Булгаков,философия кхозяиства,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0,pp.331—332.)布尔加科夫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个要求人完全社会化的
集体主义宣言。
3.马克思主义和欧洲人文主义的危机
别尔嘉耶夫还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文化史上的地位,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证明了欧洲人文主义复兴的危机,人文主义宣称人是唯一的价值,并坚持对人的无限能力的信仰,认为它渗透到了自然和历史的隐秘意义中,这是一种对人类按照他所希望的样子改变历史过程的自由权利的信仰。马克思虽然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揭露了资本主义的不人道的本质,并试图通过共产主义的构想来克服异化,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但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相反它把这种异化更加推向极致,社会主义产生了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依赖形式和人们对经济、国家、政治和文化的异化。在别尔嘉耶夫看来,社会主义的异化是资本主义对价值的毁灭的继续,压迫个人良心的虚假的集体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意欲克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异化,不料却陷入了一种更可怕的异化,这就是对集体的依赖,这个集体强大无比,它可以毁灭个性,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整齐划一,从而使得人不再代表他自己出场,而是以阶级的一员而存在。别尔嘉耶夫认为,这种用社会代替个人的做法暴露了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它终结了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传统。在马克思那里“发生了人文主义的集体主义的自我分解和人的形象的集体主义的动摇”(注:Смысл истории.,p.188.),人被看成是为实现自由王国,为克服异化的斗争中的工具,在这种斗争
中,人类的道德价值被宣称不过是偏见、意识的幻象、意识形态和反人的社会关系的歪
曲的反映,看作是有限的阶级道德。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置于所有这些之上,相信它从人
类的幻象中一劳永逸地脱离出来,因为这种理论自称是置于坚定的现实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4.马克思主义的前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前景,关于马克思主义能否获得新的历史意义,在20世纪早期,别尔嘉耶夫写道:“在实现它的努力中,社会主义将完全不同于社会主义者正在寻求的东西,它将会显露出人类生活的新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会使完成社会主义运动所设置的任务变得不可能,它永远不会取得马克思想要通过统一劳动而取得的人类劳动的解放,它永远不会把人导向丰富;它永远不会实现平等,而只会在人们之间制造新的敌意,制造一种相互分离,和压迫的新的前所未有的形式。”(注:Смысл ucmopuu.,pp.238—239.)别尔嘉耶夫认为有必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的和实际政治的方面区别开来:前者是观察世界的错误的方法——否定精神生活和人类个体自由的共产主义的宗教,然而后一方面包含着大量有效的和健康的方面。“在共产主义当中,真理和谬误如此缠绕在一起,是因为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精神现象。”(注:Истог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p.125)马克思
主义的真理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基本的社会正义的要求、它的集体地调节社会
生活的可能性的思想,它的建立一个无阶级的、基于劳动之上的社会的思想。马克思主
义的谬误在于这种学说的极权主义的性质,在于它企图独霸解决人类社会过去,现在、
将来的问题的权利。在别尔嘉耶夫看来,马克思主义只有当它包括了个人自由和人类个
体尊严的原则,当它面向普遍的人类文化而不是阶级文化的更高成就时,它才能被给予
一个新的意义。
二、宗教哲学家论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起源
1、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起源首先是与知识分子联系起来的,它首先是一个思想事件。19世纪九十年代和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俄国成为一个影响巨大的潮流,这是与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分不开的。知识分子一词在俄国有着特殊的含义,它不同于西方的intellectual。作为intelligentsia的成员,不只完全关心其个人福祉,而且更加关怀社会的福祉,愿意尽力谋求社会的利益。别尔嘉耶夫认为俄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任何一种社会实体,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某种社会理想。他说:“知识分子更像是一个有着自己非常不宽容的道德,强制性的世界观和特殊的方式和习惯的僧侣阶层或宗教教派”。(注:Бердяев:Истог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p.17.)这就注定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无根性”特点。知识分子
的无根性一方面是指俄国的知识分子长期生活沙皇专制政权之下,他们遭受着残酷的压
制,毫无自由可言,上面是“死气不化、压迫成性、缺乏想象力的政府”,下面是“饱
尝苛虐、经济破灭的农民”,而他们则是一个“人数稀少、深受西方观念影响的受过教
育的阶级”。他们不为任何一方所接受和认可,基本上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对俄
国社会的现实了解不多或根本没有了解。另一方面是指俄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由某种
客观的存在条件而统一起来的社会群体,他们完全是无私的,所思所想所为并不是从自
己的狭隘的物质利益出发的,他们与专制政府进行着百折不挠的斗争,但却并不企图在
斗争中为自己捞取什么好处,而是一切“以人民的名义”行事,为了人民,他们宁愿受
苦、坐牢、流放、受尽煎熬也在所不惜。不仅如此,在人民面前,他们有着深重的负罪
感。知识分子拥有知识,但他们却并不以此为荣,相反却觉得这是压在他们肩头的一个
沉重的负担并力图摆脱之。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获取知识是以农民受苦作为巨大代价的。
一个知识分子注定是没有阶级偏见,它不属于任何人,甚至不属于他自己,除去他的信仰,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但是他的信仰,那些把知识分子统一到一起的观念来自哪里呢?无外乎两个地方,或是西方的影响,或是本土的理想化。俄国的知识分子也因此而分成两大阵营,倾向于西方的思想,主张走西化道路的被称为西方派,而认为俄国的出路在于回到古代,主张从俄国的东正教传统和农村公社中寻求俄国的出路的被称为斯拉夫派。不论是西方派还是斯拉夫派,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或是把西方的制度与文明美化,或是把自己的传统美化,把想象的东西当成了真实的东西,而真实的现实仿佛倒成了想象的东西。
俄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他们社会地位的独特性,从恰达耶夫、普希金、卡威林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列昂季耶夫,描写多余的人就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或者说,这些作家本身就是多余的人的典型。多余的人之所以“多余”是就其无根性而言的。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无根性,并力图从这种无根性中挣脱出来。他们致力于为自己找到一个坚实的“根”,并在这个根的基础上改造那个他们如此不满、如此憎恨的社会。“无根”一方面产生了对“根”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的反抗成为可能,他们无需为了捍卫一己之利而囿于自己的小圈子内,无需患得患失,因为他们没有什么需要维护的。
无根性为他们的叛逆提供了可能和便利,但是叛逆本身却需要一个支点,需要一个目标和方向,需要一种理论,以便使得这种叛逆成为合法的和有意义的行为。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共产党宣言》响亮的口号:“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像是专门为他们而写的,尽管马克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根本没有把他的理论与俄国联系起来。无根性原来有着自己的理由和存在的价值,它肩负着超乎寻常的使命。
2、以科学和客观真理面目出现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首先是以一种科学的面目而出现的,它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向世人昭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页。)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和不容质疑的客观性而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使得俄国的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行动的根据,他们不再觉得自己悬在空中,脚下也不再是深渊,而是坚实的大地。这个理论对于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乌托邦的幻境中而又急于改变现存社会状况的俄国知识分子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他们制定和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天国乐园般的生存状态,而且指明了到达这种状态的途径和手段。他们一向梦寐以求的东西不再是毫无根据的想象了,而是有着科学的依据,是根据客观规律推算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还告诉他们,这个美好的状态尽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人们不应“守株待兔”,而应积极地为这个社会的到来而奋斗,在通向这个幸福王国的历史过程中,人并不是消极无为的。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不矛盾。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还有很大的灵活性,当没有条件的时候,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条件。历史一方面要遵从客观的规律,另一方面也是人奋斗所争取的结果,因而它既是自然的历史的过程,又是人创造的,是人类活动的结果。
别尔嘉耶夫认为,马克思的这种理论对俄罗斯极有诱惑力。一方面,马克思挑选显而易见的日常事实为自己的理论进行论证: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想出来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有一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
存在,就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然后才能从事科学、艺术、精神的生产。然而别尔嘉耶夫认为,恰恰是这些琐碎的事实成为马克思主义幻象的主要来源。别尔嘉耶夫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大致如下:没有任何前提而以“纯粹的”形式存在的人纯属理论上的假设,而这却被马克思主义当成了主要的历史事实而作为前提。人类个体的存在不仅被马克思看作是历史的前提,而且被看作是人的本质的显现。但是作为对历史的理论解释的产物的“本质”就像以“纯粹的”形式而存在的个人一样,在历史中几乎是找不到了。因而马克思的理论大厦并不具有现实的立足点,而是建筑在沙滩之上。
3、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性及其在俄国的异化
别尔嘉耶夫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矛盾的地方,它既是唯物主义的,又有唯心主义的成分,正是这种矛盾性使得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有了多样化的可能,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后来在俄国的土壤上得以进行独一无二的改造的源泉之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在俄国之所以有市场,这是与俄国的唯物主义的大众化分不开的。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改造社会的渴望,他们的哲学观与现实更贴近,唯物主义的成分也更多些。作为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所以当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作为一种战斗的无神论、作为一种其目的不只是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的哲学而出现时,对于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犹如止渴之梅,恰逢其时。但是仅有这点是不够的,因为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学说,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并不具备,俄国的资本主义只是处于初级阶段,还很不发达,更没有达到马克思所想象的那般盛极而衰的地步,因此,马克思的学说对于急于进行社会改造的俄国知识分子来说,似乎又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但是这一障碍在马克思的精妙无比的辩证法中得到了解决。马克思的辩证法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对历史的参与,强调人民群众在改造世界中的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中的这一面被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所体现。19世纪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潮,不是偶然的,也不能仅仅归结为理论宣传的结果,而是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基础的。别尔嘉耶夫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尽管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但却具有心理学上的必然性。它宣称精神可以变物质,虽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样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革命的条件是否成熟,而在于如何动员群众,把群众的热情转变成为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现实力量。而俄国的共产主义则“表明了这种观念对生活的力量是多么的巨大,如果它是一个整体并与群众的直觉相符合的话”。(注:Бердяев:Истог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pp.88,100—101.)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在俄国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主观压倒了客观,革命意志制服了必然性。而马克思主义也成了它自身的牺牲品,这种号称以客观现实作为自己出发点的理论在俄国则是作为一种客观真理而预先存在,俄国革命倒成了它的结果。俄罗斯接受的只是它所需要接受的东西,它并不对马克思主义当中所有的东西都感兴趣,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主要是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共产主义被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而共产主义又被与俄罗斯的紧急的社会问题和弥赛亚意识联系起来。从根本上说,共产主义学说能够在俄国立足、生根并结下果实是与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分不开的。关于共产主义在俄国的命运,别尔嘉耶夫写道:
“俄国知识分子的整个历史为共产主义准备了道路。共产主义包含了一些熟悉的特征:对社会正义和平等的渴望,把劳动积极安排为一更高的人类类型,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厌恶,对完整的世界观和与生活的完整关系的追求,对宗派的不可忍受,对文化精英的猜疑和敌对态度,极端的世侩气,对精神和精神价值的否定,把几乎是神学的特点归于唯物主义,这些特征一直是俄国革命、甚至激进些,是知识分子的特点。”(注:Бердяев:Истог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pp.88,100—101.)
别尔嘉耶夫多次说过,在俄国,知识分子是个不切实际和过于理想化的阶级,这也是他们的无根性的表现之一。这种不切实际和理想化常常使他们对眼前的现实避而不见,或者说,他们宁可相信他们亲眼所看到的是假的。之所以不愿意面对现实,是因为现实与他们的理想相去甚远,或正相反。因为不如所愿,与希望的不一致,便否定了其存在的真实性。闭上眼睛,还可给他们少许安慰,而直面现实,带给他们的将是恶梦,他们所有的希望都将破碎。因为俄国的现状不仅与马克思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相距十万八千里,而且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俄国连革命的资格都没有: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然而俄国尽管不具备革命所具备的物质条件,但由于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使得俄国人知道有这样一项任务需要完成。革命注定有一天要到来,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障碍固然存在,但并非不可克服。
马克思主义宣称自己的偏见最少,因为它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而在无产阶级身上,旧的残余最少,这样就不仅使其自身具有了革命性的品格,而且还与俄国知识分子的无根性相契合。其实,所谓的无产阶级在俄国也只不过是个抽象的观念,俄国人所关心的只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和思想,至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俄国是否存在以及有多大的力量,他们并不在意。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思想,一种为他们揭竿而起而鼓噪的舆论力量。别尔嘉耶夫说得很是干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不是一个经验的实在,它是由知识分子所创造的一个思想和神话。”(注:Беодяев,О рабстве и свободе человек,Paris:YMCA Press,1939,p.177.)俄国的知识
分子一向有从人民出发,一切为了人民的替天行道的侠义精神和伟大传统,要接受马克
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只需把人民替换为无产阶级就行了。对于俄罗斯大众来
说,“如果它的革命意志被充分提高,如果它被组织和训练,那么它会创造奇迹,它能
够克服社会规律的决定论。”(注:Бердяев:Истог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p.88.)
总的来说,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最为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创建自己的理论时,本来有着很强的现实感,他们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认真和详细考察的基础上得出的一套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和改造世界的方案。但是,在俄国那里,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这种依赖感被连根拔掉了,它完全成了一种面向未来的乌托邦构想,在这种乌托邦面前,现实变得无足轻重了,它丧失了独立的价值,而仅仅成为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桥梁。或者说,它只具有否定的意义,即只是在否定旧世界准备新世界方面才有意义。正因为现实不具有独立的意义,所以俄国的知识分子也很少去真正地关注和研究它,而只是把它看作一个绝对恶的和有待超越的存在物,甚至干脆闭上眼睛,等着恶梦过去,憧憬着美好未来的到来。共产主义在俄国的经历是一次浪漫的社会试验,它表达了俄国人对社会正义和人类自由王国的渴求,反映了俄国人敢为天下先勇于建立新世界的魄力。但是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真实的基础,它并不真正具备马克思所一再强调的革命所必需的物质基础,而只是靠革命的激情而行事,这种激情不仅体现在革命时期,也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俄国人靠自己的激情几乎创造了奇迹,但激情并不具有持久性,一旦激情冷却下来,被激情埋藏和掩盖的东西就会暴露出来,这时惰性的、物质的东西就会表现出其力量。应当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学说在这一点上具有无可辩驳的真理性和力量,可惜恰恰是这一点被俄国人忽视了。
三、俄罗斯宗教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分歧
以上两部分——俄罗斯宗教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以及对俄国共产主义起源的分析已经蕴含着俄罗斯宗教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分歧。下面我们再作几点补充。
第一、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它把无产阶级看作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壮大要依赖工人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其中,阶级斗争和权力问题占据了中心位置;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是农民公社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对他们来说,保存和加强农民土地所有制和俄国农村公社的自治,具有首要的意义(注:俄国传统哲学所理解和追求的社会主义是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列宁将其基本理论观点概括为“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生活的村社制度,由此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这就是鼓舞他们、唤起数十人数百人去同政府作英勇斗争的东西。”(《列宁全集》第一卷,第241页)民粹派思想家阿·普·夏波夫鼓吹“古老的、不朽的、永恒的农民米尔的支柱”是俄国“自我发展的本原和初型”(《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页)。他说:俄国“什么也不需要,只需要米尔的联合、接近与和解的精神,只需要米尔的会议和协商的精神……”(同上书,第38页)。“只有把米尔、米尔的会议和协商精神,米尔的连环保、米尔的公社进取精神的原则贯彻到自己的社会生活中去,贯彻到自己的风俗习惯中去,才能有任何全体一致的、坚决的社会主动精神,才能有任何有益的社会会议和社会舆论。”(同上书,第40页),而且他们把这看作是俄国对西方的主要优点。这种看法不仅宗教哲学家有,而且在激进的知识分子当中,如在赫尔岑等人那里也非常普遍。
第二、关于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主要从社会性和实践的角度来考察人的。人是在历史中活动的人,其首要角色是历史过程的主体,他是一个社会存在物,是各种力量的贮藏所,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只有置于社会历史中才能理解,脱离现实关系的孤立的个人是不存在的。而俄罗斯宗教哲学一开始就是人类学的,它甚至是作为一种人的哲学而形成和发展的。别尔嘉耶夫声称:“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一切都来自它,一切都复归于它。”(注:Учителъская газета,1990,no.27,p.11.)宗教哲学主要是从人的感性存在、从人与上帝的关系、从个体人格的自由、从
伦理学等角度来研究人的。它把人看作是个体的、感性的存在物,并肯定个体对社会的
优先性。在这里,人不是宇宙的微不足道的一分子,而是一个独立的小宇宙。人既处于
时空中,又超越了时空。它所强调的不是“人是历史的人”,而是“历史是人的历史”
。它认为只有一种标准适用于人,这就是道德和伦理的标准,个体的人的道德上的自我
提高是协调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
第三、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宗教哲学家基本上对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持一种敌对的态度,但他们并不是全盘反对共产主义者所从事的事业,在他们看来,革命具有某种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是正义的。他们承认共产主义有其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反对资本主义之恶、反对社会特权之恶的问题上包含着真理性的内容。但是宗教哲学家认为,俄国的共产主义缺乏精神自由原则和个性原则,而这些恰恰是他们最为珍视的,任何别的什么东西都不能与之兑换:无论是列宁的面包,还是赫鲁晓夫的土豆牛肉。他们发现,俄国的政治革命是敌视精神的,“有时,我觉得这些政治革命是精神上的反动,我在这种革命中发现了对自由的厌恶,对个人价值的否定。”(注: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第102页。)宗教哲学家赞成在社会方面,即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方面采用共产主义,但是不赞成在精神上采用它。
宗教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作为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类似的区别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很多,一一将其列举出来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想要强调指出的一点是它们的对立有着深刻的哲学基础,这就是宗教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自由的不同理解。西方的一些学者攻击马克思主义不讲自由,把马克思主义诬蔑为极权主义当然是十分错误的,这种观点不仅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所驳倒,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不相符的。马克思及其后继者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宗旨就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蓝图,把人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盲目必然性下解放出来。但是不容置疑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自由的理解与俄国宗教哲学的确存在着根本区别。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或者说是意识到了的必然性。人无法摆脱必然性的控制,企图摆脱必然性的想法和努力只能导致更大的不自由。人类的唯一出路在于去认识必然性,掌握规律,利用规律,亦即摆脱盲目性。自由从根本上说是征服自然、使自然力屈服于严格的、有意识的控制,从而成为集体命运的真正主人的能力。苏联的共产主义实践,无论是政治上的集权,还是经济上的高度集中,抑或文化上的专制,都可以看作是这种自由观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列宁和斯大林等领导人雄心勃勃地企图把全社会的力量组织起来,有意识地驾驭自发的力量,实现改造自然和规划社会生活的目的。不过,问题在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一部分人是否有权代表整个社会去思考,它对自然界和社会规律的认识(如果说有规律的话)能否做到正确而又面面俱到?如果能,那么那些作为小人物而存在的芸芸众生是否有其独立的价值,是否只有作庞大的行军中一分子的份?如果不能,这样的实践行为会导致怎样的后果?谁来为这种后果负责?更为严重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自由是指作为总体和主体的人类对作为总体和客体的自然的认识和征服,但是如果这种征服被一部分人用于另一部分人身上呢?对物的控制一旦被置换成对人的控制,“自由”便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一部分人的自由要以另一部分的受奴役为前提和代价。这些正是宗教哲学家所担心和不能接受的。此外,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还包含着人的全面发展,而列宁则更强调解决大众的基本需要,最重要的是不受饥饿的自由,要每个人有饭可吃,有衣可穿,有房可住。至于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精神自由则被看作是资产阶级骗人的谎言,是形式上的东西,而宗教哲学家恰恰把这看作是最主要的东西,精神的自由、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性才是最根本的自由。宗教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分歧似乎都可以归结到这一点上来。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基督教共产主义论文; 宗教论文; 俄罗斯历史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进步主义论文; 人类进步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布尔加科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