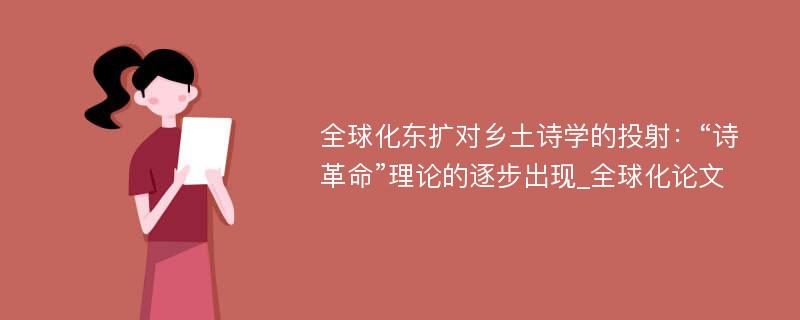
全球化东扩的本土诗学投影——“诗界革命”论的渐进发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本土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8)02-0039-09
学界都承认,是梁启超而非别人发起了轰动一时的“诗界革命”。但人们很少关注这种开风气之先的“革命”论本身的渊源何在,最多把它同之前的黄遵宪及其同时代诗人联系起来。我在这里不打算具体分析“诗界革命”论的内涵本身,而只想指出,对这场“革命”诚然可以作多种不同理解,但可以视为“全球化”在其东扩过程中的一种诗学反响。同时,梁启超所推举的“诗王”黄遵宪,其诗论实际上受到更早的王韬的影响。由这一关联可进而推知,“诗界革命”论的发生当然有多重渊源(如受日本德富苏峰“革命”论及转口日本而输入欧洲文论的影响、政治改良失败后的文化启蒙需要及其对文学的借重等),但至少可通过黄遵宪而上溯到更早一代知识分子王韬那里,正是从此可牵引出一条“诗界革命”所从中发生和演变的全球性知识型踪迹。这里只需先提及如下事实就够了: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年)在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等一道创办《时务报》并担任主笔,名震海内外;之前17年即光绪五年(1879年),黄遵宪在日本首次会见王韬;而王韬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最早赴英法考察并思考现代性变革的思想家之一。王韬年长黄遵宪20岁,黄遵宪则比梁启超大25岁。正是从梁、黄、王三人及其三代递进中(当然不限于此),可以回溯出“诗界革命”论的渐进性发生的一缕遗踪。
一、从全球化东扩看“诗界革命”
如何看待由梁启超发起的“诗界革命”?学术界已有两种观点。较早的观点认为它是一次改良主义的文学运动,或进步的文学思潮和流派。较近的观点来自陈建华先生,先是认为它“要求诗歌在‘革命之时机渐成熟’的时候,以‘欧洲真精神真思想’为‘诗料’,开辟诗的新境界,实际上要求诗歌起到反映、推动革命思潮的作用。”[1](P195)后来又从“革命”的“现代性”角度揭示了“诗界革命”同“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的渊源关系,认为“‘革命’被限定在诗歌领域,意谓一种变革或一种含有历史性的质变,和改朝换代、政治暴力、天意民心等因素没有直接关系”[1](P14)。“如果说在本世纪里革命意识形态几乎主宰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梁启超首先引进的这个‘革命’观念构成了现代动力”[1](P40-41)。这一新观察是富于见地的。
不过,如果从当今“全球化”及其扩展视角来看,“诗界革命”实际上可以看作由欧洲率先发动而后向全球各国扩展的“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具体说是“全球化”在其东扩过程中必然触发的一种植根本土而面向世界的激烈而又复杂的诗学反响。确切点说,“诗界革命”就是“全球化”东扩所造成的一种本土诗学动员或诗学投影,要求本土文学界人士起而运用诗学武器去加以应对。这不同于过去所谓“西学东渐”即西方学术的东方移植,而是指在注定要覆盖全球的普世变革进程中发生的西半球向东半球的扩张态势,在其中无论西半球还是东半球都无一例外地被规定为总体进程的一部分。“西学东渐”主要着眼于“西学”的中国化,而没有看到这种“西学东渐”本身也只是全球化的一种手段,即只相当于全球化实现其巨大目标的一只手,包括西方和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这一全球进程中,从而引发全球性变革。这样,在这种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本身既是全球化的动力源或主动方,也是被全球化的对象或被动方。
正是在这里,首先需要看到由全球化及其东扩所带来的一种基本的知识型及更根本的个体体验范型的转变: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已完成从传统中国中心的天下主义到全球普遍适用的普世主义的转变。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器变”而“道不变”的本土保守主义相比,梁启超等已拥有了全球普世主义新视野:欧洲有的中国也该有,它们注定要在全球普及。这一代知识分子完全无需像我们今天这样首先论证中西汇通的可比性之类前提,而且根本不觉得这样会丧失本土民族立场。在他们那里,像欧洲那样在全中国推行广泛的革命性变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由于这种全球普世主义知识型的形成,梁启超才会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里这样呼唤道:“乃是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我后,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2](第6集,P3734)同时要看到,对梁启超这样的谙熟我国古代“诗教”或“风教”传统而又抱负宏阔的新锐政治家和思想家来说,“诗界革命”的要务其实不在于汉语诗歌的变革本身,而在于它对享有全球普世属性的中国社会革命可以起到比之普通标语口号远为有力和有效的大众动员作用。通过汉语诗歌的变革去唤起沉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让他们自觉投身这场全球普世的社会变革,正是梁启超发起“诗界革命”的初衷。
当然,汉语诗歌毕竟有自身的语言与美学规律,不能完全按自称“吾虽不能诗”的政治家梁启超预设的轨道奔驰。对诗人来说,自己所置身其中的生存体验世界的变化及其语言表现才是真正至关重要的: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古典“天下”体验到现在的“全地球合一”的全球体验,这一转变对诗人及其他普通人造成的生存震撼是真正致命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政治家的社会动员需要而是诗人的个体生存体验的语言表现需要,构成“诗界革命”的真正核心缘由,尽管政治家的社会动员需要是其直接诱因。这一点正可以从王韬、黄遵宪到梁启超的演进找到一条容易被忽略的连贯的线索。
二、王韬:“奇境幻遇”与“地球合一”
在梁启超规定的“诗界革命”三要素(“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中,“新意境”是赫然列首位的。而中国文学中的这种“新意境”的开创不能不溯源到王韬。王韬(1828-1897)原名畹,字利宾,好兰卿,后改名韬,字子潜,号仲弢,晚年号天南遁叟。他利用被清廷追捕而亡命香港的机会转赴英法游历,获得了“开眼看世界”的先机,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并担任主笔,发表了大量现代政论文、游记散文《漫游随录》以及文言小说。正是中国现代历史上这个尤其多灾多难的特殊年代,使他成为“走向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一员和杰出代表[3]。王韬的上述作品都致力于描写作者在地球上所亲身体验到的新奇景物、人物、器物、事件等,体现了文学新境界的开拓。由于如此,王韬自己明确地主张刻画“奇境幻遇”并力求达到“意奇”状态。
“奇境幻遇”,简单地说就是奇幻的人生境遇。“境”又作“境遇”,指人所身处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状况。王韬继承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境”决定“文”的传统,强调“境”或“境遇”的作用。他在《三岛中洲文集序》里指出:“时势不同,文章也因之而变。余谓文运之盛衰,固有时系乎国运之升降,平世之音多宽和,乱世之音多噍杀,若由一人之身以前后今昔而判然者,则境为之也。”[4](P258)在他看来,“境”是为文的决定性因素,必然在文中投下印记,其变化也必然导致文的变化。但他不是如古人那样一般地谈论“境”,而是突出“境”的“奇幻”特色。“一往情深者情耳,而缘之已定,境每限之,遇每制之,至使思之不得,徇之不可,乃凭虚造为奇境幻遇,而托梦以传之,则我之欲言无可言,欲见未由见者,毕于是乎寄。”[4](P214)他相信,由“境遇”的制约作用,作者往往不得已而创制“奇”文。可见,通过想象手段创造“奇境幻遇”,是王韬文论的一个明确追求。考虑到王韬身处于其中的中国属古人数千年未遇的全球化“乱世”,充满了新奇遇。这种新奇遇的造成,主要是由于新地球观的形成。正是西方人给中国带来了令人惊羡不已和痛苦不堪的现代性文化。而落实到王韬个人,则是他的一生都与奇异的西方文化发生密切关系,从20岁那年在上海初次体验西方奇观直到后来亲自游览神奇的欧洲。
这种对具有全球化意味的“奇境幻遇”的追求,鲜明地体现在王韬的小说和诗歌理论中。他的《淞滨琐话》是谈狐鬼之作,其自序说:“天下之事,纷纭万变,而总不外乎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淞隐漫录》所记,涉于人事为多;似于灵狐黠鬼、花妖木魅,以逮鸟兽虫鱼,篇牍寥寥,未能遍及。今将与诸虫豸中别辟一世界,构为奇境幻遇,俾传于世。非笔足以达之,实从吾一心生。自来说鬼之东坡,谈狐之南董,搜神之令升,述仙之曼倩,非必有是地、是事,悉幻焉而已矣。幻由心造,则人心为最奇也。”[5](P5)这里道出了其小说写作题旨:借“奇境幻遇”表达对“纷纭万变”的现代性境遇的体验。
王韬标举“奇境幻遇”,不是要追求语言上的新奇,而是寻求新颖而独特的意义创造即“意奇”,这构成后来黄遵宪和梁启超的先声。王韬在《跋湫村诗集后》里虽然自述“余于诗亦欲以奇鸣”,但又特别解释说:“余谓诗之奇者,不在格奇句奇,而在意奇……必先见我之所独见,而后乃能言人之所未言。夫尊韩推杜,则不离于摹拟;模山范水,则不脱于蹊径;俪青配白,则不出于词藻;皆未足以奇也。盖以山川风月花木虫鱼,尽人所同见;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尽人所同具;而能以一己之神明入乎其中,则历千古而常新,而后始得称之为奇。”[4](P326)他注重的不是语言上的“格奇句奇”,而是意义表达上的“意奇”。这种“意奇”首先依赖于“见我之所独见”,即获得个人独特的世界体验;其次,来自于对这种“独见”进行加工创造,以便“言人之所未言”,表达出前人或他人都不曾表达过的原创性观点。所以,“意奇”就是指在个人独特体验(“独见”)基础上形成的原创性形象及其意蕴(“人之所未言”)。这种“意奇”的形成,要求“以一己之神明入乎其中”,取得“历千古而常新”的效果。显然,对“奇境幻遇”的刻画根本上服从于对“意奇”效果的追求。
为什么他对“奇境幻遇”情有独钟?《淞隐漫录自序》道出了苦衷:“盖今之时,为势利龌龊谄谀便辟之世界也固已久矣,毋怪乎余以直遂径行穷,以坦率处世穷,以肝胆交友穷,以激越论事穷。”[6](P2)他的小说写作是个人“穷”而后作的结果,所谓“困极则思通,郁极则斯奋,终于不遇,则惟有入山必深、入林必密而已,诚壹哀痛憔悴婉笃芬芳悱恻之怀,一寓之于书而已”[6](P2)。这种写作动力陈述同古人所谓“穷而后工”或“愤而著书”之说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而在具体写作时,他有自己的明确规定:“求之于中国而不得,则求之于遐陬绝峤异域荒裔;求之于并世之人而不得,则上溯之亘古以前,下极之千载以后;求之于同类同体之人而不得,则求之于鬼狐仙佛草木鸟兽。”[6](P2)他的艺术形象的原型或来源,往往是边缘异域处、亘古前或千载后、或神仙鬼怪自然界。这使他与蒲松龄颇为近似。但是,他的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急切地要表达的决不是什么纯粹个人身世伤悲,而是自己浪迹天涯“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尤其是他在中国和欧洲所获得的对中国文化在地球上的空前危机境遇的痛苦体验及相应的拯救意向。“昔者屈原穷于左徒,则寄其哀思于美人香草;庄周穷于漆园吏,则以荒唐之词鸣;东方曼倩穷于滑稽,则十洲洞冥诸记出焉。余向有遁窟谰言,则以穷而遁于天南而作也。”[4](P316)正是这样,他的写作才不同于通常闲来无事的“小说小道”,而是直接伴随着个人对中国文化命运的丰富的喜怒哀乐体验。
可以说,通过“奇境幻遇”而创造“意奇”效果,是王韬的游记散文和文言小说的一个共同追求。“奇境幻遇”,指的是奇幻的境遇,它是手段;“意奇”指的是意义表达上的新奇和独创,这才是目的。两者间是由同一个“奇”字贯串起来的。王韬显然把描绘奇幻的人生境遇和表达新奇而富有原创性的观点,作为自己文学活动的最高美学原则。
为了达成“奇境幻遇”和“意奇”效果,王韬还不惜抛弃正统历史观而采纳非正统的“稗史”材料,体现出一种“正稗背合”观。他在自己的历史与政论著述中,大量采撷经过考订的野史、稗史、方志、碑刻史料等。他认为:“稗史虽与正史背,而间有相合。”这是说,非正统的或边缘的稗史虽有与正史相背逆的方面,但也存在相合或相通之点,从而出现“正稗背合”情形。稗史可以“扩人见闻”,使人增长见识;同时,还可以怡情悦性,“野乘亦可怡情,艺谱亦为秘帙,山经舆论各专一家,唐宋文人,类以此自传”。由于稗史具有这种增长见识和怡情悦性作用,所以,王韬主张治史应“取资于稗史,折中于正史”①。这为后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历史研究方法》所肯定。王韬的尚奇求幻的美学观与其注重“稗史”的“正稗背合观”相合拍。王韬也曾在《蘅华馆诗录·诗评》中使用“意境”:“意境超脱,吐属韶秀”。尽管他没有具体展开和做独特发挥,但毕竟可见“意境”概念在当时已经被人们一般地采用了。
更需要看到,王韬的“奇境幻遇”说的内涵其实同他独创的“地球合一”说相互贯通。王韬在《拟上当事书》里描绘出全球各国由分离走向合一的全球性状况以及中国遭遇到的崭新的“创局”境遇:“泰西诸国,与我立约通商,入居中土,盖已四十余年矣。其所以待我之情形,亦已屡变,总不外乎彼强而我弱,彼刚而我柔,彼严而我宽,彼急而我缓,彼益而我损。今日者,我即欲驱而远之,画疆自守,亦势有所不能;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全地球东西两半球,所有大小各国,无不入我之市,旅我之疆,通好求盟,此来而彼往,其间利害相攻,情欲相感,争夺龃龉,势所必至,情有固然。”[7](P208)这里的“创局”根本上意味着中国面临一个崭新的创造性境遇——“地球合一”。在此新境遇中,中国已不可能再度“驱”西方诸国而“远之”,“画疆自守”,而只能向全球各国开放,寻求共处。他的《代上苏抚李宫保书》指出:“昔之与我为敌者,近在乎肘腋之间,今之与我为敌者,远在乎环瀛数百里之外;昔日止境壤毗连一二国而已,今则环而伺我者,大小数十国;昔之书于史者,曰来寇,曰入犯;今之来者,曰求通好,曰乞互市。今昔异情,世局大变,五洲交通,地球合一,我之不可画疆自守也明矣。”[7](P215)这里的崭新的“地球合一”时代实际上相当于今日所谓“全球化”或“全球性”境遇。这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商业贸易的全球化(“互市”);其二,交通的全球化(“五洲交通”);其三,国家间外交的全球化(“旅我之疆,通盟求好,此来而彼往”);其四,各民族国家的生存境遇的全球化(“全地球东西两半球,所有大小各国,无不……利害相攻,情欲相感,争夺龃龉,势所必至,情有固然”)。在这里,全地球各国之间形成一种必然地相互依存和相互共生的新型关系。王韬自己的《答强弱论》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故善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4](P201)试想,上面说的“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一幅多么浪漫而动人的列国助中国富强的全球化图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韬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明确地和完整地标举“全球化”视野和理论的第一人。
可以相信,正是对“地球合一”奇观的亲身体验和洞察,为王韬的“奇境幻遇”诗论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支撑。这无疑对后继者黄遵宪的以“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为核心的诗论提供了启迪。
还可以提到,人们曾对梁启超所倡导的中西文化“结婚”说及其中的中国文化“迎娶”西方“美人”的内涵颇感兴趣,但实际上,这种中西文化融会构想早已由王韬在自己的文言小说里想象和描绘过了。王韬写过几篇有关中西联姻想象的文言小说。在《淞隐漫录》卷七《媚梨小传》里,这种想象在异国三角恋故事中,通过一对相互热恋的中英男女得到了呈现。媚梨是英国世家美女,“生而警慧觉伦,书过目即能成诵,各国语言文字悉能通晓。而尤擅长于算学”。自幼与乐工之子约翰青梅竹马,“两相爱悦,目成眉许,誓为伉俪”。但碍于两家“门第悬殊”,不能结合,就私下于山上废宅幽会。父亲为她选择了“家拥厚资”而门当户对的西门·栗,她最初不愿,后来终于“心动”。结婚之日,新郎西门正要入洞房,接到约翰的信和附上的媚梨给约翰的情书,本想开枪杀死媚梨“以泄胸中郁勃”,但因爱而不忍下手,于是急写一诀别信后自杀。媚梨只好返回娘家。她在孤独中寻求慰藉之途,带巨资航海东赴中国。她在船上巧遇“自英旋华”的中国青年丰玉田,两人相互教对方英语和汉语,渐生情愫。媚梨提出嫁与丰,丰因担心中西饮食差异及家贫而辞谢,不想媚梨坚决表示自己“耐贫苦”、“可以自给”,还有家中资助的五万巨资作后盾。两人“遂成佳偶,恩爱倍笃,跬步弗离”。这对异国新婚夫妻来到中国,定居上海。媚梨精通数学,尤其“善测量”。当中国海疆受侵犯,媚梨激励丈夫奔赴疆场杀敌立功,而自己也主动请缨参战。在随军舰赴闽江的途中,遇海盗劫掠商船,媚梨“以纪限镜仪测量远近”,指挥丰玉田以三发炮弹击沉三艘海盗船,立下奇功[8](P330-334)。这类想象的中西文化融会景观及其保疆卫国题旨在后来的文学中大行其道,其实正可以溯源到王韬。在这方面谈到梁启超的广泛影响时,应该看到王韬的原创之功。
王韬就是这样率先尝试用古语表达“奇境幻遇”,这就为后来者如黄遵宪“诗界革命”意向留下了矛盾:古汉语语言和文体都不变怎能保障新的“奇境幻遇”的顺利表现?
三、从王韬到黄遵宪
如果说,“诗界革命”论在王韬时代还只是属于一种语不变而境变的朦胧的和局部的改良意向,那么,正是通过黄遵宪的新的诗歌写作实践和诗论主张,这种“革命”的意图和局部筹划已经逐渐地和雄心勃勃地披露出来,等待最后的爆发。
光绪五年即1879年农历闰三月二十八日,年过半百而应邀游历日本的王韬,在东京见到了中国驻日使馆参赞、刚过而立之年的黄遵宪。年龄相差二十岁的两人随即结为忘年之交。他们的会见或许可以作为一种象征性事件,表明“诗界革命”论的发生进程的延伸轨迹。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县)人。他年幼时就富有诗才,同王韬既有相同处更有不同处。相同处在于,置身于中国历史的巨变时刻,作为渴望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和个人命运忧心忡忡;而不同处在于,王韬由于其“私通”太平军而被放逐的缘故,一生只能在清朝体制外或者体制边缘发挥启蒙作用;而黄遵宪作为朝廷命官,却可以在体制内扮演改良者角色。黄遵宪到日本才一年多就能与王韬一见如故,其原因不难理解:这位不满中国现状、素有远大报国志向和开放心态的年轻外交官,正是在驻日期间(1877-1882)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性体验,逐渐产生了自己的维新变法思想。他初到日本时,受一些“旧学家”的“微言刺讥”、“咨嗟太息”的影响,对明治维新还持不解与反对态度,后来见识多了,才逐渐发生根本性转变:“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并对自己过去在《日本杂事诗》中表露的保守态度颇感后悔,“颇悔少作”,“余滋愧矣”[9](下册,P1095)。他的《己亥杂诗》四七自注也说:“在日本时,与子峨星使言: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将此藏之石函,三十年后,其言必验。”[10](上卷,P158)他此时终于明确认识到“中国必变从西法”,“革故取新”。这确实是黄遵宪思想历程中的一个飞跃。
这种积极的变法思想显然与王韬在香港的努力在精神上是息息相通的。而从时间上判断,这种思想转变的完成,也显然与王韬对他的成功感染或启发密切相关。因为,一方面,作为体制内的渴望变法的年轻官员,黄遵宪正迫切希望能从外面找到一条稳妥而有效的变法改良道路;而另一方面,王韬这位处于体制外的变法论者,一直在渴求自己的主张被体制内当权者承认和接纳而不得,同时,也一直在盼望得到这个体制内的中心秩序的认可。这样,当王韬被拒之于国门外而浪迹天涯,好不容易得到日本友人的青睐而壮游扶桑、并且被作家和教育家中村敬宇(1832-1891)当作“百年来访日的最杰出中国人”加以盛情款待时[11](P80),他内心真正期望目睹这幕场景的人,恐怕还是自己国家体制内的当权者和同道。因为,只有他们的认可和接纳,他的报国壮志和一系列变法方略才有真正付诸实施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人会一拍即合了。一位体制内变法者和体制外变法者在东京实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见。王韬在香港为黄遵宪印行《日本杂事诗》时作序说:“余去岁闰三月,以养疴余闲,旅居江户,遂得识君于节署。嗣后联诗别墅,画壁旗亭,停车探忍冈之花,泛舟捉墨川之月,游屐追陪,殆无虚日。君与余相交虽新,而相知有素。三日不见,则折简来招。每酒酣耳热,谈天下事。……余每参一议,君亦为首肯。逮余将行,出示此书,读未终篇,击节者再,此必传之作也!”[10](上卷,P5)两人初次订交,谈得十分投机,友谊发展极快,每隔三两天即一会,酒酣耳热,赋诗联句,畅叙平生抱负,纵论天下大势,赴忍川观花,在墨川泛舟,激情满怀,难舍难分。王韬于阴历七月初六日离开日本,黄遵宪亲自送别。大约是在与王韬订交的第二年即1880年,黄遵宪就开始接触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著作,思想受到更剧烈的震动,心志为之一变。1881年,他在日本听到清政府撤回留美学生事,激愤地写下《罢美国留学生感赋》:“自从木兰狩,国势弱不支,环球六七雄,鹰立侧眼窥。应制台阁体,和声帖括诗,二三老臣谋,知难济倾危。欲为树人计,所当师四夷”[10](上卷,P103)在这里,他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新的“环球”视野中的“师四夷”主张,显示了全球化境遇中师法西方而从事现代性建设的决心。这些无疑有助于理解王韬与黄遵宪之间在“诗界革命”问题上的一种前后传承关系。可以说,黄遵宪的诗论革新思想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应同王韬的感召和启发相关,而作为其共同支撑的正是他们共同的“地球合一”体验和“奇境幻遇”视野。
四、黄遵宪:“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
黄遵宪一生著诗不少,除散逸的外,集辑的有诗集《人境庐诗草》11卷640首,《人境庐集外诗辑》(含《人境庐集外诗辑补遗》12首)280首,《日本杂事诗》2卷200首,共计1120首[12](P260)。在这一千余首诗中,他自认成就最大的是五古诗。他自称“五古诗凌跨千古。若七古诗不过比白香山、吴梅村略高一筹,犹未出杜、韩范围”[9](上册,P10)。这也与一些诗人对他的评价合拍。俞明震说:“公诗七古沉博绝丽,然尚是古人门径。五古具汉魏人神髓,生出汪洋恢诡之情,是能于杜、韩外别创一绝大局面者。”[9](上册,P10)何藻翔说:“五古奥衍盘礴,深得汉魏人神髓。律诗纯以古诗为之,其瘦峭处,时类杜老入夔州后诸作。”[9](上册,P10)温仲和说:“五古渊源从汉魏乐府而来,其言情似杜,其状景似韩。”[9](上册,P10)丘逢甲说:“四卷后七古乃美而大;七绝大矣,而未尽化也。已大而化,其五古乎!七律乎!”[9](上册,P10)但这里不打算专门讨论他在诗歌创作上的美学成就,而主要是想简要把握他在诗歌美学上的革新要点如何推进了“诗界革命”论的形成。诗歌语言的现代性或汉语的现代性,是黄遵宪的诗歌创作探索的重大问题,尽管他并没有使用这样的字眼。他所希望的新的诗歌语言,是那种能直接抒写今人的生存体验的语言。在这里,他做出了王韬所没有做的两方面新贡献:一是俗语,即语言的俗化;二是新语,即新词语。
他长期致力于诗歌语言的俗化。也就是说,在他这里,语言俗化是文学现代性进程的一个基本层面。在21岁时写的《杂感》诗中,就喊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口号。他对直接抒写“我口”充满自信:“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10](上卷,P75)。“流俗语”也就是俗语。而他青年时代的这一思想,在后来又获得了升华:他深切地认识到整个民族的语言的雅化弊端,并对其俗化方向发出热烈呼唤。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他认为汉语书面语与口语严重脱节。“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10](下卷,P1420)。他总结古代文体发展演变的历史,主张创造一种“明白晓畅,务期达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新文体。明白而达意、适今而通俗,显然成为是他的语言现代性理想。他称赞日本文字简便易学,“闾里小民,贾竖小工,逮于妇姑慰问,男女赠答,人人优为之”。中国文字也应当出现新字体,“愈趋于简,愈趋于便”。他的汉语言现代性的目标是:“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10](下卷,P1420)。显然,在他看来,汉语的通俗化是诗歌语言革新、乃至整个文学语言革新的一个基本方向。确实,他自小就受到家乡民歌熏陶,这影响一直伴随着他。在喊出“我手写我口”的第二年,他自己就身体力行,写了以“山歌”为题的九首诗。其中说:“买梨莫买蜂咬梨,心中有病没人知。因为分梨故亲切,谁知亲切转伤离”[10](上卷,P76)。他巧妙地利用同音字取得一语双关的效果,而同时又通俗易懂,显示了汉语通俗化追求。他青年时代还写了富于山歌风味的《新嫁娘诗》51首,刻画出少女出嫁前的微妙心态。他对民歌语言的借鉴是与对“白话”的运用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民歌语言和白话其实都具有俗语特征。如《五禽言》:“泥滑滑!泥滑滑!北风多雨雪,十步九倾跌。前日一翼剪,明日一臂折。阿谁肯护持?举足动牵掣。仰天欲哀鸣,口噤不敢说。回头语故雌,恐难复相活,泥滑滑!”[10](上卷,P170)浅显的口语生动地传达出深刻的寓意。
如果说,语言俗化是为了适应最广大的各阶层读者的沟通需要,那么,语言的新颖则是要适应表现新的现代性体验的要求。求“俗”,是要竭力适应现代性社会动员;而求“新”,则是要满足现代性新变化。这两方面都服从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迫切需求。以新词语入诗,构成黄遵宪诗学的另一追求。他以其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文化阅历,接触过不少新名词、新语句,并在诗中大胆引用,如气球、地球、赤道、十字架、世纪和握手等现代新词语[13](P399-401)。在后来的变法运动中,黄遵宪更明确地标举“新派诗”:“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②
作为清末民初文学界的一个重要人物,黄遵宪由于以俗语和新语句大写“新派诗”,而在“诗界革命”方面赢得赞誉。但在我看来,他的意义却绝不仅仅在于诗歌语言革新上。应当看到,他的诗歌语言革新在当时还是有限的,不是寻求诗歌“形式”(语言)的革命而只是谋求诗歌“精神”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当然只是有限的改良而已,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界革命”。在黄遵宪那里,俗语和新语的运用只是达成有限的修补而已,而并没有导致整个诗歌文体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有限的诗歌改良?这是因为,黄遵宪所思所念的根本方面不是诗歌语言或形式的革命,这样的革命要等到“五四”时期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闯将才能真正提出来并付诸实践;而只是诗歌语言或形式以外的事。我们与其惋惜或责备他在诗歌美学上过于保守,不如认真地对待他所思虑的远为重要而急迫的事。这一点与王韬的影响可能不无关系,因为王韬的用力处也非语言,而只是“奇境幻遇”。
黄遵宪眼中的更为重要而急迫的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全力抒写当时中国的“人”和“事”。他在1891年夏撰写的《人境庐诗草·自序》中,全面地提出了这一诗歌美学主张:“士生古人之后,古人之诗号专门名家者,无虑百数十家,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诚戛戛乎其难。虽然,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10](上卷,P68-69)这里明确提出了“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及“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的诗学主张。
这两处说法的共同点在于指出,诗歌最重要的是要写“异于古”的“人”和“事”。这可以说是王韬的“奇境幻遇”说的进一步发展。黄遵宪所主张的“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按我的理解,“人”就是指“今人”,即置身于现代性巨变时刻的中国人,具体地说,既指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中国人,也指作为独立个体的中国人;这“事”,正是指“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也即“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和“耳目所历”,也就是中国人所遭遇的数千年未有之大事变,中国人的现代性生存境遇。
黄遵宪还在《致周郎山函》里指出:“遵宪窃谓诗之兴,自古至今,而其变极尽矣。虽有奇才异能英伟之士,率意远思,无有能出其范围者。虽然,诗固无古今也,苟天地、日月、星辰、风云、雷雨、草木、禽鱼之日出其态以尝(当)我者,不穷也。悲、忧、喜、欣、戚、思念、无聊、不平之出于人心者,无尽也。治乱、兴亡、聚散、离合、生死、贫贱、富贵之出而我者,不同也。苟即能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10]](上卷,P291)他强调把个人在大变动时代的“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都“笔之于诗”。这里的身遇、目见、耳闻,同前面所谓“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及“耳目所历”,是一样的,都强调“诗中有人,诗外有事”,即“异于古”的人和事。
尽管黄遵宪诗歌的主要用力处在于表现“异于古”的人和事,这同王韬一脉相承;但毕竟他不限于此,还非同一般地重视语言俗化和新词语运用并在诗歌中实践(尽管这种实践还很稚嫩),从而比王韬前进了一大步,并客观上为梁启超后来的“新意境”、“新语句”和“古风格”三者融合的“诗界革命”论铺平了道路。之所以只是客观上为“革命”“铺平了道路”而本身并没有自觉地走向“革命”,实在是由于他“有作为诗人长期的写作实践和对诗歌艺术规律的深入认识,对诗歌传统的弊端和对诗歌革新的方向比一般人认识得更透彻,也更尊重文化和诗歌创作的规律”[14](P47-48)。这样,难怪黄遵宪本人只是有限度地标举“别创诗界”论,别出心裁地运用俗语和新词语而在旧文体中开创新的诗歌风貌。他诚然希望诗人以“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10](上卷,P440),诚然有梁启超及其他同代人大力推崇,但却并没有进展到直接标举或赞同“诗界革命”的地步,可见他对这种“革命”是有保留的。
五、梁启超:新意境、新语句和古风格
梁启超(1873-1929)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海外时,急切地谋划“诗界革命”的。这一“革命”论的正式提出是在《夏威夷游记》(1899年11月)中:“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他呼唤中国“诗界之哥仑布”的诞生,其实质就是参酌“欧洲之精神思想”而推动“诗界革命”:“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他为“诗界革命”制定了三条美学标准:“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2](第3集,P1826)“诗界革命”在这里属于一种两“新”一“古”的奇特糅合物。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古风格”如何与“新意境”和“新语句”形成匹配。“风格”,如果理解为特定语言和文体在表意中形成的独特个性,那么就应当与语言和文体密不可分,并且终究要通过语言和文体表现出来。这样看,要追求“新意境”和“新语句”就必然要追求“新风格”而非“古风格”。但梁启超只让“意境”和“语句”求新而让“风格”守旧,这确实是一桩彼此不匹配的姻缘。这表明,梁启超本人就面临一种分裂的诗学境遇,就好比双脚跨进了新时代但头脑还留在旧时代一样。
梁启超在这里提出了怎样才能产生“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的问题。在他看来,“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2](第3集,P1827)。他还在《饮冰室诗话》里指出:“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2](第6集,P3791)当然,在梁启超看来,不能“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而是要“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这就是说,只有当“新语句”与“旧风格”结合起来,成功地表现出饱含“新理想”的“新意境”时,“诗界革命”才可“举革命之实”[2](第6集,P3817)。这就对“诗界革命”作了完整的美学规定。了解这个规定,才可以理解梁启超在黄遵宪的众多诗歌中何以最推崇组诗《今别离》四首了。《今别离》作于1890至1891年诗人任驻英使馆参赞期间。梁启超继“同光体”诗人陈三立(陈伯严)之后,盛赞这组诗为“千年绝作”:“黄公度集中名篇不少,至其《今别离》四章,度曾读黄集者无不首记诵之。陈伯严推为千年绝作,殆公论矣。余响者每章能举其数联,顾迄不能全体成诵,愤恨无任。季廉不知从何处得其副本,写以见寄,开缄默不知其距跃三百也。亟为流通之于人间世,吾以是因缘,以是功德,冀生诗界天国。……要之,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吾尝推公度、穗卿、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闳远也。”[2](第6集,P3802-3803)这里的夏穗卿即夏曾佑(1863-1924),观云即蒋智由(1866-1929)。梁启超基于什么具体理由推崇这组诗?可以说,正是由于认定它以“新语句”和“旧风格”而成功地开拓了“新意境”,表现了个人的全新的全球性体验。显然,梁启超格外推崇黄遵宪,恰恰是由于认定后者符合他确定的上述三条美学标准。就是否符合梁启超的“诗界革命”的三条美学标准来说,黄遵宪确实当之无愧。但是,“诗界革命”论本身如果仅仅依据这三条标准,确实又是残缺的和内在不和谐的,因而结果必然是声势大而实绩小。
六、结语
“诗界革命”论作为全球化东扩中的一种本土诗学投影,其发生是一个渐进过程。王韬从“地球合一”说出发率先开辟全球性“奇境幻遇”,先后预示了黄遵宪的“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和梁启超的“新意境”,但遗留下语言和风格问题存而未论。继起的黄遵宪兼顾书写异古之人事和语言的俗化及新词语运用,为“诗界革命”作了进一步准备。到了梁启超,“诗界革命”及其三条标准的提出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他的独特建树在于,以政治家的敏锐触角,从黄遵宪等的诗歌革新实践中认识到诗界走向“革命”的必然性并实际吹响这一号角。他的“诗界革命”的初衷在于通过诗歌的开创性变革而唤醒知识分子的以欧洲为范本的普世的社会变革渴望,但客观上发起了全球化东扩中的一场本土诗学动员,让此前较为隐晦的全球化东扩的诗学维度转而以豁然鲜明的姿态亮相。今天重溯这一渐进过程,不仅并未减弱梁启超发起“诗界革命”的历史作用,相反倒是让这一“革命”论的历史链条及其全球化东扩渊源更加完整和清晰地显示出来。正是通过显示这种历史链条及其渊源,我们得以更清晰地见出,“诗界革命”论无意识地成为全球化东扩的一种本土诗学工具,这就是说它无意识中以汉语诗歌革命的方式为全球化在中国的东扩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种作用实际上宛如一柄双刃剑:一面通过刺向现代汉诗与古典传统诗歌母体相连的脐带,而成为它走向与这种本土传统诗歌母体断裂的开放时代的预示(这到胡适《尝试集》终于成为现实);另一面则刺向它稚嫩的身躯本身,表明以传统格律体而尝试表现现代生活体验必然遭遇美学困境。于是,“诗界革命”论作为全球化东扩的本土诗学投影具有双重作用:一面是诱人追求的幻影,另一面则是令人烦忧的阴影。
[收稿日期]2007-10-26
注释:
①王韬:《呈严驭涛中瀚师》,转引自忻平著《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3页。
②梁启超《酬曾重伯编修》,收录于《人境庐诗草》卷8,转引自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