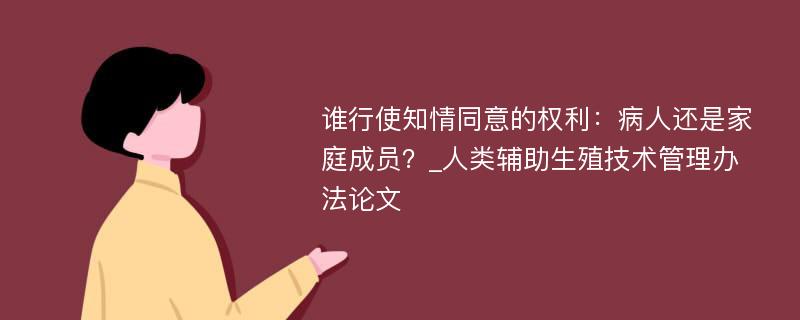
由谁来行使知情同意的权利:患者还是家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属论文,由谁来论文,患者论文,权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297(2007)01-0029-06
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意味着患者有权被告知本人的病情以及与医务人员拟采取的医疗措施相关的信息,并且有权基于所知悉的信息接受或者拒绝该医疗措施。相对应地,这意味着医务人员在采取医疗措施之前必须向患者告知相关信息并取得患者的同意。早在1982年卫生部所颁布的《医院工作制度》中,我国确立了签署手术同意书制度;① 此后,1994年国务院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② 及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细则》③、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执业医师法》④、2000年卫生部的《临床输血技术规范》⑤、2001年卫生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⑥、2002年国务院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⑦、2005年卫生部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处方管理规定》⑧ 以及2006年卫生部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⑨ 都相继对“知情同意”作出规定,从而使得该项权利获得法律的认可和保护。
然而,在我国目前的医疗实务中,“有同意能力”⑩ 的患者及其家属都能够行使知情同意的权利(11),在有些地区甚至认为患者本人的同意是无效的(12),而强调必须由患者家属来签署手术同意书(13)。医疗实务中为何存在这种做法?知情同意的权利原则上应该由谁来行使?患者家属在何种情形下能够行使该项权利?这些问题都有待法学界和医学界的回答。本文先行考察现行法的态度,接着将从正反两方面分析由家属替代行使知情同意权的理由,来探讨知情同意权的行使主体问题(14),并且最后得出笔者的结论。
现行法是讨论“知情同意”这项法律权利的出发点。(15)
上文已经提到了对知情同意权作出规定的主要现行法律;而就患者有同意能力的情形下该项权利应由谁来行使的问题,上述法律缺少统一的表述。考察各部法律的具体规定,大致有五种立法态度(请注意各部法律的制定机构和颁布时间,这将影响到法律的效力等级和立法态度的大致走向):
第一种立法态度,“仅患者家属(16) 或单位得行使知情同意的权利”,这是1982年卫生部的《医院工作制度》所作的规定。
第二种立法态度,“由患者和家属或关系人共同行使知情同意的权利”,这是1994年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
第三种立法态度,“由患者或者家属行使知情同意的权利”,这是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执业医师法》和2000年卫生部的《临床输血技术规范》所采的态度。
第四种立法态度,“仅患者得行使知情同意的权利”,1994年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02年国务院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2005年卫生部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处方管理规定》和2006年《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17) 则作这样的规定。
第五种立法态度,对知情同意权的行使主体未作规定,即2001年卫生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虽然各部法律的规定各异,但是依据法律效力等级的相关规则,仍然有解释的余地。根据《立法法》的有关条文(18),高阶位的法律效力优于低阶位的法律,同价位的法律之间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因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即在法理上而言,有同意能力的患者或者其家属均可行使知情同意权。
当然,从法律颁布的时间先后看,立法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从“仅患者家属或单位得行使权利”——“由患者和家属共同行使权利”——“由患者或家属行使权利”——“仅患者得行使权利”的变迁。此外,上述的归类也显示了“卫生部”行政规章的立法态度几经变化,即先后作出了第一种、第三种、第四种的规定;而“国务院”行政法规也经历了从第二种到第四种立法态度的转变。从法条本身很难了解这其中的原委。但是,相信法律规定的这些变化不应该只是立法机构对文字纯属偶然的选择,它们至少反映了立法机构对“由谁来行使知情同意的权利”这个问题经历了不同的认识阶段,并且透露出立法态度的一定走向:逐步强调患者本人的知情同意权、而淡化家属或单位的涉入(尽管这只是一种观察的视角,在法理上没有说服力)。
在绝大多数确定知情同意制度的法域中,有同意能力的患者均系由本人行使知情同意的权利,家属无权共同行使、更不用说取代患者来行使该项权利。(19) 而在我国,无论是法律抑或医疗实务,都认可家属替代行使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这样的规定和做法有其存在的背景或理由,并为相当数量的人群(包括部分医务人员)所支持。
最经常被援用的是基于文化的理由:我国传统上侧重家庭的儒家文化、淡视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为保护患者而对其保密病情的医学传统做法,为家属替代患者而行使知情同意权的做法提供了正当性。乍一看来,这种理由具有不证自明的说服力;谁能够否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即使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在论证的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将此作为论据。但是若继续深究下去,却仍有商榷的余地。首先,所谓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医学传统做法,都只是泛泛之言,很少有学者进行细致地考证或实证研究。对于其内容存在误读的可能;(20) 对于其所适用的时代、所适用的地域以及所适用的人群都没能作必要的说明,对于这些文化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起着所预期的作用缺少基本的探讨。实际上,它至多提出一种解释的视角,而尚不足以成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其次,将中国文化简单地贴上“儒家文化”、“集体主义”的标签,并将东方文化绝对地对立于西方文化的做法本身,就显得过于武断。中国文化自古处于不断的融合和变更中,而当前处于全球化影响下、信息丰富的中国社会更充满了多元的文化冲击和选择,自我意识、人权观念、思辨精神都流露在当下社会的诸多场合。因此,用几个含义模糊的术语来概括所谓的中国文化并不是严谨的做法;相反,针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进行微观的描述,可能要比笼统的概括有意义得多。再次,即使上述对于中国文化的描述是准确的,也不必然得出“应当由家属替代患者行使知情同意权”的结论。只有基于知情同意制度的伦理精神和规范意义,考察其与中国相关文化特征的相容性和相斥性,才可能获得有价值的结论。
第二种被时常援用的理由则是,向患者披露信息将不利于疾病的治疗,尤其是对身患绝症的患者而言。对某些心理脆弱、情绪不稳定的患者而言,向其如实全面地告知病情,可能对其健康产生负面作用,并且妨碍治疗的效果,严重地还可能导致患者采取自残、自杀的过激行为。(21) 因此,基于“不伤害患者”(Do no harm)这项最基本的医学伦理原则,在特定情形下,医生有权不向患者披露相关信息,以免对患者造成伤害。在普通法中,医生的这项权利被称为“治疗豁免”(Therapeutic privilege),它构成知情同意权的一项例外。
然而,笔者认为,这毕竟只是一项例外情形,其所依据的原理尚不足以推翻“原则上由患者本人来行使知情同意权”这项一般性的原则。首先,我国的医务人员已经就“知情同意对各种病症之患者的实际影响”展开了临床实证的对比研究,(22) 其中包括患者情绪障碍、术前焦虑、术后康复、医疗依从性等指标。而大多数的研究表明,向患者本人告知信息对患者产生了正面的作用。可见,认为向患者披露信息将不利于疾病治疗的一般性观点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其次,普通法上所指的“治疗豁免”,仅仅针对的是具体个案中的某位“特定”患者。法院在适用这项例外时,需要主观地衡量该患者的个人因素和病情的性质、严重程度,来具体判断在个案中医生是否有权援用“治疗豁免”这项例外。笼统地将其适用于“所有”潜在的患者,并以此为由剥夺患者本人行使知情同意的权利,不仅无法实现这项例外的良好初衷,而且会成为规避适用知情同意制度的借口,从而使得该项制度的根本目的完全落空。再次,普通法对待“治疗豁免”采用了极为谨慎的态度。正是因为“治疗豁免”概念本身具有过大的弹性,普通法对医生援用“治疗豁免”的条件、不予披露的信息范围、替代决定的标准等进行严格地阐释,尽量缩限适用该项例外,以防止其被滥用。(23) 此外,在考虑是否行使“治疗豁免”的时候,还需要考量不向患者告知信息而可能产生的危害;换句话说,只有当告知的危害超过不告知的危害时,才具有援用该项例外的正当性。由此可见,第二种理由并不具有说服力。
第三种理由则认为,有很多患者虽然具备同意的能力,但缺少一定的文化素质和理解能力,即使医生向其告知信息,他们也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比如那些来自农村的、年老的或者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患者。事实上,医生告知的信息中难免涉及诸多医学专门的知识和术语,对任何非学医的外行而言,要准确充分地理解这些信息,都不是简单的事情。然而,从患者对信息难以理解的事实,很难得出“由患者家属替代行使知情同意权”的结论,更何况在实务中,家属的理解能力并不见得会超过患者。其实,要改善这种状况还有赖于医生,即要求医生在告知信息的时候,尽量使用容易理解的表述并辅以必要的解释,例如医学界的《履行知情同意原则的指导意见》(24) 第2条第5项就规定:“对病人的告知,应尽可能将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此外,医生在告知信息时,还可以邀请家属到场帮助患者来理解相关的信息。实际上,在其他法域也存在“患者难以充分理解信息”的问题,但是却没有一个法域基于这项理由而剥夺患者本人行使知情同意的权利。
笔者认为,我国法律(25) 认可家属替代患者行使知情同意权、医疗实务中甚至要求必须由家属行使知情同意权的做法,其实另有潜在的现实原因。1982年《医院工作制度》规定“实行手术前必须由病员家属或单位签字同意”,卫生部作这样的规定是与当时我国实行公费医疗制度的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公费医疗的经费是由国家和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拨款,一般按照人头划拨到各单位(包括各级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高等学校、军队等)包干使用。患者手术前由所在单位签字同意,意味着手术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已经单位批准,从而避免发生事后单位不同意支付相关费用的风险。同样,要求患者签署手术同意书的做法,也部分出于医疗费用的考虑,因为不享有公费医疗待遇的患者所需的医疗费用一般是由家属予以支付,医疗机构往往将家属的签署视为其付款义务的证据,从而在事后可能就医疗费用发生的纠纷中获得有利的地位。尽管1993年我国正式进行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结束了由单位直接为职工支付医疗费用的做法(即单位不再为职工签署手术同意书),但是这种保障家属支付患者医疗费用的初衷仍然是医疗机构要求家属行使知情同意权的潜在动机。然而,手术同意书在法律意义上并不具有医疗合同的性质,(26) 因此,医疗机构不能基于经家属签字的手术同意书而主张家属系医疗合同的当事人,从而要求其承担支付医疗费用的义务。
另外,在实务中,医疗机构之所以强调由家属行使知情同意权还出于这样的顾虑:一旦发生医疗风险,即使医生已经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但是患者的家属却可能以其不知道相关的信息且未表示同意为由,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责任。(27) 尽管按照现行法,家属的这种主张无法获得法院的支持,但是遭遇这样的诉讼仍然会使医疗机构的名誉和资源遭受相当的损害。因此,医疗机构将家属的知情同意视为防止缠讼的对策。笔者当然能够理解医疗机构的这种初衷;但是,这并不能作为“由家属替代患者行使知情同意权”的正当理由。为防止被家属缠讼的风险,医疗机构可以在采取医疗措施前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同时,要求其家属作为证人在同意书上签署。例如英国、香港等地的医疗机构为鼓励家属的参与和合作,就建议家属见证患者行使知情同意权的过程,并在同意书上作相应的签署;尽管家属的参与在法律上并没有特别的效力,除了其由此获得证人的资格。家属这种“非行使法律权利”意义上的参与就能减少医疗机构被缠讼的风险,而同时并不剥夺患者行使知情同意的权利。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由家属替代患者行使知情同意权”的观点所依据的理由都缺少说服力。相反,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从知情同意的伦理基础和制度目的、患者最佳利益的确定、患者与家属存在利益冲突的可能、患者隐私权的保护等角度,来论证“应该由有同意能力的患者本人来行使知情同意权”的主张。
知情同意制度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伦理基础在于对患者自主决定权(the patient' s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的尊重。约翰·密尔(John S.Mill)就曾在《论自由》写道:“对他本身的身体及精神,其个人乃是主权者”;而被无数次引用的经典论述则出自卡多佐法官(Cardozo J.)在Scholoendorff v.Society of New York Hospital(1914)(28) 一案中所作的判决:“已达到成年且具有健全心智的任何人,对自己身体享有决定作任何事的权利”。按照普通法上知情同意的一般原则,对于一位有同意能力的患者而言,即使其所作的决定不合常理,甚至将对其健康产生致命的伤害,患者的自主决定权仍然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未经患者的知情同意而对其采取医疗措施的医生将构成对患者的人身侵犯,无论该医疗措施是否有利于患者的健康。(29) 因此,只有患者有权对自己的身体行使自治权(autonomy),其他任何人(包括患者家属、患者所在单位、医生、医疗机构乃至国家)都没有权利行使该项权利。对有同意能力的患者而言,他所享有的知情同意权不容任何人替代或剥夺。(30)
患者的“自主决定权”有时也被表述为“自主选择权”(the right to autonomic choice)。笔者认为,此处的“选择”虽然包括对利益的选择,但更强调对“风险”的选择。最安全的医疗措施都无法避免地具有一定的风险。当患者对某项医疗措施作出知情同意的表示后,这就意味着该医疗措施的正常风险将由患者本人予以承担。如果事后不幸发生该风险范围内的负面后果,患者则无权请求医生或医疗机构承担责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知情同意制度还涉及“医疗风险的事前分配”问题。同样,能否承受该风险带来的伤害和痛楚、是否承担某项风险、是否接受某项医疗措施,都应该由患者本人进行选择。对有同意能力的患者而言,其家属“越俎代庖”行使知情同意权,将有悖于知情同意最根本的伦理基础和制度目的。
如果分别让家属和患者本人行使知情同意权,那么谁最了解患者的最佳利益呢?选择医疗措施,并不纯粹是医学的问题(即哪种方案更利于患者的健康);抉择的过程还会涉及患者个性、伦理观念等其他个人因素。而且,在医疗实务中经常碰到的难题是,每个备选医疗措施都各有利弊且彼此排斥,这就进一步增加选择的难度。一般而言,每个人自身最了解自己的偏好,最能把握自己的最佳利益。尽管家属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患者,但是在医疗实务中也经常出现家属的选择并不符合患者的利益,或者不符合患者意愿的情形。例如,患者李某因阴道流血一月余入住妇科。入院后确诊为子宫肌瘤、子宫颈Ⅲ度糜烂(宫颈涂片有细胞核质变)。医生决定进行子宫全切除术,并由患者丈夫签署了手术同意书。但是,切除子宫是否符合患者的意愿或利益呢?在另一个案件中,患者是一位被确诊患乳腺癌的女模特。医生列出了切除乳腺包块和全切乳房及周围组织的两种方案(两者的术后转移风险和五年存活率不同)。患者的丈夫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并签署了手术同意书。事后患者认为选择第二个方案根本不符合她的利益,并因此引发一场医患纠纷。
更为严重的是,家属在替代患者行使知情同意权的时候,有时并不以患者的利益为重;在有些情形下,患者的利益与家属的利益还可能发生冲突。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案件,某院产科一位产妇在分娩过程中,发生了第二产程延长和胎儿宫内窘迫。但是,她的丈夫和婆婆为了让孩子出生在选定的吉祥日而拒绝签署剖腹产的手术同意书。此外,在医疗实务中,部分家属往往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行使知情同意权,拒绝对患者采取某项有益的医疗措施,或者选择另一项费用较低但效果较少的治疗方案;而《履行知情同意原则的指导意见》第5条第5项对这个问题也作了相应的规定。(31) 由此可见,家属替代患者行使知情同意权,对患者利益的保护存在着较大的风险。
最后,由患者家属替代行使知情同意的权利,可能与患者隐私权的保护发生冲突。医生获知的有关患者的信息(比如病史、病情、后遗症等),可能涉及患者的隐私,因此在医患关系中,医生承担着保密的义务。但是,家属替代行使知情同意时,医生必须告知相关的信息,以等待家属作出决定。这样,医生在向家属告知信息的时候,就会侵犯患者的隐私权。例如,被确诊患性病的患者,不希望将病情告知给其父母或其子女;未婚先孕的女子不希望让父母或其他家属知悉这一事实;曾染上肝炎但已治愈的患者不愿意将自己的病史告诉给配偶等等。由患者家属替代行使知情同意权的规则,显然会使医生处于两难的境地:要么违反知情同意的规定,要么侵犯患者的隐私权。而在规定“由患者本人行使知情同意权”的法域,就不会产生类似的问题。
综上所述,对于有同意能力的患者而言,法律应该明确地规定:必须由患者本人来行使知情同意的权利。换句话说,有同意能力的患者所作的同意表示才具有知情同意的法律效力。当然,在患者认可的前提下,医生也可以向家属告知相关信息,让家属参与患者行使知情同意权的过程,但这种参与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如果患者具备同意能力,但在特定情形下无法亲自签署知情同意书,那么患者家属也可以“行为辅助人”的身份,代替患者予以签署。
不过,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家属也有权替代行使知情同意权,这主要包括三种情形:(1)有同意能力的患者明确委托某一家属代理行使知情同意权;(2)当向患者告知相关信息将会对其造成伤害(即在医生得以援用“治疗豁免”的情形)时,家属有权替代行使知情同意的权利;(3)当患者不具有同意能力(包括永久的和暂时的丧失同意能力)时,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特定家属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行使知情同意权。如何确定这三种例外情形的具体法律规则,则留待今后予以探讨。
注释:
①《医院工作制度》第40条附则(施行手术的几项规则)第6项:“实行手术前必须由病员家属或单位签字同意(体表手术可以不签字),紧急手术来不及征求家属或机关同意时,可由主治医师签字,经科主任或院长、业务副院长批准执行。”
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62条:“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的知情权利。在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时,应当向患者作必要的解释。因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不宜向患者说明情况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患者家属。”
④《执业医师法》第26条:“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者其家属介绍病情,但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医师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应当经医院批准并征得患者本人或者其家属同意。”
⑤《临床输血技术规范》第6条:“决定输血治疗前,经治医师应向患者或其家属说明输同种异体血的不良反应和经血传播疾病的可能性,征得患者或家属的同意,并在《输血治疗同意书》上签字。《输血治疗同意书》入病历。无家属签字的无自主意识患者的紧急输血,应报医院职能部门或主管领导同意、备案,并记入病历。”
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14条:“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当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涉及伦理问题的,应当提交医学伦理委员会讨论。”
⑦《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1条:“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
⑧《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处方管理规定》第3条:“具有处方权的医师在为患者首次开具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时,应当亲自诊查患者,为其建立相应的病历,留存患者身份证明复印件,要求其签署《知情同意书》。病历由医疗机构保管。”
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第24条:“实施人体器官移植前,医疗机构应当向患者和其家属告知手术目的、手术风险、术后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预防措施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第27条第2款:“医疗机构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必须经捐赠者书面同意”;第30条:“医疗机构在摘取活体器官捐赠者所同意捐赠的器官前,应当充分告知捐赠者及其家属摘取器官手术风险、术后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预防措施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第34条:“医疗机构开展试验性人体器官移植应当履行告知义务,征得患者本人和其家属书面同意”。
⑩具有同意能力是指患者能够理解医疗措施的本质、目的、风险等相关信息的能力,它构成患者有效行使知情同意的条件之一。
(11)比如,由丈夫签署妻子剖腹产手术的同意书,见“杨丹与达州市妇幼保健院医疗事故赔偿纠纷案”(2000)达民初字第62号。
(12)高永平、王莲花、杨宣.“知情同意在临床实践中的问题与对策”.《河北职工医学院学报》,2004,21(3):66
(13)张英涛、孙福川.“论知情同意的中国本土化——中国文化视野中的知情同意走向”.《医学与哲学》,2004,25(9):13
(14)需要说明的是,此处讨论的是知情同意权的“行使主体”问题,而非该项权利的“归属”问题。本文认为,知情同意的权利始终是由患者所享有的,无论是由患者本人来予以行使,还是由家属或其他主体代为行使。
(15)司法判例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现行法的态度,但从严格意义而言,判例没有法律约束力。
(16)就家属的范围,法律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第12条则对“近亲属”的范围作了界定,即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外)祖父母、(外)孙子女。虽然“家属”的概念不等同于“近亲属”,但仍可作参考。
(17)《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第34条要求在进行试验性人体器官移植时应当同时取得患者和家属的书面同意,有其特殊的立法原因。基于试验性人体器官移植所潜在的高度风险,法律要求采取比一般的知情同意更为谨慎的态度。
(18)见《立法法》第79条、第83条。
(19)“有同意能力的患者自行行使知情同意的权利”是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等普通法国家不言自明的规则。虽然这些法域的医疗实务并不排除家属在“非行使法律权利”意义上的参与。
(20)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并非自古以来就存在为保护患者而对其保密病情的做法,参见聂精保:“知情同意在中国不适用吗?——‘文化差异论’的认知错误”.《医学与哲学》,2002,23(6):20
(21)比如,患者在得知自己的癌症病情恶化后,精神崩溃,两天后自杀身亡,参见胡硕、贺达仁、胡成平.“浅谈患者及其亲属知情同意与医生的责任”.《医学与哲学》,2003,24(1):14
(22)参见方渭清、林刃舆、李智渊:“喉癌患者知情同意后情绪障碍与应对方式的初步研究”.《浙江临床医学》,2005,7(4):338-339;曹新妹、毕翠云、陆中霞、陆萍、郑慧芳、朱学勤.“运用知情同意干预改善精神分裂症康复期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上海精神医学》,2004,16(4):237-239;黄佐、赵君、吴宗贵.“知情同意签字对冠状动脉造影患者焦虑情绪的影响”.《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1,29(3):152-154;朱祥悌、田西奎、吕德云.“知情同意签字对植入人工心脏起搏器患者焦虑的影响”.《中原医刊》,2004,31(19):8-9。但是另有研究表明详细的手术告知能使胆囊切除患者的焦虑程度增加,不利于术后身体的恢复,参见李小珍、何海萍:“手术知情同意签字对胆囊切除患者术前焦虑和术后康复的影响”.《中国临床康复》,2004,8(17):3366-3368
(23)而有些学者,基于“治疗特免”这些例外的潜在风险,甚至提出了废除该项例外的建议,参见Simpson,R.“Informed consent:from disclosure to patient participation in medical decisionmaking”.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1981,76:172-207
(24)《履行知情同意的指导意见》属于医学界的伦理规范文件,见《医学与哲学》,2004,25(9):5-8
(25)参见第一部分。
(26)它只是用来证明患者本人与医疗机构之间存在医疗合同的证据。
(27)就实务中的这种案例,可参见曾德春、官德容、雷正元.“特殊医疗活动知情同意书签字权的归属探讨”.《护理研究》,2004,18(11):1970
(28)Schlendorff v.Society of New York Hospital( 1914) 211 N.Y.125,126.
(29)参见,Re MB[1997]2 F.L.R.624.
(30)尽管我国法律没有对知情同意权的内涵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民事权利能力”、“代理”以及“权利不容侵犯”的相关规定,在本质上都出于对民事权利主体于财产或人身方面之自主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31)同前注24引书第8页。
标签: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论文;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法律论文; 医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