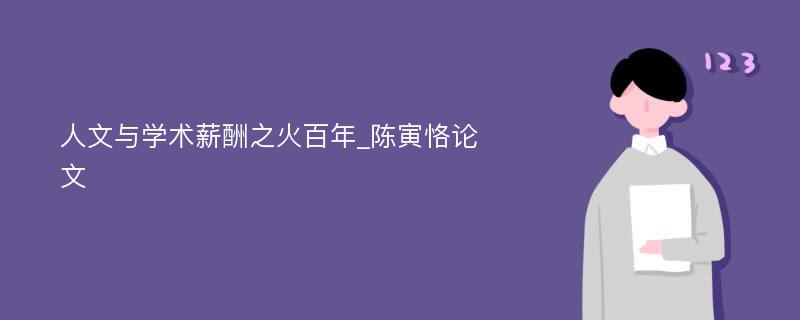
人文学术薪火的百年明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薪火论文,人文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已是1999年12月31日了。再过数小时,地平线上升起的,将是新世纪的太阳。在这辞旧迎新的千禧夜,先生想说些什么呢?
●记得某智者说过:20世纪的最后一夜与21世纪的第一个早晨并无什么不同。说得很机智,但这是就物理时间而言。物理学水平的时光流逝速率委实是均衡的,冰冷的,刻板的,对所有世纪皆一视同仁,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是也。但文化学水平的心理时间却是非均速、非机械的,它将在主体的情态体验场中被诗性地拉长(比如“度日如年”)或缩短(比如“光阴似箭”)。当溶于生命历程的时间刻度一旦被情感浸透,主体将顿悟“此时”的分量,以致从瞬间读出永恒。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一种刻骨的亲情之“思”,惹人“倍”感“节”日的非凡。故置身于千年一回的千禧夜,若比平时多一分世纪的反思,当是人情之常。而作为人文学者,我眼下最想说的,乃是重申:系统追溯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薪火的百年明灭,应是一个不无深意的话题。事实上,我用3年功夫,连续函谒安息于九泉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 吴宓、胡适、吴晗、闻一多、冯友兰及王瑶,而成即将付梓的新著《九谒先哲书》,就是想对上述话题说出我的思考。
○从《谒梁启超书》到《谒王瑶书》,先生的谒书篇幅越写越大,这是否意味着您对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传统(简称“学统”)的思考,是在写作过程中一步步地发酵、成熟的?
●我是从1997年开始系统思考“学统”命题的。1997年是我的本命年,48岁。我屈指一算,若能高寿如冯友兰活到95岁,也意味着我生命的一半已属于死神了。若我能健康地活到80岁,则生命留给我的时间也只剩30年了。这当是我今生今世可能拥有的最大财富,堪称“至尊至贵”。我随即自问:你将用这30年干什么?回答:仍做人文学术。为何非将一生献给学术不可?显然,作此抉择,亟待给出理由,方可安魂。这就是说,我必须对自己有个说法,弄清楚为何要当人文学者?若铁心直行此道,则应该怎样活,才无愧为一个纯正的人文学者?……这一连串悬念都必须“面对”,而“面对”的最佳方式,当是对话, 与那些在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史上留下世纪性的足迹的先哲对话, 亦即与他们的幽灵对话。很巧,我所选择的9位先哲,全有涉清华大学背景, 可谓是清华人文学科在民国期间的三代学人之代表: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代导师;第二代学人是闻一多、吴晗和冯友兰;王瑶属于第三代,40年代才正式涉足学界。通过甄别上述先哲烙在百年学术史上的纷沓足迹,可以或依稀或清晰地叠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传统即“学统”究竟是什么。亦即雄辩地告诫我: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学术?什么是人文学者必须做或不该做的?或何谓“有所为”,“如何为”与“不可为”?……当我写完《九谒先哲书》,我愿斗胆地说,我对自己所走的、并将继续走下去的路,确比以往明白多了。故完全可以说,我对“学统”的信念,委实是在写谒书过程中逐渐地清晰且坚定起来的。
○当先生论及20世纪中国学人在面对学术与政治关系时的价值迷失,几乎都把它归结为儒家政论文化已积淀为他们的价值的心理定势,这种沉潜到文化心理水平的剖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纵观清代“乾嘉学派”的学术人格裂变到本世纪末众多学人的价值取向,百年学术史实在留下了太多徘徊的、彷徨的“过渡学者”的身影,近乎“文化返祖”,能否说这正意味着是某种文化宿命呢?
●我确凿认定:中国文化传统先天便缺失一种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学统”之缺失,无疑是中国文化宿命之所在。我们今天在此言说“人文学者”一词,但传统辞典原本是不收“人文学者”这一条目的,古人大概更愿意称呼其为“书生”或“读书人”。而传统“读书人”之所以读书,其目的不是为了治学,更不是要为民族或人类的人文学术事业献身;读书仅仅是台阶,“学而优则仕”,旨在当官,又叫“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最高理想是能跻身朝廷而成宰辅,帮助皇帝治理朝政,横扫天下。其最高人格楷模是张良或诸葛亮。即使是“乾嘉学派”先驱顾炎武也沾此遗风。我认同现代“学统”胚胎最早是由“乾嘉学风”孕育的;但若仔细辨别,则其先驱顾炎武本身也颇自相矛盾:一方面《日知录》确实呈示出顾对严谨的科学思维的自觉追求,但同时他在骨子里又是瞧不起书生,瞧不起人文学术的。他说:“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人文学术作为异质于政论的精神创造,本无实践功用可言,这在有志于“反清复明”的壮士眼中,诚然无大价值。说白了,还是经世致用“值钱”。这个“钱”,当然不是意指货币,而是意指价值。顾炎武“以天下为己任”,不仅读万卷书,还行万里路。行万里路时,亦不像徐霞客在观赏大好河山之余倾心地理学研究,而往往用某种政治学乃至军事学的眼光去打量高山大川,发现哪儿地势险要,便设想不妨将此开辟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武装根据地。这也是一种选择,是政治或军事家的选择,顾无疑是把这种政治性活动,看得比闲暇时做学术更重要的。故当他嘲讽“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无非是说当他以政治家、军事家角色自期时,便不是“无足观”,而是“至高无上”了。所以我主张,在承认中国文化传统之悠久、深厚的同时,切勿忘记其致命的苍白或贫困。王国维早就明言,与古希腊文学、艺术、哲学相比,中国先秦在文学艺术、思辨学术层面的积累是相当薄的。陈寅恪于1918年在哈佛与吴宓曾有对话,也说中国文化传统有一种过分地讲究政治功利的倾向,而很少有人真正把文史之学、文哲之学之研究作为生命的第一要义来追求。记得王国维在本世纪初曾撰文《论近年之学术界》,也说当下出国留学者虽多,但绝大多数到西方是去学政治、法律、军事、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的,而很少有人能像王国维、陈寅恪那样“为学问而学问”,故不能不说青年王国维与陈寅恪真正是本世纪初中国“学人中的学人”,堪称“泰斗”。这不仅是指其学识,更是指其治学已臻境界,亦即因“学统”自觉而走出了传统文化的阴影。
○确如先生所言,古人即使治学,亦不免注入某种经世致用的动机,甚至可说大凡历史上的著名学者,几乎很难找到不与政要、权力发生关系的;倒反而是那些仕途多厄回头是岸者,后在学术上造诣甚深。这能否说,“政治失意而后治学”已成历代中国文人的一种生存模式呢?
●你的眼光真尖。以20世纪中国学术为例,不少学人所以最终能静心在自己的书斋置一书桌,并非表明其“第一志愿”便想做人文学术,恰恰相反,其最初的角色自期本是从政。若其气质、能力类型及社会背景适宜他从政,这倒是不错的选择;但中国的问题或“特色”往往在于,当事实已经证明他的气质、能力类型及社会背景并不适合从政,所谓“宦海沉浮非书生所宜”,但他还硬去从政,结果碰壁。于是当他实现不了“第一志愿”时,他就只能勉强地尝试“第二志愿”,去研究学术。我可说闻一多当年就是这样。1925年当闻一多匆匆告别芝加哥大学美术学院回国,连文凭都没拿,是想在本土掀起一个“现代戏剧运动”。但刚被“五卅”血案所染红的国土,根本不存在发起“现代戏剧运动”的浪漫氛围和条件,而后他又接连出任北京艺专教务长、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与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教务长、文学院长堪称高校的政官,亟需“双肩挑”,一手抓学术,一手抓管理,即学政。但闻一多的火爆性子兼诗人气质却导致他屡屡坐不稳学政官的位置,老是“后院起火”。于是他失望了。他发现自己在面对俗世方面委实缺少办法,最后只好回母校清华中文系去当教授,而一头扎进故纸堆。1934年考取清华中文系本科,至1937年脱离中共,再到1942年复学西南联大,而后潜心撰写《中古文学史论》的王瑶,亦可说重复了上述生存模式。
○先生曾说,“政学分途”是陈平原最具“中国特色”的学魂反思,其实,这也是《九谒先哲书》的核心理念。但西方现代学者如萨特却能在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领域同时扮演双重角色,不仅不矛盾,反而相得益彰,这显然同中国传统士大夫因“亦儒亦吏”而造成的“非儒非吏”之角色功能混淆迥然相异,不知这个“中国特色”该落实在哪里?
●为何说陈平原在《学者的人间情怀》一文提出“政学分途”富有“中国特色”?因为自先秦以来,中国历代书生几乎都把读书作为当官(从政)的台阶,也就是说,在其价值视野,学术与政治相比,学术永远是为权力(政治)服务的奴婢,所以当陈平原提出学人应以学术为本,学人可通过学术研究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找到自己足以安魂的归宿,应该讲这种声音是极其可贵的,它绝对是在当代语境对中国历代文人把“读书当官”视为最高生存模式的一种历史性反拨。“历史性”一词在此绝非谀词,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负面遗产,并没伴随末代皇朝的倾覆而自行消解;相反,只须稍作观察,便可发现至今仍有不少知识分子或已在做人文研究的学者,他心底仍自觉或不自觉地期待有朝一日能跻身于体制去品尝权力的快感。当一个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或人文学者骨子里仍把当官从政视为人生的第一要义,这委实表明中国人文学者的价值视野太狭隘了,因为他们只认定人的活法只有一种,人似乎只有与权力体制连在一起才活得踏实,心情才能舒畅,好像除了与权力体制紧紧地抱成一团,不知人生还有其他幸福,好像除了被权力体制冷落或抛弃,人生就没了其它的痛苦。这就未免活得太卑贱、太萎琐、太苍白了。但就面对这片苍白的精神背景,陈平原主张“政学分途”,让学者自信可从学术研究获得人生的欣慰,让政治家在正当的政治活动中实现自我价值,申明这是两种不一样的活法,是人类社会的两种异质活动领域所设定的不一样的游戏规则,亟需两种不同的专业技巧乃至智慧,这对中华民族最终形成多元化的现代文化空间无疑是有意义的。至于在法国,萨特为何能在当哲学家、小说家、戏剧家的同时还扮演社会活动家、政治斗士的角色?其实很简单,当他扮演政治斗士时,他是以公民的身份在关怀现实,介入社会。其实,这对中国学人来说同样适用,当学人认定自己可以从学术研究中实现人生理想或角色自期,但这并不妨碍他看到社会、民族亟需他出来说话时,他可挺身而出。但必须分清的是,当他因良知的召唤而仗义执言时,他并非是以人文学者的身份,而是以现代公民的身份在说话,故他也未必能比其他公民说出更多的、更有效的救世治国方略,或许更重在呈示某种道义,不忍之心或个体存在的勇气。这就是说,当社会出现危机、民族面临困境,不仅是人文学者,只要你是一个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不论在社会分工上是当个体户、医生还是清道夫,也皆有责任以公民身份站出来说话。这当然不是传统的“为民请命”,而是更具现代感的“人权自卫”。故当强调学人可从学术研究中实现人生价值时,并不排斥他以公民身份喊出良知之声。
○先生申明不排斥学人以公民身份喊出良知之声,很有意思。吴宓亦曾说陈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由此可知陈寅恪并非一味埋头典籍、不闻世事之“书呆子”,而分明是洞察幽微、知晓天下事的另类“卧龙”,但他却坚持一生“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以时俗为转移”。不知先生对此怎么看?
●我以为陈寅恪首先是百年中国学术史的一代宗师,他对现代学统的毕生践履,可谓达到了一个中国学人所可能达到的极高境界,否则,真难以想象他何以能在其生命的“最后20年”,在如此艰难语境坚持治学,尤其是篇幅长达80余万字的《柳如是别传》,竟是在失明、膑足、生活难以自理的情况下(且不提那个特殊年代的乌云压城),积十余年之血泪、脑汁而凝成的文史巨著,若无为学术献身之精神,何以有此学术史奇观?但一个视学术为第二生命的学人,并不意味着其耳朵就听不到窗外的“风声”和“雨声”,而只听到其灵魂的“读书声”。其实陈寅恪是用两个耳朵来倾听世界的,既听外界的“风雨声”,亦听内心的“读书声”,两种声音彼此碰撞、激荡乃至融汇,但绝不会让“风雨声”遮蔽乃至压倒“读书声”,相反,却要让自己的“读书声”从更高层次去穿透乃至照亮窗外的“风雨声”。否则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陈寅恪。
○先生把陈寅恪看作是演绎现代学统的纯正人格载体,近乎崇敬到视他为学术“神”。而面对“神”,由于历史记忆的魔障,我几乎怀有某种本能的畏惧。先生是否意在学人的价值理念重建?
●这个问题提得好,好就好在:当某一现实人格存在被演绎为相应价值理念的圣洁象征,确有“偶像化”或“神化”之嫌。但事实上,你又不得不承认陈寅恪确是百年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难得奇迹。在我看来,能真正以生命去践履“学统”且历经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时代却始终锲而不舍者,舍陈寅恪其谁?似乎没了。青年王国维固然在辛亥革命前曾以其学术实绩和纯正的学术理想追求把“学统”演绎得很精彩,但辛亥革命后,尤其是1923年到紫禁城去当废帝陪读后,学人本色显然逊色不少。1927年6月2日自沉昆明湖,亦显然不是为了殉学术。若王国维到晚年也能像青年时那样视文哲之学是自己实现人生价值之舞台,他就不会在冯玉祥再度威逼北京时轻生。当然从文化史角度讲,王国维确实死得令人回肠荡气,但若从学术史暨思想史角度来看,王国维撒手中国学术而去,委实是对民族精神文化创造的一大遗恨。惟独陈寅恪能在任何语境用生命去承诺他为王国维纪念碑所撰的血色碑铭:“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如此傲岸人格在百年学术史上确实太少,太少。正因其稀,故弥足珍贵。正因其珍贵,故堪称中国学术思想暨学人灵魂史上百年一遇、千古一绝的人格丰碑。所以,这一丰碑并非人为地硬撑起来的(比如“文革”时的“大树特树”),而是学界反思百年学术痛史时,从历史沉积中勘探、发掘出来的。陈寅恪所以巍峨得像碑,无非因为绝大多数中国学人远不如他活得纯粹乃至高贵,而大凡高贵者皆不免有“偶像化”之嫌。这叫“鹤立鸡群”,或曰“树大招风”,“木秀于林,必摧之”而已。
○我发现先生所说的“学统”,既含价值观念层面的本原性规范,又含操作细则层面的工艺性规范,您在(《谒梁启超书》)中称梁的功绩是把“乾嘉学派”所孕育的现代“学统”胚胎剥离出来,嗣后,又将“学统”描述为“学术本位”、“思想独立”、“科学归纳”与“朴学文体”四个层面所合成的理念整体,这就概括了作为“学统之魂”与“学统之本”的本原性价值规范,又包括了作为“学统之技”与“学统之相”的工艺性规范,而您用力最多的,还是在价值观念层面对学人灵魂作思想史阐释。能否说,陈平原的学术史研究之幅度展开得更开阔些,而您则旨在对“学魂”命题作系统阐释?
●你的感觉很准确。陈平原作为王瑶的得意弟子,他在80年代末提出中国学术赖以发展的前提是应在理念上实行“政学分途”,在90年代他有新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近期他又出任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颇有想把20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作为他毕生追求的目标之态势。我曾对陈平原说,你的学术史研究之特点,可谓“三合一”。所谓“三合一”,即在巡礼中国人文学术(重在文学学术)的百年硕果时,还甚关注学术先贤的治学思路、门径及方法。陈平原所不时强调的“学术规范”,主要是指上述先贤曾行之有效的、合乎科学思维规则的操作性“工艺”,以期后学亦能赖此而把当下学术研究弄得有学术性,经得起事实与逻辑的推敲。再者,陈平原也涉及“学人活法”,探讨学人应奠立怎样的角色价值根基,才能确保他心安理得地献身学术。综上所述,陈平原之学术史研究确有“三个维度”:“学术史”;“学术规范”;“学人活法”。而我,则通过个案系列分析,重在考量“学人活法”即“学魂”在百年学术史上的现代演化:亦即我是在研究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思想暨学人灵魂史。这就是说,我主要是在陈平原“三个维度”中的“学人活法”一维下了功夫。或说我与陈平原的研究,既有交叉部分,又有各自的色泽。
○读谒书时,我看出先生对“方法”与“方法论”也很重视,比如对乾嘉学派的“归纳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以诗证史”,胡适的“实证主义”、闻一多与王瑶治文学史的方法及其变异,都有细致分析。我还体会到《九谒先哲书》尤其注重对“发生学”方法的运用,比如极其重视“无字天书”的灵魂史与“有字人书”的文献资料之互释。能否再具体谈谈?
●九帧谒书,实是9个学魂个案研究,是对9个有世纪影响的学人的学术思想及生存样式作出我的述评。述,是史实追溯;评,是价值重估。史实追溯是想发掘那些已被风尘掩埋的先哲的灵魂历程;价值重估,则是用我所理解的“学统”参照来衡量先哲的所思所言所行,测出他们与理想化的学术境界之间有无距离:谁已臻境界;谁曾接近境界却差最后一口气;谁因无奈而游离境界;谁则漠然不知有此境界。我写谒书,确怀有这么一个“方法论”动机:企盼通过用9 个个案的系列述评串起一条线,此线即百年中国学人的灵魂演化脉络。亦即不仅想用谒书来复活一个个已逝去的学魂,而且想从这串学魂的复活,来激活学术思想史本身曾有的脉动乃至体温,而变得可供后人用灵魂的手指去触摸。一旦你真的触摸到了先哲幽灵的悸动与颤栗,沉寂的历史也就被唤醒,后人也就能在冥冥中与先哲心照不宣地相遇乃至神交,由此,后人的灵魂或许也会生发相应的颤动。这也是我为何取谒书文体,而不用史论形式,来表述我对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思想史的思考之原因。
○先生,在您看来,该怎样做,才无愧为真的学人,或学人该如何“人格自律”,才算纯正?
●首先申明,当初提出学人的“人格自律”,第一动机是我针对自己提出来的。3年后的今天,我又有了另一想法:若有人也像我那样,极想当纯正学人,那么我相信,他(她)读谒书,可能也会被触动乃至被感动。于是我又想说,这些谒书不仅是为自己写的,同时也是为那些与我有心灵共鸣的人写的。若事情果真如此,当属我的大幸。
○先生,我还想请您谈陈寅恪。陈晚年撰《柳如是别传》,对柳词《咏寒柳》感怀至深:“复次,昔时读河东此词下阙‘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诸句,深赏其语意之新,情感之挚。”作为人格丰碑,陈从自己的文史研究对象身上寻找心灵契合,有否夫子自道之意?
●对此,我是这么理解的:现代“学统”作为某种角色价值规范,其实亟需一个人格前提,这就是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所撰的著名八字:“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可惜,无论在学界还是在非学术领域,中国文化谱系中真拥有如此人格者实在太少。而对如此凄凉的人格荒漠,却执意要从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他当然渴求自我激励,渴望能从民间传奇乃至青楼女子身上发掘若干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能够相契的精神文化因子,且尊其为现代独立人格建构珍贵资源之一。这就在使他的现代人格追求获得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同时,又冲淡了一个独行者的心灵孤苦。故我觉得本土学界对陈为何在晚年对陈端生、柳如是如此钟情且称其为“红粉知己”,还甚隔膜,其深层意图未被挖掘,总以为陈写柳如是与陈端生有损大师风范,远不如陈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论述隋唐政体来得气魄宏大。我觉得这是两回事。隋唐政体研究当是陈对中国古代制度研究的高峰,但研究柳如是、陈端生则是企盼从民间传奇人物身上开掘现代人格建构所亟需的精神资源,从而使陈在风雨如磐的“最后20年”也能活出圣洁。
○您说陈在“最后20年”活出了圣洁,若时代背景和个人境遇不是这样艰难,陈寅恪这座人格丰碑是否依然伟岸?
●历史很难假设。陈的“最后20年”风雨交加,近乎冷酷,何以如此?这可留给历史学家去解释。但我敢说,即使“最后20年”多些阳光,多些和风细雨,陈那壁立千仞的学人姿态,依然是巍巍丰碑。因为当中国学人群体还不能以整体形象来呈示自己对现代学统的价值自觉时,陈寅恪的存在便不免被赋予象征性,这就是:对现代学统的人格演绎而言,陈是纪念碑;对集权政体蹂躏人文学术而言,陈又成了醒世启蒙的耻辱柱。
○学者首先需面对的当然是自己。但现代“学统”之发扬,除了学人的价值自律,宽容的多元文化空间也极重要——这本是《九谒先哲书》的命题之一。我想“多元”并非是没有标准或原则,拟应有多个标准,但“多元”本身似又是一个标准,这是否矛盾呢?
●我理解你的意思。什么叫现代多元文化空间?首先,何谓“现代”?学界往往把“现代”和“五四”精神相连。“五四”精神绝对是中国文化的“现代”纪元之源头。“五四”精神的核心可用鲁迅小说《伤逝》中子君的一句话表述:“我是我自己的”,亦即“个性本位”。每个人都把自己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与人性尊严的个体来尊重,同时也尊重你所碰到的另一个人的人格独立与人性尊严。此可谓辨别一切文化是否“现代”的普世标准或价值根基。但演绎或兑现这一“现代”价值却可通过多种角色范型,你可以当政治家,当学者,当工程师,当军人,甚至当清道夫……每一社会分工皆要求其相应角色有其角色规范或职业道德准则。无条件地泛化为一切公民亟需恪守的普世价值的绝对标准,这就将“多元”压缩成“一元”,有文化专制之嫌。这就没了“现代”意蕴,而倒退到了封建意识。这就是说,作为“现代”文化的普世标准,其精髓恰恰是在价值上承认每一个体的人生选择诚属“自然法权”。故当学人能在中国大地庄严宣布:我要从我所倾心的学术研究中获得慰藉和实现价值,这实在是为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现代”性的多元文化空间,迈出了可歌可泣的一步。请设想,若每个人皆能从他所选择的角色位置上找到其生存理由或意义,而不再盲目地屈从于权势,这个古老民族的精神风貌将会出现何等改观!
○先生在《谒冯友兰书》中把冯看作是一个世纪性“精神遗体”,而《谒王瑶书》又着意宏扬“清华薪火”,您是否亦有承当现代“学统”的拯救者或打捞者之意?当然这首先是某种“学魂自救”,但是否也有陈寅恪式的“韩愈情结”呢?况且,您还对韩愈“师说”三功能(传道、授业、解惑)作了学统意义上的新阐释。这种新“韩愈情结”(姑且这么说)是否也可说是一种启蒙,一种“学统”启蒙?
●假如可打比方,我是首先把《九谒先哲书》视作一个系统性“盗墓”工程。先哲仙逝久矣,但其亡灵未亡,还分明活在其著述的字里行间,活在其亲人、弟子的深情缅怀中,更活在其对中国学术史的深远影响里。但若你不去自觉、细心地打捞,搜集,且审慎地重估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它们迟早将封存在淡忘乃至遗忘的坟墓里。“盗墓”之功能则在于“化腐朽为神奇”,将先哲的精神遗产置于新世纪的阳光下加以重新审视,既可给我,或许也可给我的同仁及弟子以启迪,以期读出遗产之凝重。因为这不仅是用先哲的智慧,也是用先哲的血泪,更是用先哲的叹息、忏悔乃至终生遗恨而凝成的世纪性精神遗产。但当我用“学统”作参照来衡量或甄别这份遗产时,我又发现,我似乎在“招魂”。“招魂”,首先,当是为我“在细雨中呼喊”我作为一个学人所应有的“学统”之魂;同时,毋庸讳言,我也是在为我的同仁、师友及弟子“招魂”,假如他们亦想当纯正学人的话。至于说,我是否想在学术思想史扮演承上启下之角色,实现当年陈寅恪曾有过的“韩愈情结”,我坦白,我不曾有此抱负。诚然,《九谒先哲书》这一纯属学魂自救的学术行为,是否将诱发某种社会效应或思想史影响,这是“未来学”命题。我觉得,与其让我当算命先生去预测,还不如让我静下心,为以后的学术课题研究多读几页书,多写几行眉批,来得实在。
标签:陈寅恪论文; 陈平原论文; 王国维论文; 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国学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