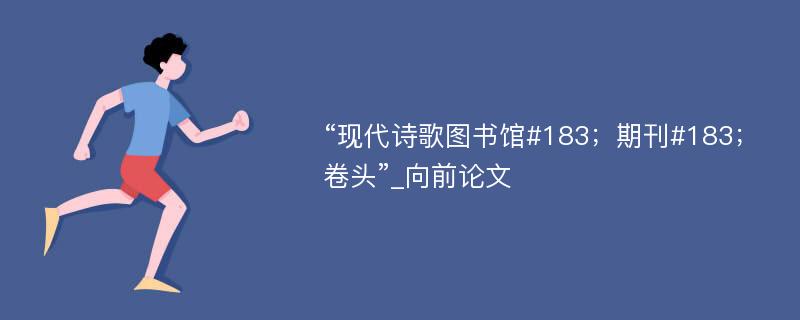
向前 向前 向太阳——《现代诗库#183;公木卷#183;卷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阳论文,现代诗论文,卷首论文,公木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木(1910.——),原名张永年,又名张松甫,现名张松如。河北省束鹿县北孟家庄人。1918年在外祖母的资助下,使他这农家子弟得以入学读书。1922年升入深泽县河疃高级小学住校学习。他的老师曹席卿是前清秀才,民国后又在天津入过师范,虽是儒生,力主新学。而且,在校助教的他的长子曹贡升,侄儿曹俊升,是新从保定师范和育德中学毕业的,有革命思想,是接受了“五四”精神洗礼,懂得反帝反封建,得到科学民主思想熏陶的年轻人。公木在此,接受了一次再洗礼。除学习英语、国文、史地、数学等课程,还接触到了《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白话文范》、《白话书信》等新书,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并开始练习用白话作文。1924年,他考入河北直隶正定省立第七中学。那正是大革命时期,校园里响彻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四·一二”政变后,同学中的共产党员多数潜撤离校,有位高克谦同学被北洋军阀杀害,这都使他声援“五卅”惨案罢课、到石家庄示威游行的爱国反帝热情更炽烈地燃起。
公木在校各课成绩均在前列,熟读了唐诗宋词。1927年以“魂玉”等笔名,将练习填写的诗词投向报刊,被《大公报》、《晨报》等报副刊采用,这更激发了他诗歌创作的兴趣。但在那个时代新的思潮下,唐诗宋词已不能解除他精神上的饥渴,而大读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刘半农、刘大白、蒋光慈等人的作品。后来他回忆说:“就在这时,蒋光慈成为我心目中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大部分都曾能背诵出来。”[①]蒋光慈的诗在那时一印再印,公木以及许多如公木那样的青年对蒋光慈那么倾心,正是一个时代的必然。
公木是1928年秋入北平师大,从对新文学的兴趣到对社会科学、政治问题的关注,他阅读了所能找到的各党派的宣传品。1929年,他就曾写过一篇小说《孟老先生歪传》,讽刺当局各种反动势力的合流。1930年初,他经郝培庄介绍,秘密地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受组织派遣,参加了“北平左联师大分部”、“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华北左翼教师联盟”、“北平文总”等组织或活动。同年八月,因参加为庆祝长沙解放和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两周年、反对国民党军阀混战的示威游行而被捕。他的老师范文澜先生也在其中,一起羁押在北平警备司令部的监狱中。九、十月间,政局变化,以阎锡山、汪精卫为首的所谓“扩大会议”瓦解,晋军仓促撤退,在押同志全部获释。从1929到1930年间,他以C.Y.N等笔名,在报刊发表作品,编过共青团的刊物《红孩儿》,可惜的是,大都没有保留下来。
“九·一八”前后,北平地下党领导大中学生学习马列主义的进步组织“鏖尔读书会”,为宣传革命思想而秘密出版的杂志《鏖尔》,就是由公木主编。1932年3月18日,因参加抗日救亡集会,再次被捕,羁押于北平市公安局,一个多月后,再由师大学生会和抗敌救亡会联合保释出来。同年冬,鲁迅先生由上海回北平探亲,公木以“左联”的关系,用学生代表名义,与王志之、潘炳皋前往鲁迅家中拜访,先生欣然接受了邀请,到北大作了《再论“第三种人”》的演讲。同年底,公木与“左联”成员、同学谷万川、王志之等着手筹办《文学杂志》。它于1933年4月15日创刊,共出了四期三册。创刊号就刊出鲁迅的《听说梦》。他们收到茅盾的《杂志办人》的原稿,力求办出“人办杂志”的风格。但七月的三、四期合刊为声援文化界营救“左联”作家丁玲被捕而发的专稿,因主编谷万川被宪兵三团逮走,押赴南京而作罢。
1933年早春,公木因躲避特务追捕,越墙逃离学校,回到河北老家。不久,北平“教联”来电叫回北平,又介绍他到山东滋阳县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教书。在他来到前后,“教联”的成员来了不少。他们在学校里发展了一些学生加入“教联”,建立了“教联”鲁南分部。1934年冬,公木离开山东,到河北正定中学教书。因为他大学没有毕业,又没著作,按规定不能教高中,于是他便把在滋阳教文字学的讲义整理一下,请语言学家黎锦熙审阅、推荐,于1935年4月由新亚印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文字学概论》。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公木在学生中讲形势,作宣传,引起校方密切注视。事变和平解决后,公安局抓走四名学生,教育厅派来调查的督学孟福堂是公木的同学,他不等作调查就通知公木:“你赶紧走!”于是,他们夫妇带着出生不久的孩子于1937年初返回北平,通过黎锦熙的关系,又在“北平师大”复了学,并写了一本《白茶斋九歌注》,请罗根泽教授审阅书稿。但此书却未能出版,书稿也在乱世散失。但他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功底,在它上面却是偶露峥嵘。
“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公木辗转到了西安,与同学唐般若、李树藩共同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林伯渠同志,林老叫他们去延安。但公木认为延安是后方,还是想上前方,而不满两岁的孩子却使他难以前行。在孩子与上前方的尖锐的矛盾中,年轻的爸爸、一代热血沸腾的抗日青年,给女儿找了个好心肠的陌生人家寄养,毅然决然轻装上阵到了晋绥前线,任二战区动员委员会《动员》杂志的编辑。一个月后,调到由程子华兼任队长的敌后游击队,任宣传股长。两个月后,又调到组织部工作,曾到神池县、岚县等地任县与专区干训班主任和指导员。
1938年8月,公木为了护送几位不适于在前方工作的女同志回后方,西渡黄河,回到延安。在抗大学习了四个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未及结业,调任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业余从事诗歌创作,作《新歌诗试论》。时值郑律成也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曾于无意间看到他抄写在笔记本上的诗稿,暗自为《子夜岗兵颂》作曲,后来连近两百行的《岢岚谣》也谱写了出来,这使他很受感动,遂相约合作《八路军大合唱》。那是受了赴延安与冼星海合作《黄河大合唱》的光未然的启发,于是郑律成提出创作《八路军大合唱》的构想。1939年抗大总校东渡黄河,迁往敌后,公木和郑律成都被留在延安,分配到筹办中的抗大三分校工作。在此工作交替之际,他们趁空完成了拟议已久的《八路军大合唱》。其中《军歌》和《进行曲》两支歌,刊登在总政主编的报刊上,得到广泛流传。此后,他与萧三、刘御、师田手、海棱诸同志发起并建立“延安诗社”,开展街头诗和诗朗诵活动,编印《诗刊》小报。他申请赴前方,回家乡冀中军区工作,中央决定暂停向敌后派遣干部,因而调任军直政治部文艺室主任,主编《部队文艺》杂志和《蒺藜》板报,并成立以发展部队文艺创作为宗旨的文艺社团“鹰社”。同时写了《鸟枪底故事》、《哈喽,胡子》、《我爱》等诗。1942年5月,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随后调“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任教。整风过后,于1944年与天蓝同赴南泥湾访问。同年冬与孟波、刘炽、于兰、唐荣枚一道赴绥德地区,下乡闹秧歌,并采录民歌。陕北《移民歌》就是这期间采录的。
“八·一五”后,参加由舒群、沙蒙任正副团长的“东北文艺工作团”,10月底到达沈阳。曾就《移民歌》首段改编并填词,写成《东方红》歌曲。《东方红》就是文工团到达东北时集体完成的。1945年末,受中共中央东北局委托筹建东北大学。1946年2月,东北大学建立后,先后任教育长、教育学院院长。1950年4月旧学校易名为东北师范大学,任教授兼副教务长等职,为东北地区的文化教育建设做出了贡献。1951年9月调任鞍钢教育处处长。1954年夏,转调作家协会沈阳分会,与杨公骥合写《中国原始文学》,共同拟就“中国文学史纲目”。秋调北京中国文学讲习所任副所长、所长。他有过这样一段自叙:“1958年春夏间,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代表,赴匈牙利及罗马尼亚访问,在文化交流上主要是宣传‘双百方针’,介绍中国文艺战线‘反右斗争’的情况。如同受着一种什么不可知的力量的嘲弄似的,七月底归来,回到中国作家协会,自己也被指控为与所谓‘反党集团’‘互相呼应,进行反党活动’,而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被开除党籍。同时,中国文学讲习所亦由中宣部及文化部决定停办。在京四年间,主要精力,用在青年作家培训和青年诗歌评论两个方面,同一代文艺战线上的新人建立了亲密的联系,生命也从而感到充实。1958年10月戴帽后,积存未复的来信与诗文稿仍有二百多件,带着负罪的疚愧心情,悄悄地分作四五批挂号退回,其情其景,黯然神伤,这是我同北京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协举行的告别仪式。”1958年腊月三十丢下妻子儿女,只身下放长春,任吉林省图书馆馆员,到农场生产队劳动,教育改造。摘除右派帽子后,1962年1月调任吉林大学中文系教员兼代系主任。“文化大革命”一来,以“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摘帽大右派”两种身分被批斗、审查、抄家,“该受的都受过了”。但他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学习的主动。比如在“批儒评法”期间,“于论孟、荀、韩外,也多读了一遍老庄,特别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上,付出较大功力,成《老子校读》初稿”,也是“该受的都受过了”中的一大收获。
1979年1月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他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于教学,带中国文学专业研究生,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以及各种委员、理事、副主席、主席等等。
诗人学术著述甚多,有《中国原始文学》、《中国文学讲义》、《诗要用形象思维》、《诗论》、《中国诗歌史论》、《老子校读》、《老子说解》、《老庄论集》、《先秦寓言概论》,以及六卷本的《中国诗歌史》等等。
诗集,除《公木旧体诗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有《鸟枪的故事》(佳木斯东北书店1947年8月版,张望插画)、《哈喽,胡子!》(五十年代出版社,1949)、《十里盐湾》(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作家出版社,1954)、《崩溃》(上海文艺出版社,1957)、《黄花集》(作家出版社,1957)、《公木诗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我爱·公木自选诗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0)。同时,完成了《第三自然界概说》、《商颂研究》、《毛泽东诗词研究》等论著。
从公木的这份论著的书目看,说他是位学者,恐怕更确切些,但他的诗,又总在伴着我们的生活,不论他的学术著作有多高的价值,也是无法替代它的。
向前 向前 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这支歌,从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唱到和平建设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唱,百姓也唱,唱出了中国人民勇往直前的豪气。在音符切分的跌宕中,“向前 向前向前!”真是排山倒海的气势。公木说:“我原不把歌词视为重要诗作,因为它的传唱或者说‘成功’,主要在歌曲,属音乐艺术范畴,声为乐体,诗为乐心,歌词仅起点醒主题作用。不过,借重音乐家郑律成同志的才华,我却获得了‘八路歌手’的美誉,受到表扬,溶溶月色,亦自婵娟,因而使干脆以军歌与进行曲开篇。”这一开篇,也就是把他在这之前的十年所写的诗都筛下在外了。1928年他在天律《大公报》发表的处女作《脸儿红》,和军歌放在一起比较,也会使作者在另一种意义上脸红的。“小饮归来意朦胧/徘徊夕阳残照中/山青青/草青青/一片春色遥映落霞明/花香暗自盈衫袖/无语对东风/蓦伤情/那人儿何处去也/秋千底下喜相逢/无奈人前却装不相识/低过头/空把脸儿红”。这种旧词曲式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情调,与他的军歌虽然可以在求多样中而并存,但总还是不相谐的吧。诗人是不信诗是可以“纯”到那里去的。他说:“‘为政治服务’(现在不再作为口号来提倡,而我也不认为它有什么不对)并不意味着做‘啦啦队’,而是兴观群怨,正变美刺,原是以诗做主体,由诗人来裁断的,即使所谓‘纯诗’以及‘纯诗人’也无法回避,莫不皆然,淡化以至摆脱政治,岂不也是一种政治态度?至于我,这一点是从来没有含糊过的。”“要进行政治宣传,也并不排斥艺术审美,力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政治与艺术,有矛盾对立的一方面,也有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对我来说,两方面都有,而主要是后者:是革命给了我的生命以意义,给了我的诗歌以生命。从整体看,从长远看,这是一点也不含糊的。所以,政治之与诗,有人看作是病原体,我无意跟他们抬杠;但是,若依我看,则无宁是维它命,这也是没有任何人任何理由能说服改变的。第二是,决然不是‘五四’启蒙精神的‘中断’或‘夭折’,而是它的发展与实现。当世界和中国进入三十年代,也就是‘五四’运动后的第二个十年间,作为一个觉醒了的中国青年,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寻找自我,要提高‘人的自觉’,要卫护‘人的尊严’,则势必由孤立的个人主义向世界历史性的集体主义转变并发展,然后才得完成‘主体意识’,才得树起‘独立人格’。实现这个转变与发展,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正道和规律,只要坚持‘五四’启蒙精神,并付诸实践,或迟或早要迈出这一步,这是难得有例外的。个人固然卑微,而在起点上得与历史的主线相结合,不是相游离,更不是相违背,没有被压顶的乌云吓昏了头,吓麻了腿,乃是深受了时代的鼓舞:‘锦云何惧倒寒侵’啊!怯阵与逃避决不是‘自由的选择’,而不折不扣是‘自由意志’的摧毁。”“近年来倡导重写文学史的论者似乎有一种说法:在延安,斗志昂扬,情绪高涨,只是审美完全被政治压扁了、挤干了,只剩下枪杆诗、街头诗和民歌,新诗被歌咏取代了,‘我’被‘我们’淹没了。可是,作为一种否定的见证,我却正是在这个环境里成熟起来的,而且是作诗与做人同步成熟起来的。在延安,我不只结识了萧三、柯仲平、天蓝、何其芳、艾青、厂民、鲁藜以及郑律成、刘炽、向隅、冼星海,而且还接触了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以十以百计的爱好诗歌的青年同志,有的结成为终生的战友;我不只阅读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以及惠特曼、聂鲁达、歌德、泰戈尔、普希金、莱蒙托夫、玛雅科夫斯基,而且还发现了《信天游》、《兰花花》、《骑白马》、《打黄羊》、《走西口》、《绣荷包》以及像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般无数无数生动活泼的民歌小调。凡此一切,都启发并助长了我的审美意识,都在我的诗作历程上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更尤其值得一提、不容忽略的,正是在延安,其时其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徘徊在欧罗巴的幽灵取得了亚细亚的形象:‘幽灵转世中华相’,它标志着改变世界形势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具体落实,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经过大闹秧歌运动,更给我、我的灵魂和我的诗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我明确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源与流的关系、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以及大众化的起真实涵义与化的途径等等。这些无一不在我的诗创作的实践中得到验证,并指导了我的诗创作。在这时间,我确立了歌诗与诵诗的观念,纠正了对民族传统的偏激情绪,除以自由诗为主体外,也认真从事歌词与民歌体的写作,在语言上更刻意追求,注意向群众学习,又努力创新……”[④]因此,他读了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的诗,写了发表在《七月》、被认为有“七月”诗风的《哈喽,胡子》。这“哈喽”二字,就是英语“heil”的音译。这惠特曼也是个大胡子。诗的副题“送一位老朋友到冀中去”,这“一位”,大概也是“胡子”。这自然只是一些偶然的巧合。重要的,还是诗人写一位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毫无保留地付出”“勇敢和忠诚”,投入到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中的形象。这从“哈喽”起的语气到惠特曼式的形式之自由,是和谐的。随着大批知识分子在抗战的号角声中涌向延安,这《哈喽,胡子》的情怀,是延安的情怀,延安的诗。到他写出《十里盐湾》,则是诗人经历了采风、闹秧歌,着迷地向陕北民歌学习之后,为“尽可能利用活在大众中的旧形式”而写的民歌体新诗。过了半个世纪,80年代了,盐工的子孙还会用家乡的小调唱着——
……草鸡下蛋脸憋红
掌柜的低头不吭声
十五个吊桶来打水
七上八下扑咚咚
掌柜的心里发了懵
好一个日子六月初八
三皇峁开会闹杂杂
掌柜们发言蚊子叫
伙计们讲话山洪发
掌柜的骨头松了架……
当年盐工们成立工会,劳资关系变化而当了家的情景,叫盐工们的子孙在今日唱来,依然舒心。五行一节,首尾押韵,以黄土高原的小调唱来,也是别具一格的新诗。它半个多世纪一直传唱下来的作品效应,无论什么人,不论他用什么“新”的文艺术语、“新”的审美的价值来贬损它,都是苍白无力的。
如此说,并非讲作品本身就完美无缺,而是没有忘记在当年历史背景的特定之时空条件下,诗人找到诗能扎根于斯的道路。要说《哈喽,胡子》的情怀,是延安的情怀,延安的诗,那么,这《十里盐湾》就更是延安的情怀,延安的诗了。仅就形式的变化而言,这两首诗之间,《鸟枪底故事》中作者尽量使用口语、乡音,用他家乡冀中的语言,《风箱谣》那还不地道的谣曲,以及用盐工答问,形式较规范的《问天》,正是他诗风转换的过渡,何况《鸟枪底故事》对人民在异族侵略面前抗战的自觉与《十里盐湾》张扬盐工在阶级压迫与剥削面前求翻身的感情,以及军人的进行曲与盐湾民间小调的音乐形式之间,并不存在鸿沟而只有通道呢。生命活动的变化,也就有了诗的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变化。具体到公木个人和他这些诗就是这样。广而视之,战前在几个大城市虽然也反映出不同诗观之斗争的新诗运动,当有了陕甘宁边区,它分流在边区不大的地域,却不亚于大后方的发展之现实,已使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是有别于沙龙文艺的进步的、左翼的,也只是亭子间的新诗,而是更能贴近现实,扎根在基层,反映与服务一并于人民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火热的斗争与生活,也使新诗在边区得到“五四”后的一次大大的发展,使新诗真正的到了广泛的群众之中。作为公木个人,他在这段经历中的人生体察,以及作为学者的诗人,用怎样的理论来概括和表述他的诗观,同时,读者和评论家不论怎么褒或贬他的这些理论和创作,都无法改变当年当地诗人们投身在群众之中写出受他们欢迎的作品,从而推动了新诗运动的史实。任何一个人,对一种诗观,一个作品的喜或厌,点头或摇头,其自由自然是绝对的。然而,任何“权威”,不论何种“自由”,都是无法改变史实的,粉饰无用,抹黑也不行。它就是诗史在那阶段发展变化的历史形态。包括公木在内的许多边区诗人这一时期的作品,毋需细说,它们的光点和不足之处,都是这一历史形态的具体表现,或说是构成这一形态的具体细部。这样,就不难找到它们定位在新诗运动中的座标。
1941年,公木的《我爱》中,认为世上“生命力最久常”,“光照得最深最强”的,就是诗——
……我把自己
投进你底光圈里,
我看见每个人头上,
都照着同样的光圈。
只有那依靠上帝和血统骑人颈上的人,
只有那借助手枪和说谎骗取荣利的人,
只有那仰仗主子威风专以鸣鞭为快的人,
只有那生就一副膝盖用来发抖或下脆的人,
只有他们,那些多余的人,
留在这荣耀而辉煌的光圈之外。
啊,你是什么,
我心爱的诗?……
由此,也可问:“啊,你是什么,公木的诗?”它,就是除了在这光圈之外者的歌。不论你喜欢或不爱,称赞或贬损,它都是一个时代形成的人生,是一种人生的诗。
从50年代后期起,公木是基本不写新诗了。偶有一首,也为其真情动人。但到80年代,作为学者的诗人,诗界的老人,再挥诗笔,就诗笔不凡了。说这“不凡”,也是正常的诗的现象。因为,一般地说,诗总是属于年轻人的。人上年纪,要作少年时的抒情,多数都难免是矫情。公木在古稀之年,以一位有成就的学者对人生的诗思,走到比他过去更广阔的诗的天地——
人类社会,一代一代又一代
繁衍生息,相昫相濡,相啮相踏
犹如长江大河后浪催前浪
鱼龙混杂,挟泥沙而俱下……
一切的一,一的一切,经过
时代回旋加速器的颠簸
而转化为信息,真情假象贮存于
历史,这个无比巨型的电子计算机
……
——《真实万岁》到了《人类万岁》,同是老庄学家的诗人,大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道“时空无穷极,自然永生/天地有大美,人类万岁”的思想,也是洋洋洒洒。它不是但丁的《神曲》,不是歌德的《浮士德》,作者哲思的诗化还不够,现代词汇的多音词与某些古汉语的字词的交错,也没有达到短诗《难老泉》之诗语纯净的程度。但它也不是概念,更不是口号,是诗,是向广博、深邃的思想境界展翅的灵感,在完成他所以是诗人向诗的高度之冲刺。将他年轻时高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意志,又从另一方“向前”于诗。
作为1928年就开始发表诗作的公木,十年后他放弃这之前的作品,从在边区写的军歌,重新开始自己诗的道路,这时的他是适逢新诗运动分流在国统区与抗日根据地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人文、地理环境的天地中进行,从这个角度看,诗人的作品就不仅是他个人的艺术个性的表现,从它也可以看到新诗的历史在那一时期活动的形态。
注释:
① 郝长海、李凤吾:《公木传略》,《新文学史料》第36期。
②③④ 《我爱——公木自选诗集·自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0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