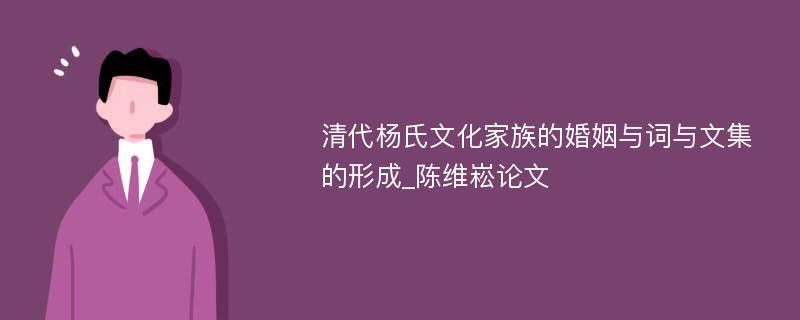
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与词文学集群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群论文,清代论文,家族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3-0102-06
清词创作集群的兴替,一直以江南为重镇,以家族词人群为核心力量。在清代江南词学的版图中,阳羡(今宜兴)尤是一个词人集中、唱和频繁的地方。继清初阳羡派拉开清词复兴的帷幕之后,阳羡词坛的唱和与创作活动一直持续到晚清民国。清代阳羡词人,大都出自本邑的文化家族,血缘相承的同时,还因家族联姻而具有千丝万缕的亲缘联系。因此,清代阳羡词的演进,始终以联姻家族为主导力量,以创作集群为表现形态。然而,在当今清词的地域性研究中,阳羡词的这一文化特质,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因此,本文拟在家族视野中,探究联姻作为一种内在机制,如何影响清代阳羡词的演变,揭示家族联姻与清代地域词学发展的内在关系。
一、清代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观念与联姻形态
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以“陈、储、吴、史、任、路、蒋、徐”等几大著姓为构成主体。这些家族大多为南渡之族,于宋元战乱之际迁徙到阳羡。阳羡位于太湖西滨,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少富商巨舶之往来,而传统文化根基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得以深植,重视耕读传家的地域文化风气相当浓厚。受此熏染,阳羡文化家族具有深厚的崇文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都坚持以儒为业,以不文为耻,以科第望其家。这由县志、府志等各类方志中屡被称颂的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便可知,如《宜兴县旧志》载吴氏家族“科甲蝉联五世”,其中吴达可,万历五年进士……子吴正志,万历十七年进士……孙洪亮、洪裕举人,洪昌进士。曾孙贞吉举人,贞庆进士;元孙元臣进士,人以为“德业之报”[1]。储氏家族“三凤家声”,即康熙五年,储方庆与兄储善庆、堂侄储振登同榜进士;雍正十年,储晋观、储传泰、储鼎泰同中举人,名震一时[1];同时“五凤齐飞”,储方庆五子右文、大文、在文、雄文、郁文同登进士榜[1],成艺林佳话。又据《万氏宗谱》《陈氏家乘》《储氏族谱》等谱牒文献,万氏家族因明代中期万士和、万士亨兄弟同时登第而名列望族。陈氏家族于晚明因陈于廷、陈一教、陈于泰、陈于鼎等人先后登第、同朝为官而称望于乡邑。储氏家族因晚明储昌祚、储国祚、储显祚等先后登进士榜被视为名士之族。由此可见,阳羡文化家族以追求科举功名作为家族发展的重要途径。
为了实现崇文尚儒的理想,阳羡家族文人在读书课业的同时,注重积累一定的学术优势或文学优势,逐渐形成明确的文化追求,因时间的沉淀而渐积丰厚。随着家族承衍,这种优势最终融汇为独特的家学传统。如储氏家族尤擅古文,陈氏家族则以词鸣,吴氏家族以诗文而著称,万氏家族专攻经学。虽然各个家族的文化素养及其各自擅长有所不同,但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阳羡文化家族的稳定发展,能够产生“文化家族叠加”关系,形成特有的地缘文化现象。
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不仅重视自身的文化建树,而且还非常重视家族婚姻圈的建立。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间具有与生俱来的地缘性,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社会交往,易形成趋同的社会观念,从而产生密切联系。这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间的一般性交往,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引发质变,而在重视宗族血缘关系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合二姓之好”的联姻,无疑成为建立超越地缘交往关系的最佳方式。阳羡文化家族正是“利用联姻策略来实现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借助联姻形式强化自身的组织性”[2]41,形成以血缘和亲缘为纽带的家族联盟,使彼此更为稳固,并以此来影响一时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阳羡文化家族联姻的过程,是以某一姓氏为中心,通过婚姻与他姓望族不断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双方家族的文化素养,这是家族文化积累沉淀的结果。以陈维崧家族的婚姻为例来看,维崧祖父陈于廷有四子,长子陈贞贻配本邑路氏女,乃路云龙的孙女;次子陈贞裕娶同郡进士吴道行女;三子陈贞达娶常州进士郑振先女;四子陈贞慧娶同郡进士汤兆京女。陈于廷的两个侄儿陈贞元、陈贞禧分别娶万炯女和万震祈之女。陈于廷的三个女儿分别适举人吴洪裕、庠生曹懋勤、进士吴简思。陈于廷养女杜氏适进士吴正心。陈于廷弟陈于明的女儿,长适太学生万诚,次适明戊辰进士路进,三适壬午解元癸未进士卢象观。陈于廷弟陈于扆的女儿,分别嫁太学生储懋学、庠生徐荪。显然,陈氏家族在其择婚过程中,非常重视对方的文化背景和功名成就。陈维崧家族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积累,以诗书传家,而与陈氏有嫁娶关系的吴氏、曹氏、万氏、卢氏等,亦世以风雅为胜,文化层次较高,体现了重视文化门第的择婚观。反观之,吴氏、曹氏、万氏、卢氏等选择陈氏,也同样是以陈氏文化声誉作为一个重要标准。
以上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说明了清代阳羡文化家族坚定的文化取向和处于共同社会层次的内在要求,而正是这种“取向”和“要求”的不断实现,使得其联姻行为具有规模效应,这主要反映在家族联姻形态上,具有世代连续和连环共存的特点。
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往往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嫁娶关系,而追求世代缔结“秦晋之好”。以清初阳羡吴氏与陈氏的联姻为例,缔结了四代婚姻,纵向历时长、辈份衔接紧。首先是吴洪裕娶陈维崧姑母,其次是吴洪裕之子吴本嵩娶陈维崧堂姐,再次是吴洪裕孙女嫁陈维崧弟陈维岳,最后是吴洪裕曾孙女嫁陈维崧子陈履端。阳羡文化家族的世代联姻,形成了亲戚关系的累复叠加。例如储氏与陈氏的婚姻,储懋学娶陈维崧堂姑,储懋学之女又嫁陈维崧,陈之堂姑又是他的岳母。此后,陈维崧孙陈克猷又娶储懋学曾孙女。再如万氏与陈氏的婚姻,万复古娶陈维崧表妹,万复古子万峰娶陈维崧女,陈维崧女的表姑同时兼为她的婆母。又如吴逢原娶储欣妹,吴逢原侄孙吴来燕娶储欣女。阳羡文化家族间的世代娶嫁,可能会出现暂时性中断,但很快就会因文化门第对等而“再续姻缘”,如储氏与史氏,明末储昌祚女适史汤诰,因储昌祚与史汤诰“同登万历壬午贤书,契甚,因此以次女为公配”[3],储氏女与史汤诰之子即著名词人史惟圆。在这一桩史、储联姻之前,史汤诰的曾祖母也是储家女。清代中期,储、史之间又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联姻,储在文之女嫁史惟圆侄孙史镕英,储在文侄孙储嗣会娶史承谦之女,另一侄孙储成璋娶史承谦的侄女。史氏与徐氏也是如此,在清初缔结婚姻后,于康熙末年再续“前缘”,乾隆初期“宜兴二史”史承谦、史承豫的母亲即著名词人徐瑶之女。
从以上家族间嫁娶关系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吴、储、陈、万、史等以各自家族为中心,形成各自的婚姻圈,而每个家族的婚姻圈又呈现交集,在共时性内,形成以某一家族为原点,向四周辐射、绾结的态势。如以陈氏为中心,吴氏、储氏、万氏聚合为姻亲族群,以储氏为中心,陈氏、史氏、徐氏又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姻娅家族联盟。虽然,因家族文献材料散缺的缘故,我们尚不能全景式地展现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间繁复错杂的姻亲图谱,但就以上陈氏、储氏、万氏、吴氏、史氏等阳羡文化家族交相迭错的联姻形态,已俨然形成了一张姻娅网络,联结着来自不同家族的阳羡词人。由此不难看出,清代阳羡词人不仅具有地缘关系,而且还保持着深厚的血缘、亲缘关系。
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通过门第对等的家族联姻,实现了共同处于同一社会结构的文化追求,缔结了一个以亲缘和血缘为纽带的亲族群。清代阳羡词文学集群的产生,正是基于这种姻亲关系。阳羡家族文学力量因联姻而得以凝聚,因创作实践而得以发挥,最终成就了清代阳羡词学的辉煌。
二、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所形成的词文学氛围
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反映了家族生存的一体化趋向和强烈的类聚性生特征,这是家族间根据自身要求所进行的文化选择。家族间如此相攀互联,持续得越久,所历世代越多,则越有利于家族的繁衍、家风与家学的培育,家族文化的积淀越淳厚。地域之内,联姻关系成为形成人才渊薮的内在机制;家族之间,随着亲缘和人文的渗透,姻娅网络就形成一个意味独特的人文空间和共同体。阳羡文化家族的词创作的兴趣与创作取向,正是在联姻所构造的这一人文空间和共同体中逐渐生成发展的。
阳羡文化家族往往都具有一门风雅、词人辈出的文化特征。陈氏家族有陈维崧、陈维嵋、陈维岳、陈宗石、陈维岱、陈履端、陈枋等,储氏家族有储福宗、储欣、储贞庆、储方庆、储国钧、储秘书等,万氏家族有万树、万锦雯、万廷仕、万松龄等、徐氏有徐荪、徐喈凤、徐翙凤、徐瑶、徐玑、徐洪钧等。同时,这些家族间姻亲关系错综,如万廷仕与陈维崧为表亲,与万锦雯为从叔侄,又与万树为堂亲;徐荪既是徐喈凤兄弟的叔父,又是陈维崧的表姑夫。然而,正是陈氏、储氏、万氏、徐氏、史氏词人共同吟酬创作,才促成了清代阳羡词兴盛的局面。清代阳羡词文学创浓厚作氛围,正是在家族间所形成的联姻关系中勃然兴发的。这种家族姻娅联盟,就是一片丰沃的词学土壤。
我们不妨转换一下视角,以储氏家族联姻脉络为路径,从时间流程上进一步纵向观照阳羡词文学氛围的流变。由此可以发现,顺康之际储贞庆、储福宗、储欣等与史惟圆、陈维崧等多有唱和,文学交往密切,雍乾之际储氏后人储国钧、储秘书叔侄与史氏后辈史承谦、史承豫则过往甚密,时相吟咏酬和,以储氏、史氏为核心,又形成了阳羡家族姻娅圈中另一个值得重视的词集群。而不同时期储氏、史氏词人的递相汇聚,足以说明联姻所形成的文学环境具有多么深厚的影响。显然,雍乾之际以史承谦为首的阳羡词人群,是联姻所构造的文学环境对家族文学力量的再聚合。而这一群体的核心人物史承谦,亦是姻亲延绵与文化渗透所胚育的重要词家。据严迪昌先生考证,史承谦系史惟圆从侄曾孙,徐瑶之外孙,史惟圆与徐瑶父徐喈凤,皆为清初阳羡派名家,徐瑶亦有《桂子楼词》《双溪泛月词》,与史承谦祖父史陆舆为同辈姻亲[4]231,史承谦所置身的词文化氛围由此可察。
联姻还有助于家族间在道义上彼此扶持,在政治、文化上共同发展,激发并增强集体忧患意识。这种精神一旦凝结为地域人文传统,必然会成为家族文人自觉的精神选择,进而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自晚明以来,阳羡联姻家族间就积淀着崇尚气节的清流之风,陈于廷、汤兆京、史孟麟等,既为姻亲,又同为东林党中的刚介之士,抗争阉党尤为坚决。清兵南下之际,阳羡卢氏、陈氏、潘氏、万氏、储氏等联姻家族同仇敌忾,自发组织抗清义军,抵御侵略,诸族都有大量遇害或牺牲的士人,人数之巨居于江东前列。阳羡姻亲家族间的这种忧患精神,随着联姻网络的铺衍,逐渐渗透到阳羡家族文化血脉之中,影响着清代阳羡词人,形成“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
清代阳羡词人是清词史上尤擅拈大题目出大意义者。特别是清初的阳羡词人,对明清易代历史现实的反思,“显得醒豁明朗,主题宏大而集中”[5]125。陈维崧《夏临初本意,癸丑三月十九日用明杨孟载韵》,以词体写作“甲申”三十年祭,表达故国之思,最为典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心态,并非独陈氏一人所有,而是清初阳羡文化家族的集体情绪。陈维崧和他的姻亲史惟圆、曹亮武、蒋景祁等人,还有题咏“虎丘五人之墓”词,及吟咏“题《钟山梅花图》”词等,都是群体性悼家国沦丧、寄托故国哀思的重要作品,是阳羡联姻家族的忧患意识的艺术再现。阳羡词人擅拈大题目出大意义还在于,具有敢于表现清初社会民生的现实主义精神,汤恩孝《念奴娇·江南奇旱,时抚臣奏欲告籴湖广而楚中荒疏复至》、史惟圆《沁园春·十月初五纪鬼声之异》、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等都是哀民生艰辛、世事艰难的优秀词篇。雍乾之际的阳羡词人,虽无大题目可拈,但仍能坚持“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史承谦《采桑子》(郁轮袍曲当时谱)、储国钧《梦横塘·晓行》、储秘书《风入松·芜城秋感》、任曾贻《甘州》等作,在感怀、羁旅中直视自我境遇,抒写才人失路、仕途潦倒的失意之情,反映被盛世所弃的寂寞寒士的真实心态,具有一定的现实精神。虽其题材未可称重大,亦不以悲慨激荡见长,但置于难有萧骚凄怨之音的雍乾词坛,亦可视为蕴含现实意义之作。
新生的姻缘联系叠加固有的地缘关系,使阳羡文化家族间建立起超越地缘交往的更为稳固亲密的结盟关系,联姻网络中核心文学人物的影响力也更为直接而深刻。曹亮武由诗转词的创作转型最为典型。曹亮武曾与陈维崧一起受业于侯方域,初涉文坛时以诗文创作为主,并不喜词。陈维崧曾言:“南耕与余少同学,长以诗文相切劘,余好为长短句,数以咻南耕,南耕颇薄之,弗肯为。”[6]然而,当陈维崧宗法辛苏,大力实践以诗为词、以词存史之后,曹亮武也受之影响,由诗转词,尝试作纪游及他词数十篇。初学词者,往往从仿婉约情韵起步,而曹亮武作词之始,就自觉以诗为词,陈维崧称其“益奇绝有宋人所不及者”[6],其词语言健举洒脱,词情沉郁,绝少柔媚之态,显然是受陈维崧词的艺术启发。
在联姻所构造的新的人文空间里,阳羡词人形成了融通无间、共同交流、知音相赏的状态。清初阳羡词家中隐逸色彩最为浓重的史惟圆,既是陈维崧的姻亲,又与之有三十年文字深交。据陈维崧《蝶庵词序》载,史惟圆与陈维崧曾探讨彼此的词风个性,“譬之‘子’,子学《庄》,余学屈焉,譬之‘诗’,子师杜,余师李焉”[7]。由此可以推想,二人之间必数次深入交流,最终各取所长,形成交相赏契的审美氛围。这也就不难理解,陈维崧为史惟圆《蝶庵词》作《鹊桥仙·蒙城舟中读云臣蝶庵词》,“读完半卷蝶庵词,吹铁笛、洒然而去”。陈维崧《乌丝词》刊刻行世不久,史惟圆《沁园春·题其年乌丝词》便随之问世:“将古人诗,比似君诗,惟髯绝伦。更倚声写句,镂冰雕玉,风樯牛马,牛鬼蛇神。年事蹉跎,交游零落,短褐赢僮逐路尘。愁凝处,纵才如云锦,不疗饥贫。”《鹊桥仙·蒙城舟中读云臣蝶庵词》《沁园春·题其年乌丝词》成为阳羡家族姻娅圈中词人共享而激活创作的典型作品。史惟圆又有《沁园春·为雪持题像》,为追和储贞庆《沁园春·自题画像》而作,其中“共钓徒词客,相对婆娑”之语流露出知音之赏,亦可视为阳羡家族姻娅圈中词人交流创作的重要表现。而随着时代的远去,词集的散佚,以上文字亦成为了解阳羡词人创作现场化特征的文学史料,弥足珍贵。
三、联姻关系网中的清代阳羡家族词人集群
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之间的词人们,通过家族联姻关系而得以再聚合,分散式的“一门风雅”由此转变为亲族相系的“数门联吟”,形成家族集群式的联袂创作的状态。家族文人本来就是地域文学的重要创造者,而一旦形成联姻关系,以之为基础的新词人集群,无疑成为引领清代阳羡词学发展的更为强劲的力量。
清初阳羡词派的诞生,是阳羡文化家族以联姻关系为纽带聚合的最为典型的例证。阳羡成派的过程中,除了文学史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时代风云际会与地域文化传统等影响因素之外,更为直接的、关键的原因在于众多联姻家族的积极支持和参与。陈维崧“僦居里门近十载专攻填词”后[8],陈维崧弟陈维嵋、陈维岳,从侄陈枋、子陈履端等,陈维崧表姐夫史惟圆、表弟曹亮武,以及陈氏的姻亲吴本嵩、吴梅鼎、蒋景祁、董儒龙、任绳隗、徐喈凤、万树、万锦雯、万大士、储贞庆、储福宗等,加之任、万二氏的姻亲史鉴宗等,纷纷积极响应,共同酬和创作,晨夕往还。他们访梅以词柬之,观牡丹以词邀之,赴约不成以词示歉,怀念朋友以词表意,离别亲人以词感怀,借物抒情以词明志,于是有了“东溪修楔”、“石亭访梅”、“荫绿轩观牡丹”、“钟山梅花图题咏”等诸多寄情抒怀的同题唱吟活动,形成“或一姓而联唱骚坛,或同声而搴芳莲社,一时作者俱为天际朱霞”[9]的局面。据稽考,从康熙元年至康熙二十年,阳羡文化家族词人群体性的唱和活动计有四十余次,以至于“人各有集,家各有集,即素非擅长,而偶焉寄兴,单辞只调,亦无不如吉光片羽,啧啧可传”[8],当时即有“近时倚声一席,独推阳羡”[10]的赞誉。而后,徐喈凤子徐瑶、侄徐玑,曹亮武子曹臣襄与路传经、路念祖兄弟,及徐氏、路氏的姻亲潘祖义、潘宗洛等,亦投身清初阳羡词坛的唱和活动之中,或继续保持阳羡派的悲豪疏朗,或另觅路径,追求清疏淡逸的艺术风貌,进一步丰富了清代阳羡家族词人基于一定联姻关系而自为集群的文学传统。
雍乾之际阳羡词的“界内新变”,亦是以具有联姻关系的家族词人为主体的。史承谦是这一时期阳羡词坛的领军人物。史承谦词博取众家之长,兼有众美,陈廷焯誉之为“一代词手”[11]3737,可与清初陈维崧、朱彝尊相比肩。这一时期围绕在史承谦周围,与之多有唱和的词人包括:史承谦弟史承豫,任氏任曾贻,储氏储国钧、储秘书叔侄等。雍乾之际的阳羡词人群,规模与名气都不及清初阳羡派,这些词家虽拥有深厚的家族文化血脉,但大都属于盛世词坛的寂寞之人,科第仕途上无大作为,其家族发展也已渐入衰微。但在乾隆初年以醇雅为宗的浙派风气之中,这一群体的词学理论及其创作实践却具有补救词坛、稍振词风的意义。
史承谦与他的词友,既远阳羡,又不近浙西,对词坛主流浙西词多有反思,明确指出词坛典范当推小山、少游、美成诸人,词体不同于诗体,应守词情、词韵之正格:“诗歌词曲,各有体制。风流婉约,情致缠绵,此词之体制也”[12],词的语言以自然为宗,但自然要从琢磨中来,“绚烂之极乃造平淡耳,若使语意淡远者稍加刻画,镂金错绣者渐近天然,则骎骎乎绝唱矣”[13]。显然,史承谦等人坚守词之婉约本色,以异量美的视野,积极疗救词作疏离于情的弊病,史承谦《小眠斋词》则是这一词学理论指导下的代表性创作成果。《小眠斋词》“于古人不屑屑句摩篇仿,而一种幽情逸韵,流于笔墨之外,盖能自出杼轴,而又得体裁之正者”[12],呈自然本色之态。史承豫、任曾贻、储国钧、储秘书等,词风大多和史承谦相近。雍乾之际的阳羡词人群,既非清初阳羡派的延续,又有别于当时一唱百和的浙派,虽仅三四人之力,亦能自出机杼,挽时风众势之所趋。是继清初阳羡派之后,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以姻亲为纽带进行集群式词创作的又一重要表征。
嘉道以后,清廷衰落,江南频起战事,阳羡文化家族经兵火摧残,日趋式微。乱世之中,仍有蒋氏一族续承阳羡词学传统,并得到妻族储氏的积极支持。蒋氏一门祖孙、昆季、胞妹并善讴吟,延续并彰显了清代阳羡词学的家族特征。蒋氏家族的重要词人包括:蒋萼,字跗棠,自号醉园,性闲静寡,自称为竹山后裔,仿蒋捷以诗词自娱,有《齑臼词》。蒋萼取法先辈陈维崧、周济之词法,既有悲慨之语,又有柔媚之言,以词抒写性情,风格多样。蒋彬若,字次园,蒋萼弟,有《替竹盦词》,艺术风格与其兄多有相近。蒋萼妻储慧,字啸凤,有《哦月楼词》,存词十余首,大多为闺帷内的侧艳之词,织丽有余,风韵不足。储慧父为蒋萼之师,亦有作词雅兴,并与储慧兄及蒋萼、蒋彬若时有唱和,惜因战乱,其词集已不传。蒋萼子蒋兆兰,字香谷,亦擅倚声,曾参加寒碧词社、鸥隐词社,有《青蕤庵词》前后两集。蒋兆兰还是民国初年重要的词论家,著《词说》一卷,总结词体特征、阐述词体流变、申发各家各派的艺术风格,颇有见地。
民国九年(1920)十二月,蒋兆兰和徐致章创立了白雪词社,社址设于宜兴西氿之滨,主要成员有储凤瀛、储蕴华、徐德辉、程适、储南强等。徐致章,字焕珙,光绪十四年举人,著有《拙庐诗词稿》。储凤瀛,字印波,光绪二十九年举人,著有《萝月轩诗词稿》。徐德辉,字倩仲,光绪二十八年举人,著有《寄庐诗词稿》。储蕴华,字朴诚,号餐菊,光绪二十九年举人,著有《餐菊词》。程适,字肖琴,号蛰庵,著有《蛰庵类稿》。储南强,字铸农,贡生。白雪词社每月集会一次,拈题作词,咏物写景之作较多,如“冻瓜”、“咏兰”、“牡丹”、“美人蕉”、“秋海棠”、“秋虫”等。有时分拈里中古迹为题,如“蠡墅”、“计山”、“胥井”、“善卷洞”、“西施洞”等。有时写节日活动,如“人日在双溪草堂雅集”、“重九活动”、“三月三日禊饮”、“纪念东坡先生生日”等。蒋兆兰曾将该词社同人的作品汇编成《乐府补题后集》,甲编有词147首,乙编有词157首,于1928年出版。[14]50-51储凤瀛、储南强为储国钧、储秘书的后人,蒋兆兰为蒋景祁后裔,他们皆承先辈遗韵,以结社和词作致以雅兴,显示出地域文风与家族传统的交融延续,具有超越时间的文化活力。
当然,阳羡联姻关系网中连接着数家、数辈的家族词人,于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词集群,并非层层相因。他们的创作实践,随着时代风会的变化、词史演进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并投射于清代阳羡词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顺康之际的阳羡派,源于深切的时代感受,欲振起一代词风,开创了清词崇意主情的传统,重视词之立意,偏重抒泄悲情;康熙中期的徐瑶、徐玑、路传经等人,适逢战乱远去、盛世渐显,虽仍承沿阳羡派崇意主情一路,但以表现闲情为主,致力于清疏词境的营造,因此这一时期的阳羡词既不劲急也乏精湛;迨至乾隆初年,史氏、储氏取径北宋诸家,强调词情婉约缠绵,虽与清初阳羡派先贤“重情”传统暗合,但其内质已大相径庭,他们更加重视词艺的精致、情韵的悠长,与豪放悲慨的阳羡派相比,气魄殊异。晚清蒋、储二家之词乃至民国初年的白雪社词人之作,虽未能形成独立的艺术风格,亦对构建清代阳羡词学作出了积极贡献,是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所营造的词文学传统的最后回应。
综而言之,联姻既是清代阳羡文化家族的社会交往,又是其重要的文化行为。家族文人借助联姻关系,自为集群,通过创作实践,确立一定的声誉和地位。事实上,文化家族联姻,并不仅见于清代阳羡,而是普遍存在当时整个江南地区,如吴江沈氏、叶氏的联姻,阳湖庄氏、刘氏、钱氏的婚姻,苏州潘氏与汪氏、陆氏的姻娅关系,都曾深刻影响了清代江南文学的发展。这说明,对于文化家族而言,联姻早已超越了“上以事宗庙、下以事继后世”的社会学意义,而演化为一种积极的文化行为。这种联姻,所稳固的不仅是双方的地位、利益,还增强了家族间的文化联系和力量,是家族依照自己的文化需要所建构的独特的交往关系,这必然会对彼此的家族文学创作,乃至地域文学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更进一步说,文化家族联姻对于形成地域文学优良的生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最显而易见的是,文化家族联姻有利于衍生、培育优秀文学人才,形成地域性人才渊薮。联姻对家族文学、地域文学发展的内在的影响,则是使各自为政的家族内部的文学创作兴趣在新的环境中得到激发,文学活动自身的组织能力由此得以增强,刺激或改变着文学创作生态,催生出富于鲜明家族文学特色的创作成果。基于联姻关系的清代阳羡词文学集群正是一个典型,其多个家族联袂创作的盛大局面,是何等辉煌,至今仍吸引我们回望,吸引我们对之加以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