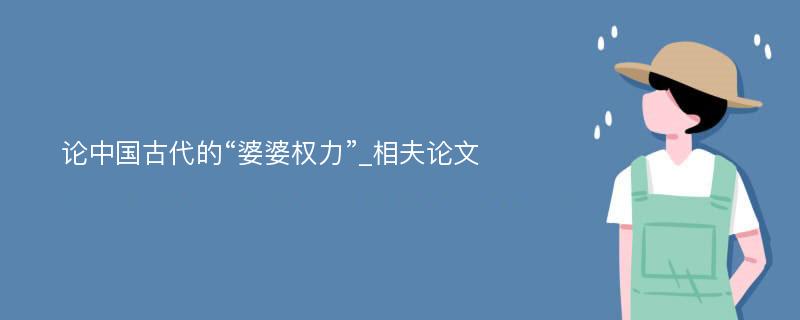
论中国古代的“婆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婆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3)01-0102-07
“多年媳妇熬成婆”,这是传统中国女人一生的理想,也概括了她们全部的人生命运。由于中国的父权本质上既不是夫权,也不是父权,而是祖权——祖先赋予最年长、最有经验、也最有人格权威的男性,代表他们管理家族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与权利,所以,中国的母权本质上也不是妻权或母权,而是婆权。解读她们“成婆”的历史,就是解读自进入父权制以后中国传统文明的另一半的历史。
一、婆权的产生
中国古代的婆权是伴随着父权制而产生的副产品,它与父权制一样,也是中国独特血缘群体共有制的产物。
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中国的妇女一直都是不可或缺的劳动者和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撑。“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男耕女织生产生活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男女双方在生产领域中拥有同等重要地位,他们只能“男主外,女主内”,相互配合,共同劳作,方能养家糊口,传宗接代。作为农业经济中主要的生产资料的土地,是全家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它的所有权只能为血缘群体所共有,由此形成了“对内实行血缘群体共有制,对外才具有私有性质的”血缘群体共有制形态。这种独特的血缘群体共有制,不但从根本上取消了血缘群体内任何成员(无论男女)拥有个体财产私有权的可能性,还将他们牢牢地束缚在家族之中,迫使他们必须以家族利益为根本利益。在此基础上诞生的父机制,只能是以家庭利益为重,强调男女两性和合的父权制,而不是基于西方个体私有制下偏重两性对立的父机制[1]。这种父权制固然也将女性置于“阴”的卑下的地位,并剥夺了她们的家产管理权和继承权,但它却一直在强调她们“主中馈”的社会职责,并相应赋予她们“贤内助”的社会地位。因此,在阴阳和合的大前提下生成的男尊女卑,是一种夫唱妇随式的男尊女卑[2]。尤其对广大农夫村妇而言,尽管他们世代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或许终生都与“帝力”——国家政治体系无涉,但却并不妨碍他们构建家内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王国,正是这一个个微小的王国,像一粒粒水滴,聚成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也构成了家本位国家的根基。
由于血缘群体共有财产是按照父系传承的,加之累世聚居地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及由此而产生的祖先崇拜意识,使得核心家庭并不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横向的夫妻关系也不是家庭关系的主轴。“以父尊子卑为经,以夫尊妻卑为纬”编织而成的父机制家族,以及按父系聚居的血缘群落,才是整个社会的基石。在累世聚居的家族式父机制王国中,父家长们是代表祖先,为着血缘传承的长远利益而行使父权的,因此,这种父权的核心既不是夫权,也不是父权,而是祖权——祖先赋予最年长、最有经验、也最有人格权威的男性,代表他们管理家族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与权利。夫唱妇随,由女人分管的世界,自然只能是男人世界的翻版,就像林太乙形容的:“女人逍遥自在的地方是厨房,那是男人从来不去的。但在厨房里也有复杂的阶级组织,一个女人凭她在家里的地位、年龄、丈夫有没有出息,决定讲话大声、小声或索性不出声。”[3](P8-9)是一言九鼎还是人微言轻,话语权就是统治权,不言而喻,统御阃内王国的,通常也都是家族内最年长、最有经验、也最有人格权威的女性——婆。中国自古之“重母抑妻”实质就是“重婆抑媳”,是父权制对阃内集权的保障。所以“‘被压迫女性’这一个名词,决不能适用于中国的母亲身份和家庭中至高之主脑。任何人不信吾言,可读读《红楼梦》,这是中国家庭生活的纪事碑。你且看看祖母贾母的地位身份,再看凤姐和她丈夫的关系,或其他夫妇间的关系,然后明白治理家庭者究为男人抑或女人。几位欧美的女性读者或许会妒忌老祖母贾老太太的地位,她是阖家至高无上的荣誉人物,受尽恭顺与礼教的待遇”[4](P131)。
在“以父尊子卑为经,以夫尊妻卑为纬”编织而成的父权制家族基石之上,是“以君尊臣卑为经,官尊民卑为纬”编织而成的君主专制政治体系,即“以家族为本位”的拟血缘国家。国犹如家族的放大,皇帝不过是一国之父——统领大大小小血缘与拟血缘群父家长的总家长;皇后不过是一国之母——辅佐君王管理江山杜稷大家业的贤内助。主外的父家长们:皇帝以天下为业,官僚以国家为业,缙绅以乡里为业,族长以家族为业,家长以治家为业。而这些“业”,不过都是他们兴家旺族、光宗耀祖的手段而已,即所谓“家大业大”。与这些父家长们协作配合的贤内助们,也必然要夫唱妇随地以“家族大业”为己任,这便意味着家族之“业”有多大,她们“主中馈”、“相夫教子”的职责、权力也就有多大。家事与国事间、公事与私事间,因此没了明确的边界。只不过因为“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主外”的男人们的专利,他们造出“牝鸡司晨,惟家之索”的古训,是为了警告女人不要“女代男职”涉足“男人的领域”,并不是为了把她们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同样也是本着家族利益至上的根本原则,当主外的父家长黯弱无能或英年早逝而又后继乏人时,主内的女人必需责无旁贷地“母代父职”。尽管这只是权宜之计或特例(一旦新一代父家长成熟了,便要归政于他,否则,就是“牝鸡司晨”,不容于天理人伦了),但有趣的是,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史算下来,竟有约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全部或部分地“母代父职”——“女主统治或男女主共同执政!”[5](P104)即使在皇帝大权在握时期,“主内”之“宫闱”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辅,亦有内助,治乱所由,盛衰从之。”(《魏志·郭皇后传》)皇家尚且如此,官僚、百姓之家又怎能例外?历朝历代哪里断过“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代子求官,为夫诉屈”(《颜氏家训》)之类的现象!所以,自古“妇者”,一向都是“家之所由盛衰也”。难怪林语堂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倘把中国人的生活再加以更精密的观察,几可否定流行的以妇女为依赖的意识。中国的慈禧太后,竟会统治偌大一个国家,不问咸丰皇帝的生前死后。至今中国仍有许多慈禧太后存在于政治家的及通常平民的家庭中,家庭是她们的皇座,据之以发号施令,或替她儿孙判决种种事务。”[4]以此观之,无论从狭义还是广义的政治角度看,“主内”的女人都不是局外人。她们一直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乃至左右着家国政治。
要言之,婆的权利是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血缘群体共有制及父家长制的产物,它是父家长专制集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至皇族,下至百姓,正是男女家长们的一阳一阴、一外一内的密切合作,才共同演绎了数千年中国家国同构的历史。
二、婆权的获得
如果将“婆”定义为女主的话,那么,女主亦如男君,若想做称职的婆婆,获得婆的权力与权利,就必需大体兼备德、能、勤、绩之综合妇道。
德。自古“女子无才便是德”,要求女子无才,是为了遵男尊女卑、男外女内之制,从而抑制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才武略,使其永远不能与男子比肩,永远臣服于男子的权威之下。这便是父权制为女子规定的“德”的标准,其核心仍是一个“孝”字。孝为治国、齐家之本。“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孝经》)大大小小的血缘与拟血缘群体的父家长们,若都能做到爱下聚众,永葆血脉的繁衍与传承,便是对祖宗最大的孝敬,对社会安定最大的贡献,自然也就是最有德之人。“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她们在家从父,以母为重;出嫁从夫,以姑为重,“譬如读书出仕,劳于王事,不遑将母;死于王事,不遑奉母。盖忠孝难两全。全忠不能尽孝,犹事姑不能事母也”[6](P559)。但若尽忠于公婆,就如尽忠于皇家,即使不一定得到功名利禄,最起码可以显亲扬名,等于尽孝于父母。因此,在“孝德”上,并无男女之别。女子的事业在婆家,嫁做人妇,她们必须具备温柔卑顺、纯一坚贞的德行,才能唯夫命是听,才能心甘情愿地成夫之德,济夫之业,恤夫之难,说到底,才能以夫家的祖宗基业——家族的整体利益为己任,是为至德,也是至孝。家有贤妻,如国有良相,倘升任女主,便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但即使贵为母后,也应守妇道本分,不能牝鸡司晨,以符“家无二尊”之旨,以免“夫妻持政,子无所适从”之弊。御下亦需克己奉公、公平正直、恩威并施、以理服人,如是,才能上对得起祖先,下对得起后代,中无愧于己心。倘若纵一己之私,逞婆婆之威,有淫而无恩,或许也能横行一时一世,却必然埋下败家的祸根,也必然有愧于列祖列宗。是故“妇德”居“能、勤、迹”之首,“四德备,虽才拙性愚,家贫貌陋,不能累其贤。四德亡,虽奇能异慧,贵女芳姿,不能掩其恶”[6](P355)。
能。女主之能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能,而是主中馈、相夫业、育子女、赡公婆、敬祖宗、睦族众之能。治家亦如治国,只有德心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与德心相配的才、学、识,方能将德心落到实处。大体说来,妇之能包括两方面,一是天赋之能,又当首推育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媳妇不过是家族生存、融合和发展的工具而已。倘不能举男,不管责任在谁,媳妇都被认为是天生无能之辈,当属“七出”之列,即使不把她打发回娘家,也难免备受冷落。更主要的是,对女人自身而言,她终生的理想就是多年媳妇熬成婆,无子何以成婆?只有做了母亲,她才能有功于夫家,才能有望“母以子贵”。因为丈夫能够休妻,儿子却只能孝母。“夫为妻纲”确实是中国女子无法挣脱的宿命,但儿子却是她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唯一真正属于她的、并寄托着她的全部理想和希望的活的资本,也是她摆脱卑下地位、成为“人上人”的唯一有保障的投资。故中国传统媳妇能够守寡,却不堪丧子。其次才是心灵手巧、精明能干之类的天分,才拙性愚女人,心地再善良、再温顺听话,虽不妨碍她当母做婆,却让她难以当家执政,就像《红楼梦》中愚弱的邢夫人。二是习得之能——贤能。这是一种中国式的、以血缘群体为本位而非以个体为本位的才能。它要求女子既卑弱曲从、温良体贴、恪尽职守,又通情达理、明辨是非、顾全大局,这种本领是从出生就开始学习实践而成的。《诗经·小雅·斯干》曰:“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声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贻罹。”除极少数天性贤能者外,绝大多数人的贤能都是后天习得的。一个女人只有在家从父时,学好为人妻母之道;出嫁从夫时,恪尽为人妻母之职;娶媳抱孙后,方能成为子孙后代之师——一个称职的婆婆。主内本身就是一门学无止境的人生艺术!它要求婆婆不仅要成为调适人际关系的高手,还要具备“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度量。婆的典范莫过于《野叟曝言》中的水夫人,她“只消一言出口,可令她身为卿相的儿子下跪于她的面前;而一方面运用着无穷智慧,很精细的照顾全家事务,有如母鸡之护卫其雏群。她的处理事务用一种敏捷而慈祥的统治权,全体媳妇是她的顺从的臣属”[4](P132)。
勤。勤居德、能之后,也是妇人持身、主内不可或缺之本。受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制约,“一女不织,将受之寒”,倘若没有女子的主中馈、务桑蚕、赡公婆、育子女,不仅家不能为家,国亦将不国。女子之勤,实在是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勤。所以,班昭才在《女诫》中谆谆教导天下女子:“生女三日,……弄之以瓦,……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晚寑早作,不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然而家人是否能齐心协力劳作,主要还看家长能否身先士卒。“男胜耕,悉课农圃,主人身倡之;女胜机,悉课蚕织,主妇身先之”[6](P314)。在劳动者家族中,成婆只不过如同从小跑升任主管,也许可以少受些累,但却要多操不少心。劳力者如是,劳心者也不能例外,敬姜身为贵胄之母.犹纺绩不缀,她的纺绩已非为了生计,乃是为了以身作则,向儿子明示“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的治家安邦道理[6](P359)。家业越大,操心事也就越多,主内的责任也就越重。“是故天子公侯,王后夫人”,都“莫不旦暮忧勤,各修其职业”[6](P360)。这是一种脑力与心力之勤,而不是体力之勤。比如贾府内,表面上看是能干的王熙凤在持家,实际上,却是贾母在掌舵。她那阖家至高无上的荣誉地位、享尽子孙的恭顺与爱戴的福气,以及关键时刻排忧解难、拍板定论的功力,都是用她一生的辛勤换来的。没有耕耘,哪来收获?“廿年媳妇廿年婆,再熬廿年成太婆”,不经一个“熬”字,如何能当成老祖宗!但勤也必需与德、能相配,若只勤却缺德或少能,也当不成好婆婆:缺德者,越能越勤就越不得人心;少能者,再德再勤也只会大权旁落。
绩。既是对一个女人德、能、勤的综合评估,也是她一生的业绩、口碑与功名。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古代妇女追寻“多年媳妇熬成婆”的理想,并非为图一个好婆婆的虚名,而是出自自身生计的需求。在这个讲求“德”与“孝”的国度里,好的口碑就是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赖以生存的本钱,也是她们的经济基础。强大文化习俗的力量迫使她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地约束自己的言行,不得不用心良苦地维护自己的名声,不得不一点一滴地积累自己的业绩。首先,女嫁曰归,注定女子的归宿在婆家。娘家,不过是她学当媳妇的寄宿学校。婚姻是合两姓之好,是关系到家族兴盛、光宗耀祖的大事,婆家择媳就是要全面考察她在娘家的业绩——“妇道母仪,始于女德。未有女无良而妇淑者”[6](P347)。所以,若想寻个好婆家——安身立命之所,就必需先在娘家赢得一个好的口碑。对贫家女而言,身强体壮、勤劳朴实、吃苦耐劳就是她最大的资本;而对富家女而言,则是用自己的孝心换来的娘家人力、物力上的支援。其次,嫁做人妇,如同一粒种子被播撒到一片陌生土地上,面对的是夫之家族那一张世代密结的、相互关联的亲情网。“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唐·王建《新嫁娘词》)。欲得意于夫主,必先欢喜于舅姑;欲欢喜于舅姑,必先获爱于叔妹。她只有打点妥当上上下下的关系,才能结成最广泛的联盟,以免孤军奋战之苦和不遗父母之羞。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异家族文化间同化与排异的过程,也是一个相当艰难的磨合与历练过程。唯有待到她如履薄冰地熬成婆时,才有资格凭自家的业绩,获得“主内”的全权。再次,如果说“受气的媳妇”是传统妇女出人头地所必需的投资的话,那么,“熬成的婆’其所拥有的极高的社会地位,及其实际享有的其他民族的“婆”们所望尘莫及的权力与权利,便是对她为媳业绩的最大、最好、最终的回报。但成婆是当家理政的开始,却不是功成名就后的“致仕”。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家族关系越复杂、等级结构越森严,做“管家婆”也就越难。她倘若从此只吃老本,不立新功——坐享其成甚至作威作福,不仅难以博得媳妇真正的孝心,还易造成妇姑勃谿器之势,同样难以确保自己的“生有养,死有祭”。
要言之,婆权既然是父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便是以父系血缘群体利益为重。因此,只有兼备德、能、勤、绩者,方可成婆之典范,获婆之全权。四者缺一,都会影响婆的权力与权利的获得。但在实际生活中,就像中国的皇帝都不能保证自己拥有全权一样,即使中国的婆们拥有成“婆”的内在条件,她们也还要受娘家经济、政治实力以及天灾人祸等其他外在成婆条件的制约。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良婆与明君一样难得。
三、婆权的构成与运作
婆的权力主要是由相夫、教子与御媳三种权力构成,三位一体不可拆分。
首先是相夫权,它是教子与御媳两权的基础。父权制赋予女子相夫的职责与义务,同时也赋予了她相应的权力与权利。《白虎通》云:“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至庶人,其义一也。”故“妇人无爵,从夫之爵,坐以夫齿”(《郊特牲》)。夫妻一体,共荣共辱,丈夫的地位,就是自己在社会与家族中的地位,所以,相夫是她们嫁为人妇后的第一要务。她们之所以尽心竭力地孝公婆、和妯娌、侍叔妹,不仅仅为了讨丈夫之欢心,更为了免除丈夫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全心全意地养家糊口、显亲扬名,从而夫贵妻显,使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与声誉得到提高。在父权制保障下,妻子们大都以督导丈夫为己任,上至长孙皇后,下至乐羊子之妻,皆因相夫以正道,不仅受到丈夫的尊敬,而且成为全族、全国乃至全体后世妇女们效仿的楷模。中华民族一向是讲求实际的民族,在血缘群体内部,亲尊与贵贱从来都是互为条件的。谁最有公心、最有能力、贡献最大——谁最有利于家族发展的长远利益,谁就最有主持家政的权力与威严。所以,倘助夫有方,持家有道,虽上有公婆,也不妨碍她成为实际的家族主妇。反之,若得不到父家长的认可与尊敬,即使名分为婆,其教子与御媳的权力也要大打折扣。
其次是教子权,它既是相夫权的发展,又是御媳权的保障。“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伦理道德之所以一再强调“糟糠之妻不下堂”,恰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妻子地位的低下与不稳固。所以,她们若想成为家族中真正的内当家,还必须通过“教子”有功而“母以子贵”。这样才能将自己置身于“长尊幼卑”的孝道保护之下,从而为自己投下双保险。所以,“生儿”只是当婆的硬件,“教子”才是当婆的软件。若生而不教,儿子不务正业,不走正道,娶了媳妇忘了娘事小,绝了她跻身为婆、母以子贵的理想才是大事。严父慈母式的家庭角色分工,恰好为母亲提供了培育母子深情的天地,多少畏惧于严父的儿子,终生感怀着慈母的恩情。倘若慈母再身兼父教之严,由她一手调教出的儿子,便更具有中国式的“恋母情结”。而中国儿子们“恋母情结”的浅深又直接与婆权的轻重成正比——恋母越深,责妻越重,所以,婆的最高权威莫过于儿孙满堂的寡母。她上无公婆,中无丈夫,下有孝子贤媳,集祖权、母权、婆权于一身。这样的老祖宗才是真正的女君!试想,倘若有贾公在世,贾母也不会有如此的威风。由此可见,在“孝”文化中,中国妇女“教子”的权力与权利要远远高于“相夫”的权力与权利。所以“牝鸡司晨”、干预朝政都多为母后,为国家栋梁的士宦们,也经常会发出“母命难违”的慨叹。
最后是御媳权,它是集相夫权与教子权之大成的必然结果,也是一个女人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奋斗成果。御媳首先要“择媳”。自古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主外之父为主内之母挑选其“臣属”时,当然要征询她的意见。因此,“七出”中第一条便是“不事舅姑”,不管儿子对媳妇是否满意,只要她不合公婆的意,便可以“不孝”的罪名将她如“退货”般休还娘家。事实上,像《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之妻刘兰芝,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妻子唐婉等,都是由于始终不合其直接主管——婆婆的意愿而被“退货”的。尤其是在传统的大家族中,“主中馈”的婆婆就等于是主管内务的“内务部长”,添一门媳妇就意味着增加了一名准“部级干部”,无论从大局利害出发还是出于个人好恶,她都必须严格把好这婆媳关系的头一关。其次,尽管传统伦理一再强调婆媳要相待以情,但婆媳关系毕竟迥异于父子关系。儿子与父亲血脉相联,是父权的潜在继承者;儿媳却与婆婆无骨肉之亲,而且是婆权的潜在争夺者,这便奠定了两代异血缘女人间命定怨仇。一方是苦熬而成的婆婆,终于有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机会,无论是出于补偿心理,还是出于占有欲和嫉妒心,都会让她最大限度地行使婆权,所以,她们的“退休”或“致仕”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谁肯将自己用一生心血打下的江山拱手让出呢!另一方则是初出茅庐的媳妇,她们不得不承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历练。她们未承婆婆生与育之恩,却要替丈夫行孝与养之道(童养媳除外)。一个女人能取悦于另一个女人,已非易事,若能取悦于婆婆,简直就是一种英勇的行为。这就难怪自古婆媳有恩义者寡,有怨仇者众了。如果说针对儿子而言的母权多少还要受到“夫死从子”之规条、母子连心之情感的制约的话,那么,针对儿媳而言的婆权,受到的则是“孝道”——这种文化习俗的社会力量无条件的保障。籍此,昔日对家族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婆婆们,即便有权,大多也只能在媳妇面前颐指气使,为所欲为,“多年媳妇熬成婆”自然也就成了古代中国女人们毕生的理想。
要言之,在由相夫权、教子权与御媳权构成的婆权中,前一个权利都是后一个权利的基础和保障,其权力与权利的大小程度和行使范围,也随着其基础的雄厚与保障的有效而逞递增趋势。但说到底,地大大不过天去,婆权毕竟是父权的产物,它只能与父权如影随形,相辅相成。
总而言之,在血缘群体共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家国同构”的拟血缘国家中,血缘群体与拟血缘群体的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的,阴阳和合则是它们得以长远发展的根本原则。婆权与父权就是这样相伴而生、相随而长的。但构成这个阴阳世界的却绝不仅止于男女:君为阳,臣为阴;尊为阳,卑为阴;贵为阳,贱为阴;强为阳,弱为阴……如此伸发开去,多年媳妇熬成婆,又何止是中国女人的理想与命运?要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当官执政、永葆江山,哪一样不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后“熬”出来的?又有哪一样离得开阴与阳既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的契合呢!
收稿日期:2002-09-20
标签:相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