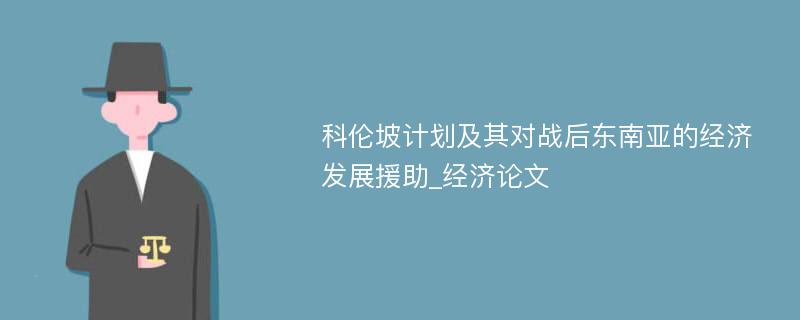
科伦坡计划及其对战后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援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伦坡论文,东南亚论文,战后论文,其对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06)02—0020—06
科伦坡计划是亚洲第一个国际性的、政府间相互援助计划,它起源于1950年召开的英联邦外交事务会议,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久的援助计划之一。该计划最初是为了促进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合作,后扩大成为一个旨在加强亚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际经济组织。早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者如安东尼·巴施(Antonin Basch)等就对这一计划开始关注。随着科伦坡计划的实施,一些学者如哈里·班斯伯格(Harry F.Bansberg)、尼古拉斯·塔林(Nicholas Tarling)等,进一步探讨了西方大国与科伦坡计划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官方及学者对科伦坡计划的兴趣突然增强,他们主要强调澳大利亚通过科伦坡计划对东南亚发挥的影响。丹尼尔·奥克曼(Daniel Oakman)等学者分别从政治、经济、安全以及文化、教育交流等多角度对澳大利亚参与科伦坡计划的原因、过程及其作用进行了探讨。此外,一些第三世界学者,如尼日利亚的阿德莫拉·阿德莱克(Ademola Adeleke)等对科伦坡计划也有深入研究。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科伦坡计划的研究有所涉及,如刘雄对科伦坡计划与美国的亚洲遏制政策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考察,但总体上国内的相关研究还不足①。鉴于此,本文对科伦坡计划的起源、目标、实施的形式及其对战后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合作的影响等进行探讨,并试图揭示科伦坡计划的深层动因及实质。
一、科伦坡计划的缘起
科伦坡计划的提出,与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政治背景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东南亚地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留下了严重的创伤,战后初期的东南亚经济恢复缓慢,人口增长较快,人均国民收入很低,仅约56美元,还不到美国的二十分之一,亟需经济重建。与此同时,东南亚地区的非殖民化正在蓬勃展开,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影响交织在一起,造成政治局势动荡,社会和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加上冷战背景下苏联的政治宣传和共产主义影响在东南亚的扩展,这一切都对西方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利益形成挑战。出于人道主义以及冷战地缘战略、政治、经济等因素的考虑,西方国家希望通过设计一种新的国际合作制度以赢得南亚和东南亚的人心,通过国际合作努力帮助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
战后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使英国和澳大利亚等主要英联邦国家意识到必须针对东南亚提出一种新的地区政策。它们认为该地区社会政治的动荡源于其饥饿和贫困,“东南亚政治问题的关键在于粮食问题”[1]。它们力图通过促进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来构建一种稳定的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1950年1月,英联邦国家外长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召开会议,这是英联邦国家外长第一次聚集一堂讨论与英联邦各国有关的经济、地区事务和国际政治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锡兰和澳大利亚的代表分别提出了建议。锡兰财政大臣杰伊沃登(J.R.Jayewardene)提出一种针对东南亚的英联邦“马歇尔计划”。他强调英联邦应该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贸易区,工业国向农业国提供资本货物,并确保后者的初级产品在市场上的稳定价格。
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利益密切,希望通过某种有美国参加的技术援助形式,发展东南亚地区经济。澳大利亚外长斯彭德(Percy Spender)提交了一份题为“南亚和东南亚经济政策”的备忘录。他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越来越成为该地区的威胁,因此需要国际上努力稳定该地区的政权,改善当地经济条件和提高生活水平,以抵制共产主义的吸引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增加原材料和粮食生产,最终将有利于英国和欧洲大陆。他还建议英联邦富国应该向东南亚提供贷款,同时要争取世界银行向该地区提供技术援助,以及争取美国的支持[2]。这一备忘录成为英联邦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和技术援助的蓝本。
1950年5月,新的英联邦协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悉尼举行, 澳大利亚准备了一份详尽的三年技术合作计划。1950年9月,伦敦会议召开,七个亚洲的英联邦成员国即印度、巴基斯坦、锡兰、马来亚、新加坡、北婆罗洲和沙捞越,都提交了各自的6年发展计划纲要。经过讨论分析,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报告, 即“南亚和东南亚经济发展合作的科伦坡计划”,这份长达100 页的文件构成了科伦坡计划的规章。这在战后的国际合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英国看来,科伦坡计划,将有助于加强英国在英联邦国家的地位,扩大其在整个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3]。1951年12月,英国保守党政府采纳了这一政策。为了争取美国对东南亚经济发展和政治安全做出承诺,以及避免出现由于美国从欧洲撤出援助而导致世界上美元短缺问题更趋严重,英国和澳大利亚等极力拉拢美国参加该计划,以使科伦坡计划成为真正的地区性计划,并让美国承担起更大的资金援助责任。美国的美元援助对于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显得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科伦坡计划的预期目标将难以实现[4]。1951年2月, 美国正式加入了科伦坡计划。到50年代末,美国向科伦坡计划国家提供的所有技术援助,都被视为在科伦坡计划名义下的援助[5]。
科伦坡计划的主体是英联邦成员国和英属东南亚殖民地,后来亚太地区大多数非共产主义国家都同意加入这一计划。到1954年,美国以及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成为科伦坡计划的成员或者伙伴国。到1973年,科伦坡计划协商委员会成员国已达26个,包括21个亚洲国家和5个西方国家,其中以澳大利亚、日本、 新西兰和美国为最大的施援国②。科伦坡计划最初设计期限为6年,但实施过程中数次延长时限, 一直到1980年后才无限期延长。
二、科伦坡计划援助的目标及特点
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对科伦坡计划的提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西方学者,如刘易斯(W.Arthur Lewis)、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罗斯托(W.W.Rostow)等研究了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指出不发达经济的特点主要是农业人口过剩、农业生产效率低、技术设备不足、缺乏科技知识以及资本生成困难等。他们主要集中于探讨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和摆脱贫困的出路,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认为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人均收入低下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而其根源在于缺乏资本和投资。资本稀缺是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条件,而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增长,就需要提供大量资本[6]。他们认为,实现现代化有着一系列的共同因素,包括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工业化、更加完善的管理机构、大规模的发展计划和外来援助。还有学者认为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于西方的技术、开放的贸易政策以及获得外援,同时这些国家的自助也很重要。
从现实和长远意义上来看,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东南亚地区,其发展速度受到两方面的制约,即缺乏熟练的技术人员,以及资本的严重匮乏(无论是国内资本还是外来资金),尤其是资本匮乏成为其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7]。因此,科伦坡计划的两个核心内容就是协调技术和资金援助,主要援助形式是为该地区各成员国的发展项目提供捐助和贷款,提供包括粮食、化肥、消费品等商品,以及一些机械、农业设备、交通工具、试验设备等特殊设备,提供专家和技术人员服务,向该地区国家的学生提供高级技术培训等。领域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主要在农业、交通、卫生、通讯、教育等方面。
科伦坡计划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帮助南亚和东南亚克服、摆脱贫困和不发达状态,提高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经济合作和发展。这不仅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且有着政治和战略上的考虑,因为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对于其自身的社会稳定和自由制度的巩固必不可少,同时也有利于远东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稳定。该地区经济的复兴在世界贸易中居于关键的地位,不仅对于亚洲国家自身,而且对于建立在多边贸易基础上的世界经济的增长都至关重要。在冷战背景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下,科伦坡计划开始被西方国家作为一种有利于实现其在东南亚整体目标的工具。
按照英联邦的设想,科伦坡计划主要是为了解决贫困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相关问题,消除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严重恶化的生活水平带来的威胁。通过该计划,西方的资本和技术援助能够被该地区国家所利用,促进其经济制度发生巨大的变革,使该地区经济和社会得到发展,生活水平得以改善。因为贫困和不发达以及众多的人口,使得亚太地区的非共产主义国家面对共产主义的扩张十分脆弱,经济发展是遏制这一威胁的最为有效的途径。非共产主义政权的巩固有利于提高其抵御共产主义的能力,将能够加强地区稳定、促进贸易和工业发展,促进亚洲和西方的关系和谐。
科伦坡计划一个独特的特点就是其中的合作和互助成分。尽管科伦坡计划由多国成员组成,但其实施以双边主义为基础。该计划是根据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各成员国所提出的具体援助请求而提供援助,所有的援助都是双边基础上通过施援国(Donor)和受援国(Recipient)之间的协商而进行。在科伦坡计划下,各成员国相互之间通过培训援助,进行工程、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每一年来自该地区内部的培训资助一直在上升,专业化的教育和培训制度使该地区各国受益很大。
实际上,所有成员国至少在理论上并没有被分为施援国和受援国,而是设想所有国家都通过一种合作、自助及互助的形式致力于促进该地区的发展,使得科伦坡计划也能够被那些奉行中立主义政策的国家所接受。与同一时期美国向亚洲国家提供的相互安全援助不同,科伦坡计划不需要任何国家立法机构的支持,不反映某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从形式上看,科伦坡计划所提供的援助都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受援国也不要求任何回报,这无疑对南亚和东南亚新独立的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亚洲国家在独立后,一方面认识到其自身的发展迫切需要外来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但另一方面它们普遍对西方国家提供援助的真正动机表示怀疑,对西方援助的附加条件以及其可能付出的政治代价表示不安,而科伦坡计划的提出则以一种不同的特殊形式和方法减少了亚洲国家这方面的怀疑和不安[8]。
在结构和职能上,科伦坡计划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它缺乏集权化的机制和一个固定的组织框架,其基本的政策事务取决于协商委员会。协商委员会也是在磋商、非正式和共识的基础上运作的,它没有决策权力。该地区的经济和其他有关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处理,都通过科伦坡计划协商委员会进行安排,该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委员会由科伦坡计划各成员国的代表组成。该计划的另外一个机构就是设在科伦坡的技术合作委员会,负责技术援助事务。从成立开始,科伦坡计划就没有设立任何永久性的秘书处,这反映了该计划的初衷并不希望在国际社会中缔造一个繁冗的行政机构,而保持一种非正式的双边合作的形式。另外,科伦坡计划也没有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参加。从这两方面来看,科伦坡计划对于地区主义的作用要小于联合国的机构,但该计划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其“开放的地区主义”,与战前“封闭的地区主义”相比更为有利。
三、科伦坡计划的实施及其对东南亚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国内资源不足,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资源等问题。因此这些国家通过引进外资、利用外国援助等途径从外部获取资金是必要的。国外资源的流入,可以解决一国储蓄不足、外汇短缺、资本品稀缺等问题,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从而促进经济发展[9]。在这种情况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针对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状况,试图以外国援助的形式,通过提供同样的要素——资本以及技术,来帮助亚洲新独立的国家,尤其是对那些已经制定了发展计划、准备将所获得的援助进行投资的国家[10]。
(1)资金援助。1950年5月,参加科伦坡计划协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英联邦代表在酝酿这一计划时,就认识到制约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发展规模的两个主要因素在于,缺乏受过专门培训的技术人员和资金的匮乏,尤其是缺乏从国外进口必需商品所需要的资本。澳大利亚外长斯彭德在提交会议的备忘录中,把亚洲的经济不发达视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请求政府在科伦坡会议上为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发展筹集资金。同时,还呼吁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优先考虑亚洲的需求[11]。英联邦国家同意从1950年7月起,提供一项为期3年的双边技术援助,总金额达800万英镑。其中英国提供的资金约为300万英镑,澳大利亚提供了相近的数额, 印度提供75万英镑,其他国家提供的数额较小[12]。
科伦坡计划的资金援助主要是针对该地区各国发展项目提供的赠款和贷款;提供的商品包括粮食、化肥、消费品、机械和设备等。各国提供援助的具体形式也不尽相同。澳大利亚当时是一个资本净进口国,所以起初其资金援助是以商品和服务的形式进行的,主要是提供固定设备和初级产品等。而加拿大则主要是资金援助,其通过科伦坡计划提供的援助中97%是以资金的形式提供援助[13]。英国也承担起向其殖民地,即马来亚和新加坡、北婆罗洲以及沙捞越提供资金援助的责任。在此之前,美国根据其对外援助计划,已经向该地区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1950—1951年度,美国向该地区参加科伦坡计划的国家提供的资金约为7,000万美元。1951—1952年度通过赠与的形式提供的资金约为1.5亿美元。另外,从1950年7月提供的第一笔贷款开始,到1952年12月美国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的资金援助已经达到2.8亿美元[14]。
在科伦坡计划实施的第一个10年期间,所有施援国向科伦坡计划地区提供并被利用的资金援助,估计总额约为22.5亿英镑,几乎占该地区国家新的经济发展实际投入资金的1/4;用于经济发展所需英镑的1/4直接来自于科伦坡计划施援国,而其中约90%的援助来自于美国。这些数字还不包括赚取的英镑余额(2.5亿英镑),也不包括日本支付的1亿英镑赔款补偿, 这两笔资金对于受援国的资本需要极为重要[15]。到1959年6月,由主要的6个施援国提供的援助已经超过60亿美元,其中美国单独提供的援助约为56.6亿美元[16]。可见,该计划在资金上几乎主要依靠美国的财政支持。从1950年到1972年,来自科伦坡计划主要施援国(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提供的外部援助,包括技术援助、资金援助和商品在内,总额约达320亿美元[17]。外部提供的贷款和赠款、设备等, 为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支持,科伦坡计划在两个方面获得了很大成功——即促进和协调了外部资金的流入,以及促进了各成员国内部的公共投资[18]。同时,科伦坡计划的援助有利于保持该地区各国的财政稳定。
除了科伦坡计划的援助外,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援助来源是世界银行。从科伦坡计划开始到1960年6月,世界银行向该地区提供的贷款总额超过了11.07亿美元(3.39亿英镑),仅在1959至1960年间就向该地区提供了8500万美元(3030万英镑)的贷款[19]。这些资金对于战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计划的实施起了巨大的作用。
(2)技术援助。二战后西方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 发展中国家普遍具有二元经济的特征,而技术进步是促使这些国家实现二元经济转型,向现代经济过渡的关键因素;认为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扩散,能够改变其农业部门的技术落后和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局面,有助于改造其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科伦坡计划援助正是基于认为科学、技术和发展能力能够引导穷国摆脱不发达的处境。1950年,科伦坡计划协商委员会伦敦报告概括了这些现代化设想:“这些发展计划,包括使南亚和东南亚传统经济和不发达国家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在来自外国的管理人员、科学家、技术人员的帮助下,以及在其自身人民的不断努力下,这些国家开始采用用于和平目的的先进科学技术,将能够为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物质利益。”[20]
科伦坡计划下的技术援助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有三种形式——提供专家服务、提供培训设施及赠与设备。科伦坡计划通过交流计划、留学教育计划等为东南亚地区培训大量人力资源。1951年7月, 科伦坡计划的发展项目正式实施,而技术合作计划实际上从1950年7月已经开始实施。1950年至 1960年,科伦坡计划成员国和联合国机构为该地区培训的人员超过了25,000人,提供的服务专家约为11,600人[21]。到1963年6月底,施援国政府在科伦坡计划名义下提供的援助总额约达49.35亿英镑,其中包括技术援助、贷款和赠款以及其他[22]。到1970年12月,科伦坡计划共为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72,544名学生及受训者提供了技术培训,向该地区提供了14,102名专家和价值4.795亿美元的设备[23]。
(3)教育及培训。20世纪60年代以来, 人力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越来越受到发展经济学家的重视,甚至有人把它当作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指出:“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决定性要素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24] 因此,科伦坡计划十分重视通过交流计划、留学教育计划等为东南亚地区培训大量人力资源。根据科伦坡计划,从该计划开始实施到1957年,约有1500名学生到英国接受了培训和教育,600名学生到加拿大,375名学生到新西兰,4000名学生到澳大利亚[25]。到1970年12月,科伦坡计划共为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72544 名学生及受训者提供了技术培训[26]。到1980年时,通过该计划培养的学生达35万人[27]。
科伦坡计划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对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计划的影响。从1950年1月科伦坡会议开始,英联邦国家试图寻求一种促进经济合作的发展战略、技术援助以及一种地区方式。1950年的伦敦报告在讨论了战争对该地区的破坏影响之后,提出了该地区各国应该为经济发展制定出现实的长期计划。1950年5 月悉尼会议到9月的伦敦会议期间,英联邦国家各自提出了其6年发展计划。同时还鼓励非英联邦的东南亚国家也制定其发展计划。科伦坡计划尽管没有制定关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总体计划,但是各个国家都力图以一种科学的手段制定出自己的发展计划,为了完成这些计划,各有关国家与其他成员国就资本援助和技术援助进行磋商,建立起双边经济关系,这些对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外,南亚和东南亚各国自身的努力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地区内部各国之间也不断采取措施增加彼此之间的援助,缅甸、锡兰、马来西亚、印尼、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也提供了技术援助。该地区国家经济发展计划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是由区内国家所提供的,该地区内部在技术援助和某些发展基金资本方面进行了互助合作。然而,科伦坡计划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对于其经济关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并影响到了它们之间在发展计划方面的合作。
四、科伦坡计划的实质及其影响
战后西方国家对外援助计划背后的动机极其复杂,既有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有人道主义因素。英联邦的领导人认为在经过战争的蹂躏之后,亚洲也需要像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一样的计划。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科伦坡计划成为针对亚洲的第一个多边援助计划。正如马歇尔计划一样,科伦坡计划有着广泛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不能仅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理解。
作为一种广泛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科伦坡计划优先考虑的是国际安全以及施援国国内的利益需要。澳大利亚外长斯彭德在1950年提出并倡导科伦坡计划援助时,蕴含着很大的地缘政治安全因素的成分。他指出,该计划“不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政策,也是一种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政策”。他希望能够通过科伦坡计划的实施,对亚洲的经济和政治前景施加影响,加强东南亚地区抵御共产主义的能力,确保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28]。科伦坡计划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长远利益,将有利于加强地区合作,促进东西方之间在立场、观念、恐惧、动机、习俗等方面的沟通和理解。它与西方国家的冷战计划结合起来,其显著特征就是“作为扩大西方影响的重要工具”[29]。可见,科伦坡计划实质上成为一种遏制工具,乃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基于战略和安全方面的考虑,把南亚和东南亚视为一个战略整体,目的是促进科伦坡计划地区国家的团结和稳定,力图避免使亚洲的所有国家——英联邦和非英联邦国家落入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和安全势力范围。他们把经济发展视为实现地区稳定、阻止共产主义传播以及开拓未来市场的重要手段。
二战后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援助的条件主要由国际体系的结构和符合规范的价值观所决定。随着欧洲殖民帝国在亚非的崩溃,产生了一系列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些国家贫穷、落后,极其需要发展的资本以消除贫穷。当这些新独立国家加入国际体系的时候,它们面临着按照意识形态划分为由美国和苏联主宰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的形势。在冷战背景下,两个超级大国与其盟友一起,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自己的影响,而对外援助显然就是它们展开这种竞争的工具之一。由西方国家所设计的科伦坡计划,目的也是为了吸引处于亚洲共产主义世界边缘地带的非共产主义政权。对外援助为施援国向不发达地区施加影响提供了途径,同时它也使受援国能够获得发展所需要的外部资金[30]。事实上,这些援助计划的动机乃是国家利益和地区主义的结合,援助常常与购买施援国的产品联系在一起。科伦坡计划施援国的最终目的与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很少考虑受援国的国家发展计划,援助项目缺乏灵活性。出于保持其影响力或符合其自身的过剩资源的特殊需要,以及对于这些项目的重要性认识不同,双方关于援助项目的优先性方面存在很大分歧。援助评估的基础不在于受援国的需求或人口数量,而主要依赖于施援国在受援国的利益大小[31]。对于绝大多数施援国来说,盈利是主要的动机,而对受援国来说,其主要任务是要认识引进国外资源所起的作用,并学会巧妙地利用发达国家输出资源的各种动机,尽量利用有利的条件来引进外资,使之有效地用于经济发展的目标。
尽管科伦坡计划本质上是防御性的,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但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为南亚、东南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进一步密切了施援国与该地区以及该地区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科伦坡计划以其关于发展、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的现代理念,使其成为传播西方价值观的重要手段[32]。在战后的几十年里,科伦坡计划成为亚洲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成千上万的人从该计划中受益。尽管科伦坡计划在规模上不如美国旨在重建西欧的马歇尔计划那么大,但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一个重要媒介[33]。科伦坡计划帮助亚洲发展中国家完成了数千个发展项目、技术培训和培养了大批专家学者。在科伦坡计划的援助下,东南亚地区的农业科技、土地灌溉、电力、疾病控制、环境保护、公路及铁路交通建设、钢铁工业等方面的许多项目和计划得以正常运作,从而使该地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开始得到更加科学合理的开发,国民收入明显增长,粮食产量增加,棉花、橡胶和茶叶等商品作物的产量大大增加,该地区受援国的经济开始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
20世纪70年代后,科伦坡计划的形式不断被仿效,又出现了诸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亚太经社会(ESCAP)、亚洲开发银行(ADP)等双边援助计划和地区性的多边援助机构,科伦坡计划的作用也因此而减弱。像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等地区组织的出现,使人们对科伦坡计划逐渐淡漠。另外,随着东亚经济的繁荣,在技术培训方面需要的外来帮助越来越少。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和加拿大对科伦坡计划失去兴趣并退出,援助基金开始减少,该组织濒临消亡。在1989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名施援国的代表曾经建议科伦坡计划应该“体面地退出国际舞台”。到20世纪90年代,科伦坡计划已经变得模糊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曾经作为该计划施援国的日本和韩国决定采取措施振兴该组织,开始注入资金复兴科伦坡计划。科伦坡计划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之后,在日、韩的倡议下重新获得了生机,其目标在于:把该组织转变成一个泛亚洲的组织,以帮助该地区的穷国从东亚新兴经济国家的经验中获益。日本希望在亚洲国家之间加强更大范围的合作,同时希望像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能够成为更加积极的成员国。在1994年的汉城会议上,科伦坡计划的复兴计划被批准,目标是试图使科伦坡计划成为亚洲内部进行技术专家交换的“南南合作”的主要机构。科伦坡计划的大多数东亚成员国已经成为经济腾飞之虎,不需要太多的援助。这样,该计划决定将目标集中于一些经济最为脆弱的国家——那些最不发达的封闭的内陆小国以及越南等。
注释:
① 国内外关于科伦坡计划的主要研究,参见Antonin Basch,“The Colombo Plan:A Case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9,No.1,February 1955,pp.1—18; H.F.Angus,“Political Aims and Effects:Colombo Plan,”in Political Studies,Vol.3,October 1955,pp.325—344; Harry F.Bansbe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lombo Plan,”in India Quarterly,Vol.15,April-June,1959,pp.130—141; Keith Spicer,“Clubmanship Upstaged:Canada's Twenty Years in the Colombo Plan,”in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25,Winter 1969—1970,pp.23—33; Nicholas Tarling,“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ombo Plan,”in 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Vol.24,No.1,March 1986,pp.259—274; Daniel Oakman,“The Seed of Freedom:Regional Security and the Colombo Plan,”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Vol.46,No.1,March 2000,pp.67—85; Daniel Oakman,“The Politics of Foreign Aid:Counter-Subversion and the Colombo Plan,1950—1970,”in Pacific Review,Vol.13,No.3,October 2001,pp.255—272; Daniel Oakman,Facing Asia:A History of the Colombo Plan,Pandanus Books,2004; Christopher Waters,“A Failure of Imagination:R.G.Cassey and Australian Plans for Counter-Subversion in Asia,1954—1956,”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Vol.45,No.3,1999,pp.347—361; Auletta Ales,“A Retrospective View of the Colombo Plan:government Policy,departmental administration and Overseas Students,”i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Vol.22,No.1,May 2000,pp.47—58; Ademola Adeleke,“The Strings of Neutralism:Burma and the Colombo Plan”,in Pacific Affairs,Vol.76,No.4,Winter 2003—2004,pp.593—610;刘雄,“美国的亚洲遏制政策与科伦坡计划(1949—1958年)”,载崔丕主编《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259页。
② 即阿富汗、澳大利亚、孟加拉国、不丹、缅甸、加拿大、柬埔寨、锡兰、斐济、印度、印尼、伊朗、日本、老挝、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尼泊尔、新西兰、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泰国、英国和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分别于1991年和1992年退出,而越南和蒙古加入,成员国仍然为26个。
注释:
[1] Daniel Oakman,Facing Asia:A History of the Colombo Plan,Pandanus Books,2004,p.73.
[2] Alex Auletta,“A retrospective View of the Colombo Plan:government policy,departmental administration and overseas students,”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 Management,Vol.22,No.1,May 2000,pp.47—58.
[3] A.N.Porter and A.J.Stockwell,British Imperial Policy and Decolonization,1938—1964,Vol.1,the MacmillanPress,1987,pp.63—64.
[4] Arthur Tange,“Political Objectives of the Colombo Plan,”19 March,1952,(NAA:A1838,3004/11,part.1),http://www.pandanusbooks.com.au/online_addenda/PB41B/documents/colombo_ 1.pdf.
[5] Daniel Wolfstone,“the Colombo Plan after Ten Years”,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Vol.33,No.5,1961,p.221.
[6]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
[7] 同[5],pp.219—220.
[8] Ademola Adeleke,“The Strings of Neutralism:Burma and the Colombo Plan”,Pacific Affairs,Vol.76,No.4,Winter 2003—2004,pp.603—604.
[9] 同[6],第413页。
[10] 〈美〉吉利斯等著,彭刚等译《发展经济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81页。
[11] Daniel Oakman,“The Seed of Freedom:Regional Security and the Colombo Plan,”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Vol.46,No.1,March 2000,p.76.
[12] 同[7].
[13] 同[5],p.220.
[14] Rajenda Coomaraswamy,“The Colombo Plan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Vol.19,No.4,Dec 1952,pp.106—107.
[15] 同[5],pp.224—225.
[16] Russell H.Fifield,Southeast Asia in United States Policy,Frederick A.Praeger,Inc.,1963,pp.276—277.
[17] Colombo Plan Consultative Committee,“Toltal Capital And Technical Aid,1951—1972,”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1973,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1973,p.110.
[18] An Australian Correspondent,“Australia's Participation in Colombo Plan,”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Vol.26,No.12,1959,pp.390—391.
[19] Colombo Plan Consultative Committee,“the Colombo Plan Year,”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Vol.31,No.4,1961,p.150.
[20] Commonwealth Consultative Committee,The Colombo Plan for Coope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A Report by the Commonwealth Consultative Committee,London,1950,p.46.
[21] 同[19].
[22] Colombo Plan Consultative Committee Communique,“Colombo Plan:Hard work insid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65 Yearbook,p.55.
[23] Colombo Plan Consultative Committee Communique,“Co-operation and Capital,”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1972,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1972,p.99.
[24] 同[6],第194页。
[25] Mark T.Berger,The Battle for Asia:From Decolonization to Globalization,Routledge Curzon,2004,p.235.
[26] 同[23].
[27] “A New Plan for the Colombo Plan”,available at:http://www.himalmag.com/97mar/f-new.htm.
[28] 同[1],p.74.
[29] Daniel Oakman,“The Politics of Foreign Aid:Counter-Subversion and the Colombo Plan,1950—1970,” Pacific Review,Vol.13,No.3,October 2001,p.257.
[30] 同[8],pp.609—610.
[31] Daniel Wolfstone,“Colombo Plan Issues”,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Vol.34,No.5,1961,pp.267—268.
[32] 同[11],p.68.
[33] Alexander Downer,“Launch of ‘Australia and the Colombo Plan 1949—1957’”,Speech,Canberra,23 May,2005,http://www.foreignminister.gov.au/speeches/2005/050523_ colombo_ pla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