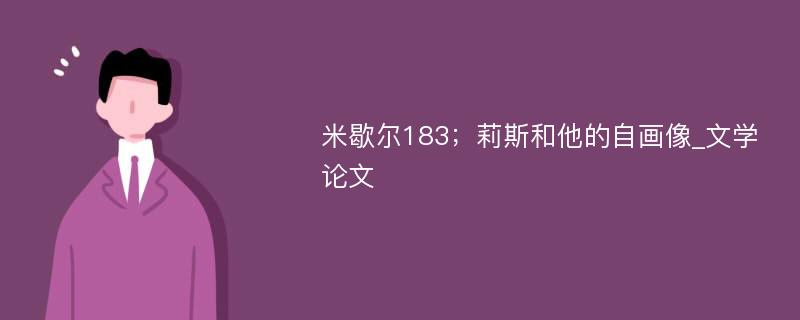
米歇尔#183;莱里斯和他的自画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里斯论文,自画像论文,米歇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米歇尔·莱里斯(1901-1990)这个名字,在中国还是鲜为人知,在法国则是大名鼎鼎,他是法国20世纪的著名作家和人种学家,尤其以其新奇、怪异的自传作品而蜚声文坛。莱里斯是以诗歌创作而踏上文学之路的,青年时代曾参加超现实主义运动,1925年发表了近乎文字游戏般的第一部诗集《幻影》,两年后改写叙事作品,先后发表《基点》和《奥罗拉》,作品笼罩在一种似梦非梦的气氛中。作者运用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法,探索人的潜意识领域,充满了各种幻象,一些同音异义的词语组成了妙趣横生的文字游戏。1929年标志着莱里斯的创作轨迹发坐了转折,他与超现实主义决裂,转向探索写作的哲学意义,对写作的神圣意义和破坏性消解功能进行思考。这个时期,他又对神话和人种学发生兴趣,1931至1933年参加了人种志学家马赛尔·格里奥尔组织的横穿非洲的达喀尔——吉布提之行,对非洲的神话和人种志进行实地考察,这一活动在其回来后写成的散文集《虚幻的非洲》(1934)中作了记述。莱里斯时刻不忘对自我进行探索和反思,1939年发表了备受评论家推崇的自传《成人之年》,从此,自传题材便成为他创作的主要倾向,从1939至1988年,莱里斯共出版了8部自传性作品,其中尤以四部曲《游戏规则》最为重要,它包括《一笔勾销》(1948)、《乱七八糟》(1955)、《细纤维》(1966)和《微弱的声音》(1976)四部作品。这是一部奇书,从书名上便可略见一斑。作者运用人种学研究的方法,用文字游戏般的语言,对自我进行探寻。他对字典中的词语进行拆解,加入一些随机因素重新构造和阐释,使其获得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甚至瞠目结舌的意义。作者还使用一些盘根错节的长句子,以求更好地探测记忆的沉淀,读者在探索语言奥秘的过程中象做了一次奇妙的旅行。这种对语言及其神奇魅力的狂热还体现在其游戏性作品《词汇集——我储存我的注释》中(1925-1939),其方法与《游戏规则》同出一辙:即对一个词语的要素(意义、形态、声音等)进行拆解和重构,使其传统意义丧失而获得一种具有诗意、甚至可笑意味的意义。例如,“自传”被定义为“真实的记事簿,你用爪子乱涂乱画的生活,你故作一本正经地送给别人看的你自己所拍摄的自己的照片”,“忏悔”被定义为“我们所坦露的、将我们彻底击垮的事实”。(注:Jacques Lecarme et Eliane Lecarme-Tab-one,L'Autobiographie,Armand Colin.Paris,1997,p.121.)(可惜由于两种语言的差异,原文中词语及其定义之间的谐音效果在译文中丧失殆尽,这也许是莱里
斯的作品难以翻译、在中国鲜为人知的原因之一。)
莱里斯没有写过小说、戏剧等虚构性作品,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素材的不拘一格的自传。自古以来,诗歌、戏剧、小说被视为“正宗”的文学体裁,而自传被视为作家或政治家在晚年或闲暇之余的“业余”创作,与上述三大体裁相比总是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名正言顺,是一种“边缘文学”,甚至不被视为文学作品。而莱里斯对自传却情有独钟并乐此不疲,倾注了半个世纪的精力与才华,取得了与任何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都毫不逊色的成就,在法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独此一家了。在自传创作上,他提出了“斗牛文学”的概念。“斗牛”与“文学”,不论从哪方面看,都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东西,而莱里斯却有自己的高见。20世纪,自传性作品(包括真实的自传、自传体小说、日记、回忆录、散文等)在法国曾盛行一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然而这些作品似乎都是在塑造一个完美的自我,即使这个自我不是很完美,有着种种缺点和污点,却对作者的人格和荣誉没有任何损害,反而使其增色,作者对过去的“我”抱着一种自恋的情感。莱里斯则对此类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提出了质疑,认为它们就象芭蕾舞演员的舞姿,尽管动作优美高雅,却是浮华和虚空的。自传创作应象是斗牛运动,斗牛士一旦置身于斗牛场中,面对发狂的公牛,便随时有生命的危险,稍有不慎,便命丧锐利的牛角。自传不应只写作者美好、高尚的一面,还应写自己的懦弱、卑微、丑陋、肮脏的一面。只有当斗牛士在面临最大威胁的一刻才有机会表现得最为悲壮,同样,自传作者应把对名誉和人格威胁最大,即把人们最不堪启齿的感情和性欲方面的困扰和痛苦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高声地、公开地忏悔出来,这样做,就使作者在公众面前面临身败名裂的危险,就象斗牛士面对公牛具有生命危险一样。这样,作者在写自传时心中便徘徊着公牛之角的阴影。莱里斯的这一主张的确够骇人听闻的了。“说真话并且说真话,”(注:Michel Leiris,De la litterature considérée comme une tauro machie,dansl'Age d'homme,Gallimard,1939,p.18.)这是莱里斯为自己规定的准则。在斗牛场中,斗牛士对规则的遵守越是严格,他面临的危险也就越大;在自传创作中,作者面临的危险也是与遵守上述准则的严格程度呈正比的,因此“说真话并且只说真话”是不够的,作者必须以最高度的清醒、明确、坦率、真诚的态度来忏悔。为此,作者不能象意识流小说的作者那样把自己的这些难以启齿的思想和行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危险转嫁给虚构的人物
,也不能象以前的自传作者那样采取一种半遮半掩或名为暴露、实为美化的虚伪态度。此外,斗牛的规定一方面使斗牛士处于一种巨大危险之中,使这种运动具有刺激性的一面;但它还具有观赏性的一面,斗牛士必须做到潇洒、悠雅,不能把斗牛变成一种屠宰活动。所以斗牛的规定既有战术意义,也有审美意义。当斗牛士在一系列连续而密集的交锋中脚步纹丝不动,斗篷慢慢地飘动,最后将剑刺入公牛的身体,高傲地抬起头面对观众时,人、披风、倒地的公牛便融为一体,组成一尊赏心悦目的雕塑。自传不仅要以合成摄影般的方式尽可能客观地展现自我,将生活的一个个片段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它还要感染读者,使作者的情感也传达给读者,象斗牛一样具有一种浪漫的色彩和诗一般的愉悦的功能,否则,自传就成了笔录般的流水帐了。
《成人之年》是莱里斯的一部代表性自传,是他所谓的“斗牛文学”的一部典型作品,以作者童年到35岁在性欲方面的经历为主线,冒着在亲朋好友和读者的眼中名声扫地的危险,真实地披露了自己在感情和性欲方面的压抑和痛苦以及20年代在巴黎的几次不成功的感情历程。作者好象在进行着一场“内心斗牛”,他那支无情的笔就象公牛的角,不断把自己逼入危险境地。他既是斗士,又是公牛,既是锋利无情的牛角,又是鲜血淋漓的伤口。《成人之年》不再是一部发自自恋情结的自传,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极力自戕、自毁。自戕自毁的结果当然使作者受损,却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自传。一个矛盾的现象是,《成人之年》为作者赢得了比其它自传作家更多的尊重和敬仰,作者的自我仇恨所激发出的竟是读者的喜爱,自我受难非但没有使作者的形象受到贬低,反而显得更加真实生动。莱里斯对此或许始料不及,或许预谋已久。
自传作者在作品伊始往往对以前的经历作一简短的总结,为自己画一幅自画像。如卢梭在其《忏悔录》开篇便慷慨陈词:“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只有我是这样的人。我深知自己的内心,也了解别人。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于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生来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我不比别人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您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您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面前,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注:J.-J.Rouss-eau,Les Confessions,dans Jean-Jacques Rousseau,Oeuvres compl-ètes,tome I.Gallimard,1959,p.5.译文参见黎星、范希衡译《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3页。)这样,一个个性鲜明、感情真挚、傲视众生、横空出世的形象便跃然纸上,尽管卢梭声称把真实性放在首位:“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注:J.-J.R-ousseau,Les Confessions,dans Jean-Jacques Rousseau,Oeuvresco-mplètes,tome I.Gallimard,1959,p.5.译文参见黎星、范希衡译《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3页。)而读者一眼便可看出:卢梭的《忏悔录》是发自一种自恋情结,是为了消除社会和世人对他所形成的误解和不良印象,还原一个“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的自我,所谓的“卑鄙龌龊”只是这一自我形象的陪衬。
与卢梭光芒四射的自画像相比,《成人之年》中莱里斯的自画像则显得“灰溜溜”的。与传统自传的主人公人格形成过程的时间叙述顺序不同,《成人之年》是按照主题进行叙述和划分章节的,时间顺序受到很大冲击,甚至被打乱,每个章节都由一个标题来点明题旨,如“衰老和死亡”,“超自然”,“无限”,“灵魂”,“主体和客体”等。耐人寻味的是,自画像这一节既没有一个点明主题的标题,也没有“前言”或“序”之类的字眼,标题所在的位置是一片空白,作品直接进入正文“我刚到35岁,生命已走过了一半。”或许这一空白是本书标题“成人之年”的一个延伸,因为本节是作者为35岁时的自己所勾勒的一幅速描;或许作者留此空白是为了促使读者进行思考从而总结出一个主题。
作者从身体、社会和精神三个角度来描绘自己。首先是身体特征,其描写可谓细致入微,从头写到脚,从面部表情写到习惯动作。这是一幅精细却并不美观的画像,甚至带着一种漫画式的夸张。首先是身材:“我是中等身材”,(注:Michel Leiris,L'Age d'homme,Gallimard,1939,25页。以下引文均出自该书,参见25-29页。)这还不错,至少不好不坏,但作者随即补足道:“说矮小更为恰当”,这就变成一种缺陷了;他的头发剪得很短,并非是为了好看,而是害怕越来越严重的脱发;他的脖子很直,“就象一堵墙或一个悬崖般垂直地竖着”;他的额头突出,但“有些凹凸不平,颞血管结节过多且过于凸起。”他的眼睛呈褐色,但“通常眼睑边缘发着炎”;他的脸色红润,但“呈现令人烦恼的烧红且皮肤闪亮”;他的手瘦削,却“毛茸茸的,血管明显地向外鼓出”,令人联想到动物的手;他的两个中指向指尖弯曲,“暴露出性格中的某种十分软弱或不可捉摸的因素”。作者每当提及身体的某一特征,总是随即笔锋一转,毫不留情地指出缺陷,并用贬义的词汇将其夸大。
以上是身体细部的特征,其整体形象也不美观。“我的头相对于身体来说有点太大;我的腿相对于上身来说有的太短,我的肩膀相对于髋部来说有点太窄;当我坐着时,显得有些驼背;我的胸膛不宽,而且没有肌肉。”他总是尽最大可能打扮得漂亮些,纯粹是为了掩盖身体的缺陷,最后作者明确地说出了“丑陋”一词,“我害怕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去照镜子,每一次我都发现自己丑陋得令人耻辱。”
如果说以上缺陷均属先天不足,作者对此并无责任的话,而他后天所形成的一些习惯同样没有丝毫美感,诸如“嗅手背”,咬拇指直到快出血为止,头略向侧歪,咬嘴唇,缩鼻孔等等。然而作者仍嫌不够,声明尽管某些习惯动作后来抛弃了,但又添上了一些新的,而且他还可能忘了某些细节。作者不仅自己为自己画像,还邀请读者为其丑陋的形象再添一笔。
自画像的第二个方面在于其社会状况,包括三个方面,即文学活动、旅行经历和人种学家职业。这是三种高级且令人敬重的活动,莱里斯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了成功。然而与上述对身体特征的精雕细刻相反,作者对本应不惜笔墨加以描写的社会活动却惜墨如金,写得既简约,又平淡,好象无足挂齿一般。莱里斯首先是一位作家,但他没有使用“作家”一词,而是用了一个贬义词“文人”(littérateur),而且这种活动并无特别高深之处,“任何喜欢拿着笔思考的人都是文人”。对于其等身的著作,他没有提及任何一本,只是说“我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几本书没有为我赢得任何声誉”。在旅行方面,应该说他还是走过一些国家的,但他却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旅行家,而且对于所到之处未作任何描写,只是提及了一些国家的名字。至于在人种学研究中取得的成绩,他也未作任何描述,只是说给他带来了某种舒适的生活。他身体健康,时间相对自由,似乎应属于生活中幸福的一类人,但“我生活中很少有些事情回想起来让我感到满足,我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我是在陷阱中挣扎,而且没有任何文学夸张,我感到很苦恼。”他在什么陷阱中挣扎,又为何感到苦恼?作者并没有说出来,我们只能到后面寻找答案。
自画像的第三个方面是其精神世界,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因为全书的宗旨即在于此。但这种精神世界是从性生活开始描写的。他说:“在性方面,我想我不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只是有点冷淡,但很久以来我便倾向于认为自己几乎无能。”可谓赤裸裸地暴露了。死亡的阴影总是笼罩在作者心头,这使他尤其不能忍受怀孕的妇女和新生的婴儿。他的姐姐生了一个女儿,他感到的不是快乐,竟是一阵恶心,一方面是由新生儿丑陋的外观引起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新的生命面前感到了自己的“衰老”,尽管他当时只有9岁,因为“我不能忍受我不是最小的了,不再是家中的那个‘小不点儿’了。”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强烈,他不仅感到自己的衰老,而且从新生儿身上看到的不是生命的胚芽,而是死亡的阴影,因为孩子一旦来到世上,便一步步不可挽回地走向死亡。即使在他年纪最小而且是其一生中唯一幸福的时期,也“包含了它自己走向瓦解的因素”。从童年走向成人之年,不是一步步走向成熟,而是走向退化、衰老和死亡。
爱情在作者笔下失去了浪漫的抒情色彩,而是一些清醒的思考,甚至带有色情的成分:“一段时间以来,我就不再把爱看作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看作一个比较特殊的事件,它需要某些特别悲凉或特别幸福的内心感情。”而且“如果我把做爱行为视为一种生育或人类繁衍的本能的话,我就不可能做爱。”更为可悲的是,爱也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爱和死(即生殖和垮台,其实是一回事)是十分相近的事情,以至于我在感到肉体的快乐时,总是伴随着一种迷信般的恐惧,好象做爱行为,在把我的生命引向极顶的同时,只会给我带来不幸。”因此,有关精神世界的意象总是二元的,对立的,如爱与死,肉体快乐与迷信般的恐惧,新生婴儿与衰老,一生中唯一幸福的时期与它的瓦解等。这样我们就可找到前面两个问题的答案了:如果说他总是感到在陷阱中挣扎,那是他无法摆脱的命定的死亡的陷阱;如果说他感到苦恼,那是因为他的身心逐渐走向衰退。在这幅自画像的描述中,有三个词作者用斜体标出以示强调,即“苦恼”、“衰老”和“我童年的形而上学”。“苦恼”是其一生的写照,走向“衰老”是其生命的轨迹,而“童年的形而上学”本身是一个十分矛盾的搭配,“童年”是一个具体的生活词汇,而“形而上学”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术语,二者一起使用,就把有关童年的一切具体的往事都抽象化为深沉的哲学思考,这也正是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
莱里斯的这幅并不雅观的自画像尽管看上去像幅漫画,但却缺少了漫画的幽默调侃的意味,代之以一份斗牛运动般的悲壮和深沉。作者好象端坐在一面镜子前为自己画像,就象纳齐疏斯(Narcisse)端视自己水中的倒影一样。但纳齐疏斯因为迷恋上倒影竟憔悴而死,而莱里斯则把自己的笔变作残酷的公牛之角,把自己扼杀了。的确,作者这幅貌似可笑的自画像不是促使我们发笑,而是促使我们对爱与死等严肃深沉的问题进行思考,作者写作自传不是为自己辩解、美化、粉饰,而是恰恰相反,走向了自恋文学的反面——斗牛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