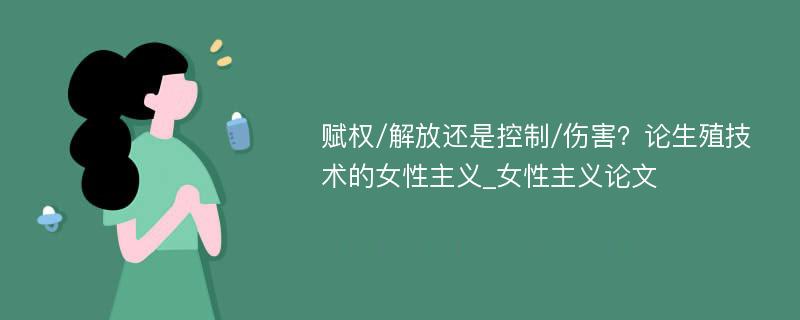
赋权/解放还是控制/伤害?——有关生育技术的女性主义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主义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558(2012)03-0179-09
今年三·八节,收到大学同学的网上留言,很有意思,照录如下:
女人这辈子挺难:漂亮点吧,太惹眼,不漂亮吧,拿不出手;学问高了,没人敢娶,学问低了,没人想要;活泼点吧,说你招蜂引蝶,矜持点吧,说你装腔作势;会打扮,说你是妖精,不会打扮,说你没女人味;自已挣钱吧,男人望而却步,男人养吧,说你傍大款;生孩子,怕被老板炒鱿鱼,不生孩子,怕被老公炒鱿鱼。这年月做女人真难。祝所有MM妇女节快乐。
同时又在网上发现一条可以与前述内容相联系的新闻,是中国内地身兼演员、导演、制片人数职,且有“才女”之称的徐静蕾的一段自白:
……36—40岁吧,我会考虑生个孩子。我还是想当母亲的……我本质上是个比较会异想不太可能实现的状况的人,比如说我希望将来自己生孩子的话能够采取代理孕母的方式,就是让别人代替我的子宫把孩子生下来,我觉得我不可能有整整十个月的时间抛弃其它一切去做孕育的事情。①
那么,徐静蕾的选择是不是已经给广大“受苦受难”的姐姐妹妹们带来了“福音”——现代生育技术将会帮助她们摆脱困境,既不会被老板炒鱿鱼,也不会被老公炒鱿鱼,从此走上了“解放”的康庄大道?
事情就这么简单吗?生育科学技术到底给女性带来了什么?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视角,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笔者自己的研究实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根据Michelle Stanworth(1987)的说法,目前介入人类生育过程的技术手段主要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和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组是与生育控制有关的手段,包括避孕、胚胎移植、终止妊娠等。第二类涉及对分娩过程的驾驭,如剖腹产、侧切、测量胎儿心律和活动的方法等。第三类关注胚胎的早期发展阶段,希望通过基因工程消除健康隐患,得到一个完美的孩子(也就是所谓“优生”)。第四类是针对不孕、不育的治疗技术,像体外受精、代孕。②徐静蕾提到的就是第四类,但对她来说,这一技术,不是治疗手段,而更像“解放”手段。虽然,近年,生育技术不断发展,但从其使用目的来看不外乎两类:用于避孕或受孕,和一些相关的辅助措施,如观测胎儿的发育状况、实现胎儿早期与母亲的互动等。
一、早期女性主义者对生育技术的态度
关于现代生育技术和女性的关系,不同的女性主义派别持有不同的观点。激进—自由女权主义者(radical-libertarian feminists)认为女性应当借助生育技术摆脱自然生产,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去。相反,激进一文化女权主义者(radical-cultural feminists)把女性的生育能力当作她们唯一的力量源泉,这一能力的被剥夺和被取代只能使女性面对男性强权毫无反击之力。③很显然,前者把自然生育当作女性受压迫的原因所在,如Shulamith Firestone在“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中谈到的:因为最初的阶级差别源自男性和女性在生育活动中的角色不同,与生产关系相比较,两性在生育过程中的关系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所以女性的解放只能通过生物革命来实现。……当技术克服了自然生产的局限,一些人拥有子宫,另外一些人拥有阴茎就不具有文化意义了。④Marge Piercy的“时代边缘的女性”(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继承了Firestone的观点,且更为激进,她描绘了一幅通过生育技术实现两性平等的乌托邦图景,把生育技术当作革除性别歧视的灵丹妙药。⑤后者把自然生育看作女性解放的力量源泉。她们认为,女性仍然受着压迫,她们不能放弃自己唯一的优势力量,正如Azizahal-Hibri所观察到的“使用技术手段的生育活动并不能使自然生育过程中的权力结构变得平等——事实恰恰相反。它把女性的生育特权交诸男性,他们现在既能控制精子,也能控制生育技术。这一技术洗刷了男性必须依赖女性而得以繁衍的耻辱。”生育技术强化了男性的权力。⑥更有激进一文化女权主义者批评Firestone的女性解放蓝图,其实却使女性进一步被奴役。她们认为,男性对女性生育能力的嫉妒才是女性受压迫的最终原因,男性期望通过生物技术实现对女性生物特性的控制。Mary O'Brien总结了男性在生育过程中处于权力劣势的主要原因:首先,除了受孕之外,他不能在自己的体内感受生育的连续过程。其次,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在怀孕和生产。第三,女性和孩子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而男性却无法确定自己与婴儿的生物关系。这种在生育过程中被隔离的状况导致男性力图限制女性的生育特权,以把父权制“进行到底”。⑦正如Adrienne Rich在“女人所生”(of Woman Born)一书中总结的:男性为了确保自己在社会中的权力优势,介入到生育活动的各个环节——男性产科医生取代了女性接生婆,他们甚至指导女性在怀孕和生产过程该怎么做,而这些法则却往往和女性自己的体验、直觉相冲突,使得女性无所适从。⑧当技术的发展让女性在生育活动中显得毫无价值的时候,她的命运就只能是:性工作者或者家务工人。所以Dworkin敦促女性抵制生育技术的进一步发展。Rowland则忧心忡忡地提出,如果女性的最后一点特殊权力也被男性控制,她们在新世界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⑨
笔者以为激进一自由女权主义者把生育技术完全作为女性解放的手段有些过于理想化,因为技术的实施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它无疑会受到当时社会文化、权力结构的影响。而激进一文化女权主义者把男性和女性置于二元对立的模式中,过分强调了二者之间的“性”差异,把生育能力作为女性唯一的力量源泉,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女性的弱势地位,把女性等同于生育机器。而且正如他们自己已经意识到的: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不可能保持自己在生育中的特权地位,男性的霸权即使不从生物技术中表现出来,也可以从其它方面(如抢夺子女的监护权等)表现出来。所以,女性与生育技术的关系的核心不在技术本身。
二、女性主义生育技术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承接激进女性主义的传统,后来从性别视角对生育技术进行的女性主义研究,无论深浅,都未超出“赋权/解放”和“控制加剧”的范围,只不过对各种技术的效果分析更为具体了。
(一)赋权/解放
Jyotsna A.Gupta(2000)在“新生育技术,女性的健康和自主:自由还是依赖”(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Women's Health and Autonomy:Freedom or Dependency? )一书的前言中谈到:“无论是本世纪早期妇女运动中的生育控制者还是新的妇女运动,都将生育技术,尤其是避孕技术看作是提高女性自主性的手段,这一点很重要。”⑩“对于(西蒙·波伏瓦)来说,妇女的自由解放和新科学技术对生育活动的调整密切相关。在她看来,怀孕是对妇女的奴化和异化,使她们无法主导自己的命运并实现超越。”(11)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为女性摆脱身体束缚、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提供了可能。Deborah Wilson Lowy(2004)在“作为监视组合的生育技术”(Understanding Reproduction Technologies as a Surveillance Assemblage)一文中谈到,虽然人们的讨论集中于生育技术对妇女的不利影响,也有女性主义学者注意到它的赋权能力,而且生育技术对于特定女性的消极作用,也可能是无意的。(12)Diana C.Parry(2005)的“女性的不孕体验:探索赋权的结果”(Women's Experiences with Infertility:Exploring the Outcome of Empowerment)更是把重点放在生育技术对于女性的赋权作用。作者认为在经历不孕的痛苦过程中,女性自己决定是否采用生育技术,通过积极的选择技术帮助和认识、了解相关信息。女性对于技术发展给自己带来的影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表现出相当的主动性,并不是技术的受害者。经历过不孕,她们变得坚强起来,更有信心地面对将来的生活。作者还回顾了女性主义对生育技术态度的历史发展。上个世纪6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技术可以帮助妇女避免意外怀孕,这就意味着女性不再只能用母亲的身份来定义自己,女性也不会因为“要做母亲”的命运而被排斥在工厂之外。70年代,新的生育健康法则进一步发展,1973年,流产合法化,生育控制的权利扩大到未婚人群,妇女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有关生育问题的法律支持,但同时,女性主义者开始对妇女使用生育技术产生质疑。(13)
(二)控制加剧/伤害
Deborah Wilson Lowry在同一篇文章(Understanding Reproduction Technologies as a Surveillance Assemblage)中谈到,许多批评者指出胚胎监测技术成就了胚胎的社会—道德地位,游动的胚胎影像突出了它作为独立个体的形象,母亲仿佛只是一个容器。强调胚胎的优先地位并不是真正关心它的福祉,而只是为了控制未来的母亲——女性;生育技术可以跟踪胎儿发展状况,一旦不符合社会优生标准,母亲必须做出继续或终止怀孕的决定,增加了母亲的责任负担;另外,对专家咨询的要求剥夺了怀孕妇女的权力和自主性;携带有风险胎儿的怀孕妇女成为多种机构(如诊所、医院、雇主、警察、福利办公室等)关注的对象,她们被近距离观察,数字化分析,最终完全转化成一系列数据。作者在这里强调了现代生育技术导致怀孕妇女进一步被边缘化的趋势。Lene Koch(1987)在“走向生育技术的女性主义评价”(Towards a Feminist Assessment of Reproductive Technology)一文中提到Pat Hynes所总结的生育技术给女性带来的风险:在妇女身上实施的各种试验,效果无法保障;生育技术使对妇女生育活动的控制合法化,“从长远来看,体外受精将决定妇女必须生育孩子和什么样的孩子”(14);生育技术把妇女简化成了卵子库、胚胎温床和子宫,进而消除了女性作为自主个体的价值,就像湿地被当作没用的土地任意开掘和填充,女性的命运与此相同;生育技术制造了技术成功的假像,它忽略了真正的主题,即不孕或怀孕的原因。(15)而且,妇女在技术实施过程中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和生理痛苦,却无人领会,最令人费解的是,当事实上是丈夫不孕时,也要由绝对健康的妻子来承受治疗的痛苦。Maren Klawiter(1990)同样认为现代生育技术给妇女带来了极大的危险,挑战了女性主义革命改变人类关系的企图。同时,胎儿与母亲相对立,和技术上强调前者,使妇女变得近乎无形,牺牲了她们的整体性。作者不仅认为由男性控制的技术伤害女性的历史由来已久,而且更从哲学意义上谈论抽象的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科学技术立志消除各种差异和多样性,把所有的变量都置于控制之中,以消灭不稳定因素,生育、妇女自然成为受控制的对象。(16)Anne Donchin (1989)的“日益升温的新生育技术的女性主义论争”(The Growing Feminist Debate over the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文章中引用的1985年瑞典会议的宣言认为:妇女的身体被用作技术生育的原材料。呼吁所有的妇女反对把我们自己的身体为男性所用,抵制把我们的身体用于谋求利益、人口控制、医学实验和厌恶女人的科学的强权。(17)Diana C.Parry (2005)的文中提到Woliver说:“妇女是被新生育技术拨掉皮的子宫,她们的内部一览无遗的被医学专家、国家所检测、监视和控制。”(18)性别选择技术使女性更加处于不利地位。如印度的羊膜穿刺术政策(amniocentesis),这一技术的初衷是发现基因异常的胎儿,但现在却被用来进行性别测定,目的是流产女性胎儿,以避免高额的嫁妆开销。
总体而言,这一类讨论更偏重于揭示新的现代生育技术给女性造成的伤害,不仅加重了她们肉体上的痛苦,而且使女性进一步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更加边缘。唯一为自己所特有的生育能力、生育体验也遭遇以专家面目出现的所谓男性权威的威胁甚至控制,女性沦为单纯的器物(containers of embryos)或者器官,更容易陷入多种力量的监视之中,而少有做人的权利和尊严。“当科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功,技术代替子宫成为先进的生育方式时,女性被进一步贬值。在现有的权力结构中.基于男性对女性的历史性嫉妒,技术会导致对女性的完全孤立。女性被排除在生育活动之外,男性克隆他们自己。简单的说,女性就要绝种了。”(19)性别选择技术的出现,导致更多的女性婴儿被剥夺了生存的可能。还有批评者指出,社会应该倾注更多的精力研究导致不孕的原因,以防患于未然,而不是亡羊补牢的雨后送伞。
(三)有关性别、种族、阶级与性取向的综合研究
随着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的出现,西方国家的有色人种妇女和第三世界的妇女开始反思以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妇女为中心的女性主义理论,从而把种族、阶级、性取向等因素与性别研究结合起来,认为任何一种形式的压迫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往往错综复杂的纠缠在一起。这一类的女性主义研究者总会注意到少数民族妇女和低阶层的妇女和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在获得有关生育技术咨询和服务过程中的不平衡地位,通过胎儿、血液检测和社会服务,贫穷的非洲裔母亲往往受到更大的监视、控制和驯化。在一个性别、种族、阶层极度分化的社会中,处于最弱势地位的女性的身体被用来实施不育的治疗技术。Jyotsna A.Gupta(2000)的研究提到:在发达国家绝对禁止使用的避孕产品,总是毫无障碍的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有关这些产品的副作用和医疗禁忌却很少被提及。通常是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的、文盲、半文盲妇女成为新型避孕产品的实验对象,她们总是容易被财政补贴所诱惑,如避孕药丸就是首先在波多黎各妇女身上测试的。(20)所以,可以很保险的说,在现有分类标准(阶层、种族、民族、性取向等)中处于底层的妇女成为生育技术的最大受害者。有些国家和政府甚至借节育、优生之名,运用避孕技术和多种控制妇女身体的手段,努力降低少数民族的人口出生率——他们总是很愿意为低收入的有色人种妇女做绝育手术(Donchin 1989; Deborah W.L.2004; Tong 1998; Maren K.1990)。在“身体边界,女性的自我想象:权力、女性主义和生育技术的民族志研究”(Body Boundaries,Fiction of the Female Self: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on Power,Feminism,and the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一文中Gillian M.Goslinga-Roy(2000)对一名由于自身特殊经历而愿意充当代孕母亲来回报社会的女性进行了深入研究,使作者感到诧异的是,虽然两人在合作过程中已经结成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而且当事人也知道作者的丈夫是有色人种,但她仍然表示,为白人夫妇代孕对她来说没有任何障碍。可是她反问作者:“你能想象金发、蓝眼的我生出了一个黑人吗?”(21)如何实施现代生育技术不再只是两性之间的问题,它还牵涉到种族、民族、性取向等社会类别(categorv)。Lene Koch(1987)的研究早已指出,同性恋妇女和单身女子被排除在体外受精的治疗范围之外,因为权威人士认为只有稳定的异性恋家庭才能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所以体外受精不仅仅是一种不孕不育的治疗手段而且是社会的控制手段(22)。
三、现代生育技术对女性的影响
前述研究,一方面说明生育技术确实属于科学技术范围之内,它使“神圣”的人口繁衍过程变得可以由人来控制,科学技术的发达使“人从哪里来”的问题的答案不仅仅存在于各类“神话”中,但同时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生育技术的创造、实施又不是单纯、客观,超然于物外的所谓“科学”(natural Science)话题。它的产生、实践中渗透了复杂的社会因素,其最终的影响结果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于这些社会因素,如种族、性别、阶层、性取向、民族等的微妙互动和历时变化。
所以,依笔者看来,同一类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实施在不同社会中会对同一人群产生不同的影响,关键是看,这一技术是在何种社会中产生、它被掌握在谁的手中。因此,前人的研究把现代生育技术对于妇女的影响集中在对妇女的伤害和控制上,是有道理的。在大多数社会仍然是父权制社会的今天,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地认为科学技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一切问题,包括妇女因生育而遭遇的歧视。
首先,生育还是不生育,什么时候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不是妇女所能够决定的。如中国当代社会中的主流价值观念仍然很少变化,女人生孩子似乎与生俱来(23)、天经地义、责无旁贷(Ann Oakley已经反驳过这一观点,她认为女性是在社会化过程中慢慢接受母亲情结的,与她们的卵巢和子宫无关(24)),人们不遗余力地歌颂伟大的母亲和母亲的伟大,竭力昭示其“至高无上”之地位,用于给女性提供行为准则,于是,多数出现在公共领域的成功女性形象都是事业上的强者,家庭中的“贤妻良母”,一旦不能兼顾,总会为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而惭愧。不愿生育的女性往往被贴上“自私”的标签,当作反面教材。再则,正如留言中所说的,不愿生育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家庭破裂。最后,在家庭成员以外,还有许多其它“权力所有者”能够决定她们是否生育、什么时候生育孩子和生育几个孩子,如职场的老板、国家力量、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等,体现在不时出现的热门话题中,如“女人,你是生还是升?(后者指升职)”、“女博士,你到哪里去生孩子?”
那么,仍然回到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生育技术的推广是否就能使无奈不得不生育又不得不在一个特定时间生育的女性获得了自由,而在职场和家庭之间应付自如?首先,我们看到,即使女性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25),避免了意外怀孕,但它是有代价的,这一代价的承受者在父权制社会中很少例外的都是女性。服用避孕药可以避孕,使用“安全套”也可以避孕,但避孕药在依然会造成许多不良后果的情况下(如内分泌紊乱、月经失调、造成不孕、宫外孕等),还在被大范围使用,因为丈夫们不愿让“安全套”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于是,大量的权威研究出面证明“安全套”避孕并不安全,以迎合男性的需要)。Jyotsna A.Gupta(2000)的研究也证明:虽然人们都知道“安全套”的避孕作用,但是当医生和病人谈论避孕问题时,几乎不会提到“安全套”,这就强化了避孕是女性的责任的观念。(26)虽然学者们已经意识到男性应当和女性共同承担生育控制的责任,过去缺乏对男性避孕手段的研究和提高的状况需要得到改观,但是男性并不像女性那样容易被说服来接受各种试验。男性担心如果他们的荷尔蒙受到干扰,自己会丧失“利比多”(libido)和性功能,但同样的对女性造成的危险和伤害却被大大地低估了,医生们不关心,甚至女性自己也不关心。(27)另外,代理孕母使少数人摆脱了“生育”的麻烦和不得不生育的尴尬处境,如徐静蕾之类,但她们的“解放”是建立在其它女性的身体被“使用”的基础上的,只是一种“危机转嫁”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女性因生育而被边缘化的整体局面。
第二,如果有不孕不育的现象出现,为了拥有后代,人们通常有两种选择:抱养或接受人工受孕。女性对抱养往往没有抵触情绪,和她们的丈夫相比较,她们更能接受这一行为。但是,为了满足丈夫希望拥有一个生物学意义上与自己相关联的后代的愿望,她们也只能选择接受人工受孕或者代理孕母等方式,虽然自己所承受的心理和生理压力比丈夫要大得多,如要忍受注射激素、提取卵子和胚胎植入的痛苦,或者密切注视代理孕母的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惯,担心会给自己的孩子带来不良影响,并在焦虑和忐忑不安中等待自己的孩子“回家”。(28)
第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时候,即使不孕的一方是男性,却仍然是他的绝对健康的妻子来承受治疗不孕的各种痛苦。
因此,技术只是一种工具,它给人们带来的是福祉还是灾难,是人人都能平等享受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还是把部分人的幸福建立在对其他人的剥夺(explore)的基础上或者自己的痛苦却要通过技术转嫁给别人?都决定于这一技术掌握在谁的手中,在怎样的社会中产生、发展、运用。例如,有学者认为,现代生育技术可以使同性恋妇女不用借助男性而获得自己的后代(conception without sexual intercourse),完全意义上的摆脱男性的控制,理论上是讲得通的,但事实上,是很难实现的。同理,现代生育技术给妇女提供了选择的可能,但并不意味着女性就可以在生育问题上做出自己的选择。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罗伊案”就是典型的例子,1969年,一位化名为杰内·罗伊的妇女和其它人一起向得克萨斯州限制堕胎的法令提出了挑战——该法令规定,除非因为维护孕妇的生命,州内一律禁止妇女实施堕胎。罗伊认为:德州限制堕胎的法令剥夺了她在妊娠中的选择权。该案最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29)虽然罗伊最终胜诉,但这一过程表明,单纯的技术并不能给妇女带来更多的选择自由。
Lene Koch(1987)提到,Corleen Gee Bush的文章的出发点就是技术本身是一个平等的话题,为了认识技术的发展是有利于妇女还是相反,我们需要对其所运作的社会进行全面地了解。(30)Maren Klawiter(1990)认为:“作为女性,妨碍我们自由的不是我们的身体,而是被现代社会所容纳和鼓励的各种价值观、目标和活动。”(31)Deborah W.Lowry(2004)也谈到:要成功的挑战现代社会的生育政治,我们不仅仅要面对生育技术,而且要同时考虑社会关系、愿望和技术如何被阐释而形成的特殊组合。(32)所以,父权制社会中产生和发展的所谓“价值中立”的科学生育技术虽然可能给女性带来些有限的自由,但充其量只是适应父权、资本主义社会的副产品(33),却很大程度上成为妇女被控制的工具,由于其与妇女身体的亲密关系而会对女性造成更大的伤害,使其承受更大的生理和心理的痛苦。在女性被歧视,两性不平等的社会中,即使技术的本意无可厚非,其结果也可能造成对女性的控制和伤害。上文提到的羊膜穿刺技术在印度的应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其初衷是为了提高人口素质,却成为扼杀女婴的帮凶。Deborah W.Lowry(2004)在“作为监视组合的生育技术”(Understanding Reproduction Technologies as a Surveillance Assemblage)一文中呼吁生育技术向对顾客“友好”的方向发展,降低“专家”的指导作用,减少对怀孕妇女的习惯和行为的监视,而代之以为她们所关心的事情提供良好的咨询,使之在有关自己的怀孕和健康问题上能够做出更好的个人判断和决定。(34)但如果不消除父权制社会,这些美好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短时间内完全消除延续数千年的父权制社会,自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从一些可操作性的措施开始,如足够的收入、带薪产假、可靠的婴、幼儿托管服务等,为女性(如果她们愿意生育)也是为整个人类的未来创造一个友好的“繁育”环境和气氛。
因此,关于生育技术会给女性带来何种影响,笼统的讨论解放/赋权或者控制/伤害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要对生育技术产生、实施之社会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性别结构等等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而在全球一体化程度越来越深、国际权力格局极度不平衡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对生育技术可能被滥用保持高度的警惕,这是关涉国家、民族的大事。同时,我们不能再纠缠于一般女性的共同性,社会分化和文化多元化,使女性之间的差异日益明显,必须注意不同情境、不同身份、地位的妇女以及她们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最终改变父权制观念和社会结构,使“生育”既不是不得不完成的“不二法门”,也不是“影响经济效益”的“麻烦事”,更多应当是女人自己在充分享有知情权的前提下的真正的自由选择的实现,而各种形形色色的机构的主要功能不是监视和测量怀孕妇女和可能怀孕的女性以及她们未来的孩子,应当是为她们提供各种她们需要的服务,如能够降低生产痛苦的“水下分娩”等,却不代替她们决断。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才能放心的欢呼生育技术给妇女带来的自由和解放。
以下,笔者试以自己的研究对象为例,用具体个案论证上述结论。在笔者做研究的甘肃省东乡族地区实施的生育技术服务主要集中在节育方面:
1.未领到生育证的无孩妇女可采取上环或使用避孕药具等措施。
2.汉族和少数民族生育一孩以及稀少民族生育两孩后应在42~90天之内采取上环措施,至达到间隔,符合生育措施并领取二孩生育证和稀少民族领取三孩生育证后,方可申请取环。
3.汉族及少数民族生育二孩及以上、稀少民族生育三孩及以上者,应在三个月内采取结扎措施,确因禁忌证不能结扎者,应及时采取上环或其它避孕措施。(35)
另附,环孕情检查的具体实施情况一例:
坪庄乡环孕情检查时间安排的通知
韩则岭村大山社马木毯:
你妻马麦来也属于环孕情(指上环、放环、怀孕情况,笔者注)检查对象,限你妻在规定时间内到乡计生服务所进行检查,若逾期不到者,按县委发(98)10号处以50~500元人民币的罚款……
坪庄乡计生站2001年10月15日(36)
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些节育技术的实施对象均是妇女,另有老庄社计划生育情况统计显示,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03年共有结扎情况31例(37),全部为女扎。所以,权力不均衡的社会现实使女性要么承担避孕的痛苦,要么忍受非自愿怀孕的无奈,这时恐怕还不能过多的奢侈的谈论解放,从而给人们特别是女性造成误解,影响真正的解放的进程的展开。
当今社会中,生育技术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性别关系,与生育有关的事情还是女性的责任和义务,它只是在顺应原有的性别分工模式,而且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不平等的性别等级制度,因此,我们不能依赖生育技术改变现实的性别不平等状况,恰恰相反,如果希望生育技术发挥出解放妇女的功能,就只能从改变男性主导地位和消除种种压迫现象开始,这正是女性主义者的任务和使命。
[收稿日期]2011-10-09
注释:
①徐静蕾“娇点”写真[EB/OL].太平洋时尚女性网,http://www.pclady.com.cn/office/ft/mr/0603/75683_2.html,2012年6月10日访问。
②参见Michelle Stanworth (ed.),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Gender,Motherhood and Medicine,Cambridge:Polity Press.1987.
③参见R.Tong,Feminist Thought (Second Edition):A More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Boulder:Westview Press,1988,pp.71~72.
④参见Ibid,pp.72~73.
⑤参见lbid,pp.73~75.
⑥参见lbid,p.75.
⑦参见Ibid,p.76.
⑧参见R.Tong,Feminist Thought (Second Edition):A More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Boulder:Westview.Press,1988,pp.76~77.
⑨参见Ibid,pp.76~79.
⑩Jyotsna Agnihotri Gupta,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Women's Health and Autonomy:Freedom or Dependency? New Delhi; 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2000,p.27.
(11)Ibid,p.33.
(12)参见Deborah W.Lowry,"Understanding Reproduction Technologies as a Surveillance Assemblage",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2004,47(4),pp.357~370.
(13)参见Diana C.Parry,"Women's Experiences with lnfertility:Exploring the Outcome:of Empowerment",Women's Studies,2005,34(2),pp.191~211.
(14)Lene Koch.1987,"Towards a Feminist Assessment of:Reproductive Technology",Acta Sociologica,1987,30(2),p.189.
(15)参见Ibid,p.182.
(16)参见Maren Klawiter,"Using Arendt and Heidegger to Consider Feminist Thinking on Women and Reproductive/Infertility Technologies",Hypatia,1990,5(3),pp.65~89.
(17)参见Anne Donchin,"The Growing Feminist Debate over the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Hypatia,1989,4(3),pp.136~149.
(18)Diana C.Parry,"Women's Experiences with Infertility:Exploring the Outcome of Empowerment",Women's Studies,2005,34(2),p.195.
(19)Jyotsna Agnihotri Gupta,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Women's Health and Autonomy:Freedom or Dependency? New Delhi: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2000,p.112.
(20)参见Ibid,p.223.
(21)Gillian M Goslinga-Roy,"Body Boundaries,Fiction of the Female Self: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on Power,Feminism,and the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Feminist Studies,2000,26(1),p.116.
(22)参见Lene Koch.1987,"Towards a Feminist Assessment of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cta Sociologica,1987,30(2),pp.173~191.
(23)2004年,在我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一名学生曾经质问我说:如果女人都要工作、追求高学历,而这一类女性往往不愿至少不愿过早地生孩子,那么人类社会如何延续,老龄化社会状况如何改观?
(24)参见R.Tong,Feminist Thought (Second Edition):A More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Boulder:Westview:Press,1988,p.81.
(25)这一自由也许就是为了适应父权社会的步伐和时间表。
(26)参见Jyotsna Agnihotri Gupta,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Women's Health and Autonomy:Freedom or Dependency? New Delhi; 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2000,p.238.
(27)参见Ibid,p.310.
(28)参见Gillian M Goslinga-Roy,"Body Boundaries,Fiction of the Female Self: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on Power,Feminism,and the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Feminist Studies,2000,26(1),pp.113~140.
(29)“用刑法遏制重男轻女”的误区[EB/OL].搜狐网,http://star.news.sohu.com/20060427/n243021777.shtml,2012年7月14日访问。
(30)Lene Koch.1987,"Towards a Feminist Assessment of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cta Sociologica,1987,30(2),p.183.
(31)Mareh Klawiter,"Using Arendt and Heidegger to Consider Feminist,Thinking on Women and Reproductive/Infertility Technologies",Hypatia,1990,5(3),pp.83~84.
(32)参见Deborah W Lowry,"Understanding Reproduction Technologies as a Surveillance Assemblage".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2004,47(4),pp.367-368.
(33)如为了更好地利用女性廉价劳动力。
(34)参见Deborah W Lowry,"Understanding Reproduction Technologies as a Surveillance Assemblage",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2004,47(4),pp.367.
(35)秦臻,马国忠主编.东乡族——甘肃东乡县韩则岭村调查[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55-56
(36)同上,第56页。
(37)笔者在2007~2008年间的田野调查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