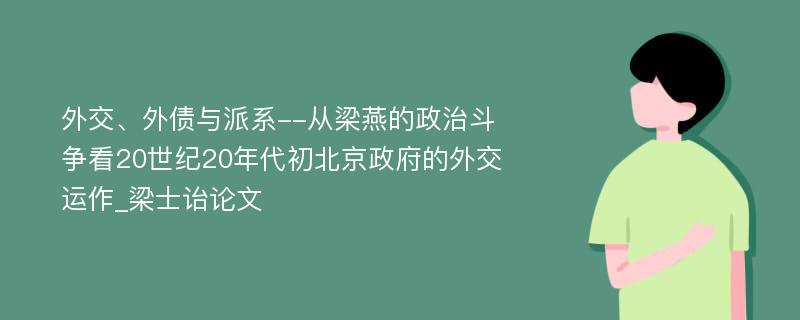
外交、外债和派系——从“梁颜政争”看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政府的外交运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外债论文,派系论文,北京论文,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外交肇始于北京政府时期,一些外国学者在评价北京政府的外交部和外交家时充满溢美之辞。如路希恩·派认为“北京外交家为中国最成功的文人领袖,他们巧妙地利用国际形势及当时世界的同情,取得了与中国国力完全不成比例的成果”(注:Lucian Pye,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New York,1971),p.152.)。罗伯特·波兰德亦认为:“军阀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由一小撮人决定,他们在欧美受过国际法训练,有外交经验,了解国际大势……外语流利。内阁与派系上下起伏……而外交部与使领馆却一直由这群年轻的留学生掌握。”(注:Robert Pollard,China's Foreign Relations,1917—1931(New York,1933),p.407.)不少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对此多有证明,如唐启华、王建朗、石源华、金光耀诸教授的专著、论文中都有述及。(注:唐启华:《北京政府外交行政机构的演变》,《中华民国外交志(初稿)》,台北,“国史馆”2002年版,第225—248页;唐启华:《一九二○年代中国外交的重估》,《一九二○年代的中国》,台北,史料中心2002年版,第33—59页;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金光耀:《顾维钧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应该看到,从清政府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在中国发萌开始,历届中国政府都未放弃外交实践和制度现代化的努力。北京政府时期的确取得过一系列的外交成果,但是在派系纷争、军阀混战的20世纪20年代,这批主要由留学生构成的职业外交官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实践,他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呢?本文拟以华盛顿会议期间围绕山东问题而引发的“倒梁(士诒)风潮”和“梁颜(惠庆)政争”为例进行分析。
1921年10月,当时与奉系关系密切的总统徐世昌和倾向直系的总理靳云鹏间因烟酒署长职位等问题引起争端,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乘机运动,遣干将叶恭绰密赴沈阳,利用直奉之间的尖锐矛盾,许张作霖以利,说服奉系采取行动倒靳。12月17日,靳云鹏内阁倒台,由外交总长颜惠庆暂代阁揆。12月19日,曹锟应张作霖之邀赴京会商,在张作霖的鼎力推荐与支持下,梁士诒再次得到组阁的机会。12月24日,梁士诒出任国务总理,颜惠庆仍任外长。孰料,梁内阁好景不长,因其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处理山东问题不力,遭吴佩孚等军阀实力派通电抨击,至1922年1月25日被迫下野,颜惠庆再代阁揆。梁士诒此番执掌阁揆前后不过一月,但却风潮迭起,不仅牵涉军阀派系争斗,也裹挟着北京政府赖以维系的两大重要支柱——外交和外债,成为这一时段北京政府外交运作的重要案例。
梁颜渊源
黎安友在《北洋政治(1918—1923):派系政争与宪政夭折》一书中将北洋时期的政坛代表人物按时间顺序分成三代:第一代出生于19世纪60年代,以梁士诒为代表;出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颜惠庆被归入第二代。黎安友认为第一代多数握有进士功名,也有不少接受过一些新式教育,而第二代则大多有举人功名,虽然更多、更广泛地接受过新式教育,但仍然较为保守。叶恭绰、顾维钧等则被列为第三代,“留学生”是这代人的重要标签,在他们身上个人主义、自由平等观念强化,反抗意识强烈,虽然言行并不激烈,但更强调共和。(注:Andrew Nathan,Peking Politics 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Berkeley,Uni.of California Press,1976),pp.7—25.)
北洋政治人物年代分类表
出生年代代表人物 特征
19世纪 文人:梁士诒多有进士功名,同时亦接受
60年代 武人:王士珍、王占元、曹锟 一些新式教育
留学生:段祺瑞、黎元洪、张绍曾、
唐绍仪
19世纪 举人:朱启钤、王克敏、潘复、张弧大多有举人功名,接受新式
70年代 新式学堂毕业:龚心湛、吴佩孚教育较上一代人强化,但仍
进士:熊希龄然较为保守
留学生:陈锦涛、曹汝霖、颜惠庆、
王揖唐
19世纪 叶恭绰、李思浩 新式教育更为加强,传统教
80年代 留学生:徐树铮、黄郛、钱永铭、 育大为减弱,留学资格尤为
顾维钧、罗文干 突出,个人主义、自由平等观
念强化,反抗意识强烈,是五
四运动时期的领袖官僚,受
前代的庇护,观念并不激烈,
但强调共和
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称梁士诒是中国的“皮特庞特·摩根”,“是北京最能干和最有势力的人”。(注:〔美〕保罗·S.芮恩施著,李抱宏、盛震溯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9—80页。芮恩施生动地描述梁士诒是“广东人,身材矮胖,脑袋很大,像拿破仑一样;他沉默寡言,但他的插话表明,他总是首先提出问题引导讨论,在他研究问题时也是如此;在直接问到他的时候,他总能够对任何事情做出清楚的、有条理的说明。中国官员一向都是利用金钱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他并不例外。对某些人来说,他是欺诈和贪污的老手,另一些人把他看作财神,还有一些人佩服他的组织才能,对他很尊敬。梁士诒虽然并不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但是他在那些把他当作一个几乎是超人的狡猾诡谲、精明强干的人物的人们中间,却充分引起了离奇的兴趣。”(第80页))贾士毅则评价梁士诒“早年科举高中入第,录进词馆,气度豁达,见识远大,处事刚果,重实践而不空谈,做事有魄力”(注:贾士毅:《民国初年的几任财政总长》(二),(台北)《传记文学》第5卷第4期,1964年10月,第42页。)。而出生于传教士家庭、从小接受西式教育、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上海人颜惠庆与梁士诒之间的差别自然不仅表现在“代”际,他们的教育背景、气质性格、为人处事的方式都各不相同。
1921年在梁士诒内阁中的相逢并非梁颜之间的首度共事,他们在袁世凯政权中都曾经是重要人物。梁士诒在袁世凯政权中的重要地位众所周知,因此在袁死后,他才会以安福系首领身份而遭到通缉。颜惠庆在袁政权中虽仅任外交次长,但却是个“不倒次长”(注:详见陈雁《颜惠庆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61页。),曾经主持外交部改革和中俄外蒙谈判等项事务,在袁氏外交中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只是后来因“事无巨细,均唯袁氏之命是听”难有作为,而自愿外放北欧,担任公使。
那次短暂共事,梁颜间有无矛盾已无案可考,而在同阁任事前两人之间存在分歧却是显而易见的。1921年8月,北京政府内部开始协商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代表人选时,梁士诒曾经表示“应召集沪上知名人士,代表团成员由他们认可”,这种公然的指手划脚,令时任外长的颜惠庆十分反感。(注:上海档案馆编:《颜惠庆日记》第2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当1921年底,徐世昌提出由梁士诒出面组阁时,颜惠庆曾竭力反对,认为因支持袁世凯复辟等政治污点,梁在全国民众中“其信用人格,早已完全破产”(注:《沪商反对梁士诒组阁》,1921年12月24日《新闻报》,第2版。)。虽然颜惠庆深知暂代阁揆仅为过渡,但仅代一周就被梁取而代之,颜“自亦不无怏怏”(注:沈云龙:《徐世昌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78页。)。他在日记中明确表示“我不愿意与他(梁)一起工作”,并向梁士诒提出辞呈,在梁挽留后,还“通过周诒春回绝了他”。(注:《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00—101页。)从颜惠庆的日记可以看出,梁颜间的矛盾在组阁之初已经萌芽。
梁士诒交通系的身份勿庸置疑,“颜虽然没有明显的派系身份,但是实际上他被认为是亲直系的人物”(注:黄静:《谣言与政坛风潮——梁士诒内阁倒台事件研究》(硕士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03年),第8页。)。叶恭绰曾指称颜惠庆作为孙宝琦的妹夫,与直系关系密切,称他加入靳云鹏内阁是“以张志潭的介绍”,而“中间颜、张拉线人却是江苏人宗舜(鹤?)年(常熟人,以一个不通外交的人,久为外交部科长、秘书)。后在颜内阁期间,曾为颜跑奉天,疏通张作霖,张作霖拒不款待,后来找张的秘书郑谦(鸣之),还表示以外交上的理由,希望延长颜代阁寿命。可见颜惠庆是热爱做官的,他是想久代转正的。”(注:叶恭绰述、余诚之录:《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189),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79—80页。)而颜惠庆本人在回忆录和日记中也有多处流露对于吴佩孚的敬佩与欣赏,称其为中国的“鲁登道夫”(注:颜惠庆著、姚松龄译:《颜惠庆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12页。)。
曾任《民生报》总编、江西督军署驻京代表的齐协民在回忆录中则更明确地道出颜惠庆与直系之间的渊源,称1917年府院之争时,帮助黎元洪争取英美两国支持的就是当时刚从欧洲卸任回国的颜惠庆,从此后,“颜惠庆与直系军阀的勾结”,“就更深入了一步”。(注:齐协民:《我所知道的军阀官僚一些内幕》,党德信等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997页。)由此可见,有关颜氏与直系关系紧密的传言绝非无因。
倒梁风潮
北洋政权是一个在“宪政框架下运作”的“由派系构成的政治体制”,而“各派系都不可能产生压倒性的组织力量以扼制对手并长期操纵政府”(注:〔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289页。),即便某一派系据有总统或总理的职位也无济于事,他的对手们仍然能够通过国会、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中外资银行以及地方军阀或联合、或分头攻击谩骂,散布谣言,撤回资金,拥兵自重,直至取而代之。这样的政治闹剧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循环反复,不断上演;主角轮流担当,配角或群众演员轮番出场。外交上的进退变化常常能够演成派系斗争的导火索,1921年的“倒梁风潮”和“梁颜政争”的导火索就是中日间有关胶济铁路问题的谈判。
1921年11月12日,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意在解决巴黎和会所遗留的国际问题,重在商讨限制海军军备竞赛和东亚国际局势。拒签《巴黎和约》给当时中国政府的对外交涉造成诸多不便,因此南北政府都对此次会议寄予厚望。时任外交总长的颜惠庆原拟亲自赴美,后在多方斟酌后派出了以驻美公使施肇基领衔,驻英公使顾维钧、大理院长王宠惠和广州政府外交部次长伍朝枢(后未赴美)为代表,由130余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出以“各国尊重并遵守中国领土完整及政治行政独立,中国不以本国领土割让或租借于任何国家”为核心思想的10项原则,所涉问题包括主权领土完整、关税、铁路等等。(注:北京政府外交部编:《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1923年印行,第59—60页。)
华盛顿会议开始前,中日间在有关山东问题的谈判方式上就已僵持不下,后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把会谈形式改为“边缘会谈”才得以解决——中日两国代表单独谈判,但美英派出观察员,且无论协商结果如何,都必须列入大会记录。这是中方为竭力避免直接谈判的嫌疑,一再坚持的最终结果。因为早在华盛顿会议开始之前,国内已经舆论鼎沸,包括梁启超这样的社会名流都坚决反对中日就山东问题直接交涉,寄望于华盛顿会议公开的、多边谈判的方式。(注:参见《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69、71页。)
“边缘会谈”开始后围绕山东官产、海关和公产等问题中日间渐成协议,惟独围绕胶济铁路诸问题双方分歧严重,争执不下,而胶济路的赎回方式更成了这一争执的焦点。中方先后提出“现款赎路”和“以国库券形式分期支付”两个方案,而日方则坚持“中日合办”或“借款赎路”。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国内对于收回胶济路的呼声甚高,很多民众甚至希望完全无条件地立即收回山东权益,各民众团体在国内掀起反日高潮,各地发动集会请愿,矛头直指北京政府,希望政府在对日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注:有关华盛顿会议前后的民众运动情况参见来新夏《华盛顿会议与中国民众运动》,《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颜惠庆不得不亲自出面,代表外交部向集会群众保证政府会尊重民意,努力保全山东主权。
正当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与日本人谈判拉锯时,国内局势风云突变。12月27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晤见颜惠庆,“问中国是否愿意为铁路借款,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就停止谈判”。颜惠庆将此事提交内阁会议讨论后,决定由叶恭绰以交通总长的身份答复小幡中方尚无此方面计划。(注:《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03页。)12月29日,小幡以贺新名义拜访梁士诒,他与梁的谈话内容如今已无案可查,在《日本外交文书》里也遍访不见,颜惠庆日记则对此语焉不详,只称“小幡见梁,表示日本愿意支持他。梁谈起向日本借款;关于借款自办铁路;安福系流亡等问题。”(注:《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04页。)
外交部于12月31日发往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的106号电称:“小幡于29日访晤梁揆,切询胶济办法,告以拟定借款自办,至一切细目,仍由华府商之。”(注: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3—484页。)该电只称“借款自办”,并未指明是借内债(即中方提出的国库券形式分期支付)还是借外债(即日方提出的借款赎路)。也许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措辞导致日后事态失控。106号电抵达华盛顿后,立即就传为“借日款自办”,并在美国和中国的各大报章上大加披露。(注:如1922年1月5日的《申报》登载了在华盛顿的国民代表蒋梦麟的电报,称“昨梁士诒专使嘱借日款赎路,用意可知。鲁案危机,专使决否认北京训令。请速反抗北京政府,并组织机关速筹路款。”再如1月7日的《新闻报》也报道了“闻由日借款一节,小幡已得梁士诒允诺”等消息。)日本代表也将小幡在北京取得的所谓“成果”大肆宣扬,一副成竹在胸的架势。这一变化令中国代表团深感挫折与委屈,他们于1922年1月2日以电码可能有误为由,请求北京外交部就小幡与梁士诒会面一事“详情迅赐电示”(注:叶恭绰的《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一书详引此电,称出自“外交档案钞档”(第248页),但郭廷以在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2年正月至二月卷)时则称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的外交档案钞档中未见,但同时也承认“外交档案钞档所不录者,似钞档遗漏或散佚颇不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印行,无出版日期,第62—63页)。)。1月5日,外交部发107号电解释“所谓借款自办,即赎路自办”(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中日关系史料——山东问题》(下),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版,第380页。)。但实际上“借款自办”难免举借外债,路权又将操纵于外人之手,为国人所反对;而“赎路自办”是指国人自筹现款赎路,是国人所支持的;两者在概念上有本质的区别,外交部如此解释未免太过牵强。
在107号电发出的同日,远在洛阳的两湖巡阅使吴佩孚公开发表“歌电”,打响了直系倒梁的第一炮。在“歌电”中,吴佩孚详述“边缘谈判”的前因后果,指称梁士诒“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纵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我全国父老兄弟亦断不忍坐视宗邦沦入异族。祛害除奸,义无反顾。”(注:《公电》,1922年1月7日《申报》,第2版。)吴佩孚的通电及时准确得蹊跷,他身在洛阳,远离京畿,却对外交部与中国代表团之间的往来电文一清二楚,难怪事后交通系指责颜惠庆有勾结直系的嫌疑。
当日,梁士诒立即“通电报告交涉现状并征全国意见”,表示“前次迭经在美磋商,我均主筹款赎回自办。至筹款办法,或发债票,或发库券,不论向国外筹款,均以在截清先后界限,申明该路收回自办性质为要义,仍拟先尽向本国商民筹借,以期稍挽利权。”但梁氏在该电中仅解释12月27日小幡晤颜惠庆时北京政府的答复是“仍主赎路自办,未变初旨”,却绝口未提两天后他本人与小幡会晤的情形,这也不免引起人们更多的猜想。(注: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民国丛书》第2编“历史·地理类”85(影印本),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180—181页。)
1月7日,梁士诒不得不再次发表公开声明:“士诒视事以来,对于此问题,商询同僚,迭次会议,多持筹款赎回自办之主张。前此外交部训条,所谓漠然借款形势者,持论具有深意,盖自办必先赎回,赎回必先筹款,若筹诸国内而立可得三千万日金之巨款,自一切无复问题,否则无论其为债票、为库券,期无论短长,还无论整零,其为债一也,其为分年偿还一也。盖既无现金,只言赎路,将以何物为赎?则不得不出于库券与债票一途,事理灼然,无可讳言,亦无庸再计。故筹款赎回自办之主张,其上固望国人之自筹,否则国内外合筹借款,亦可两害取轻,要未尝言及限于日本,亦非但尽日本也。至于交涉方式,自有常轨,小幡公使前来贺任,原为礼节之常,并非交涉谈判。”(注:《公电》,1922年1月7日《申报》,第2版。)从梁士诒的声明来看,他认为以库券或外款并无本质区别,均是举债而已。
因此,声明非但未能平息民愤,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反梁热潮。7日,齐燮元、王瑚、萧耀南、刘承恩、陈光远等直系各路干将纷纷通电讨梁。(注: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2年正月至二月卷),第57—58页。)8日,太平洋会议协会、上海总商会、上海各路总联合会、上海工商界、第二师范等单位团体又都发出“反对鲁案交涉、反对借款赎路”的呼声。(注:《本埠新闻》,1922年1月8日《申报》,第3版。)甚至梁士诒的家乡父老也痛骂其“为乡里所不容”(注:《本埠新闻》,1922午1月12日《申报》,第4版。)。
吴佩孚仍然穷追猛打,随后接连发出“庚”、“真”等通电,19日,更是联合苏、赣、鄂、鲁、豫、陕等省军政长官齐燮元、王瑚、陈光远、萧耀南、刘承恩、田中玉、赵倜、张凤台、刘镇华和冯玉祥等北洋系军人致电徐世昌大总统,要求或“立罢梁士诒以谢天下”,或“解佩孚等之职以谢梁士诒”,并表示与梁士诒内阁断绝关系,同时又联名致电各国驻华外交使团,声明“凡梁士诒内阁任内所有对外私订条约,概不承认有效”,甚至不惜以大兵压境相逼。(注: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6页。)在四面楚歌中,梁士诒不得不于1月25日通电下野,颜惠庆再代阁揆。
国内的这场倒梁风潮给华盛顿的“边缘谈判”造成了不小障碍,一度陷入停顿。后来美英代表马克谟和蓝普生在中方的要求下非正式提出4种调停方案,才使中日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边,日本代表据调停案提出的修正案获得了英美的认可。(注:日方修正案为:同意中国以国库券形式赎路,期限15年,5年后可先行付清;该路雇中日会计长各1人,职权相同,并雇日人为车务长。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22,Vol.I(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p.942。)经此延宕,华盛顿会议已近尾声,美英两国对中方的坚持失去了耐心,美国国务卿休斯向顾维钧等人施压,称“华会将闭幕,现在确切解决之时机已到中国国民与代表之前,失此不图,则机会决不再来,即欲再行集会,势亦有所不能”(注:《收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2年1月21、24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中日关系史料——山东问题》(上),第414、416页。)。1月25日,美国总统哈丁更是亲自向施肇基施加影响,希望中方接受日本方案。同时,美国驻华公使舒曼也向颜惠庆表示,如果中方选择决裂,将无法指望再从美国获得支持。(注:"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Jan22,25,1922",FRUS,1922,Vol.I,pp.942—945.)在多方压力下,颜惠庆于1月26日向中国代表团发出了签订有关山东问题协定的全权授权书,2月4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在美英代表的监督下得以签署。条约接受了日本的修正案,同时对将胶州湾德国旧租界地交还中国、日本从山东撤军等问题都做了具体规定。(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08—212页。)
库券还是日债?
那么1922年的北京政府有无现款偿付或发行库券赎路的能力呢?(注:因内债发行陷入困境,公债不再受到欢迎,北京政府从1922年开始改发“库券”,一般数额较小,用于应急。参见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自北京政府成立以来,“各省区又以政变迭出,军费日增,截留应解之款,而以为未足,复日仰给于中央。应之则库空如洗,罗掘无由;不应则函电交驰,追索益急。”(注: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政府》第4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406页。)“1921年,中央能够指派解款的省份只有2个,解款金额为366万银元。”(注: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10页。)但实际上中央政府分文未得,因为“田赋与常关税,虽为国税,实则就地流用,厘金更为地方所赖以挹注,中央无从染指。因此岁出日增,而岁入且无确实之着落,弊在国税与地方税虽曾定有区分之界限,只以中央政令不能行之于各省,自各省截留盐税以来,而财政上之藩篱尽撤矣。”(注:章伯锋等编:《北洋军阀》第4卷,第417页。)正所谓,“吾国财政,自清之季,已渐竭蹶,至于今日而穷迫已极”(注: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卷,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页。)。截止1921年底,“中央政府已欠内债合四万万元以上。外债到1922年9月共欠128411244英镑,339729615法郎,12338689美元,4418185马克,162486102日元,规元银136917两,公法银16610两,行化银2202879两,银元5211870元。”(注:马陵合:《吴佩孚的筹饷与其沉浮》,《安徽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
财政上的困难极大地限制了直系政府在外交和内政上的作为,“中央各机关及内外债权之索欠,既以应付俱穷,绝无活动之余地……日处此扰攘纠纷之中,中央与各省区,遂交受其困,而无振拨。循此以往,势必因财政问题之不能解决,牵及于政治及外交各问题,举凡破产之危机,共管之动机,实已迫于眉睫。中央既不能自存,各省区又宁能无恙,此非故作危言也。”(注:章伯锋等编:《北洋军阀》第4卷,第406页。)颜惠庆为筹措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的经费已是伤透脑筋,政府在外交上能够使用的资金相当有限。
当然,国人要求无条件收回胶济铁路也无可厚非。此路并非日人所造,系德国于1899—1904年间建造,全长约394公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德宣战,于1914年11月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其中就包括胶济铁路。日本当年攫取该路利权时并未费多少人力枪炮,但当中国要求赎回路权时却索价高达4000万日元,而对于财政濒临破产的北京政府而言,4000万日元绝对不是小数目。(注:根据当时的汇率1银元≈1.1日元,1美元≈1.95银元;4000万日元≈4400万银元≈2256万美元。相关汇率参见许毅主编《北洋政府外债与封建复辟》,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附表三·北洋政府时期汇率一览表”,第614页。)
虽然,当时国内群情鼎沸,各省政府、政界要人和群众团体都相继表示愿意解囊相助,但实际上中国代表团通过上海银行公会秘密了解到,“募集到的尚不足五十万美元,而且据他们看来,有指望得到的总数不会超过两三百万元……从中国的经济与金融形势来看,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应加以考虑,即所需的款额即使真能募集到,也会在金融界产生货币危机,会剧烈影响中国外贸的主要港口上海的金融形势。因而……代表收到的电报中的诺言是靠不住的。而且,即使诺言能够兑现,交出二千五百万元这样一笔巨额外汇,会造成上海金融界的严重危机。”(注:天津编译中心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8—229页。)
北京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先后经历了滥举外债(1912—1915)和乱发内债(1916—1921)两个阶段,到1921年末,已经不得不使出“整理公债”的最后一招,靠借新债来偿付旧债。所以,到1922年时,北京政府的外债和公债发行都“已陷相对停滞状态,势成强弩之末。而且,在发行方式上及数额上均有所迁就。”(注: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15—23页。)显然,以当时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现款赎路几无可能,借内债赎路,恐在短期内也难实现。
因此,北京政府最后接受日方提出的修正案也属迫不得已,在华盛顿会议上签署之《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议决由中国以价值4000万日元的国库券于1923年1月1日将胶济铁路赎回,该券年息6%,每半年付息一次,期限15年,5年后可全部偿清,以胶济铁路财产及进款为担保。(注:许毅主编:《北洋政府外债与政府复辟》,第427页。)同日,北京与日本政府签订总额4000万日元(折合银元3600万)的借款协议。(注:许毅主编:《北洋政府外债与封建复辟》,第592页。)该笔借款在1926年前本息均能按期偿清,此后因军事影响,铁路运营收入锐减,再未能照付。(注:许毅主编:《北洋政府外债与政府复辟》,第427页。)
备受争议的颜惠庆
梁士诒倒阁的导火索是胶济铁路谈判,背后却是错综复杂的派系争斗。1921年冬,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同盟”浮出水面(注: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3年版,第129页;吴相湘《国父联系北洋皖奉各系的一些史料》,《现代史事论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1—82页。),吴佩孚决定先发制人,从推倒亲奉的梁氏内阁入手,以图确立直系对北京政府的绝对控制权。《颜惠庆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曹锟反对梁,吴佩孚、齐燮元等也反对梁?是张志潭在活动?梁与张取得谅解,拟通过与广州联合来推翻政府,所以对张提供经费。”(注:《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01页。)这种复杂的派系关系,恰给颜惠庆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力量。
吴佩孚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仅用“电报战”就战胜了财大气粗的交通系,实在是只有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政坛才可能出现的怪事。正如当时《大公报》一篇社评所称,“内阁置于军阀势力之下,得于此者失诸彼,危机所伏,一触辄发。吾人已司空见惯。况梁阁之组织,完全为一系色彩,今所得之反响,早在人意料之中。甲之所是者,乙以为非,乙之所非者,丙或转而非议其后。”(注:《论齐吴反对梁阁》,1922年1月11日《大公报》,第1版。)因此,“电报战”就成了北洋体系内部争斗历程的一个明显特点——“战争双方通常是雷声大、雨点小,通电多于交战”(注:罗志田:《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年》,《史林》2003年第1期。)。《申报》主笔杨荫杭早在1920年即注意到,当时战事“直与演戏无异”,各方并不“出其全力以从事于战”,反倒是“用其全力于打电报”。实是“诸公好‘滑稽’,以国事为儿戏”。(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5、126页。)在这场倒梁风潮中,吴佩孚棋高一着,不费一枪一炮就铲除异己,重新夺回了直系对于北京政权的控制权。
在这场倒梁风潮中,处于政治漩涡中的外交总长颜惠庆在其中的作为颇受人们争议。在各方力量均要求外交部澄清事实时,他仅于1922年1月7日向华盛顿发出108号电,轻描淡写地表示“院中晤谈,亦只一次,已由院另复,希更正讹言,免滋误会”(注:《秘笈录存》,第485页。)。此外颜惠庆从未替梁士诒做任何辩白。因此叶恭绰断言此一事件是“小幡故意虚构成直接谈判,藉以哗众取宠,邀功疑敌,其作用故不少;而颜惠庆则藉此将这顶白帽子给梁戴上,嫁祸给梁,从此他就一帆风顺,由胜利走向胜利,其作用也自不小。可是这位勇于任事的梁士诒,却不晓得颜惠庆暗中给他一箭,也没有料到小幡也正在此时拨弄是非,更没想到替美国奔走的余日章也乘机给他背后扎上一刀(注:当时在华盛顿的国民代表,另有蒋梦麟在得知“借日款自办”消息后通电回国,公开反对,在倒梁风潮中亦起到一定作用。),尤其是没有料到吴佩孚、张志潭是与颜惠庆连在一起,他们背后还有强有力的英美布下了天罗地网内外夹攻。”(注:叶恭绰:《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第228页。)
也有材料指明,当时命令梁士诒直接指示中国在美代表团采取“会外交涉”方式的是大总统徐世昌,而非颜惠庆。而后又是颜惠庆向吴佩孚通风报信,“训令非出自主管部门,乃由国务总理所径发”,颜惠庆在京洛之间传递信息,成为吴佩孚“在京之耳目”,互通声气,互为应援,实在是他“为自身计,正利用梁氏之倒乃可取而代之也”。(注:史后民等:《军阀祸国》,《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第79—80页。)
吴佩孚的亲信孙丹林是“歌电”的亲撰者,他回忆称当时“有一吴姓者由北京到洛阳,向吴佩孚面递一包东西之废纸,其上用铅笔书有百余字,大意为国务总理梁士诒,密电中国出席太平洋会议之三代表,告以鲁案将由政府与日本驻华公使直接交涉,毋须在太平洋会议上进行折冲等语”。而送来此讯的,是时任徐世昌总统府侍从武官的吴春康的胞弟,而吴春康是吴佩孚在陆军测绘学堂时的老师。吴春康的消息得自外交部办公厅第一厅厅长张效彬。张在外交部负责收发电文,发现了梁士诒致三代表的密电后,告诸吴春康,当时吴正在竹战,他在牌桌边找来一张废纸用铅笔录下电报内容,连夜派胞弟赴洛阳告密。后来梁士诒向颜惠庆追查此事时,张效彬向颜自承后就离职赴津,梁士诒也未敢追究。(注:孙丹林:《吴佩孚倒徐拥黎始末》,《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第385页。)从当事人的这段细节描写可以看出,给吴佩孚通风报信的虽然不是徐世昌、颜惠庆本人,但大总统府和外交部都难脱干系。
据《颜惠庆日记》记述,当靳云鹏内阁倒台时,直系曾经透过周自齐向颜惠庆表示想请他先代理4个月总理,而非1周。(注:《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63页。)《颜惠庆日记》虽于1996年翻译出版,但其中1922年部分却不幸缺佚,无法窥见梁颜政争的第一手资料。《颜惠庆自传》对于这一段倒有较详细的描写,但对梁士诒充满贬辞,称“此次内阁人选,奉系彩色过重,新政府的生命,难望长久,早在意料中……不久直系将领吴佩孚将军,号称中国鲁登道夫,即领衔对梁总理,通电攻击,措词十分严厉。指斥梁氏亲日蠹国,对日本公使要求我国借用日款,赎回胶济铁路,竟然让步接受,抨击尤烈。国人遂有倡议国民捐,代替借债赎路之举。此种爱国热情,用意可嘉,究亦无补实际。正值旁铄繁兴,外交关系微妙之际,梁总理履任未久,对于华府会议,中日谈判,不甚深悉,竟贸然接见日本使者(小幡酉吉),已属不智。他违反我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的宣言,对日本公使要求,遽作肯定答复,尤失计较。结果引起严重纠葛,招致舆论指摘,殆非始料所及。后来纵有文字更正,辞费而已。”(注:《颜惠庆自传》,第112页。)颜惠庆在自传中的这段总结陈词明确指斥梁士诒确曾允借日款赎路,与事发前后他本人的解释有很大出入,难以自圆其说,可信度不高。也有日本末次研究所的材料说,当时颜惠庆是同意“中日合办”胶济路,并对小幡酉吉有所承诺的。(注:《外交总长答へず(北京廿八日电)》,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日文资料》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页。)
当梁士诒称病请辞后,颜惠庆得以再代阁揆,对此他颇为得意,认为华盛顿会议期间,“总理与外长职务,目前最好一人担任,对于华盛顿会议的种种问题,可由一人负责裁决”(注:《颜惠庆自传》,第113页。)。由此沈云龙认为颜氏在“此番政潮中为惟一幸运之胜利者。楚弓楚得,原甚自然。其运用直、奉两系之矛盾对立,卒获得重登揆席,手腕亦自不凡。”(注:沈云龙:《徐世昌评传》,第688页。)颜惠庆认为中国在华盛顿会议的谈判中取得不少成果,他也有意“在华盛顿会议闭幕之后”,“约三位代表即行返国,重新组织内阁,以便实行此次会议所决议有关我国各案”。可惜,施、顾、王三位代表仅王宠惠一人返国,“时机一逝,国内政局,日趋险恶”,颜惠庆也难逃“代理”的宿命。4月4日,周自齐出任国务总理,颜惠庆短暂退隐,赋闲南下。(注:《颜惠庆日记》,第115—116页。)随后数月内,颜惠庆又是几上几下,沉浮不定。尤其是曹锟贿选后出任“光杆内阁”总理,难免给世人留下表面淡于名利,实际贪恋高位的印象。
外交与外债中的派系因素(注:此处所指之派系并非仅指直系、奉系、皖系这样的军阀“系”,往往在一“系”内部有更多的、各次级的“派系”,他们的关系除由军队、政府、企业团体中的上下级构成外,更因兄弟(结拜兄弟)、师生、血亲、姻亲、同乡、同门、同学和僚属等关系显得更为错综复杂。参见Andrew Nathan,Peking Politics 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方惠芳《曹锟贿选之研究》,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83年版,第61—64页等。)
围绕山东问题产生的“梁颜政争”因为裹挟着北京政府赖以维系的两大重要支柱——外交和外债,当可视为这一时段北京政府外交运作的重要案例之一。北京政府的合法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列强的承认与支持,外交部和外交事务显得空前重要。但是北京政府的大总统们除袁世凯外,其他人都“不大参与外交事务……徐世昌是个学者,受过极好的教育,由于长期与袁世凯合作,完全理解对外关系的重要性。但他虽关注此事,却缺乏自信,感到自己没有实际经验,因此将对外事务一任外交部去办。”(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92—393页。)
而北京政府的历任外交部长多由留学生担任,如颜惠庆、伍廷芳、顾维钧和施肇基等。事实上,清末留美幼童回国后,就已经在外交界崭露头角。(注:清末的100名留美幼童回国后,从事外交行政工作的有24名,其中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梁敦彦、梁如浩、唐绍仪是他们中的佼佼者。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布成立内阁,梁敦彦出任外务大臣,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第一次成为外交最高主官。)到北京政府时期,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已经成为外交队伍的主体,并在中国政坛逐渐形成了一支职业外交官队伍。他们较少受政府内阁更迭影响,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维系。(注:从1912年起,正式担任过外交总长的有王宠惠、陆徵祥、梁如浩、孙宝琦、曹汝霖、唐绍仪、陈锦涛、伍廷芳、汪大燮、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沈瑞麟、胡惟德、施肇基。除陆徵祥、孙宝琦、汪大燮、沈瑞麟等少数几人外,其余全是留学生出身。)随着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职能的日益完善,事务的日渐繁杂,职业外交官队伍也日益壮大,在派系林立、军阀纷争的北京政坛虽未能形成自己的派系,但也独树一帜,并多以中立自居。当然,因为留学目的国的不同,他们被自动地分成欧美系和日本系,并被贴上“英美派”或“亲日派”的标签。
有学者认为,“在北京政府时期外交部颇具独立自主性与专业决策权力,在执行攸关国家利益,全民一致支持的‘国策’时,较少受到实力军人的干预,在这一点上超过日后国民政府时期”。“职业外交家常以超乎国内党派政争自许,以追求国家民族的永恒利益为职志。这种特色,在北京政府外交家身上,表现得最明显。”(注:唐启华:《北京政府外交行政机构的演变》,《中华民国外交志(初稿)》,第248页。)这种超然的独立性也是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官们所特别标榜的。如顾维钧就坚持“当办理重要交涉时,惟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能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因为如果有了这些考虑,你的外交从民族利益的观点来看就不会成功。你要末牺牲民族利益实现你的政治野心,要末使谈判完全破裂。”(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97—398页。)
但是从本文的这一案例来看,在山东问题这样重要的外交实践中,外交官们的言行不仅受到派系政治的影响,而且像颜惠庆这样重量级的外交官实际上已经深深地卷入派系斗争之中,甚至能够成功地利用派系政争,成为政潮中惟一“幸运之胜利者”。在北京政府内办外交,要真正实现完全超脱于派系争斗之外几无可能,因为说到底,北京政府就是一个派系政权,而且在袁世凯死后没有哪个派系能够长时间、压倒性地控制中国的局势,光1917—1928年间,“北洋政权在直皖、安福、交通等派系的把持下,前后十二年间,十易国家元首,四十五个内阁,五个国会,七个宪法,动乱频仍,表面上有共和之名,骨子里为派系之实”(注:张朋园:《黎著〈北洋政治:派系政争与宪政不果〉》,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版。)。即便如顾维钧这样声称只考虑民族利益的人,也会或因与张作霖的多次合作被贴上亲奉的标签;或因多次加入直系内阁,而获得曹锟这样的直系大佬的绝对信任。(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68页。)
更何况,不倚仗或接近某个派系,不得到当权派系的首肯,这些外交官根本难以进入外交部主政,遑论入主内阁,主持国政了——往往内阁内部就是派系林立,关系复杂。比如,在梁士诒内阁中,“鲍贵卿、齐耀珊是属于奉系,高凌霨属于直系,颜惠庆、王宠惠属于英美派而接近直系,张弧属于亲日派的新交通系,叶恭绰属于旧交通系,李鼎新和黄炎培则无所属。这是一个直奉两系和旧交通系的混合内阁,而交通系的新旧两派则由分而合。”(注: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85回。)而颜惠庆则认为“阁员中,除司法总长王宠惠博士(时尚在华盛顿),教育总长黄君炎培,海军总长李君鼎新及我外,其余均属奉系。直系方面,则无一人入阁”(注:《颜惠庆自传》,第111页。)。
梁士诒组阁虽然得到奉系的支持,但却非总统徐世昌和外长颜惠庆所愿。除“段、奉、张”三角同盟对直系的打压,引起吴佩孚等直系军阀的不安外,梁士诒上台后,释放安福战犯、盐余大借款、起用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等,不断激起民愤,也成为他倒台的重要原因。
梁氏内阁阁员情况统计表(注:此表参照日本外急流务省外交史料官藏外务省记录:1门,政治/6类,诸外国内政:1项·亚细亚·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ノ部/奉直纷争第1卷,海军军令部海谍报第2712号。)
职务 姓名 出身派系
外交总长颜惠庆留美学生,上海人 英美派,近直系
内务总长高凌霨前清举人,天津人 直系
财政总长张弧 前清举人,浙江萧山人 新交通系
陆军总长鲍贵卿军人出身,奉天人 奉系
海军总长李鼎新福建船政学堂,福建福州人 无
司法总长王宠惠香港及天津北洋大学,广东广州人南方“系”,梁士诒好友
教育总长黄炎培留日学生,上海人 “近”交通系
农商总长齐耀珊前清进士,吉林人 奉系
交通总长叶恭绰留学生交通系
20世纪20年代,老交通系虽已过鼎盛时期,但力量仍然十分强大。梁士诒本身势力也不可小觑,他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藉由同乡、同僚等关系织就的关系网,这是他重要的政治资源。他还控制着一批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交通和银行部门,这是他关键的政治资本,令他即使在政坛失意时,也能让反对派心存忌惮。但是,颜惠庆这个并没有太多政治关系网的“职业外交官”在这场政争中不仅主动出击,把梁士诒拖入外交漩涡,还巧妙地利用军阀“电报战”,令梁几无招架之力。可以说,在这场政争中,颜惠庆成功地利用派系斗争,既争得了外交部对胶济铁路交涉案的控制权,也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在外交界和政坛的地位。
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外交体系成型和完善的重要时期,早在陆徵祥和颜惠庆执掌第一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时就已经着力于革新中国传统的外交体制,并取得一定成效。(注:参见《颜惠庆传》,第49-53页。)文本的制度虽然逐步完善,但在中国这样一个重政道、轻治道,重人治、轻法治,重权术、轻政术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即使出现一些表面上或可看作制度的“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也往往难以成为制度性的规范。
在北京政府这样一个主要由派系构成的政治体制中,虽然宪政政体表面成立,但始终无法避免基于派系的各种形式的政治冲突,在相对“独立”的外交界也不能幸免。更为糟糕的是,北京政府林立的派系集团往往并非现代意义的政党组织,各派系主要基于中国传统的“关系”而非组织制度而存续,各派系也不可能产生压倒性的优势从而长期操控政府。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中国的外交官们虽然表面上标榜独立与中立,但常常不得不依靠非正常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外交实践,甚至主动参与派系斗争。而当他们越来越深地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对于权力的迷恋也日渐加深的时候,“独立”和“制度”都是可以搁置和牺牲的。
标签:梁士诒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日本内阁论文; 华盛顿会议论文; 申报论文; 吴佩孚论文; 叶恭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