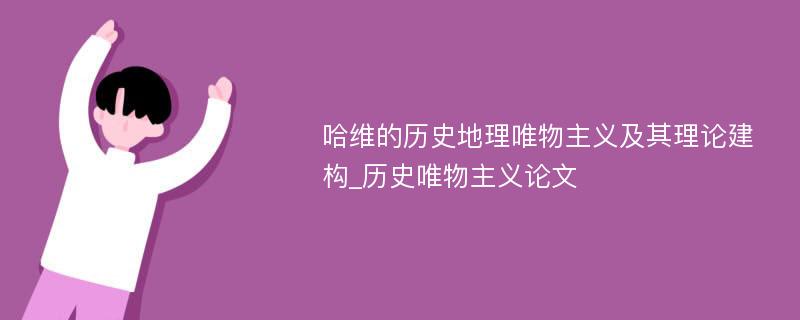
大卫#183;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及其理论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维论文,大卫论文,唯物主义论文,地理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是哈维空间理论的一个核心范畴,哈维提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旨在对内涵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理—空间维度的重申,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空间探索传统的积极重建,且在此基础上开辟一种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表达;同时,通过这种重申,试图建构一种有效的空间性话语和理论叙事,且这种话语重视日常生活的空间性,致力于解构传统叙事对空间的“捆绑”,并能动地回应当代处于深刻变迁的空间空践。用哈维自己的话来阐释:“我所关心的是,毋宁说,以这样一种方式来重建马克思的元理论,以便把一种对时空性的理解整合进其框架之中。”①
一、“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何以可能?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空间”是一个待植入的可能的外部变量?抑或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内含着一种地理维度?两者代表着不同的致思路径,前者显见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的各种空间隐喻,“空间”在其中被作为一种对传统的社会理论元叙事进行解构的概念工具,哈维对这一研究路径持审慎态度,认为“空间性”的嵌入可能导向无法通约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从而带来理论和实践的重重困境。后者是哈维致力于探索的,即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地理维度的新阐释,探索空间在理论和实践上被有效理解的方式。
(一)对地理学传统的知识论反思
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哈维曾醉心于实证主义地理学研究,在对实证主义地理学的批判性反思中,哈维认识到地理学的知识传统中对于价值的顽强抵抗,只会使地理学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渐行渐远,于是,他开始尝试寻求一种辩证的人文视野,以弥合地理学与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断裂”。
首先,对地理和空间的审视不能与生产它的社会过程分离。“地理知识的形式与内容无法脱离该知识生产和运用的社会基础而得以理解”②。地理学不是一个孤立的事实知识的容器,而是一种系统化的关于社会进程的空间表达,地理学的知识要素和问题形式取决于社会内容(the social context)。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自己的地理学,这种地理学涉及领土疆域、空间权力、对使用价值空间样态的塑造、地理和空间的文化想象等空间生产诸方面,生产方式的嬗变总是伴随着社会生活地理的变迁。哈维将资本主义时代的地理实践(geographical practice)归之为六个方面:一是领土权的精确界定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图学的发展;二是以探索新的使用价值为导向,对物理和生物环境的地理学描述;三是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地理变迁的关注,并将这一知识元素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构,如19世纪晚期的“商业地理学”已被异化为一种服务于殖民政治、帝国管理和市场开辟的工具;四是关注空间的政治安排及其后果;五是注重空间资源的有效利用,谋求人口、产业、基础设施、生态资源在空间上的合理分布,使之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社会控制;六是地理学知识体系中渗透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③。可以看出,地理学在资本主义时代正在经历深刻的变迁,这一变迁的现实语境是资本的空间拓展、商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与两者密切相关的专业和学术分工的变革,这些都为地理学的批判性重构提供了可能。
其次,地理学的知识论建构必须关注历史实践及其衍生的相关问题,地理实践必须重新面对自己的历史学。哈维对于地理学知识传统的反思主要立足于对现有地理学的重建,这一重建的重要路径是“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的转向,后者指涉着一种新的地理解释学,在这其中,“地理学的现状以及重建地理学的方案都必须牢牢奠基于其对历史的认识”④。这不仅源于对地理的多维阐释必须关注空间生产的“具体历史性”,地理学知识体系中的要素、结构和功能都是一种历史的生成物,更意味着走向未来的地理学之路必须与时俱进,回归对于持续变迁的社会需求和时代境遇的关注,这既构成对地理学的当代挑战,同时,亦为地理学的批判性重构提供了出路。“历史地理学”不仅要关注历史进程中的空间生产,更要致力于探讨特定历史过程的空间诉求和空间构型,地理学的知识论框架必须引入历史经验和历史想象,“历史地理学”将为摆脱地理学科诸多的二元论(如实证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困境提供有益的启示。当代地理学(包括物质生产的地理学和日常生活的地理学)必须将对历史的关切整合其中,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再次,新的地理学探索必须关注地理学的文化属性与价值重建问题。哈维认为,实证主义地理学将地理学绝对中立化的预设会面对诸多现实困境,也使地理学研究成为独立于社会历史进程的“绝缘体”,哈维呼唤一种地理学研究的新气象和新视阈,这其中,地理学将致力于在宏大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探寻自己的“立场”。哈维强调,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的“历史”和“地理”,尽管这种创造并不是在我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进行的。地理学需要建构某种“应当”,这种“应当”关涉的正是我们究竟要创造什么样的“历史”和“地理”的问题,是资本主宰下的充斥着金钱政治、阶级偏见、物质剥削的“历史”和“地理”?还是尝试探索某种超越物质必然性的自由王国,这其中,人民有权利以自由的原则和对多元利益的尊重来创造自己的“历史地理”?如果是前者,人的积极存在何以彰显?如果是后者,这种变迁和转型的社会动力学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涉及“历史地理学”价值向度的核心层面。哈维重申了作为地理学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强调地理学应当是“人民的地理学”⑤(people's geography),这种地理学有自己的群众基础,并深深扎根于人民意识中,这种地理学是一项“政治事业”⑥(political project),其基本目标在于,以历史地理的眼光关注从资本主义向作为其替代性方案的社会主义的转换。新的地理学探索应当关注民主精神的空间培育,致力于开辟新的沟通和共同理解的可能性,在文化的普遍理解中植入地理的敏感性。在这个过程中,推进地理学与社会理论的交汇,开启新的世界概念以及空间干预的可能选择。
(二)对传统历史叙事的话语批判
“空间”长期以来仅仅是一些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些传统空间学科包括:传统的地理学、建筑学、城市学等⑦。后者通常把“空间”当作一个纯粹的科学对象,“空间”在这种研究视阈中体现为一种单向度的、可以被量化的物理空间,事实上扮演着人的实践活动“容器”的角色,空间的社会意蕴长期被湮没在主导性的历史叙事中。因此,也就有了福柯的经典陈述:“从康德以来,哲学家们思考的是时间,黑格尔,柏格森,海德格尔。与此相应,空间遭到贬值,因为它站在阐释、分析、概念、死亡、固定还有惰性的一边”⑧。
作为19世纪的话语体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经常被认为是一种湮没了地理想象的历史叙事,“空间”在其所勾画的世界图景中被抽象化为一种被动的地理容器。与之相适应,历史唯物主义所阐发的历史规律,也主要体现为一种线性的决定论和对多样性差异空间的抵抗,这种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充斥于当代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和被哈维称之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之中。美国当代人文地理学家苏贾(Edward W.Soja)就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并不仅仅限于其体系的唯心主义,更指向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潜藏着的空间主义本体论,后者以领土国家、绝对精神运动的空间表达为基础⑨。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历史”,空间是否游离于其外?哈维的思考与其深入扎实的马克思文本阅读是分不开的,这一思考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空间内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视阈中。哈维指出,马克思承认空间和地理的重要性,体现在马克思对于城乡对立、生产力向都市的空间聚集、分工的地域性、价值规律运作的地理差异和世界市场等问题的关注,城市化、地理转型和全球化在历史唯物主义探讨中占据着显著的位置,马克思关注资本积累与空间拓展、阶级斗争与空间策略、物质生产与空间资源、殖民统治与空间差异等空间议题,这些议题中有些虽然未能系统展开,但马克思的文本中蕴含着巨大的空间分析的张力,这一点值得我们认真挖掘和系统梳理。《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文本,哈维深入探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地理学,认为“关于地理转型、‘空间定位(spatial fixes)’和不平衡地理发展在资本积累的漫长历史中的作用,《宣言》包含了一个独特的论证”⑩。《共产党宣言》详细阐释了资本主义是如何生产自己的历史地理学的,资本主义的矛盾最初体现为一个特定地理范围内的资本过度积累,为了缓解过度积累的危机,资本主义求助于“空间修复”,将无法释放的资本向更大的地理空间转移。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地区和社会形态不平衡地嵌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进程,资本积累的“地域历史地理学”开始向“全球历史地理学”转变,资本的基本矛盾也开始跨越地理和文化的特殊性,并在全球空间带来危机的普遍性。
其次,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统摄于实践的总体视阈中。哈维将“实践”作为马克思最为鲜明的理论旨趣,指出“马克思洞悉到了在他之前的所有人都没有能洞悉的问题,那就是困扰西方思想界的无数的二元论(在人与自然、事实与价值、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身体与心灵、思想与行动之间)只有而且必须通过作为人类实践的生成物而得以解决”(11)。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历史”,是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产物的“历史”,而“时间—历史”维度和“空间—地理”维度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基本维度:前者关涉实践活动的“历时性”,后者关涉实践活动的“并时性”。因此,以实践为基石的历史认识论是与单向度的历史决定论相悖的,它始终面对的是正在生成中的历史,马克思警惕和质疑对历史的普遍性阐释。在历史认识论中一直存在着两个向度:一是作为历时性的“过程”,一是作为这一过程空间投射的并时性“结构”,两者在马克思的实践视阈中不是割裂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其现实路径是在历史再现中融入空间变迁、将空间多元性引入总体性的历史审视。
再次,空间的阐发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是不充分的、待发展的。哈维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存在着使空间分析在对社会过程的关注中被遮蔽的风险,马克思的文本虽然内含着敏锐的空间视角,但总体而言缺乏对于社会过程中多样化空间及其生产过程的深入探讨。马克思的空间分析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他虽然提出了一些有洞见的空间论断,总体上缺乏一种空间分析的元理论的支撑。由于时代境遇的不同,马克思的空间阐发受到了他所处时代的具体历史地理性的制约。比如,《共产党宣言》关于“野蛮民族”和“文明民族”的划分存在着忽略民族国家空间多元性的理论倾向;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中心—外围”模式的探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地理不平衡发展与资本积累的内在联系。此外,在资产阶级权力与地缘政治策略、资本积累与领土构型(territorial configuration)、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政治行动与地理重构等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尚待深化,这也正是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致力于发展的重要领域。
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阐释路径
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可能的阐释路径有哪些?在这一点上,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是必要的,这源于“马克思主义运动具有可观的历史和地理力量”(12),以下我们将尝试结合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和哈维的相关阐述加以探讨。
(一)历史的观念与空间
历史的观念从哪里来?是从先验的理性出发,抑或只是主观分析的产物?这是历史研究中的元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彰显了历史哲学的不同面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从“物”到“心”的唯物主义致思路径,认为历史观念的生成源于人的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历史的观念正是对这些经验材料加以抽象的结果,而作为历史观念生成的基石,经验材料本身具有空间性。
首先,现实的历史总是储存在特定空间中的历史,“空间”是对历史的经验材料进行描述时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是与特定的“场所记忆”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场所是存在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3),场所本身构成把握历史的重要线索和历史再现的物质载体。福柯指出:“我们的世代相袭是空间带给我们的,是因为场所间的不同关系而形成的。”(14)哈维也将“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作为研究欧洲现代性的典型个案,奥斯曼对巴黎的城市改造传达的正是这一时期巴黎社会复杂的历史变迁过程,改造后的巴黎景观处处都记录着与传统社会过程的断裂,见证着现代性之都的历史生成。
其次,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空间相关性是历史叙事的重要内容。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历史人物从来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人,是被特定的社会空间塑造、打上了鲜明的社会空间烙印的人,同样的,历史事件本身不过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行动,后者有着特定的时空属性。作为历史链条上的不同节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是在动态的时空建构中被定义的,其差异性正是源于时空建构过程的差异性。当我们言说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同时就是向那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一种“回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空间相关性,要求我们在进行历史评价时充分考量这种相关性。
最后,各种以物理空间样态存在的古迹、废墟等本身就构成了鲜活的历史文本。对古迹、遗址、废墟等历史景观的考察是获取历史材料的重要渠道,“为了保存群体的历史和思想,景观充当着一个巨大的记忆系统”(15),作为一种“历史的空间”,历史景观既是历史活动的空间印记,也是历史记忆的存储器,它们能够传达多维的历史信息,表现特定的物理、生物、社会或文化的历史过程,它们是一种文化地理现象和空间隐喻的符号。历史的时间序列中充斥着大量的物理空间符号,它们是历史的重要表征方式,是无声的历史话语。空间从来不是历史再现中可有可无的外部因素,而是内在于历史叙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地理的历史,是一幢没有地基的建筑”(16)。
(二)历史的本质与空间
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本质的探讨置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视阈中,以实践的视角审视历史,历史不是某种在时间里游走的神秘的抽象物,它的根基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本身,包括现实的物质生产及其所决定的精神生产的多维性。
作为历史根基的社会生活具有空间性,这种空间性首先体现在人类对于“地理环境”的依赖。“地理环境”在历史的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生态资源、生物资源和矿物资源,是人类赖以存续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关注地理环境对物质生产实践的影响,并将“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共同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内容。他区分了“自在的自然”与“人化自然”,“自在的自然”关涉我们的活动尚未到达的地方,既是我们的有限活动能够无限扩张的可能性空间,亦是尚未被人的实践活动所规定的自然。当“自在的自然”一旦成为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时,它就与人的活动建立了联系,成为被人的实践活动所改造和塑造的“人化”的自然空间。人的能动的“类”本质决定了人不像其他生物那样仅仅让周围的环境“同化”自己,而是主动地在外在空间打上自己的“烙印”,通过不断干预和改变外在空间,将人的内在目的性加诸其上,从而建构一个“属人”的世界。
除了自然空间,历史唯物主义视阈的空间还包括抽象的“社会关系空间”,它是一切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社会条件。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7)人在能动地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建构了与改造自然的现实能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两个过程是同时进行的,人与人之间不结成一定的关系,现实地改造自然的进程也无法进行。在这里,“社会关系空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人类在改造自然空间的同时,亦进行着一种特殊的“空间的生产”,即“社会关系空间”的生产。
由是观之,关于历史本质的探讨不能脱离始终处于流动和变迁中的社会生活及其呈现的空间样貌,历史的真相就潜藏在人类周而复始、永不停歇的空间探索中,停留在人类对空间的不断建构与解构的空间实践中。人类在空间中存续,也在空间中迷失;在空间中确证自身,亦在空间中消解自身。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历史即是空间变迁中的存在。
(三)历史的规律与空间
历史的规律是何以可能的?如果可能,这种规律是何种意义上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视阈的历史规律不是某种去空间化的历史决定论,而是自觉地将空间的特殊性和差异纳入其中,是在充分承认历史的具体多样性的基础上对历史进程所进行的抽象。
历史规律是历史多样性的统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的发展不仅体现为时间的持续性和历时性,同时,历史进程的具体展开又伴随着空间的延展性和并存性;后者关涉各种社会空间的差异所导致的多种社会形态的相互渗透和共存,它是人类社会体系多样性的体现。只强调“历时性”而忽视“并存性”,就会消弭历史存在的多样性,从而导致一种“独断论”——社会历史进程在其中被界定为某种“线性运动”,历史运动的多向度性和复杂性在其中被剔除了。这种超历史的“历史哲学”只承认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而忽视了其中的“多”,因而无法解读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出现的“跳跃”和“超越”现象,这种历史哲学及其致思路径是马克思一直致力于扬弃的。
以马克思对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探讨为例,在这其中,“历史的跳跃”之所以可能,一是源于俄国特定的社会空间状况,比如保存至今的“农业公社”模式;二是俄国与“西方生产”的并存,这种“并存”使其能够利用资本主义的成果来发展自身,这种并存性的影响在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体系后更为凸显。资本主义以“世界市场”为动力揭开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新篇章——“世界历史”,如果我们对“世界历史”这一范畴进行简要的语义分析的话,那么,这里的“历史”传达的主要是一个“社会时间”概念,而“世界”则主要是一个“社会空间”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时空结合体。马克思从来都不是抽象地谈论“历史”和“存在”,他视野中的“历史”实质上是处于一定社会空间的人的现实活动,社会历史规律相应地体现为一个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社会空间的重组与转换,历史的现实过程是线性的相互作用和非线性的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
历史规律是在多样性的历史存在中得以表达和呈现的,这种多样性为历史规律的抽象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事实,没有这些经验事实,历史规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些经验事实最初是纷乱、杂多和无序的,历史规律的探寻就是要从中剥离出历史过程的各种“杂多”,呈现历史之流的“主干”。
(四)历史的动力与空间
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发展的动力归之为每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矛盾运动,主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现实地体现在空间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诸环节。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矛盾具体化为不同阶级空间享用上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抗和斗争,这使“空间分异”成为所有阶级社会的共有特征,这种分异不仅体现在作为生产资料的空间(如土地),更体现在作为生活资料的空间(如游憩空间和居住空间),在这里,空间内在于历史发展的动力体系中。
以居住空间为例,其生产本质上是现实的生产关系建构其空间秩序的过程,每一种社会关系体系都会生产自己的居住空间形态,居住空间既表征着社会关系,又受到特定社会关系体系的制约。马克思在《资本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论住宅问题》中对城市居住空间进行了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城市居住空间的生产中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空间剥夺,在这一过程中,城市雇佣工人的居住权被资本的空间权力所宰制。马克思将“空间剥夺”与“级差地租”、“城市贫困”的探讨结合起来,在谈到城市建筑地段的地租时,马克思指出:“垄断价格在许多情况下的优势,特别是对贫民进行最无耻的剥削方面的优势……在这里,社会上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要求一种贡赋,作为后者在地球上居住的权利的代价,因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土地,剥削地下资源,剥削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18)。
哈维将“阶级”理解为一种基于特定社会过程的空间构型,将阶级斗争理解为一种组织化的空间抵抗。“空间”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承诺的重要砝码,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阶级利益融入“历史的合力”之中,并与空间政治学密切联系在一起。哈维深入阐释了《共产党宣言》的地理维度,指出《共产党宣言》中的相关探讨把握了19世纪阶级斗争发展的某种共性,在其中,阶级斗争依赖于对地理重构、空间策略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整体审视。相应地,新的替代性社会方案必须充分考量阶级斗争的地理维度,深入评价地理事实和空间整合的多种可能性,包括政治设计方案对于不同社会空间和地理环境的敏感性,马克思所批判的“德国式社会主义”正是忽视了这种敏感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探讨首先是根植于各种空间差异的,是在空间多维性中建构的一种普遍性,在这里,历史的张力潜藏于多样性的地理事实中,探寻历史变迁的核心动力,必须关注历史过程中持续性的空间建构与解构。
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展开
哈维关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探讨是与其“过程辩证法”联系在一起的,两者互为表征。从历史上到当代关于辩证法一直存在诸多争论,这使辩证法及其相关研究成为了一个歧义丛生的领域。
(一)历史辩证法是一种“过程辩证法”
哈维关于辩证法的思考受到了怀特海、奥尔曼和大卫·波姆阐发的“过程哲学”路径的影响,哈维认为他们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有亲缘关系,同时,亦从列斐伏尔“时间—空间—社会”三元辩证法中获得了有益启示。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中,哈维将辩证法原理阐释为“过程”,认为“要素”、“物”、“结构”只有在“过程”、“流”、“关系”中才能被界定和把握,物的异质性在于创造其过程的异质性,对离开了过程的纯粹的“要素”、“物”、“结构”的研究只适用于理论分析的必要抽象。矛盾内在于作为过程的辩证法,矛盾双方是由两个或多个内在关联、既统一又对立的过程支撑的,在其中,思想和行动、理论和实践、心和物之间的笛卡尔式的对立和断裂被消弭。
哈维认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石的“历史辩证法”是一种“过程辩证法”,在其中,历史唯物主义体现为一种社会过程的理论表征,是社会过程的历时性结构化的产物,它体现着特定的社会关联模式。生产关系、资本、阶级、需求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其本质都体现为一种社会过程的建构物。哈维认为,“过程辩证法”是与马克思的实践观相契合的。在1978年发表的《对抗马克思主义的迷思》一文中,哈维就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整体论(holistic),这种整体论尤其关注部分如何与整体产生关联。整体并非其成分的加总,也不是具有独立于其部分之外的某种意义,整体是‘具有内在关联的各部分的整体’,各部分作为‘一种可以拓展的关系,每个完全的部分都可以代表整体’”(19)。马克思对辩证法的思考始于黑格尔,通过对其进行彻底的唯物主义改造,成功地将辩证法注入其实践之流。“实践”是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基点,实践昭示的不是某种僵化的结构,而是一种不断生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本体论和认识论、可能和现实、历史和地理等内在于其中,彼此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它们的并存与统一体现了辩证法的特有张力。
基于过程的辩证法内含着时空维度,因为“过程并不在时间和空间中发挥作用,而是积极地建构它们,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为它们的发展定义出与众不同的规模”(20),在这里,时间和空间同时根植于“过程”之中,而每一种特定的“过程”本身都会生产不同的时空属性。在对传统历史叙事的话语重构基础上,哈维指出,相对于对“历时性”的时间维度的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更需要认真对待的是“共时性”的空间问题,空间、位置、规模、环境等地理学范畴,应当成为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了解世界的核心,如列斐伏尔所言:“今日的辩证法已不再拘泥于历史的真实性和历史的时间,也不再受制于‘正题—反题—合题’或者‘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的时间结构,要认识空间,认识空间里所发生的事情及其意图,就要恢复辩证法,这种分析将会揭示有关空间的诸种矛盾”(21)。
哈维认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代表着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过程辩证法”是这一范式的核心。“‘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一种无限制的和辩证的探究方法,而不是某种封闭和固定的理解实体。元理论并不是对总体真理的一种陈述,而是与历史和地理真理达成协议的一种努力,那些真理在总体上和在现阶段赋予了资本主义以特征”(22)。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应该始终保持着对于差异和他者的开放,致力于探讨空间自身是如何通过社会过程得以建构的。历史的普遍性与差异性作为一对辩证统一的范畴,并存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框架体系中,前者是作为总体性的抽象的历史,后者是作为特定社会情境的具体的历史。从“过程辩证法”出发,资本主义所表征的也只是人类宏大历史过程中的某种具体的“历史地理性”,“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没有所谓‘自然’的基础,它们只是特定历史过程的产物”(23),而时空的重组与变迁就潜藏于这一具体的历史过程之中。
(二)社会过程与空间的生产
哈维将“社会过程之流”具体阐述为以下六个环节:话语(discourse)、权力(power)、物质实践(material practices)、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制度和仪式(institution and rituals)、想象、欲望和信仰(imaginary,desire and belief),它们共同建构了一个再现社会过程之流的辩证的“认知图式”,这一“认知图式”不是要建构某种社会过程的元理论,而是旨在强调“社会过程流入、贯穿并包含着所有这些环节,并且每个个体的行为都同时包含所有这些环节”(24),这些环节是社会过程的表征,其中每个环节都通过社会过程与其他环节建立联系和实现转换,哈维还分别阐释了这些环节的空间意蕴。
1.话语。话语的表现能力与沟通行为本身是以一定的空间辐射为前提的,话语的实践有赖于传播学意义上的地理半径,后者建构了一个“语言的空间”。话语的建构与解构有着特定的空间指向,话语规则中内含着对“结构”、“边界”、“框架”的空间性诉求,这一规则具有社会属性,并受到实践水平的制约。话语体系中内含着权力博弈及空间政治。话语形态直接指向了政治权力的空间场域,后者划定了政治权力的作用边界,不同政治权力系统会生产不同的话语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构成了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而话语霸权的形成往往需要一种压迫性的政治经济权力的支撑。作为文化符号的话语是培育信仰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心理空间的重要载体。话语是文化的载体,它不仅表征着真理,同时,也作为文化反思的重要领域。
2.权力。每一种权力体系都对应着一幅空间地图,标识着权力作用的边界,跨越边界将带来权力的僭越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权力的争夺也往往与统治空间的重新分配密切相关。权力体系现实地塑造着空间生产的样态。在权力体系所划定的空间边界内,权力关系会生产出与自身相契合的空间样态和空间美学,后者是权力关系的空间表达。“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25)。空间是凝固的权力文本,权力的空间生产一直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内容。权力秩序的建构具有空间性。权力秩序的安排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权力分配机制得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空间格局得以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其中占据不同的位置,每一个位置都是权力的一种空间隐喻。
3.物质实践。物质实践着眼于对经验空间(包括自在的自然空间和人化的自然空间)的能动改造,它提供了社会生活的基本物质条件和可能的空间视阈,是我们全部空间知识的来源和基础。“客观空间和时间的社会定义深深扎根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之中”(26),这一定义以对物质世界空间属性的探索为前提,方位、地理、区域、场所等空间概念都是在现实的物质实践中、在人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的。物质实践活动伴随着人对赖以生存的外部空间条件的不懈求索,在物质实践活动中,人形成了对于作为“大宇宙”的外部世界和作为“小宇宙”的人自身的观望和认知,物质实践使人能够穿梭两种不同的空间视阈,在广袤的宇宙空间中探寻人何以存在之“根”、如何存在之“轨”,从而实现一种“诗意的栖居”。
4.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由现实的社会过程催生,并且存在于某种物质的、文化的或比喻的空间性框架中,这一框架具有相对稳定性,阶级、组织、个人被“安置”(place)于这一空间框架中的不同位置,并且依据这种位置性在社会分工中扮演着不同角色。社会关系是社会空间变迁的晴雨表。社会关系既表现为静态的社会环境,又时常处于动态的建构和解构之中。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变迁突出地体现为不同阶级间核心—边缘之间的空间对抗,相对于社会空间冲突的绝对性,社会空间的和谐只是相对的。邻里、社群、城市、民族作为社会关系聚合的不同形态,它们既是现实社会空间生产的土壤,也是谋求社会空间变革的社会基础。与之相适应,对于社会空间的宏观审视,也必须要关注社会关系的各种历时性结构和并时性样态。
5.制度。制度本身是具有相对持久性的时空秩序,是一套相对稳定的空间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模式,是在经常性的空间交往中被固定化的交往模式,制度使对空间的控制组织化。制度的权威性体现在它是一种具有广泛空间辐射力的组织模式,是人类思想和欲望的系统化表达,话语实践和权力运行只有纳入制度的轨道才可获得某种现实性。对符号体系的空间控制是制度实践的重要内容,制度的生成和运行会创造相应的符号体系,后者体现着制度的意义建构,是制度运行的媒介,并扮演着诠释、表达和推进制度实践的角色。制度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对符号体系进行空间设计、规划与控制,使其成为可视的制度文本。符号体系本身可以划分为:经济符号、政治符号和文化符号三类。
6.想象、欲望、信仰。想象是描绘和探索各种可能性社会空间的肥沃土壤,哈维提出了“空间形态的乌托邦”(utopias of spatial form),并将其作为对现存秩序的替代性方案的积极探寻,想象是各种乌托邦建构的起点,想象中潜藏着各种被压抑和边缘化的空间诉求,承载对新的空间秩序的渴望。欲望是人类空间生产的源动力。欲望在现实的空间生产中具有双重导向:一是与主导秩序相“契合”,二是以抵抗性空间的形式对主导秩序进行解构与颠覆,现实的欲望体系往往是两种导向的混合体。信仰建构了一个以信念为基础的精神空间。信仰关涉信心、信任、归属等心理和价值层面,它们是现实社会过程的一种精神建构。信仰催生了一个与现实社会过程相对的信念体系,后者与集体忠诚、文化归宿和价值认同紧密联系,为社会行动建构意义框架。
在具体的社会行动中,以上这些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每一个环节都把来自其他环节的力量和异质性内在于其中,这种内在化使环节之间保持着流动性和开放性。以话语环节为例,话语隐匿着权力游戏,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是话语建构的基石,话语的内在界限和表现能力受制于物质实践的现实条件,制度本身是一种具有稳定结构的“刚性话语”,想象、欲望和信仰是话语争夺的重要舞台,话语的效力渗透于社会过程的其他诸环节中。
①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②David Harvey,Spaces of Capital: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p.109.
③参见David Harvey,Spaces of Capital: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pp.109—112.
④Ibid.,p.108.
⑤Ibid.,p.120.
⑥David Harvey,Spaces of Capital: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p.120.
⑦参见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by Donald Nicholson—Smith,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p.94.
⑧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
⑨参见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1~72页。
⑩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关于spatial fixes目前学界有两种译法,一是译作“空间定位”,二是译作“空间修复”,本文统一采用第二种译法,即“空间修复”。此处引文中采用了“空间定位”的译法,因涉及对引文原貌的尊重,故不作更改。
(11)David 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Oxford: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s,1998,p.287.
(12)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第493页。
(13)诺伯格·舒尔茨:《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施植民译,台北,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5~6页。
(14)Michel Foucault,"of Other Space",Diacritics,Vol.6,1986(1).
(15)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16)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序言”,徐鹤林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71~872页。
(19)David Harvey,Spaces of Capital: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p.75.
(20)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第62页。
(21)转引自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第67页。
(22)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41页。
(23)David 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Oxford:Basil Blackwell,1982,p.27.
(24)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第90页。
(25)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26)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第240页。
标签: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地理论文; 地理学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历史地理学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大卫哈维论文; 历史学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