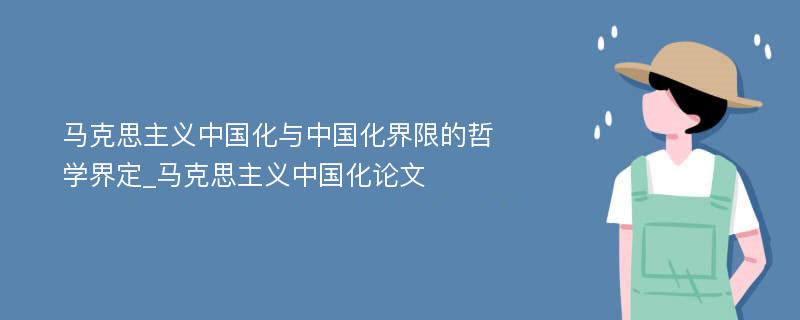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界域的哲学厘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界域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3-0028-0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进入我国人们的日常话语系统,成为了思想家、政治家和理论工作者等论述问题和思考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在日常话语中,人们往往忽略其不同的内涵和界域。这样就造成了使用上的随意性,在应规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有的却表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反之,亦然。这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命题的科学性。因而有必要从哲学层面探究和厘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及其界域。
一、一个时代实践中产生的科学命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一个时代艰难曲折的实践中产生的科学命题。它们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可以区分为传播、结合、创新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出场等几个方面。
1.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阶段,马克思主义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论争中展现了自己的生命力。鸦片战争的失败,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国进入了有史以来最黑暗最痛苦最屈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探索救国救民之路。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发展起来了。各种各样的思潮,一时竞相纷呈,而马克思主义只是当时其中的一种思潮。但是,在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了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聚焦点。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三种思潮成为了时论的中心,影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直接成为解决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中的文化选择问题、经济制度选择问题和政治制度选择问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早的思想启蒙。李大钊等人通过与胡适等人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批判了胡适借研究问题为名所推销的实用主义偏见,最终导致了中国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而不是美国式的实用主义。同时,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同梁启超等资本主义改良者对与文化选择相伴随的经济制度选择问题的讨论。陈独秀等人认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此路不通。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进行社会革命,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的选择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幻想进行了批判,其结论是,为了最终不要国家,无产阶级就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次论争,初步接触和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一核心问题,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
2.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马克思主义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向前发展。过去人们总是对教条主义绝对地否定,这不符合辩证法。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原教旨主义的教条,不顾实际地照抄照搬,这是其消极的方面。但事实上,教条主义也有它合理的方面,那就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毛泽东为了纠正党内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 (P111-112)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的正确态度应是,一要坚持和学习,二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一时期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与教条主义者论争,实际上接触和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是否需要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一核心问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提供了实践和思想理论前提。
3.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看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肯定阶段,把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马克思主义发展看作是否定阶段,那么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提出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否定之否定阶段。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 (P499-500)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即“按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教条主义的要害是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了一个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被动容器;而中国共产党人应是一个学习、认识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动主体。这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联系,而且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按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在这里,毛泽东表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武器;在中国掌握这种理论武器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按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提出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不存在因国家、民族的情况不同而具体化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在修订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为了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其实,这种改动是策略性的,它们形式上虽然有不同,但不能证明二者有何实质性的差别。
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命题提出则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要晚得多。1945年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在于我们的党从最初建立时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3] (P315)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命题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刘少奇又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3] (P333)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表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意思,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还远远不能反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所包容的内涵。
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不仅明确地提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命题,而且对其内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他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在这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且明确表述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界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产生在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命题成熟在后。时间上的先后是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科学命题的内涵有着严格的界域。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并不相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过程和结果是不能混淆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事物都不具有最终性质。事物都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而不是静止的、孤立的和一成不变的。事物就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正如一棵植物,它是一个经由播种、发芽、生根、成长、开花、结果的过程的集合体。可见,过程是事物的具体进程,过程所揭示的是辩证发展的观点。发展就是一个过程。集合体就是事物发展过程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正如上文所述,它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传播、结合、创新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出场等几个具体阶段。它的特质在于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不是一次完成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们的结合,都经过了长期的曲折的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结合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融为一体,创新为一种中国式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所以,结合也是一个艰难的创新过程。创新的结果和目的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出场。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它内在地包含这个过程的结果。换言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一个环节。但是,作为结果的环节,与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又是不同的,它包含了整个过程的全部内容。结果就一个过程的阶段而言,它是这个阶段成熟的标志。它不仅是一个阶段发展过程的终点,同时也是新的发展过程的起点。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两种不同状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在变化和发展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发展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发展过程,随着这个过程的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就呈现出不同的状态,而衡量这种状态的具体标志就是是否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形态。所谓新的理论形态是指适应一定时代需要又能满足一定时代实际要求而形成的比较完整的具有创新内容的理论体系。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形态,都是由新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构成的关于某一事物和领域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不同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新的理论形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又可以区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新的理论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又创新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新的理论形态。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新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但它又是由自己新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构成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不仅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新的概念、范畴,还有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十大关系”等基本原理。这些概念、范畴和基本原理的提出和创新,都不是一次完成的。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多次反复探索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互结合的过程,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逐步形成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成果,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发展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者具有质和量的区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者质与量的区别,不是指总的质变过程中质和量的变化,而是指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因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与马克思主义性质不同的另一种性质的学说。但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决定其总是随着时代的需要又不断地满足时代需要而增添自己新的内容,这就使它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包含了部分质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相互结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总的量变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样一个总的量变过程出现的部分质变。如,经过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理论为根据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在教条主义严重危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互结合的关键时候,毛泽东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观点,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们又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同的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化过程中总的量变中的阶段性的部分质变。所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总的量变中阶段性的量积累到阶段性的质的飞跃和上升的过程。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事物质量互变的特殊性和形式的多样性,表现为事物总的量变过程包含了事物的部分质变,这就决定事物的发展呈现出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特征。所谓总的量变过程的部分质变,就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未变而比较次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保持了其基本本质属性情况下的量的变化过程,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连续性,说明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保持了其基本本质属性情况下的比较次要的性质发生的变化,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阶段性,它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内在根据。比如,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它首先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本质属性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规定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是一致的。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与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同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这样一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相比较,就有某些方面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内容一致的前提下发展了一些新的内容。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按劳分配为主的按资分配的理论等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原理,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发展的连续性,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无限延伸的过程,只要共产主义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就不会终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要不断地继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发展的阶段性,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适应一定历史阶段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目标所产生的新的理论形态就只能满足这种具体目标实践的需要。换言之,随着这种具体目标的实现和适应一定历史阶段的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具体目标的出现,另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就必然会因新的具体目标的出现而产生出来,以满足新的具体目标的需要。比如,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邓小平理论则是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产生的新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现的不同的新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发展的阶段性说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适应一定历史阶段具体需要的阶段性的新的理论形态。因而,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和不断地创新。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发展,还必将产生更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才能适应和满足新的目标的需要。
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凸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具体来说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世界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具有何种历史价值和历史地位,存在着什么样的历史局限性。1945年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他说: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3] (P236-237)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是19世纪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对立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动力的原理、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等,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理论原理。这些一般理论原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和意义。但是,由于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所以,以19世纪欧洲发达资本主义为历史背景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个别结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条件就表现出它的局限性。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必须同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性的因,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结成的果。如果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可能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凸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是指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和意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何价值与意义,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实践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只有实践才能检验和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它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因而,如果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也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
标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