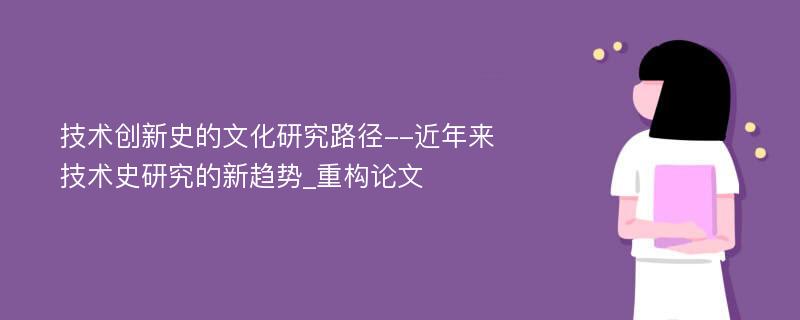
技术创新史的文化研究路径——近年来技术史研究的新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创新论文,路径论文,新动向论文,史研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09)02-0101-07
国内学术界在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该领域中对技术创新的历史研究却尚未充分开拓[1]。而试图思考建构论和后现代史学对技术创新史研究的启发意义,并对技术创新编史学作系统思考的尝试就更少。这无疑制约了技术创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国外技术创新史新成果进行综述和理论定位,以考察国外史家在技术创新史研究中是如何引入建构论和文化理论。考虑到《技术与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以下简称T&C)刊物在技术史研究领域中的权威性与国际性,本文就以它最近十几年间发表的论文为文献分析对象,以探讨技术创新史研究的方法论走向。
一、技术创新史视野的扩展及新的解释方式
概括地说,20世纪80年代前T&C的技术创新史研究在编史原则和论题上存在明显局限,学者们大多都在熊彼特的经济学范式下研究技术创新,有明显的技术或经济决定论倾向。技术史家普遍认同克隆兹伯格倡导的“与境论”编史原则,力图把人造物及其创新过程与经济社会环境结合起来,以解释技术创新的产生、扩散及历史影响,但却无法完全摆脱技术决定论和默顿范式的影响,从而也就始终不能很好地解决“与境论”问题。比如说,讨论技术转移时显示的西方中心论,整个技术史界对经济因素以外的更广泛的社会(尤其是文化)因素的忽视等,都表明学者们的研究带有辉格史观痕迹[2]。T&C第二任主编R.Post一针见血地把上述与境论概括为,充其量只是把“建制、社会变迁、智识源流、经济趋势等阐述为(技术的)周边要素”[3]。
但80年代后,技术创新史研究视野有了极大扩展并开发了多样的历史解释方式,其中最具活力的就是建构论范式被引入技术史并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历史解释方式——这可以说是开启了技术史的“文化转向”。笔者将从以下两方面展开考察,以展示这种新路径。
1.创新过程的视野扩展
学者们更完整地描述了创新过程的更精微的进化过程与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工业化历史进程。有的学者着眼于考察创新的完整过程,有的讨论创新认识论,有的则着眼于揭示创新活动的某个以前未受重视的特殊阶段。
Morton关于有线录音设备创新的案例分析是着眼于展示创新进化全过程的代表性文章。该文考察了发明家及其发明活动、研究与开发过程、企业家投资经营、专利管理、该技术在公司和国家间的扩散与转移、技术的衰退以及新工业的产生等一系列阶段,展示了有线录音机创新的全过程。“并对那种系统建构的过于简单的解释方法发出了警告”,体现了对早期建构论的批判性发展[4]。与上述研究类似,许多学者尝试运用并改进建构论方法来综合考察创新的进化过程与机制,如J.B.Gough(1998年第1期)、P.Neushul(1998年第2期)、M.Hard和A.Knie(1999年第1期)、E.P.Russell(1999年第4期)、D.Mindell(2000年第3期)等的论文。上述研究表明,技术史家已不再孤立地研究发明或开发,而是以技术创新为平台把发明和研究开发等活动统一起来,把技术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进化过程加以考察。换言之,他们消除了研究、发明、开发和创新的人为界限,如今的创新研究已是以“创新”为指向的对整个技术活动的关注。正是这种全程关照使技术史家对创新扩散、管理、使用、衰退等问题投入了特别关注。
有学者直接讨论了创新的认识论问题。McGee考察了19世纪以前历史上存在的三种创新活动传统,即手艺(craft)、机械艺术(mechanical arts)和建筑设计(architectural design)三种传统,从而着重分析的是发明和开发的认识论[5]。Reynard则试图通过对18世纪法国造纸工场(mill)如何进行机器维护(坚持常规修理而尽量推迟大修理)的历史考察来解释一项技术创新的持久性(long-enduring)[6]。Aldrich和Reuss则通过对铁路事故案例和河道建设案例的考察来说明创新活动中测试与理论建构的认识论问题[7-8]。
除上述综合考察外,还有学者着眼于发掘以前未进入研究视野的阶段。自1998年以来就有十多篇论文集中考察“使用”(use)问题。这些学者着重强调了技术使用者如何构建异质网络来定义或重新定义(改变)某项技术创新的功能含义,以及该过程对技术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影响。这是对定位于“创新”的产生阶段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重要扩展。另一转变则体现在Meikle的一篇综述中。该文评述了最近出版的三本关于技术“设计”的技术史专著,指出这些论著关于技术逸事的讨论是引领技术史超越“工业化”中心主义的尝试,从而扩展了技术史家的视野:通常职业史家所关注的技术都集中于与“工业化”和“现代化”有关的技术,而这些论著关注的却是“日常生活技术”。这正显示了技术史家对“读者反应批评”的关注[9]。
与“使用”问题相联,许多学者都涉及到创新的“衰退”和“扩散”问题,比如Russell在讨论DDT的“使用”网络时也分析了DDT走向衰退的原因正在于网络结构(政府、公众、环境)的变化。Epperson的文章更典型[10]。该文考察了POPE(自行车)制造公司从创建、兴盛到衰退的全过程,着重分析了POPE这个“自行车王国”瓦解的网络进化机制。T&C中关于技术创新在同一工业体系中的扩散的研究非常多,而讨论技术创新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扩散的建构过程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Moon讨论印尼农业机械化过程的文章[11]。他考察了美国在帮助印尼实现农业机械技术转移的过程中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目标和文化上的冲突。Rasmussen则通过对生物显微镜向澳大利亚扩散的研究建立了“智识技术”与“物质技术”(intelleetual and material technique)、技术接受的环境硬件与社会(组织)的二元认识论结构[12]。这些都深化了行动者网络理论。
工程理论创新研究则很好地说明了学者们把“研究”结合进了创新过程,并很好地体现了技术史家对“文本”理论的回应。比如,T&C 1997年的一组专题论文的三位作者都借用了麦肯齐把工程理论看做是与机器等同意义上的“人造物”(artifact)的观点,从而强调我们可以像对待其他技术创新一样采用技术与社会互为文本和语境的方法来考察工程理论创新。Vencenti考察了工程师们如何在理论与实践的复杂作用中实现突破声障的工程理论创新的问题[13]。Johnson回顾了二战后政府—大学—工业综合体中“系统管理”工程的产生过程,建构了一个科学家、工程师、管理者、技术实践、内部使用者和外部批评者相互作用的网络[14]。Carlisle探讨了二战后关于核技术的“可能性风险评估”工程管理理论的产生过程,着重分析了专家知识网络与公众话语网络之间的断裂。这是对建构论者试图把创新活动描述为一个“无缝之网”的解释方法的质疑,而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专业知识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断裂问题[15]。
随着上述研究视角的转换与视野的扩展,学者们改变了对工业化历史过程的目的论叙事方式,而把工业化解释为一个充满选择的多元进化过程。比如,Alder通过对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布兰克采用的可互换标准化生产体系创新的产生与衰退过程的考察指出,工业化和美国生产体系并不是目的论过程,而是一个充满竞争与选择的过程[16]。Rydén通过编史分析指出工业化中技能(skill)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过程,由此他探讨了瑞典钢铁工业中技术工人与管理者的斗争与协商过程,展示了技术工人如何发展他们的技能并利用它实现与资方的权力分配的历史过程[17]。A.Sverrisson则通过对冰岛渔船制造工业中小规模制造业主的考察指出,小规模渔具生产的技术进化动力机制构成了冰岛渔船制造工业发展的动力核心,这批判了学术界通常认为小生产企业只是大工业的辅助部分的观点[18]。
综上所述,近年来技术史家在“技术创新”视野上有了重大的拓展,所采用的文化解释方案也更加多元。其主要表现是,把原来局限于技术创新的研发试制阶段的、特别强调科学家和工程师等精英的“作者”霸权的视域扩展到生产制造、管理创新、创新扩散、使用、衰退等环节,从而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不同行动者(如工人、中间管理人员、市场中介)在参与对技术创新和工业进程的建构与协商。这种拓展并不仅仅只是技术史家的研究论题范围的扩大,而是同时意味着“文化转向”的深入;也就是说,技术史家已经充分把握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的文化分析策略,试图超越“唯生产论”并打破科学家和工程师等精英的“作者”霸权,从而凸现大众在文化建构中的作用。
2.多维视角的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对创新失败、性别与技术创新、创新的国家风格和技术创新与环境等的集中研究已使这些问题成为在技术编史学上更具活力的专题。他们尝试对技术创新作“文化”解释。
(1)创新失败的新解释
由于认识到创新是一个充满选择的进化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重视创新失败的研究。一些学者在研究中明确提出了“文化”分析视角。以Lipartito的论文为例,他分析了前人关于可视电话创新失败的研究,批判了前人在该问题上采用的技术功能决定论和需求偏好决定论。作者指出历史偶然因素(非理性的和无理性的因素)在这次失败中起了重要作用[19]。他的研究将考察“失败”相关因素的视野引向了文化(心态、行动者实践意识等)领域。新的研究也尝试从文化的角度去扩展失败的意义域。如Kline所考察的并不是某项创新本身的失败过程,而是美国20世纪20至30年代所有家用水电设备这一创新群的功能相对于当时这一领域中存在的“节省家务劳动时间”的创新文化而言所表现的“失败”。这样,Kline就把创新“失败”定义为相对于某种创新文化而言的解释方式——“失败”并非由技术功能本身决定,而是相对于创新文化而言的[20]。特别值得注意的是Kline的方法论。近年来,他的研究专注于通过对美国历史上的技术概念及话语进行(后)结构主义分析,以考察技术文化、社会群体心态的建构。其研究方法显示了语义学分析在技术史中的重要方法论意义[21-22]。
(2)技术与性别研究方法论的转换
如今的女性主义技术创新史研究已由单纯的工业资本主义批判转向新性别文化的建设性思考,由单纯的女性取向转向社会性别的整体性思考。这种新变化集中体现在该刊1997年第1期一组题为“性别分析与技术史”的专题论文中。Lerman等指出近来女性技术史研究中在视野方面表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人造物”(artifact)的重视。究其原因在于,这些“人造物”被当做文化符号(表象),学者们试图通过它们来讨论男性和女性特征是如何被象征性地(即当做文化符号)使用着;这种研究中看“人造物”的视角已完全不同于以前研究技术物的内史所采用的视角,学者们通过“人造物”得以揭示,“文化活动并非技术发展的外部因素,而本身就是技术发展的组分”。换言之,文本和语境的清晰区分已被解构,技术活动本身被理解为文化活动[23]。
(3)创新的国家风格比较
在这个论题上,学者们试图采用(后)结构主义文本分析的方法来考察作为“文本”的技术创新由于文化情境的不同而显示的风格差异。学者们试图通过不同国家就相似技术开展的创新活动的比较,来揭示造成创新活动的国家风格差异的原因与机制。在前人的讨论基础上,Heymann进一步讨论了各国在研发方式上体现出国家风格的历史根源,以及不同技术文化所造成的创新目标的差别等[24]。Brown则比较了英美两国在机械工程制图方面的国别差异。二战期间,英国请美国制造大型运输船舶。出于节省设计时间的考虑,英方带来了设计图。但出乎意料的是英国工程师绘制的设计图在美国工程师那里派不上用场,这主要是因为两国在机械工程制图范式上不同[25]。基于此,Brown采用建构论方法进一步指出了英美两国的不同背景因素对工程实践的影响。在此Brown引入了符号理论,把工程设计图定义为“技术表象”并考察了文化语境对它的建构[26]。Hard与Knie的研究则试图对国家风格的形成机制作认识论分析,以开发一种分析创新的国家风格的SST解释工具。该文也采用了“技术表象”的分析视角,借用布迪厄《语言与象征权力》一书提出的社会语言学方法,类比官方语言中“方言”、“国家语言”和“语法”等概念来解释“内部一致性技术”的形成机制,从而为解释国家风格的形成与差异提供一个认识论工具[27]。还有K.Koizumi考察了日本战后制造技术超越欧美的文化动因,旨在比较日本与其他国家在创新方面显现的文化动力[28]。
(4)技术与环境研究的新视野
上个世纪60年代兴起的环境运动曾促进了学者们关于技术对环境的影响的历史研究,但直到80年代,学者们才真正深入理解那些造成环境破坏的创新是如何由“技术—社会”网络构建出来的(而并非仅归因于技术本身或使用者),并重视环境文化如何对技术创新产生建构作用。T&C1997年第3期组织了专题就上述两方面作了深入探讨。Reynard则开辟了创新的环境文化史研究视角[29]。另外一个重要路径是“自然景观”(landscape)研究。这是一种把自然景观当做“符号”来研究的方法论进路。其出发点在于,所谓自然景观是人类通过技术改造自然界而创造出来的“技术人工物”;该人工物的建造过程是一个赋予技术、人类、自然或者国家与民族身份、意识形态、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意义的过程[30]。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创新史研究已促进了技术建构论的多元化与文化分析。他们广泛吸收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等文化理论的概念分析工具,大大深化了技术史的“文化转向”,为技术史确立“文化研究”方案奠定了坚实的经验基础。
二、技术创新史新的理论定位:文化研究进路
下面我们探讨上述技术创新史研究的理论定位,从总体上考察上述研究的理论渊源与方法论基础。
上述研究可概括为两方面:视野扩展和新解释方式。这主要表现为,学者们不断改进“技术—社会”相互建构的历史解释程序,通过对消费(而不仅是生产)的关注而重构了工业化的历史进程;通过对创新的扩散、使用和衰退等阶段的关注(而非孤立地考察发明及生产)而重构了技术变化的历史过程;通过对“操作自然”的“深描”而加强了技术创新中自然—文化的接合意义(例如Rasmussen的“物质技巧”概念和技术史家对“工程理论创新”的研究都试图从认识论上进一步深入认识技术创新中自然—文化的联结,以超越行动者网络理论对技术创新中自然因素的作用的随意性解释)。从而更好地解决了自然与文化以及行动者之间的认识论关系问题,超越了以前建构论专注于科学技术的“表象”的狭隘,但又不是否定符号学的分析。这表明,学者们已把技术史建立在建构论基础上,并进一步揭示了技术创新的文化实践性质。可以这样来总结,上述技术史研究突出了“文化”这个核心概念在技术史解释纲领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从以上综述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技术史研究实践已走上文化研究的多元解释路径。由此我们就被引向把“文化实践”作为核心概念的文化研究与新文化史领域。
那么,什么是新文化史?到20世纪90年代,通过引入(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等广泛的“文化研究”理论,西方史学界已重构了历史解释框架,使“新文化史”成为显学。新文化史采用“文本”类比,将文化、社会和一切历史事件比拟为一个文本,同时采用“互文性”隐喻又把文化当做一种语境,二者的相互建构赋予社会事件、行为、体制、过程以局域性的、具体而流动的意义。这样一来文化就不再是反映社会情势与结构的一种镜像,而成为理解一切社会事物意义的基础。同时,“社会”(如“经济”、“阶级”)就不再是客观的历史实在,而只是历史行动者依据具体文化情境建构意义网络的过程,并不存在稳固的社会历史结构。这样,历史研究就不再是寻求表象之下的客观规律,而是探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各种实践活动过程中如何生产、表达、阅读、体验和重构这些“象征”及其意义[31]。
从此出发,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技术创新史研究新进展的思想脉络。我们看到,技术创新史的视野扩展与(后)结构主义的文化研究对“读者”的强调的转向相契合。在结构主义看来,文本的意义决定于文本的生产,而在后结构主义看来,文本的意义已脱离作者的掌控,读者才是文本意义的解构者与重构者。受此启发,可以认为,一项技术创新的使用功能和它显示的文化意义就依赖于使用者与阅读者的理解;而这必然反作用于创新与生产者。由此,技术史家就突出了对创新的扩散、使用和衰退等阶段的关注,从而扩展了技术创新的视野。
同样,技术史家尝试在技术建构论中引入“文化实践”作为解释资源也是受到了文化研究的启发。根据上文所述,新文化史通过“文化实践”概念而把历史事件理解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各种实践活动过程中如何生产、表达、体验和重构这些“象征”及其意义的过程。从而技术史的文化研究进路就可以把技术创新理解为人们(专家与大众)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各种实践过程中如何通过把自然、社会、个人,知识、利益、政治、情感、规范、个人意向等要素具体地有选择地接合起来生产、表达、购买、消费、体验和重构“技术活动的意义”的“文化实践”过程。这样就把技术创新史从狭义的建构论(如强纲领、实验室研究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引向多元化从而也更有竞争活力的文化研究和新文化史范式。
三、对技术创新史研究的展望
笔者认为,技术史的文化研究范式比狭义的建构论更有解释力,它预示着技术创新史的新方向。原因在于,技术建构论中的实验室研究和行动者网络理论虽然很好地解决了自M.克隆兹伯格以来技术史中始终存在的与境论困境,但其自身也存在缺陷,即过于注重对技术知识和技术物的“生产”的关注而忽略其“表达”、“传播”、“消费”与“重构”,并主张纯粹的人类学描述,而丢弃了对技术的批判性,从而陷入相对主义的反身性困境。文化研究进路则可以用“文化实践”概念来充分显示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识、技术物和技术文化的“表达”、“传播”、“消费”与“重构”等非“生产”阶段的重要性,并重申历史的批判功能。
当然也还有些问题要解决。其一,学者们有必要进一步把视野从“技术创新”扩展到“技术文化的塑造”,深入考察历史行动者参与技术的意义建构与使用的实践过程。一旦技术与社会的作用关系被理解为行动者借助技术及其他文化表象来重构日常生活的实践过程,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通过文化史来重构技术—社会史,重构技术社会学的基本范畴,尝试用“新文化史”视角来重新定义经济、政治、阶级、性别、民族、伦理等范畴及其在具体历史境域中的相互作用关系,并通过借鉴“新文化史”中的“霸权”、“认同”和“集体记忆”等极具批判力的概念来反思技术文化,以超越狭义建构论对技术创新仅作纯粹的人类学描述的主张,从而重申技术的人文研究的历史批判力。
其二,根据理查德·约翰逊“文化循环”理论的理解,意义生产、表达、体验和重构的过程是非线性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因此,技术史家还需要用“文化循环”概念来充分整合技术创新过程中“生产”、“表达”、“传播”、“消费”、“使用”与“重构”等阶段的非线性关联,从而做到决不脱离其他环节来孤立地考察“技术创新”的某一阶段,而是充分注意行动者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是如何把技术实践的某个环节与作为语境的整个“技术文化循环”接合起来。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技术创新研究的平台,“技术文化的塑造”比“技术创新”概念更有拓展力。
其三,需要超越文化研究的符号学与文本分析立场。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技术哲学家的技术文化批判理论(从海德格尔到当代的温纳、费恩伯格、伊德等),还是建构论的技术社会学研究(从SSK、女性主义到ANT),或者是前文综述的文化研究进路的技术史研究,大多都局限于语言学与文本理论,采用解释学进路,把技术还原为作为符码的机器,以考察行动者如何制造和解读符码的意义。这样,我们就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技术总是通过个体的切身化的体验而运作的。换言之,技术除了作为符码与人打交道(解读意义)以外,更主要的是通过个体的身体的直接接触和切身体验来为人所经验,也就是说技术并不是只通过语言来给我们提供认知和情感经验,而更主要的是通过切身感受来提供这些经验[32]。这样我们就需要超越语言学,而发展出一种能与身体现象学融合的理论框架。
总之,本文认为,文化研究路径的技术史将对更好地批判性思考技术文化并促进其与更广义文化的融合提供更多可能性。
收稿日期:2008-07-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