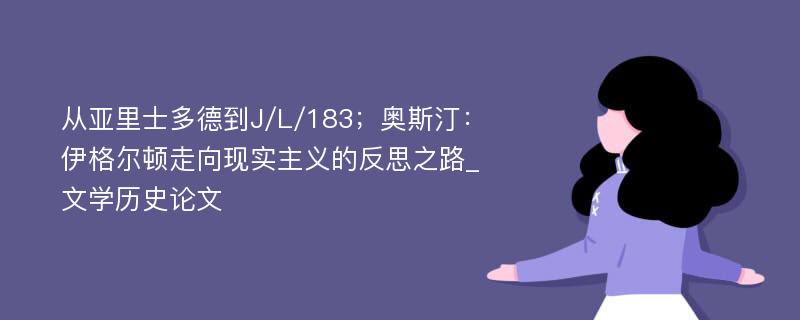
从亚里士多德到J·L·奥斯汀:伊格尔顿对现实主义的反思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斯汀论文,亚里士多德论文,现实主义论文,路径论文,伊格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6-04-009 讨论作品的道德意图,在21世纪似乎有些过时;钻研文学虚构又难免坠入语言迷宫甚至钻到形而上学的死胡同;而现实主义作品更不属于当下时髦话题——然而伊格尔顿(Eagleton)就是这么“任性”——在新世纪出版的多部著作中[如How to Read Literature(2013),The Event of Literature(2012),How to Read a Poem(2007),Sweet Violence:The Idea of the Tragic(2003)],他花费了大量篇幅把这三个关键词汇集到一起,这其中有没有什么深刻洞见?有什么现实价值?他的理论依据在哪里?如果回到古希腊,重新回到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诗学、修辞学、政治学甚至伦理学传统当中,我们就会比较清晰地呈现出伊格尔顿这位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源头。 一、从摹仿到虚构 在文论研究中,摹仿和虚构这两个关键词向来备受研究者们青睐,特里·伊格尔顿也不例外,此前曾有人探讨了他在《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一书中对于“虚构”与现实之关系的看法,并初步谈及伊格尔顿所理解的奥斯汀(J.L.Austin)言语行为理论[1]。而在2012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事件》第四章《虚构的本质》中,他举例说:儿童的说谎、幻想、言语能力、摹仿(mimesis)以及假扮(make-believe)并非认知偏差,它们恰恰就是成人知识与行为的发源地[2](P30)。就摹仿(mimesis)来说,在某个特定的社交生活仪式当中出生,摹仿(miming)其特定的风格做派,直至它们成为自然而然的东西,经过这个过程,儿童将学会如何思考、感受并行动……摹仿(mimesis)与人的实在性(human reality)密不可分[2](P30)。咿呀学语的孩童通过想象并摹仿成人的行为与言语实现了成长,摹仿虽为假扮,可它影响了现实,可以“弄假成真”;剧本虽为虚构,演戏虽为模拟,我们却要用“逼真”来评价它。所以,伊格尔顿说:“既在做一件事情,同时又在假装完成它,这是有可能的。孩童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假扮游戏中出戏入戏,此事提醒我们,事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其实微乎其微。”[2](P113-114)也就是说,儿童的摹仿打破了事实和幻想之间的界限,假装、幻想、虚构、模拟……这些词本身就蕴含着某种行动的潜能,一旦付诸行动,便会产生实际效果。伊格尔顿指出,在文学里,“某个文本可能在同一时刻既是事实,又是虚构”[2](P114)。为了引人入胜,作者要重组真实事件,这样事实就被虚构化了;为了某种实用目的,研究者会从《麦克白》当中寻找史料,这样虚构反而变成事实;作品的真实感源自于它符合主体经验或者认知水平;但即便是《史记》、《物种起源》,仍然不可能完整还原那个变动不居的真实世界……这样的话,何为事实?何为虚构? 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提醒我们:从孩提时代人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最善摹仿,并通过摹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3](P47)。为了阐释人类为何拥有诗艺,亚里士多德提到了孩子的摹仿本能,这种能力不仅可以产生快感,而且可以获取知识,“求知不仅于哲学家,而且对一般人来说都是一件最快乐的事”,“人们乐于观看艺术形象,因为通过对作品的观察,他们可以学到东西”[3](P47)。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摹仿同时指向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性与感性,求知和审美得到了统一。然而,按常理,知识对应于真实(事实),真可以产生美,可当我们继续考察其《诗学》时却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但不排斥虚构,相反还有些赞赏的意味,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推崇荷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后者能“教诗人以合宜的方式讲述虚假之事”[3](P169),亚里士多德甚至说:“如果诗人编排了不可能发生之事,这固然是个过错;但是,要是这么做能实现诗艺的目的,即能使诗的这一部分或其他部分产生更为惊人的效果,那么,这么做是对的。”[3](P177)这样的话,虚假(构)在什么意义上是“对的”呢?伊格尔顿在其《怎样读诗》(How to Read a Poem)中指出,亚里士多德眼中的诗人“与历史学家不同,诗人不必拘泥于事物本来的样子。因为包括历史小说在内的文学作品,无须紧扣历史事实,他们可以重新组织这些事实,这都是为了突出这些事实所体现出的道德意义。”[4](P35)在古希腊悲剧的摹仿活动当中,为了呈现出鲜明的道德意义或者真实的普遍性,虚假(构)是合理的、“对的”、有意义的,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赞许,那么,真(普遍性)、善(目的)、美(快乐、惊人)和虚构之间有什么重要的联系? 返回到2003年出版的《甜蜜的暴力:悲剧观念》(Sweet Violence:The Idea of the Tragic)中,伊格尔顿深入研究了从古希腊到现代的悲剧理论,他提出一个看上去十分“形而上”的命题:归根到底,悲剧不过是虚构,对我们这种胆小怕事之人,为了被迫去承认好日子也不过是向死而生的,悲剧毕竟还是一种可以忍受的方式。否则,真实存在的事物带来的创伤将会异常可怕,那样我们根本无法苟活[5](P169)。作为虚构的一种形式,悲剧居然可以用来抵抗真实带给我们的创伤,如何理解这个判断?那个“真实”是否就是我们难以理解、无法表述甚至不敢面对的物自体(康德)或者真实界(拉康)呢?反过来说,我们目前所生存的时空,难道不也是我们自己通过想象力与实践从无到有把“虚构”变成现实? 二、从《诗学》出发考察现实主义小说的道德意图 在《文学事件》一书中,伊格尔顿提到了《克拉莉莎》的作者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后者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自己并不希望读者觉得小说中的克拉丽莎真实存在,但与此同时,他也不想承认这个故事纯属虚构。不论宣称故事是真实的“调查报告”,或者承认故事是虚构出来,两种举动都会导致作者想要实现的、那个更具普遍性的道德意蕴大打折扣,所以伊格尔顿认为理查德森“力图将故事悬浮于虚构与现实之间的某个地方,如此方可确保他自己在虚构和真实世界的最佳位置”[2](P86)。那么,虚构与现实之间的最佳位置在哪里? 就理查德森来说,“虚构”是一种影响现实的手段,作品所要力图实现的“道德意蕴”才是“目的”,然而小说虚构与现实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很难截然两分,在这二者之间进行连接的是“目的”二字吗?实现了目的、达成了功效,就完成了从虚构到现实的转化吗?再看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过的另一段名言: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3](P81)。根据陈中梅先生的注解,此处的“职责”(ergon)相当于“功用”或者“功效”,实现功效便是达到目的,诗人摹仿的目的等同于它要实现的功效与价值。如果已发生之事为真实,可能发生之事为虚构,那么诗在亚里士多德这里的作用,便在于运用虚构来影响真实,悲剧不是对历史的复述,它是一种有目的的“技艺”①,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技艺”与“制作相关”,“使某种事物生成”,“学习一种技艺就是学习使一种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事物生成的方法”[6](P171),技艺要促使某种事物的生成,用砖盖房的建筑术是技艺,把生病的人恢复原状是技艺,把丑陋的石头变成美丽的雕塑仍是技艺,也就是说,把不完美的东西变得完美,让不存在的东西存在于世并符合我们的目的,这是技艺的功用。正因如此,“诗”这门技艺当然不是照搬照抄式的、没有任何主观创造性的活动。 如果说在古希腊的悲剧里,诗的目的是卡塔西斯(Catharsis),净化(或疏泄)人的情感,进而实现稳定城邦、教育公民的功效,那么《克拉莉莎》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道德教化,主人公的悲剧是可能发生之事,再现其经历是为了警醒世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作为诗的典范,古希腊悲剧要去描述可能之事,这种可能之事必须具有普遍意义,而非个别价值,相比较而言,若说克拉莉莎是真实的故事,这仅仅代表个别,不具备普遍意义,影响现实的效力是有限的。 亚里士多德还说:“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3](P81)已发生之事代表过去,可能发生之事才指向将来。已经发生的属于个别之事,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才能彰显某种普遍化的意义。诗(广义的文学)之所以更有哲学性、更严肃就在于它的任务是去表现普遍而非个别。既要去表现普遍性,同时又要去描述可能发生、而非已发生之事,那么,虚构对悲剧而言就是必不可缺的,因为虚构只是手段并非目的。故而亚里士多德说,尽管阿伽松的《安修斯》“事件和人名都出自虚构,但仍然使人喜爱”[3](P81),能描述可能发生之事,能表现普遍性的,就代表着卓越。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也表示:“通过某种创造性的伪造,虚构作品可能更忠实于现实。”[2](P116-117)在诗与历史二者之间进行比较,伊格尔顿几乎完全照搬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虚构之所以更真实,是因为历史回顾的不外乎偶然事件,为了某一特定叙事目的,历史编纂者不得不去有选择地进行扭曲、裁剪,甚至填充、改写。伊格尔顿提醒道:“任何叙事都必定牵涉到遴选、修改、弃置,因此也就不可能向读者提供原汁原味的真相”[7](P127-128)。若按此逻辑,诗(虚构作品)和历史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东西,为什么要强调诗的普遍性价值呢?难道历史不也力图再现普遍性吗? 原因就在于,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记述了个别、偶然之事,诗却要根据可能性或者必然性,来表现某一类人在特定情况下会说的话或者会做的事,亦即,这种普遍性是经过理性反思之后重建出来的一种哲学式认知,类似于通过定义来把握具体、个别事物,定义是普遍的,但事物是个别的,掌握具有普遍意义的定义就是去把握事物的本质,进而有效地预测并且掌控外部世界,古希腊人认为,诗是技艺,历史不是,诗可以揭示本质,而本质即事物之所以如此存在的根源,可以由理性予以把握。 那么,伊格尔顿认为,诗(文学)所要去表现的普遍性指什么?他提出:在文学当中更重要的是关乎道德寓意的断言(moral claims),而不是关乎经验事实的断言(empirical claims),这一事实意味着作者可以让后者屈从于前者[4](P35)。这里出现了两个关键词:一是断言,二是道德寓意。断言是对事物、事件的命题,当我们为某一事实所作的命题符合客观事实时,此命题为真,若不符合便假。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某部作品是虚构的,原因在于它不符合事实,或者不符合人们当下的认知,比如弥尔顿的《失乐园》、吴承恩的《西游记》以及一些科幻小说、穿越小说,皆虚构之作。但伊格尔顿认为,这并不是核心问题,即使拿人们最经常用于辩白的现实主义小说来说,后者仍然是虚构的,只不过虚构的技法有所不同:现实主义作品选取的人物、事件和情境都是能够帮助它建立道德世界的。但是,为了掩盖这种刻意的痕迹,保持现实的氛围,它通常会向读者提供许多信笔拈来的细节。……这些细节完全没有道理可讲,只不过是为了营造真实感罢了[7](P128)。 现实主义小说的目的是构建一个理想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世界,让读者在情趣描述中接受道德启迪[8]。它描写的不过是作品当中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并非对世界的镜像,试图还原现实主义小说就如同水中捞月。《包法利夫人》当中对帽子的铺陈简直有些“不择手段”,伊格尔顿认为“这种帽子只有文学里才有,它完全是由语言编结而成,无法想象谁会把它戴到街上去”[7](P128),《呼啸山庄》中的“画眉山庄”读起来很拗口,可这是作者费尽心机的构思,如果起一个更为可读的名字,那就泄露了小说的秘密,这种看似无意的偶然性,实际上要为了某种意图十分明显的必然性服务,现实主义小说认为自己发现了世事之所以如此的必然性,所以才找一些偶然性来作为点缀或者伪装。不仅如此, 许多现实主义小说都欢迎读者能够认同他们的小说人物……现实主义小说让我们通过想象去重建他人经验,这种方式开阔并且深化了我们的同情心。在这意义上,这是一种无需在事实上进行道德教化的道德现象。也许,这种道德寓意的依据是作品的形式,而不仅仅是它的内容。[9](P75) 现实主义小说终究还是小说。无论多么逼真的语言堆积都不过是为了让它显得“真实”,这种真实仅仅停留在作品里面。伊格尔顿认为,现实主义小说最大的目的不是再现那一个又一个看上去无比真实的情境和人物,而是要通过构造无比真实的情境和人物来方便读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再现一些关于他人的经验,这样才能深化人们的同情心,进而实现道德改良和社会稳定。比如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希望那些读到自己作品的人们“能够更有效地设想并且体验那些和自己迥然有别之人的喜怒哀乐,而事实上大家都不过是在苦苦挣扎当中不断犯错”,艾略特认为人运用想象力才能对抗世俗生活中的利己主义,想象力能让人们进入到他人内心,伊格尔顿因此指出:“艺术在这个意义上非常类似于伦理学。只有当我们可以从他人的视角上来理解世界,我们才能够对他人怎样以及为何如此行动有着更加全面完整的认知。”[9](P75)因此,对现实主义小说来说,这种无限逼真的小说形式只是手段,最终是为了提出一些“关乎道德寓意的断言”(moral claims)。 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诗人所力图表达的普遍性,如果放到现实主义小说当中,大概可看作后者想要提出的“关乎道德寓意的断言”,只有小说情节与人物呈现出某种内在的逻辑必然性,那个所谓的道德命题才是令人信服的,这样,现实主义作品之所以引入某些偶然性因素,最终是要呈现某种作品所期待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的运行要符合读者认知,符合因果逻辑,只有这样,那种具有必然性意味的“道德寓意断言”才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对现实产生影响。因而伊格尔顿认为,《米德尔马契》“和许多现实主义小说一样,它预设了历史本身含有一个意义的设计。经典现实主义作家的任务与其说是要虚构一个寓言,不如说是要把内含于现实中的隐藏的故事逻辑表现出来”[10](P43)。也就是说,作家和作品的功效便是虚构一个具有普遍意味的寓言,用于呈现那个作者以及那个时代人们能够认知和理解的道德意义,此过程便是提出那个“关乎道德寓意的断言”。 就“断言”一词,我们仍有必要再回顾一下亚里士多德对于断言(命题)的看法: 所有句子都有意义……但并非任何句子都是命题,只有那些自身或是真实或是虚假的句子才是命题。真实或者虚假并不为任何句子所有,例如祈祷就是既无真实也无虚假可言的句子。…… 对这些句子的解释主要属于修辞学或诗学的范围。[11](P52)(解释篇17a1-a7) 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体系当中,首先要研究事物的范畴以及由这些范畴构成的命题,才能对世界上万物之存在与本质进行探讨。我们关注任何外部对象的时候,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给它们下一个直观判断,有时需要借助定义来理解陌生事物,但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并非所有句子都是命题(断言),人是会呼吸的动物,这是真命题;人是会飞的动物,这就是假命题,可是并非所有句子都有真假可言,比如祈祷就不是命题,因为它并无逻辑真假,祝福、宣誓、恐吓也类似。 那么我们便进入了下一个话题,伊格尔顿对表演和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的理解。 三、基于意图的表演:作为施行话语的文学 同样在《文学事件》中,伊格尔顿举了一个有关表演(performance)的例子[2](P119):当现场正好需要一位演员出演被劫持的皇太子之时,一位真正的皇太子误打误撞跑了进来,结果,这位皇太子在扮演自己的时候显得非常真实!因为他知道真正的皇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对。这就如同剧情需要演员打喷嚏,开拍之际演员恰恰打了一个真喷嚏,于是这个真实的“表演”非常成功! 事实上,真人演真事,未必效果真实,装模作样地演,效果反而会真实,这就是“摹仿”和“真实”之间的悖论。任何人都可以表演,但表演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符合那个所谓的原初“真实”,原初情境无法还原,表演只是一种虚构,虚构的目的是它试图产生的实际功效。伊格尔顿举这例子是为了说明,真实也好,虚构也罢,在文学艺术层面上只能从它对现实的效果来进行考察,摹仿或者表演的目的不是还原真实,而是追求效果。 进一步看,皇太子之所以演得“真实”,是因为他“摹仿”了自己,但是不具备皇太子身份的演员同样可以演得惟妙惟肖,他可以摹仿真实的皇子,也可以摹仿想象中的皇子,这是人类拥有想象力和摹仿能力的结果,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亚里士多德对摹仿所作的区分:人们可以用同一种媒介的不同表现形式摹仿同一个对象;既可以凭叙述或进入角色,此乃荷马的做法,或以本人的口吻讲述,不改变身份也可以通过扮演,表现行动和活动中的每一个人物[3](P42)。这段话的意思是,人们可以在戏剧当中用不同方式来摹仿同一人物,或者用第三人称去叙述这位人物的行动和言语;或者把诗人自己当成某个角色。然而,亚里士多德更重视第三种“摹仿”,即通过“扮演”来表现行动中的各种人物,他在《诗学》第24章中之所以表扬荷马,就是因为后者擅长表演各种角色,荷马没有把自己当成旁观叙事者,或者把自己固定成某一个叙事者,因此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 诗人应尽量少以自己的身份讲话,因为这不是摹仿者的作为。其他史诗诗人始终以自己的身份表演,只是摹仿个别的人,而且次数很有限。但荷马的做法是,先用不多的诗行作引子,然后马上以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或一个其他角色的身份表演。人物无一不具性格,所有的人物都有性格。[3](P169) 亚里士多德为什么推崇诗人扮演各种角色,称赞他们善于改变身份?原因在于,这种方式可以表现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普遍性”,普遍性源于特殊性、个别性:以诗人自己的身份叙事,只能摹仿诗人自己,而摹仿某一类人,只能表现个别性。每个人的阶层、履历、才华各有不同,如此受局限的表演不适合去表现人类的普遍性,通过摹仿各种身份来表达普遍性才是荷马的价值所在。可见,亚里士多德推崇的摹仿实际上就是表演(扮演),不去扮演那些各不相同的角色,普遍性就没有说服力。 罗念生先生在《诗学》的译者导言中明确表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摹仿”便是“再现与创造的意思”,“他的摹仿活动就是创造活动”[12](P4)。在这意义上,“摹仿”即“虚构”,摹仿便是利用想象力从无到有去创造,在劫持皇太子的演出中摹仿自己,是虚构了一个被劫持的自己;出身低微的演员去表演皇太子,则是虚构了一个想象中的皇太子,进而摹仿这个虚构出的形象,而这些“摹仿”、“虚构”实质上都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人类活动。美国学者戴维斯(Michael Davis)在注疏《诗学》时评论道:“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选择做什么,我们总是为自己设想了一个行动,仿佛我们在从外面审视着这个行动似的。……所有行动都是行动之摹仿”,而这本身便是“诗性的”(poetic)[13](P13)。不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生活中,我们的行动事实上都是在“摹仿”,行动与表演、摹仿与创造、真实与虚构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界限。在生活中我们既是演员也是观众,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行为方式,但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演员,不会永远停留在舞台之上,当面具摘下或者角色更换后,我们就不得不反思自己刚才在舞台上的表演,悲剧(诗)其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思自身“摹仿”与“虚构”能力及其成果的机会。 既然亚里士多德不介意诗人创作与历史事实之间逻辑真假,既然他如此推崇荷马进入各种角色的“表演”天赋,既然他曾明确表示“并非所有句子都有真假可言”,祈祷这样无所谓逻辑真假的句子应当属于诗学或者修辞学的研究范畴——那么,我们不由得联想到另一个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当然,伊格尔顿也想到了。 伊格尔顿曾以蒲柏的《愚人记》为例指出:诗歌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反讽是一种施行式的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它类似于“用威胁恐吓式的语气来劝诫世人谦虚是一种美德”[4](P88),伊格尔顿设想的是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境:奉劝世人谦卑恭顺的神父,紧绷着脸威胁着他的信众要相信他刚刚说过的话。因此,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看待悲剧,伊格尔顿把诗视为一种有目的的功能性存在,“诗皆表演,而不仅仅是纸面上的实物”[4](P88),“诗是一种用于产生某种效果的语言组织方式”,“诗组织言辞的部分目的就在于展现言辞的本质”,“诗是一种讲究修辞的表演(performance)”[3](P89),“诗歌形式都有其明确的目的,比如表扬、诅咒、抚慰、鼓舞、祝福、庆祝、谴责、提出道德忠告,等等”[4](P89)。诗通过组织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它并不揭示真伪,其言其行是合二为一的。这样的话,亚里士多德对祈祷并非逻辑真假命题的看法,便与伊格尔顿对诗歌目的的看法,产生了一致性—— 文学上的言语行为属于更大范畴中的言辞表达行为,这便是所谓的施行语句(performatives),它并不是用来描述世界的,而是通过言语行动来实现某些目的。问候、诅咒、乞求、辱骂、威胁、欢迎、发誓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当你说发誓的时候,就是在发誓;当宣布百货公司开业的时候,就是令其开业。[2](P131-132) 言语行为理论由J·L·奥斯汀(J.L.Austin)提出,他把言语行为区分为述事式(constative)与施行式(performative)两种,前者用于述说或报道事件,是描述性的,有真假可言;后者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其表达本身便是在实施某种行为,说即是行,有适当与不适当之分。“施行行为并非针对现实的断言,因为它们没有真假”,这种言语行为的“意义既体现在行为当中,也体现在语词当中”[2](P132)。诗正是这样一种施行式的言语行为,诗之所说便是诗之所行,它的目的并非判断真伪,这恰恰呼应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祈祷无真假,并非命题,是施行语句,属于诗学和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既然我们不再受限于虚构与真实、摹仿与创造、行动与表演之间的二元对立困惑,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比如伊格尔顿说: 小说最主要的含义并不是虚构。……所谓的文学文本最重要的意图并不是提供事实。相反,它邀请读者“想象”事实,即用事实建构一个想象的世界。也就是说,一部作品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既是实在的,又是虚构的。[7](P137) 虚构与否不是文学的充分或者必要条件,它不是对真实世界的镜像或者重组再造,考察文学不能用真实与想象、实在与虚构之类的范畴,那样失之简单化。进而,当我们回头看待现实主义小说的时候,亦如此。 一切所谓的现实主义都是带有某种角度、经过编辑的现实……现实主义小说的意图是反映存在的本来面目,包括各种枝枝蔓蔓的细节;但是,它也必须从这些杂乱无意的事件中理出头绪。[7](P127) 反映“本来面目”并从中“理出头绪”才是现实主义小说的意图和目的,它本身所制造出来的那个文本的世界绝对是不可还原的,在伊格尔顿看来,“现实主义”不过是一种技法,在这些作品当中,“语言被做了最大限度的透明化处理,稍事抵挡就将意义拱手交出,从而使读者感到它呈现的是现实的原貌。”[7](P143),这样的语言“完全是被当作工具使用的……根本不存在‘更贴近现实’的语言”[7](P144)。现实主义小说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都把语言当作一种表达意图的工具。行文至此,我们就必须回到“意图”或者“目的”的问题上来,也就是《诗学》中提到的“诗人的职责”问题上来,如果把职责理解为功效,那么我们必须知道,诗人和诗(文学)的“目的”是什么。 四、道德意图:伊格尔顿现实主义文学新论 文学虚构都是有道德寓意的,《动物庄园》、《威尼斯商人》、贾宝玉、孙悟空、南慕容北乔峰都是要表达一些明确的道德意图,此道德不是私德,而是展示特定情境当中人们所作出的道德抉择,而这种抉择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没有只写给自己读的文学,文学要实现人们在道德与审美上的双重提升,文学之所以不同于政治宣传或者宗教布道辞,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文学并不通过直白的口号来向人们头脑中强行灌输某些东西。伊格尔顿曾指出:“文学并不把生动的经验简单地转译为法则和规范,相反,文学通过某种理论和实践的一体化,为我们提供一种别样的道德认知。”[2](P64)一方面,文学艺术就像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样,既能为人们带来审美和认识上的双重快感,能疏泄(净化)人们的情感,强化公民的道德伦理意识,进而稳定城邦;但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并不打算为我们提供一些法则、规范之类的东西,因为那样的话,文学艺术还不如道德说教或者政治宣传做得好。 就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他更强调后者的重要性,“人们没有理由认为,文学作品无如如何都应该羞答答地淡化其道德目的”[2](P69),《复活》、《动物庄园》、《汤姆叔叔的小屋》、《社会栋梁》都有明确的道德目的,把文学艺术当成一个独立的审美领域,从而与社会、政治、世俗生活截然两分的想法,既不理智,也不现实,尽管道德不是文学的充分条件,但它是一个必要条件,“没有对于人类生活之价值和意义的探询,怎么会有文学?”[2](P70)伊格尔顿还说:诗歌都是关乎道德的陈述,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会依据某些道德法则来作出某些具有说服力的判断,而是因为它们所论及的是人类的价值、意义与目的问题[4](P29)。上面这些看法从根本上都讲了同一个问题:道德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道德规范,不是像驾驶手册那样的条条框框,而是驾驶本身。人类在生存过程当中,必然要遇到一些关乎价值、目的、意义的整体性问题,而这些问题决非仅仅面向某个个别的人,而是面向所有的人,面向每个必然要和周围其他人发生各种社会联系并从中产生道德、伦理判断的人,人们会沉浸在这个虚构物当中,或者在与这个虚构物产生现象学关系的时候,设想自己在遭遇类似情况的时候如何进行抉择。 伊格尔顿说菲尔丁(Henry Fielding)的小说常常用大团圆式的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来收尾,可这种结局其实是反讽,因为坏蛋罪有应得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是虚构出来的,这是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之间的反讽,实际生活当中,恶棍们很有可能早就当上了大主教。因此“小说越是赞美诗性正义,它越是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朝相反方向吸引到文本之外的黑白颠倒上来”[5](P142)。写真实和写虚构一样,都有着明确的道德意图,但这种意图作为“内容”,必定要通过某种符合人类认知、情感与道德接受模式的具体“形式”来实现,形式上出现了缺陷或者失误,内容无论再正确、再符合人类利益,它的效果也是极其有限的,甚至会起反作用。 当苏珊·朗格(Susanne K.Langer)说,喜剧象征着幸运而悲剧象征着命运,伊格尔顿认为,这个判断的精致度超过了它的精确度[5](P101)。原因在于,就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来看,悲剧的发展应当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必然如此的,所谓必然如此,就是符合因果律的。悲剧不像史诗那样散漫冗长离题万里,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自然而然的必然性是一种形式上的要求,而不是某种不可捉摸的形而上学要求。亚里士多德要排除的是偶然性、个别性或者说是不可言说性——个别之物无法言说,因为语言是用于交流的普遍性工具——亚里士多德关注的不是什么形而上的命运无常,诗学中的必然性就是人类头脑中的“因果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一方面是人类理智的一种倾向,一方面也体现了一种审美和道德上的要求,因为非理性的、不可控的、不可言说的、无穷无尽的外部世界更加令人恐惧,与其真实地、毫无偏差地、原封不动地再现那种不可名状的真正的“真实”,不如用人类的理智去设想一种比较完美的、符合自身知性与理解力的“审美对象”,正因为如此,悲剧才是“虚构”和“摹仿”的统一体,虚构是为了满足理性需要,摹仿则是为虚构提供了素材,因为摹仿的对象是精心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那个最原初的、没有任何因果必然性可讲的、混沌的、甚至可怕的外部真实。 在《文学阅读指南》(How to Read Literature)里,伊格尔顿举了莎士比亚《暴风雨》第四幕第一场的例子: 我们这一些演员们……他们都已经化成淡烟消散了……入云的楼阁、瑰伟的宫殿、庄严的庙堂,甚至地球自身……都将同样消散,就像这一场幻景……构成我们的料子也就是那梦幻的料子。[7](P57) 伊格尔顿想要借这部作品来表达:剧场、人物、事件都是虚构的,可是舞台上再现的人生却是实实在在的,因此虚构和现实之间并没有什么明确界限,难道演戏和看戏不也是真实的活动吗?尽管戏是虚构的,但人生是真实的,文学艺术用虚构的方式为我们再现出一个又一个值得反思的真实生存境遇,这不就代表了它最大的真实吗?进一步说,我们自己创造出的世界,那些亭台楼阁、宝马香车不也是我们演出每个自我人生的布景吗?于是,伊格尔顿再次回到了文学艺术与道德关系上来,他说:“剧场能给人真知灼见,但这见地是关于人生之虚幻的。……人既知必死,才会生出谦卑之心。……因为我们的道德困境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人人都不自觉地以为自己会长生不死。”[7](P57)文学艺术既是对人生和现实的虚构和摹仿,同时还要利用这种手段,让人们在构想未来的同时反思现状,这不正是文学艺术所具有的最大的政治与道德伦理价值吗? 自从进入新世纪以来,伊格尔顿关注的领域更加宽泛,讨论他发生各种“转向”的观点应运而生,“神学转向”[14]、“哲学转向”[15]、“伦理学转向”[16],不一而足,难道伊格尔顿把注意力转到文学之外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文学依然是伊格尔顿最关注的学术领域,只是这些年来,他借助美学、哲学、伦理学甚至神学中的一些概念,从新的视角出发重新对文学进行了审视。而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对文学与实践、现实生活与乌托邦、政治与伦理道德、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诸多问题的真实看法。 ①此概念包含技术与艺术,亚里士多德把诗歌、绘画、雕塑、演奏等艺术活动和医疗、航海、战争等专门职业的活动都划入工匠的制作活动的范畴,详情参见廖申白:《亚里士多德的技艺概念:图景与问题》,《哲学动态》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