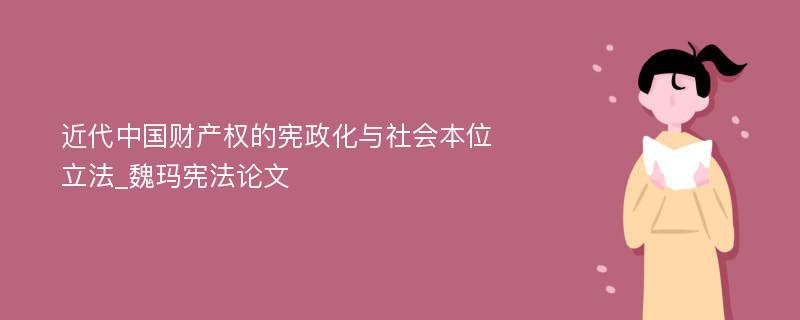
财产权宪法化与近代中国社会本位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产权论文,本位论文,宪法论文,近代论文,中国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民法典颁布后,吴经熊撰文鼓吹国民政府的社会本位立法:“俗言说的好,无巧不成事,刚好泰西最新的法律思想和立法趋势,和中国原有的民族心理适相吻合,简直是天衣无缝!”吴氏总结西方20世纪以来的法律社会化对个人主义的扬弃,认为“泰西的法律思想,已从刻薄寡恩的个人主义立场上头,一变而为同舟共济、休戚相关的连带主义化了”,这与中国法律道德合一的传统不谋而合,也为近代中国移植西方现代民法提供了“本土资源”。①学者王伯琦在20世纪50年代反思近代中国社会本位立法,对吴经熊上述观点批评说:“这件天衣,虽是无缝,但是件狐裘。西洋的时季已届隆冬,体质已剩了点皮骨,穿上这件狐裘,非常舒适。我们的季候仍是盛暑,体质亦肥浮不堪,穿上了这件狐裘,看来虽是漂亮,终不免觉得发骚……我们固有的道德观念,与他们(西方)道德,根本的不相为谋……他们的社会立法是从个人出发而到社会的,没有个人权利观念,根本就无从谈起社会利益……脱离了个人观念的社会观念是单纯的义务观念,单纯的义务观念近乎奴隶观念”,在近代中国个人权利观念不发达的法律文化背景下,以民生主义为指导的大规模社会本位立法破坏了民法的自治,不利于公民私权的保障与人格的发展。②实际上,在20世纪20-40年代民国大规模立法过程中,“法律社会化”几乎是众口一词;而王伯琦本人在早年也曾高举“法律社会化”的大旗,还翻译了法文版的《权利相对论》。③王伯琦晚年对社会本位立法的反思,或许与不尽如人意的私权保障现状相关;他对近代中国社会本位立法的批评的确有一定道理,但这在某种程度只是“事后诸葛亮”、“成败论英雄”。近代中国法制必须要走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老路,逆20世纪西方法律社会化的潮流而动,“刻薄寡恩”地培育“个人本位”的法律文化、维系“私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吗?本文拟以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财产权为中心,考察近代中国财产权的社会立法,比照外国理论与经验,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一、欧美财产权的理论与实践演进 (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古代无所有权思想,及社会稍进步,动产可归私人之所有,而不动产则个人仍无完全所有权,所谓‘王土主义’,此征之历史而易知者。认人民有完全所有权者,近世文明之制度也。”④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大都鼓吹财产权,马基雅维利在政治上主张君主专制,在经济上却强调尊重公民的财产权,认为统治者不能恣意侵夺公民财产或随意征税,如此方能令个人安居乐业进而实现作为整体的国家的发展与富强。⑤洛克思想在财产权理论方面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他详细论证了财产权(包括获取和保有财产的权利)乃是个人的自然权利,这意味着它不是主权者恩赐的而是天赋权利,自然不能为主权者所恣意侵夺。⑥主权理论的开创者博丹虽主张主权归于君主,认为君主不受实证法约束,但他同时强调:“君主应受自然法的限制,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就是自然法之一”;“欧洲国家能由重商主义,而引起工业革命,造成灿烂的文化,就是由于财产权之有保障。”⑦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颁布,财产权作为与自由权、生命权并列的基本权利(古典权利),“神圣不可侵犯”。⑧在美国宪法(包括权利法案)颁布的时代,洛克思想为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所吸收,财产权保护是普通法的核心内容之一。美国宪法宣称财产权“不可侵犯”,但征收条款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个人自主性的要求必须受到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摩擦冲突的节制”;基于公用目的,个人财产是可以被“夺取”(taking)的;尽管宪法规定征收财产必须提供相应的对价,但宪法也暗示财产权“不再受到绝对的保护”(不再“神圣”)。⑨ (二)“财产权负有义务”:宪法社会权的创设与公、私法界限的崩塌 一直到《德国民法典》颁布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当时的经济生活完全由一种自由主义所左右,这种思想倾向相信,只要经济力量的作用能够不受国家干预的阻滞而自由扩展,那么普遍的繁荣兴盛就会自然成就。”⑩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在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却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公平的财富分配以及伴随而来的各种社会邪恶,使得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兴起不可避免”。(11)《德国民法典》据称加了“几滴社会主义的润滑油”,但总的来说当时法律社会化的倾向仍未渗入私法领域;不过在民法典之外,基于社会本位的立法开始涌现,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单行立法,如竞争法、住房建筑法、租赁法、农地租赁法、劳工法都发展起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新兴的社会法与经济法打破了私法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垄断地位,例如关于住屋保障的立法与土地交易的管制,都“深刻突破了契约自由与财产利用自由”,并消解了私法“内在的统一性”;究其原因,与近代中国类似,德国两种非自由主义(反个人本位)的法律理念,即封建的、父权主义的传统国家理念与现代福利国家思想“不谋而合”、“天衣无缝”,为社会本位立法的发展提供了土壤。(12) 1919年《德意志联邦宪法》(《魏玛宪法》)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现代资本主义宪法,与民国时期的中国类似,它要同时面对现代化的民主自由要求与现代后的社会本位、福利国家问题。在涉及国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第二编中,《魏玛宪法》囊括了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法国宪法的人权宣言,还采纳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条文,可说是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妥协的产物。(13)它的颁布具有重大意义,社会本位(社会连带)的思想本源自法国,但其在宪法上最典型的产物却是德国《魏玛宪法》。在此之前,社会与国家在理论上是分离的,私法通过组织起一个“非政治化的”排除国家干预的经济社会,维护了法律主体的消极地位,并因此维护了法律自由的原则,公法在法律分工上主要是限制政府权力。尽管政府已经开始以权威主义方式实施社会保护的义务,但直到魏玛宪法颁布,“私法据说具有的那种自足性的宪法基础才归于消失”;它标志着私法(个人的消极自由)对宪法(以福利国家的强制力量为背景的公共利益)的实质优越性的终结。(14)二战后的德国基本法尽管废弃了魏玛宪法关于社会权的具体条文,但却将“社会国原则”作为与民主国、法治国原则并列的宪法基本原则之一确定下来,并最终将德国建成福利大国。以房屋租赁管制为例,本来只是一战时的临时性的应急法制,却成为持续性的社会住屋法的滥觞,历经魏玛德国、纳粹德国的政权更迭而延续到二战后。 自洛克以来,“自由与财产就成为自由之国家市民社会的守护神”,市民不动产法制的出发点乃是“所有权人拥有事实上与法律上之自由处分权的土地所有权”。但是,在社会本位立法之下,作为产权之王的土地所有权也必须服从公法管制,“土地所有权所负社会义务所达到的程度,在私财产史中绝无前例”;“经济社会不断整合进公法秩序之内”,这显然并非“古典自由主义所乐见”。(15)在人民饱受饥饿之苦时,“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经济法不是自然法,他们要由人类制定。”(罗斯福语)(16)美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福利国家,宪法中也没有社会权的内容,但其通过罗斯福新政肯定了社会福利权与“有为政府”(positive state)的正当性。1941年罗斯福将“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of want)列为“四大自由”之一;1944年,罗斯福提出所谓“第二个权利法案”,它具体包括了足以应付衣食与消遣的收入,充分的医疗保障,体面的居所,好的教育,养老、疾病、事故与失业的救济等。(17)可直至今天,罗斯福新政的合宪性与社会福利立法的正当性,在美国仍然遭到秉持古典自由主义与经济分析工具的学者的根本性质疑,他们认为公、私法分立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崩塌,破坏了古典普通法的法制一贯性与智识统一性;为了尊重财产权的基本规则,避免福利政策的带来的恶性循环与最终失败,最佳的选择是政府彻底放弃福利政策,“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18) 二、传统中国的财产权保障及其限制:以土地产权为例 (一)古典成文法的颁布与土地私有财产权的确立 在夏商周三代,中国奉行“王土主义”的土地国有制度。从春秋中晚期鲁国“初税亩”到秦国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国家逐渐承认土地私有制。并非偶然地,几乎在土地私有化同时,从郑国子产率先“铸刑书”到魏国李悝编纂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还发生了公布成文法运动。虽然我们无法确知“刑书”与《法经》的具体内容,但这些成文法无疑为平民(新兴地主阶级)提供了“权利保障书”,在下者可以据此对抗在上者的恣意妄为。据学者研究,最早的成文法“刑书”的主要内容便是关于财产与司法等方面的规定。(19)根据史书记载叔向对“铸刑书”的反对意见,如公布成文法会令民“有争心”、“权移于法,故民不畏上”,(20)我们也可以推知成文法保障了平民的基本权利(如财产、生命与身体自由)不再受到政府官员(贵族)的任意处置。由此,中国古代法制虽未对人民财产权提供“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保障,至少也有了适度的保障。在当时的法家看来,法律的重要作用之一便是通过确立财产所有权来“定纷止争”,“允许人人都有财产所有权,正合乎‘因人之情’的‘天道’,不是立法为私而是立法为公”。(21) (二)财产权的“浅化”与“深化” 尽管传统中国成文法制出现很早,其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也远远早于西欧封建国家,但基于特殊的政治与社会文化背景,古代中国在财产权(特别是土地财产权)绝对化的问题上却始终犹豫不决。土地制度史的权威学者赵俪生先生用私有制的“浅化”与“深化”来描述传统中国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从土地私有制的“浅化”来说,土地“私有制从一开始就遭遇障碍”,“古老共同体(公社残余)是私有制深化途程上的第一重障碍;国家权力对私有财产(包括土地私有权)的干预,是第二重障碍。”(22)从理念上,“言必称三代”、“扬公抑私”的中国古人,往往将代表古老共同体传统的公田制(井田制)作为土地产权制度的最高理想,尽管因现实局限无法彻底贯彻土地公有理想,土地制度也要向理想一面靠拢、限制私人土地产权;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国自古人多地少的矛盾就比较突出,抑制土地兼并、扶助无地少地的农民成为古代中国政府的重要社会政策。古代政府常常试图限制私人土地产权,如晋之限田制、北魏延续到唐之均田制。顽强的古老共同体基因与发达的国家权力相结合,使得在私有财产权尚未“深化”之际,中国的社会本位立法就已相当早熟;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理念不同,传统中国国家对人民土地产权的干预不是一种天然的“恶”,反倒自始便是一种必要的“善”。可公田制的理想终究敌不过有产者私有化土地的经济动力,均田制对土地私有与买卖的限制,逐渐为“贵者”、“富者”所冲破。宋代以后中国的土地产权已经高度私有化,尽管国家依然拥有大量土地,但此时国家已经“纯乎与私家地主相同的身份”来经营土地、“与私人地主已无大差异”,是为土地私有制的“深化”。(23) 即使在宋以后土地私有制深化(国家放弃土地社会政策)的背景下,古老共同体的传统依然会对私人土地财产权的绝对化形成重大障碍。传统中国“个人不能由团体而独立,个人依赖于团体而存在”,(24)在家族、宗族与乡村范围之内,小共同体的公产仍然与个人的私产并存。(25)另外,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处理民间财产争讼案件的最高原则是和谐共存,而非财产权的绝对保障;当财产权的实现威胁到他人的生存权时,传统法律则不支持、甚至否定财产权绝对化的正当性,“无视邻人生存权主张而试图彻底贯彻自己权利的做法经常会得不偿失”。(26)例如,地主夺佃(合法收回其土地)如造成佃农一家走投无路,佃农作为弱者一方可以自杀作为最后的对抗手段,这时根据刑律“威逼人致死”条,地主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尽管从现代法角度看,地主财产权的行使与佃农自杀并非直接因果关系。 三、近代中国制宪史上的财产权社会化 (一)财产权的法律限制 晚清以来不少有识之士反思近代中国的“积弱积贫”原因,认为家族主义造成中国民众“一盘散沙”、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在传统中国小共同体主义之下,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都无法伸张。于是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两种看似对立的舶来思想交织在一起,国家主义部分吸收了个人主义,正面对抗传统的家族主义。检视20世纪30年代初完成的民国民法典,在身份法方面已大致实现男女平等,并基本破除了个人对于家族等小共同体的依附关系;在财产法领域,新民法的立法精神除提供财产权的保障外,已开始强调社会公益,以预防个人自由权利的滥用。(27)就制宪史而言,20世纪初中国开始制宪之时,古典自由主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在西方已开始褪色,宪法财产权自引入中国就并非绝对排他的权利。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人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犯”,这几乎是照搬日本明治宪法条文。(28)1912年《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第6条第2款),但《临时约法》没有美国式的征收补偿条款,只是笼统授权立法者可以限制人民财产权等权利:“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29)在民初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关于天坛宪草条文的《说明书》中,负责起草财产权条款(30)的委员何雯认为:“私权应否受限制,此系私法上之问题”,“关于人民财产全部有自由权之原则,须在民法规定非宪法上之问题”;此观点在财产权问题上区隔了公法与私法,接近西方法律社会化之前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31)在对天坛宪草包括财产权在内的人民基本权利条款审议过程中,有代表主张自由权规定应采宪法保障主义,反对将自由权交由法律限制;但制宪者多数认为对自由权亦有限制之理由:“近人多误解自由意义”,“自由既非绝对”,“故必明定限制”,当然法律亦“不能抵触宪法”、“不能非分剥夺自由权”。(32)在这里,近代中国制宪者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上接受了基本权利(包括财产权)的相对主义。 可是,正如古典自由主义所担心的,政府有滥用其权力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倾向,这一点在近代中国表现得尤其突出。清末民初以来,人民饱受“武人、政客、帝国主义的蹂躏”,袁世凯政府更利用宪法的立法授权制定恶法、侵犯公民的自由权利。糟糕的人权经验使得人们开始质疑基本权法律限制主义的正当性:“是宪法畀予之自由,皆得以普通法律剥夺之,宪法保障,不几等于虚伪吗?”(33)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宪法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张知本也主张废弃宪法基本权利条文中的“法律限制”字眼、采宪法直接保障主义。但宪法起草委员会另一位副委员长吴经熊则认为:对人民基本权利采宪法保障主义并不现实,“二十世纪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已经离开纯粹的自由很远了”;更何况,人民权利的被侵害,主要不是因为“‘依法’限制的缘故,实在是行政官吏未能依法办理所致”。针对吴经熊的答辩,张知本反驳说:所谓“世界趋势至二十世纪以来,自由主义趋势已不适用”,“此系指关于人民财产等自由言之”,他本人强调的是对于人民身体及言论自由应采宪法保障主义,至于财产权则可继续授权立法机关以法律限制之。(34)这意味着,制宪者可能对人民身体自由与政治权利的法律限制问题高度敏感,但他们对于20世纪的法律社会化潮流与财产权的限制问题则有相当的共识。事实上,张知本个人在其著作中也鼓吹二十世纪西方的宪法财产权转型:“从前各国宪法,均视私有财产为神圣不可侵犯,而定于宪法条文之中,绝不加以何种限制”;而德国魏玛宪法则对财产权在保护的同时施加了不少限制,例如魏玛宪法第153条第2项规定“国家因公共福利之故,得依法律所定,没收私人财产”,再如魏玛宪法第155条第2项规定“国家因住居之需要,以及奖励移民开垦或发达农业之故,得没收其私有土地”;“所有权负有义务,所有权之行使,同时又当增进公共福利”。(35)“财产绝对自由之结果,必然形成一方为有产者之财富集中,一方为无产者之数量增大。此时人类之共同生活,在经济上已失均衡,而社会上之全体利益,自必随之而供牺牲。故现代宪法,为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调和起见,一方固仍承认个人之私有财产权;以保障个人利益,同时又不得不于相当范围内,与于个人财产权加以限制,藉以巩固社会利益。”(36)当时有学者甚至明确指出财产权“不能与各种个人自由权相提并论”;而继承权则更是“次等”的财产权,对其可加以“重大限制”:“私产只是暂须容忍,而不是长应拥护的一种制度。私产如果完全由子嗣继承,私产制度固益见巩固……所以晚近各国的法律皆有限制继承权的倾向,德国1919年的宪法,且明白宣誓国家可以征收继承财产的一部分(第154条)。”(37)由于财产权与其他自由权相较是“次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将财产权在体系上安排于总纲、而非人民基本权利义务一章,这放在民国语境下似乎也可以理解;而张知本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所做的个人试拟稿,便将财产权规定于“民生”章,而非“人民基本权利义务”章。(38) (二)财产自由与国民生计的平衡 其实,近代中国的主流宪法思想对于财产权一直是主张予以节制的,如果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宪法思想因其“党义”色彩不为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赞同的话,德国《魏玛宪法》的社会福利权思想经过张君劢等人的引介,则在制宪史上大放异彩。近代中国将社会福利权纳入宪法的努力,较早始于1922年国是会议宪法草案,当时不论是张君劢主稿的“甲种草案”还是章太炎主稿的“乙种草案”,尽管其政体设计迥异,但均专章规定了“国民之教育与生计”;具体包括规定专款以促进教育文化之发展,用税收等手段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并限制土地所有权,以保障普通人民之生计。(39)将社会权详细列举于宪法,这似乎是受了当时的欧陆社会连带主义思潮以及1919年颁布的魏玛宪法的影响。《魏玛宪法》颁布之际,张君劢正在德国游学,他第一时间即看到宪法文本,还拜会了宪法起草人柏吕斯(Preuss)。(40)张君劢明确指出《魏玛宪法》在世界宪法史上代表着最新的范式:“美国宪法所代表者,十八世纪盎格鲁莎克逊民族之个人主义也;法国宪法所代表者,十九世纪民权自由之精神也;今之德国宪法所代表者,则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潮流也。”(41)作为张君劢的老师,梁启超在清末曾鼓吹重商主义,强调“摆在中国面前最严重的问题不是财富的分配,而是生产问题”;“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但一方面,其理论前提是梁氏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不同,在经济上不存在两极分化,故而不需要社会革命;另一方面,他并非无条件的接受英美式的资本主义,而是提倡一种混合的制度,其观点更接近一种德国式的社会改良主义:“在这一制度里,私人企业将受由政府确立的一套社会主义政策的调节,这些政策与俾斯麦时代德国确立的政策十分相似。”(42)以张君劢(也包括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一战”后,对个人主义的英美哲学有了更多的反思,开始结合欧陆(典型如德国)哲学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新宋学”),通过对西方物质主义的批评,强调人的价值以及人民幸福的优位性;这反映在宪法上,则是对魏玛所创设的宪法社会权的鼓吹。(43) 到1946年拟定中华民国宪法时,考虑到当时的人权状况,张君劢等人放弃了社会权优位性的主张,强调国民“应享有凡民主国家人民一切之权利及自由。法律规定应出于保障精神,不以限制为目的。”(44)即便如此,1947年颁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基本国策”一章还是用15个条文之多详细规定了国家社会经济政策,强调“国民经济应以民生主义为基本原则,实施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谋国计民生之均足”(第142条),其中有的宪法条文基本照搬了《魏玛宪法》的规定,(45)例如该宪法第143条第3款“土地价值非因施以劳力资本而增加者,应由国家征收土地增值税,归人民共享之”,这与《魏玛宪法》第155条第3款后半段“土地价值之增加,非由投资或人工而来,其福利应归社会”符合若节。(46)政协宪草送交制宪国民大会审议通过时,原本单纯的财产权保障条款(“人民之财产应予保障”)(47)竟发生重大变化,与生存权、工作权“搅合”在一起,并且将财产权列为该条最末之权利:“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应予保障。”(宪法第15条)究其立法理由,据制宪者称国大代表“讨论时,咸以为人民之财产权,固应保障;然对于无财产者之生存权及工作权,亦应加以保障,否则本宪法仅保障有财产者之财产,实属有违民生主义之精神,及成为偏重保护资产阶级之流弊”。(48)将自由权与社会权并列,生存权、工作权与财产权“三位一体”,这与《魏玛宪法》“经济生活”章的原则规定(49)异曲同工,也回应了古代中国平衡财产权与生存权的传统。关于生存权的性质及其与财产权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生存权虽非私法意义上之权利,然亦非单纯之自由权,具有更积极的意义与内容……为与自由权相区别起见,可称为经济的基本权”;将财产权“列于具有受益权性质的生存权、工作权之后,尤可见其保障财产权之用意,实由于维持人民生存权之必要,而为达到保护生存权目的之手段”。(50)与古典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同,现代社会“个人生存保障与生活形成的基础,很大程度上已不再建立在民法的传统意义的私人财产所有权上面了,而是建立在每个人的工作以及参与分享由国家提供的生存保障与社会救济的基础上。”(51)对照政协宪草与中华民国宪法,财产权条款为其中罕见的几处变动之一,而以政协宪草全文通过为条件参加制宪国民大会的民社党及其党魁张君劢,对此并未激烈反对。 四、作为社会性权利的宪法财产权:以土地与房屋产权管制为例 (一)宪法财产权的性质之争:纯经济利益还是社会性权利 早期宪法财产权的性质与内涵直接承袭自私法,“只不过宪法财产权是指向国家而非私人,是要绝对地排除国家公权力对于个人财产权的干预”;可随着《魏玛宪法》的颁布,财产权是社会义务被写进宪法、财产权的内涵也大为丰富,这也是魏玛宪法被视为“近代宪法转向现代宪法的界碑”的重要理由。(52)随着宪法作为高级法观念的普及、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以及社会本位立法的实践,私人财产权绝对化的观念已不复存在。尽管如此,直至今日各国关于财产权的性质及其法律效果仍有很大争议,财产权的理念与制度在世界范围内仍在演进之中。有学者比较各国的宪法财产权理论与实践,认为宪法财产权在当代发展出两个趋势:其一是私人财产权所负社会义务的宪法化(典型如德国);其二是宪法财产权条款由个人所负之社会义务,发展至政府的社会改革义务,典型如南非宪法财产权条款规定国家应推动土地改革以实现人民(贫民)获得土地的权利,该款也明确所谓“公共利益”即包含国家实行土地改革的承诺(1996年《南非宪法》第25条第4、5款)。(53)考察近代中国法制史,南京国民政府在土地改革方面的努力与上述南非范式接近,是直接由政府挑头推动社会改革;而其在房屋租赁管制方面的尝试则与德国经验高度类似,是尝试通过“基本权的第三人效力”平衡房东与房客的权利、“间接”地实现社会福利。 “土地为国家成立之要素,一切财富生产之基础。”(54)各国在宪法意义上的财产权争议,通常都与不动产所有权的限制高度相关。以土地征收为例,尽管各国在宪法上均规定了应对征收给予补偿,但补偿标准仍然有相当大的差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原则上坚持补偿应按市场标准足额补偿;《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3款笼统规定“赔偿应公平衡量公共利益与关系人之利益”,德国宪法法院认为这意味着补偿通常应按市场标准,但根据基本法的授权立法者经过利益衡量给出的补偿标准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背离市场的价格;南非宪法法院则认为,基于南非特殊的社会与政治历史背景(种族隔离与种族压迫的历史造成严重贫富分化),征收补偿必须综合考量社会经济目的与市场标准,因此市场价格并非征收补偿的唯一标准。(55)印度关于征收补偿的标准则长期存在争议:1950年《印度宪法》颁布时,基于土地改革与经济改革的现实需要,印度政治领袖尼赫鲁总理认为宪法“财产权条款只不过提供的是对财产权的有限保护,它包括对小型强制征用的补偿,却不适用于让全国大多数人受益却只是对少数地主有不利影响的大规模社会工程方案。”“如果从社会的视角而非财产所有者个人的视角看”,政府即使未按市场价格支付土地征用补偿也仍然是公正的。尼赫鲁的“社会主义”观点很快遭到保守的(对财产权持古典自由主义观点)最高法院的坚决反对,酿成印度最高法院和国会长达25年之久的冲突,并导致印度国会最终将财产权条款移出权利法案。(56)《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1款规定“财产权与继承权应予保障,其内容与范围由法律规定”,这也确立了财产权的法律保留(法律限制)原则;第14条第2款规定“财产权伴随义务”。这表明在德国制宪者看来,财产权是一项社会性权利。在社会国原则之下,由于财产所有权伴随的社会义务,财产所有者可能要承担征收补偿低于市场价格的风险;考虑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局限与市场资源的稀缺性,如果政府要对所有私人财产权的社会限制均予以市场价格的补偿,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将会少得可怜。或者我们可以说社会政策本来都是建立在对自由市场原则的修正之上,如果没有对私人财产权的限制(包括直接的征收或间接的转移支付),一切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都不可能存在。 关于财产征收补偿标准争议的核心实际是财产权的性质问题。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将财产权作为纯粹的私权利,即使国家基于公共目的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要征收私人财产,那也必须是以市场的价格给予补偿,宪法征收补偿的规定在此意义上乃是私法上的买卖规则(等价交换)的拟制,从纯市场的观点看征收不会造成财产所有者的经济损失,这也意味着财产所有者无须为公共利益承担经济上的义务。美国与德国宪法财产权的差异,不在于宪法文字的丰俭或财产权在整个基本权利体系中地位的高低,而在于财产权内涵的不同。在美国通过严格审查而获得更多保障的财产权主要是“完全商业性质”的“财产性利益”,而在德国的财产权体系中,“一些财产性利益,由于不直接体现人的尊严和自我实现这些基本价值,它们在德国基本法中仅获得最低限度的保障。”(57)如何理解德国与美国财产权内涵的不同,德国宪法法院房东—房客案(Landlord-Tenant Case 1993)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该案中,面对房东行使财产权的要求,房客所提出的抗辩理由是根据基本法14条财产权条款第2款“财产所有权附有义务,它必须服务于公共福利”,以社会权对抗房东的财产权;但宪法法院在保护房客安居权利的同时认为,房客住房权与房东所有权的宪法依据是同一的,均为宪法14条第1款“财产权应受到保护”,这意味着房客的房屋租赁权被宪法法院同样认定为财产权,因为在宪法法院看来安居(房屋租赁关系的稳定)对于房客来说意义重大:宪法保护房屋财产权的核心不是物本身,而是个人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自由空间;宪法保护财产权的首要目的不是促进经济效率,而是保障个人自我发展所必须的物质条件。(58)与德国宪法法院类似,欧洲人权法院也通过判决(Iatridis v Greece,1999)丰富了宪法财产权的内涵,在房屋租赁关系中,该法院经由适用宪法财产权条款,将私法上并不视为财产权的房客缔约利益,转化为宪法上的财产权。(59) 与德国相仿,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将财产权与生存权并列在同一条款的做法高度肯定了财产权的社会属性,宪法对财产权也采用了法律保障(法律保留)原则,这意味着对财产权的限制与社会正义的实现必须通过国会立法获得合法性,再将法律交由行政机关予以落实。与南非的状况相近,近代中国残酷的社会经济现实要求政府必须积极作为、实现人民的社会权,而民国宪法也在“平均地权”等方面课以政府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奉孙中山民生主义为宪法指导思想的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立法,管制土地及城市房屋的产权,以保障农民生产与市民安居的基本社会权利。早在1947年宪法颁布之前,1930年土地法便触及了财产权的核心——土地产权,甚至试图对于土地进行再分配,这在理念与制度上打破了传统私法的“法制一贯性与智识统一性”。考虑到民国土地法与民法典几乎同时颁布,我们也可以说在近代中国语境下,在法律意义上财产权自始便受到社会本位立法的规制。 (二)土地改革:财产权的“社会革命”及其挫败 关于近代中国农村严重的贫困问题,当时不少中外观察家均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地分配不均,地主通过收取高额的地租剥削农民使后者陷于绝境:“在(造成农村危机的)经济及社会因素中,也许租佃制度是最令人不安的因素。”(60)与欧美近代资本主义崇尚个人主义与自由竞争的理念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财富观与“大同”的理想。近代中国人甚至将儒家“均平”的思想介绍给西方,对于凯恩斯主义与罗斯福新政发生过一定影响。(61)孙中山更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作为民生的核心,与民族、民权共同构成其三民主义的思想。孙中山提倡的民族主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击中了晚清民族矛盾尖锐的要害;但是,就国民党的政治、社会基础而言,民生主义则是“躐等”、激进的思想。在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修正过的土地政策与之前相较已经比较温和,由土地国有、“不耕者不有其田”转变为“核定地价、涨价归公”。到1912年3月,同盟会吸收包括唐绍仪在内的其他士绅团体,由革命团体改组为公开政党——国民党。此次改组使国民党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为达成妥协,国民党放弃了同盟会之前相对激进的社会革命政策,在其党纲中删除了同盟会“男女平权”的主张与孙中山关于地租与“地权”的政策。孙中山的土地政策尽管已经变激进为温和,但仍然让“出身上层社会”的人感到不安。(62) 尽管在地租与地权问题上,国民党为团结士绅,于民国草创之时即与其达成了妥协,但1924年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后,又重提“耕者有其田”的理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奉孙中山思想为最高指导思想,在立法院长胡汉民的领导下,立法院于1928年和1930年先后通过了《土地征收法》和《土地法》,以解决农村土地问题。(63)作为“最富社会性的法典”,(64)《土地法》规定了佃租率的最高上限(地租不得超过正产物收获的37.5%);还规定对不劳而获的土地增益征收累进税(涨价归公),以税收的方式使土地收益回归社会,并通过税负促使地主转让土地所有权给国家或佃农。《土地法》还提出消除地主所有制的远景,例如承租人连续耕作10年以上之耕地,(65)其出租人为不在乡地主时,承租人得请求政府代为照价征收该耕地(仍交与承租人耕作);地主出佃土地超过法定面积的部分国家得予以征收;而法定国家征收土地的首要公共目的,就是实施国家经济政策、调剂耕地。土地改革也得到知识界的正面回应,当时中国地政学会对“中国宪法中关于土地事项应如何规定”所提九项原则与国民政府土地政策事实上非常接近,具体包括“土地之使用,为所有人对于社会应尽之义务,须受国家之督促与限制”;“土地之分配,由国家统制之。农地之分配,以扶植自耕农为原则”;“地价之增益,非因所有人实施劳力或资本于土地所致者,应收归公有”等。(66) “平均地权”的“国父遗教”乃是国民政府的“最高指导思想”,它符合20世纪西方法律社会化的潮流,得到知识界的广泛拥护,在纸面上也落实为宪法与法律的条文。照理讲土地改革应当能顺利推行,可“1930年土地法始终不过是一份极好的表达意向的文件,因为南京政府从未执行过。”土地法没有真正实施的原因在于:国民党作为一个与保守的士绅阶层密切联系的政党,并不希望因为土地政策而疏远地主;“他们害怕解决租佃制度会引起社会革命,其结果他们既不能控制,也无法预见。”(67)由于其阶级局限性,国民政府根本无法贯彻其党纲国法中的土地改革政策。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当时财产权仍受到相当的保障,政府即使在获得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仍然不能重新分配产权;与财产权的消极保障相较更严重的问题反倒是宪法与法律上的社会权无法得到政府积极落实。无独有偶,尽管1996年南非宪法规定了政府土地改革的权力与义务,但南非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至今尚未得到矫正,人民积极财产权的实现依然遥不可及。私有财产权作为一种“自然权利”相当强大,即使宪法与法律并未对其提供充分保障,它还是能够对抗公权力、甚至消解财产权的社会革命立法。 (三)房屋租赁管制:公法与私法上财产权冲突的平衡 市民“居者有其屋”,与农民“耕者有其田”一样,都是生活基本需求。在国家财力有限、公共住房项目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对私人房屋租赁关系予以管制,限制房东的财产权以保障房客的安居权,也成了近代中国与德国的共同选择。如前所述,德国房屋租赁的管制,本来只是为应付大规模战争造成住房紧张的临时措施,却历经“一战”后重建、“二战”、“二战”后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而长期化;尽管联邦德国逐渐放松了房屋管制,但租金上涨的管制与租约终止的保障仍延续至今。(68)“无巧不成书”的是,与前述中国古代地主土地所有权的行使(夺佃)要受到佃农生存权(以自杀相抗)的制约类似,在当代德国也有相应的极端案例:房东有合法的理由将租屋收回自用而房客拒绝搬走,尽管房东财产权的行使获得了法院裁判的支持,但如果房客心理特别脆弱、有自杀倾向,且房客不稳定的精神得到了医生的官方证明;根据德国法就出现了法律执行的障碍,法院必须推迟执行(将房客驱逐出租屋),在极端的案件中甚至无限期中止执行。(69) 就南京国民政府的居屋保障政策来说,早在1930年《土地法》中,便设立专节规定“房屋救济”:为保障房屋承租人安居,房屋出租人无法定理由不得解除租约;为保障房屋供应量,规定城市应以所有住房总数的2%作为准备房屋(所谓“准备房屋”是指随时可供租赁的房屋);当准备房屋额连续6个月不足房屋总额的1%时,市政府应:(1)规定房屋标准租金(以不超过土地及其建筑物之估定价格年息12%为限);(2)减免新建房屋之税款;(3)建筑市民住宅,该公共住房的租金不得超过土地及其建筑物之估定价格年息8%。在抗战期间,受战事影响,人口集中于后方,房屋供需关系严重失衡,房屋所有人趁机索取高额的房租与押租(担保金)、并尽可能缩短租赁期间;为保障承租人利益,国民政府于1943年12月公布《战时房屋租赁条例》,对于房屋所有人收取租金、担保金的标准,以及终止合约的理由,都进行了更严格的限制;同时规定承租人于约定租期届满后,得继续承租。(70)与德国的经验类似,抗战胜利后《战时房屋租赁条例》有效期届满,但政府并未就此放松对于租屋的管制,1946年修正《土地法》的相关规定比1930年《土地法》更为严格;(71)临时性管制立法《战时房屋租赁条例》也于1947年“升级”为《房屋租赁条例》,该条例堪称“史上最严”的租屋管制法,略举数条如下:为开辟房源,该法授权地方政府可强制房屋所有人出租其既不自用又不出租的多余房屋,对于房屋所有人“自用房屋超过实际需要的”政府也可“限期命其将超过需要之房屋出租”,房屋所有人如违反上述规定政府除强制其出租外还可对其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房租上限由当地政府经民意机关同意后,根据当地经济状况予以确定;约定租金超过前述上限的,超过部分为不当得利,房屋承租人得于支付租金后6个月内要求予以返还;房屋所有人收回自用之房屋,如有3个月空闲不用,或于1年内转租他人者,原承租人有权要求继续承租并得要求房屋所有人予以赔偿;条例还限制转租以避免“二房东”从中谋利。(72)《房屋租赁条例》颁布之时已是国共内战正酣之际,当时国民政府可说是“民心尽失”,但“该条例一出,获得实务界和学界的一致好评,并被认为是所有权社会化学说指导下的立法典范。”(73) 土地改革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与当代南非都失败了,房屋租赁的管制在德国与近代中国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将私人财产权所负的社会义务的宪法化,平衡财产权的私权属性与社会属性,这远比直接重新分配所有权要来得容易。 回到本文开篇王伯琦对民国时期法律社会化的批评与对吴经熊观点的揶揄,笔者怀疑:当其批判中国传统对于独立人格的压抑时,批判的究竟是身份的不自由,还是财产的不自由。就身份自由而言,个体化(社会的原子化、家族的解体)会随着市场化与全球化而完成,财产的不平等却很难通过“看不见的手”予以矫正。一个民族的法制选择难免与其固有文化有关,父权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的传统为福利国家的大政府提供了政治与社会资源,德国便是如此,从这个角度讲,近代中国似乎也可以安心披上吴经熊所谓“天衣无缝”之狐裘,而不必如王伯琦般担心水土不服、“热得发骚”。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可以有高下之分的,面对现代福利国家的潮流,宪法财产权似乎不必完全与人身权(包括人格尊严)等量齐观。限制财产权的社会立法之发达,似乎与社会上发生的公民自由权与生命权的侵害案件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就近代中国而言,与一般民众的普遍贫困、亟需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的严酷社会经济现实相较,有产者财产权的保障现状不能说特别糟糕;从当时的法治现状来看,公民积极社会权与消极财产权的保障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绝大多数对于私人财产的侵害也未见得是基于公共目的。如前所述,吴经熊针对当时宪法基本权利是采宪法保障主义还是法律保障主义的争论,便提出解构式的回答: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立法机关是否会违宪制造恶法侵害人民权利,而在于政府官员根本不遵守法律、恣意侵害民权。 当代不少人拘泥于所谓宪法财产权的“形式主义陷阱”,将宪法财产权条款与市场经济、法治联系在一起,片面强调没有宪法的保障就没有财产的安全也就没有自由、繁荣的市场。(74)这可能是对财产权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误解。首先,在古典自由主义法制之下财产权专属于私法领域、高度独立于公法,私法作为封闭的体系为财产权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反倒是现代宪法关于财产权的规定为公权力侵入私法领域、并限制财产权提供了宪法依据;其次,自20世纪法律社会化以来,宪法财产权的内涵已发生重大变化,与财产权的社会属性相较,纯粹商业视角的经济利益在财产权体系的重要性已相对降低,对宪法财产权的保障有时反倒意味着对私法意义上财产权的限制。在当下中国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财产权的规定在具体内容与体系安排上有如下“缺憾”:其一,将公有财产描述为“神圣不可侵犯”,而紧随其后的私有财产权条款却无类似规定;其二,在体系上将财产权规定于总纲而非人民权利义务章。其实,对照近代中国宪法史,我们或可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一宪法体系与理念上的“特殊安排”。在近代中国制宪史与民权思想中,财产权几乎自始就不能与其他自由权及政治权利相提并论,将其规定在宪法不同章节似乎并无不可。对照1947年宪法的财产权条款——如果“较真”依据条文先后列举生存权、工作权、财产权的顺序,我们也可称1947年宪法第15条为“生存权条款”而非“财产权条款”——今天宪法将公、私财产权分条规定,并且在文字表述上“待遇不同”也属正常。(75) 注释: ①吴经熊:《新民法和民族主义》,《法律哲学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2-176页。 ②王伯琦:《社会本位法制与传统道德观念》,《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1、57页。 ③参见俞江: 《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8-252页。 ④程树德述、胡长清疏:《朝阳法科讲义》第2卷,苏亦工、何悦敏点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24页。 ⑤参见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09页。 ⑥参见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8-33页。 ⑦萨孟武:《中国宪法新论》,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118页。 ⑧法国《人权宣言》第2条:“一切政治上之结合,目的在维持人类之天赋不可让与的诸权利。此等权利,为自由、财产、生命之安全、及对于压制之抵抗”。第17条:“财产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权利,非因依法规定之公共需要,并给予以正当之事先决定之赔偿者,不得剥夺个人之所有权。” ⑨理查德·A.艾珀斯坦:《征收——私人财产和征用权》,李昊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序言”,第3页。 ⑩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18、226页。 (11)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0页。 (12)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册,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524-525页。 (13)参见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译本前言”,第2-3页。 (14)参见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493-494页。 (15)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册,第524-525页。 (16)参见布鲁斯·阿克曼:《建国之父的失败:杰斐逊、马歇尔与总统制民主的兴起》,江照信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0页。 (17)参见Vicki C.Jackson and Mark Tushnet,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New York:Foundation,2006,pp.1661-1662. (18)参见理查德·A.艾珀斯坦:《征收——私人财产和征用权》,“序言”第1页、第345页。 (19)参见黄东海、范忠信:《春秋铸刑书刑鼎究竟昭示了什么巨变》,《法学》2008年第2期。 (20)参见《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25-1230页。 (21)参见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5页。 (22)参见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10页。 (23)参见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第327-329页。 (24)戴炎辉:《中国法制史》,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6年,第304页。 (25)从数据上看,直至20世纪中叶,中国北方地区的族庙公产不超过全部耕地的1%,为纯粹私有化地区;长江流域如湖南、湖北,族产占全部耕地的15%左右;而在广东、浙江、江苏这些传统中国民间小共同体(宗族组织)最为活跃的省份,其全部耕地的30%—80%为公田,“与其说这三省许多地方的传统农民是‘小私有者’,不如说是宗族公社成员。”(参见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2-313页) (26)参见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王亚新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3-225页。 (27)参见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下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50-756页。 (28)参见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 (29)参见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156-157页。 (30)天坛宪草第12条:“中华民国人民之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但公益上必要之处分,依法律之所定。”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相关规定与之几乎完全一致。 (31)参见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于明等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214页。 (32)参见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第234-235页。 (33)参见章友江:《对宪法草案初稿关于“人民权利”规定之批评》,俞仲久编、吴经熊校:《宪法文选》,上海:上海法学院编译社,1936年;王揖唐:《宪法草案之商榷》,《大公报》,1934年4月10日。 (34)上述张知本与吴经熊的辩论,参见吴经熊、黄公觉:《中国制宪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23-127页。 (35)张知本:《宪法论》,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3年,第82-83页。 (36)张知本:《宪法论》,第219页。 (37)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范忠信校勘,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1、126页。 (38)参见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896页。 (39)参见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749-769页。 (40)参见杜强强:《民生与宪法:社会权规范在我国宪法史上的缘起——民国初年关于宪法“生计章”草案的论争》,谢立斌主编:《中德宪法论坛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24页。 (41)张君劢:《德国新共和宪法评》,《宪政之道》,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4页。 (42)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189-193页。 (43)参见薛化元:《民主宪政与民族主义的辩证发展:张君劢思想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3年,第38-39页。 (44)“政协宪草十二原则”第9项,参见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1092页。 (45)考虑到魏玛共和的崩溃与纳粹德国的兴起,以及二战期间中国与德国乃是敌对国,制宪者继续照搬德国宪法的条文需要一定的勇气与智慧。 (46)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条文参见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1116页;《魏玛宪法》条文参见立法院编译处:《各国宪法汇编》第2辑,南京:1933年自刊,第230页。 (47)政协宪草第16条参见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2004年,第1094页。 (48)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国民大会实录》,南京,1946年自刊,第432-433页。 (49)《魏玛宪法》第151条:“经济生活之组织,应以公平之原则及人类生存维持之目的相适应。在此范围内,个人之经济自由应予保障。”(参见立法院编译处:《各国宪法汇编》第2辑,第229页) (50)林纪东:《中华民国宪法逐条释义》(一),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221、235页。 (51)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47页。 (52)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53)参见Gregory S.Alexander,The Global Debate over Constitutional Property:Lessons for American Taking Jurisprudenc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pp.124-127. (54)孟普庆:《宪法上之土地问题》,俞仲久编、吴经熊校:《宪法文选》,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6年,第642-647页。 (55)参见Tom Allen,“The Right to Property,”in Tom Ginsburg and Rosalind Dixon,eds.,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Cheltenham and Northampt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1,pp.513-515. (56)参见沃尔特:《宪法上的财产权条款:在保障和限制间达致平衡》,林来梵、宋华琳译,《北大法律评论》第5卷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341页。 (57)G.S.Alecander:《财产权是基础性权利吗?——以德国为比较项》,郑磊译,谢立斌主编:《中德宪法论坛2014》,第384-385页。 (58)参见Gregory S.Alexander,Global Debate over Constitutional Property,pp.125-127. (59)参见Tom Allen,“The Right to Property,”in Tom Ginsburg and Rosalind Dixon,eds.,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p.507. (60)参见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50页。 (61)参见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450页。作为二十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论文,该书对凯恩斯及罗斯福时期副总统华莱士均有启发。 (62)参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11页。 (63)参见《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土地法》,上海:上海法学编译社,1931年。 (64)参见张群:《民国时期房租管制立法考略——从住宅权的角度》,《政法论坛》2008年第2期。 (65)1946年修正《土地法》又将时限由10年以上减为8年以上。 (66)参见胡长清:《我国宪法中关于土地事项应有之规定》,俞仲久编,吴经熊校:《宪法文选》,第627-634页。 (67)参见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第150页。 (68)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册,第527页。在美国,尽管房屋租赁管制并非普遍现象,但作为大都会的纽约却“特立独行”地实行租金管制,其地方性管制规范如《租金稳定法》、《承租人紧急保护法》还整合成为《租金稳定法典》(Rent Stabilization Code);面对租金管制合宪性的挑战,大法官霍姆斯曾回应说由于房租赁涉及重大社会利益,对其进行适当规制是正当的。(参见许德风:《住房租赁合同的社会控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69)参见来汉瑞:《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谢立斌、张小丹译,谢立斌主编:《中德宪法论坛2014》,第364-365页。 (70)《战时房屋租赁条例》条文参见《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631号,1943年12月15日。 (71)举例来说,关于房租管制1946年修正《土地法》进一步将最高上限由土地及其建筑物之估定价格年息的12%降至10%。(1946年修正《土地法》参见《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1046号,1946年4月29日) (72)《房屋租赁条例》条文参见《国民政府公报》,第2993号,1947年12月1日。 (73)俞江:《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第232页。 (74)参见Gregory S.Alexander,Global Debate over Constitutional Property,p.24. (75)本文的匿名评审专家也特别提醒笔者:与1947年宪法的财产权规定不同,我国现行宪法对财产权的规定方式反而更符合古典自由主义的理念,这在一定意义上也造成我国宪法财产权条款与社会主义条款之间的张力。消弭的方式似乎应为对两类条款分别做退让的解释,而非单方面强调财产权的社会性或者私权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