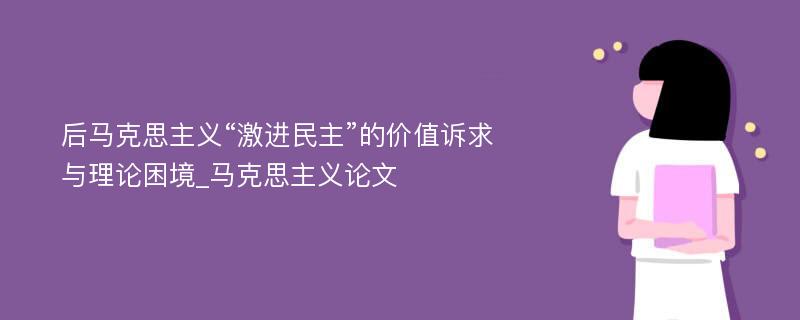
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的价值诉求与理论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困境论文,民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拉克劳、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著作,集中体现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诉求与策略选择。在拉克劳、墨菲那里,“民主”与“社会主义”相关联,并成为“激进的”。那么,其涵义究竟何在?实现这种价值诉求的“策略”是否可行?本文试对这些问题作一分析。
一、社会主义与民主革命
在拉克劳、墨菲那里,“社会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摒弃”(Laclau & Mouffe,p.192)。拉克劳曾表白:“我并没有拒绝马克思主义,不是这回事,是马克思主义自己解体了,我相信,我抓住不放的是它最好的碎片。”(转引自迪斯金,第279页)但在他们的著作中,难以看到他们是如何把社会主义这一维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加以维护的。
“社会主义”与“民主”是什么样的关系?在拉克劳、墨菲看来,两百年前,自由与平等的民主原则开始成为社会想象的新的母体,或者说成为政治建构的新的节点。这一转换也可以在托克维尔的意义上说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所针对的就是那种体现不平等的等级制,这种体制把个体固定于一个差异性的位置之中。法国大革命第一次把合法性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之上。由《人权宣言》所象征的与专制政体的断裂,提供了这样一个话语条件,有可能使不平等的各种形式成为“不合法”和“反自然”的,因而也使它们等同于压制形式。(Laclau & Mouffe,p.155)值得注意的是,拉克劳、墨菲把这种转变说成是一种政治的或社会的“想象”,隐去了作为这种转变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事实上,平等与自由正是“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敬”,而且这种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99页)正是这一“隐去”,使他们得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民主要求先于在经济上的民主要求的结论。
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在19世纪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诸如宪章运动等,成为民主话语把自由与平等扩展到更为广阔的领域的强劲推动力。通过不同的社会主义的话语,人们将对政治不平等的批判移向了对经济不平等的批判,这又导向了对其他服从形式的质疑和其他新权利的要求。因此,社会主义的要求可以被视为内在于民主革命之中。(Laclau & Mouffe,p.156)照他们的分析,“社会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摒弃,就是由对政治不平等的批判进入对经济不平等的批判,因此社会主义内在于民主的诉求之中。但他们其后又在《无需认错的后马克思主义》中说:“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接合完全不是自明的公理,而是一项政治工程;即是说,它是长期而复杂的霸权建构的结果,它总是受到威胁,因而需要不断地重新加以界定。”(拉克劳、墨菲,2007年a,第129页)说社会主义内在于民主,并不是宣称社会主义显而易见就是民主的。这一方面是出于他们对所谓的“斯大林专制主义”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需要工人对于“民主”的意识。
为了说明后一方面,他们分析了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对抗是围绕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这一点形成的,但是,只有当工人反抗资本家对其剩余价值的剥削时,劳资关系才会成为一种对抗关系;这种对抗关系并不能从工人作为“劳动力的出卖者”中逻辑地推导出来。因此,对抗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内在固有的,而是在生产关系与外在于这一关系的某些事物之间建立起来的,这些外在的事物如工人的工资过低,以致不能满足其体面的生活、孩子的教育以及娱乐的参与等等需要。因此,对抗的模式及其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人在生产关系外部被建构的方式。当今,工人的期望越来越同他们对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认识密切相关;而这种认识又取决于工人对不同领域的参与,取决于工人对他们自身权利的觉醒,这些都有待于民主的话语愈益深入到社会之中。(同上,第31页)故而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深化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其可能性取决于民主革命的扩展。”(同上)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拉克劳、墨菲那里,民主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专利。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斗争,需纳入更为广泛的民主斗争后,才能成为民主革命的环节。这也正是后马克思主义与他们所谓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差别之所在:阶级不再是历史进步的承担主体。这样,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就被移出了民主革命的中心。
那么,现实的政治斗争状况如何呢?按他们的分析,现实的政治斗争并不是围绕着特殊的“阶级利益”建构起来的。“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晚期变得越发突出而且将在随后10年里扩展并获得它自己的动力的诸种对抗,展现出了新的和独特的性质。这些新的政治主体:妇女、学生、年轻人,种族的、性的和地区性的少数派……不能仅仅定位于生产关系层次;除此之外,这些新的主体以根本不同的方式来界定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敌人不是由剥削的功能来界定,而是由某种权力的行使来界定。而且这一权力也不是从生产关系的一个地位获得,而是具有该社会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的结果。这一社会诚然是资本主义的,但这并不是它的唯一之特征;它也是性别歧视主义的和父权制的,更不必说是种族主义的了。”(同上,2007年b,第61页)按此说法,所谓“其中心定位于阶级斗争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话语”,已难以适应各种新的矛盾。
他们主张“从阶级的退却”,但又声称这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按他们的说法,“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之“后”的,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的。(Laclau & Mouffe,p.4)那么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是如何体现的呢?这表现在他们所提出的“霸权”观念上。
拉克劳、墨菲对苏联的共产主义模式失败以后的左派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放弃了自身的左派认同并宣称左派与右派的观念变得陈旧了,提出左派所需要的只是“激进中心”的政治。在他们看来,其结果就是“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对抗”消失了,一种“双赢”的政治现在成为可能。(ibid,pp.XIV-XV)但放弃对抗,只能使内在于社会民主之中的反资本主义因素被彻底根除。
“对抗”被他们看成是“我们当前研究的中心内容”。他们将“对抗”与“对立”和“矛盾”作了区分。“对立”被视为是现实事物之间的,其公式是A-B,而“矛盾”被视为是逻辑命题之间的,其公式是A-非A。“对抗”则既不是“对立”也不是“矛盾”,“对抗”与后两者的差别是重大的:在后两者之中,客体具有自身完全的同一。就“矛盾”来说,正是因为A是一个完全的A,因此非A就是一个矛盾,是一种不可能性;就“对立”来说,正是因为A是一个完全的A,因此它与B的关系不会产生在客观上可以确定的后果。但“对抗”却是另一种情形:“他者”的呈现使自我不能成为完全的自我。对抗关系不是源于两者完全的整体之中,而是源于两者构成的不可能性。对抗的双方并不是完全构成的,不是完全固化的,而是具有一种不稳定性。(Laclau & Mouffe,p.125)
但是,拉克劳、墨菲对“对抗”的如此阐释,也使对抗的双方成了游移不定的了。于是,“敌人”消失了,我们与之相争的只是“对手”:“‘他者’不再被看做是被消灭的敌人,而是被看做‘对手’(adversary)——我们得与他的观念作斗争,但是,他为他的观点辩护的权利将不再受到置疑。我们可以说,民主政治的目标就是把‘对抗’(antagonism)转化为‘竞争’(agonism)”(墨菲,第119页)。按这一推理,资本主义也成了一个竞争的“对手”,而不是要去“反”的对象。
二、话语理论:主体的重释
拉克劳、墨菲关于“对抗”的这一阐释,是与其所说的超越“社会(the social)”之“实证性”相关的,是要为对于各种对抗的霸权连接进行理论铺垫。他们对“society”和“the social”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所谓作为society的社会,其所有因素都是内在必然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社会”被他们称为是一种“缝合的空间(sutured space)”。他们拒斥这种社会,反对把社会视为必然联结起来的整体。(Laclau & Mouffe,pp.95-96)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论似乎为他们提供了理论支撑。这种观点宣称存在于社会(the social)中的一切皆被多元决定,实际上就是宣称社会缺少一种可使它们还原为内在规律之必然环节的终极的确定含义。但他们认为,阿尔都塞仍然残存着一种本质主义的因素,这表现在他力图使他的上述思想与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的观念一致起来。拉克劳、墨菲的批评是,如果肯定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必然的推论就是:如果“经济”对于每一社会类型都是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它就必定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社会类型;经济的存在条件也必定独立于任何其他具体的社会关系。这些“存在条件”的唯一的实在性,就是确保经济的存在及其决定作用的实在性。换言之,这些条件就成了经济自身的内在要素。(ibid,p.98)更为严重的是,阿尔都塞又肯定了他批判过的抽象客体:“经济”就是一种抽象普遍的客体,它产生了各种具体的后果;“存在条件”也作为一种抽象普遍的客体,它的各种形式却历史地变化着。因此,在阿尔都塞那里,“多元决定”就只是在有限领域中发挥作用。但是,“多元决定”所包含的两个潜在的重要思想:颠覆“最终决定”的观念和肯定“认同”或“同一”的脆弱性,显示了社会总体各个因素之间的必然联系的不可能性,以及“社会(society)”作为理性地联结起来的总体的不可能性。(ibid,p.99)这正是预示了与本质主义的决裂。
拉克劳、墨菲推进阿尔都塞的工作,找到了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的“话语理论”。他们在谈及对于社会的“建构”时,常用的一个词就是“construct”,而这个词不仅有“建构”之意,还有“构想”与“解释”之意;他们实际上暗示了社会理论与话语理论之间的关联。
他们把在诸因素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的实践称之为“连接(articulation)”,把由这种实践建构起来的总体称之为“话语(discourse)”,把在话语之中连接起来的不同位置称之为“环节(moments)”。(ibid,p.105)大部分后现代主义者把社会视为由语言、符号等组织起来的。这种观点也被归为“文本主义”,即把一切事物都还原为文本,还原为话语的结构形式。而福柯与此稍有不同,他肯定社会是由话语的因素与非话语的因素共同构成的。故而福柯对于话语的分析最终还是着力于对各种机制、实践的分析,揭示其中的权力运作。拉克劳、墨菲则拒绝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区分,并由此批评福柯思想中的不连贯性。(Laclau & Mouffe,p.107)他们特别作了一些说明,其中一个重要的说明是认为,每个客体都被建构为话语的客体,但这并不关涉思想之外是否存在一个世界的问题。例如,地震就是确然存在的一个事件,它此时此地发生了,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但是,这一客体的特性是按“自然现象”还是按“上帝之咒”来解释,则依赖于对话语领域的建构。(ibid,p.108)拉克劳、墨菲的这一说明是值得推敲的。人们对于一个事件的解释或认识虽然总是通过话语层面呈现出来的,但如何解释和认识无疑有其深层的原因,这个深层的原因就是客观的现实社会生活。所以,话语与非话语的区分是不宜抹杀的。他们曾辩护说:“在我们与世界的交换过程中,对象从来没有向我们呈现为纯粹存在的实体,它们总是在话语接合中向我们呈现它的存在”(拉克劳、墨菲,2007年a,第108页)。亦即他们承认“客观对象”,但却认为它是包裹在话语之中的,是难以穿透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只是停留于话语的表层,而没有超出话语的层面去分析经济结构、政治实践等非话语的因素。“多元决定”似乎还能让人们看到作为其中一元的现实的影子,“话语理论”却将现实的因素全部消融于“话语”之中了。正如伍德在批评“后马克思主义”时所说的:“现在,话语建构已经取代物质生产成为社会生活建设性的实践。这样一来,社会可能永远不会有革命的重建,却总有对文本的无情解构”(伍德,第10页)。
拉克劳、墨菲颠覆了本质主义,把“话语”背后的根基掏空,于是使连接实践成为可能的“无主之地”浮现了出来:“同一”与“关系”都失去了必然特性,“社会”不再成为“已完成的”或“被缝合的”,一切固定的都烟消云散了。但是,他们又强调这种固定的不可能性还暗含部分的固定:为了颠覆意义,至少还必须存在着某一意义。如果社会(the social)并不设法把自身固定在社会(society)的缝合或理智的形式之中,它就仅是作为一种建构不可能的对象的努力而存在。任何话语都试图去捕捉差异之流并建构中心之点。这一具有特定优势的局部固定的话语之点被称为节点(nodal points)。连接实践就在于对于局部地固定意义的节点的建构。(Laclau & Mouffe,p.112)
可以说,任何社会实践都是连接性的。但这种连接是在话语领域中的,而不是由某一先验的主体或固有的主体来担保的。拉克劳、墨菲还是沿袭福柯的看法,把“主体”只是当成话语结构之中的“主体立场”。他们认为,强调主体位置的差异即“主体立场的弥散”,并不能等同于主体立场之间的分隔。这种分隔只能是在本质主义的概念柜架之中先验地建立起来的。正是主体立场之间的多元决定,使得主体立场之间有了弥散,也才有了主体立场之间的连接的可能。(ibid,p.115)他们以“人”为例进行了说明。按他们的分析,“人”并不具有一种本质的属性,“人”实际上只是话语建构的一个主体位置。重要的是要说明“人”作为一个没有差别的在人性上同一的承担者,在近代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它如何出现在某些宗教话语之中,如何体现在司法实践之中,以及如何在其他领域之中得到多种多样的建构。而这正是多元决定的结果。(ibid,p.116)因此,拒绝把“人”视为具有某种天赋的本质的实体,就可以去分析它得以出现的历史条件以及它在目前所具有的脆弱性的缘由。于是“人”也成了一个重要的“节点”:从18世纪以来,人们正是由之开始了对大量的社会关系进行“人性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处于“民主革命”的进程之中的。(ibid,p.117)
拉克劳、墨菲在这里的分析,似乎又要超出话语本身而走向对福柯意义上的“非话语因素”的分析。但是,他们放弃对整体性、必然性的分析,热衷于对偶然性、破碎性的分析,实际上是放弃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因为,“如果要屈从于资本主义不可抗拒的强力,除了宣称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势力没有系统性的起源,没有统一的逻辑,没有可确认的社会根基,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借口吗?”(伍德,第2-3页)
三、霸权连接:激进民主之路
霸权正是在这种连接实践的领域之中浮现出来了:任何霸权都是以社会的未完成和开放性为前提的。拉克劳、墨菲接下来的分析是,既然有了连接,就有了一个谁是连接主体的问题。他们认为,从列宁到葛兰西的第三国际给出的答案是:霸权力量的最终核心包含着一个基本阶级。这样的霸权关系实际上是把领导者与被领导之间的差别视为不同本论论层面上的差别,于是这两者就成为完全构筑起来的差别系统,成为被缝合起来的实体。这一点是他们反复申说的,他们强调霸权连接实践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对抗力量的呈现及其划分边界的不稳定性。就前一点来说,如果仅有连接的要素而没有对抗,就不可能有霸权:连接实践是在与其他与之对抗的连接实践的对峙中产生的。就后一点来说,并非每一对抗都预设了霸权实践:如果没有可以连接的流动的要素,如果对抗双方从一开始就是划定好了的,就不存在连接实践。(Laclau & Mouffe,p.136)
在他们看来,霸权并不是预先决定的,而是需要努力建构。这就意味着:新的斗争并不必然具有进步的特征,因此,认为这些斗争自动地在左翼政治的语境中占据一席之地是错误的。无论是工人的还是其他政治主体的斗争,就其自身来说,都只具有部分的特性,并可以被连接到极为不同的话语之中。正是这一连接而非这些斗争由之而来的处境,赋予了这些斗争以特性。(ibid,pp.168-169)
各种反抗完全可以被连接到反民主的话语之中。近年来的“新右派”即是一例。它被成功地连接到了一系列对社会关系变革进行民主抵抗的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之中。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新右派”质疑这样一种连接:这种连接把民主自由主义用来论证在反对不平等斗争中国家干预的合法性,以及福利国家设置的合法性。(ibid,p.171)
在哈耶克等人的整个新自由主义批评中,存在争议的问题就是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的连接。自由主义的“民主化”是多样斗争的结果,也必将对自由(liberty)观念之如何被构想产生深刻的影响。“自由”最初在洛克那里是指“免于他人的限制与暴力”。其后,政治自由与民主参与被作为重要因素注入“自由”之中。近年来,在社会的-民主的话语中,自由意味着作出某种抉择和享有选择的能力。因此,正是贫困、教育的缺乏、生活条件的巨大不平等,在今天被视为对于自由的最大威胁。新自由主义要质疑的正是这种自由观念的转变。新保守主义则是从另一方面来颠覆自由主义与民主的连接。他们力图重新界定民主的观念,限制民主的应用领域,把政治参与限定在一个更为狭窄的领域。布热津斯基提出:要不断地把政治系统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并把两者看成是独立的实体。其目标是把公共决策从政治控制中分离出来,使这些公共决策成为专家的职责。在他看来,这样的社会“在自由主义意义上”就是民主的。(ibid,p.173)拉克劳、墨菲则认为,虽然民主的理想并没有受到攻击,但是民主的实质却被抽空了,并通过对民主进行新的界定,使政治参与不再可能的体制合法化了。(ibid)
拉克劳、墨菲坚持以自由与平等为核心的民主原则,对种种反民主的攻势深感忧虑,明确指出低估重新界定“自由”、“平等”、“正义”、“民主”等观念的重要性是错误的。左派的传统理论只对与经济基础或在其中建立起来的主体相关的狭窄领域感兴趣,而将文化的广阔领域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对于现实的重新界定,将对各种话语形态的重新的霸权连接的整个努力,拱手让给了右派。(ibid,p.174)左派的任务并不是拒斥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而是相反,是要在激进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进一步加深和扩展它。而自由主义关于个人权利的话语并不是固定的,它既可以与保守主义话语中的因素连接起来,又可以与民主的因素连接起来。(ibid,p.176)
在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合流、形成对民主的强大攻势之际,“新左派”面临何种选择?拉克劳、墨菲的回答是:激进民主。这就是要承认社会的一切价值都具有偶然性和开放性,放弃对于单一基础的渴望。(拉克劳、墨菲,2007年a,第130页)
对于单一的、统一的主体的放弃,必然导向主体的多元化,这正是激进民主的核心所在。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诸如普选权、多党制、公民权等,必须加以维护。但是,自由主义的理念需要超越,并且“超越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念是不够的,这种观念限于通过单单增加各种形式的基层民主而参与议会,通过基层民主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人将参与工厂的管理。承认在这些传统主体之外其他的社会主体及其政治特性的存在是重要的:妇女和各种少数派团体也有平等自决的权利。接受多元主义(远远不限于政党多元主义)必须也包括主体多元主义。”(同上,2007年b,第64页)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政治空间的多元性是否与把具有相同价值诉求的要求联系到一起的“同类逻辑”的统一性相矛盾?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自主与霸权之间的关系问题。
拉克劳、墨菲分析了同类逻辑与自主逻辑的关系。从同类逻辑来看,对一些特定的民主斗争的强化,要求把同类的链条扩展到其他的斗争。例如,在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之间的同类连接,就需要一种霸权的建构,这种建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成为巩固其中任何一种斗争的条件。同类逻辑达到极致,就暗含着对自主逻辑的消解,但这并不必然的是因为把任何一种斗争屈从于其他的斗争,而是因为把这些斗争都变成了某种独一无二的和不可分割的斗争的同类符号。(Laclau & Mouffe,p.182)从自主逻辑来看,每一斗争都有相对于其他斗争的不同特性。这些斗争在其中得以建构的政治空间是完全不同的,并且不能与其他空间进行沟通。而如果每一斗争都把其自身的独特因素变为绝对的同一原则,这些斗争系列就会被构想为绝对的差异体系,这个体系只能被设想为封闭的体系。(ibid)拉克劳、墨菲认为,如果把同类逻辑绝对化,否认自主逻辑,最终会导致极权主义;而如果把自主逻辑绝对化,否认同类逻辑,最终会失去在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建立起共同意义的连接的可能。因此,民主的经验应包括对于社会逻辑的多样性以及彼此连接的必要性的认可。但这种连接应是不断地重新创造和重新协商的,并不存在一个最终的点可以达到一种确定的平衡。(ibid,p.188)
由此,拉克劳、墨菲转入了民主逻辑与霸权规划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民主逻辑对于霸权规划的表达来说并不是充分的。因为民主逻辑只是将平等主义的想象深入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领域。民主逻辑只是一个对于屈从与不平等关系的消除逻辑,它显然是一种颠覆性的逻辑,而不是社会的实证性的逻辑,不能为社会网络的建构提供一个节点。因此,它还必须要与一种实证性的逻辑相结合。这种实证性逻辑就是要建构新的秩序。霸权的情境将会是这样:社会实证性的安排与各种民主的需求的连接达到一个最高程度的综合。(ibid,p.188-189)
从这里,他们又回到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其回答是:两者的关系是一个长期霸权建构的结果。为何如此?因为:“每一激进民主的规划,正如我们所说,包含着社会主义之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摒除;但是,它拒绝这样的观念:从这一摒除必然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种种不平等的消除”。(ibid,p.192)可以说,民主的规划包含着社会主义的维度,但相反则不是。因此,民主的实现并不是某一个特权阶级的事业,而是需要承认各种反抗自身的特性,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对各种反抗进行霸权连接。因此可以说,“霸权”概念是被当作“恢复社会主义主动性的尝试而提出”的。(拉克劳,第316页)
但是,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颠覆了“本质主义”之后,难以说清其“霸权”会把人们引向何方。他们曾抽象地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优点在于它阐释了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基本趋势及其所引起的反抗”,但却话锋一转又说:“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里的分析并不完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分析是褊狭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局限于19世纪欧洲的经验”(拉克劳、墨菲,2007年a,第134页)。事实上,他们抽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虽然他们仍然坚持作为民主原则之核心的自由与平等这一价值诉求,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而随着对“本质主义”的颠覆,马克思主义理论仅有的“阐释了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基本趋势及其所引起的反抗”这一“优点”也不再有了。虽然他们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宣称,不同话语与斗争的“去中心”与“自主性”,多种对抗的增加和多元空间的建构,构成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想之不同成分可能得以达成的先决条件(Laclau & Mouffe,p.192),但最终我们还是一头雾水,因为我们不清楚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被保留了。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自由资本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政治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