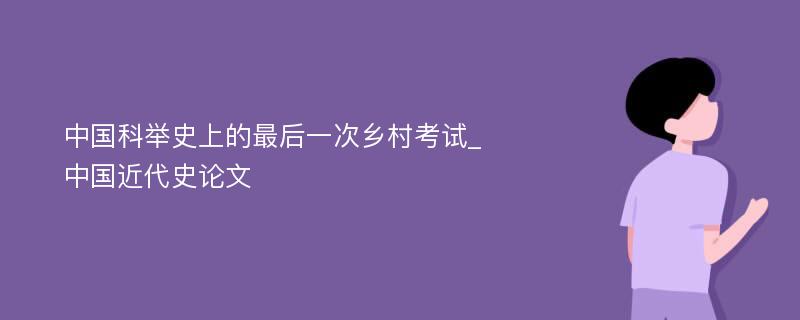
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试论文,科举论文,史上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3)05-0021-06
整整100年前,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光绪二十九年(1903)是癸卯年,在中国科举史上是很特殊的一年。按科举成式是三年一个周期,乡试之年是没有会试和殿试的,但该年不仅在三月举行了“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五月举行殿试,而且在六月举行了经济特科考试。八月(1903年9月底至10月初),各省又举行恩科乡试,而当时一般人都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为1300年中国科举史上的末科乡试。
乡试是中国科举史上各层级考试中最迟出现的一级考试,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级考试,而且还是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一级考试。中国科举制虽然到1905年才正式被废止,但乡试和会试是三年举行一次,1905年不是“大比之年”,此前一年即1904年举行的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会试就成为最后一科会试,而1903年举行的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乡试则成为最后一科乡试。如此算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科乡试至今正好一百年。在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探讨历史上乡试的形成及其影响,回顾末科乡试的历程及相关科举革废的动议,对我们反思科举制的功过和废科举的影响,都具有特别的意义。中国学术界即将于2005年迎来“科举制百年祭”的重要时刻,对中国科举制的尾声之一——1903年末科乡试作一世纪回顾,便是意在揭开废科举百年祭的序幕。
一、乡试的形成与影响
乡试的本意是地方一级的举送考试。唐代科举考生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央和地方官学的“生员”,一是由府州考试选拔自学成才的举子,称为“乡贡”。唐代各地举子要获得参加中央省试的资格,通常需经过县、府(州)两级地方的考试。府州一级的选拔考试称为“解试”,意为解送举人入京的考试。不过,唐五代获得府州解送资格的举人并没有其他特权或待遇。从宋代以后,解试合格的举人尤其是曾多次被举送参加省试的举人,逐渐获得一定的身份地位,例如可以补充担任地方的摄官、可以为参加解试的其他举子担保、可以免服丁役等。[1](p297-313)金朝科举分为乡试、府试、会试、御试四级,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因考虑到“举人四试而乡试似为虚设”,将乡试罢去。[2](P1136)当时是以县试为乡试,洪皓《松漠纪闻续》说:“金人科举,先于诸州分县赴试,号乡试。”乡试之名始于金朝,不过,我们通常所说的省一级的乡试则是始于元代。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在中断科举多年之后,终于重建科举考试制度。当时科举分为乡试、会试、御试三级。元代已开始设立省一级的行政区划,其乡试虽也是地方性的选拔考试,但已是省一级的考试,而没有府州一级的考试。元代乡试按11行省、2处宣慰司、4处直隶省部路共17处举行。元代乡试三场的日期和考试内容,据《元史·选举志》载为:“乡试,八月二十日,蒙古、色目人,试经问五条;汉人、南人,明经经疑二问,经义一道。二十三日,蒙古、色目人,试策一道;汉人、南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二十六日,汉人、南人,试策一道。”[3](P2020)
明清时期科举大体分为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其中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乡试又称为乡闱,在南、北直隶(南京和北京)及各省省会贡院举行,据明代张弘道、张凝道《皇明三元考》和张朝瑞《皇明贡举考》所载,明初洪武三年(1370)、四年各设12个,洪武五年设13个乡试贡院,从洪武十七年(1384)开始,明代多数时间乡试设有14个贡院,至嘉靖十六年(1537)云南和贵州分闱,此后到明末各科都有15个闱场。据法式善《清秘述闻》、王家相等《清秘述闻续》、徐沅等《清秘述闻再续》所录,清代乡试闱场也是从少到多,顺治二年(1645)乡试仅有6个场所,到顺治十七年(1660)后设15个乡试贡院;雍正二年(1724)湖广分闱,湖南与湖北分设贡院,光绪元年(1875)甘肃从陕西分闱之后,全国共有17个乡试闱场。乡试每三年一次,通常在子、卯、午、酉年,考试的时间是在农历八月初九、十二和十五日三天,又称为秋闱、秋试、秋榜、桂榜,也叫“大比”。清代还在皇帝登基、大寿等喜庆的年份特别举行乡试,称为乡试恩科。乡试是由皇帝任命的正、副主考官主持,凡是本省各府州县的生员、监生、贡生等,经科试合格都可以参加考试。考试中选者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从明初开始,除了继续参加会试以外,举人也有入仕的资格,已成为具有特定身份地位的一种出身。明代举人阶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4]但总体而言,明清时期举人在社会上地位相当高,获得举人科名是令人羡慕的快事。为了实现中举的梦想,不知有多少士人上演过一出出人生悲喜剧。乡试对广大与考的秀才个人是一件大事,对地方来说则是各省人文教育活动的重大事件,对明清两代区域政治、文化、教育、民风等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一)乡试是科举系统中影响最大的一级考试。明清时期所说的“科举”最经常是指乡试,特指的“科举”便是参加乡试的科举生员。乡试虽然分省考试,但统一时间,统一步调,统一考试大纲(尽管考题不一),实际上是一种全国统一组织的考试。为了在同一时间开考,边远省份的主考官往往须提前2个月从京城动身前往该省贡院。大比之年的八月前后,各个举行乡试的省会城市都以乡试为中心话题。同治三年(1864),有位西方人曾详细地描述了当年广东乡试激动人心的情形,谈到省城广州在乡试到来之际,“无论是在富人华丽的邸宅中,或是在穷人肮脏的陋室中,没有其他事物被人们思考和谈论。在每个商店,在每个货栈,在街头的贫民中,在公共场所的人群中,使说话者和听众罕见地兴高采烈的,只有一个完全吸引人的话题。每个人都知道某人在将要进入贡院的名单中,不同举子的名字在那些熟悉他们各人特长的人们中被议论着。每个演说者都有一个关于他看到或听到的人的故事,谁通过贡院的关口获得了运气和声望,通过他们自身名望的显赫,在所有他们的宗族中提高了地位。繁忙的城市被一种更热闹的生活搅动了。”[5]由于清代广东盛行猜测中举者姓氏的“闱姓”赌榜风俗,广东人尤其热中于谈论乡试话题,但其他各省社会上对乡试的关注程度也差不了多少。以乡试为代表的科举制对各地教育、民风、习俗乃至社会心理等许多方面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二)乡试是科举系统中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级考试。明末顾公燮曾说:“乡试难而会试易。乡试定额,科举三十名中一人,不过二三千人入场,其得于宾兴者,殁后且著之行述以为荣。至于会试,进士有三百余人,其途宽矣。故俗有‘金举人银进士’之谣。”[6](P68)明代乡试通常的竞争比例是30:1,即1个举人名额允许30名考生入场。而清代中期以后则竞争更为激烈,录取比例从50:1到80:1不等,甚至有过100:1的录取率。[7](P347-348)成功的机会如此之小,中举之后的命运改变又非常巨大,难怪会出现像范进中举那样喜极而疯的人。据一位西方人观察,“在科举考试制度三大阶段中,据说中间阶段的乡试是最受关注的,各地数千名秀才聚集省会,对那些中举者也给予相当高的荣誉。”[8]乡试的竞争激烈到几近残酷的地步,以至于不少人挖空心思企图靠作弊取胜。清代的科场案多数便发生在乡试层次。获得了举人科名便意味着成为中高级绅士,在社会上享有相当高的声望。因此有一些举人终身没有再去参加更高层次的会试和殿试。
(三)乡试与区域政治文化密切相关。明清两代各省都力图增加举人录取名额,而举人定额是根据各地人口多寡和文风高下分配的。例如,明代江西、浙江、福建、湖广(今湖南、湖北)被称为科举“四大省”。[9](P371)乡试录取的举人虽有定额,但省内务府县之间并无举额分配制度,完全是自由竞争,这有如现代高考分省区定额划线录取,但省内地区间并未限定上线指标。这样,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便成为全省各府县秀才的教育水平和知识智力的大竞赛,备受全省士人的瞩目。各朝代都出现了科名的地区性结聚现象,中举人数的多少颇不平衡,最初科举较为成功的地区在先辈的示范激励之下,愈发热中于读书应举,而科名衰少的地区缺少帮助提携,往往容易失去信心,出现中举人数分化的马太效应。[10](P151)不过,无论中举人数多么悬殊,各县在一个长时期内多少都会考中一些举人。乡试所取举人是可供作科举人才地理分布的最丰富的对象,尤其是进行特定时期同一省内各地区之间的科名分布比较时,进士的样本偏少,而明清举人的数量则相当大。各地方志对明清举人的记载相当详尽,现存科举录也以乡试录为多。而各地中举者或入仕为官,或居于乡间,对朝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等方方面面都具有广泛的影响。
总之,科举是隋唐以后历代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乡试则是明清500余年间各省最令人关注的活动之一。乡试的重要性和稳定性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出现明显的变化。
二、末科乡试与科举制的终结
在庚子事变之后的1900年11月,被《万国公报》主编林乐知称为西方人中“寓华最久知华最深”的“美国通儒”丁韪良曾说:“今为十九周之末年,明岁即二十周之元年。天意欲辟东方大新之局面。”[11]身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一些通古今之变的人士感到中国社会将发生大的变化,而科举制的衰废则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重要标志。
自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各省举行丁酉科乡试、二十四年(1898)举行戊戌科会试之后,科举制已成强弩之末,显露出衰废的迹象。戊戌变法时废八股文的努力虽然被否定,但实际上废八股文的动议并不完全是以失败而告终。由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科乡试因义和团事件未能如期举行;次年辛丑(1901)补行庚子恩科乡试,也仅有甘肃、广东、广西、云南、贵州5省举行,顺天、江南等另外12直省则于1902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而此前清廷已于1901年下令改革考试内容,废止八股文体,规定从次年开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因此实际上戊戌变法中废八股的政策还是得到了实施。
1903年是科举考试特别繁忙的一年。该年是癸卯年,却在三月于河南开封“补行”了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五月举行殿试录取了315名进士。闰五月还举行了从戊戌变法以来便多次酝酿的经济特科考试及复试。从考试方式来看,这也是一次空前绝后的特科考试。当年八月又举行恩科乡试。一般情况下,会试之年不会有乡试,但该年的科举考试却接二连三。该科乡试与1902年的乡试一样,还有一特别之处是顺天乡试借闱河南。
末科乡试是在科举制摇摇欲坠的氛围中举行的。在此之前,有关科举革废的议论蜂起,对科举制的批判日盛一日。当时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欲废科举的传闻此起彼伏。《大公报》1903年1月6日第203号载:“近日官场传说明年确有永停科举之意,然因皇太后七旬万寿在迩,拟甲辰年后永远停止。闻此议创自王夔石中堂,云科举不废,虽有学堂,无成效也。”但是,清代科举为一百多万读书人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一旦这种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遭到颠覆,必将使这些人陷入困惑、彷徨和幻灭之中。《大公报》同年6月7日第344号“时事要闻”栏载:探闻张之洞近日与政务处诸公商议科举革废之事,“兹悉其确实情形”。说张之洞被慈禧太后召见,在回答关于停废科举问题时奏云:“现在改试策论,虽较八股为有用,然亦究属空言。譬如臣系以八股得功名者,今日若进场考试,亦非不可以作策论,若问臣以声光电化诸学,则臣一无所知。可见取士非由学校不可。但科举不停,则学堂仍不能大兴。”慈禧太后说:“若废科举,又恐失士子之心,如之何?”张之洞便说,废科举所不便者主要是三四十岁之老生员,其年富力强者皆可以入学堂。且学堂大开,此三四十岁之老生员多可为小学堂之教习,又为之宽筹出路,并非科举一停即无事可作。况请停科举并非当下即行罢废,而是待三科以后逐渐减尽,“故失士心一层,亦万不足虑。”慈禧太后于是才下定决心准备停废科举。随后几天,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演说时,张之洞又声称:“科举必废,科举废则学堂大有人才也。”[12]
面对张之洞和袁世凯废科举的主张,也有“某侍御递有封奏,力陈科举不可废”,并说张、袁两人为今日之人才,何尝不出自科举。只是奏折“留中未报”,慈禧太后没有看到。1903年6月,举行了选派该科乡试考官的试差考试,当时有数人在试卷中“畅言学堂不可恃,科举不可废”,结果皆被取在前列。[13]《大公报》同年6月28日第365号“时事要闻”栏又载:“探闻张香帅近日会议罢废科举一节,阻力太多,势难勉强。刻经彼此商定,拟请嗣后乡会两场,于策论之外,添考专门。凡与考者,令其自行报明。非肄业专门,不得取中。庶于科举之中,仍寓学堂之制。闻政务处诸公皆已画诺云。”
不过,1903年有关科举存废的传闻虽然很多,但传闻归传闻,毕竟按该年二月袁世凯、张之洞奏准的预定计划,废科举是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渐进过程,准备在此后三科递减录取人数,得十年之后(1911年)才会完全停废科举。许多人也还为科举改革出谋划策而不是考虑完全停罢科举,如该年五月御史徐士佳便奏请乡会试增设兼通洋文中额以造就外语人才,[14]还有一些人声言科举不可废,认为“科举者,当变而不当废”。[15]因此当时几乎没有人会预料到该年秋季举行的乡试竟成中国科举乡试的绝响。
该年八月九日至十五日(1903年9月29日—10月5日),各省贡院按章同步举行乡试。末科乡试的考试内容已脱离了八股取士的格局,改为讲求经世致用。1903年2月,图书集成局在发售《二十四史》的广告中便说:“自科举改章以后,大小考试,皆以史事命题,博求通达之才,借收宏济之效。若非贯通全史本本原原,断不足以应俊乂之旁求,挽艰危之时局。”[16]据徐沅等《清秘述闻再续》卷1所载,该科17省(包括顺天)乡试题目都是以史论为题。例如,顺天乡试便以“汉初弛商贾之律论”、“隋唐二史不为王通立传论”等五道史论题发问。而当年江南乡试的考题不仅不再用八股文体而改策论,甚至采用新学问题发问。英文刊物《东亚杂志》1903年第2卷中刊载一篇题为《中国的三年大比》的文章,谈到该科江南乡试的具体情况,并提到具有相当代表性的西式题目:“1.编书、出版报纸、杂志时,文章应平和、真实。如果文章攻击政府政策,就是在阻碍国家和平,那么就是在煽动反叛。请提出一条法律建议以阻止这一状况发生,稳定民众思想,以建立国家秩序。2.邮政服务正在极大扩展。有多少邮路,就要多少官员吗?是否应该扩展和改进管理来保证邮政活力?”[19]这应该是江南乡试第二场或第三场的题目。
与过去一样,乡试是广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大事,中举名单是非常重要的新闻。该科发榜之后,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通过电报迅速获得各省乡试之题名录,并刊载出来。如1903年11月1日《大公报》便刊出《癸卯科顺天借汴乡试题名录》241名举人和29名副榜举人的姓名和籍贯,并特意注明“电码难免错误,阅者谅之”。该科的举人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批举人。
乡试结束后,有关废科举的议论再度兴起。《大公报》1903年10月20日第479号“时事要闻”栏目载:“闻近日张香帅又提倡废科举之说,两宫及庆邸皆以为然,惟某相力阻之。”随后两年,情况急转直下,科举制未按原先预定的计划再实行三科,而于1905年被最终废止。这标志着一个漫长时代的终结,也预示着清朝帝制的覆亡。
末科乡试表现出来的科举妨碍学堂的现象是直接导致提前废止科举的原因之一。在1903年的时候,尽管京师大学堂已开办有年,且已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但科举的吸引力还是比新式学堂更大。末科乡试前夕,“大学堂两馆生均已纷纷赴汴乡试,两馆所存学生不过三十余人,每日功课亦不认真,徒存大学堂外观而已。设诸公乡试得意,似较学堂出身为优,想诸公必不肯再入堂肄业,以待三年卒业也。科举误人,岂浅鲜哉?”[18]结果,京师大学堂仕学、师范两馆赴开封参加顺天乡试的学生中果真有7人中举,这还不包括改用他名无法查实及返回本省参加乡试中举者。据1903年底王仪通为《京师大学堂同学录》所作序文中说,该年大学堂学生醉心于举业科名,“至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者盖十之八九焉。暑假后人数寥落如晨星,迨九月中,各省次第放榜,获隽者利速化,视讲舍如蘧庐,其失意者则气甚馁,多无志于学,胶胶扰扰者先后殆九十,阅月而一星终矣。竭管学大臣、中外教习、管理诸员之心思才力,一岁之春秋两试堕之于无形,顾谓学堂与科举能两存焉?”[19](P1-3)当时关于科举与学堂的优劣、科举与学堂能否并存有许多争论,但1903年春天的会试尤其是秋天乡试,让人看出科举对学堂学生的吸引力大到足以阻碍学堂的发展,这就促使张之洞等人更积极地推动废科举的进程。
从1903年末科乡试来看,20世纪初科举制已进行了旷古未有的改革。尽管从科举考试的内容到形式都试图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但仍然无法逃避灭亡的命运。由于长期以来科举竞争过于激烈而导致科场弊端丛生,且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意识十分强烈,主政大臣以为通过新式学堂培养人才是振兴中国的不二法门,而在当时科举与学堂难以协调发展的情况下,最终导致了废科举兴学堂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