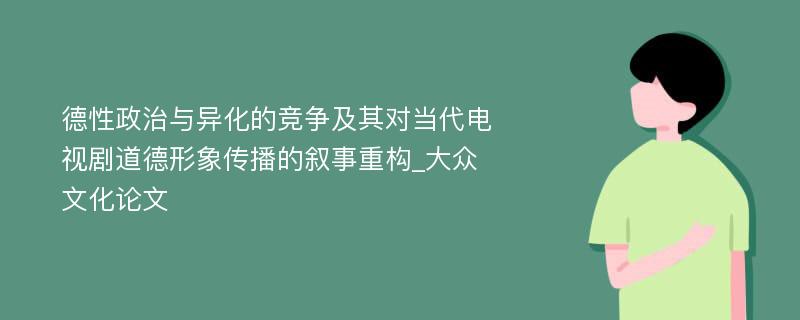
德性政治、异化的竞争及其叙事重建——论当前电视剧中的道德形象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性论文,剧中论文,道德论文,形象论文,竞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电视剧中的道德形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标志着现实社会的道德状态以及理想价值的时代要求,意味着传统道德借助现代媒介在当下的重建。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社会中,道德、私人生活领域与政治、公共生活领域叠合,形成了以政治价值为最高理想,伦理道德为现实途径,并制度化为一套重义轻利的行为规范。这种泛道德—政治的观念影响深远,最典型的莫过于将英雄人物等同于道德形象。在古典文本中,“仁”作为儒家文化具有较强思辨力与说服力的理论话语,把行动能力与思想能力突出的英雄强行纳入道德轨道中。
目前,历史话语、社会境遇、观众心理、知识背景等均发生了根本变化。裹挟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西方文化引起新一轮“殖民化”扩张,却反向刺激起文化多元化的浪潮,国际范围内的文化竞争进一步加剧。电视剧借助现代电子媒介,在想象、形塑、阐释当前社会生活,积极实践、输出民族文化观以及有效建构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毋庸讳言,我国电视剧的制作与传播缺乏全球意识与文化竞争意识,大多限定在国内观众(在境外传播的历史剧也局限于海外华人社区),而电视剧中的道德观念及人物陷入尴尬境地:要么以大众流行的世俗观念简单迎合观众,要么在封闭的历史时空中无关痛痒地图解传统道德。这导致了名著改编剧中的道德形象缺乏真实感,如唐僧、刘备、宋江等形象失去应有的性格魅力,丧失必要的英雄气质,甚至给人以委顿之感。在消费文化思潮中,面对现代观众对道德形象怀疑、挑剔的目光,电视剧制作者们缺乏思辨能力,难以令人信服地重建传统道德观念,只能自欺地将之放逐、停留在虚构的传统空间(尽管这一空间在当下已经不复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电视剧承续传统文化与对外传播力。
一、道德—政治的重合与分离:影视形象的现代性嬗变
旅美文化学者徐贲把借助电子媒介传播的群众文化(mass culture)与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作了区分,目的在于厘清曾经作为大众文化的民间文化(folk culture)①。由于传播媒介的差异,已然经典化的民间文化、文本在当下文化传播的异态中折射出“大众文化”观念的根本变化,突出表现在古典名著改编剧的道德形象上。道德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德’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它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建构,文化形象的塑造,都起到基础和骨架的作用”。②如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刘备,与众多的历史演义的原型人物一样,在传统文人整理润色过程中,引进了自周以来的“敬德”思想,以承载国家纲常的道德理性功能替换了历史原型丰富复杂的人性张力。“在《三国》叙事中,遵循的是儒家的政治理路,一直想以道德的力量来提升政治行为,使政治变为德化的政治”。③可以说,这种泛道德倾向与编码逻辑贯穿在古典小说从通俗走向经典的整个历程。如宋江(一个历史中的“勇悍狂侠”的绿林豪杰)与玄奘(一个大智大勇、只身西去的修道高僧)都在传统文化持久的诠释中,演变成指称道德的单一文化编码。而伴随文化符码的完成,民间文本也就上升为经典文本。可以说,以“仁爱”为最高理想的道德伦理,既象喻了实现政治目标的人生途径,又成为塑造人物的艺术标准。这一叙事策略使“俗化”的文本“雅化”,把民间底层的流行空间,提升到国家政治文化塑造的经典行列,完成了特定的政治意识、国家想象的塑形,如上述古典名著的人物形象虽被灌注的是仁义等道德情感,却指向了政治理想这一最高旨归。这正是徐复观所说的“仁”既成已(自觉地追求人格与知识完善)又成物(对他人有应尽的无限责任)的精神状态。④
与之不同的是,古典名著改编剧面临的则是另一种挑战。如果说,改造民间文本是“文人化”、主流政治化的过程,那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剧的改编,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将已然文人化的古典名著再次“世俗化”。在2010年热播的《三国》(突出演绎压制、反压制的权力欲望)以及仍处制作阶段的李少红版《红楼梦》(强调青春偶像型演员)、张纪中版《西游记》(影视特技打造视觉奇效)中,消费文化、世俗化与传统文化、经典化的抵牾更加突出。这种“通俗化”不是指重新回归传统社会中的民间文化,而是一种借助现代媒介强化消费的大众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媒介传播的经典故事与传播媒介的现代属性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传统文化强力黏合的道德与政治,在现代媒介建构的社会公共领域中彻底分裂开来,这是现代政治结构性调整的必然结果。如万俊人认为:“现代政治生活结构的公共化转型,使传统的‘德’‘法’一体的政治哲学不再具有哲学的理论解释力和知识合法性。”⑤换言之,古典小说能以“道德、政治—体化”为基点建构起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与价值理想,但当电视剧借用古典名著中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时,由于传统道德在当下接受语境的失效,难以唤起现代观众的道德共鸣,顺畅地通往代指人生理想的政治权力,也就不可能支撑起电视剧的人物形象与人生价值。因此,电视剧的改编必须重新寻找构建人物形象的道德基点。
然而我们看到,以上的名著改编电视剧并没有触及这一关键处。在“忠实经典”的制约下,人物形象、政治理想的表达仍然牢固地局限在传统道德的层面(《三国》虽然增强了刘备的个人能力,但仍然突出仁义道德),而缺乏现代政治的维度以及对人物形象的整体观照。事实上,“忠实原作”、“保存经典”透露出轻视大众文化的倾向,把电视剧这一具有较强传播力的文化产品视为二手的艺术“赝品”,这显然是观念滞后的表现。当前,由于历史语境的变换,社会文化经历了从生产到消费的转型,刘备等人物身上的伦理道德的“审美惯力”已然消失。以传统道德为主要诉求的人物形象缺乏个性与情感,必然流于平庸,“仁”的道德境界缺乏现实针对性而苍白无力。相对来说,唐僧的形象变化则属于另一种情况。经典文本对唐僧的揶揄反讽在影视改编中消失殆尽,这显示出道德形象的接受语境越来越狭窄,一方面喜剧人物的道德感往往遭到剧中其他人物、观众的讽刺与嘲弄,如赵本山在《刘老根》、《马大帅》中饰演的人物,观众过于关注道德人物的喜剧因素,而完全忽视了道德本身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其他种类电视剧中,由于缺乏真实的道德体验,电视剧制作者完全受制于以间接方式获得的道德观念,难以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思、审视道德形象。这关乎电视剧创作者的勇气:是否敢于用现代精神审视传统的道德伦理?如《西游记》中,编导能否在严肃与轻松之间举重若轻地出入唐僧的情感、道德、宗教信仰等复杂世界;在对西去取经的庄重叙事中,能否戏谑地表达正面人物,而不是亦步亦趋恪守传统道德观念。可以说,目前国内电视剧的创作仍停留在道德—政治之间的简单指称,而没有寻找人物塑造的其他可能,演绎现代政治的情感力量与人格魅力,也就甚为艰难。
如果缺乏对人物的整体观照与有效的道德体验、政治观念,编导们即便具有审视经典、塑造道德形象的勇气,传播效果也未见好转。相反,现代观念在缺乏整体控制的情况下,对传统人物可能存在更大的损害。这在电视剧《水浒传》中表现得较为典型。宋江形象的改编主要遵循两种方式:用平等的性别观念为古代女性正名(如阎婆惜盼望明媒正娶,与宋江结为合法夫妻),用现代的政治观念否定忠君招安的思想(如强化宋江与晁盖招安,重归封建专制与反招安,叛逆的民主理想的两条政治路线斗争)。但结果却是,人物遭到“反英雄”的颠覆。前者在私人的生活空间中消解了宋江的善良,揭示出浓厚的男权意识;而后者在政治的社会领域中将宋江定位为失败者,展示了“愚忠”思想如何将梁山英雄群体一步步引向衰败、死亡的悲剧过程。这虽然显示出电视剧的批判性,但是,这既超越了历史人物,也脱离了经典文本,过于突出接受语境中的平等、自由的现代文化,忽略了宋江是梁山英雄的军事、行政的现实代表,否定了他的绝对权威对梁山好汉的理性约束,电视剧从情感上排斥、贬低了此类形象,这就影响了人物的合理性。可以说,宋江在现代传媒中不仅是传统文化的替罪羊,而且也成了现代意识的牺牲品。
总体上说,道德形象所指称的文化矛盾在影视文本中较为复杂,一方面要表现、弘扬已被理想化的传统道德,另一方面又受到消费文化与世俗人情的猛烈冲击。传统文化与当下语境不约而同地涂抹、修改道德形象,这使得他们遭遇了双重的损伤:虽然是传统道德的化身,却失去了令人信服的感染力量。虽然保持着领袖地位,却没有足够的权威性以及让人追随的号召力。在电视剧中,刘备的“仁厚”,唐僧的“慈悲”,宋江的“名声”就是人物唯一的力量,然而,当刘备的“仁厚”成为建功立业的武器时,伪善浮出了水面;宋江的“名声”表现出金钱本色时,就不由地虚伪起来;唐僧的“慈悲”常常是用错了地方,成了懦弱与迂腐。
二、异化的竞争:新意识形态与追求成功的心理欲望
从受众角度考察,经典文本与大众文本无论在接受心理还是方式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果说经典文本的接受者需要一种距离(既是反思静观的审美距离,也是保持尊敬的心理距离)的话,那么大众文化的受众则在接受过程中把“自我”融进文本而力图消除这种距离。这种“消融”并不是传统审美意义上的“神与物游”(个体跃身宇宙生命源流之中),而是将主观性情感与经验消融在社会群体的日常生存经验中,并以社会经验取代文本意义。经典文本的封闭性,与大众文本的未完成性形成了鲜明对照。费斯克指出,影视观众首先是社会的人,其次才是观众。也就是说,观众首先是“社会性主体”,然后才是“文本性主体”,后者不仅不能代替前者,而且在大众文本的接受、影响方面,远逊前者。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社会性主体所指涉的日常化生存经验“不仅是观众对文本‘妥协阅读’的根本,而且也是对文本进行选择和评价的依据”⑥以上论述表明,经典文本在封闭的空间(如历史记忆、博物馆等等)与特殊的距离(如与受众构成审美关系)中获得令人尊敬的地位,它指向了一种无关乎受众的当下环境的超越性精神价值、观念。而电视剧等大众文本的传播,从根本上说是对社会群体的日常经验的传播,唤起观众对自身经验的认同,因此和时代语境、社会心理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当前电视剧在重新构建道德人物、组建故事情节时之所以没有积极寻找新的观念去支撑,是因为仍然强调受众的“文本性主体”,而对“社会性主体”缺乏足够重视。毫无疑问,大众文化的传播语境、受众心理已然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在文艺思潮的转折可见一二。1987年拍摄的电视剧《西游记》成为一个社会性议题,但唐僧除了英俊之外,似乎难以引人关注,作为世俗欲望的代表,猪八戒受欢迎程度远超前者,随后就出现了《春光灿烂猪八戒》、《福星高照猪八戒》、《喜气洋洋猪八戒》、《天上掉下个猪八戒》等电视剧。道德形象普遍遭到人们的质疑、忽视。借助现代传媒无限扩张的大众文化,在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等多方力量的促成中,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它以“成功者”、“新富人”为形象代言人,在现代都市文化中越来越具有偶像意义。王晓明说得好:“‘新富人’阶层的膨胀,它岂止是意味着财富的转移和新的权力结构的形成,分明还意味着一个新的人生偶像的凸现、一套新的生活理想的流行、甚至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笼罩。”⑦大众在时代偶像的召唤中,派生出对消费、欲望、享乐合法化的无尽要求。丹尼尔·贝尔认为:“后现代反对美学对生活的证明,结果便是它对本能的完全的依赖。对它来说,只有冲动和乐趣才是真正的和肯定的生活,其余无非是精神病和死亡。”⑧这虽然是对西方后现代社会而言,但对我们也有所警示。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中,商品拜物教、享乐主义不可抑制地四处蔓延,本能的冲动与感官的乐趣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力。当效益失去价值背景后,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可操作性的“技术”就成了获取物质财富、事业成功、社会地位的最直接、最可靠的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大众文本的核心。
现代消费社会追求现世成功的渴望与前工业社会的道德神话大异其趣。由传统文本构形的道德神话成为个人与外界关系的想象诠释与美好向往,道德神话曾作为文化传统强烈的欲求,强有力地支撑起唐僧、刘备、宋江等一类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文化日趋世俗化的今天,道德品质在当下已然脆弱,渴望成功的竞争替代了道德称许的谦逊。但是,市场经济无处不在的竞争也暴露出现代性困境。波兰尼说:“市场体系在处置一个人的劳动力时,也同时在处置附在这个标识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人’。如若被剥夺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暴露中消亡,他们将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所造成的社会混乱。”⑨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人们反而更加需要来自文化层面的自我保护、防御,更需要充满人文精神的道德关怀。从这个角度说,传统道德难以有效地阐释剧烈的社会变动、复杂的现实矛盾、痛苦的人生体验,这种缺陷也导致了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边缘化。如唐君毅、韦政通等都曾指出,传统儒家文化的“人性善”是一种较肤浅的人生体验。“儒家在道德思想中所表现的,对现实人生的种种罪恶,始终未能一刀切入,有较深刻的剖析……儒家的道德思想,对生活安适、痛苦较少的人,比较适合而有效;对生活变动幅度大,且有深刻痛苦经验的人,就显得无力”⑩。因此,电视剧传播道德观念的失效,源于现代道德的沉默与传统体系的失范。
随着社会的开放、自由空间的扩大,竞争成为当今社会难以避免的现象,并已成为再普通不过的心理因素深入到人们的思维逻辑中。“拟实”的电视娱乐栏目策划清楚地告诉我们,竞争是怎样一步步地紧逼我们的日常生活。历史剧、宫廷剧乃至爱情剧(包括《十面埋伏》、《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国产大片)则把人物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欲望渲染得波澜起伏,甚至悖离人之常情、常理(当下热播的《三国》就是以这种权力欲望勾连起魏蜀吴的故事,如强调诸葛亮与关羽张飞的利害冲突、荆州势力与刘璋旧部的矛盾、孙权对周瑜的无端猜忌,等等),凡此种种的影视剧,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激烈的现实竞争,但是,完全抛弃了竞争的公平、公正等积极意义,夸大、异化了竞争,无限度、无节制地放大了在竞争中可能出现的人性丑陋。
三、电视剧的道德形态:以叙事重建道德形象
“现代自由是通过挣脱旧有的道德视阈(moral horizon)而赢得的”。现代人在获取前所未有的自由之后,在挣脱旧有道德视阈获得经营自我权利时,也提出了重建自我或生产自我的任务。(11)因此,民族的道德传统不应被简单地放逐或孤立地封锁起来,它需要复杂的现代观照。或者说,需要对文化本身做出认识性调整。在费斯克看来,大众文化并不创造艺术杰作的形式与理想的审美价值,也难以建构超越时代、国界的人类精神,乃是“工业化社会中意义的生产和流动”,一种工业化社会中生活的方法,它涵盖了社会人生经验的全部意义。(12)即是说,文化工业产品不以古典艺术为参照,而是从自身的价值出发,结合当下社会的某种意义,对现存的文化资源加以选择性运用,从而召唤起大众积极参与意义的再生产。不久前《无极》、《夜宴》、《赤壁》等一系列华语武侠大片在影院接受中出现“笑场”、在网络媒体上引发“恶搞”风潮,虽然暴露出艺术文本存在的种种缺陷,但恰恰证明了自身作为大众文本的娱乐价值,受众的“笑场”、“恶搞”,就是借助电影文本进行文本意义的再生产。同样,以电视剧为代表的文化工业想要在当下语境中传播道德意识,让英雄人物获得旺盛的生命力,必须积极与现代对话,只有用现代意识编码传统道德,使之出现多重的复杂意义,才能最大限度地激活古典文本的价值潜质,吸引受众的主动参与,进而完成道德观念的现代转型。
如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与当下消费文化的双重挤压下,电视剧中的道德形象不仅与真实的历史原型相差甚大,而且与民族文化记忆中的人物形象也渐行渐远。刘备等形象在历史、经典、电视剧中有着不同内涵。在这一演变中,传统文化“敬德”、“崇德”的文化编码不宜全然照搬,但更不能随意舍弃。消费文化一再强调他们体能的孱弱、意志的软弱、技巧的无能,恰恰使得他们难以用单薄的肉身担当起沉重的道德重负(《三国》对刘备的塑造有所改善,增强了个体能力,但仍然没有解决好伪善与道德的矛盾)。但如果舍弃了道德文化的传统,也就取消了此类人物存在的价值。因此,道德形象的自我重建,关键在于借道德文化传统激发起当下接受的多义性。这种多义性并不强调传统道德观念在当下的一致认同,也不意味着以文化消费的逻辑解构传统道德,它产生于抽象道德观念与具体情境表达之间、个人的道德理解与观众接受之间可能发生的错位与争辩中,尤其存在于现代理性对过去道德的温情回眸之中。在现代对传统的眷顾中,培育起独特的道德个性来。
然而,设想由电视剧这种大众文本(甚至包括精英的艺术文本)创造现代性道德观念,对电视剧来说无疑是苛求。事实上,作为一种叙事艺术,电视剧(包括精英的艺术文本)并不以提出、建构某种可行性道德实践、规范为目的,我们更不能要求影视艺术如道德哲学一样进行纯粹理性的思辨,提炼出一种可供社会大众共同遵守的道德理念。更何况,从当前社会道德状况来看,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型面临诸多困境,即便是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都未能提供明确有效的对策,又怎能要求重点本在叙事的电视剧做到呢?因此,作为大众文本,电视剧中的道德状况应当是这样的:叙事提供逼真的情境重复着某种普适性的道德观念,唤醒并且增强人们心中原已存在的道德情感,完成理解道德观念的过程,达到证实、坚定某一道德观念、价值的目的。卡罗尔说得好:“叙事是为了得到预期观众的理解而创作的……叙事并没有教会我们什么新的东西,相反,它只是激发了我们已经拥有的道德和其他方面的知识和情感。”(13)从这个角度说,电视剧中的道德形象不仅需要多种道德观念、文化的冲突、碰撞,而且要求深沉的情感冲突与曲折的故事情节。如果说前者关注当下观众依据日常生活经验进行的理性选择(这种理性选择先在于电视剧等叙事文本,电视剧不过是唤起这种道德理性的选择),那么,后者则是观众在虚构的故事语境中不知不觉地卷入情感漩涡,体验一种混沌多义的道德困惑。如果说前者折射出道德文化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硬性”的冲突,那么,后者则是在共通的情感体验上,挣扎于理想价值与现实选择之间,产生出确证道德观念的情感力量。
目前国内电视剧往往实践着一种传统与现代兼容、妥协的普适性道德观,这种观念实际上已经被大众所接受,如仁爱、良善、平等、自由等,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观念的叙事表达已被认同。当电视剧难以在道德内涵创新时,就更需要丰富的叙事策略与动人的情感力量。因此,电视剧中的“道德指向”存在缺陷,也就意味着叙事的失当,卡罗尔在《超越美学》一书中指出,“因为我们对叙事性艺术作品产生的道德经验是受故事的作者引导的。从叙事中可以获得某个层面的道德经验,而这种经验依赖于作者向我们提供的引导。我主张我们对叙事的道德判断可以建立在作者的引导所计划引起和支持的道德经验性质的基础之上”(第460页)。这样,我们就涉及一个重要的命题:怎样引导故事情节、人物命运传达既定的逍德观念。作为大众文化读本,金庸的武侠小说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典范,由伦理神话、技击崇拜、人文精神等三点支撑的文本结构异常稳定,在各种影视剧版本中,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价值观念都很少遭到现代电子传媒(无论是香港媒体还是大陆媒体)的改动。这意味着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播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总会受到现代观众的抵制。
如上所述,刘备等道德形象之所以苍白,是因为传统文化语境中的道德与政治是一纸两面,然而在当下被强力拆除,道德缺乏足够的伦理价值与审美趣味,非但没有在“技”的竞争层面增添现实意义,反而取消了现代文化话语反思的可能。而作为凡僧,唐僧在神怪世界中,技能已经被完全破除,在丢失了原著的反讽戏谑色彩后,胆怯与懦弱也因失去“可爱”的喜剧成分而被不恰当地强化,缺乏独立的人格以及情感(风靡一时的网络小说《唐僧传》反证了这一点)。相对来说,在宋江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现代人文精神的渗透以及对形象的改造。但他在伦理神话的渲染与知识分子话语反思的双重影响下,实质上是作为英雄的对立物出现的,具有了反英雄的意味。道德形象如此种种缺陷,提示我们:(1)塑造道德形象,需要真切的道德体验,叙事就是既传达、又证实这种切实的道德体验;(2)塑造道德形象,需要在原文本的道德困境中增强更具冲突、爆发力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行动,这才能使当下观众更深入地卷进道德选择的两难处境中,体味道德情感的情境悖论;(3)塑造道德形象,更需要道德自信,敢于迎难而上,主动设置具有现代意味的道德困境,表现人物艰难的道德突围,以雄辩的力量,确证道德选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注释:
①徐贲:《影视观众理论和大众文化批评》,《文化批评往何处去》,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
②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9页。
③冯文楼:《伦理架构与批判立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④参见赵林《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9页。
⑤万俊人:《政治如何进入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⑥徐贲:《影视观众理论和大众文化批评》,《文化批评往何处去》,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
⑦王晓明:《九十年代中国的“新意识形态”》,《半张脸:中国的新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⑧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98页。
⑨转引自陈刚《破除自由主义市场崇拜的乌托邦》,http://www.tecn.cn/data/24852.html.
⑩韦政通语,转引自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16页。
(11)唐文明:《现代人的道德追求》,《读书》1999年第8期。
(12)徐贲:《影视观众理论和大众文化批评》,《文化批评往何处去》,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
(13)诺埃尔·卡罗尔:《超越美学》,李嫒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50页。
标签:大众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道德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三国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道德观论文; 宋江论文; 刘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