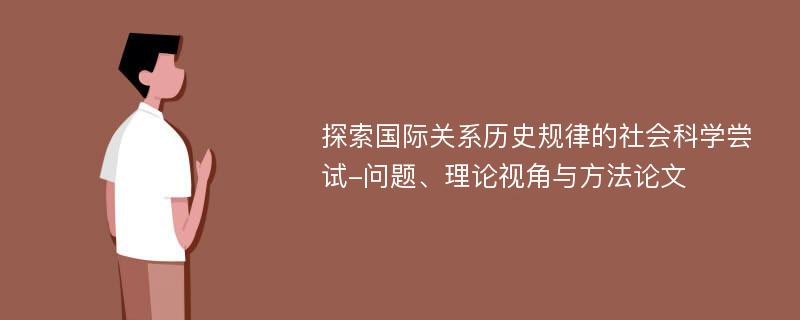
探索国际关系历史规律的社会科学尝试*
——问题、理论视角与方法
黄琪轩
【内容提要】 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与作为历史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研究国际关系史。但是,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会执着于“解释历史”,而不是“理解历史”与“描述历史”。他们不仅会探索国际关系史中的规律,而且会致力于探寻有较广适用范围、简约与精确的规律。在对国际关系史提问的时候,社会科学学者倾向于提出“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或者“怎么样”的问题;他们也更愿意从历史比较中提出问题。在对待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即便是坚持“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家也会将国际关系的历史素材嵌入理论,包括宏大理论与中层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大部分社会科学家不是在用史学方法,而是在用社会科学方法,来寻找国际关系史中的规律。无论经过多少次检验,使用多么精致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史上的同一问题往往都能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找到迥异的答案。这些不同的回答往往都能找到历史证据支撑,都会有它们各自的追随者,也都会经历兴衰起伏。
【关键词】 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学者;社会科学;历史规律;研究方法
随着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研究分野的日趋明显,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的学者希望展示自己的研究和人文学科有所差异,希望自身的研究更靠近“科学”。即便如此,坚持“实证主义”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都与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政治学者会围绕政治议题来展开历史探索;经济学者会依照经济视角来审视历史事实;社会学家会根据社会理论来组织历史素材。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与作为历史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探究历史,寻找规律。① 关于国际关系与历史二者关系的探索,国内研究参见:时殷弘:《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期,第20—25页;高程:《历史经验与东亚秩序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视角》,《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1—19页;王存刚:《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向度》,《外交评论》2008年第4期,第53—58页。 他们的著作既存在很多共通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在寻找历史规律时,所关注的问题、理论视角与方法有自身的特征。
想到这里,风影说做就做,他直奔庙门口而去,可是大门口有两个和尚持棍守着,说是师父吩咐过,谁也不能出这庙门。风影忙问为什么,他们看着风影,那意思是你问我们,我们问谁去?如果你一定要问个明白,那就等师父回来直接问他吧。风影瞅了一眼寺院门外,风摆柳似的在山坡上游来荡去,一步三摇的样子,他就想说不定红琴也像风摆柳似的,正朝那系有红腰带的地方赶呢。他垂头丧气地返回天井,来到佛殿上时,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师父了空法师头顶香火跪倒在佛陀面前。原来师父并没有去云游,而是在向佛祖忏悔自己开了淫戒的深重罪孽哩。风影脸上火辣辣的,也在师父旁边的蒲团上跪了下去。
一、解释历史:国际关系史中的因果关系
在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学者中,有一部分研究者倾向于做“科学研究”,也有一部分人则偏好人文。前者往往给自己贴上“社会科学家”的标签,而后者大部分以“历史学者”自居。尽管这两个群体的研究有重叠,有交叉,但他们也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国际关系史的“社会科学家”大都就职于美国各大学的政治学系。《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期刊发表的与国际关系史相关的论文,大都出自这群人笔下。这一群体所秉持的理念是:国际关系的历史可以拟合出一些规律。他们会努力寻找国际关系历史现象中可被观察的、有规律的联系。比如,从历史上大战爆发的诱因中总结规律;从历史上国家结盟的模式中寻找规律;从历史上区域化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拟合规律。
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在寻找历史规律时,深受16世纪以来“科学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影响,也深受牛顿模式的影响。他们往往致力于从国际关系的历史中寻找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的“自然法则”。正如18世纪的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所写的:自然和自然法则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来,一切遂臻光明。(Nature and Nature’ law lay hid in night ; God said, 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为了让一切看起来更清晰明了,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寻找历史中隐藏的规律性认识。因此,他们在分析国际关系的历史时,和“历史学家”存在显著差异。大多数历史学家倾向于相信“历史偶然”而拒斥“历史规律”。这构成了社会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看待国际关系史的一项重大差异。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爱德华·卡尔(E. H. Carr)除著有国际关系名著《二十年危机》,也写过历史学著作《历史是什么?》。他的看法和社会科学家更接近。“有人告诉我历史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时,我往往倾向于怀疑这个人要么是个思想上的懒汉,要么就是智力不高。”① 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10—111页。 如果一些国际关系的历史现象难以寻找规律,那么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会倾向于略过这段历史。
花色苷由于其来源广泛、有较好的生理活性、无毒副作用及丰富的颜色,在食品、医药、化妆品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尽管研究者们对花色苷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仍有很多问题尚待进一步解决,如花色苷的稳定性问题,花色苷生理功能的作用机制等问题。采用高新技术,不断提高装备水平,扩展应用领域,使花色苷类物质发挥更大的作用。
社会科学家为国际关系史上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与事件提供解释,而不是对偶发事件予以阐释与理解。事实上,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两个传统。一个传统重视“解释”(explain),而另外一个则传统重视“理解”(understanding)。②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15.社会科学会试图寻找历史中不断重复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探索因果关系背后的作用机制,这是在“解释”国际关系的历史。而解释的结果往往会有一些规律性的表述。这样的“规律”要被世人所接受,就需要经过两重检验:第一是逻辑自洽;第二是经验证据支撑。如果这两重检验都通过了,他们就把这样的规律叫做国际关系的科学“理论”。
那么,国际关系学者从历史中寻找出了形形色色的“规律”。哪些“理论”与“规律”更好呢?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比较重视三条标准。
1906年5月31日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17页的初步报告。他们的主报告,《州地震调查委员会报告,第一卷》,由Lawson编辑并于1908年出版。该报告包括对断层作用的地质和形态的大量描述、振动强度的详细报告,以及包括40幅超大尺寸图和对折纸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地图集。第二卷,由Henry Fielding Reid编辑并于1910年出版,主要描述此地震的地震学和机制方面。在本文后面的叙述中,将 《州地震调查委员会报告》(两卷:Ⅰ卷,Lawson,1908,和Ⅱ卷,Reid,1910;共643页)统称委员会报告,适时标出相应的卷号。今天该报告仍可通过购买或在线获得(见参考文献)。
首先,社会科学家在总结国际关系历史规律的时候,重视规律的“适用范围”(scope),总在努力解释更大范围的国际关系历史与现实。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到:“我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修昔底德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从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中找到了人类战争规律性的认识,“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③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8—19页。 而后来的社会科学家根据修昔底德的论述,从国际关系历史中总结出了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该理论主要是关注国际关系史中世界领导权变迁的研究。这一理论沿袭了修昔底德的论断,指出当挑战国在世界政治舞台崛起的时候,领导国与挑战国双方容易爆发战争。④ 早期有关权力转移理论的文献有:A.F.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 New York: Knopf, 1968; A. F. 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如果把修昔底德的论述放到更广阔的国际关系历史中检验,那就符合了社会科学所追求的较广阔的“适用范围”这一目标。
其次,社会科学家希望从国际关系史中寻找的“规律”简约(parsimony)。一般而言,历史学家喜欢展示历史的复杂性。比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他们会细致描绘偶然事件与形形色色的重要人物。而社会科学家则喜欢用更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复杂事件。他们认为社会科学需要抓住关键。因此,社会科学家所关注的国际关系史最后往往都可以简述或概括成两句话。一种概括是:在什么条件下,有什么事情会发生(if……then);另一种概括是:有什么因素朝一个方向变化,那么,结果会朝特定的方向随之变化(the more……the more likely)。比如,国际关系学者总结的“民主和平论”就是这样的历史规律,而且被称为国际关系中经过长久历史检验,罕有例外的规律。“民主和平论”的最简单表述是:如果双方都是民主国家,那么它们之间就不会发生战争。社会科学家看待国际关系史,和他们看待其他社会现象一样,他们相信世界要以“地图式”的方式展示,而不能以“照相机式”的方式呈现。不同于“照相机式”的、事无巨细地复原历史,“地图式”的展示历史要求研究者抓住历史关键,简化历史。社会科学家往往认为,如果把国际关系史展示得无比复杂,既难以提炼规律,也难以指导现实。
再次,社会科学家从国际关系史中总结的规律,需要具备“精确”的特征。而有关霸权稳定论的大部分研究都强调,开放的国际经济是公共品。这个公共品的提供需要一个政治前提:即霸权国家的存在。正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所说:“一个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需要一个稳定的提供者”。① 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p.305.金德尔伯格的表述被后来的学者总结为霸权稳定论。这是从国际关系的历史中抽象出的规律。而这样的规律会面临诸多挑战,因为它可能不够精确。比如,什么样的国家是“霸权国家”?以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实力来衡量?什么样的国际经济秩序才算得上“开放”?因此,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 Krasner)、蒂莫西·麦基翁(Timothy McKeown)等人又从国际关系的历史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修正。② Stephen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 Vol. 28,No.3, 1976, pp.317-347; Timothy McKeown,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nd 19th Century Tariff Levels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 37, No.1, 1983, pp.73-91.事实上,不少当代社会科学家从大规模的历史统计中,寻找更大限度的“精确性”。他们试图寻找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确立模型的显著性水平,来为规律寻找更大限度的确定性。因此,尽管国际关系的研究与历史紧密相关,但是嵌入在社会科学中的历史与嵌入在人文学科中的历史有显著差异。③ 现代历史研究也在吸收社会科学的方法,比如计量史学就强调用统计来展示历史规律。参见:Charles Feinstein and Mark Thomas, Making History Count: A Primer in Quantitative Methods for Historian 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采用WBS-RBS工作风险耦合矩阵分析法,对施工作业按照分离立交桥梁工程施工步骤流程进行了分解,并对工程项目可能存在的所有风险因素进行划分,细化了作业和风险的映射关系,运用LECD建立风险评价模型,计算出各作业单元风险值.
二、提出问题:社会科学家的问题意识
社会科学家在探索国际关系历史的时候,往往是用变量来思考问题,他们的研究有自变量和因变量。一个清晰的因果关系,自变量是原因,因变量则是结果,机制会牵引二者。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问题往往是“因变量”。
冰臼,壁陡而内部光滑,内部一般无填充物,有的可见有少量泥质成份并生长杂草,小兴安岭国家地质公园内发现的唯一一个冰臼有积水和砂;二龙·长寿山地质公园内的冰臼中沉积有泥土并生长有杂草。
首先,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往往倾向于提出“为什么”(why)的问题,而不是“是什么”(what),“怎么样”(how)的问题,更罕见提出“在何时”(when)与“在何地”(where)的问题。“为什么”的问题是可供解释的问题,而不是可供描述的问题。比如,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会关注美国对外大战略。作为历史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在研究美国对外战略时,可能写出的就是《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这样的宏大历史叙事会涉及美国对外战略的方方面面,历史跨度大,涉及议题广,气势更恢宏。而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在研究美国对外战略历史时,往往会选取一个结果作为问题。比如历史上美国的大战略常常出现摇摆,有时候,美国对外大战略的重点是边缘国家与地带;而在另外一些时候,美国对外大战略的重点则转向欧洲等核心地区。那么,社会科学家在关注美国对外大战略的时候,会根据这一结果提出问题:什么时候美国对外大战略的重点在边缘地带,什么时候转向核心地区?② 凯文·纳里泽尼:《大战略的政治经济学》,白云真、傅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 由于需要解释国际关系的历史,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往往会提出可以解释的问题,而不是可供描述的问题。
其次,社会科学家在关注国际关系史的时候,往往从对比中提问,从比较中寻找因果关系。单一不变的个案往往难以寻找出历史规律,因此,社会科学家从比较中寻找国际关系历史中的规律。社会科学家的比较基于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求同”与“求异”方法。他们既可能从单一案例在不同时段的变化进行案例内比较(within-case study),也可能从多个案例中的历史事实从寻找规律,进行跨案例比较(cross-case study)。
我以为父亲随身所带的讲义夹是贩卖养猪知识用的。李打油笑得憋岔了气。好不容易缓过来,告诉我,上殿嘛,不得持笏?原来讲义夹是身份的象征,尽管里面夹的不过是一张记账的纸。前几年我父亲过世,李打油逼着我翻箱倒柜把讲义夹找出来,塞在父亲手里,让他像个真正的斯文那样上殿去了。那是绿色的塑料壳子,上面粘有一块写着“农业基础知识”字样的白胶布。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杨再兴之光耀及的后人,我想我是有责任的,有责任去吸引社会对小商桥的关注,让更多人望见渐行渐远的英烈之光;有责任引导人们挣脱名缰利锁,将目光投向小商桥的历史精神和文化。虽然力量很弱小,但至少我可以通过一篇文章,让小商桥的历史更明朗,让小商桥的文明之光照亮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
比如,有些社会科学学者试图从单一案例在不同时段出现的变化来提问。对美国与中国在冷战初期的互动,托马斯·克里斯滕森(Thomas Christensen)发现在1947年到1958年间,即在冷战初期,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呈现一次又一次的敌对状态,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克里斯滕森不是关心一次事件,而是一系列的事件。比如,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美国的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美国政府援助中国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随着朝鲜战争一步一步升级,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也在升级;1958年,毛泽东主席决定炮轰金门,引发中美危机。克里斯滕森由此提出问题,这一系列中美关系恶化事件背后的共同逻辑是什么?① Thomas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从多次历史事件中寻找问题,试图展示背后共同的逻辑,这是社会科学家试图呈现的历史研究。而作为冷战史研究专家的陈坚,他的专著《中国通向朝鲜战争之路》,则探索在冷战开始初期,中国走向朝鲜战争的来龙去脉。② Jian Chen,China ’s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这样的问题适合描述历史,为我们展示鲜活的历史故事。同时,这样的研究不是从因变量出发寻找更广阔的历史解释。与此相关的是,探索新中国的领土争端,历史学家往往会专注于中国历次领土争端的特殊起因、主要参与者、政府应对策略以及领土争端的结果。而社会科学家则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何在有的时候,中国政府会在领土争端中持强硬立场,而有时候却会做出妥协。③ Taylor Fravel,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 ’sTerritorial Dispute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在这样的案例内研究中,社会科学家会从一个案例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的变化来提出问题,并由此寻找更具规律性的解释。
本文将对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的研究进行综述,着重对其制备类型、在有机污染物处理中的应用等方面进行介绍,并根据现状分析目前研究中尚存在的问题,及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因此,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研究历史与作为历史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探索历史存在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差异就是提问的方式。首先,社会科学家在研究国际关系史的时候,喜欢问“为什么”的问题,以便他们对此给出解释。其次,社会科学家喜欢用比较的方法来提出他们的问题,无论是案例内比较还是跨案例比较。不管怎么提问,“因变量”是问题的核心。他们的问题会关照更普遍的意义而不是讲好一个故事。
三、选择理论:将历史嵌入国际关系理论
一般而言,社会科学家研究国际关系史并不是将重心放在新史料的发掘,但是,他们却需要考虑将史料和以往的国际关系理论对话。如果他们对历史规律的总结是社会科学的“微观理论”,那么,他们往往需要将历史研究嵌入两类理论:一类是宏大理论,另一类是中层理论。宏大理论往往来源于实证,却又超脱于实证。从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中形形色色的主义就是宏大理论;而不少中层理论则是源于实证检验总结的具有时空和地域限定的同类规律集群。这些中层理论可以发展出一系列的微观理论,即更具体的国际关系规律。
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首先要将史料嵌入宏大的理论视角。不同理论视角看待的历史事实会有差异。历史学家常常强调让历史说话,而历史从来不自己说话。卡尔举了一个例子:“琼斯在宴会后开车回家,他比平日多喝了点酒,车子的刹车又不大灵,开到一个死角那里又什么都看不见,一下撞到了罗宾逊,把他压死了。罗宾逊是走过街道,到街角拐角处这家香烟店来买烟的。”① 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桂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13页。 那么,这场车祸的原因是什么呢?琼斯不开车,就不会发生车祸;琼斯不喝酒,或许车祸也不会发生;琼斯的刹车没有坏,这场车祸也可能避免;发生事故的街角如果装有路灯,那么,琼斯可能就不会撞到罗宾逊;罗宾逊如果不抽烟,他就不会出门买烟,也不会被车撞到,这个清单还可以列得很长。尽管卡尔认为有些原因可以被剔除,但是在寻找因果关系来组织历史事实的时候,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视角有着重要的作用。卡尔的看法是:“事实本身就能说话,这一点当然并不真实。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② 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桂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页。 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讲就是:你是否能观察到一个事物取决于你用什么理论,理论决定了你能观察到什么事物。③ Abdus Salam, Unification of Fundamental Forces: The First 1988 Dirac Memorial Lecture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99.不是世界在那里,你观察到了这个世界;你有怎样的国际关系理论决定了你观察到怎样的世界。国际关系中的宏大理论提供不同的视角,会让即便是坚持“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家在看待同一段历史的时候,找到不同的证据,得出迥异的结论。
比如,看待全球化,不同的理论视角就会找到不同的历史事实。一般而言,自由主义者较多地梳理全球化历史的一个侧面,他们强调理性的个人遵循比较优势展开国际分工与交换;强调技术进步降低了各国的运输成本;强调国际组织对国际合作起到的促进作用。因此,理性的个人、进步的技术、国际组织成了他们书写全球化历史的重要内容。
我跟乔振宇因为这些“政见不合”的事争执过多次,他一辩不过我必然出口抱怨:“我乔振宇堂堂一个大丈夫,当初怎么就猪油蒙心找了你这个油盐不进的三等女了呢?”
第二,找新解释。学者也可以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统计检验来验证一个国际关系的猜想,为已有研究贡献一个自变量。例如,有研究通过统计1807到2002年间的数据发现:那些财政能力不足的国家,如有较高债务负担且难以获得国际信贷的国家,更愿意与大国结成军事同盟。③ Michael Allen and Matthew DiGiuseppe, “Tightening the Belt: Sovereign Debt and Alliance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 Vol.57, No. 4, 2013, pp.647-659.因为这些财政能力不足的国家缺乏独立发展军备的财政资源,它们用结盟的方式来搭大国的便车。这样的统计检验为联盟形成的文献贡献一个新的解释变量——财政能力。
而建构主义者则强调理念在全球化演进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大英帝国是18—19世纪全球化的引领者。有研究展示,早在18世纪80年代,英国就开始尝试摒弃重商主义,推行自由贸易。英国的贸易政策转变离不开自由主义的关键人物——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斯密的推动和影响下,大英帝国的政策制定者如谢尔本伯爵(Earl of Shelburne)所秉持的理念也在发生转变。在谢尔本伯爵担任英国首相后,他开始按照斯密的自由主义理念进行改革。英国决策层不仅允许了美国独立,还尝试和欧洲国家和解,并积极推动英国和世界各国展开自由贸易。像斯密这些思想家积极行动起来,积极推动其理念付诸实施,也推动了全球化进入了一轮自由贸易时代。② James Morrison, “Before Hegemony: Adam Smith, American Independ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Era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66, No.3, 2012, pp.395-428.
ALE处理出站入站流程,是SAP系统信息的输出;IDoc处理的是数据信息的传递,是SAP系统信息的流入。二者协同合作,起到信息交流的作用。
事实上,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理论、绿色政治等不同的理论视角会梳理出非常不同的全球化历史。每一种理论视角都会重视一个方面的历史事实,而忽略其他方面的事实。因此,即便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者希望追求“价值中立”,但是也难以实现对国际关系历史的“全景式”展示。嵌入“宏大理论”的需要让他们集中呈现部分历史。这样的历史呈现尽管不够完整,但是这样做的显著优点是保持了理论连贯、逻辑自洽、证据集中。
一般而言,社会科学家在研究国际关系史时,他们的实证研究不仅需要与宏大理论对话,还需要和中层理论对话。中层理论是依靠实证检验总结的具有一定时空和地域限定的规律集群,它们由一系列的微观理论构成。将自身的研究嵌入中层理论,是让自身的微观理论找到对话的对象。这样的对话使知识的去伪存真、积累进步成为可能。比如,国际关系中有民主和平论、贸易和平论、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理论等一系列的中层理论。
尽管统计与案例二者存在竞争,即传统的定量与定性的分野,但二者的共识却大于分歧。采用这两类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家都认可要用“科学”的办法来收集证据、找到规律。统计可以用大规模的数据来检验历史。战争的原因、结盟的模式、国际条约的签署等国际关系议题都可以从历史数据中寻找规律性的模式。有研究通过统计检验陈述一个以往研究所忽略的历史事实;有研究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统计检验来验证一个国际关系的猜想,为已有研究贡献一个自变量;有研究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统计检验来找出已有理论成立的条件;也有研究通过统计检验来反驳一个已有命题;还有研究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统计检验来裁定已有的理论纷争。
概言之,社会科学家在研究国际关系历史时,会执着于“解释历史”(explain history),而不是“描述历史”(describe history)、“理解历史”(understand history)或“阐释历史”(interpret history)。他们会寻找国际关系中反复重现的规律,并以更广阔的适用范围、更简约、更精确的方式来概括这些规律。乃至有研究者指出,通过研究历史,总结规律,可以对国际关系的未来做出预测。①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预测,参见王建伟、陈定定、刘丰主编:《国际关系中的预测: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阎学通、漆海霞:《中外关系定量预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 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对“解释历史”的执着会影响他们提问的方式、理论诉求以及方法应用。
贸易和平论的学者展示了贸易对和平的促进作用。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贸易依存度很高的英国和德国二者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呢?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与英国互动历史的梳理,戴尔·卡普兰(Dale Copland)的研究展示了相互依存大国之间对未来贸易的悲观预期致使二者走向战争。高度的相互依赖既不必然导致战争,也不必然带来和平。卡普兰认为其具体走向取决于贸易预期,即双方对未来可能展开贸易的判断。只有当国家对未来贸易预期是积极的时候,较高的相互依赖才会是和平导向的。② Dale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20, No. 4, pp.5-41.另外他的相关作品参见:Dale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社会科学家试图从国际关系史中发展出自身的微观理论,大都需要和这些中层理论对话,来清晰界定自身的贡献。
华北地区人口占全国26%,水资源量仅占全国6%,人均水资源量只有556m3,是全国缺水最严重地区。上海市、江苏省经济发达位于全国各省市前列,2013年人均水资源量仅117m3、358m3。云南、贵州田高水低,绝大部分耕地和人口位于平坝区,云南省水量少的平坝区占全省面积的6%,耕地却占全省的40%;四川盆地底部面积占全省26%,耕地却占全省62%,水资源量仅占全省22%。水资源分布在区域内是分散的,而人口相对集中(城市化形成城市聚集群),导致人均水资源量很少,废污水排放量巨大,水质污染严重,河湖水系难于承载。
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者在研究历史的时候,都会嵌入理论,包括宏大理论与中层理论。一旦将自身研究嵌入宏大理论,他们往往会发现,不同理论视角常常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历史证据。“实证”的过程让不止一种理论得到历史证据支撑。竞争的理论之间,都会有相应的历史证据与反证。你会发现:无论对宏大理论还是中层理论而言,没有哪一种理论凭空出世却找不到历史证据支撑;也没有哪一种理论是“终极方案”,将国际关系的历史一览无余。事实上,社会科学家在进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时候,往往不会说自己“证明”(prove)了什么,而是说自己的研究展示(indicate)了什么。理论之间的竞争已经很难用“对错”来表述,大都数竞争的理论只不过存在解释力强弱的差异。那么,怎么获得更强的解释力呢?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往往会诉诸更“科学”的方法,让自身的“理论”获得更强的解释力。
四、运用方法:用科学方法探究历史
历史学家研究国际关系史常常采用一些历史学的方法,比如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著有《历史学家的技艺》,华人历史学家严耕望也著有《治史三书》等。马克·特拉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的著作《国际史的技艺》介绍了研究国际关系史的技艺,包括如何研读文本、分析档案和文件等。① Marc Trachtenberg, The Craf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A Guide to Method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而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者的方法和作为历史学家的技艺会存在一些差异。因为社会科学家大部分不是在用史学方法,而是在用社会科学方法。简略概括,比较流行的方法可以归纳成四个词:模型(model)、实验(experiment)、统计(statistics)、案例(case)。模型主要使用的是演绎法,实验、统计以及案例大都依靠归纳。现实中,这四类方法往往混合使用。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著作《冲突的战略》就是使用博弈模型来研究军备竞赛、国际谈判等议题。② 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 而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教授使用“连锁店博弈”模型来研究国际咖啡组织兴衰的历史,则是模型和国际关系史结合的典范。③ Robert Bates, “The International Coffee Organ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in Robert Bates,Avner Greif, Margaret Levi, Jean-Laurent Rosenthal, Barry R Weingast, eds., Analytic Narratives ,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94-230.
除了从纵向比较中提问,还有不少研究从横向比较中提问,比较典型的做法是跨案例比较。社会科学家关注战争与和平的历史,他们会从比较案例中求同或者求异。有学者展示,欧洲国家以外有两个重要的“和平区域”。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南美洲的国家之间保持了长久的和平;同时,自20世纪60年代独立以来,西非国家之间也没有发生过战争。为何会存在这样的和平区域,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④ Arie Kacowicz, Zones of Peace in the Third World ,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社会科学家会从这两个和平区域的历史演进中寻找共同点,探索历史规律。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各诸侯国之间的竞争类似于今天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形成了一个早于西欧体系的华夏体系。历史学家看待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更重视历史叙事,比如《古代中国及其敌人》梳理了古代中国和北部游牧民族匈奴二者之间的竞争与互动。①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这样的历史叙事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这样的研究难以聚焦可供比较的问题,因此是人文研究。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在对比古代中国和欧洲历史的时候发现:在战国时代的中国,诸侯国之间爆发的战争打出了大一统的秦王朝;而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却遵循“制衡”原则,维持了欧洲诸国分裂的局面。她提出的问题是:为何古代欧洲没有打出大一统的国家,而古代中国却打出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② 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徐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从对比的历史中提问,无论是横向比较、纵向比较还是交叉比较,社会科学家试图寻找与回答国际关系史上的规律。
就实验法而言,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教授的《合作的进化》用实验展示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即“一报还一报”(tit-for-tat)是得分最高的策略。④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吴坚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这一研究影响深远,不过实验方法却难以在研究国际关系史上有用武之地。与实验法相对应的是观察法,统计和案例的资料来源就主要依靠观察,观察现实与历史的数据与案例。
人们普遍感到这是个物质上快节奏发展的时代,是个精神上有些浮躁的时代。物质的繁荣让吃饱穿暖的人们有闲暇去追求娱乐和令人愉悦的东西,以颜值为代表的观念应运而生。这让我想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风气是那么的相似。年少时看书,看到潘岳、卫玠的出场是那么让人眼前一亮地欢喜,看到慕容冲和独孤信的出现是那么让人惊为天人地欢呼!他们不但有一定的才华能力,还都那么容颜绝代,留下了许多美丽的故事和画面:掷果盈车、珠玉在侧、侧帽风流、凤止阿房,造化把多少灵秀之气都聚集在了这样的几人身上啊!
以民主和平论为代表,国际关系学者发展出了一系列与国际关系史相关的研究成果。例如,有研究嵌入这一中层理论,并试图指出,不是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而是人们会根据事实不断修改民主国家的定义。① Ido Ore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Changing U.S. Perceptions of Imperial Germa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20, No. 2, 1995, pp.147-184.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国际关系史来看,美国曾把普鲁士德国界定成民主国家,随着美国与德国关系日趋紧张,美国人又把德国界定成了非民主国家;苏联在与美国一同抗击法西斯德国的时候,也被美国人视为民主国家;但是,随着二战结束后美苏竞争的加剧,苏联在美国人眼中变成了非民主国家。作者将历史研究嵌入一个中层理论,试图展示民主和平论的主观性。其他研究也对这一中层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比如有研究展示民主和平论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历史上民主国家数量比非民主国家少,且民主国家之间大多不接壤,因此发生战争的概率自然比较低。
“过程追踪”这个词来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心理学。过程追踪强调按时间次序展开叙事,探析从原因到结果经历的中间步骤,展示事件发生的过程如何一步步展开,如何导致结果的出现,这样可以更清晰地展示因果链条。因此,过程追踪就像多米诺骨牌,如果桌面上有50张多米诺骨牌,过程追踪要展示出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怎么会一步一步传导下去,导致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④ Andrew Bennett and Jeffrey Checkel, “Process Tracing: From Philosophical Roots to Best Practices,”in Andrew Bennett and Jeffrey Checkel, eds., Process Tracing: From Metaphor to Analytic Tool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6.过程追踪法不同于历史学家对事件顺序的细节描述,而是需要展示关键步骤如何导致了事件的结果,围绕着因果链条进行历史叙事。对社会科学家而言,他们最好能概括这些关键步骤不是特殊的,而是可以推广的。
同样是看待全球化的历史,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会看到强权对整合世界市场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他们眼中,世界市场的兴起离不开强权的作用。代表性的著作就是罗纳德·芬德利(Ronald Findlay)与凯文·奥罗克(Kevin H. O’Rourke)合著的《强权与富足》。④ 罗纳德·芬德利、凯文·奥罗克:《强权与富足:第二个千年的贸易、战争和世界经济》,华建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这两位作者尤其强调“强权”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因此主导全球化的历史主线离不开国家权力。而世界体系论的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著作则展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全球化历史。他强调世界体系是一个经济实体,他称之为“世界体系”。从16世纪开始,以西欧为中心,世界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经济体系”。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部分组成了一个整体,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劳动分工。不同的区域承担了不同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也使得中心地区从世界经济的运转中获得不平等的收益。①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十六世纪的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尤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页、第194页。 因此,沃勒斯坦用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的分工,中心对边缘地带的剥削来组织全球化的历史。
第三,找新条件。学者也可以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统计检验来找出已有理论成立的条件。有篇援引频率很高的研究展示:盟国之间更容易有贸易。④ Joanne Gowa and Edward Mansfield, “Power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87, No.2, 1993, pp.408-420.但是有研究通过分析1885到1938年间欧洲国家的数据,挑战了这一理论。该文章通过细致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合作协定很重要。如果盟国之间存在经济合作协定,那么军事结盟就可以加强双方的经济联系;但是如果两个国家不存在经济合作协定,结成军事同盟以后,二者的经济交往并不会得到加强,甚至并不比它们与那些非同盟成员国的经济交往程度高。⑤ Andrew Long and Brett Ashley Leeds, “Trading for Security: Military Alliances and Economic Agreement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 Vol.43, No.4, 2006, pp.433-451.因此,该研究的统计检验展示,已有理论是有问题的,或者它的成立是有条件的。军事同盟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并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经济条约作为支撑。
第四,驳旧命题。学者可以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统计检验来反驳一个已有命题,挑战已有的理论。例如,针对上述研究,有学者通过统计展示:与他国结盟并不能“搭便车”,相反,与他国结盟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如果想要加入一个军事同盟,一个国家需要向同盟者传递有效的信号,展示其强烈的意愿和实力。1816年到2001年的数据显示:那些进行了大规模征兵的国家,为此支付了高额成本,借此向盟国传递明确的信号。如此一来,它们就更容易加入一个军事同盟的俱乐部。① Michael Horowitz, Paul Poast and Allan Stam, “Domestic Signaling of Commitment Credibility,”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 Vol.61, No.8, 2017, pp.1682-1710.因此,这一研究反驳了国家加入军事同盟是“搭安全便车”的理论。还有研究通过历史数据来修正贸易和平论,该研究展示:并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而是“贸易共同体”有效预防了战争。当两个国家都在一个“贸易共同体”内的时候,两国的战争会影响整个贸易共同体的利益。因此,在共同体内的其他国家会积极介入,防止两国走向战争。如此一来,人们不应该把和平的期望寄托在双边贸易上,“贸易共同体”对战争的预防作用要比两国贸易的影响更显著。② Yonatan Lupu and Vincent Traag, “Trading Communities, the Networked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 Vol.57, No.6, 2012, pp.1011-1042.
第五,裁旧分歧。统计检验不仅能展示主要变量的相关关系,还能裁定相关理论争论。例如,学界常常对此争执不休:究竟是选举权的扩大促使政府加大了财富再分配的力度,还是战争加大了政府再分配的力度?两个竞争的假说都有自洽的逻辑。可以想见,选举权的扩大会增加穷人的选票,迫使政府加大再分配力度以满足穷人的诉求。但是,有研究分析了从1816年到2000年近两百年的历史数据发现:在战争期间,政府需要动员穷人参战,因此加大了对富人的征税,以补偿穷人。统计展示排除了选举权的影响,是战争动员,而不是选举权的扩大促进了再分配政策的实施。③ Kenneth Scheve and David Stasavage, “Democracy, War, and Wealth: Lessons from Two Centuries of Inheritance Tax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106, No.1, 2012, pp.81-102.历史数据展示:要解释福利国家的兴起,国际影响要大于国内影响。这是用统计的方法来裁定已有理论的分歧。
如果说统计代表了定量分析,那么案例就是定性分析的代表。不过,即便是定性分析,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者和历史学家的方法也存在较大差异。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科学试图从国际关系史中寻找规律。大部分定性研究都可以纳入案例研究的范畴,但是社会科学的案例不同于商学院的案例,不同于法学院的案例。在社会科学家看来,他们希望通过案例寻找规律。下文通过比较历史分析、反事实分析以及过程追踪这三项社会科学与历史学最接近的方法来探讨二者的差异。
和历史学最接近的社会科学方法是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比较历史分析的学术抱负宏大,它聚焦于理论创建而非理论检验。它从宏观层面解释大问题,包括国家构建、战争与和平、民主转型等。比较历史分析有一些引用频率较高的概念,如:关键时刻、路径依赖、时间快慢、时间长短、先后顺序等。在2003年参与编辑了《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一书以后,2015年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及其合作者重新主编了《比较历史分析前沿》。①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在这本书的导言部分,编者列出了2000年至2014年比较历史研究的获奖图书,这份名单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获奖图书中,和国际关系相关的是杰弗里·赫伯斯特(Jeffrey Herbst)的《非洲的国家与权力》。该书试图探讨:为什么非洲国家积贫积弱,长期难以建立起现代经济?② Jeffrey Herbst,States and Power in Africa: Comparative Lessons in Authority and Contro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针对这个问题,赫伯斯特将非洲的国家建构历史与欧洲进行对比。他给出的解释是非洲国家间缺乏战争。传承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解释,赫伯斯特展示了欧洲的战争可以打破原有政治经济结构,使执政者能够加强对社会的汲取能力,塑造强有力的官僚系统,加强民族主义,锻造有凝聚力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历史上,欧洲国家的战争促使了现代国家的形成。但是非洲独立后历史却被纳入了西方世界主导的所谓“文明社会”,国家之间不能再发生战争。非洲国家缺乏欧洲国家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战争史,因此,也缺乏建成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的驱动力。社会科学家使用比较历史分析这一方法服务于其寻找规律与理论建构的需要。
“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s)也是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常用的方法。这一方法是研究者通过提供历史上并没有真实发生过的,与事实相反的“可能选择”或者“替代选择”,进而探明什么原因导致了特定结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问:如果裴迪南大公没有去萨拉热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就不会爆发?如果没有希特勒,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否就不会爆发?① Jack Levy, “Counterfactuals and Case Studies,” in Janet Box-Steffensmeier, 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627.历史学中也常常用反事实分析,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反事实分析是为了在缺乏可对比的历史案例时,创造出虚拟的案例来探索“规律”。对社会科学家而言,在运用反事实分析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其中一个基本要求是:要最小限度地改写历史。② Richard Ned Lebow, “What’s So Different about a Counterfactual?” World Politics , Vol. 52, No.4,2000, p.565.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就这一方法进行了一系列卓越的研究。③ Richard Ned Lebow, “Contingency, Catalysts and Nonlinear Change: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in Gary Goertz and Jack Levy, eds., Explaining War and Peace: Case Studies and Necessary Condition Counterfactuals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Richard Ned Lebow,Forbidden Fruit: Counterfactual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他批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著作《虚拟的历史》以及《战争的悲悯》中,错误地使用反事实分析。因为弗格森大胆地改写了历史来完成反事实分析。事实上,对社会科学家而言,为了探讨因果关系,不能随意地进行“反事实”分析。即便要假定没有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会出现,也要保证这样的事实在历史上首先要是可能的。如果纳粹德国根本无望赢得战争,那么人们就不能随意假定“假如纳粹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即便运用同一种方法,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研究国际关系史时也存在差异。
第一,找新现象。学者可以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统计检验陈述一个以往研究者所忽略的历史事实。例如,有研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历史上的战败国愿意支付赔款而不是赖账?经过统计检验,该研究展示:参与战争的国家并不能有效代表所有的主权国家,缺乏财政基础的国家根本不愿意打战,所以即便是战败国也有能力支付战争赔款。① Patrick Shea and Paul Poast, “War and Defaul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 Vol.62, No.9, 2018,pp.1876-1904.还有研究通过对1870年到1992年的历史数据分析发现:尽管在战争爆发初期,战争会影响交战双方的贸易往来,但是战争对交战两国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历史数据显示:交战双方往往与对手展开贸易。② Katherine Barbieri and Jack Levy,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The Impact of War on Trad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 Vol.36, No.4, 1999, pp.463-479.这样的统计通过数据,向人们展示了新的历史现象和事实。
通过展示过程,社会科学的学者可以减少因果推断中的不确定性。尽管过程追踪的方法强调对历史细节的叙事,但是它是有假设检验的历史叙事。在展示历史事件演进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家需要对这一过程进行解释性的分析,从而从中寻找更普遍的规律。过程追踪的名篇是《展示理念作为原因》。① Craig Parsons, “Showing Ideas as Causes: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 56, No. 1, 2002, pp.47-84.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是二战以后的重大问题。二战结束以后,在具有共同体意识的政治精英——时任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等共同体派的推动下,“欧共体”“欧盟”这样一套独特的政治理念在法国逐渐形成发展。这一理念像滚雪球那样,影响的人越来越多,影响力越来越大,乃至改变了原本持有强硬立场的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等法国领导人的看法。在这一理念的推动下,战后欧洲最终实现了一体化。因此,过程追踪很好地展示了法国国内的共同体派的理念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形成。一体化的理念对欧洲走向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科学与历史学都会使用一些方法,而社会科学家的方法则更多是社会科学方法而不是历史学方法。社会科学家使用的方法的目标却是服务于其探索国际关系史中更具普遍性的规律,而并非指向甄别史料的真伪与挖掘新的史料。
五、结语与讨论
国际关系史学界存在两个研究群体: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与作为历史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他们都在研究国际关系史,都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自身独特的贡献。尽管双方都关注国际关系的历史,但是,二者所关注的重点、提问的方式、嵌入的理论以及运用的方法都存在较大差异。
在一部分历史学家拒斥“规律”的同时,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往往执着于寻找历史中隐藏的规律。同时,尽管有一部分历史学家认同历史规律,社会科学家与他们仍存在差异。与寻找历史规律的历史学家相比,社会科学家希望他们寻找的规律有较广的适用范围,简约,且精确。社会科学家在研究国际关系史时,会执着于“解释历史”,而不是“理解历史”。
在提问的方式上,社会科学家往往倾向于问“为什么”的问题。而避开“是什么”“怎么样”“在何时”“在何地”等问题。社会科学家也更愿意用比较的方式提问,包括案例内比较以及跨案例比较。从比较中提问有利于他们解释历史,这与历史学家更愿意专注于一个具体历史事件或者单一个案存在较大差异。
在运用理论上,坚持“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家在看待同一段历史时,往往会找到不同的证据,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这是因为他们需要将历史嵌入“宏大理论”。“宏大理论”与“中层理论”,这样的诉求驱使他们根据理论的自洽性裁剪历史。由于国际关系中存在多重视角,因此,无论是宏观理论、中层理论还是微观理论,理论竞争会永远持续下去,难有终结。
在方法问题上,大部分社会科学家不是在用史学方法,而是在用社会科学方法。即便社会科学家与历史学家有时在使用类似的方法,但是,他们使用方法受到“社会科学”基本框架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方法永远不完善,因此国际关系史与理论的对话也不会停歇。
换句话来讲,即便使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学者们也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可能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面对同样的历史证据,学理背景不同、信仰不同、采取的范式不同,所看到的历史证据就会有差异。学者们往往用自身的视角来解释历史。他们相信“眼见为实”,但是即便面临同样的事物,不同的眼睛却看到不同的现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大部分人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从二维画面中辨认出三维图画,而生活在非洲部落的民众则缺乏这一能力。因为他们没有相关的学习经历与视角训练。因此,即便看一副普通的二维图画,不同背景的人也能看到不同的画面。① Alan Chalmers,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Science ,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2013,p.6.
其次,在不同空间,机制的强弱有异,因此学者们观察到的历史证据也会有所差异。在做横向历史比较的时候,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存在较大的差异。社会情境不一样,不同社会占主导作用的机制就会存在较大差异。在自由主义信仰占主导的国家与地区,“一步快,步步快”这一机制发挥的作用会更显著;而在盛行集体主义信仰的国家与地区,强调“和光同尘”,那么“枪打出头鸟”这一机制发挥的作用就会更显著。不同的学者考察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历史,这些地区占主导作用的机制不一样,那么,他们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也会有差异。他们发现的规律都会深刻地嵌入到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再次,在不同时间,机制会相应改变,学者们找到的历史证据也会呈现差异。在进行纵向历史比较的时候,同一个国家与地区,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在不同时期也可能不同。“记得前苏联阵营在20世纪90年代垮台时,许多人跟我说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是回不来了。我当时的回答是:‘等着吧,它会回来得比你想象得快。’自由主义犯自由主义的错误,左派犯左派的错误,法西斯犯法西斯的错误,科学主义者犯科学主义者的错误,原教旨主义犯原教旨主义的错误。一个观念一旦变得强大并成为从国家到社会的实践,后继者就会放大该观念的误区,再后继者就会排斥这一观念并把另一种观念推向高峰。”① 赵鼎新:《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4期,第16页。 在同一个地方,发挥主导作用的机制也会变化。如果一种机制发挥到极致,削弱它的力量就会成长,相反的机制就会凸显。机制的消长也存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情况。同样一个问题,学者观察下一个阶段的历史时,就会得出与前期历史迥然不同的结论。
最后,社会科学中的机制常常成双成对出现。在研究国际关系史的时候,完全相反的理论常常都能得到检验,无论是定性的检验还是定量的检验。这是因为,机制常常成对出现。② John Elster, “A Plea for Mechanisms,” in Peter Hedstrom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Social Mechanism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49.例如,体量大会有显著的优势,即可能存在类似的机制——“船大好顶浪”,同时,我们会发现存在相反的机制,体量小也有显著优势——“船小好调头”;我们看到强大的庇护者提供帮助,其发挥作用的机制是“大树底下好乘凉”,而强大的庇护者也会带来坏处,即“大树底下不长草”;积极发声会有优势,其发挥作用的机制是“爱哭的孩子有奶吃”,同时韬光养晦也会占据优势,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就是“闷声发大财”;大集团可能会有强大的影响力,其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众人拾柴火焰高”,而小集团也会有很多优势,其机制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因此,即便通过“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史,不同的学者可以发掘出方向完全相反的历史智慧。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速,而公路工程行业作为城市规模发展的核心行业,其施工管理工作也要不断进行革新和发展。公路工程施工管理中尤其要做好目标管理工作,多层次、全方面的落实管理方法,从而让施工管理中的目标管理辅佐施工管理人员作为参考依据,并快速适应公路工程施工,保证公路工程施工的效果和质量。为此,必须对目标管理的原则进行分析,并掌握其基本方法。
无论经过多少次检验,使用多么精致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史上的同一问题往往都能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找到迥异的答案。且这些不同的回答往往都能找到历史证据支撑,都会有它们各自的追随者,也都会经历兴衰起伏。因此,探索国际关系历史规律的社会科学尝试,为持有不同理论偏好的国际关系学者提供了思维展示的空间、方法竞技的场所。即便在有的时候,有的学派会从巅峰走向颓势,但这却是一场没有落幕的竞技。
【作者简介】 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 邮编:200030)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19.04.007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9)04-104-18
* 本文为上海社科一般项目“以国际产能合作扩大中国与战略支点国家利益交汇点研究”(项目号:2018BGJ004)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4-03】
【责任编辑:张志洲】
标签:国际关系史论文; 国际关系学者论文; 社会科学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研究方法论文;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