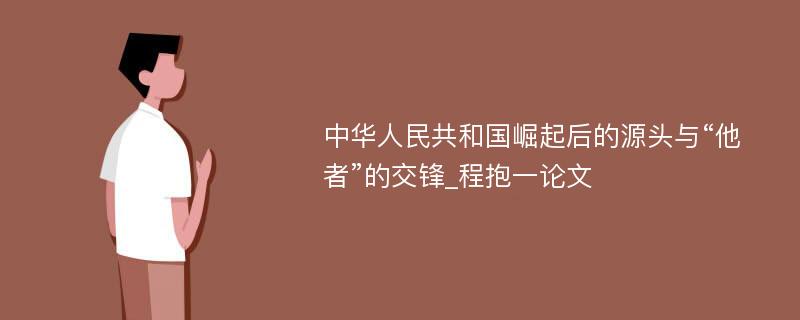
本源與“他者”交流後的升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界華文文學各大板塊中,歐洲華文文學(以下簡稱“歐華文學”)之所以具有獨特性,不僅在於它生長於世界性語種最多樣、文化傳統悠久豐富的西方大洲,更在於它富有建設性地參與了中國“五四”新文化傳統的形成、發展,極有創造性地開啟、推進了中國文化傳統的現代性轉換;它讓中西方文化以從未有過的接近,對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播、走向世界做出了富有實績也最有世界性影響的貢獻。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歐華文學的發展史,那麽,“遠行而回歸”可以說是最爲貼切了。所謂“遠行”,不僅指它地理疆域的跨度,更指它深入至迥異於中華文化的西方文化世界;所謂“回歸”,也並非是它簡單地回到中華文化傳統,而是以“在地”的方式完成傳統的現代傳承,從而豐富了中華文化傳統。 海外華文文學版圖主要由東南亞、北美、歐洲、東北亞、大洋洲等區域組成,其中的歐華文學一直顯得“波瀾不驚”,尤其是與作爲海外華文文學重鎮的東南亞華文文學形成鮮明的對照。 在中華文化的現代發展進程中,“五四”新文化傳統無疑是一個重要維度。而從“五四”新文化傳統形成之始,東南亞華文文學就與“五四”新文化所包含的“中國性”發生了直接而複雜的糾結。東南亞華文文學是被中國南來文人催生、成長的,而從辛亥革命到抗戰時期的中國革命黨人也往往把南洋華人社會作爲其重要的海外根據地。所以,東南亞華文文學從一開始,就在社會意識層面上深深地介入了“五四”新文化慼時憂國的傳統。在相當長時間裏,“感時憂國”之時勢、國家都指向了中國,其文學思潮、運動等也幾乎依傍中國現代文學中“感時憂國”那一流脈的模式。以海外華人人口比例最高的馬來亞地區爲例,其華文小說從問題小說起步,隨後有了南洋鄉土地域色彩的倡導、“新興文學”(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興盛、抗日小說的蜂起等,其內容和時差大致呈現出中國新文學思潮向外輻射並產生直接影響的軌迹,形成“同步”於中國新文學的格局。①尤其是1937-1941年的馬華抗日文學,援助中國抗戰的救亡運動壓倒了馬華現實主義本土文學傳統的開展,甚至被認爲存在“過於極端的中國表述”②。這種深深介入“中國性”的狀況使得馬華文學“驚濤駭浪”不斷。1948年發生“僑民文藝派”與“馬華文藝派”的激烈論戰後,馬華文學的當地語系化進程變得自覺起來,但“感時憂國”的現實主義傳統始終是馬華文學根本性的價值尺度。在馬來亞獨立建國後,馬華文學界一再提出“愛國主義的大衆文學”等口號③,其“愛國”自然指向了馬來亞。然而,當馬來西亞確立了“以馬來語爲國語”、“以當地土著文化作爲國家文化的核心”、“馬來人用馬來語創作的作品構成國家文學的範疇”之原則④,華人文化明顯受到族群排斥、國家歧視時,馬華文學必然要承擔起以傳承中華文化傳統來凝聚族群力量、抗爭民族壓迫的重任,其“感時憂國”的現實主義傳統成爲抗衡之道。 長期的抗衡,使得傳統的現實主義成爲馬華文學的主宰,也使馬華社會、馬華文學無法避免某種無奈的“惡性”循環。1960年代、1980年代馬來西亞都曾發生過馬來族與華族的大規模社會衝突、騷亂,而執政的馬來民族主義者更加大對華族文化的壓制。中華文化在維繫民族血脈、抗衡外來壓迫中更多地成爲被消費的資源,馬華文學如何豐富、提升中華文化的問題較難顧及,自身的發展也受到制約。自1991年起,馬華文壇接連發生幾場爭論,包括“馬華文學的定位”、“經典缺席”、“文學及其研究的困境”、“斷奶論和馬華文學”等,其規模、激烈程度、影響等是馬華文學史和同時期其他地區華文文學中絕無僅有的。例如,黃錦樹《“馬華文學”全稱之商榷》⑤一文在“對馬華文學史做全盤整頓、探源、瞻遠”中力圖打破“‘華極’的思考模式”,將馬華文學史從偏向於“文化上強烈認同中國,甚至有‘純化’傾向的華人”中解脱出來,以“探索、前瞻大馬華人的未來”,但卻跟馬華文化的歷史和現狀產生了激烈衝突。禢素萊《開庭審判》⑥一文更在馬華文壇引發“擲彈”效果。文章敍述了“日本東南亞史學會”中“權威袞袞諸公”斷言“馬華文學”“不以本土語言爲本”,是“連自己的政府也不承認的文學”,“根本不能冠以‘馬來西亞,四個字”,由此道出的是馬華文學的某種歷史困境。爭論的激烈,其實都是針對馬華社會的封閉傳統和華文文學現實主義的自我桎梏而發生的。馬華文學在經歷了這種激烈的爭論之後,逐步實現了自身的蜕變。 相比較之下,歐華文學則顯得格外平和悠長。在以往文章中,人們已經談及“五四”時期的旅歐作家取一種全身心地融入世界文化潮流而又較爲自然地溝通於傳統文化的創作姿態的諸多原因。這裏還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五四”時期旅歐作家以這種生存狀況積極參與了“五四”傳統的形成。他們並不缺乏感時憂國之責任,但更看重文學本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也更多展開於文化建設的層面。包括徐志摩、老舍、巴金、林徽因、蘇雪林、艾青、傅雷、朱自清、朱光潛、錢鍾書、鄭振鐸、宗白華、戴望舒、許地山、馮至、季羨林等在內的旅歐中國作家,可以說是“五四”新文化建設者中最有成就的群體之一。當從魯迅、周作人、陳獨秀始,經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一直到夏衍、穆木天、胡風、周揚等幾代留日作家,以對中國社會變革的激情參與建構了中國新文學大半個舞臺時,旅歐作家卻較多地潛心藝術、學術,展開的是平和悠長的文化建設。蘇雪林(1897-1999)的《棘心》(1929)一書就展示了這一點。 《棘心》是最早涉及旅歐題材的長篇小說之一,蘇雪林曾很肯定地表示,小說“真的是我的自傳”⑦。她借小說主人公醒秋之口回憶自己1920年代初旅歐的情景:“留學生之愛戀法國,一半爲學問慾之難填,一半爲法國文化的優美,實有教人迷醉的魔力。”而身處法國,感受到“法國教育發達……高中學生,其智識程度,都堪與我們大學生相比,甚或過之”,於是“對於學問,遂更抱着一種熱烈的研究心”。⑧這當是衆多中國作家留歐的重要動機和追求。《棘心》的女主角思想開放,個性獨立,但《棘心》對於女性婚姻等個性解放話題卻“少了五四小說習見的激烈張揚,多的是新知識女性對於愛情的種種理性思考”⑨,顯示出與蕭紅(1911-1942)等“激進而徹底”的“女權思想”迥異的道德選擇:在深刻的自省覺悟而非盲目的傳統保守中、有着“對德行之美的崇仰”、“謙虛接納真知的無我不執,以及仰慕聖賢遇事虔禱的開放交託”⑩等,整部小說的文風也開放而溫和。 《棘心》展示的實際上是“五四”女作家的“另類現代性想像”:同屬於“五四”新文化陣營,審視着中國文化和民族性,關注女性命運,但無論對於傳統親情還是西方宗教,都能納入“愛”這個“五四”課題中。蘇雪林這樣的作家過去往往被視爲保守,但她其實“勇於走出舊時代家庭對於女性的桎梏,實踐自五四運動以來,追求人文自由主義的精神”,“樹立終身不懈追求生命、創作、閲讀、教學與學術研究的形象”。(11)其他“五四”旅歐作家大多也抱有這種心態:並非激進式的斷裂,而是在文化延續中的開放、變革。新月派、京派成員多出自旅歐中國作家,就說明了這一點。這使得在“五四”傳統激進變革的潮流中,也開啟了堅守文學本分、注重文化長遠建設的流脈,使得“五四”新文化傳統從一開始就是多源多流的。 “五四”時期的旅歐作家大多在學有所成後回國,不少人也有着異域寫作經歷,雖然難以歸入海外華文文學,不過他們感知個體生命、文化平和交融的創作取向成爲“五四”文學傳統形成中的一種建設性力量,不僅影響了日後的歐華文學,而且影響了日後中華文化傳統的海外傳播。而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後至1970年代長期留居歐洲的中國作家,由於他們的創作突破了東西方“冷戰”意識形態對峙,延續了“五四”新文化傳統核心價值的論述,以他們爲代表的歐華文學在此時期“中國與海外”文化格局的形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50-1980年代,不僅東西方意識形態嚴重對峙,即使在中國內地,受泛意識形態化思維的影響,“五四”文學革命後的創作觀念也逐步被壓縮成了“工農兵革命文藝”。但在歐華文學中,“五四”所開啟的現代意義上的“人的文學”和“自由的文學”得以堅持、發展,程抱一(Francois Cheng)、熊式一(1902-1991)、熊秉明(1922-2002)、趙淑俠(Susie Chao)、韓素音(Elisabeth Comber,1917-2012)等歐華作家的創作都富有“五四”文學精神。例如,1956年,熊式一將他早期的英文劇本《王寶川》(Lady Precious Stream)改寫成中文。這一被歐洲部分國家列爲中小學必讀教材的劇本改編於中國傳統戲曲《王寶釧》,而中文版本更大篇幅改寫了民間流傳甚廣的王寶釧與薛平貴的故事,充溢着“五四”的人文氣息:一是增寫了“賞雪作詩”一幕,使王寶川與薛平貴的相識有了慧眼識真的基礎。二是改寫了原先一夫二妻的結局,讓西涼公主與薛平貴以兄妹相處,不僅淘洗了傳統戲曲中的糟粕,也讓王寶川與薛平貴的情義更純真。三是劇中人物相國老夫人的塑造滲透出現代氣息:一方面,她是一位傳統的賢妻良母,信奉三從四德,“當父與夫不能兼顧的時候,她就捨父而從夫,若是夫與子不能兼顧,她便捨夫而從子”;另一方面,在對待女兒婚事時,開口“男子漢大丈夫,要是怕老婆,一定有出息的”,閉口“普天下的好家庭,都是婦女做主的”,溫慈和善之中透出十足的現代“女性主義”氣派,風趣中讓人會心而笑。四是劇中的西涼雖然是一個“所有一切的風俗習慣與我們中國的恰恰相反”的“古怪”地方,但西涼公主卻溫順賢良、善解人意,她幫助薛平貴登基稱王,在得知薛平貴家有結髮之妻後,不僅原諒了薛的毀約之舉,而且保護薛返回家鄉。這就使《王寶川》讚頌的人性、人情之真,傳統儒家貧賤不移、富貴不淫的堅貞情操更有了“全球倫理”的視野。又如,程抱一此時的散文,延續、拓展了西南聯大詩人群和“七月派”的人生精神。再如,始終視中國爲自己根之所在的韓素音的小說,在揭示世界動盪中東西方政治、文化複雜關係中,以包括儒道在內的中國文化意識表達出對人類黎明的理解和追求。這些均表明,“五四”傳統在海外得到了有力的延續和發展。 1980年代之後,歐華文學已足可與東南亞、北美華文文學相媲美。在這一時期,大規模的中國移民潮給歐華文學提供了豐富的作家來源,其中也包括了對中國大陸現有體制持不同看法而出走的作家。但是,借文學來宣傳其政治主張的情況在歐華文學中很少發生。在歐洲一體化進程時期,歐華文學始終以其深切豐厚的文學關懷回應社會,視“溝通”爲作家職責,使得“五四”時期開啟的堅守文學本分、注重文化長遠建設的流脈得以延續、豐富,成就了程抱一、高行健等文學大家,更養成了包括楊煉、林湄、虹影、鄭寶娟、呂大明、蓬草、綠騎士等來自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的一大批富有創作實績的“新移民”作家。例如,來自臺灣的陳玉慧(1979年留學法國,現定居德國),1990年代後出版了十餘部作品。她的長篇小說《海神家族》(2004)獲香港第一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2006)和臺灣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2007),並被譯成德文出版。該小說在臺灣女子“我”和德籍丈夫的回臺之旅中,多綫索交叉地講述了臺灣移民和殖民的歷史。作者海外女性視角中的家族敍事,使臺灣歷史在去蔽除魅中得到了豐富呈現。這是臺灣本土作家的創作難以匹敵的。 總之,恰如瑞典華文作家萬之在《諾貝爾文學獎傳奇》中所言:“挖掘文學之美,維護詩歌之美,就是最高的倫理。”(12)歐華作家在各種政治盛行時期都顯示出對人性的深刻關懷,其創作人文氣息濃厚,並以形式多樣的有效探索表達出文學的力量。這種努力,也使得包括“五四”在內的中華文化傳統與西方文化的對話得以成功展開。 歐華文學對中華文化做出的最重要貢獻,是它身處近現代以來對中國最有影響的西方文化環境中,“不斷地在其本源文化積澱中最精華部分與‘他者’提供給他的最精彩的部分之間去建立更多的交流”(13),從而既將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提升爲人類普世性價值而使之得到世界性傳播,又在中華文化的現代轉化中豐富了中華文化傳統。 與東南亞華文文學相比,歐華文學無需承擔以傳承中華文化傳統來凝聚族群力量、抗爭民族壓迫的重任。旅居海外的狀態,還可以避免華文主流(華人主導)社會常常發生的政治、經濟等現實功利需求對振興民族文化傳統的制約和壓力(例如,1950-1970年代,臺灣當局對傳統儒家倫理的大力倡導,大陸對孔子學說進行的革命性批判)。尤其在1990年代之前,中華文化在歐洲遠未被民衆關注,華人作家是從內心生發傳承中華文化傳統的願望,甘於寂寞地耕耘於民族文化,往往較長時間處於“隱居”生活,但也由此成就了歐華文學對中華文化傳統價值的重新發現和提升。 這種發現和提升,首先在於對中華文化多源多流價值的把握,尤其是對被歷史遮蔽的文化傳統的開掘。與東南亞華文文學中儒家文化主導性影響不同,歐華文學中中華文化傳統的影響更爲多源。以往人們多關注高行健創作中“以老莊的自然觀哲學、魏晉玄學和脱離了宗教形態的禪學”爲代表的“純粹的東方精神”(14)的重新發現,其實他對非儒家正統文化的傳統的開掘,源自他對文學自由精神的追求。他一直主張“一種冷的文學”,作家“置身於社會的邊緣,以便靜觀和內省”,寫作也純然是“精神自救”,“以區別於那種文以載道,抨擊時政,干預社會乃至抒懷言志的文學”。(15)例如,長詩《逍遙如鳥》(2009)追求的是看透“這一片混沌”的澄明通透以及“飛躍泥沼,於煩惱之上,了無目的,自在而逍遙”的超脱自得的境界。這種境界,是卸卻一切心靈重負的自由自在寫作:“從冥想中升騰,消解詞語的困頓,想像都難以抵達。”另一首長詩《游神與玄思》(2011),也以大鵬高高遨遊的形象,在戲謔“上帝”、“魔鬼”、“伊甸園”中表達“守住內心”,“了卻妄念,抵達一個人,所能的極限”的曠達胸懷。高行健所希冀的這種文學境界,延續了從魏晉玄言詩開始萌芽,經唐、宋、元諸多名家充滿禪味的山水、隱逸詩,直至明清“性靈”說等的傳統,但展現的是現代人的心靈自由。應該說,歐洲的文化環境使他得以實現自由寫作的心願。 高行健對另一種中華文化的重新發現,還聯繫着他對民間文化傳統即小傳統的關注。1956年,美國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R.Redfield,1897-1958)在他的《農民社會與文化》(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中首次提出“大傳統”與“小傳統”這一對概念時,意在說明複雜社會中往往存在着不同層次的文化傳統。而中國人類學家李亦園則結合中國情況說道: 所謂大傳統是指一個社會裏上層的士紳、知識分子所代表的文化,這多半是經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所產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 culture);而相對的,小傳統則是指一般社會大衆,特別是鄉民或俗民多代表的生活文化。這兩個不同層次的傳統雖各有不同,但卻是共同存在而相互影響,相爲互動的。(16) 以往作家關注的重點往往集中於大傳統文化,即便在“五四”倡導“人的文學”之後,啟蒙現代性關注的也往往是用大傳統去影響小傳統。然而,從傳統與現代的角度看,大傳統較易接受新的變革觀念,體現出與“現代”的緊密聯繫。這種聯繫,也使它易受居住國社會的現代性變動影響而發生變化。而生存於民間的小傳統,雖然受到大傳統的制約,但有其獨立性。尤其是它更多地通過日常的、感性的生活形態密切聯繫着“過去”,即使在發生劇烈的社會變動,大傳統受到巨大衝擊時,它仍能保持某種穩定,因而有着更頑強更恒久的傳承力量。而且有意味的是,“小傳統的延續在很多方面是通過底層社會的活動來實現的。換言之,傳統中國的‘下九流’者,如樂戶、優伶、算命者等,通過各種社戲、儀式、卜卦活動,將一些被大傳統所定義的價值和行爲取向傳遞到民間社會。即便在許多人認爲傳統已不復存在或處於不斷被再創造過程中的今天,這些價值仍然頑強地延續着”(17)。 高行健的創作是非常自覺地展開這一點的。他將“民間文化,從多民族的神話傳説、風俗習慣到民謠、演唱、說書、舞蹈、遊藝,乃至由祭祀演變而來的戲曲,以及話本小說”等視爲“中國古典文學中最富有創造性的作家和作品”的重要“來源”。(18)長篇小說《靈山》多畫面展現了少數民族、民間文化所保留的豐富世界:“我”作爲“民歌採集者”,遊歷彝族村寨、凱里苗族區、神農架山地的吊樓山洞、寺廟道觀,參與對歌、賽龍舟等民俗活動,採集到民歌、巫術、神話傳說,由此展開對民族“始原”的想像,尋回種族失落的根源。他的戲劇創作更一以貫之地展現民間文化的頑強和豐富。早期劇作《野人》中出現的歌隊、舞蹈,就是對長江流域山地族群的婚嫁、祭祀文化中傳統的展現。《冥城》(1991)取材的着眼點是民間傳說,而在表演形式上加入了古今諸多民間戲曲的趣味表現,包括來源於遠古祭祀傳統的儺舞、京劇臉譜、川劇變臉等地方戲曲特色,高蹺、雜耍、魔術等民間娛樂方式等,與角色演員的表演一起形成“一種大格調的儀式和劇場性”。(19)這不僅恢復了現代戲劇所喪失的娛樂和遊戲功能,更在大大增強演出的感知色彩中凸顯了民間文化傳統的活力。另一劇本《山海經傳》(1989),在以七十多個天神的登場展現從女媧造人到大禹一統天下的歷史時,意識到“中國遠古神話豐富多彩不亞於古希臘,可惜被後世居於正統的儒家經學刪改得面目全非”;爲了“恢復中國遠古神話的那份率真”,劇作借用擺地攤、賣狗皮膏藥、耍雜技、弄木偶皮影等民間賣藝方式,並參考苗、彝等少數民族和荊州、蘇北等地民間“且說且唱、似誦非歌的各種方式”,諸神扮相表演更“借助於抹花臉、戴臉殼、插翎毛、舞刀槍……翻筋斗、走鋼絲”等數十種民間演藝方法,這一切都“切忌落入唐宋以後宮廷和世俗的趣味”(20),從而回到《山海經》時代民間傳說的古樸率真。 “失去了大傳統的文化制度,民間所遺留下來的小傳統文化則不但抵擋不住社會轉型的壓力,本身所能發揮的文化功能也十分有限。”(21)所以,大小傳統應相互依存、補充、滋潤。高行健的創作正是將道教、玄學、禪宗等“經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所產生的精英文化”與民間生活文化互相滲透,從而呈現中華文化傳統的活力。三幕八場現代戲曲《八月雪》(1997)將禪宗六祖慧能(638-713)作爲禪宗革新中的思想家來展開他的一生。慧能出身平民,“斗大的字不識一個”,又被“放逐”到蠻荒之地的嶺南、海南,然而他堅守本心,入門八月就能悟出“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台,佛性常清靜,何處惹塵埃?”抵達“到彼岸都是大智慧,發平常心即是大慈悲”(22)的生命大自在。劇作突出了來自民間的慧能如何依靠內心的力量,得到五祖弘忍(601-674)信任,傳法於他,他也窮其一生普度衆生,成爲大哲人,由此顯示了高行健所尋找的另一種中華文化所交織的民間和“上層”文化傳統。 如今研究者都已知曉,高行健《靈山》中的“我”、“你”、“他”表述的實際上是同一主體的感受。當小說敍事人物面對中國文化中久被遮蔽的那部分時,產生了複雜的感受,以至於要用“我”、“你”、“他”三個人稱相互轉換表達纔行。但即便這樣,仍有難以溝通之處,所以《靈山》中又出現了“她”,暗示敍事人物要竭力走入“中國長江文化”而不如意。如果說歐華作家在面對本民族文化久被壓抑的部分尚且能產生如此複雜的感受,以致頻繁地轉換視角;那麽,當他們面對有着自身穩定結構的西方異質文化時,其“跨文化”對話會更艱難。可恰恰是這種對話,使得中華文化得以提升並在獲得世界更大敬重中得以傳播。 一位旅歐作家在21世紀初曾經感歎,近三十年興起的許多新價值,“本是我們的固有思想”,我們“對這些新價值並不感到陌生,甚至應當有自然的親和”;然而,“這些新價值又一次在西方形成。而我們又一次被動接受……”(23)從“我們的固有思想”中產生出“又一次在西方形成”的“新價值”,正是“傳統的現代轉換”所產生的人類性價值。事實上,歐華作家的寫作一直致力於中華文化傳統與世界文化潮流的對接。這種對接,不是被動地回應西方文化潮流,而是積極主動地展開中華文化傳統核心價值與西方文化的對話,在兩者交流中提升人類普世性價值,把握世界文化進步的潮流。程抱一(原名程紀賢,1948年赴法,2001年成爲法蘭西學院成立三百餘年來第一位亞裔院士)致力於“本源”與“他者”兩種文化精華之間建立起生命感受交流的寫作,最能代表歐華作家的這種努力及其取得的成就。 對於程抱一提出中國本源思想的一個核心是老子明確宣示過的三元思想,學術界已做過不少研究。但是,有兩個重要問題沒有論及:其一,程抱一是在對整個中華思想史作全面考察的背景上展開道家“三元”思想研究的。他明確地意識到,儘管“在中國思想發展過程中,道教思想一直與儒家學說相抗衡”,但儒家學者提出的以人爲中心的思想也是三元的:“‘天’即‘陽’的概念,‘地’即‘陰’……‘人’必須循‘中庸之道’而行,以構成‘天地’之組合中的第三方”,“道家的沖氣,即儒家的中庸”;(24)所以,三元思想是道家和儒家共同之道。它強調了支撐生命世界的是“彼此間的緊密相連”,是“中國思想所奉獻的理想化的世界觀”。(25)其二,程抱一對中國文化傳統精華更深入的把握是在與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展開的。他高度評價中國文化傳統,但也切實認識到中國文化傳統的欠缺,“衹有滋生於真‘二’的‘三’纔是真‘三’”。儘管中國藝術家(中國美學)在敞開胸懷與生命宇宙對話時,達到了真“三”的意境,但中國歷史及其“危機之境”表明,“中國歷來因爲未能創造真‘二’的條件,也就是說未能給予主體以絕對的尊嚴與權利,所以,它所達到的‘三’,往往衹是妥協,衹是折中;而妥協與折中乃一種‘次二’,根本不能創造使‘三’滋生的條件”。中國思想在源頭上推崇“天人合一”,這一思想包含了人與自然共處的極高智慧,但也導致古代思想家尚未嘗試把主客體區分,從而未能具體系統地探測、分析、把握客觀世界。而在人作爲主體的問題上,儒家雖然給予“人”以至高的尊嚴地位,卻“過於把個人置於社會組織的人際關係中”,無法對“人”作爲主體的存在本身展開充分而切實的思考。同時,儒家偏向“性善論”,“未曾正眼面對人性由於具有智力與自主而包孕了‘至惡’可能的嚴峻問題,也未曾推出和發揮法權觀念來保障主體的存在”。(26)這是中國未能創造“真二”條件的思想根源,不僅阻礙了真正實現“三”,而且還會走入難以化開的“一元”的“混沌”。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程抱一充分肯定了西方思想家從二元的邏輯出發,區分“主體”和“客體”。這是西方思想成熟的重要標誌,人們得以系統地觀察和分析問題,進而在人類內部確立了“主體”和“權利”的概念。這一“整個人類的財富”,“是所有非西方國家所應該吸取的”,更是“邁向真正現代的中國”需要重視的。但他同時又指出,長期推崇“二元”思想的西方也不能停留在“二元”論層次上,因爲“二元”是對立的,需要超越“二”,讓“三”成爲“開向無限的生命之道”。(27)西方藝術思想也加深了程抱一對“三元論”的思考。例如,他意識到,拉康(J.Lacan 1901-1981)“真實、想像、象徵”的“三領域說”與道家“陰、陽、沖氣”的“三元說”有着精神上的暗合相通。至此,程抱一將三元論這一“中國思想所奉獻的理想化的世界觀”提升爲人類的宇宙觀。 從世界文明的角度看,西方文化主要是指歐洲文化,與中國文化有着先驗的不同,但又是互相認識自身最重要最有意義的對話夥伴。近代以來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幾乎都無法離開歐洲爲代表的西方文化與中國、印度等爲代表的東方文化之間的交流。程抱一展開中西文化交流視野的開闊,在於他看待文化不作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這種簡單而固化的區分。在程抱一立足人類、放眼世界的胸襟中,中西被看作交流、對話中的世界,傳統與現代也成爲人類社會變革中並非衹是斷裂、隔絕,更有着延續、對接、轉化等不可分割的過程,現代性存在於中西雙方的對話、交流中。如果說,“傳統”被程抱一視爲世界多源並存中形成的區域文明,那麽,“現代”就是區域隔絕被打破後,世界各國、各民族交流越來越頻繁而產生的文明進步。“對話”與“溝通”始終是傳統與現代的主題,交流本身就讓人不斷擺脱束縛而豐富、提升自己。但程抱一也深知,“文化之間的真正對話是多麽困難”,“對話要求對話者超越表面差異,要求他們接受進入個人存在的深層,那裏纔是生命提出基本的極限的一些問題的所在之處”,而文學藝術是“進入個人存在的深層”最有效的途徑。(28)這是程抱一選擇文學創作最根本的緣由。 程抱一從1960年代開始寫詩,自言“我的詩是以‘溝通與對話’爲主題”。從第一部詩集《雙歌》“與有生宇宙各基本元素之間的對話”,第二部詩集《韻曲曲韻》“擴大了的與大地之間的對話”,一直到後期詩集《沖虛之書》(2004)“圍捕有生宇宙中各元素間所產生的生命意義”,都在表明,“唯有在這間隔地盤上所產生的‘交互’纔永遠是新鮮的”。(29)“交互”的最高境界是“真三”,那就是他在詩集《萬有之東》(2005)呈現的“超越‘萬有’之外,超越東、西之外,超越一切之外的‘東’,這是一種包容一切的境界”(30)。他的新詩集《真光出於真夜》(2009)以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藝術功力所表達的“真光,從黑夜裏噴湧而出;真夜,孕育噴湧而出的光”(《夏娃》)的“創世記”景象呈現了“光”與“夜”雙重存在的真相,它們各以其“真”互依互存,啟發每個人在自己與天地萬物交流的思考中實現生命大開。 程抱一在詩歌創作取得豐碩成果後纔轉向小說創作,是“渴望能夠以一種更持久、更意味深長的形式”,釋放“充滿啟示”的“歲月積澱”。(31)這種釋放,恰恰是用中國傳統思想嘗試解決包括現代西方在內的人類共同的困境,因而一次次在歐洲讀書界引起強烈反響。 《天一言》(1999)是程抱一創作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出版當年即獲法國極有影響的“費米娜文學獎”,也是21世紀在中國大陸影響最大的歐華文學作品。法國是“大河小說”的誕生地,而《天一言》這部法籍華人作家的“大河小說”以長江、盧瓦爾河、黑龍江三條亞歐大江的綿延不斷,呈現主人公趙天一生生不息的生命體驗。小說的敍事方式非常獨特,由“我”(天一留居法國時的中國友人)講述天—1982年在中國一間收容所裏所回憶的往事,而“天一言”肇始於午夜的“叫魂”——天一感到自己的靈魂與肉體分離,從此,“我身上的一切都將是錯開來的”;小說結尾的敍事中,又奇異地發生了“我看見天一;我看見自己”。從“叫魂”對生死界限的模糊,到“我看見自己”的個體生命感知,都暗示出《天一言》的全部敍事都是從生命源頭發生、綿延。小說的最後一段話是: 那肉眼看不見的元氣,既然它是生命之源,便不會忘記這塊土地上的一切經歷——無盡洶湧夾雜着無窮滋味。元氣也有那樣多的懷念,自然會再回來的,在它想要的時刻,在它想要的地方。 而那支“永不放開手中的筆”,將讓生命“連綿不斷地暢流下去”。生命的永恆正是存在於來自生命源頭的寫作,而《天一言》正是以“語言的力量”實現對生死二元的超越,達到生命的永恆。 程抱一的第二部小說《此情可待》在2001年出版當年便獲得法蘭西學院頒發的“法語文學大獎”,這也是該學院三百多年來第一次頒獎給亞裔作家。這部再次被法國文學界視爲“傳世之作”的小說講述的是明末時期一對情侶的兒女私情,由此展示“人類精神潛在地具有的最高境界:開向無限,開向永恆的神往境界”(32)。小說的男主人公道生原在戲班演奏二胡,與趙家二爺之妻蘭英相遇生情,後來他漂泊江湖,占卜行醫,以“愛情與藥物的結合”,使重病的蘭英得以康復,又在二爺勒死蘭英之際,以“手心如一的超我之境”使蘭英“死而復生”。程抱一將兩個無名男女對於“永恆之愛”的追求置於東西方文化對話的語境中。先是在《前言》部分虛擬了一個在巴黎羅岳蒙修道院舉行的“以不同文化間的交流爲主題”的討論會,一位在中國度過漫長歲月的老漢學家從中國帶回來明末手稿《山人敍事》,記述了道生和蘭英“所經歷的激情”,藉此說明《山人敍事》恰恰是借助男女之戀體現的“愛的永恆”這一“堪稱‘無時間性’的主題”來“超越時代的局限”。(33)小說正文兩個“激情”高潮的關鍵時刻也安排了道生與歐洲傳教士的交往。一是中秋夜蘭英赴約私會道生,相約“今生今世,以至來世,都永遠在一起”,身體得以淨化,心中全無雜念;而在兩人心靈契合的重要時刻前,道生行醫結識了傳教的異國人,雖然道家和基督雙方信仰差異巨大,卻在“真愛”問題上能毫無阻隔地交流:“真愛、至愛”“出自我們又超越我們”。產生於男女兩方卻又超越雙方的“真愛”,寓意了“三”的精神世界。二是道生救活蘭英後卻無法再見蘭英,孤寂泣血,他要“去聽聽那個一口說‘愛’的異國人的話”;異國人對道生和蘭英的相愛表示了理解、同情、讚賞:“他們之間尚有許多事難以交流難以理解。互相注視時,卻有巨大同情迴旋在沖虛之氣所開啟的空間。”(34)這“沖虛之氣”,寓意了不同文化“互相注視”而生的生命真愛。 程抱一最新創作的小說《游魂歸來時》(35),從“荊軻刺秦”的歷史“積澱”中激發出“友情和愛情是否能並存?‘三’的關係是人類所能及的嗎?”這一人類生活的根本性問題的答案。內容與形式的密切融合,使它又一次印證了程抱一的深切感悟:“美的作品總是產生自某種‘(二者)之間’,它是一種‘三’,它從相互作用的兩者之間噴發而出,使得兩者都能超越自身。”(36)小說分爲“五幕”,每幕由合唱和小說人物的獨白組成,講述春娘、荊軻、高漸離“生來就是爲了彼此相遇”的故事,人物各自的獨白有着潛在的對白,每個人都透過其他人看到生命的不同景色,三個人不是被限定在三角關係中,而是存在於生生不息的生命循環中,有無窮的可能性和衍生萬物的力量。爲了制止“始皇帝肇始的非人性專制將會久久地被許多皇帝效仿”,荊軻、高漸離相繼刺秦身亡,三十多年後,他們的遊魂回到春娘身邊,愛情的激情和友情的延綿性而生的至真至美的情感呈現生命自由的至高境界。這部小說以詩化的東方語言證明,“藝之大者在於傾聽自身靈魂與天地之魂的感應,並讓他人也能聽到這種感應的共鳴”(37)。推開來看其他歐華作家作品,人們會感受到,程抱一的創作不是孤立的,他有着衆多同道者,這正是歐華文學的迷人之處。 海外華文文學是“靈根自植”的中華文化,即海外華人憑藉自己的力量,使原本多源多流匯合的中華文化在不同地區、國家中自成傳統。這種“靈根自植”,也使“中華性”成爲一種不斷展開中的開放的生命進程。與東南亞華文文學作爲華人族群、社區的代言人不同,歐華文學從形成伊始就呈現一種“散中見聚”的狀態。一方面,旅歐作家散居於歐洲數十個國家,這種“散居”狀態爲歐華作家內省、獨思創造了前提,從而形成歐華文學藝術追求的不同層面;另一方面,歐華作家作爲個體雖然處於“孤獨”之中,但從個體生命感知出發的中華文化傳承往往更多呈現“在地”生產——有孜孜不倦追求超越於中西兩元之上的藝術至高境界的,有心存漢思但又關懷居住國人民的,更有在文化差異中渴求美的實現的。 定居荷蘭的女作家林湄1990年代的小說《漂泊》、《浮生外記》等就表現出相容併納東西方文化的開闊視野。2004年,她出版長篇小說《天望》,利用自己的邊緣視角,通過巧妙的構思,在深刻繁複的探討和追尋中,力圖解答關於人之存在意義的終極命題。小說設置了兩條主綫:一條是通過女主人公微雲來刻畫華人移民的邊緣狀態,另一條是通過弗來得牽扯出海倫和羅明華的故事。海倫父親曾留學國外,幼時受基督教影響,後來成爲教徒;羅明華是個歐洲混血兒,也是基督教的教友。這兩個人物的人生軌迹是邊緣性的最佳詮釋,而他們的最終選擇也強化了整個小說的主題。《天望》結構新異,以微雲和弗來得兩條互相交織的主綫串聯起小說中的其他人物,類似《水滸傳》式的嵌套型結構。整個故事分成長短不一的五大篇,以傳統的五行(水、土、火、金、木)命名,既有中國特色,又形象地概括了情節發展的五個階段。小說敍事筆法細膩,而敍述中穿插了大量思辨考問和議論化的心理描寫。儘管小說藝術空間是否支撐得起這些思辨追尋還有待努力,但《天望》的哲思傾向是明顯的。2014年,林湄又出版了六十萬言巨著《天外》,繼續其超越現實的對人性、自我終極的探尋。由於她挑戰“讀者不喜歡用腦又無法靜心,習慣一目十行的閲讀法”,也不相信“世上有絕對的、權威的、公義無私的文藝批評家”(38),注定了該書所表達的實驗性。全書分《慾》、《緣》、《執》、《怨》四篇,五十五節的標題皆爲《原我、舊我和今我》、《生命本質源於“性”》那樣的形而上思考或《“家”就是家人家務和家事》、《活的真諦就是勞苦愁煩》那樣的日常感悟。小說以郝忻、吳一念夫婦的留歐經歷爲主綫,展開新移民在歐洲的心靈歷程。他們都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第一批大學生,畢業後不久出國,在“異鄉生活清靜無喧,人際關係單純少慮”而又“言論自由、無人監管、秉法行事、全民福利”的環境中,郝忻迷上了浮土德(Faust),一心要寫一部“探究浮士德、堂吉訶德與賈寶玉、孔乙己、阿Q精神的異同”的“傳世之作”,雖然也被妻子拉入21世紀中歐經濟、文化交流大潮,但始終要從歐陸的歷史和精神沉積中探究信仰。小說穿梭於商界、家庭等慾望實象與思考人類生命深度的“天外”視角中,充滿靈魂的悲欣,也在中西文化交流等問題上發人深省。 林湄的創作大致代表了歐華作家中自甘寂寞、潛心於超越現實的哲思努力,這種努力最終指向超越於中西兩元之上的藝術境界。僅就女作家創作而言,在旅法女作家中,呂大明的散文“如屈原的詩一般”(39),呈現出自然心靈化、人文歷史化的美境;蓬草的小說有如她自己說的,“是真真正正的以四海爲家”,在展示生活“無窮無盡的可能性”(40)中充滿了對人的自由的渴望;黎翠華的散文充滿現代人對自在生活的尋求,是“現代”讓她明悟“傳統”,是“城市”驅動她去尋找“鄉村”,也唯有“遠行”纔讓她“回歸”;鄭寶娟把寫作視爲“一條朝自己內在掏剖、挖掘的冒險歷程”(41),筆下人物都有着海外生存環境強化了的人性沉淪、靈魂救贖。在旅居其他國家的女作家中,旅英的虹影小說,中西、華洋交織,糾結中呈現人性升華的豐富內涵;荷蘭的丘彥明散文,在異國他鄉將中國傳統的田園生活、隱逸文化表現得真切豐盈,又透出現代生活的熱情;瑞士趙淑俠的衆多作品,始終在體悟人類之情、人性之根中顯示出開闊的藝術視野……林林總總,藝術品質都趨於上乘,令人感受到歐華文學對中華文化的充實、豐富、補充和拓展。 “靈根自植”取決於在地化,這樣在異國的中華文化纔能扎根深,成果豐碩。不少歐華作家,如趙淑俠、楊煉等人的作品被翻譯成所在國母語,自然是歐華文學在地化展開的一種方式,而在地程度最深的當是以所在國家和地區非漢語的官方語言寫作。這些作家如果是雙語寫作,其非漢語作品又被翻譯成漢語,在漢語讀者中產生影響,就會是域外中華文化生存、發展的最佳狀態。早在1950-1960年代,熊式一、熊秉明的雙語創作就取得了重要成就,而如今歐華作家雙語寫作的更不在少數。除了程抱一、高行健這樣的文學大家雙語寫作,關愚謙(定居德國漢堡,爲漢堡州政府1956年設立“藝術與科學獎”後第一位獲此獎的華人)等前輩作家致力於中華文化典籍的翻譯外,一些較年輕的新移民作家雙語創作也成果豐碩。例如,山颯的八部法語小說,屢獲法國各種文學獎項,使得法蘭西既是“巴爾扎克的故鄉”,也是山颯的“家園”;(42)戴思傑的小說《巴爾扎克與中國小裁縫》獲法國“費米娜文學獎”,進入法國尋常百姓家;王露祿用荷蘭文創作了十餘部小說,在荷蘭文中融入豐富的中國元素;友友的英文長篇小說《鬼潮》等藝術感受力敏銳豐富,文學敍事常從極爲細膩的文字表現走向中西交融的知性表達等,都顯示出歐華文學在地生產能力的提升。當歐華文學不再是異國消費中華文化,而能在地“生產”時,它的生命也由此大開。兩種甚至更多種語言的對話,是不同文化生命源頭的對話,足以產生豐富雙方(各方)根本性的新的東西,中華文化傳統也必然獲得更大的豐富。 ①④黃萬華:《新馬百年華文小說史》(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第39—53、21頁。 ②[馬來西亞]許文榮:《南方喧嘩:馬華文學的政治抵抗詩學》(吉隆坡:南方學院出版社,2004),第8頁。 ③[新加坡]方修:《戰後馬華文學史初稿》(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總會,1987),第78頁。 ⑤[馬來西亞]黃錦樹:“‘馬華文學’全稱之商榷”,《星洲日報·文藝春秋》1991-01-19。 ⑥[馬來西亞]禢素萊:“開庭審判”,《星洲日報·星雲》1992-05-01。 ⑦⑩吳達芸:“高貴的人生抉擇——解讀女性自傳小說《棘心》”,《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1蘇雪林》(臺南:臺灣文學館,2014),陳昌明編選,第166、173頁。 ⑧蘇雪林:《棘心》(臺中:光啟出版社,1957),第179頁。 ⑨劉乃慈:“愛的歷程——論《棘心》的行旅書寫”,《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1蘇雪林》,第185頁。 (11)“小傳蘇雪林”,《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1蘇雪林》,第44頁。 (12)[瑞典]萬之:《諾貝爾文學獎傳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4輯。 (13)[法]貝爾托:“當程抱一與西洋畫相遇——重逢與發現(達·芬奇,塞尚,倫勃朗)”,《程抱一研究論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褚孝泉主編,陳良明譯,第142頁。 (14)[法]高行健:“文學與玄學·關於《靈山》”,《沒有主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第201頁。 (15)[法]高行健:“我主張一種冷的文學”,《沒有主義》,第1頁。 (16)李亦園:《人類的視野》(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第143頁。 (17)鄭萍:“村落視野中的大傳統與小傳統”,《讀書》7(2005)。 (18)[法]高行健:“文學與玄學·關於《靈山》”,《沒有主義》,第201頁。 (19)[法]高行健:“有關演出《冥城》的建議與說明”,《冥城》(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第100頁。 (20)[法]高行健:“有關演出《山海經》的建議與說明”,《山海經》(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第108頁。 (21)[馬來西亞]鄭庭河:“華族文化的自卑和困境”,《星洲日報》1999-10-24。 (22)[法]高行健:《八月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第128頁。 (23)趙毅衡:《握過元首的手的手的手》(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第45頁。 (24)(25)高宣揚、[法]程抱一:《對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張彤譯,第104、68頁。 (26)[法]程抱一:《美的五次沉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朱靜譯,第63頁。 (27)(29)(31)高宣揚、[法]程抱一:《對話》,第120—124、110、113頁。 (28)[法]程抱一:《此情可待》(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劉自強譯,第2、3頁。 (30)朱靜:“譯者前言”,《萬有之東—程抱一詩輯》(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7),第3頁。 (32)高宣揚:“愛與美——與程抱一的對話”,《此情可待》,第168頁。 (33)(34)[法]程抱一:《此情可待》,第5、145頁。 (35)(37)[法]程抱一:《游魂歸來時》(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裴程譯,第28頁。 (36)[法]程抱一:《美的五次沉思》,第108頁。 (38)[荷]林湄:《天外·後記》(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第557頁。 (39)呂大明:《流過記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第5頁。 (40)蓬草:《森林·自序》(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3),第2頁。 (41)鄭寶娟:“自序·有一個女人”,《三十歲》(臺北: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7),第2頁。 (42)法國前總理拉法蘭(Jean-Pierre Raffarin)之言,見山颯:《柳的四生》(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