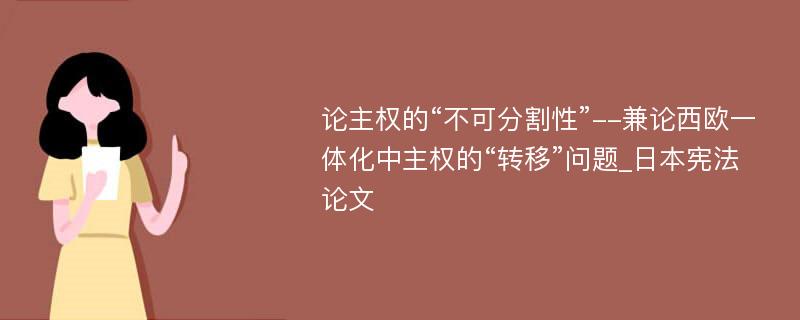
论主权的“不可分割”性——兼论西欧整合中的主权“让渡”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权论文,西欧论文,不可分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冷战后挑战主权的诸多理论思潮中,“主权让渡论”是比较普遍地得到认同的一种 。“主权让渡论”的理论基础,就是历史久远的“主权可分论”,而今天的欧盟,则几 乎无一例外地被引为“主权让渡”的成功典范。然而,笔者认为,主权并非“可割”, 也不可“让渡”。本文拟分析这两种观点的逻辑和历史谬误。
一
“主权可分——让渡论”的基本观点如下:主权不是质的、而是量的概念,因此具有 可增减性。主权有多种表现形式,如经济主权、政治主权、文化主权、金融主权、军事 主权、司法主权和信息主权等。(注:可参考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第267页;孙建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主权问 题上的不同战略意图”,《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1期,第34—36页;王沪宁:“文化 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第9 —10页;王铁崖:“第三世界与国际法”,《王铁崖文选》,邓正来主编,北京: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0页;黄琛瑜:《欧洲联盟:跨世纪政治工程》,台北:五 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第107页。)不同主权能够履行多种不同的功能。没有名义 和法理平等的主权。主权就像一个篮子,每个篮子里的东西不完全是一样的。大国和强 国的主权成分多些,小国和弱国较少。不仅不同国家的主权内容不一样,同一国家在不 同时期的主权内容也不尽相同。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导致主权含量变化的因素很多,如 人权问题和国际协定等。因此,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享有主权的标准不是一国应该怎么做 ,而是实际上怎么做。(注:[日]星野昭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当代国际关系理论 沉思录》,刘小林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380页;[美]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3页。Also see Mic hael Ross Fowler and Julie Marie Bunck,Law,Power,and the Sovereignty State-The Evolu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Pennsylvani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23-129;Stephen Gill,“Gramsci and Global Politics”,in Stephen Gill ed.,Gramsci,Historical Materialsi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11.)
主权既然“可分”,当然也就可以“让渡”。不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割让部分主权,建 立经济、政治联合体,谋求共同发展,实现区域甚至全球联合。欧盟就是“主权让渡” 的成功范例。40多年来,西欧国家通过主权让渡,把一体化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实 现了经济(如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统一货币、统一大市场等)、政治(如欧洲议会 等共同体组织和欧洲公民资格、共同海关等)、法制(如欧盟法律的优先适用性)、外交 等方面的整合,把合作从“外捆式”转变到了“内嵌式”,超越了邦联阶段,具有了国 际法主体的资格。欧盟正在向欧洲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建立“多民族”的欧洲联邦国 家奋进。欧盟发展的每一次飞跃都是成员国向其转让部分主权和国家职能的结果。正是 主权让渡造就了今天的欧盟。(注:参考付小随:“从欧盟看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主权和 职能的转移现象”,《全球化的悖论》,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第166—167页;邵景春:《欧洲联盟的法律与制度》,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9年,第262—265页;戴炳然:“欧洲一体化中的国家主权问题:对一个特例的思索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41页。Also see Martti Koskenniemi ed.,International Law Aspects of the European Union,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8,p.20;William Wallace,“The Sharing of Sovereignty:The European Paradox”,Political Studies,Special Issue,1999,p.506;Andrew Linklater,“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in the Post-Westphalian European State”,in Daniele Archibugi,David Held and Martin Kohler eds.,Re-imagining Political Community:Studies in Cosmopolitan Democracy,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14.)
二
“主权可分论”混淆了主权与政治、管辖权之间的区别,从而给主权的正确界定制造 了困难。
早在18世纪,主权可分与否,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并成为18—19世纪国际法学界争 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例如,洛克(John Locke)眼中的主权就三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对 外权。(注:[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1996年,第5—16、82—91页。)劳特派特(Lassa Francis Lawrence Lauterpacht)认 为主权“可分”,但他又指出:“主权可分”只是一种“例外情况”。它涉及的只是一 国的主权受限制的情况。(注:[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默国际法》,王铁崖、陈 体强译,第1卷,第2分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第2—7页。)而主权 所受的限制不是对主权本质的限制,而是对主权行使的限制。(注:王铁崖:“国际法 与中国:历史和当代”,《王铁崖文选》,第366页。)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日耳曼帝国 的地位问题、1787年美国由邦联变成联邦,以及19世纪瑞士和德意志联邦的建立等等, 都引发了相关的讨论。(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第50—51页。Also see Lassa Francis Lawrence Oppenheim,International Law:A Treatise:Vol 1:Peace,London:Longman Group Ltd.,1995,p.108;Hideaki Shinode,Re-examinin g Sovereignty:From Classical Theory to the Global Age,London:Macmill an Press Ltd.,2000,pp.55—57.)但一战后,这种论调逐渐消失了,关于主权 的讨论转移到主权是否受限制这个问题上。(注:王铁崖:“国际法与中国:历史和当 代”,《王铁崖文选》,第365页。)
所谓管辖权,指的是国家有关机构根据本国的法律或政策,办理、管理或处理有关的 人、物及事项的权力。它包括各国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方面的权力,是国家主权的具体 体现,也可以称为国家的“治权”。(注:赵建文:“当代国际法与国家主权”,《郑 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9期,第115—116页。也有学者把治权定义为 国家合法政府行使主权的权力,包括对内、对外的各种权力,见金应忠:“国家主权的 最高权威不容动摇:评《浅议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问题——对欧共体(欧盟)特例的研究 》”,《国际观察》2000年第5期,第36页。)所以,经济主权、政治主权、军事主权、 司法主权、信息主权等等,实际上都属于治权的范畴。
主权与治权的关系历来是政治学研究和分析的重要课题。例如,博丹(Jean Bodin)所 列举的九种主要的“主权权力”,包括宣布战争和平权、铸造货币权和征税权等,其实 都是治权。(注:Jean Bodin,On Sovereignty:Four Chapters from the 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London:St.Martin Press,1992,pp.110-127.)卢梭(Jean-Jaque Rousseau)反对把主权分为“强力和意志,分为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分为税收权、司 法权与战争权,分为内政权与外交权”。他认为,这一错误源自未能形成主权权威的正 确概念,而仅仅把主权权威所派生的东西误以为是主权权威的构成部分。但这些被认为 是主权各个部分的那些权利都只是从属于主权的,并且永远要以至高无上的意志为前提 ,那些权利都只不过是执行最高意志而已。(注:[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5—39页。)
在主权和治权的关系上,笔者的观点是:主权和治权属于不同层次的权力。治权或管 辖权是国家宪法赋予国家具体职能部门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高于治权。而国 家的政权要具备统治的合法性,其宪法首先要维护和巩固国家主权。也就是说,主权高 于宪法。潘恩(Thomas Paine)早在《人权论》中就指出,宪法归一国国民所有,而不是 执政者所有,一国国民具有制订宪法的权利。(注:[美]托马斯·潘恩:“人权论”, 《潘恩选集》,吴运楠、武友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56、263—266页。) 现代国家的立法机构一般都依据人民主权的原则制宪。一国政权的更迭往往导致宪法的 修改或重制,但在许多情况下并不影响本国享有主权。例如,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 以来,阿政权和宪法几经变化,但阿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并没有动摇。可以认为, 主权、宪法和治权在权力的层级中呈从高到低的分布。一国主权的法律特征在于它是最 高的、最终的和最普遍的权力和权威。(注: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 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27页。)宪法是主权与治权的中介因素。 宪法以维护和巩固主权为目的,赋予有关机构治权,并由宪法及依宪法制定的各种法律 ,限定治权范围内的各项权力并相互制约。简言之,治权是由主权派生的权力。(注: 金应忠:“国家主权的最高权威不容动摇:评《浅议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问题——对欧 共体(欧盟)特例的研究》”,第36页。)
尽管如此,并不能说治权之和就是主权。原因在于:(1)主权是质的规定,治权是量的 概念,两者不能互相转化。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威来体现其主权。如果介入另一 个最高权威,就意味着主权的丧失。(注:摩根索指出,在同一领土内的主权不能同时 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权力机关,即主权是不可分割的。见[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 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39 7页。)因此,邓小平才说:“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注: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页。)治权作为一个 量的概念,则可以通过分权的方式来实现。例如,联邦国家中州的权力,就是治权的分 权,而不是主权的分割。因此,治权在数量上的增减并不能简单地得出主权增强或弱化 的结论。(注:陈舟望:“现当代挑战主权思潮批判”,《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 8年第1期,第42—43页。)(2)更重要的是,治权或管辖权并不能穷尽主权的意义。例如 ,主权在国际法上的意义,就不是治权之和所能涵盖的。卢梭说,主权权威只有一个; 我们分割它,就不可能不毁灭它。(注:[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第121 页。)主权的“可分割性”显然破坏了主权的最高属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造成这种误 解的原因在于,把主权本身同主权的行使、主权的表现混为一谈。正如克莱斯纳(Stephen Krasner)所言,“经济主权”实际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的异文合并,实际 上应该叫做“经济自主权”(economic autonomy)(注:Robert H.Jackson,“Introduction:Sovereignty in World Politics:A Glance at the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Landscape,”Political Studies,Special Issue,1999,p.432.)、经济治 权或经济管辖权。
三
“主权可分论”把主权定位于“功能”,忽视了主权的法理性,其逻辑后果是否定国 际法主权原则。
“主权可分论”有着明显的“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例如,克拉托克维尔(Friedrich Kratochwel)认为,主权就像罗马私法下的财产所有权,即私人占有、使用 和转让自己财产的权利。所有权的行使要有一些基本条件,如不能损害其他所有者的所 有权;所有权不是“自然”地发生,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罗马所有权制度的排他性原 则也与主权雷同:所有权空间上的排他性类似于国家的领土主权原则。财产所有者可以 任意地行使这种权利而不受道德的约束则类似于专制国家的统治精英滥用主权的现实。 在现实国际生活中,类似所有权分割的主权分割已经形成,例如,欧洲一体化就像一个 控制和使用有形财产的过程,而非主权从民族国家向超民族行为体“移动”。(注:Friedrich Kratochwel,“Sovereignty as Dominium:Is There a Right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in Gene M.Lyons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Beyond Westphalia: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State Sovereign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pp.26—28.)
“主权所有权化”理论中的“主权”,事实上指涉个别的治权或管辖权。这种论点解 构了主权,置主权的本质属性即法理性于不顾。其实,主权不是一种供交换的资源。从 法理上看,它是一种地位,是一种参与并同其他主权国家订立协议的权利。(注:Robert H.Jackson,“Introduction:Sovereignty in World Politics:A Glance at the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Landscape,”Political Studies,Special Issue,19 99,p.453.)
对主权的定义通常从三个角度出发:(1)主权是一个法理和政治的概念,是通向国际讲 坛和主权国家俱乐部的通行证,以此区别于非国家行为体;(2)主权是一种政治权力话 语,使之能够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3)主权是一种法理上的自由,意味着国家 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处理内外事务。(注:Michael Ross Fowler and Julie Marie Bunck ,Law,Power,and the Sovereignty State:The Evolu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p.92.)“主权可分论”定义主权的角度显然是把主权作为上 述的“政治权力”话语,从而忽略了其他两种涵义。
这种“简化论”思想对国际关系实践可能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可以设想,如果一个 政治共同体仅凭强大的“政权权力”就可以获得主权国家地位,那么,现存的国家体系 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台湾省学者吴嘉生认为,从国际法的实践看,国家权 力(国家之管辖权)最重要。面对“国家”之角色与定位的问题,不必去强调其是否具备 国家构成领土、人民、政府等法律要素,需要强调的只是其是否具备一般国家所享有的 国家权力。如果具有国家权力,无论外国承认与否,它都是一个“事实”国家。国家权 力,而不是国际法上的承认,才是判断主权国家的准则。(注:吴嘉生:《国家之权力 与国际责任》,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第2—4、13、24—25、59—63、 148、151、467—468页。)这是强权即公理的逻辑。此论的症结在于:否认了主权的法 理性内涵,即国际法或宪法上的独立。如果“主权”在功能上是“可分”的,当代的任 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注:日本学者星野昭吉的观点与此相似。 他说,今天的每个国家都不过是半主权国家或准主权国家,即任何国家都缺乏完全的自 治权力来为它们的公民提供安全、经济富足和国内治理。见[日]星野昭吉:《全球政治 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刘小林、张胜军译,北京:新华出版 社2000年,第88页。)然而,虽然世界各国都广泛地融入了国际生活,但主权并没有因 此而过时或“削减”。主权所受的内部或外部“限制”,并不能改变一个国家主权本质 上的独立性。这种“本质”,就是法律的本质。比较恰当的说法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 景下,国家权力的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但宪法的抽象权威并没有被削弱。(注:Daniel Philpott,“Westphalia,Authority,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Political Studies,Special Issue,1999,p.575;范士明:“主权原则和国际新秩序”,《国际政 治研究》1992年第3期,第52页。)所以,只要国际法还存在,主权就不会过时。“主权 可分论”对主权的量化处理,从根本上瓦解了主权“质”的属性,进而把国际法也推上 了断头台。
四
“主权可分论”的实质是主权相对论,结果将为西方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提 供理论上的依据,直接危害到发展中国家的主权。
“主权可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事实支持”就是所谓“完全主权国家”和 “非完全主权国家”。《奥本海默国际法》的两代修订者劳特派特、詹宁斯(Robert Yewdall Jennings)和瓦茨(Arthur Watts),都持这种观点。(注:罗伯特·霍尔顿认为 ,后殖民国家唯一依赖的是国际社会对其管辖国家身份的同意,而不是依靠有效地行使 管辖权。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弱”国家。See Robert J.Holton,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 State,Hampshire:Macmillan Press Ltd.,1998,p.105.)
历史地看,所谓“完全主权国家”,通常都指西方发达国家;而“非完全主权国家” 则是欠发达的弱小国家的专利。这种观点中有浓厚的现实主义意味。但是,二战后的一 系列国际法文件,如1974年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都确认了“主权可分 ”的原则。(注: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年 ,第797页。)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更从理论上区分了所谓“消极主权”(negative sovereignty)与“积极主权”(positive sovereignty):前者是一种形式上 的规定,即国家免受干涉的权利;后者是一种实质性的规定,即国家要努力成为自己的 主人。积极主权的内容与时俱变,消极主权的内容相对稳定。积极主权涉及的是多少( 程度)的问题,消极主权涉及的则是有无(质)的问题。享有消极主权的都是前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它们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国家,只是“准国家”(quisa-state)或“半 国家”(qemi-state)。这些国家在不具备独立治理的条件下贸然独立,结果使人民损失 了许多宝贵的利益,如经济自由、民主政治等。它们同正常国家的区别在于只有“独立 ”而没有“自由”,所以其主权不完善。相反,享受积极主权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则为主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做出贡献。积极主权是一种至关重要,但却一直被忽视 的机制。它不仅使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得以维继,也压制了这些国家内部的人权诉求和社 会经济发展。杰克逊进而否定了二战后的非殖民化历史。他指出,“在经典的国际法中 ,政府效能是主权国家的一个核心前提。但在二战后的国际法中,殖民政府的继承者就 是建立主权国家的前提。”他还认为,第三世界在二战后的独立依靠的是以自然法概念 为基础的主权原则,但对于完全主权国家来说,事实上的主权比法理上的主权更重要。 (注:Robert H.jackson,Quasi-States:Sovereignty,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d the Third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1,21—28,34,79.)
杰克逊的“积极主权/消极主权论”有着显而易见的危险性:他从“主权可分”这一前 提出发,质疑了国际法上的主权平等原则,进而否定了第三世界的国家主权。冷战后“ 人权高于主权论”、“新干涉主义论”的盛行,同这种论调不无关联。区别仅在于:“ 人权高于主权论”是规范性的理论,而杰克逊的理论更具经验/实证色彩。
五
欧盟国家的“主权”让渡严格地说是主权权力或治权的“让渡”。从长远来看,欧盟 一体化进程也有底线,那就是:一体化不能剥夺成员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归根到底,制 约欧盟成员国行为的仍然是民族国家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
“主权让渡论”与主权可分论有着同样的逻辑基点:主权是量化的、功能性的标准。 笔者认为,所谓“主权让渡”,严格地说只是主权赋予的管辖权或治权的“让渡”。从 逻辑上讲,如果存在让渡,则让渡对象也将享有主权,不同国家让渡主权的集合,便是 超国家组织乃至世界政府的逐渐形成,这显然与主权乃国家所有之根本属性相矛盾,因 此,这种被“让渡”的主权只是国家具体行使的权力。马克思(Karl Marx)说:“人们 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注:[德]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 的辩论: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第82页。)欧洲一体化的历程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欧洲一体化在二战后启动,三个 基本的原因就是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抵制两大阵营斗争的威胁以及修复德法宿仇。 (注:参考[英]温斯顿·丘吉尔:“欧洲的悲剧”,《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编 》,李巍、王学玉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页;[法]罗伯特·舒曼: “舒曼计划”,前引书,第9—11页;[法]让·莫内:“激发变化的催化剂”,前引书 ,第24页。Also see Harry G.Gelber,Sovereignty through Interdependence,Lond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pp.203-223.陈玉刚在总结欧洲一体化起因的三种主 要学说(新旧功能主义的利益自决说、政府间主义的国家偏好说以及交流理论和超国家 治理理论的跨国交流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利益说,可以作为参考。见陈玉刚:《国 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7—144页。) 一体化过程暴露出来的问题,最重要的特征仍是现实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
纵观二战后西欧整合的历史,从最初的三个共同体到欧共体,再到今天的欧盟,欧洲 联合的基础和核心主要是由欧洲经济共同体发展而来的欧洲共同体。这表明经济利益不 仅是欧洲一体化的基础,也是根本的驱动力。(注: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 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127—128页。)虽然欧盟规定成员国可以自行退出 联盟,但没有一个国家这么做。甚至连傲慢的英国和有着中立传统的瑞士也要丢下“面 子”跳进欧洲的“熔炉”,这并非简单地因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欧洲形成了一些共同的 准则,以及得到普遍认可的体系结构。(注: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 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邵文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 ,第444—445页。)最重要的原因是:脱离欧盟将损害成员国在欧洲的地位,从而造成 难以想象的经济损失。在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联合起来的欧洲或许能够和美国分庭抗 礼。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正式的框架来规范行为规则,消除阻碍了欧洲国家间经济和社 会交流的国内障碍,经济和社会的融合就不可能进行下去。(注:William Wallace,“The Sharing of Sovereignty:The European Paradox”,Political Studies,p.516.) 欧洲一体化中“自主自愿性”的原则,掩盖了隐藏着的“结构性”经济压力。所以,在 欧盟与成员国的关系上,也存在着手段—目的的逻辑。这种情况下受到限制的主权,不 能等同于主权受到侵蚀。
通过“平行四边形合力法则”计算出的不同的国家利益之和决定了“欧洲统一”的限 度。欧洲一体化基本的情况是,“超国家化”的结果总是以“取”与“舍”大体相符为 底线。例如,50年代讨论组成共同市场时,法国获得发展农业的补贴与德国获得工业品 的国外市场互为条件;80年代,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进行的所谓“一揽子谈判”同样是 有条件的,即需要各成员国增加财政摊款,减少英国每年从共同体领取补偿性的“回扣 ”。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不例外。欧共体1986年的谈判结果反映的就是成员国力 量的大小。(注:[美]安德鲁·摩拉夫塞克;“《单一欧洲法令》的谈判:国家利益与 欧共体传统的政治才能”,《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编》,第212页。)正如陈氏 民先生所言,欧盟要实现某种超国家的权力(而非主权),有现实的可能,但这种超国家 安排不仅在原则上,而且也在实践上绝不能损害国家个体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利益。( 注:陈乐民:“黑格尔的‘国家理念’和国际政治”,《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第139页。)
欧洲一体化虽然达到了国际一体化有史以来的新高度,但距离“超国家的联邦政府” 仍然相距甚远。欧盟在三个方面远远没有达到联邦制国家的要求:(1)没有真正的宪法 。欧盟虽然设立了立法机构(欧洲议会)、行政机关(欧盟委员会)和司法机构(欧洲法院) ,建立了欧盟内部经济、政治、文化和一般社会生活的秩序,并直接规定了成员国公民 的基本权利,但它们只不过是“宪法性条约”,还不是真正的宪法。(注:“宪法性条 约”有两层含义:(1)这些文件在表现形式上是条约,是不同主权国家通过谈判协商共 同制定的。(2)它们含有某些宪法规则的内容,这些规则缔造了欧共体—欧盟以及内部 机构,规定了机构的基本制度和秩序,在欧共体—欧盟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表 现出了类似于宪法的法律性质。参见邵景春:《欧洲联盟的法律与制度》,第37—40、 45—46页;黄琛瑜:《欧洲联盟:跨世纪政治工程》,第114—116页。)(2)没有中央权 威。欧洲议会实际上只起到提供咨询的作用,真正对立法负责的是部长理事会。欧洲法 院的司法权也非常有限,只限于欧盟三个支柱的第一个领域——三个共同体。而且,欧 盟法的效力并不及于欧盟成员国的一切领土、领水和领空。例如,《欧共体条约》不适 用于荷兰在欧洲以外的领地或主权控制,如苏里曼和安的列斯群岛;该条约也不适用于 丹麦的法罗群岛。(注:邵景春:《欧洲联盟的法律与制度》,第70页。)(3)从法律上 讲,欧盟成员国可以自由选择退出联盟。虽然欧盟规定欧盟法的法律效力优于各成员国 的国内法(见《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第41条、《欧洲共同体条约》第177条、《欧洲原 子能共同体条约》第150条),(注:参见欧洲共同体官方出版局:《欧洲共同体基本条 约》,戴炳然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19、179、320页。)但欧盟不 能阻止任何一个成员国退出欧盟,而联邦制国家一般不允许成员国退出联邦。(注:Robert H.Jackson,“Introduction:Sovereignty in World Politics:A Glance at the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Landscape”,p.453;王丽萍:《联邦制与世界秩序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24页。)这说明,欧盟一体化的机构要成为联邦 国家的机构,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欧盟的实践,仍然主要停留在主权国家间经济和政治 合作这一层面。毕竟,欧盟不能代替成员国履行提供公共产品这一民族国家最基本的职 能。
欧共体前主席德洛尔(Jacque Derol)曾就欧洲一体化的前途乐观地指出:“如果国家 感到它们在地理上、历史和价值观方面相互接近,必要时候它们应当统一。”(注:[法 ]雅克·德洛尔:“一个必要的联盟”,《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编》,第64页 。)他显然过于乐观了。即使是在欧盟国家内部,他也只代表比较激进的联邦主义。20 世纪80年代以来,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一直存在着新职能主义、新制度主义和政府间主 义之争。90年代的主导趋势,则是政府间主义和超国家主义逐渐合流。(注:参见张茂 明:“欧盟一体化理论中的政府间主义”,《欧洲》2001年第6期,第45—54页;王展 鹏:“国际关系理论,还是比较政治学:简评政府间主义与两种‘治理’理论在欧盟机 构问题上的分歧”,《欧洲》2002年第1期,第91—97页;房乐宪:“政府间主义与欧 洲一体化”,《欧洲》2002年第1期,第81—90页,等等。)联邦主义并没有太广阔的市 场。笔者认为,虽然欧盟实现了较高程度的一体化,欧盟国家的领土边界依然清晰,人 民在日常生活中也作为独立国家的公民存在。政府仍然主要是国家的。只能说在国家的 授权下,某些职能由超国家机构来行使。欧盟只不过是“主权国家的联盟”而已。(注 :See Robert H.Jackson,“Introduction:Sovereignty in World Politics:A Glance at the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Landscape”,pp.450-454;Magdalena M.Martin Martinez,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6,pp.66—67.)
而且,欧盟这种地区主义的治理模式,并不具备普遍性。欧盟国家有相似的历史、政 治文化价值和经济发展水平,现实中又没有巨大的利益冲突。并且,这些国家有着共同 的地缘基础和战略利益。这些,都是实现权力让渡或权力分享的必备条件,欧洲以外的 地区很难具备。
六
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联盟主义)之争。(注:邵景春 :《欧洲联盟的法律与制度》,第5—6页。)但无论联邦主义还是邦联主义,都对主权 作了功能化的处理。它们都忽略了主权的一个重要的非法理内涵,这就是民族文化对主 权建构的重要性。国家对全球化的强大适应能力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国家继续拥有绝 大多数人民的忠诚。(注: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Foreign Affairs,Sep./Oct.,1998,p.82 .)20世纪90年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矛盾现象是:尽管跨国治理日益多层次、日益 同复杂的制度相结合,共同体法律的权威性似乎已经明显地“腐蚀”了成员国的法理主 权,而且欧盟成员国在自己的疆界内已经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注:[英]戴维·赫尔 德等著:《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 。)但象征、忠诚和认同仍然根植于传统的民族国家制度,作为政治代议和责任的民族 象征和民族团结的精神仍然如故。(注:William Wallace,“The Sharing of Sovereignty:The European Paradox”,p.521;Pippa Nowis,“Global Governance and Cosmopolitan Citizens”,in Joseph S.Nye and John D.Donahe eds.,Governance in a Globalising World,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2000,pp.157 -158;Martti Koskenniemi ed.,International Law Aspec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pp.21—23.)
1995年诞生的欧洲联盟公民资格,只是一种不完备的、集体性的政治身份,即通过赋 予欧洲一体化普遍的价值和意义,给予每个成员一种分享的政治身份。但欧盟联邦化能 否成功,还取决于一种更基础、更重要的政治身份,即历史性的政治身份。它不能靠行 政命令或欧盟成员国首脑签订协议来实现,而必须把共同体置于一种历史连续中,给予 它一部历史,从而赋予共同体以价值。历史性政治身份的获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 是经济全球化可以催生的。但缺少这种身份,成员国的公民就难以认同欧洲。因此,欧 洲联盟公民身份的产生,从目前来看主要起着一种功能性的作用,即方便成员国公民在 欧盟范围内自由迁徙和居住,以便创造一个人力资源的共同市场。从这个意义上看,仅 有《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价值还远远不够。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发祥地,欧盟内 的几个起支柱作用的大国,如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都形 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抛开几个大国间的勾心斗角不谈,以经济全球化来同化 这些国家的民族文化,几乎无法想象。(注: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p.82.)显然,无论是布 尔(Hedley Bull)的“国际社会”,(注:see 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p.13.)还是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欧洲公民宪法”,(注:[德]于尔根·哈贝 马斯:“还有选择”,歧人译,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82—83页;[德]于尔根·哈贝马斯:“欧洲是 否需要一部宪法?”曹卫东译,《读书》2002年第5期,第83—90页。)都无法弥合国家 间文化认同的差异。直到现在,欧洲的一体化建设仍然缺乏天然的文化背景或合法性, 这已成为制定真正的欧洲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主要障碍。(注:Martti Koskenniemied.,International Law Aspects of the European Union,p.19.)布拉斯韦特(Alan Branthwaite)的看法颇有见地,他指出:创造统一欧洲身份的努力迄今为止没有多大起 色,最大的原因就是,欧洲身份被视为对现存国籍认同以及对国家传统和遗产的忠诚的 潜在威胁。(注:Alan Branthwaite,“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 Independent Statehood”,in Robert H.Jackson and Alan James eds.,States in a Changing World:A Contemporary Analysis,London:Claerendon Press,1993,p.60.)
因此,虽然主权既不可“分割”,也无从“让渡”,但“主权让渡论”为我们建构全 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提供了一个反面的启示:主权是历史的、变化的。随着历史的发展 ,主权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主权日益由一个一元的法理学概念向一个包含政治、文化 等因素的多面体转化。文化的认同在主权建构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