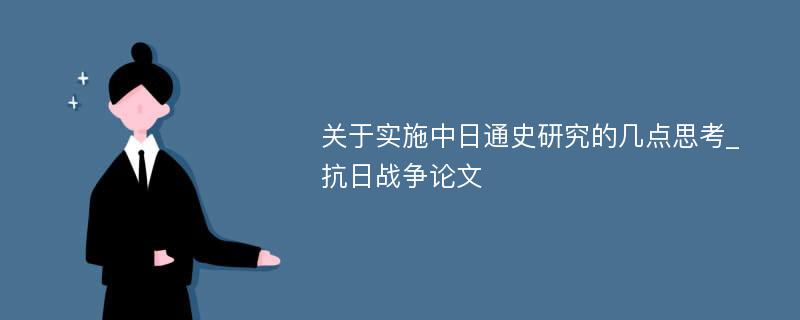
关于落实“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6)11-0068-04
改善中日关系“政冷”局面已经成为中日朝野的共识。除领土争议、东海能源开发等长期处于协商中的问题外,政治敏感性强、国民关注程度高、社会影响大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历史领域。在历史问题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长期性障碍的情况下,安倍晋三就任日本首相后访华,10月8日,中日双方通过联合新闻公报发布“年内启动中日学术界共同历史研究”,这将成为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突破口。
中日历史问题既包括日军在华遗弃化学武器等战争遗留问题,也包括右翼势力通过教科书歪曲史实、内阁要员否定侵略战争等历史认识问题。其中,教科书问题尤为重要,应该将改善教科书作为共同研究历史活动的成果与目标。改善教科书能够对历史教育、学术研究、社会舆论,特别是官方的历史认识产生直接影响,是改善中日政治关系的选项之一。我国应借鉴日韩历时三年共同研究历史活动的经验教训,参考法德、波德等欧洲国家共同研究历史、改善教科书的成功模式,向日方建议,中日共同研究历史与改善教科书相结合,以保障共同研究的实效。
一
中日共同研究历史、改善教科书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其敏感性主要牵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直接影响两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如果共同研究不能取得实效,有可能会加大甚至激化中日双方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韩日两国共同研究历史活动的教训值得借鉴。2001年4月,日本文科省审定通过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右翼教科书,并拒绝韩方的修正要求,导致外交僵局。金大中总统接受小泉首相的提议,两国于2002年3月发表“推进韩日共同研究历史计划”,2005年6月韩日共同研究历史委员会发表最终研究报告,活动结束。但是,其结果不但未能对改善日本教科书产生影响,而且也未能形成共同的“历史认识”,史实见解也存在严重分歧。韩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①将日本教科书歪曲历史、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激化韩日独(竹)岛领土争议等问题一起作为转变对日“平静外交”的政策依据。由此可见,共同研究不仅没有起到改善韩日关系的作用,反而产生很大的负面效果。究其原因,是韩国没有得到日方的明确承诺,将共同研究成果反映到教科书中。所以,改善教科书是中日共同研究历史的实效保障,是形式与效果的统一,如果不能落到实处,共同研究不过是暂时缓和两国政治氛围,转移外交矛盾的权宜之计,从长远来看,负面作用大于正面效应。
第二,直接影响海内外华人的民族凝聚力。在中日政府主导共同研究的前提下,如以欠缺实效的结果结束活动,难免在客观上对海内外同胞的民族凝聚力产生不利影响。2005年美、韩、朝、日、菲、荷等国与中国内地以及台湾等族裔社团的代表在洛杉矶联合发起“全球百万人签名”活动,要求联合国拒绝不能正视历史的日本“入常”,抗议书征集到全球4200万华人华侨的签名,6月30日由反对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民间组织代表在联合国总部递交安南秘书长。此举彰显了炎黄子孙不忘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民族凝聚力。此外,海外华人华侨还通过出版书籍、举办展览等多种方式记载这段国难史;向所在国家的议会提交议案,呼吁将日本侵略罪行写入历史教科书;②通过向杰出活动家颁奖活动来扩大影响;与大陆民众通过信息网络联结互动等等,在国际社会不断扩大影响。因此,中日政府有关历史问题的举措必然牵动海内外华人华侨的历史情结。
第三,直接触及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日本文科省对内通过审定指导教科书贯彻政府意图,对外宣称教科书制度不允许政府干涉,出版社“自主编撰”教科书。但事实并非如此。文科省审定的教科书直接宣示官方的“历史认识”,与“言论自由”的普通出版物有着本质区别。自1948年实施新审定教科书制度以来,教科书关于日本对外战争的表述几乎受政府审定意见的左右。文科省通过制订和修改《学习指导纲要》,直接指导教科书的编撰与审定,即日本政府完全能够在现行教科书制度内指导教科书编写者和教科书出版社,改善教科书内容。由于教科书可以直接反映政府立场,所以改善教科书具有正本清源之功效,可以直接影响教辅资料及课外读物,引导社会舆论。
中日共同研究历史如果与改善教科书相割裂将失去实效保障。姑且不论中日双方可能也如韩日那样,在最终研究成果中各持己见,即便取得某种程度的共识,在客观上既不能代表日本史学界,也不会对教科书产生影响,在压倒多数的否定日本侵略历史的出版物中,仅为“一家之言”而已。因此,只有将研究成果与改善教科书相结合,活动才能获得实际的成果。
二
中日共同研究历史改善教科书是一项相当艰巨的活动。但是,改善教科书的艰巨性与快捷性并存,困难与机遇同在。
首先,改善教科书的艰巨性在于,中日历史问题缠绕着现实利益矛盾,容易相互影响,恶化矛盾。一方面,由于日本侵略我国的历史最长、加害最大,化学武器等历史遗留问题至今未得到完全、妥善的处理等原因,形成中日间积怨久、隔阂深、民族感情严重对立的现状。另一方面,近年来,日本对华举措咄咄逼人。例如,推进钓鱼岛“国有”化、试图阻挠我国开发东海中方一侧能源、围绕俄罗斯能源与我国进行恶性竞争、将我军作为“假想敌”展开军事战略部署等。“敲打中国”已成为日本媒体的最大“卖点”。中日关系是两国媒体重点报道的对象,也是普通民众密切关注的焦点,容易引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所以,中日共同研究历史不得不面对多方挑战与困难,双方不能不做好充分的抗干扰准备,坚定不移地争取成功。
其次,改善教科书的艰巨性还在于冷战思维依然主导日本政坛。中日完全不同于法德,法德间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障碍,也不存在军事战略上的对峙。中日也不同于波德,波德间价值观差异较大,但改善教科书的门槛较低——德国教科书内增加关于波兰的表述内容是交流的重要成果。由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性质是不能正确表述历史事实,所以中日双方统一史实见解的难度很大,中日(右翼)学者之间的观点对立尖锐。如果日方出于冷战思维,选任不能代表日本史学界主流、否定侵略历史的右翼学者,与我方开展共同研究,或者以所谓价值观不同为口实,采取妨碍如实表述历史的举措,活动势必难以取得成果。这些因素都应引起双方注意,提前制订最佳运作方案。
最后,改善教科书的艰巨性还来自日本复杂的教科书制度。在现行制度下,日本政府同时审定多种同类教科书合格;学校从中选择一种使用;约有8家教科书出版社抢占教科书市场,商业利益缠绕其中;自民党通过各地教育委员会支持选用右翼教科书,与坚持和平民主教育的教师和市民团体展开学校选用教科书的争夺战;中韩等亚洲受害国抗议日本通过审定教科书歪曲殖民侵略的历史,日本右翼分子却大肆渲染中韩“干涉内政”。上述五个因素对教科书进入市场并最终被学校选用的过程产生不同影响。这是涉及日本内政与外交、教育行政和商业利益的综合性难题,需要长期、全面、艰苦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是,改善教科书的艰巨性与快捷性并存,困难与机遇同在。同为侵略战争的加害国,日本修改教科书的立场与德国截然不同。德国执政党将加强国际交流、改善教科书作为国家外交战略的一部分,而日本执政大党自民党的主流坚信,美化侵略历史是日本实施政治、军事大国国家战略的必由之路。20世纪50年代以来,自民党“文教帮”就是政界与民间右翼势力篡改教科书的策源地,现在仍然是其大本营。90年代中期发动第三次历史教科书攻势的政界力量,就是在日本现任主要领导人的召集下实现组织化的——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不仅是“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和“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联盟”等团体的成员,而且担任“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之会”的代表、“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的代理会长、“超党派议员联盟、思考历史教科书问题之会”的会长,可谓集政界右翼三大团体的最高职位于一身的核心人物。安倍首相当时担任“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联盟”和“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之会”两个国会议员团体的秘书长、“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的代理秘书长,同时也是“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超党派议员联盟、思考历史教科书问题之会”等政界右翼团体的骨干。③上述情况说明,改善教科书面临前所未有的艰巨性。但是,艰巨性的另一面则是快捷性:第一,因为自民党是与教科书问题有关的政界团体的核心和主流,所以拥有绝对的主导能力,能够直截了当地通过与其对话解决问题;第二,来自国内外的制约因素,例如,不同于党内的代表政府的公开立场、对抗在野党攻击特别是选举需要、顺应美国意愿改变亚洲外交困境等因素,促使安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军慰安妇问题上,承袭历届政府的“历史认识”。④虽然有媒体指出,安倍用“政府见解”为其真正的政治主张“加封”,⑤但安倍能够遵守“私”与“公”的客观限制,至少表明其目前改善中日关系的真实愿望。没有任何一届政权比安倍内阁在这个领域更有组织、号召和决策能力,更有发言权。因此,改善教科书的艰巨性与快捷性并存,困难与机遇同在。
克服上述艰巨性、抓住快捷性的关键在于,为中日共同研究历史活动制订双向改善教科书原则,即通过共同研究改善中日两国的教科书。
改善教科书的双向性源自法德、波德改善教科书的成功模式。按照国际惯例,改善教科书并非针对某一方。毫无疑问,日本教科书应该如实、充分表述加害我国的史实,同时,我国教科书也有必要改善。中日双方都有意见指出,我方历史教科书重视日本侵华史实的表述,而忽略二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事实。安倍来华访问前曾说,要向中国“讲战后日本的历史”,说是日本已成为“为和平做贡献的国家”,⑥中日联合新闻公报也写到:“日本强调,日本战后60多年一直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今后将继续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⑦此外,中日在经济上互补互惠的现状等等,也是应该让我国青少年理解的事实。
首先,改善教科书的双向性,体现我国平等睦邻的和谐外交。中日政府都有义务为共同历史研究活动取得预期成果制订平等的保障措施。与一味批判谴责、居高临下的态度相比,体现大国风范的平等姿态或许更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德国的经验证明,经过不同意见激烈交锋,到达理解并接受改善教科书建议的过程,恰恰是争取国内多数民众理解与支持的必需阶段。
其次,改善教科书的双向性,对排除日本国内阻力最有说服力。2005年我国几个城市发生民众抗议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入常”的示威游行,日方将此误读为中国进行“反日教育”的结果。这一误读至今得到政界的普遍认同,由此产生应该改变中国“反日教育”的紧迫感。这在客观上为日本接受我方建议,改善中日双方的教科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最后,改善教科书的双向性,有利于防止激化中日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的矛盾。如果将改善教科书的范围,从历史教科书扩大到地理及公民(政治)教科书,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效。例如,钓鱼群岛(日本称尖阁列岛)的主权归属、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等,可以采用两国都能接受的、缓和矛盾的表述方式写入教科书。2005年4月,日本文科省在审定初中公民教科书时,指导强化日本对争议领土拥有“领有权”的表述,一举将教科书问题从历史领域扩展到现实领域,引发日本与中韩等国之间的现实利益冲突。如何做到在教科书内既表达本国的领土主张,同时也表明两国政府通过和平协商方式处理领土矛盾,特别是中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立场,无疑有助于两国民众认识中日之间存在领土和海洋主权争议的客观事实,有利于防止损害国家利益的极端民族主义影响青少年甚至干扰政府外交。总之,通过改善双方的教科书,能够对社会各界产生导向作用,有效稳定和改善中日关系。
三
目前,日本多家教科书出版社在教科书市场展开激烈竞争,能否占有一定市场比率是决定其赢利或赤字的关键。各出版社运用其在政界、教育界、大众传媒等领域的关系网,千方百计地争取学校的选用订单。选用率低的教科书如果没有外来资金支援,将被淘汰出教科书市场。这意味着中日共同研究历史改善教科书活动的成败取决于两个阶段:其一是教科书的编写阶段,这一阶段决定共同研究成果能否反映到教科书的内容中;其二是教科书的选用阶段,这一阶段决定反映共同研究成果的教科书能否进入学校。只有反映共同研究成果的教科书成为大多数学生的课本,才意味着活动获得成功。
从教科书的编写阶段来看,按照国际惯例,共同研究的成果是,两国专家针对双方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撰写改善教科书的“共同建议”。但是,“共同建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保障研究成果切实反映到教科书内,也不容许一方的观点强加给另一方。这是第一阶段的局限性。为此,两国政府应该做到:在教科书撰写者、教师、教育行政官员中普及“共同建议”,将其落实到教科书的改善及教育领域。中日两国政府发挥指导作用对于克服上述局限性尤其重要。如果日本政府将“共同建议”写入文科省指导教科书编撰的纲领性文件《学习指导纲要》,并积极引导贯彻实施,则可以对改善教科书起到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在教科书的选用阶段,有很多因素影响学校能否选用反映共同研究成果的教科书:有教师、学生家长、各地教育委员会、地方议会及行政首脑、政党、政界组织、教育界和历史学界的相关团体等。其中,政界和各地教育委员会是两大重要因素,政界能够通过地方议会及行政首脑施加压力,各地教委则直接掌握学校教科书选用权。就现状而言,尽管扶桑社两个版本的右翼历史教科书受到强烈抵制而严重滞销,⑧但却出现了去“左”“右”而取其“中”的选用倾向,致使“模糊表述”日本加害史实的教科书销量大增,明确记载日本侵略史实的教科书失去大部分市场。所以,日本政府特别是支持美化侵略历史的国会议员团体,对于克服第二阶段的局限性至关重要。对此,安倍首相及自民党新任领导核心能够发挥无可替代的“解铃”作用。
四
共同研究历史、改善教科书活动,具有促进在战争受害国与战争加害国之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积极作用,具有其他交流活动难以与之比较的重要战略意义。
法德、波德的成功经验证明,改善教科书不仅发挥了遏制德国新纳粹否定战争罪行的积极作用,而且帮助德国与受害国实现了历史和解,是富有成效的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日两国政府只有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认识其重要性,才能站在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高度担负起组织和支援共同研究历史活动的责任,使其发挥改善两国政治关系、增强民众之间感情的重要作用。换言之,我们应该努力促使日方将“共同历史研究”这一缓和中日政治关系的战术性举措,转变为有实效保障的战略安排——中日共同研究历史改善教科书。
改善教科书是一项政府组织的民间工程,运作成功可以取得官民结合、影响深远的长久效果。学术界作为活动主体,对于化解两个民族间的积怨能够发挥民间外交作用。政府的组织与支援工作,赋予民间参与者以代表性和权威性,并保障共同研究的成果普及落实到本国教科书中,使中日双方在各自国内、双方之间形成垂直和横向的互动关系,以民促官、官民联动、两国朝野相互影响,与单一的官方或民间交流相比,渗透力强而阻力较小。遴选具有高度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中日学术界人士,组成“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其研究成果自然具有国际权威性,中日双方共同撰写的改善教科书的“共同建议”,不仅能为出版社编撰教科书提供导向与依据,而且能够有效遏制日本右翼分子美化侵略历史的活动。
注释:
①“日韩委员会最终报告序文(要旨)”,《朝日新闻》,2005年5月7日第4版。
②例如,由华人王裕佳组织的加拿大战争史维会,在2004年和2006年两次组织35位加拿大历史教师与教育界人士到南京、北京等地参观,访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及被日强掳的中国劳工。2005年9月,安大略省教育厅决定,该省900多所中学将载有侵华日军所犯罪行等内容的教科书作为历史必修课,当年史维会首次成功地将包括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和细菌战等内容的日本侵华史实,写入了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教科书还将推广到加拿大其他省。“安大略省教科书写入日侵华罪行,将广泛推广。”
③俵义文:“第二次小泉内阁成员参加自民党政治团体一览表”,http://www.ne.jp/asahi/kyokasho/net21,2004年4月11日。
④关于二战,安倍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说,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损失和伤害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表示继承1995年的“村山首相讲话”。在慰安妇问题上,他也表示政府的基本立场是,承袭1993年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的、旨在承认日军强迫亚洲妇女随军充当慰安妇的事实,并对此进行道歉的讲话精神。“众议院答辩:首相、个人也承袭村山首相、河野官房长官谈话”,《朝日新闻》,2006年10月6日第1版。
⑤“安倍首相历史认识:用‘政府见解’给真心话‘加封’”,《朝日新闻》,2006年10月5日第2版。
⑥“日本政府方针:日中首脑会谈联合发表文件”,《朝日新闻》,2006年10月5日第2版。
⑦“中日发表联合新闻公报”,《人民日报》,2006年10月9日第4版。
⑧在2001年、2005年的两次选用中,扶桑社历史教科书的选用率都未能突破0.4%。详见李秀石:“右翼教科书成滞销‘危险品’”,《人民日报》,2006年3月13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