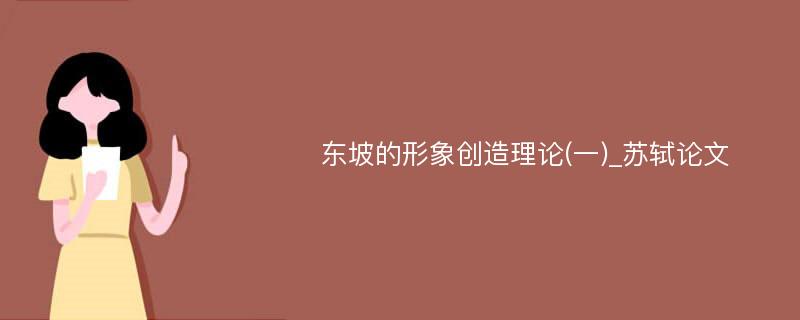
东坡意象创造论(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坡论文,意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意象,指经过作者运思而构成的形象,它是文艺创作中的首要因素。南朝齐梁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说道:“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也。”[1] 其意谓:“具有独特见解的艺匠,窥探寓意深刻的形象进行创作,这是驾驭文思的首要方法,谋划篇章结构的重要开端。”可见,意象在创造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苏轼更把意象看作是创造成功的基本依据。他评论陶渊明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所以成功,在于作者“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注:苏轼《题渊明饮酒诗后》,卷67,第2092页。本文所引苏轼文章,均出自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3月1版,孔凡礼点校的《苏轼文集》,以下简称《文集》,随文给出《文集》的卷次及页码,不再另注。)(《文集》卷67,P2092)我国古来把“意境”与“意象”通释,如黄庭坚言及“意境”时,即直称“意象”云:“革囊南渡传诗句,摹写相思意象真。”(注:黄庭坚:《同韵和元明兄知命弟九日相忆》。)苏轼所说的“境与意会”,即指意象。他说的“境”,指菊花、东篱、南山的“物象”,“意”,指采菊见山情态的“我意”,“我意”与“物象”契合为一,即构成了诗歌世界的意象。这便是我国传统意象含意的最通常解释。
一、苏轼“意象论”的内涵
苏轼对传统的意象含意是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的。
我国早在先秦《周易·系辞上》中即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说法。苏轼曾对这段话进行诠释道:“圣人非不欲正言也,以为有不可胜言者。惟‘象’,为能尽之。故孟轲之譬喻,‘立象’之小者也。”[2](卷7)其意谓:“道德智能极高的人并不是不想说他公正不偏的话,而认为有不可尽言的地方。只有‘物象’,才能穷尽地表达其意想。所以孟轲的运用譬喻,也只是‘立象’的一部分啊。”苏轼这段话,把“象”看作是具有极其丰富内涵的客体事物,而“意”则是主体观察物象所生发出的纷纭复杂的意绪感受。故“立象尽意”,简单说来,即树立物象来表达思想——象由意出,意赖象生,主客观统一,就是“意象”概念的特征。苏轼的“意象”说源于此,并直接与他的艺术创造论息息相通。
苏轼把王维诗的“意象”方式概括成两句著名的话:“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文集》卷70,P2209)这段话典型地表述了王维意象式诗歌创作的特点。
“诗中有画”,指“诗”中包有“画”的物象;“画中有诗”,指在“画”中含有“诗”的意蕴。前句强调诗的外在描述性景象,后句强调画中的内在含蕴性意趣。在王维诗中,确有许多“情景分写”、“意象并列”的作品,譬如《山中》:“荆溪白日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前两句是景语,描绘出了荆溪之“白日出”、寒天的“红叶稀”景象;后二句是情语,抒发出了路本无雨,却被翠叶露水打湿衣裳的诗意感受。王维诗中还有先抒情,后写景者,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前两句写主人公“独坐幽篁”与“弹琴长啸”的孤寂心绪;后两句则画出极深竹林的清幽和空中明月来相照的澄澈环境。以上二诗,均是王维塑景造意、托物寄兴的杰出作品。
王维在论诗画创作时早已有了鲜明的主观意象理论,如他论述的“凝情取象”[3](《裴右丞写真赞》,P381)、“审象求形”、“传神写照”[3](《为画人谢赐表》,P305),都在强调着诗画意象的主体意蕴。诚如苏轼论述王维诗画的突出特点是:“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注:苏轼《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本文所引苏轼诗歌,均出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2月1版,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以下简称《诗集》。随文给出《诗集》的卷次及页码,不再另注。)(《诗集》卷3,P108)“象外”,即象外之意,这个象外之意,有如仙鸟冲出了鸟笼,获得了解放。指王维诗画的意蕴往往脱离开物象外形本身,使其意境超乎常法之外。为此,苏轼尝引唐·司空图论诗云:“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文集》卷67,P2124)是故苏轼特别注重艺术上的“意在言外”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化境,他随时都在追求笔墨蹊径之外的超然高韵,以抒发他内心蕴藏的高妙意境。所谓“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集》卷17,P905 )便是苏轼论诗的主要题旨,也是他意象论的基本植根点。至明代,而有陆时雍的论王维诗云:“摩诘写色清微,已望陶(渊明)、谢(灵运)之藩矣。……离象得神,披情著性,后之作者谁能之?……体物著情,寄怀感兴,诗之为用,如此已矣。”[4] 陆时雍所说的“离象得神,披情著性”和“体物著情,寄怀感兴”的理论概括,甚合苏轼意象论的要旨,也甚合王维诗、画意象方式的实际情况。
二、苏轼意象论的特征
通过苏轼评王维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论析,我们便已体味到苏轼意象论的基本意向了。即苏轼主张“意象”应该属于作家主观的产物。尽管他也主张意象具有依赖于自然景物而产生的属性,如他说过“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文集》卷69,P2170),但他更接着说:“有形则有弊。……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圣贤之高致也。”(《文集》卷69,P2170)即他认为意象是可以冲出客观物象的外在形式,着重张扬作家主观之“意”的作用,使物象转化成为一种高层面的人生理念和哲见,成为“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的“圣贤之高致”。这种“转化”,究其根源,是有着原始“立象尽意”概念的内在合理因素的——“象”之所以能够“尽意”,必须具备与“意”相似相通的条件。即“象”并不是用任何一种物景都能“尽”主体特定之“意”的。因此,举凡出现在作品中的“象”(或“境”),便都是要经过作家主体意识所过滤的事物;它或者是能起到触发主体“意”的审美存在的“象”,或者是能符合表达作家内心特定旨趣的“象”。而这两种“象”,无一不是经过作家主观选择而确定下来的事物。故在艺术作品中,其实并没有纯客观的“象”。苏轼在其《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文中明确说道:石屏上的水墨画,“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嵋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诗集》卷6,P227—228)他明言“独画”,可见峨嵋雪岭老孤松的形象,乃是画家精心选择的物象,是“有为而作”,是画家主观“神机巧思”的结果。是故苏轼结论说:“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这便强调了画家“摹写物象”的主观意趣,是与诗人的主体情感抒发基本相同的。这样,“诗中有画”的“画”,便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画,而是有着诗人主观意趣的画;“画中有诗”的“诗”,也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而是透过画面所显露出来的具有“象外之旨”的诗。因此,把苏轼评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象创造,仅仅局限在客观的“象”与主观的“意”相结合的认识上,则是狭隘、浅近的、不完全符合作家整体含意的看法。此其一;其二,意象的特征,除主观性特质之外,还有深层的超越性审美特征存在,“诗中有画”与“画中有诗”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两者不仅相互交融,又相互促成,形成为超越有形物象的、具有内在象征意义的“象”,是一种具有形上品格的“象”,一种实现了真正心灵超越的审美的“象”。苏轼在其《题王维画》中形象地以“行吟坐咏皆自见”(《诗集》卷48,P2598)的主观意志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王维脱离世尘、飘然自得的隐居之乐,显示了他超越性的审美理想。三国玄学家王弼在其《周易略例·明象》中曾经说过:“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苏轼的哲学著作《东坡易传》曾深受王弼观点的影响,在意象说方面则尤为显著。如苏轼在《东坡易传》卷7中曾这样论述道:“有其具(指器用形象)而无其人,则形存而神亡”,这便强调了“人”、“神”相对于器用形象的主导作用。苏轼接着又说:“我有是道(指“刚柔相摩,八卦相荡”的“意”),物各得之。……所遇而为之,是心著于物也。”意谓:只有当“象”中已融进了“人”之“神”时,其“象”才“存意”、成为“象生于意”的“象”,再经过主体的“所遇而为之,是心著于物”的审美陶铸,便导致了“得意而忘象”和“所存者乃非其象”的那种上升到形上高度、具有超越意义的“象”。在苏轼的创作实践中,确有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象式篇章,如《东栏梨花》诗:“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诗集》卷15,P730)前两句极写清明时节梨花满城的绚丽景色,诗人将梨花之“淡白”,与柳叶的“深青”交互染色,形成色彩的强烈反差,醒人耳目;而“柳絮”的飞飘,与“梨花”的满树怒放,动静结合、交相弥漫,形成“满城”和谐而独特的艳丽清明景色,可谓描景如画,沁人心脾。然而诗人在后两句春花烂漫、生气勃勃的欢愉氛围中,却透露出作家主观的“惆怅”心绪,煞时形成情感的对比,令人心荡神迷,生发出“象外”之旨的探寻作用。“东栏”的那“一株雪”,虽然勾魂诱人,但是,时不我待,人生几何?人们能有几个“清明”来欣赏这满城梨花的迷人春色呢?诗歌以景入情,以情凝景,再以回复句式叠加渲染,顿使作者的哀伤感慨联翩而至,逐步上升到春光难驻,人生如寄的哲理体验上,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据说,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他“好诵东坡《梨花》绝句”,“每吟一过,必击节叹赏不能已,文潜(张耒的字)盖有省于此。”[5] 也就是说,张耒从这首《东栏梨花》诗中深深感受到了人生苦短的哲理体验,从而感慨叹赏不已。
但是,苏轼还有更多“心著于物”和“存意忘象”的诗歌,而且构成为他主体的意象方式。譬如《东坡》诗:“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诗集》卷22,P1183)这首诗可说是作家以雨后夜步东坡的意象,整体抒发他独立危行人生态度的优秀诗篇。诗中的“景”,无一不是围绕这种志趣精神进行托意抒发的。开头的“雨洗东坡月色清”,先从“体物著情”入手,诗句呈现出一片清幽澄明的境界:那白天骤雨的冲刷,已把东坡清洗得干干净净,夜间的皎月,又把万物照射的晶莹澄澈、万里无尘。这都集中显现了诗人内心的无比纯洁和淳真。而“市人行尽野人行”,承接前句进一步渲染出诗人鄙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6] 的世俗趋利者;他果断地认为,只有远离尘嚣市集的高洁“野人”(自喻)才能独享这清幽胜景的乐趣。这表达了诗人不甘心与小人为伍的自矜胸襟和自豪傲骨。末两句“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则着力皴染诗人的不畏艰险、履险如夷、挺拔昂扬的迈往心态。我们看到,诗人拄着手中的棍杖用力地敲击着脚下的丛错顽石,使得坡头腾起了空谷声响,他正信心百倍地迈着矫健步伐,向前行进着。这哪里是在写景,可谓全身心地抒发着诗人内心的不畏仕途坎坷、不惧贬谪流放的襟怀和胆识。诗歌突出表现了一个征服者的胜利愉悦,和他遗世独立的傲岸伟姿。
再进一步看,苏轼的意象又往往发展到“离象得神”的纯主观方式的创造性方面。譬如他的名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诗集》卷3,P96)诗中“飞鸿踏雪泥”的意象,只是存在于作家的想象中,并没有具体的画面场景描绘,它是诗人议论人生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虚幻的、抽象的,它任凭作者的驰骋臆想或联想,以其审美心态去悟证漂泊的“人生”、或悟证“坏壁无由见旧题”的现实、或悟证超越崎岖坎坷道路的“本心”。总之,“飞鸿泥爪”的意象,跟随诗人的驰骋神思,多方蔚发奇想,寄托妙韵,既丰富了意象的奇趣,又使读者获得有益的人生美学启迪。
按现代的科学定义,“意象”的整体含义是:“人脑对事物的空间形象和大小的信息所作的加工和描绘。和知觉图像不同,意象是抽象的,与感觉机制无直接关系,精确性较差,但可塑性却较大。而且,我们可以用意象方式来加工智力这样抽象的定量特性。”(注:《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九册,第102页“意象”条目。)苏轼意象论的特征,颇近于此。
三、苏轼意象论的创造
意象在人类创造力的发生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从以上分析论证中可以清楚看到,苏轼的意象论及其创作实践,充分表现了诗人的创造性特质。我们说正是他的意象主观论,奠定了其艺术创造的基石。
在苏轼意象创造领域里,诗人的主观体验达到了最高峰。意象纯粹是一种内心活动的表现,是一种依赖对象真实所升发的心理的现实。这种主观审美状态,是诗人所觉察和体验到的“不可思议的”整体现象的组成部分,它的意义甚至可以超出诸般科学的理解。因此,分析和研究意象形成的过程及其特质当是提示其创造价值的关键所在:
(一)意象创造的可塑性
意象既然是作家一种内心活动的表现、一种内心心理的体验,它便呈现出流动变化、短暂易逝的状态,与外部世界的状态相较,它便显得愈加不稳定。一般说来,主体的“意”,总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以及个体时空遭际的变化而变化着。意象与具有相对稳定和可靠特征的“知觉”相反,“知觉”在通常情况下,总会呈现出相当意义的客观价值;但意象却在大多数情况下,呈现朦胧的特性。这是因为人的心灵总是在不停顿地活动着、变化着。于是,意象的这种可变性、流动性特征,便给我们提供了可塑性的巨大艺术空间。它能使我们从刻板的真实再现中解放出来,在意象形成过程中引发出不同于现实存在乃至与以往历史印迹完全相反的崭新意象,这就是艺术上最初创造力的萌芽。苏轼诗云:“西湖亦何有?万物生我目。”(《诗集》卷32,P1681)西湖的美景又表现在哪里呢?它完全是由诗人自我眼睛的感触而生发出来的。试看苏轼的西湖名诗《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的成功创造,便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范例:“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诗集》卷9,P430)西湖的“水光潋滟”美景,在苏轼的眼中,“晴”天时最好看,而“山色空濛”的景色,“雨”天里更加迷人。自然界的天然美,是最值得称道的。有如西施美人的自然姿质美貌一样,不论是“淡妆”(晴日)或是“浓抹”(雨天)都是美的。所以把“西湖”比作具有天姿美的“西子”,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这就是说,西湖总体的“美”,都在苏轼的“目中”千变万化着。诗人可以随着天气的阴晴差异选择其观赏意向。作家凭其“目”,用“西子”比喻“西湖”,结果形成了“西湖之定评”。可见,诗人的主观意识对意象可塑性的创造会有多大作用。
苏轼的意象创造可大可小,任凭“吾意”塑造,“听我所用”。他说:“世人写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则不然,胸中有个天来大字,世间纵有极大字,焉能过此?从吾胸中天大字流出,则或大或小,听我所用。若能了此,便会作字也。”[7] 从“胸中有个天来大字”方面看,苏轼有《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诗,它抒写李白的阔大精神有如吸吞宇宙,他形容“谪仙非谪乃其游,麾斥八极隘九州。化为两鸟鸣相酬,一鸣一止三千秋。”(《诗集》卷30,P1994)前两句意谓:“人间的谪仙李白,并非天上谪降的神仙,而是上苍神仙在天地间的遨游。他纵放于九州中华大地,又驰骋于比九州更远、更辽阔的天地极境。”——《淮南子·地形训》说:“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又说:“九州之外有八寅,八寅之外有八纮,八纮之外有八极。”可见,博大的“九州”仍嫌狭小;而“八极”,则指比九州更为广阔遥远的天地极限空间。诗歌下面两句又说李白化为一只天外飞来的神鸟,与另一只神鸟杜甫相互争鸣酬唱,他们争唱的不朽诗作,形成为千载难睹的旷世奇句。而“一鸣一止三千秋”的描述又从长时间上形容了李白的难能逢世。苏轼在这里以其“胸中天大字”的襟怀,极具夸诞地描绘出李白伟岸、恢弘的精神境界。另一方面苏轼有时又以其“或大或小”的意念把自己的精神缩小到虫豸般细小物体上:“静看月窗盘蜥蜴,卧闻风幔落伊威(即“地虱”)。”(《诗集》卷42,P2301)这是苏轼遭贬海南儋州时所写的形容其精神无比苦闷孤寂的诗,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月窗上盘爬的壁虎(蝎虎)和从风幔上跌落的地虱小虫身上。有时甚至还把自己的精神聚集到墙壁的狭小隙缝中,透过日光去观看孔窍中飘动着的极微灰尘,真可谓更加微乎其微了!《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一云:“斜日照孤隙,始知空有尘。微风动众窍,谁信我忘身。”
苏轼的精神意象,不仅可大可小,还能可远可近,可深可浅,可屈可伸、可聚可散,极富弹性张力。如其聚远楼诗:“云山烟水苦难亲,野草幽花各自春,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诗集》卷12,P591)矗立的高楼把空中的云山烟水、远处的幽花野草都聚拢到自己跟前,它使宇宙间那些“苦难亲”和“各自春”的种种疏离、冷漠景象都极其紧密地关联、亲近、交织起来;与此相反,苏轼有时又把原来统一的肉体自身,煞时分散为互不联系的诸多独立事物,可谓奇而又奇:“我性喜临水,得颖意甚奇。……画船俯时镜,笑问汝为谁?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诗集》卷34,P1794)诗人在静看似“明镜”般的颖水水面时,突然一阵微风吹来,水面荡起了无数涟漪,把自己的胡子眉毛的影像全都搅乱了,自己的肉身,也被煞时分散成为百余个东坡……。
总之,苏轼的意象创造,是充分自由、充分自便的,他说:“东南山水相招呼,万象入我摩尼珠”,(《诗集》卷36,P1961)“策杖无道路,直造意所便”,(《诗集》卷13,P644)这便是苏轼意象论的核心理论所在。
意象的发生,既是人类心灵活动的功能,意象便不再是现实的忠实反映,而只是一种不完全的复现,只是一种外在对象的替代物。美国现代创造学家S·阿瑞提这样形容说:“意象是另一面镜子(知觉)的镜子,它虽然不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却是一面有创造性的镜子。”[8] (P524)阿瑞提又强调说:“意象”作为“一面有创造性的镜子”,它“不仅能够帮助人更好地理解世界,而且还能帮助人创造出一种外部世界的代用品。”
(二)意象创造的真实性
意象既然是诗人的主观心灵活动,并不是现实的忠实再现,那么,怎样理解和把握艺术创作中的真实性呢?苏轼曾强调说:“古人所贵者,贵其真。”(注:(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1引东坡云。)又举例说:“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诗集》卷6,P227—228)并概括地说:“不如丹青不解语,世间言语无非真。”(《诗集》卷16,P798)可知他对“真”的特别重视。与此同时,苏轼又以物之“理”阐发“真”,说道:“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文集》卷11,P367)可见,意象不管如何铺张扬厉,随心所欲,“直造意所便”,但最终必须显其实质之“真”,这是一切艺术创造的归宿。实象与心象的神韵契合,以“心象”之虚,表现“实象”之真,这是苏轼意象论的根本要求。即“真”是目的,“象”是手段,“真”是“道”,“象”是“器”。主次分明,决不可本末倒置。如果意象失去了其“常形”之“理”(真),则“举废之矣。”可见,求真辨理的至高无上性质。故苏轼说:“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这决不是夸张的话。“高人逸才”如何辨理求真?苏轼曾举文与可画竹为例道:“老可能为竹写真。”(《诗集》卷43,P2347)“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谓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蹙,如是而条达遂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缕,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通达事理的人)之所寓(寄托本意)也欤。”(《文集》卷11,P367)原来,苏轼把写“真”和达“理”的要义归结为“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的理念上。“天造”,即自然之真,凡“天造”之“真”,必然“厌”(满足,美好)于“人意”。文与可所画竹石枯木,之所以能够“得其理”,堪称为“写真”,就在于他的画“合于天造,厌于人意”,把握了事物生长的内在自然规律:“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蹙,如是而条达遂茂”,一旦把握了竹子的“天造”生长规律,则可任意挥洒,使其“根茎节叶,牙角脉缕”,随时达到“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的自由至真境界。
苏轼为深入地发挥他意象创造论的自由至真论,曾以“水”的“无常形”来比喻和阐发道:“万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为形而已。世以有常形者为信,而以无常形者为不信。然而,方者可以斫以为圆,曲者可以矫以为直,常形之不可恃以为信也如此。今夫水虽无常形,而因物以为形者,可以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惟无常形,是以遇物而无伤。惟莫之伤,故行险而不失其信。由此观之,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2] (卷3)在这段话里,有三点含义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其一,“世以有常形者为信,而以无常形者为不信。然而, 方者可以斫以为圆,曲者可以矫以为真,常形之不可恃以为信也如此。”“信”即“真”,普通世人总是以“有常形”当作“信”的标准,而以“无常形”指为“不信”,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因为事实上,人们常可以把“方”的东西砍削成“圆”的事物,把“曲”的东西矫正为“直”的事物,所以“常形”是不可当作“信”的直接依据的。其二,“惟无常形,是以遇物而无伤。惟莫之伤,故行险而不失其信”。“伤”,指妨害、损伤,只有“无常形”的“水”,才可以碰到万物而不被伤害;唯有不会受到伤害的事物,才能在冒险中不失去它的本质之“真”(信)。这便淋漓尽致地形容了苏轼本人“直造意所便”的主观意象创造论的正当性。其三,“水虽无常形,而因物以为形”。这就是说,苏轼的创造意象有如“水”的“无常形”和它“因物以为形”的特征,意在表达他重“神似”轻“形似”的艺术主张。亦即重在“取法”。他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诗集》卷29,P1525)“传神”,指“写真”,要能生动地传达出人物的神情意态,达到艺术真实的高度。为此,苏轼评价文与可画竹的艺术真实造诣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诗集》卷29,P1522)文与可画竹之所以能够“无穷出清新”,是由于他在创作时全身心地灌注在竹子上,甚至把自己的气质和个性都镕铸在竹的形象之中。因此,他才能摆脱一般竹的表象描写,获得了他艺术个性的“清新”之意,达到了他艺术真实的最高成就。
正由于此,我们才看到苏轼一方面强调“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得,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文集》卷70,P2210)的真实性方面;另一方面又看到苏轼更强调了吴道子画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同上)的艺术典型化方面。苏轼认为,艺术创作不应是单纯摹拟生活真实的自然主义附庸,而应通过艺术形象的真实塑造表达出“新意”,并在“豪放”的艺术风格中表现出人生的“妙理”。这也就是说,艺术创作需要从生活真实上升到艺术真实的高度。如果光注意现实事物的细微末节的真实,而忽视事物本质特征的真实性,他就会遭致整体性的失败。苏轼举例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而已,无一点俊发气,看数尺便倦。”[9] 所谓“意气所到”,即指把握了事物的本质真实,所谓“俊发气”,即指艺术真实的生动性。舍此,即使把“鞭策、皮毛、槽枥、刍秣”等种种细节描绘得逼真入微,也只会令人观之生厌,享受不到艺术真实的愉悦和陶冶。
(三)创立“似花还似非花”的“传神”意象论
既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不是简单的互联共处,“意”和“象”也不是僵硬的拼联合一,而是“诗”、“画”的“心物交融”、“意”、“象”的内在契合。那么,诗画意象的真实性便必然通向了“传神”的艺术要求上。任何真正的艺术作品,它总是要借物言情的,“物”只是引线,“情”才是根本。由此,苏轼便总结出了“似花还似非花”的卓越意象理论和艺术实践要求。他说的“似”,指的是具象“花”的形貌,“非似”,指花的内在传神之真即作家“意造”之“似”。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10],表面处处写杨花的“萦损柔肠”、“困酣娇眼”的外貌情态,及它被晨雨冲进池塘化作“一池萍碎”的凄恻景象;但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实是通过杨花表象暗喻一个梦中万里寻郎的愁妇形象,最后把败落的杨花说成“点点是离人泪”,从咏物直接过渡到写人。整体上成为了一首缠绵幽怨的言情词,从而引发出“象外”的无限韵味想象,形成“意造之似”。故清·沈谦《填词杂说》评此词云:“东坡《似花还似非花》一篇,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而清·刘熙载《艺概》卷四更把“似花还似非花”上升到对整体艺术作品评价的理论概括高度上:“《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清·黄苏《蓼园词选》更说:“二阕用议论,情景交融,笔墨入化,有神无迹矣。”皆把“似花还似非花”看作是超乎花像却显示艺术规律(传神“取法”)的理论概括。“似花还似非花”的理论概括,最终形成了宋代以来中国文人写意画的特质,即它注重“意似”和“神似”,不重“形似”,而与西方画论所注重的“摹仿”、“表现”理论迥乎相别。据此,当代画论家殷杰指出:“因为中国画并不重型而重象,不追求严谨的质感、量感、比例及形,也不采用直观的透视空间,而是表现感受性的,需以心契的意象空间。”所以,中国画意象的“意似”、“神似”,便与西方的“摹仿”、“表现”并无瓜葛。中国绘画的本质不是“摹仿”,也不是“表现”,而是“创造”(注:殷杰:《中国绘画的独特性——论意象艺术》。《美术(京)》1984年第2期,第57页。以下所引王绂、齐白石、黄宾虹语,皆转引自此文。)。是故苏轼的“似花还似非花”正是一种“表现感受性的、需以心契的意象空间”,它的本质是“创造”,而对后世的影响甚大。明代王绂曾生发出“不似之似”的说法,他以为“不似”是为了“似”,是为了似物之“真”。到了当代画家齐白石则发展为“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看法,他的“似”或“不似”,虽是从“形”的视角出发,但对两者“之间”的超越,已与苏轼的重神似、轻形似的观点十分接近;而至当代画家黄宾虹的“作画当以不似之似为真似”的说法,便道出了苏轼意象论的真髓,从而确认了中国意象论的美学本质特征,表达了它的独创高格。
(四)确立“象外”形上品格的新意象论
苏轼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集》卷29,P1525)他认为:用“形似”当作论画的标准,则与儿童的见解相邻近;写诗必认知诗句本身的意思,一定是不懂得诗歌作意的人。苏轼反对对诗画进行外象直观和“形似”判断的见解。他认为,真正的诗、画艺术,讲求其内在意蕴和“神似”之旨,而“象”,仅只是处于形器层面的外在表达工具而已,而人们所追求的是内在心灵“对感性进行超越后的新的情理融合的情感”的“形上品格”。[11](P631)
苏轼论王维诗、画的最高造诣是“得之于象外”。(《诗集》卷3,P108)“象外”,是指王维诗、画所散逸出的“超然心悟”,亦即指其处世审美理想的形上品格。王维把其诗中那种种深林明月、水流花开、孤鸿落照、白鹭复下等外在景象,已全部融入了他内在心灵的审美感受之中,使之在“诗情画意”的交融中上升到哲理层面的形上高度。对王维的这种形上造诣,苏轼有着精湛的总结性论述道:“摩诘本词客,亦自名画师。平生出入辋川上,鸟飞鱼泳嫌人知。山光盎盎著眉睫,水声活活流肝脾。行吟坐咏皆自见,飘然不作世俗辞。”(《文集》卷48,P2598)王维作为一代著名的“词客”兼“画师”,他把辋川著在“眉睫”的“山光盎盎”的外在景色,与似乎奔涌在内部肝脾中的“水声活活”相互融会交错,使之溶化在“鸟飞鱼泳嫌人知”的辞世环境之中而流连忘返。即王维在“得意忘形”的化境中,以其全部旨趣赞颂着超脱喧嚣尘世、潜入宁静和谐的审美境界。苏轼以此诗阐明了王维的诗、画都在超越山水田园的表象,引导我们去发现和体味其“禅趣”的形上品格。据此,苏轼又发表了他的著名论题:“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集》卷29,P1525)“诗”和“画”只是在艺术门类上有所不同,而从艺术反映规律上看,却都是一致的,它们最终总是向着超越表象的“自然清新”的形上审美目标迈进着。“诗”与“画”的一致性,标明了任何艺术门类的意象创造都是相通和相同的,从而扩大了意象论的覆盖范畴,成为了带规律性的艺术理念。这就是苏轼新意象论的重大理论贡献。
(五)独创个性化的比喻意象和典故意象
苏轼的意象创造,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意义和价值,但作为强调“自出新意,不践古人”的苏轼,他更注重个性的“独造”,因而他的意象艺术也便出现了“变法出新意”(《诗集》卷8,P371)的创造性新面貌。
宋代高度发展繁荣的知识文化精神,炼就了博大精深的人文气象;在宋人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深厚艺术背景下,苏轼的意象创造也出现了新的蜕变——譬喻性意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有如前述:苏轼在论及《周易·系辞上》的“立象以尽意”时,曾举出孟子的“譬喻”作为“立象尽意”的一种方式。而苏轼在创作中又极善用譬,这便使他自然地把“譬喻”当作了意象创造的手法之一。
“譬喻意象”,即不把现实真实景物本身作为艺术对象,却以其他类似事物以及历史陈迹中某些相近事件用作比拟,进行着新的意象创造。它把王维“即景造意”的画面感,转向了“无形画”(《诗集》卷48,P2630)的颇具“滋味感”的意蕴形象,使人发生联想和揣摩,在“蹈虚”中翻出新奇,产生出更为深刻更为生动的情理感染效果。譬如前举“飞鸿泥爪”的意象,便是一个譬喻,它在诗中并没有具体景象的描绘,而全在阐发一种人生短暂和萍迹不定的哲理思考。由于其譬喻意象的新颖贴切,题旨机警而被衍化为成语,至今广泛流传。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比喻是天才的标识。”苏轼诗中还有更多简洁、锤炼的譬喻意象,它们有的几乎只是运用一个景物的文辞符号,从而着重表达苏轼的“自我心境”。例如“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诗集》卷45,P2444),其中的“浮云”、“孤月”全无具象描画,它们都是诗人内心心理的代意词或象征词:“浮云”象征“世事”、“孤月”代表孤寂心境。所以南宋学者王应麟在其《困学纪闻》卷18中曾鲜明指出说:“‘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见东坡之心。”苏轼这种以表达“自我心境”为目的的比喻方式,常能产生“非图画式”的审美效果。法国现代启蒙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和剧作家莱辛说过:“诗往往有很好的理由,把非图画性的美看得比图画性的美更重要。”(注:参见其《拉奥孔,论画与诗的界限》。)苏轼的譬喻意象,十分丰富而多彩,他常常把比喻的内涵扩展和延伸,连类创造出更为新颖的寓言意象,禅趣意象和典故意象等多种譬喻式意象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