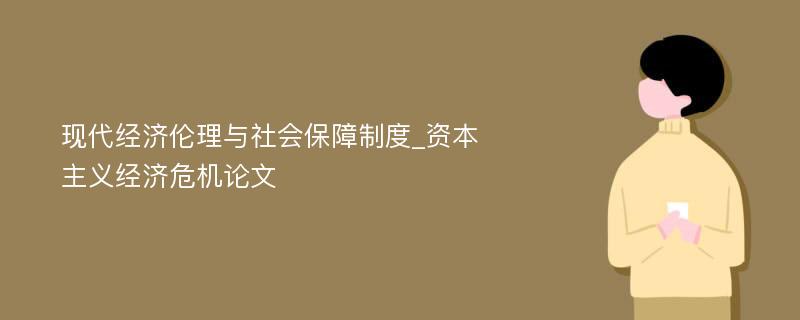
现代经济伦理与社会保障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社会保障制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国家最初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安全,所以社会保障又有“社会安全网”之称,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资本主义世界的重建与发展,尤其是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扩大和完善的阶段,与当初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的宗旨比已有了较大的不同。
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无论是国家整体还是劳动者个体的经济状况都有了较大的好转。以美国为例,1979年一个有高中文凭的30岁妇女,如果她在产品制造业部门工作,每年可挣得17200美元,最低的服务业周工资为230美元。[1](P140-141)。贫困家庭的生活也处在一个较高水平,1979年全美20%贫困家庭平均年实际收入5439美元。[1](P128)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人就业,生活就会相当富足。1983年,美国主要食品的人均消费总量为643.3千克(日本为503.3千克),平均1.5人有一台电视机,1.3人有一部电话机,1.4人有一辆汽车。而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在3%以下,有的行业还出现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的状况。[1](P98)再从工人运动的情况看,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暂时地还处在安全状态。美国工人罢工次数1976年为5648次,参加者2420千人,到1981年为2568次,参加者减少为1081千人。法国工人罢工次数1976年为4384次,参加者2023千人,到1981年为2442次,参加者329千人,客观上工人运动处于低潮。[1](P121)
如果这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降低工人的保障水平,削减保障经费的支出应是合乎情理、符合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初衷的。可事实正好相反,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工人生活有所提高的情况下,社会保障水平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还有大幅度的增加。仍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福利支出1940年为88亿美元,人均68美元,1980年为4934亿美元,人均2145美元。[1](P123)1999年更是高达1.1万亿美元,人均4070美元。[2](P936)其增幅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这其中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一般意义看,或许有这样一些原因:经济上,这既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政治上,可能是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已成为有很大政治力量的政党,他们或是执政,或是成为联合政府的重要成员,他们的主张就是扩大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另外,资产阶级政党为笼络人心,拉拢选票也被迫抛出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诱饵,在实际执行中为此也做了一些努力。有的专家在研究瑞典社会保障制度时指出,“总工会(LO)、雇主协会(SAF)、国家议会三座大厦彼此近距离地鼎立,这是瑞典利益均衡特征的生动标志。在主导整个瑞典经济模式过程中,瑞典的工会‘利益集团’起到了社会支柱的作用”。[3](P47-48)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包含着各种政治力量妥协的因素,终使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保障制度,完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过程。
虽然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执行过程中仍有不少反复,有的对过高社会保障收入开始征税,也有的取消了部分属于社会保障的补贴,但种种做法都没有根本改变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点:(1)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已不是简单的对劳动者实行的生活保障,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包括了劳动者的发展需要,甚至有部分是属于享受需要了。(2)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不再是简单地出于社会安全需要,并非只是为社会编织一张“安全网”。
那么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扩大与完善究竟还有何种因由呢?我们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扩大与完善,仅仅从上述一般意义的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看还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因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不管经济是处在高涨还是低迷的状况,都是持续稳定提高的。我们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扩大与完善是与现代经济伦理观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联系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分配关系都要受到人们道德行为的监督与评判,道德行为对社会制度与分配关系的监督、评判不同,影响人们的不同行为,终于也会影响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变化。就象西方伦理学家所指出的:“经济体制是一个价值实体,它包含着一整套关于人的本性及其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价值观”,[4](P322-323)“每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义。”[4](P324)人们的思想和观念总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及其行为所形成的制度。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伦理观主要是强调人的主体地位,认为个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是目的,而政府,国王或执政者都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要求人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生活和奋斗,强调自由意志与人的自由的重要性,大力提倡节俭和勤奋,推行责任与创新,认为人是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的成败其功过归于个人,倡导竞争中求生存,竞争中求发展,个人自我负责。[5](P43)这既是新教伦理的主调,也是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观的主要内容。马克斯·韦伯在评说早期资本主义伦理思想时指出“在现代经济秩序中,只要干得合法,赚钱就是职业美德和能力的结果与表现。”[6](P27)这反映了资本主义早期经济伦理观的主要方面,它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是停留在维护社会安全的水平上,只要穷人不造反,不危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安全就行了。所以,资本主义早期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水平必然是极其低下的。
这种早期的经济伦理观一般认为是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解释有关,斯密认为“每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7](P27)这一思想后经边泌(Jeremy Bentham 1748-1832)、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等人的进一步阐述,形成了在伦理学上被称为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和经济伦理观方面的自利观、功效观。在这样的一种伦理思想支配下,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早期经济伦理观在一定程度上的片面性,即只强调个性自由、解放与自我负责。换句话说我行我素,后果自负,一切都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观的重要内容。
在世界经济史上,比较早地为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经济人”——的这类行为做出伦理辩护的是英国思想家孟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他的《蜜蜂寓言》一书中指出,个人对自身利益和幸福的追求,“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命力和支柱;我们应当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完全毁灭,也不一定衰落。”[8](P57)它对作为社会公共组织的政府,只要求一个“自由权”而很少涉及到一个“保护权”、“责任权”,相反他们认为如果要求政府给予“保护权”、“责任权”就意味着同时要让出“自由权”或部分自由,这是得不偿失的。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或充分认识到政府对个人的“保护权”、“责任权”是自己已经出让部分“自由权”的结果,由于传统的伦理观中害怕“自由权”的丧失,对政府的要求也就没有太多的奢望与深展。
事实上,说资本主义早期只有利己主义的伦理观也是不确切的,如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1759年)中,也不断提及“无论人类如何被视为自私自利,然而在他本性之中却很明显地存有几种原则,使他能关怀别人的祸福,而且以他人之能有幸福为自己生活所必需,虽然除了看见他人幸福时感到欣慰,他别无所得。”[9](P177)从这里可以看出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观中也包含了利他主义的内容,问题是在一个物质还处在相对贫乏的市场经济初期,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功利主义和自利观的伦理思想成了社会的一种主流意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无法流行开来。物质文明的发展为伦理观的转变和利他主义伦理观占居社会主流地位创造的条件。物质文明的发展,带动了人们观念的转变,从而确立了利他主义伦理观的主流地位。物质文明的发展是观念转变的一个必备条件,人们文明程度的提高,人对社会合作作用的认识,人们对一味追逐个人利益所带来的损害,以及一部分人天然的同情性,以人之乐为乐(亚当·斯密)的入世之态等共同形成了新的伦理观。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光有物质文明的发展是不够的,因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具有无限性,不管物质丰富到什么程度,人们并非必然就要利他。
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严格来说新的伦理思想是萌芽于20世纪前后),由于经济与社会条件的变化,新的经济伦理观逐步形成了。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观除了继续强调人的自由、竞争、创新、自我负责外,有了新的内容。这些新内容建立的基础有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等。他们强调政府干预,指出企业、个人、市场在政府干预过程中具有一致性。伊丽莎白·拉蒙德在《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一书中提出“对一个人有利的事,也对另一个人有利,也许还有所有的人有利,甚至对国家有利。一大笔财富由许多便士构成,一便士与另一便士合在一起,再与第三个和第四个便士汇合起来,就逐渐形成很大一笔金额;同样地,每一个人同另一个合在一起,就形成国家的整体。”[10](P62)而199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干脆认为亚当·斯密就没有简单的经济人的解释,他认为:自利行为与非自利行为的结合是团体忠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其《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涉及讨论自利行为问题时,他指出:“区分以下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们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能否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比如这样一种或者那样一种的效率。这两个问题都与亚当·斯密有关。人们常常引用亚当·斯密关于自利行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观点。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他相信这两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11](P25)。而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勒蒂奇在评说阿马蒂亚·森所著的《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时,提到阿马蒂亚·森曾批评:“是经济学中极为狭隘的自利行为假设,阻碍了它对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心。”
对当代经济伦理学的兴起,瑞士经济伦理学家彼得·乌尔利希(Peter Ulrich)认为:“从现实上看,这是对两百多年来工业社会‘脱缰了的’经济合理性过程导致的内外否定性效应的忧虑的产物。这些否定性效应包括:经济的生态代价、社会代价和心理代价。人们日益明确地意识到,现有经济系统框架内经济上合理的东西,在生活实践上并非无条件地也同样是理性的。从理论上看,这是要克服两百多年来西方‘纯粹’经济合理性和‘纯粹’道德性的两个世界的分裂。这两个世界是一个表现为只讲经济效率的经济学世界,和另一个只讲非经济的人性的伦理观,所以现代人们的目标是将两者科学地统一起来”。[12](P3)在这样一种新的经济伦理观的支持下,产生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否定意识形态的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13](P506)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要与物质文明建设相适应,在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反复指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建立社会主义互助互利道德情操和个人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重要性。这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伦理观的形成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的经济伦理观的形成还与人的全面发展有关,因为个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他人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从社会接受文化知识,进行娱乐,享受愉悦的生活环境等,就如厉以宁先生所说:“人们有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的愿望。人们在改善自己生活的过程中,会越来越感觉到个人生活的改善同周围的人的生活的改善是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个人的生活改善了,但如果周围的人的生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恶化的趋势,从而个人生活的社会环境比以前更不安全了,那么这也很难说明生活质量是否真的有所提高。”[14](P135)关心他人,提高人们的共同生活质量,才能更好地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战后日本教育他的国民“作为一个社会成员:(1)尽忠职守;(2)增进社会福利;(3)富有创造性;(4)尊重社会规范。”[15](P43-45)并且崇尚企业集团主义,倡导人生价值在于工作的劳动道德,也就是说人不能也不应只为自己而活着。
客观上说,今天的经济社会已是一个互助互惠的社会,即便是穷人与富人也离不开相互合作。根据福利经济学的理论,穷人的货币边际效用与富人的货币边际效用是不一样的。穷人的货币边际效用大,富人的货币边际效用小。穷人的货币边际效用大,他需要花钱满足消费,但没有钱可花,富人的货币边际效用小,他花钱的欲望逐渐减弱,因而会有大量的钱在“闲置”。撇开人们的投资行为而言,人的生活消费是有一定限制的,人的消费受到人的生理需求的限制。人们吃、穿、住、行各方面的消费,并不总是表现为价格越贵越好,数量越多越好。现代人们的富贵病最能说明这一点。从这个角度讲,落到某一个人,需求并不是无限的,需求的无限性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或许比较合适。一个社会要是长期表现为穷人买不起商品,富人不想买商品,那么是对谁也不会有好处。
从更深的层次看,现代伦理观的形成又是与西方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变化是分不开的。从当前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社会经济出现危机与困难,大多表现为需求不足,而不是生产供应的短缺。这种情况在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与许多不发达的经济管制型的国家有较大的不同。经济管制型的国家的危机与困难主要出现在生产供应跟不上需求,老百姓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商品匮乏方面。这样常常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商品供应越少越要实行管制与配给,越是搞管制与配给,商品的价值就越会受到扭曲得不到合理实现,那样商品的供给也越少,因为生产者不可能有积极性,甚至不需要有积极性去生产,企业的盈亏凭借政府管制在预先已经设置好了。
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出现的经济危机或困难,明显地表现为严重的消费不足,尽管这中间在不同时期也有一些区别。20世纪前后的情况是表现为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和商品的相对过剩,有堆积如山的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的机器设备闲置不用、生产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或困难并非一定是生产能力和商品的相对过剩。现在主要表现为潜在的生产过剩,生产与消费的比例可能是平衡的,市场上也见不到多少卖不出去的商品。问题就是消费能力不足(也属于有效需求不足),然后厂家就不生产,使就业减少、经济增长放缓。这时只要市场有需求,厂商可以立刻将商品生产出来。因而如何增强消费能力成为发达国家政府中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我们认为利用社会保障制度中社会保障支出的变化对消费品市场进行调节,可以部分达到调控经济的目的。
当市场发出消费不足信号、投资回报因需求不足而下降、市场主动性投资减少时,政府就可以增加转移支付,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使居民消费水平有所增加。通过居民消费支出增加,带动生产走出困境;而当经济出现高涨、就业增加、GDP增幅上升时,政府则可以减少转移性支付,适当削减社会保障支出,尤其是可以减少用于居民福利部分支出,以平缓经济增长速度,预防通货膨胀。这时还可通过税收杠杆调节,增加财政收入,为社会保障进行积累,扩充社会保障基金,为日后市场低迷时,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作好准备,使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的宏观环境得到改善。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干预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主要依靠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来解决市场低迷的问题,事实表现在当时的作用明显,但因基础设施建设建成后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后续支出较少,所以对以后出现市场低迷的调控作用就降低了。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当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经济运行调控作用降低以后,一种主要的、可持续的调控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手段,尤其是在市场低迷时的调控手段,主要是依靠不断扩大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运用好社会保障支出的变化来实现。而且我们认为在将来很长一个时期里,社会保障支出的变化将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可供选择的调控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
所以,经济活动方式的变化,引起了观念的变化,才产生了现代经济伦理观念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事实上社会主义的伦理观更加优越于资本主义的伦理观。不说我们较少受到早期资本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亦即功效观、自利观的伦理道德影响,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直接嫁接于现代市场经济中,较为强调政府、社会、利他观的新的伦理道德观,而且我国的经济伦理观既有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作基础,重视人的生存、发展,享受权;又与我国的历史文化相衔接。我国工人、农民长期受党和政府的教育,加上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人们有一种为国分忧,自谋出路的好传统,大多家庭和社会成员都有耐心去体谅政府的困难,不会太多地将自己的不幸转嫁于政府和社会,就是在市场竞争中失去工作也不会给政府带来太多的麻烦,更多地是转而去自谋出路。按西方国家的充分就业率标准算,有5%以上的劳动者失业,可能会给社会造成不稳定,这一点在我国也不一定适用。因为我国工人、农民有绝对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多年来受党和政府良好的教育。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再像西方国家早期那样,先由市场经济自发发展,然后再行规范的过程。在我国现阶段既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要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的经济伦理观,也应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只有现代经济伦理观深入人心,才有可能建立起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为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作贡献才能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才能对现在存在的偷税漏税现象起到抑制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健康平稳地发展,社会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得到实现。
标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