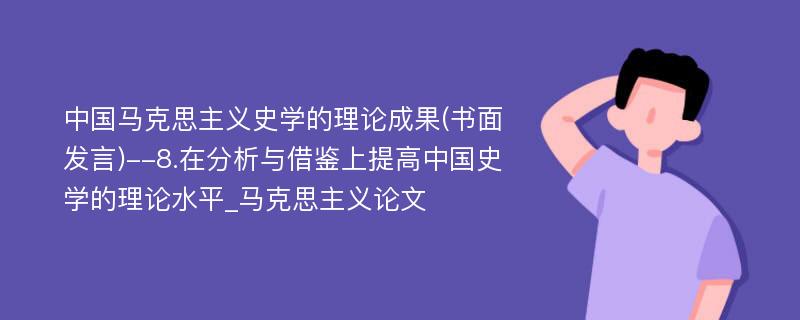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笔谈)——8.在分析与借鉴中提高中国史学的理论水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笔谈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1-0098-17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其一诞生起就是在分析与借鉴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五四”前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讲授唯物史观、史学概论的同时,也讲授史学思想史。而这个史学思想史就是西方历史思想的发展史,涉及从 16世纪的法国学者波丹、18世纪的维科、孟德斯鸠、孔多塞到19世纪的圣西门以至李凯尔特等德国西南学派。他讲授西方史学思想史是从与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关系角度来讲的,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思想就是吸收了以往时代和当代最新的思想成果发展而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为我们创立了分析和借鉴西方新学理的榜样[1]。
但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各方面的原因未能把李大钊的这样高度重视理论特别是国外理论的传统继承下来。具体表现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多地关注有关中国历史的实际问题和中国史学中的理论问题,对国外的史学理论关注较少,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对待国外史学理论方面则出现一边倒的倾向。当时,只能引进苏联的史学理论,而苏联的史学把近当代西方史学一概称为“腐朽没落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国读者只能在苏联史学家对他们的批判中获得一鳞半爪。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有所变化,一些西方史学名著开始被翻译出版,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鲁宾逊的《新史学》等。但由于当时这些史学名著是作为批判材料内部发行的,因此,虽然中国学者对这些著作也写了一些文章,但主要是立足于批判,还根本谈不到有什么借鉴。
中国史学对国外史学的真正分析与吸收借鉴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主要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是在整体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分析借鉴;二是在具体的史学领域中的理论与方法的分析借鉴。这里着重谈前一种情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反映西方历史哲学新变化趋势的史学理论著述不断被介绍进来。1982年,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的出版,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在书中,克罗齐提出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命题,他的观点无疑给了那些希望认真了解西方史学理论的学者一种新鲜感。1986年,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的代表作《历史的观念》一书的出版使得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思想在中国又一次产生新的冲击。柯林武德认为,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的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尽管在基本的历史观上,柯林武德的观点与我们不同,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却引发了更多的中国学者的思考。
学者们认为,最近几年,中国史学终于发展到再也不能无视西方史学,而要求与当代世界科学并驾齐驱的地步。当代西方批判的历史哲学发展的势头,理所当然的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多少年来,我们忽视主体认识能力方面的研究,不敢承认在历史研究中加强主体意识、发挥史家主观能动性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不能不说是一定时期内中国史学沉闷、迟滞、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学者指出,柯林武德和克罗齐等人强调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方面,确有其合理处;较之那种强调只需“排除”主观因素而以“纯客观”态度去吃透史料就能恢复历史真面目的机械反映论,并不更差到哪里。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建立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历史思维的特殊规律进行系统的专门研究,自觉地将历史认识同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现代思维科学的发展联系起来,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历史认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重要史学流派对中国史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法国年鉴学派对中国学者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有学者指出:西方年鉴派—新史学的发展中,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与西方传统史学只注重研究政治史和精英人物不同,西方新史学大大拓宽了研究领域,与此相适应的,又大大扩大了史料范围;第二,与西方传统史学只注重考证不同,新史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注重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和自然科学结合,借用一切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并由此产生出一系列新的分支学科;第三,与西方传统史学只注重叙述、不注重理论概括不同,新史学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主要是史学自身的理论、方法论的重要性[2](P77-78)。学者们认为,对年鉴派的研究更重要的在于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国际史学的发展趋势,启发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历史学的根本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深化我们对史学的认识,推动史学的革新。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亦称英国新社会史学派,也对中国学者在社会史的研究方面产生很大影响。汤普森反对经济决定论,重视人对历史的创造作用,注意研究文化方面的因素,力图寻找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模式。他主张考察那些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赖以构成、社会意识形态得以实现的东西,即家族关系、习俗、各种社会准则、宗教信仰、行为举止、法律和意识等。霍布斯鲍姆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那里解放出来。他提倡建立一种总体的社会史。这种社会史既区别于传统的社会史,也不同于所谓社会结构史。他主张,“社会的历史是历史”,就是说必须把历史研究整个领域作为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历史学应该把有关的社会科学构成一个整体,社会史不应是与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等并列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应该是上述各个学科的综合。霍布斯鲍姆这种把历史研究整个领域作为社会史研究领域的观点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积极反响。有学者认为,必须明确社会史的研究范围应该是像霍布斯鲍姆主张的那种总体史,即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这样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透视同一个问题,使史学著作深刻。他们认为,社会史应是再现人类过去的经历,包括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整体历史①。
比较史学的方法在中国不仅影响早、影响大,且持续时间也长。中国学者在宣传、介绍西方比较史学长处的同时,也发现了西方比较史学的局限。在西方比较史学的启示下,中国史学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运用比较史学中大大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深化。许多学者都有历史比较研究的著作或论述比较史学的文章,其中涉及到了古今中外的各种历史问题,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以及各种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制度,甚至包括两本不同的历史著作。这些论著大多涉及中外历史问题的比较,大大促进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深度,是新时期中国史学研究工作的突出亮点。
此外,由于中国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正在向跨学科方面发展,因此引进国外各个学科领域的理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例如,在社会史的研究中引进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在现代化研究中研究西方学者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比较现代化研究等方面的理论;在中国古代早期国家的研究中引进国外人类学的理论;在新兴的环境史的研究中引进国外人类学和生态学方面的理论,等等,都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我们并非对西方的新理论、新观点都盲目地加以引进和运用,而是首先要分析它是否真有道理,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近年来,有的西方学者在批判“欧洲中心论”时,把马克思的理论也说成是欧洲中心论;还有的学者提出了“中国中心论”的观点,这些都是多数中国学者所不能接受的。
中国史学发展的事实说明,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正确对待西方史学,积极借鉴其有益的理论与方法,对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而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史学所取得的成就,几乎都与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吸收了国外史学的最新成果有关。那种把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与吸收、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对立起来,似乎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学者必然排斥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而善于吸收和运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学者必然背弃唯物史观。这种观点无疑是形而上学的。
应该看到,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相对于过去的封闭状况而言的。真正的吸收与借鉴还必须建立在对西方史学的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需要进行长期地、扎实地研究工作。就目前情况看,这方面的工作还仅仅是刚刚开始。相信在新世纪里,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和借鉴,一定会朝着健康的方向稳步发展,这是新世纪中国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注释:
①参见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蔡少卿《扩大视野,注重理论方法》(《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收稿日期]2006-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