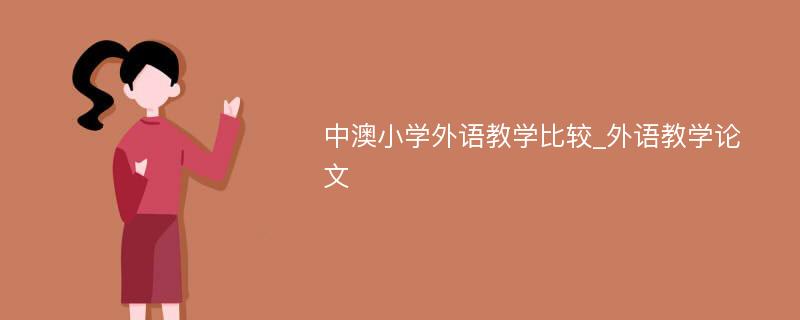
中、澳小学外语教学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语教学论文,小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作为交换教师,我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的Sunn-ybank Hills小学工作了一年。那是一所公立小学,全校有7个年级,各年级除开设英语、数学、社会学、宗教、科学(类似我们的自然常识)、体育、美术、音乐等学科外,自五年级起还开设外语课,Sunnybank Hills小学的外语课就开中文,我在那儿担任六、七年级的中文教学。
一年来,我与澳方合作老师Janctte(珍妮)共同备课、钻研教材、准备教具、互相听课、探究教学方法。通过深入澳大利亚小学中文教学使我亲身体验、感受到中、澳在小学外语教学上的差异,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外语教学几乎就是单纯语言教学,而澳大利亚的小学外语教学却是着眼于对学生进行所学语言国度的文化熏陶,这一教学总目标上的不同造成了两国小学外语教学在选材、教法、教学结构等诸多方面的不同。
随着与外面世界日益增多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和澳大利亚都愈来愈认识到外语教育的重要性。上海、昆士兰州分别从小学开始就开设外语课,但上海的小学外语仅开设英语一门,而昆士兰州的各小学分别开设德语、法语、日语、中文等不同语种。昆州的小学的外语作为必修课,每周两课时,到了中学自九年级开始,学生便可以自行在学校开设的外语中选择一门学习。一般来说,一所中学通常开设两至三门不同的外语,各语种视选修学生的多少来确定是否继续保留。这样的外语选修班学习人数较少,只要有十来个学生便可开课。全州小学开设多语种外语,中学又提供一定的语种供学生选择,这有利于学生更多地了解世界。这样,每个学生在中、小学阶段都修过一门或两门外语,从总体上说,这一代的学生对世界的了解面比中国学生广。
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交换信息、表达情感的工具。除语言本身外,语言的交际功能还受一定社会背景、文化习俗的影响。因此,学习一门语言就包括了解所学语言国度的政治、文化、风俗习惯等背景知识。澳大利亚的小学外语教育(中文教学)重视让学生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通过各种以中国为主题的教学活动,激发起学生对中国的好奇和学习中文的动机,为学生进一步学习中文作好准备。因此,澳大利亚的中文教学中对语言训练的要求相对来说就比较低,这与上海的小学“英语教学”恰恰相反。我们的英语教学更偏重语言本身,我们在制订教学目标时往往不外乎语音、语调、词汇、句型、语法。因此,我们的教学从语言知识上来看是比较严谨的,从语言训练上来看是严格的。但我们往往忽视与这些语言相关的背景知识。就以数词教学为例,澳大利亚的中文教材中制订了非常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在communications(交际)、le-arning how to learn(学习方法)、socioculture(社会文化)、lin-guistic awareness(语感)、general knowledge(常识)这些子目标下又有若干关于数字教学的分目标。在communications一栏中有这样几条:1.学会数数到20。2.能就20以内询问和回答年龄。3.能认读和书写数词一到二十。4.能就电话号码提问与回答。在Learning how to lear-n一栏中是这样提要求的,1.从上下文来推断语言的意义,2.理解汉字书写时笔顺的重要性。3.了解中文语音,语调的模式。这是些关于语言知识本身的教学目标。此外,在socioculture一栏中有下列分目标。1.了解数字在中国的运用。2.知道在中国如何正确询问年龄。3.理解中国文化中尊敬老人的重要性。4.了解日常生活中如何运用数字。教材正是根据教学目标而选定,而教学则围绕教学目标而开展。关于数字的这一单元共有10个课时的内容安排,除分别落实语言教学的要求外,还就文化习俗中的数字运用作了介绍。比如中国人对于数字1—10的手势表达方法,要求学生学一学用手势来表示数字,与此同时,告诉学生这通常用于人们较远距离的交流或嘈杂的市场上;又比如在询问年龄时,教材中出现了“你几岁”?和“您多大?”两句问句,告诉学生这两句问句须根据对方年龄而定,一般问年长者用“您多大”以示尊敬:教材还介绍了中国人眼中的吉利数字与不吉利数字,并简单介绍了其原委,数字“八”正因为与“发”音相似而被认定为吉利,而“四”却恰与“死”发音相同仅声调不同而被认作不祥。这些关于数字的社会文化知识有利于帮助学生学会在一定情景中正确使用数字,以更有效地进行交际活动。
基于文化熏陶上的澳大利亚小学中文教学形成了语言要求不高,而文化熏陶要求不低的格局。在这独特的教学目标指引下,澳大利亚小学中文教学课堂形式多样,教学方法活跃,学生爱学、乐学中文。中文课上,教师常组织起各类以中国为主题,围绕中国文化开展的教学活动。课上我们组织学生包饺子、做春卷、炒蛋炒饭,边介绍配方边指导学生具体操作,最后让学生品尝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并学着说:“真好吃!”“不好吃”这两句话。有关中国饮食文化的背景知识中还介绍各地的特色,食品如北京的烤鸭、上海的海鲜、北方的饺子等,这样的教学活动极有效地激发了学生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兴趣,而这种兴趣也间接转化成了学生对中文学习的积极性。
除烹饪活动外,中文课上还介绍中国的书法和国画。在大多数澳洲人眼中,那方块字就好比一幅幅画,真是又神秘又好看,那是因为他们不懂汉字的基本结构的缘故。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我们在课堂上教学生中国书法。作为中国人,我义不容辞地担任这门课的主讲老师。我先取出文房四宝,一一介绍它们的读音与用途,并让学生仿说“笔、墨、纸、砚”,然后发给每个学生一支毛笔、一张纸。两个学生合用一瓶墨汁,我边示范边要求学生摩仿,从捏笔、蘸墨、舔笔到练习基本笔划,边练边学说“点、横、竖、撇、捺、钩”,最后学生学习将若干笔划合起来组成“十、人、山、水”等汉字。由于有了捏毛笔的基础,学生学画国画便容易多了,看似随意几笔,竹子两三笔便跃然纸上,再添上稚拙可爱的大熊猫,用大拇指蘸上红印泥权作印章,真是又有趣又好玩。常常到了下课时分学生还不肯罢笔,并将各自的作品悬挂出来,当场将教室布置成了中国画展览会。这样的课虽然学生说中文不多,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感受却不浅,而正是这种感受使学生越来越爱上中文课,越来越爱学中文。
在上海,若是我们问正在学习英语的小学生有关英国、美国的基本情况,恐怕十有八九的孩子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我们的教材尽管从Hello,Hi,How are you?这些英语开始,却没有介绍多少英语国家的基本情况。而澳大利亚的中文教学却正好相反,在教“中国、中文”这两个词语的课上,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告诉学生中国的基本情况。珍妮给五年级学生的第一堂课是这样上的:她先取出世界地图,要求学生找出中国的位置,接着她出示五星红旗告诉学生这是中国的国旗,并介绍五星红旗的含义,那一颗大星和四颗小星的关系。然后教学“中国”这一词语,先听说,然后出现词形让学生认认,接着珍妮要求学生说说他们各自对中国的了解,学生马上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当然全是用英语说,有的说,中国人很多;有的说,中国有万里长城;有的学生说,中国的菜很好吃,老师马上不失时机地问上一句,你最爱吃哪个中国菜。大部分学生的回答是sweet and sour pork(甜酸猪肉,即咕老肉),最后教师作一归纳小结,帮助学生对中国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看法。在学生再次认读“中国”一词的基础上,教师发给学生印有“中国”空心字样的练习纸,上面还印有中国地图、中国国旗、万里长城、大熊猫、人群、自行车流等图画,要求学生描一描“中国”两字,并取出红、黄彩色笔为中国国旗涂色。旋即教师引入“中文”一词的教学,在英语中“中文”与“中国人”为同一词,教师从图片中的中国人引伸到“中文”,告诉学生他们要学的就是“中文”。这一堂中文课上,尽管学生才学说“中国、中文”两个词语,且说得并不熟练发音也不够准确,但他们获得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却远远超过这两个词语本身。
同为外语,由于目标立足点不同,教学上差别不小,且教学效果迥异。总体来说,中国小学生的英语语音、语调正确,语言规范,语法知识扎实,而澳洲孩子却说不了几句正确、规范的中文,并且怪腔怪调,但澳洲小学生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的了解,却大大超过中国小学生对英语国家的了解。我想若是我们的外语教学中继续保持教材严谨、教学结构严密、语言训练严格这些长处,再借鉴澳大利亚小学外语教学中的种种长处,在增加语言背景知识信息量的同时,开展各种形式的围绕西方文化的教学活动,那么,上海的小学英语教学一定会有一个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