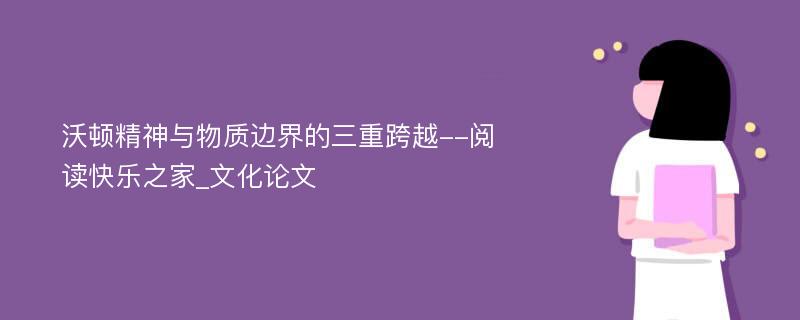
华顿对精神与物质的疆界的三重穿越——读《快乐之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疆界论文,之家论文,物质论文,精神论文,快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女作家华顿(Edith Wharton )的成名作《快乐之家》(TheHouse of Mirth)1905年出版时曾引起过巨大反响,创下两个月内售出14万册的惊人记录。有读者称赞此书说,不但它的每一个字,就连它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令人倾倒。(注:有关此书出版时的销售与反映,见刘易斯(R.W.B.Lewis)的《华顿传》(Edith Wharton:A Biography),弗洛姆国际出版公司1985年版,150—156页。)然而,由于华顿常被看作詹姆士(Henry James)的模仿者, 还由于重形式轻内容的新批评派长期影响等原因,这部曾拥有大量读者的作品与华顿的其他作品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冷落。近一二十年来,这种局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阿芒斯(Elizabeth Ammons)和本斯托克(Shari Benstock)于1990年和1994年编辑出版了附有代表性研究成果的两个版本的《快乐之家》(注:阿芒斯的《快乐之家》由诺顿出版公司出版。本斯托克的《快乐之家》由圣马丁出版社出版。)后,这部作品越来越受重视。著名华顿研究专家贝尔(Millicent Bell)最近指出,自80年代以来,华顿已成为文学评论者们,尤其是女权主义评论者们争相研究的对象,《快乐之家》也成了华顿的最受瞩目的作品。(注:见贝尔的《导言:批评史》(Introduction:A Critical History),载贝尔的《剑桥华顿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harton),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19页。)
《快乐之家》的主要情节写美丽聪慧的姑娘莉莉试图在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的纽约上层社会中追求幸福,结果却屡遭她所依赖的特莱纳和白瑟等人的欺辱与诽谤,最后在极度的困苦与孤独中过早地死去。《快乐之家》可被看作一出悲剧,通过描写以莉莉为代表的精神上的富有者与以特莱纳和白瑟为代表的物质上的富有者的冲突,表现了精神在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遭受物质力量蹂躏的可悲命运。可以说,《快乐之家》的意义主要是由精神与物质的对立产生的。肖沃尔特(ElaineShowalter)就认为,莉莉不融于其环境的原因在于她是淑女, 受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太深,“不能变成新女性”。(注:见她的《淑女(小说家)之死:华顿的〈快乐之家〉》(The Death
of
the Lady (Novelist):Wharton's House of
Mirth),载她的《姐妹的选择:美国妇女作品中的传统与变化》(Sister's Choice:Tradition and Change in the American Women's Writing),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97页。)迪莫克(Wai-chee Dimock)指出, 在《快乐之家》的所有人物中,“莉莉·巴特与市场的关系是最不可思议和格格不入的。”(注: 见她的《降低价值的交换:华顿的〈快乐之家〉》(DebasingExchange:Edith Wharton's The House of Mirth),载本斯托克的《快乐之家》,375—390页。)在小说中,被莉莉看作导师的赛尔顿也强调精神与物质的对立。他认为,成功就是“摆脱一切与物质有关的事情”和“维持一种精神共和国(republic of the spirit)”。(注:本文中的小说引文均译自本斯托克的《快乐之家》。)在他看来,有钱人是难以进入这个国度的;他们将自己囚禁于莉莉所说的“镀金大笼子”(great gilt cage)(70)里, 已经忘记了如何“将金子再变回别的什么东西”(83)。
这里的“精神共和国”和“镀金大笼子”形象地表现了精神与物质这两个在小说中似乎是势不两立的因素。然而通观全书,读者也不难发现,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不只是对立和上下的关系。精神共和国并非是一块完美无瑕的净土;镀金大笼子里也并非毫无良心义举。华顿在颂扬精神国里的美好景象,批判金笼子里的丑恶言行的同时,也揭示了前者的问题和后者的潜能,对精神与物质的疆界做了勇敢的穿越。这种穿越表现出她对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的深刻认识,也增加了小说人物、情节与主题的复杂性。所以,讨论她的这种穿越对于我们认识《快乐之家》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很有意义。下面试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精神共和国”里的瑕疵
在《快乐之家》里,精神国的一个重要的存在形式就是书房。莉莉与赛尔顿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发生在赛尔顿的书房里。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天下午天气闷热。在去赛尔顿的寓所的路上,莉莉注意到大街上有熙熙攘攘的度假归来的富人,也有拼命摇着芭蕉扇的面黄肌瘦的穷人。但一进赛尔顿的书房,景象则豁然一变:
她突然发现自己是在一间小书房里,光线暗淡,但气氛宜人,四周书籍作墙,中间是一块色泽褪得恰到好处的土耳其地毯,书桌上摆满了东西,窗下的矮桌上放着他刚才提到的茶盘。凉风袭来,撩起那薄纱窗帘,送进一股阳台上花盆里的木犀花和牵牛花的清香。(28)
书房内外的这种差异在关于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描写中也得到了强调。那是两年后冬季里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走进赛尔顿的书房,莉莉看见赛尔顿正在读拉布吕耶尔(La Bruyere)。(注: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道德学家,擅长写讽刺作品,代表作是《品格论》。)书房里点着罩灯,壁炉里燃着炭火,使莉莉顿时感到书房内的光明与温暖“将它”(书房)与外面大街上不断变黑的世界隔离开来“(284)。
小说里还有一间与赛尔顿的那间非常不同的书房。它是特莱纳的祖上留下的。但到了特莱纳这一辈,它已不用于阅读,“而作为吸烟室或安静的调情地,它倒是小有名气。”(73)这间书房的主人特莱纳也与上一间书房的主人大相径庭。他金玉满堂,但言行粗野。透过莉莉的双眼,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嵌在他肥胖的大脸上的一对令人恶心的小眼。他三句话不离钱,刚与莉莉见面就叫她善待赚钱有方的犹太人罗斯代尔。他没有助人之心,嘴上说帮助莉莉克服经济困难,心里却想着如何占有她。面对着莉莉的不从,他一边气急败坏地扑向她,一边喊着“我是野兽”(149)。
与这头金笼子里的野兽相反,精神国里的赛尔顿虽不富裕,但博学多识,乐于助人。他爱好文学艺术,对美十分敏感,能“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以一种快乐的神情客观地看人表演”(69)。当莉莉问他为何专程来贝勒蒙特看她时,他说:“因为你是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杰作:我总是乐于看你做事。”(79)在他眼里,连莉莉的哭泣都是值得欣赏的艺术。在布莱家举办的活画展上听到有人对莉莉的造型妄加评论,他不禁联想到莎士比亚的《暴风雨》,自问“难道人们会去向那些半兽人讨教对米兰达(Miranda)的看法吗?”(139)他对生活在这群“半兽人”和“野兽”中的莉莉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决意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佩尔修斯(Perseus)拯救美女安德洛默达(Andromeda)(注:佩尔修斯和安德洛默达分别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和美女。在寻找墨杜萨的途中,佩尔修斯在埃塞俄比亚海岸发现一美丽少女被锁在岸边的峭崖上。她名叫安德洛默达,因母亲得罪了波塞冬而被抓来向海怪献祭。佩尔修斯杀死海怪,救下安德洛默达,并与她结婚。)那样拯救莉莉。他先后在莉莉与特莱纳、白瑟以及哈奇的关系中发现潜在的危险并提出警告,使莉莉把他比作“黑暗中的一点光亮”(287)。
在《快乐之家》的所有人物中,赛尔顿确实是他所描绘的那个精神共和国的最好代表。通过他,华顿谴责了镀金大笼子里鄙俗、冷酷的物质主义。但与此同时,她也对精神做了反思,主要围绕三个问题:1.精神能否离开物质而存在;2.如果不能的话,那么精神在多大的程度上依赖物质;3.精神是否是完美无缺、无所不能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赛尔顿的回答是肯定的。当莉莉说到“不去想钱的唯一途径是拥有一大笔钱”(82)时,赛尔顿表示反对,认为有钱人不会停止挣钱,因为他们的理智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就像人的大脑控制不住肺的呼吸一样。而当莉莉指出,除了珠宝和汽车,钱还可以买别的东西时,赛尔顿挖苦道:“你或许会在享用了它们之后再盖座医院赎赎罪。”(84)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赛尔顿的影响使莉莉丧失了快到手的格雷斯及其大笔家产,使她自那以后怕见赛尔顿,“不是因为她怕他的影响,而是因为他的出现总会使她的愿望变得卑贱。”(99)精神高贵而物质卑贱,两样东西互不相容,这些便是赛尔顿极力要灌输给莉莉的。但他的观点也不是颠扑不破的。当莉莉间他是否从不介意没有足够的钱买他想买的书时,他无可奈何地回答:“难道那不正是我所介意的吗?难道你以为我是那立在柱子上的圣人吗?”(33)
既然精神离不开物质,那么就有一个前者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后者的问题。其实,一直强调精神独立性的赛尔顿的物质生活是比较舒适的。尽管他的工作业绩并不突出,但他是有着一定收入和地位的律师。尽管他住的是公寓,但这对于寄寓在姑妈潘尼斯顿夫人家的孤儿莉莉来说,不能不说是值得羡慕的。可以说,经济上能独立,这应是精神对物质的起码要求。当然,买书的钱也应足够,否则赛尔顿就不会有那满满一书房的藏书。对赛尔顿来说,他父母为精神与物质如何结合的问题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他们并不富裕,但“家庭有限的财力正好制止了挥霍浪费:家里的东西不多,但它们都是稀罕之物,价值很大。 ”(154)这种物质上少而精的状况表现了他们的理想,即“将禁欲主义者对物质漠然置之的态度与享乐主义者能从物质中发现乐趣的本领结合起来”(154)。
既然精神离不开物质,那么它就难免不受物质的局限性的影响,就难以做到完美无缺、无所不能。被莉莉视作指路明灯的赛尔顿在蒙特卡洛事件中也被白瑟制造的假象所蒙骗。而且总乐于看莉莉做事的赛尔顿并不了解莉莉做的许多大事,比如她对慈善事业的慷慨捐助、对特莱纳的无礼所做的反抗、为偿还特莱纳的钱所受的苦难,尤其是她为了保全赛尔顿的名誉而烧了白瑟的信。作为莉莉言行的“法官”,赛尔顿对莉莉一向是严格要求。看到莉莉半夜从特莱纳家出来后,他不辞而别。可他自己却与有夫之妇白瑟有过长达四年的暖味关系。这件事虽然并没有成为莉莉与赛尔顿交往的障碍,但它无疑是精神导师赛尔顿及其精神共和国的一个最具讽刺意味的瑕疵。
近来,评论者对赛尔顿的贬词颇多,有的几乎完全把他当成反面人物。女权主义评论者瑞丝图西亚(Frances L.Restuccia)就把赛尔顿看作父权的典型化身,谴责他一直从事“简化”与“说明”的活动,企图将莉莉这个充满“多样性”和“不可捉摸性”的“文本”变成“作品”,而且在莉莉死后还没完,还要对她尸体说上一句,再“闷”她一下。(注:见瑞丝图西亚的《莉莉的名字:华顿的女权主义》(The Name of the Lily:Edith Wharton's Feminism(s)),载本斯托克的《快乐之家》,404—418页。)现在的评论者完全可以根据各种新理论挑赛尔顿的毛病,挑作者的毛病。但也必须看到,华顿是把赛尔顿当作正面人物来写的。白瑟和特莱纳才是真正的反面人物,代表冷酷无情的物质上的富有者,而赛尔顿代表的则是温文儒雅的精神上的富有者。可以说,华顿通过赛尔顿表达了自己的社会思想。赛尔顿所代表的精神共和国之所以有瑕疵,原因比较复杂,可以有作者的反思、人物真实性的需要、情节发展的需要等。但不论原因是什么,这种写法反映了作者对精神与物质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的认识,反映了她对所谓完美无瑕的东西不轻信的思想特点。
二、“镀金大笼子”里的义举
与崇尚文雅和仁爱的精神共和国相反,被莉莉比作镀金大笼子的纽约上层社会则充斥着粗野与仇恨。这些粗野与仇恨主要起源于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专注。金笼子里虽然有着热闹的聚会和频繁的互访,但人际关系实际受金钱支配。作为金笼子里核心人物的特莱纳夫妇一开始之所以乐于邀请位于金笼子之外的莉莉,不是同情她,而是因有利可图。莉莉这样向天真的格蒂透露她与特莱纳夫妇那样的笼内人交往的内情:
你以为我们只是靠他们养着,而不是互相依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依靠他们——但这一特权却是需要我们付出代价的!我们吃他们的饭,喝他们的酒,吸他们的香烟,用他们的马车、他们的歌剧包厢和他们的私人汽车——是的,但为这每一种享受你都得交税。男人付钱的方式就是给佣人高额小费,不惜一切地打牌,购买鲜花和礼品——还有——还有——许多其他费钱的东西;女人付钱的方式也有小费和打牌——哦,对了,我就是不得不再次拾起桥牌——还有去最好的裁缝店,在一切场合都穿着得体,永远使自己保持艳丽、优雅和风趣。(251)
特莱纳夫人后来嫉恨莉莉,也出于经济原因,即莉莉困难以支付上述代价而用了特莱纳的钱。
莉莉用特来纳的钱所引起的不止是他夫人的嫉恨,还有特莱纳威逼莉莉偿还的丑恶言行。开始时,特莱纳说他给莉莉的钱是用她的本钱炒股挣来的。可不久他就开始向她勒索回报,包括要她在公开场合向罗斯代尔献媚,在众目睽睽之下陪他自己逛公园等,直至在深更半夜将她骗到家中,向她提出无理要求。见莉莉不从,他就指责她的行为“不符合游戏规则”。这里的游戏规则就是有关物质交易的原则,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人花了饭钱,通常就应该在饭桌旁有一个座位。”(148 )但他的貌似公平的原则却掩盖不住他引诱莉莉的阴谋,也限制不了他仗势向莉莉提出非分要求并强迫她答应等严重破坏公平交易原则的野蛮行为。
然而,特莱纳的野蛮与白瑟的相比,要逊色得多。特莱纳还有一点“虚荣心”。他开头之所以答应替莉莉炒股,最后之所以停止扑向莉莉的疯狂行动,在较大程度上,是由于莉莉唤起了他的虚荣心。而白瑟则不然,她是真正心狠手辣。在莉莉与特莱纳的冲突中,双方基本上是打了个平手,因为特莱纳给莉莉的钱最后莉莉全还了,他没丢钱;而莉莉成功地摆脱了特莱纳的纠缠,她也没失贞。但在莉莉与白瑟的冲突中,莉莉却一直是输家,输掉了嫁给年收入有80万元的格雷斯的机会,输掉了继承潘尼斯顿夫人的大部分财产的权利,输掉了几乎所有的朋友,输掉了生存的希望。可以说,《快乐之家》写的是女人如何欺负女人的故事,即赛尔顿所说的“女人对其同类的残酷”(210)。
白瑟的残酷的一大特点是隐蔽性好;叙事者说她能“将恶毒的锋芒藏在她漫不经心的外表之下”(90)。白瑟残酷的隐蔽性在蒙特卡洛的那场风波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在布莱夫妇的宴请开始之前,赛尔顿已预感到夹在不和的白瑟与乔治之间的莉莉可能会遭受不测,但他并不能肯定。晚宴开始后,白瑟与乔治又以他们“往常的面孔”出现在公众面前,使莉莉“对结果有了信心”,赛尔顿的“全面警戒”也松懈下来(206)。可就在晚宴结束,莉莉准备随白瑟与乔治回他们的游艇时, 白瑟突然宣布不准莉莉回游艇,把莉莉与赛尔顿打了个措手不及。
白瑟残酷迫害莉莉的原因也在钱上。白瑟深知乔治不爱她而爱莉莉,但她“因为钱而不愿放他走”(61)。为了钱,她可以信口雌黄,把自己与西尔维顿外出偷情而没能按时到达火车站说成是莉莉想与乔治偷情而蓄意不等候他们。为了钱,她可以当众背弃一直在为她和乔治效力的莉莉。为了钱,她不断地诽谤与排挤莉莉,直至莉莉穷困潦倒,走投无路。钱使她丧尽天良,钱也给她以巨大权威。当格蒂为莉莉的遭遇深感不平,要她向世人公开全部真相时,莉莉笑答道:
全部真相?什么是真相?如果事情牵涉到一位女子,真相就是最容易被人相信的那种说法。在这件事情里,白瑟·多赛特的说法要比我的说法可信得多,因为她有一座大房子和歌剧包厢,和她搞好关系也容易。(215)
不仅莉莉,就是西尔维顿,最后也在被白瑟刮得一贫如洗后拒之门外。
总之,这个金笼子是一个物质至上、尔虞我诈、是非颠倒、暗无天日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与精神国一样,也不是绝对的。它里面还存有怀恻隐之心者,比如罗斯代尔。罗斯代尔原是个金笼子之外的犹太人,凭着执着与精明成了华尔街上的风云人物,打进了金笼子。他的直线上升与莉莉的直线下降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照。伴随着各自社会地位的升降,他俩的关系也发生着戏剧性变化。开始罗斯代尔把莉莉视为一件值得拥有的物品,但他逐渐对她产生了真诚的敬慕;起初讨厌他的莉莉后来也发现了他内心“粗俗的友善”(280)。
罗斯代尔对莉莉的友善基于他对莉莉的遭遇的强烈不平。他认为白瑟背信弃义的行为“邪恶至极”。而且他还认为这个“懒惰与自私”的社会也应对莉莉的不幸负责。在这种强烈不平的驱使下,在莉莉拒绝嫁给乔治和坚持还钱给特莱纳等可敬行为的感召下,罗斯代尔的友善得到了令人感动的表现。他主动提出支持莉莉用白瑟写给赛尔顿的那些信迫使她为莉莉正名雪耻,还表示愿意借钱帮莉莉还债,从而使莉莉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粗俗的友善……似乎正在挣扎着钻出他物欲的坚硬外壳”(280)。
在莉莉眼里,罗斯代尔的友善是粗俗,还没有达到赛尔顿那样的文雅程度,但这种友善的可靠性却是不容置疑的。罗斯代尔入木三分地向莉莉指出,要想治住白瑟,“世界上所有的信件也达不到那个目的”(245),但如果有他的雄厚财力作后盾,“你就会叫她任你指挥。 ”(280)相比之下,赛尔顿的友善是文雅的,但他的友善只限于口头。就像莉莉说他的那样,他既反对别人追求物质,又不能向别人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所以,尽管罗斯代尔在莉莉谢绝了他的友善之后说的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粗俗,但也不无道理:“如果我能看到你能从他(赛尔顿)那里得到什么感谢的话,我就不是人!”(245)
霍华德(Maureen Howard)对罗斯代尔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西门·罗斯代尔是唯一一个能真诚对待莉莉的人,是唯一一个……能对她直言的人。在小说中,他被表现为一个极为精明的人,也是一个较有同情心的人。”(注:见莫里恩·霍华德的《〈快乐之家〉:单身汉与婴儿》(The House of the Mirth:The Bachelor and the Baby),载《剑桥华顿指南》,137—156页。)华顿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金笼子里安插了这样一个坦诚而又有同情心的大富翁,无疑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物质的新角度。
三、“海葵”与“岩石”
精神与物质的复杂关系在莉莉这个核心人物身上得到最为集中的体现。可以说,整部《快乐之家》写的就是莉莉努力在精神与物质之间达到平衡而最终却失败的过程。
与只有精神追求的男主角赛尔顿不同,莉莉对精神与物质都有兴趣。他们两人的家庭背景有助读者理解他们的这种不同。在赛尔顿的父母那里,禁欲主义者对物质的漠然置之的态度与享乐主义者的能从物质中发现乐趣的本领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这种家庭背景滋养了赛尔顿轻物质重精神的态度。而在莉莉的父母那里,物质与精神严重对立。莉莉的母亲巴特夫人最忌讳的就是“寒碜”。巴特先生收入不高,但她生活极其奢侈。为此,巴特先生不得不拼命挣钱,晚上回家累得没有精力读他酷爱的诗歌,最后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不久巴特夫人也死了,死前叮嘱莉莉要利用她的天生丽质找个有钱的丈夫,“尽量逃避寒碜”(53)。因此,逃避寒碜就成了莉莉追求物质的动力。但“她的抱负不像巴特夫人的那样粗俗。”(52)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她喜欢把自己的美貌看作行善的力量,比如给她某种地位,使她在这个地位上能在施加她的影响的同时自然地表现她的优良品质和高雅情趣。”(53)由此可见,莉莉从小就有意要将物质与精神结合起来。
要实现这样的抱负,对于一个无依无靠又没有谋生技能的莉莉来说,就是要先找一个既有钱又有修养的丈夫。可以现实中,这样全面的人实在难寻。小说开始时,莉莉已29岁,依然孤身一人。而她这时的三个人选中,没有一个符合要求。格雷斯与罗斯代尔有钱,但乏味或粗俗。赛尔顿修养好,但没什么钱。因此便有了莉莉内心倾向于物质与精神的两个自我的不断冲突。莉莉这样概括了这种情况:“我不得不反复谋划,时退时进,就好象是在跳一种复杂的舞蹈似的,一步错了,就会使我永远跟不上节拍。”(64)但无论她怎样精心谋划,她始终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丈夫。
瑞丝图西亚在谈及莉莉失败的原因时说:“莉莉的柔韧性和不确定性使她不能就范,所以她就遭受抛弃。”(注:见瑞丝图西亚的《莉莉的名字:华顿的女权主义》( The Name of
the
Lily: Edith Wharton's Feminism(s)),载本斯托克的《快乐之家》,404—418页。)这里的意思是,莉莉之所以没有结婚,是她不愿忍受婚姻可能带来的制约,想永远保持自己的“不确定性”。这种说法未免使莉莉过于后现代化。在小说中,莉莉显然是想结婚的。尽管她因候选人不合要求而时常犹豫,但她仍然作了选择,曾先后选了格雷斯、赛尔顿和罗斯代尔,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结果。另外,那些抛弃她的人,比如白瑟,怕的就是莉莉结婚,尤其是与乔治结婚,因此才会千方百计挑拨离间。所以,莉莉遭受抛弃的原因与其说是她想保持“不确定性”而不想结婚,还不如说是她没有结婚,没有获得有力的物质支持。
莉莉追求格雷斯出于物质上的考虑。尤其在打牌输钱之后,一想到有把握嫁给格雷斯,就立即觉着“能飞入那安全的、债主们无法看穿的最高天。她将永远摆脱穷人家的那种东拼西凑、低三下四的生活。”(65)但赛尔顿的出现引起了她内心精神与物质的冲突。这一冲突,再加上白瑟的暗中破坏,导致了莉莉这次追求的失败。当她随赛尔顿散步回来发现格雷斯已离她而去时,她又从“最高天”坠回“牢房”。为了节省开支,她决定立即返回她姑妈那牢房般的住处,去过“便宜”而又“乏味”的生活。
然而,这第一次物质追求的失败给莉莉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她贪图物质的自我很快又抬头。她利用特莱纳的虚荣心使他主动提出替她炒股,不久就得到9千元的收入。可特莱纳并不像莉莉以为的那样, 只是“一出昂贵的演出中的一个跑龙套的角色”(96)。随着莉莉在物质上对特莱纳依赖的增大,她的精神自由越来越少,自己开始演起跑龙套的角色,迫不得已地按特莱纳的旨意干违心事,最后还险些遭他强暴。这一重挫使莉莉转回精神。赛尔顿这时成了“她的唯一希望”(172)。 也就在这时,罗斯代尔前来求婚。而莉莉却发现“钱堆之后的罗斯代尔”更加讨厌,很快就打发了他。罗斯代尔刚走,莉莉就在报上发现她等待的赛尔顿去了哈瓦那。赛尔顿不辞而别是因为看到莉莉半夜三更和特莱纳在一起。莉莉不曾想到,她因贪图物质而与特莱纳做的这笔失败的交易竟然使她付出了两个追求者的巨大代价。
《快乐之家》的上篇写的主要是莉莉的物质追求,而下篇则侧重表现莉莉的精神魅力。她的精神魅力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1.忠诚,2.自尊,3.文雅,4.善良。莉莉的忠诚集中反映在她与白瑟的关系中。白瑟邀请莉莉去地中海旅游完全出于私利,即为了自己与西尔维顿的私情而让莉莉去转移乔治的注意力,但莉莉则因迫切需要新环境忘却痛苦而欣然接受了邀请。凭着她出色的交际能力以及对白瑟的感激,莉莉使白瑟的计划实施得非常顺利。她听不进赛尔顿要她多为自己想想的忠告,认为离开白瑟是一种背信弃义的不道德行为。她就这样忠诚地守候在白瑟和乔治身边,直到白瑟为了保住乔治及其财产而真正背信弃义地诽谤和抛弃她。
在莉莉后来的极为艰难的处境中,她的自尊得到了考验与展现。当罗斯代尔在莉莉表达了同意嫁他的意思后说他因为曾遭拒绝而不想再追求她时,莉莉立即用“略带尊严的语调”做出机智的回答,使罗斯代尔发现“正是她的不可企及的高贵,她不带轻蔑地表现出的距离感,使他感到最难放弃她”(240—241)。莉莉的自尊还表现在不愿领受别人的同情与帮助。乐善好施的格蒂知道,身陷困境的莉莉一直回避她是怕成为她的包袱。当赛尔顿要莉莉立即离开她所投靠的哈奇夫人,去和格蒂同住时,莉莉的“每一种涉及自尊与自卫的本能”(262)都被唤起, 使她断然拒绝了赛尔顿的帮助。
物质的匮乏使莉莉不得不投靠高默夫妇等暴发户。这些人的粗俗反衬出莉莉的文雅。一进入高默夫妇的圈子,莉莉就发现这些人身上的缺点,“从男人们的马甲的款式到女人们说话的变音方式。一切都定在一个较高的调位上,每一样东西都是过多的:过多的噪音,过艳的色彩,过量的香槟,过分的亲近……”(222)。他们对人“不加区别”, “不知或无视那些对于礼貌的细微要求”(225)。这些人的特点是缺乏修养所致。而“她的高超的社交技巧、她的既能适应他人又不丧失自我的习惯、她对其行当中的各种精良工具的熟练掌握”(225 )使她不久便成为他们效仿的楷模。
当然,莉莉的精神魅力中最突出的是善良。乔治曾客观地称赞莉莉说:“你善良——你仁慈——你一贯如此!”(230 )莉莉手头宽裕时善良。她曾慷慨地捐助格蒂的慈善事业。经她救助的一个病魔缠身贫苦女工耐蒂后来不仅恢复了健康,还过上了幸福生活。莉莉身陷绝境后还善良。白瑟写给赛尔顿的那些信最后成了唯一能帮莉莉恢复名声、嫁给罗斯代尔、实现她的生活理想的东西。但为了与赛尔顿的友谊,为她崇尚的道德信念,莉莉背着赛尔顿将它们投入壁炉。赛尔顿最后根据莉莉的遗物意识到他对莉莉与特莱纳之间关系的误解,但他却始终不知道莉莉为保护他及其精神共和国到底做出了多大牺牲。
奥钦克劳斯(Louis Auchincloss )在评论莉莉这个形象在小说中的变化时指出,莉莉开始时像一条“无舵”的小船,“但我们读完全书就会坚信,在那个争吵不休、黑暗至极的城市里,莉莉是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淑女。”(注:见奥钦克劳斯的《〈快乐之家〉与旧新纽约》(The House of Mirth and Old and New New York),载阿芒斯编《快乐之家》,317—318页。)华顿之所以要塑造这样一位物质上不断下降而精神上不断上升的淑女,当然是想强化精神与物质的对立,进一步颂扬精神,批判物质。华顿自己的言论可以支持这一观点。她在回忆此书的构思时说她当时认识到:“一个轻薄的社会只有通过被其轻薄所破坏的事物才能获得戏剧意义。……答案……就在敏感而又充满活力的莉莉·巴特身上:故事就要写莉莉是如何被一个极为麻木的社会一步一步地害死的。”(注:见刘易斯的《华顿传》,150页。)
然而表现在莉莉身上的这种精神与物质的对立,就像发生在赛尔顿和罗斯代尔身上的情况那样,也不是绝对的。例如,莉莉支持格蒂、救助耐蒂、购买白瑟的信等行动,没有一个离得了钱。而意味深长的是,莉莉用于这些活动的钱,都是出自特莱纳给她的钱。在一定程度上,没有粗野的特莱纳的金钱,就没有文雅的莉莉的善举。这一点其实也是华顿想要表达的。她是这样描写莉莉认出她所救助过的耐蒂时的感觉的:“使她感到特别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她所用的那笔钱是格斯·特莱纳的。”(291)可以说,这个“反讽”所针对的就是单纯的精神, 就是那种把精神与物质截然对立起来的做法。在这个意义上,瑞丝图西亚把莉莉的死归咎于像赛尔顿、格蒂这样的思路单纯、喜好简化的“好人”的观点(注:见瑞丝图西亚的《莉莉的名字:华顿的女权主义》(The Name of the Lily:Edith Wharton's Feminism(s)),载本斯托克的《快乐之家》,404—418页。)是有一定道理的。莉莉的死可看作是对与物质势不两立的纯精神的最有力的反讽。
《快乐之家》的书名出自《旧约·传道书》第七章。原句是“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注:见《旧新约全书》,香港浸信会出版部1980年版,755页。)且不论书中谁智谁愚。通过描写莉莉如何从开头的快乐之家坠入结尾的遭丧之家,小说无疑传达出了某种有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的智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莉莉把自己比作一株海葵,把适合她生存的环境比作岩石,认为她的不幸是“脱离了岩石的海葵”的不幸(281)。莉莉对海葵与岩石的界线的突破,不是类似于华顿对精神与物质的疆界的穿越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