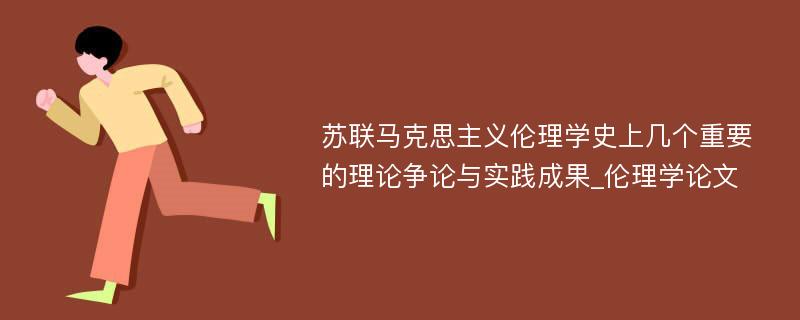
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史上的几个重大理论争论与现实结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几个论文,伦理学论文,史上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伦理学范畴之争确立学术研究的科学转向 20世纪60年代是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诠释其科学性的初始年代。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的那些繁杂多样的思潮已随历史之风荡然无存;20世纪30年代初期直至50年代中期则是一个鲜有争论的年代,不但是伦理学界,整个社会科学界都是这样。从1932年到1955年的《哲学问题》和《哲学科学》杂志的文章目录上看,未见以“争论”或“讨论”为标题的伦理学文章。这大概与斯大林政权力图结束意识形态争论以统一思想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努力有关。 但不能否认的是,60年代的伦理学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萌荫下呈现出明确的体系化特点,这一点恐怕与海啸般的“反斯大林运动”难脱干系,文学领域的“解冻”迅速蔓延至整个思想界,包括伦理学界。事实上,道德理论化就是与开始于1961年《哲学科学》杂志组织的有关伦理学范畴的讨论息息相关的。 伦理学范畴及其本质问题率先引起学术瞩目事出有因。首先,对伦理学范畴问题的关注是学科本身研究纵深化的体现。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还处于感受性研究和全景式解读阶段。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伦理学研究自然地向理论解构的深处进发。伦理学研究自身的发展遵循着一个由浅入深、化零为整的过程,这在客观上反映了学科知识本身发展的科学逻辑路径。随着研究内容的拓宽、研究态度的科学转向,研究深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纵深化发展趋势。在这一前提下,如何科学定论的争论在所难免。诸如伦理学范畴、道德价值、道德评价、道德功能等以往未曾深入涉猎的问题都逐渐纳入争论式研究样态,这在客观上促进了6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理论化的本质性特点的生成。 伦理范畴是反映道德最本质的方面和最基本理论构成的概念,是理解伦理学问题的开端,其他诸如道德本质、道德结构和功能、道德价值、道德判断、道德意识等道德理论问题的研究无不以对伦理学范畴的理解为逻辑起点。而在当时的伦理学界,对于伦理学范畴的界定还有很多分歧和不甚明晰的地方,这个问题不弄清楚,等于学科的研究对象不能确定,那么接下来的问题都将止步于这一原点理论问题。可以说,对伦理学范畴问题的研究构筑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基础和理论前提,是学科本身研究纵深化的开端。 其次,对伦理学范畴问题的关注是伦理学研究从道德意识形态向道德理论化转变的标识。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多致力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道德意识形态建设。那时的伦理学研究与苏联社会主义文化道德建设紧密相连,伦理学的规范作用受到特殊的重视。《道德信念、情感和习惯教育》、《论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和个体的形成》、《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本质问题》、《论培养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原则》、《苏共二十一大和对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问题》、《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某些问题》是1958年到1961年苏联《哲学问题》杂志刊登的伦理学文章的题目。从这些文章标题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道德应然”问题是当时伦理学研究的主题。伦理学以批判资产阶级道德、阐释“共产主义道德原则”、探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实施路径为核心任务,研究的道德意识形态特色突出。随着伦理学日渐纵深的理论解构,更多的伦理学理论问题被放置在核心位置,道德意识形态色彩逐渐被淡化,道德学术理论研究结果渐丰。伦理学研究从关注道德意识形态向关注道德理论本身转化,而有关伦理学范畴的本质问题的讨论正是大幕渐起的支点。 有关伦理学范畴的争论(有文称为“讨论”)从1961年持续到1965年。争论一方的代表是时任高尔基乌拉尔国立大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的副教授Л.М.阿尔汉格尔斯基,另一方是苏联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列宁格勒分所所长А.Г.哈尔切夫教授。争论以Л.М.阿尔汉格尔斯基1961年3月发表在《哲学科学》第3期上的题为《伦理学范畴的本质》一文为开端,以А.Г.哈尔切夫1965年3月同样发表于《哲学科学》的文章《有关伦理学范畴之讨论的总结》为终结。当时一些著名的伦理学者,如А.Ф.施什金、Г.К.古姆尼茨基、Ю.В.索果莫诺夫等人也参加了争论。 阿尔汉格尔斯基一方的观点主要有:第一,弄清伦理学范畴的本质是解决其他理论迷惑的关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对全面分析伦理学范畴、阐释其本质和内部关系提出了要求。而明确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又是把握伦理学范畴的关键所在。第二,伦理学范畴是一些最基本的伦理学概念。阿尔汉格尔斯基指出,伦理学范畴是“一些能反映道德根本特征的最基本、最主要的伦理学概念,如客观能动、具体历史的道德评价标准(善和恶),针对道德职责(义务)、道德责任(良心)、道德尊严(诚信)和道德满足(幸福)提出的道德要求”①。此外,还包括人类行为内部动机的个体道德信念和道德情感。第三,伦理学范畴与道德原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阿尔汉格尔斯基承认道德规范、道德原则、个体道德品质在广义上都可以被看作是伦理学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没有区别。“善”、“恶”作为核心的道德范畴,随着阶级利益和要求历史地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善”的概念更多地反映某种公认道德原则的核心内容,需要道德原则来呈现。“‘善’的范畴的具体内容通过道德原则来揭示,另一方面其他伦理学范畴的内容也直接取决于对‘善’这一核心范畴的理解。”②第四,伦理学范畴是科学概念。阿尔汉格尔斯基认为将义务、良心、诚信和幸福等概念称之为道德范畴是不准确的,这样是对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道德”和作为道德科学的“伦理学”的差别的忽视。日常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习惯是作为社会意识呈现出来的,而伦理学范畴,是科学概念,是对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习惯进行理论分析的结果。间接地反映社会道德原则和道德观念是伦理学作为科学的现实基础。 哈尔切夫一方则在若干观点上持相悖态度。首先,伦理学范畴包含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哈尔切夫认为阿尔汉格尔斯基将伦理学范畴单纯界定在道德意识层面显然过于褊狭,那些突出道德实践性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理应被纳入伦理学范畴之内;道德活动、道德关系和道德意识紧密相连,在逻辑上密不可分,合力构成完整的道德范畴体系;一定社会的道德观念必然是相应道德关系的反映和道德活动的结果。其次,道德属于价值范畴。哈尔切夫认为阿尔汉格尔斯基没有彻底弄清“道德”和“伦理”概念的界限。“道德”属于价值类型,而“伦理学”属于科学范畴。他基于道德本质和道德发展规律的科学性出发,判定伦理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学术特点。“伦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较“道德”更高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特征。“道德”是伦理学研究的对象,它更多地被看成是社会价值意识,而不是科学理论。这一结论的现实影响清楚地表现在伦理学研究从此名正言顺地卸下了以往负载的众多“道德说教”的“包袱”。古谢伊诺夫甚至认为,对这一局限的克服在苏俄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它甚至超越了索洛维约夫的道德哲学体系。③如果这一理论分野能被看作是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自我批判的话,那么,它无疑是后来“伦理学是科学”的开篇词;此外,争论的同时就是对“范畴”概念在伦理学体系中关键地位的确证,“范畴是反映伦理学最本质最主要内容”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这一结论使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迈向体系化和科学化的脚步渐甄极境。事实上,这貌似的小举动背后隐藏了大心思,因为就是不久之后,苏联伦理学对全人类道德规范的研究便大规模铺展开来。 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中期有关伦理学范畴的争论掀起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科学化的大幕,它一边让伦理学更有伦理学的味道,一边慢慢卸载着伦理学道德劝解的功能,为后来走向彼岸、进行另一种批判孕育胎胞。 二、道德判断标准之争奠定理论认识的真理基础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伦理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和伦理范畴的理解熟稔而深厚,经年的理论积淀和深入研究淬炼成研究者的学术自信。理论联系实际地对现实问题进行道德评价和道德判断的积极性增长是学术自信的反映。此外,更多的社会道德实践也给了学者们施展评价实力的空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道德判断铺设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由理论向实践进发的可行路径。当然,还有足够优越的社会环境提供的外部保障:在事实上将《共产主义道德法典》纳入党纲的苏共22大,在客观上拓宽了道德因素的作用范围,道德调节上升至与行政调解几近趋同等值的地位。“在完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上提供了帮助”④,这等于给道德问题进行评判提供了发言权。上述条件都为道德判断标准之争培育了理论和实践语境。 道德判断问题占据当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术高地,有据可循。首先,社会道德实践需要科学的道德判断标准指引。取得长足理论进展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和谐高尚的社会道德生活交相辉映。一方面社会道德风尚总体向善,道德生活规范有序;另一方面,社会道德生活领域的实践也被积极拓展:集体与个人关系的调试、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实施、社会义务的承载、社会利益的分配、创造性劳动的开展等既是道德实践,又是伦理考验。这些考量制度合理性的探索性试验,没有预设范本,全都是实践典型。理论从实践中来,升华后还要指导实践。何以指导实践?唯有科学性能担此重任。这样,道德判断的科学标准亟待确立。 其次,学术研究实践增加了主观认识的参与比重。一方面,社会道德实践的极大拓展需要科学的道德判断标准;另一方面,伦理学的学术关怀也从伦理本体自发地逐渐转向认识论领域,即伦理思维如何认识道德世界的问题。正如汉斯·斯鲁格所言:“首先,哲学家们思考这个世界,接着,他们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⑤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伦理学,能够说明伦理学从形而上学上升到道德认识论,最终走向道德语言哲学的自然进程,这既是规律表现,又是现实要求。与先前对伦理学本质、起源、功能、范畴等基础理论研究不同的是,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中,主观认识的学术参与比重增加了。主观认识是在研究具体的道德理论问题时遇到的。但解决理论问题离不开道德价值立场、道德评价标准、道德判断准则。在此情境下,对道德评价和道德判断问题的研究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当时围绕着道德评价和道德判断展开的研究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其一是道德评价的对象。伦理学界对道德评价对象的界定有广狭之分。广义的界定将人的全部行为均纳入道德评价范畴,狭义的界定则只承认反映社会心理的人的行为、道德规范和道德关系等是道德评价的对象。但广狭之分并未造成学术分歧,有关道德评价对象的界定基本形成定论。其二是道德判断的依据。此前有关道德评价的依据问题未见伦理学者着墨陈词,其原因在于社会约定俗成的道德要求长久地替代了道德评价依据的角色。但道德要求尚且不等同于道德评价,遑论学术意义的道德评价标准。学者们对道德评价依据的认识另取新路,最终皈依到К.А.施瓦尔茨曼和А.Ф.施什金那里:“能够最大程度反映人本性的要求、反映那些为未来而团结奋斗的人的评价标准,才是唯一正确的道德评价依据。”⑥其三是道德判断的知识基础。与道德评价呈现逻辑接续关系的是道德判断,而道德判断则离不开它的真理标准,价值和真理互为逻辑统一。但在苏联时期,直到1962年才首开道德价值研究的学术先河。对道德价值和真理基础的关系问题存在诸多理论分歧,甚至于构成截然对立的论争派别。 两个学术派别的重大理论分野在于是否承认道德判断的真理标准。这一具体理论争论的出现与伦理学界有关“伦理学是科学”的判断密切相关。到1965年,持续了四年的“伦理学是不是科学”的纷争尘埃落定于科学视野,但持不同见解的学者的观点仍在一定范围内保留下来。既然伦理学是科学,那它就应该有客观的道德依据,能兼容多元的伦理思考,经得起道德实践的检验,它的评价标准更要具有实证性。可就在1961年,学界新宠К.А.施瓦尔茨曼还发文立论,直言“新实证主义消解伦理学”⑦。很显然,这样的学术纷争必然导致对道德判断真理问题的立场对峙。以Д.П.葛尔斯基和Г.克劳斯为代表的一派否认道德判断的真理标准。在他们看来,道德判断时常使用道德规范,而道德规范本身并非科学知识,所以不具备认知功能;道德规范系人为操作,故缺少与客观事实相吻合的要素;无法用实证的方法确证道德规范。这一派观点因否认道德判断的真理标准,继而否认“伦理学是科学”的判断。与之相反,以М.本格、А.Ф.施什金和Н.Н.莫克罗乌索夫、В.П.科布拉科夫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坚持道德判断具有真理性。本格在《伦理学研究方法》一文中集中阐释了道德判断具有真理基础的观点:在经验方面,可以把道德判断的标准与描述性的假设相对比,以确定它是否符合于某种实践需要;在逻辑方面,可以通过把道德判断的标准同社会中其他起作用的规范和原则进行对比,以证实这些规范体系彼此之间并不矛盾;在科学理论方面,可以通过把道德判断的标准和对阶级利益和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认识相对比,实现对道德判断的学术理论论证。⑧ 争论基本上以承认道德判断具有真理基础一派的胜利而告终。В.П.科布拉科夫1968年在《哲学问题》上发表的《论道德判断的真理问题》一文中做了总结性陈词:道德判断基于道德认识,因而具有知识基础;真理范畴可以为道德判断提供标准;对道德判断的真理标准进行学术检验理论和实践可行;伦理相对主义在科学伦理学框架内无立足之处。 有关道德判断真理问题的讨论在道德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厚成果。这是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伦理学理论的突出创建,是伦理学研究在认识论问题上的真知灼见,它保证了苏联伦理学在其后的近20年研究的科学性,直至古谢伊诺夫《新思维和伦理学》的发表。这20年间,苏联社会道德生活和伦理学研究方向经历了戏剧性嬗变。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框架下,从60年代的道德意识形态和道德理论形态平衡存在状态,到思想价值体系和科学研究体系呈现最佳统一的70年代,再到思想理论多元分解的80年代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说,伦理学研究在对社会道德活动和道德现象进行的伦理判断,都是坚持真理标准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语境中,伦理学实事求是地反映社会道德生活,在社会历史理论体系中落下公正的道德判锤。到80年代后期,时隐时现,却从未缺场的“人道主义”占据了伦理学术舆论和研究主场,并从具体彻底走向抽象,为“新思维”鼓吹下的“全人类道德”造势,致使道德判断完全抛弃真理标准,走向学术虚无。 所以,有关道德判断真理标准的确定保证了苏联伦理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相当程度地平稳科学发展,对今天俄罗斯和世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世界伦理学轨道上科学运行,仍具有前景性意义。 三、价值问题之争引发伦理思想的多元趋向 从60年代下半期开始,苏联社会的精神生活状态发生变化,变化来自对个体存在意义的确证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对创作自由的追求也产生了发展自由个性的需要。公民责任问题对很多人来说讲成了道德、伦理选择问题”⑨。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足无忧,精神世界鲜活生动,道德情操神圣崇高,批判意识峥嵘渐露。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70年代正式开启了对价值问题研究的破冰之旅。 首先,60年代有关价值问题的讨论先期铺陈了研究基础。1964年4月、1965年3月和10月,苏联先后召开了三次关于价值和价值论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的目的是想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框架内的价值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尤其是道德价值观相区别开来。在价值哲学还是彻底的唯心主义理论的认识时期,针对道德价值范畴的专门阐释是不存在的。理论回避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但是先前围绕着“价值”的讨论为后来热议“价值”推开了方便之门。对伦理学者来说,那些曾经被批判的“价值”理论似乎并不陌生,立场变了,素材还在。而且,向来好走极端的俄罗斯人,在学术上也一样喜欢以今日之美批判昨日之陋。甚至于自我批判也绝不做作,完全发自文化本能。这样,那些从前了解的东西就成了目前研究的极好材料。不能否认,60年代有关价值问题的批判性讨论为70年代的集中研究做了先期素材准备。 其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愈发显现出政治和社会功能。与40、50、60年代不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不再以外部的意识形态迎合为特色,而是研究内容本身对社会和政治元素的容纳。政治决策和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科学的价值指引,对价值问题的关注无疑为具有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意义之问题的解决提供实践思路。比如,А.И.季塔连科的《道德与政治》一书就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和方法进行了伦理阐释;Л.М.季塔连科的《个体理论的社会伦理问题》、古谢伊诺夫的《道德的社会本质》、莫斯科大学伦理学人的集体著作《道德的社会本质、结构和功能》都将道德作为调节社会意识、指导政治决策的行为手段和价值导向来看待,以确定行为和现象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 有关价值问题的立场分歧巨大,推动对价值问题的研究上升到激烈而富于创造力的理论争论境地。В.П.图加里诺夫和О.Г.德罗伯尼茨基各成一派。争论从1970年开始至1974年德罗伯尼茨基的生前著作出版为止,并以后者的胜利而告终。其中,图加里诺夫认为,价值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价值是满足需要和利益的手段;价值是以规范、目的和理想形式呈现出来的思想和动机⑩;价值由生活价值、社会—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三部分构成;价值方法具有重要认知意义;价值具有实践指导意义。而德罗伯尼茨基的认识较之更显系统,其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价值”是包含主客观因素的概念,价值的主观方面应得到重视;价值范畴对于理论认识的意义不大;价值方法可以被科学研究的方法代替;价值与人的认知和意志紧密相连;价值具有社会实践性、历史性和可知性。 德罗伯尼茨基的理论贡献不容置疑,而且他把对价值和道德价值的阐释放到了自己完整的“道德概念”体系中,以严密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的伦理学研究方法逻辑地阐述价值概念的来龙去脉,其价值主观性理论受到学界重视。在70年代其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特别多地强调了道德行为和道德现象甚至道德原则制定的主观因素。同时道德本质的客观内容被逐渐消解,道德价值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在80年代甚至被当成全部人类文化的神经枢纽和行为指南。 道德主观性元素受到重视在客观上给个体道德意识的自由表达推开了绿窗。任何群体和个体的道德行为都受其道德动机促动,受道德意志控制、受道德情绪感染、受道德直觉牵引。这些主观选择的因素被助力发酵,施力于道德群体或道德个体身上,其结果必然引发伦理思想的多元趋向。加上社会文化领域自由活跃的氛围、西方持久不懈的“分化”努力,学术思想和研究取向的多元化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框架下渐成定势。多元化促使伦理学对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迎合性接纳,导致无定论无原则的学术争论激增,思想立场极端化趋势增强。最后,伦理思想的多元化在某种程度上与走向极致的人道主义研究、作为终极道德指南的“全人类道德”原则等一起肢解了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加速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迈向终结的步伐。 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历史中,学术争论犹如一条细细的红线,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最有价值的概念范畴、理论疑惑和现实主张联系起来,为社会历史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伦理学家不甘作壁上观,以争论实现理论创新,解决疑难问题,构筑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逻辑篇章。伦理学范畴之争确立学术研究的科学转向,道德判断标准之争奠定理论认识的真理基础,价值问题之争引发伦理思想的多元趋势。伦理科学转向打开道德认识的真理之门;善价值源于真理,指导成功的道德实践,而摒弃真理的道德价值又有陷入立场多元、形式极端的研究泥沼的可能,甚至成为损害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肇始之源。 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史上的重大争论虽已成为学术过往,但当历史之风浮掠而过,这些争论就显现出了让未来人逐本溯源、明晰是非的独特理论魅力和实践功能。争论本身也是克服社会道德问题的学术反映,这一点恰好说明道德伦理研究和社会发展变化、学术理论变迁和社会制度嬗变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践行理论联系实际的范本。 ①Сушность этических категорнн//Наука философии.1961.3.Л.М.Архантелъск:С.125. ②Сущиность этических категории//Наука философии.1961.3.Л.М.Архангельск:С.119. ③История э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А.А.Гусейнов:М.,ГАРДАРИКИ,2003,С.889. ④М.Г.Журавков:XXII съезд КПСС и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этики,Вопрос философии.1962.2.С.5. ⑤[美]斯鲁格:《弗雷格》,江怡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⑥К.А.Шварцман,А.Ф.Шишкин,О некоторых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проблемах этики,Вопрос философии.1965.4.С.89. ⑦К.А.Шварцман:Неопозитивизм уничитажает εтику,Вопрос философии.1961.1.С.64. ⑧参见武卉昕:《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兴衰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 ⑨[俄]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⑩Теория ценностей в марксизме.В.П.Тугаринов:Л.,1968.С.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