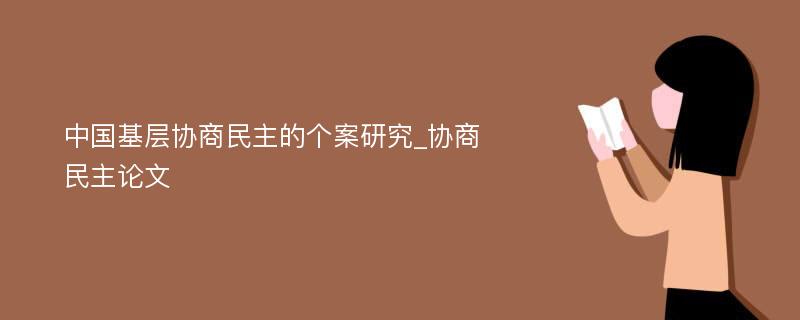
中国的基层协商民主:案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基层论文,民主论文,案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多数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与分析都着重于民主国家。埃尔斯特(Jan Elster)在其编写的一本有关协商民主的书中,将协商民主定义为“由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进行讨论而做出决定”。①冯雅康(Archon Fung)和艾瑞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编写的一本有关协商民主的书,主要讨论了四个案例:巴西有关市政预算问题的“邻里协商”;芝加哥有关地方警务和公立学校问题的“社区议会协商”;美国有关保护濒危物种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协商”;印度喀拉拉邦以促进公平发展为目的的“村级协商”。②这四个地区性协商论坛都由富有改革精神的政府机构建立,它们相信通过赋予民众参与治理的权利,可以拓展民主原则。 中国看起来不大可能像是这种基层创新的代表。但是,与许多人的认识刚好相反,当下的中国有着十分丰富的协商民主实例,它们在远比世界其他地区多得多的民众中践行着。实际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过去的30年中,众多的中国农民都体验过基层协商民主。 在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曾在三类地方——偏远的小村庄,城市中的村庄(即所谓的城中村),以及国有企业——领略过一些人们未曾注意到的协商民主实践,这些协商民主实践有时涉及一些对于参与者而言极为重要的问题。在基层,中国为民主参与或民主程序提供了较小的政治空间:广阔的公共空间为官方组织、倡议和表达等所控制,而非官方的协商活动或独立的社团生活只有很小的生存空间。 我们所考察的三个案例都具备协商民主最直接的形式,即所有协商的相关方都直接做出主要决定,而不仅仅只是施以间接影响。在三个案例中,普通人之间的座谈会是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做出决定,参与者具备所讨论问题的相关知识,且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讨论将所有可能受到决策影响的人都包括在内。在这些座谈会上,往往通过带有道德取向和照顾大多数人利益的理性争论进行说服,小组内部在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且这些集体达成的决定能够得到完满的执行。 文章的结论部分提出了几个关键因素——总体而言,对于世界各地的社区来说,这些因素会增强其协商民主的潜能,甚至对那些缺失国家层面的选举民主或公民自由的国家来说,也并非没有这种可能。 一、农民中的协商民主 在中国农村,协商民主的例子随处可见。这不是指1988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村级领导人选举,这些选举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按照合法的民主形式进行的,并且,即便是这很小的一部分也少见协商实践。相反,我们指的是村级以下的组织,即村民小组内部的协商。 这些村民小组在农业集体化时期被称作“生产队”,那时,15户家庭至50户家庭组成一个生产队,他们共同拥有土地,一起劳动,年底根据每个家庭的劳动贡献大小分配产品和现金。后来,到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主政的早期,土地被包产到户,其分配原则主要是按照各家人数多少而决定。尽管如此,农民并没有获得合法的土地所有权。就是说,直至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是由村民小组集体拥有土地,农民有权无偿使用分配给他们的土地。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农民喜欢这种体制更甚于土地私有化。例如,中国问题研究者2004年对安徽省40个农业县306个农民家庭所做的调查发现,71%的被调查者支持保留中国学者所称的“土地合作社”,只有7%的人表示反对。 之所以如此,一个突出原因是,农业“去集体化”和回归家庭耕种给许多家庭造成了困难。这些家庭发现,随着孩子的出生和家庭规模的不断扩大,他们面临缺地的情况。他们和村民小组成员转而采取一个不寻常的解决办法。2008年,本文一位作者主持了一项对安徽省57个农业县476个村民小组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其中452个村民小组(即95%)自1984年以来至少在各家庭间对土地做过一次重新分配。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土地中的大约3/4要根据家庭人口重新进行均等化分配。简单地说,村民小组决定进行土地再分配,是为了腾出更多土地给那些因生子或结婚而扩大了的家庭,而那些因有人去世或女儿出嫁而规模缩小的家庭就会失去一些土地。 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决定用这种办法解决问题,是基于他们先前作为生产队队员的经验,那时具有确保一个家庭周期③生存需求的机制。在毛泽东时代的早期,粮田由集体耕种,但每个家庭可以分到几块住宅附近的自留地,在上面种些自家食用的蔬菜,但这些自留地每年会随着各家人口的增减而扩大或缩小。那些习惯于呆在生产队中,并用这种经济上的调整来平衡家庭周期所遇到的经济压力的村民们,倾向于继续这样的调整,只是希望用一种更加完整的形式,即以家庭人口数量为基础,定期均分村民小组拥有的土地。总之,土地再分配在静悄悄地继续着。 值得注意的是,自重新出现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以来,这种类似紧密联结的社区一样的村民小组的行动是少有的。由于农业生产是在相对小块的土地上进行的,因此大型机械有时就被废弃不用,而不是在各家庭间共用,农民们也几乎不会将自己组织起来,通过进行非正式的交易或市场化合作以求得市场中的有利地位。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在进行着土地再分配,尽管这很难实施并且在每个村民小组中产生了获益者和受损者。许多家庭明显地感受到这与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息息相关,这就足以使他们摒弃不愿作为一个社区而行动的想法。 这些土地的再分配是通过民主的方式决定的。2008年,在安徽省进行的调查中,调查者问及最近的土地再分配是如何决定的,调查数据显示,68%的受访村民小组表示,应该在小组全体成员家庭参加的会议中由大家投票通过。根据访谈来看,通常的情况是,一些家庭由于规模扩大而形成了再分配土地的压力,他们便要求村民小组组长召集小组会议。安徽的调查数据显示,平均来讲,一次土地再分配要获得小组会议3/4的赞成票才能通过(具体调查数据为74.87%)。实践中,一些村民小组甚至要求更高的同意率。一些受访者告诉我们,如果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会议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会召开一次更长时间的会议,如果有必要,则召开第三次会议,直到他们达成压倒性共识或大家意见一致为止。 要说服那些即将失去一些土地的家庭,关键在于告诉他们土地再分配是为了和家庭周期相一致,在不同的时间有利于不同的家庭。那些此时失去土地的家庭在日后的土地再分配中可能会获得土地。这种情况有时会因为追求公平而得到加强——这是正确的事情,值得去做。这些以及与之相似的看法代表了一种道义经济的观点。埃德华·汤普森(E.P.Thompson)提出的“道义经济”指出了一些因经济环境变化而受到影响的民众,渴求恢复之前时期的一些道德秩序和行动,认为应当用这些价值理念来指导当前的决定,尤其是涉及确保他们的生存需求之时。④正因为如此,需要土地的家庭可以依照盛行于村民小组内部、以保障生存需求的传统精神为基础的共识,来获得家庭周期中的各种支援。 时光流转,随着中国经济的巨大转型,土地再分配的做法变得不太流行了。我们在安徽省的调查数据显示,从1996年至2008年期间,只有33%的受访村民小组进行了土地再分配,以便给扩大了的家庭提供更多的土地。土地再分配率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更多数量的年轻村民离开了农村,去城镇的工厂和工地上找活干了。在许多村子,这意味着对农业的依赖在下降,同时,也意味着村里的劳动力在减少,以及土地的人口压力减轻了。 调查显示,与这种趋势相一致,只有16%的受访村民小组组长认为他们的小组在未来10年中会再分配土地。45%则认为不会,38.5%回答说不知道。但是,与此同时,85%的受访村民小组组长却声称他们个人支持继续进行土地再分配。他们当中的一位认为这样做既是承诺,也体现了公平。他解释说,一些村民在之前的土地再分配中放弃了土地,是希望能在将来土地再分配时重新获得土地。其他一些小组长提醒说,那些长期或永久地到城市务工的村民打破了村民小组内部的土地平衡,因此需要新的土地再分配。还有一些人认为需要为那些外出务工人员建立安全网,因为他们可能会因为丢掉了城镇工厂的工作岗位而返回家乡。 因此,即使土地再分配的做法减少了,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持续变动,这种做法也不大可能会被完全摒弃。未来会怎样做,将取决于村民小组会议长时间协商后能否达成共识。而且,随着其他影响村民小组的更重要问题的出现,可以预料,村民小组会议会继续召集村民聚在一起,用民主协商直至达成共识的办法来做出决定。迄今为止,村民小组集会仍然是影响世界上大部分村民的最普遍的协商民主范例。先是在生产小组内部,再到新名头之下的村民小组,这些邻里之间或共有财产者之间的聚会,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没有理由认为它们在未来几十年中将不再继续。 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继续提速,土地对家庭生计的重要性也在发生变化。下文将会谈到,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比如城镇化的农村,在不同的场景下、用不同的方式就土地利用问题进行的协商已经出现。 二、城镇化农村的协商民主 在中国的一些地区,随着一些邻近城市的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村民小组的土地和村民的宅基地被征用,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而在其他一些地区,村民小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设法保住了他们的大部分土地,并且村民们在这一过程中也获益颇多。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本文的三位作者进行调查的广东省。当然,在中国的其他地区,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况。 在广东的珠江流域——工业全球化的核心地区之一,也是塞满我们储物柜的大多数商品的来源地——保留集体土地是常见的现象。在这一地区,村庄通常被保留在原地,成为居住区;工厂和工人宿舍则建在农地上。为了获得最大收益,村民小组通常(虽然不总是)将一个村的土地合在一起,以形成一片足够大的土地并将之变成工业区。他们也正式注册成立股份制资产公司。通过这个办法,他们的土地就不太容易被上级拿走。在村民小组中,每个村民都有一份股份,他们每年从集体资产中分红,有时甚至超过城市中产家庭一年的收入。 村级公司一般被认为会召开由所有成员参加的大型股东大会,以决定公司的政策和公司领导人的任免,但是,通常这种会议要么没法召开,要么没有或只有很小的影响,其中也少见协商民主。原因很清楚,即将村民小组的土地所有权提升至为整个村庄所有,从之前邻居都可参加并做出决定的没有既定权力结构的一个场所,提升到了由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庄正式组织所控制的层面。作为主导性力量,他们总是同时担任村级资产公司的总裁与主管。由于与这些资产密切相关,普通村民有正当理由向村级公司的领导们实施非正式的集体压力,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当然,这些做法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在笔者曾调研过的珠江流域的一个工业化村庄里,社区的社会压力——意见的力量——成功地阻止了村领导们过分眷顾自己的利益而损害社区的利益。在该地区的其他例子中,村民们必须用强烈的对抗性抗议行动才能对他们的集体财产施加影响。 当广州和深圳周边的村庄被这两个日渐扩展的大城市整合时,一个相似的整合整个村庄的集体土地、保留私人住宅区的过程也曾出现过。其中一个这样的城中村叫“新乡”,由于广州市的扩展未触及这个村的住宅区,不久之后精明的村民们推倒了自家的房屋,私自建起了5至8层的廉价公寓楼,这些建筑严重违反了城市安全和建筑的有关规定。他们招来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租住在这些房租不菲却极易酿成火灾的公寓楼里。 这些还不是他们的收入的唯一来源。广州市政府将大部分村庄的农地征用以建设道路和城市社区,村里的股份公司得到了足够的补偿,并将大多数收益分给了村民。但是,一些村民抱怨那些既是村长又是村党支部书记的股份公司领导人做事缺乏责任感和透明度。根据正式规定,每个村民在其中都占有股份的公司,应该每三年举行一次领导人选举,但是,实际却并非如此。由于控制着大量资金,村级公司的领导们已经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强有力的、自我固化的职位。当新乡的住宅区日渐成熟而有利于再开发的时候,不信任感开始涌上人们的心头。 2007年,广州市政府提出了“重建新乡”、将村民们自己建造的公寓楼改造为办公楼及高级公寓的建议,引发了村民们的强烈争议,不少人对放弃控制自家房屋租金而更多地依赖他们并不信任的股份公司的领导人十分警惕。村民们要求公司公开财务情况,并在未来的再开发中与村民们协商。公司与村民之间的争论导致市政府的介入。迫于压力,股份公司做了部分妥协,公布了村民们所要求公开的财务信息,并且在2009年组织了三次家庭调查以获得村民们对重建、开发的意见。每次意见调查都将详细的问卷调查表和最新的开发计划送达每个家庭。 意见调查结束之后,又组织了两次大型的、公开的座谈会,公司所有领导人都出席了座谈会,村民们公开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在这两次会议上,村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协商的结果是公司建设办公楼与高层居民住宅楼的混合体,它们将属于本地村民私人所有并容许出租。村民们有权将这些公寓和租金收入传给后代,但是不能将任何一间公寓出售给非本地村民。包括所有的公寓楼在内的这些财产的所有权属于股份公司所代表的集体所有。村民们支持由公司或村集体最终保留资产所有权。村民们普遍的想法是:村里的土地是祖先留下来的,所以是神圣的,应当永远传承下去,而不应该用来出售以赚钱。这些土地永远属于作为一个群体的他们的集体所有。 这种想法看起来令人惊讶,因为在当今中国的城市里私人资产市场已是常态。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因为时间久远许多村民都不记得了——村庄土地就归集体所有,他们接受这种做法并觉得挺好。这是毛泽东时代的特殊遗产与他们的社区情感之间的共鸣。 这种情感也受到华南地区家族传统的影响。新乡有四个大家族,但传统上有五个祠堂。作为资产再开发的一部分,村资产公司负责修建了五个昂贵的新祠堂。修建祠堂的地块将完全用于非商用目的,这不应当是一个正常的追求利润的公司所为。但是,公司管理者或村领导人也只得服从民众的这些意愿和信仰。 通过村民之间非正式的讨论以及正式的公开座谈,协商民主取得了成效。在中国,有成千上万类似的集体股份资产公司,为民意表达和在关键时刻通过协商的办法作出决定提供了平台。在新乡,村民们希望将来在社区作出重要决定时能够对决策产生影响,决策过程会受制于基层的压力。 三、国有企业里的协商民主 我们所了解的中国搞得最好、最为广泛的基层协商民主案例,发生在一个内陆大城市的成功的国有酒厂里。这家酒厂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打开国门走向市场经济后繁荣起来。30多位受访者向我们追忆了1994年发生的一次热烈的协商民主活动,当时,该酒厂领导人决定用一部分利润购买一大块空地,建一个新住宅楼,供厂里300多名工人使用。那时,大多数工人还住在散落在城市周边的年久失修的房子里。因此,建设计划一宣布,工人们立刻就充满了热切的期盼。 为了遵照90年代中期的国家相关政策,新住宅楼将以低于市场价的售价出售给工人。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谁有权优先得到这些新住宅,谁又有机会能够买到最好最大的房子?为了避免有人偏袒,国家政策规定每个企业都应坚持在透明的基础上制定一个积分制度。这些政策强调以工龄为原则,规定每在企业工作一年就可获得1分的积分。此外,企业还会给予受过高等教育者、有一定技术职称者和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以额外的积分。 酒厂指定了一个由16人组成的筹备小组,其中包括来自公司不同部门的13名代表。小组走遍了这座城市的其他企业,调研如何确定谁有权优先得到房子。他们发现存在巨大的差异,在一些企业中,即便是企业最高领导人也只能额外给1分的积分,工程师可获得0.5分,这些额外的积分和工人每工作一年所获得的积分相比,就变得不怎么重要了。在其他一些工厂里,厂领导则可获得20、30甚至40分的额外积分。 当调研还在进行之中时,一些酒厂管理人员提出意见,明确支持后一种做法。企业领导人指定由自己和其他8名副职组成一个9人房屋分配领导小组,私下商议应当给那些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较多的额外积分,哪怕他们是新进人员。关于这一情况的谣言很快四处传播开来。对于工人们来说,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机会,他们可以将房子留给自己的儿孙辈居住。 一些于70年代早期作为工人进入酒厂工作的后来的中层管理者们起草了一份请愿书,抗议谣言中所说的做法,提出住房分配的主要标准应当依据在企业里服务时间的长短。许多普通工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字,包括大多数生产车间的工长或领班,以及上了年岁的白领职员。这些人都诉诸道义经济的观点来支持他们的看法,但是,他们的观点却有别于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工人之间那种常见的道义经济争论。那时,与这个酒厂的情况大不一样,许多国有企业财务状况很差,政府要求它们裁减工人,大批工人因此被辞退。这些下岗工人对被辞退的回应方式是诉诸之前毛泽东时代的官方说辞,即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并暗示人们应当对工人抱有一份感激之情,特别是那些年纪大的人。90年代,酒厂的工人们还记得这种观念,铭记在心,并利用了这种观念。不过,他们采取了一种非常不同的道义经济的方法。与中国其他许多地方那些受到下岗威胁的工人怀念毛泽东时代不同,这个酒厂的工人们认为他们忍耐了以前岁月的极度贫穷和困苦,为企业和国家的利益年复一年地努力工作,是他们自己建设了这座酒厂。利用原先的一些官方说辞,工人们认为今天的酒厂领导负有一份必须善待他们的道义责任。他们希望企业领导能够赞同他们的观点。 埃德华·汤普森在一篇分析18世纪英国城市因为食物匮乏而引发暴乱的文章中提出了“道义经济”这一概念。他指出,在暴乱中,“拥挤的男女被告知一种观念,即他们是在维护传统权利和习惯,任何触犯这些道义观念的行为,正如实际的剥夺一样,都是采取群众行动的正当场合。”⑤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用扩展了的道义经济概念来理解有着紧密社会联系的前资本主义的东南亚农村。在斯科特的描述中,贫苦农民持有的道义经济观念通常不需要什么暴力抗争即可奏效。通过社区内意见和舆论所形成的压力,富裕农民和地主被迫用慈善行为进行再分配活动,或者在干旱时以降低租金的方式来迎合大多数穷人的经济公平观念。简而言之,那些拥有财产的人会共享社区的道义经济理念,并乐于接受源自社区的压力。毕竟,道义经济假定了个人之间的敌对和对抗是不能借重的,成功的抗争要依靠社区内有权者对“共享的道德观念结构以及有关何为公正的共同观念”的遵守。⑥ 这就是酒厂里发生的事情。当酒厂领导人——同时也是党委书记——收到那些要求按照在酒厂服务年限的长短而享有获得房子的优先权的请愿书时,他召集了一次酒厂中层干部会议。他们大多数人都已在公司工作多年,并且获得了提升,也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字。酒厂领导人认同了他们的要求的正当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酒厂领导人明确指出,像房子这样重要的问题不应该由企业领导简单地决定如何进行分配,而应该交给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去决定。中国国有企业里的这种会议体制是由苏联和东欧历史上所谓的职工大会发展而来。在理论上——尽管在实践中并不常见——职工大会有权审查企业的主要战略决策,特别是那些有关企业命运的决策,如所有权的变更、与其他企业的合并、宣布破产等。职工大会还应该有权反对新领导人的任命或者解除现任领导人的职务,在工资、企业安全、工人福利、住房等问题上也都享有发言权。但是,职工大会往往由企业的工会组织,而工会则是企业的一个管理部门,因此,在现实中,职工大会通常不起什么作用。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管理权力的扩张,以及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陷入财政困境,职工福利开始被削减,工人数量也被缩减,很少有国有企业再继续召开职工大会了。不过,也有职工大会比较活跃的案例,比如1998年辽宁省有2300多名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因为未获企业职工大会60%的信任票而被辞退或降职。同一年,天津有660名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被解雇,另有1550名企业管理人员因所获职工大会信任票低于50%而被降职或更换岗位。 21世纪初,对一些国有企业的研究表明:虽然在大多数企业里,职工大会只起橡皮图章的作用,可是,即便如此,它们仍具有一些意义。比如,在一个受访的科研机构里,员工们由于对一些同事将科研经费挪用于谋取私利不满,突然“发现”了职工大会的力量。自此以后这种大会开始定期召开。 在其他国有企业,比如这家成功的酒厂里,直到21世纪,每年仍会举行一至两次职工大会,实际上,有时候是企业领导人自己发起召开职工大会的。 1994年的那次大会在几个月内共召开了三轮长时间的会议,每轮会议中间休会几周。每次休会之初,每个车间的所有职工会在车间会议上讨论大会上的协商事项,讨论有时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职工们一个接一个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接下来的几周,同事们之间还会进行非正式的讨论。据受访者所说,有一种表达和坚持公共意见的意识发展了起来,代表们带着车间意见的重托再回到下一轮大会议程中去,以影响大会进程。受访者当然不会使用“协商民主”这个词,但是,他们所描述的情况却正适合这一概念。通过这些协商机制,许多特殊问题在车间内或职工大会上得到了解决。该企业的大多数部门主要由蓝领工人组成,他们希望用在他们看来比较公正的方式公平地获得住房,他们的意见会一直保持到大会作出最终决定的那一天。最后的结果是:企业领导都排得很靠后,最好的房子没有分给他们,而是分给了级别较低的老员工们。 在我们调研的中期,这家酒厂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3年,当我们坐在一户人家门外的院子里时,有人指给我们看当天的地方报纸,其中一个标题显示,酒厂管理者会在不久之后收购公司资产,将其私有化。在当时,这种收购越来越普遍。为了使收购更加正式,这家酒厂召开了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以批准这次收购,但是,会议是由上面控制的,文件是在会上发的,会上宣读了关于收购提案的报告,其中包括所有的细节,但是,会议代表们却并未深入了解情况,也没有提出什么疑问。他们不理解提案的复杂性,也没有做好准备去质疑其合理性。会议代表们提出的问题都是围绕着个人担心的事情,如私有化会给就业、退休和退休金发放等造成什么影响。在没有进行实质性讨论、也没有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该企业的私有化就通过举手表决获得了通过。 酒厂虽然私有化了,但是仍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以温和的作风对待工人。然而,在一个私人公司里,职工大会很难再存在下去,我们也很怀疑它今天还能否发挥真正的作用,尽管职工大会继续存在于许多控制着国民经济重要部分的国有企业里。据报道,有些这样的职工大会仍在正常发挥作用,当与职工相关的事务增多时,它们仍可作为潜在的协商平台。 四、更高水平的参与式民主之障碍 尽管参与式的决策协商在许多场合实行,但是,中国的环境氛围不太有利于基层实施更高层次的非政府控制的协商民主。有时,城市会就公共物品使用率这样的问题举行听证会,但是,人们并不清楚这些听证会是否真能影响政策。像中央政府一样,每个县、市、省都有一个固定的政治协商会议,但是,政协委员主要由党组织推荐以及由精英人士组成。政府制定政策时希望能掌握良好的信息,特别是忠诚的专家所提供的信息。这种咨询渠道对于非精英、非专家或非学术人员是关闭的。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各类协会会提供有组织的场所供选民们去表达和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而影响公共政策。这种介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会是公民社会的要素。组织化的公民社会在中国非常薄弱,因为政府强调所有的协会都要注册登记,并且由一个政府部门主管。这是一种典型的国家社团主义。一些地方性组织,如果确实没有什么危害,比如一些邻居之间的慈善团体,其志愿者志愿提供一些必要的社会福利服务,就会被允许在国家社团主义框架之外运作。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比如一些小型环境组织,则巧妙地在政府的监管下存活了下来。但是,一般来说,协会的存在必须屈从于国家的或地方政府的社团主义框架,其中很少有自主的、哪怕是半自主的协商空间。 总之,我们所观察到的三种类型的案例表明协商民主在中国确实存在。但是,我们所考察的丰富的实际案例却无法与基层之上的任何更高层次开启协商,基层与上层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断裂。 协商民主理论家约翰·德雷泽克(John S.Dryzek)写道:“如果中国确实有什么协商能力,它可能存在于地方层次上的参与式创新之中,这些创新主要是被用来应对经济高速增长而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副作用的。中国国内那些对中国的民主化感兴趣的人士可以从这种地方能力中寻求构建民主之道。”⑦我们对德雷泽克的这一设想的最后一句话,即他有关从地方能力中构建民主的那句话,有些怀疑。 五、结论 虽然中国有组织良好的控制架构,但是,在基层,中国那些直接参与过基层协商民主的人的数量十分庞大,尤其是过去30年中国大部分农村家庭卷入到农地再分配的过程中,而这些再分配是在村民小组的协商会议上集体决定的。 本文所描述的协商民主案例并非中国存在的仅有类型。其他研究者考察了大量其他的协商民主场景,包括一些市政府所做的通过代表小组调查民众的政策倾向实验、咨询委员会、听证会参与式预算协商机制等。总的来说,与我们所描述的基层情况相比,这些场景都更加精英化并受到更多的控制。实际上,最近一篇有关协商民主主题的文章认为中国是“威权主义式协商”,其中“大多数活动都包含着政府对议程的高度控制,但也有咨询和协商”。⑧另一篇有关中国协商民主的文章也指出:“迄今为止,研究表明,在中国发展协商政治,特别是建立商议机构,是为了收集或整合公共意见,使之进入政治决策过程,而不是要分散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因此,在目前的协商实践中,我们看到的最重要的中国特色就是政府的主导性角色,这一点也不奇怪。”⑨ 相反,本文关注的是基层协商,在基层,形成决策的动力源自社区内部,官方并不最终控制议程,并且协商能够引导大多数社区成员积极参与进来。 所有其他研究者的案例中提到的协商平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都没有先例。可见,它们是为了解决新问题而发展起来的新实践。在毛泽东时代,生产队开会讨论每年的作物轮作等工作计划,但是不允许决定更大范围的事情,这与后毛泽东时代村民小组均分土地不一样。广州市新乡的村股份公司召集的长时间的村级讨论会在毛泽东时代也没有先例。在毛泽东时代,工厂的职工大会废弃了1/4世纪之久,在邓小平掌权后才重新设立。 但是,源自于毛泽东时代的观念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近期中国的协商平台?这在其他人的研究中看不到,也许原因在于上述问题与他们所研究的协商平台所要处理的问题并不契合。这些平台中的精英参与者也不会认同嵌入其中的道义经济观念。 相反,有关毛泽东时代的情感和观念在我们的案例中的基层工人身上明确起了作用。官方支持的理想格外看重物质平等,强调工农的价值,以及社区共享观念。正如本文中阐述的那样,历史赋予后毛泽东时代的普通民众以观念和话语遗产,有时,当他们在社区中碰到一些重要问题时,就会使用这些观念和话语遗产。人们现在已经能够选择他们想要的之前那个时代的语言或观念,摒弃其中的一部分,而关注那些依然吸引他们的几个特殊方面。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协商中策略性地使用过去的语言或观念,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现象。除了1966年中期到1968年中期文化大革命这两年的混乱时期,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几乎是一切重要问题都由党的官员自上而下进行决策,基层组织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真正的想法或参与会议进行协商。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考察,可以概括出如下几个促进协商民主的因素。 第一,参与者都有一种属于某个社区的情感,并伴有相应的物质利益。酒厂在毛泽东时代以及后毛泽东时代的早期形成了一种氛围,即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工厂,酒厂应当注重成员之间整个工作生涯中的共同联系。在这种特殊的单位中,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形势又加强了这种情感。在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酒厂领导必须关注实现党和国家的目标,在工作场合几乎没有空间去关照别人,因为他们无法决定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些都是由上面决定的。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年代里,国家允许企业保留大部分利润,并且由企业自己决定如何使用这些利润。然而,90年代,许多国有企业没有利润,实际上经常处于亏损和萎缩状态。在酒厂和其他一些同样盈利的国有企业中,工人们觉得他们在企业的繁荣中有一种既得利益,相互之间也有一种特别的共同联系。 更加明显的是,村民小组都是些自然形成的亲密的社区,有时还有共同的祖先这样的血缘联系。几十年的共事和共有土地的经历加强了村民小组的内部归属感。同样,城中村是一个古老的社区,在这里,邻里之间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如今,周围居住着大量的外来人口,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祖先的身份意识。在这三种类型的群体中,共享社区的情感为共同协商以作出决定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第二个促进协商参与的因素,是所有这些群体面对的是相对容易理解的具体问题,各群体成员在这些问题中都有着直接的利益。在酒厂,能否有机会获得体面的住房是工人们首先关注的问题,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有资格去讨论谁可以优先获得住房。村民小组里的所有家庭在获得足够的耕地这个问题上有着巨大的利益关系,并且他们从集体化时期分配自留地时起就对土地分配非常熟悉了。城中村居民的关键利益在于建筑的重建,他们都希望保留租金收入。这些群体的成员都有无数理由去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协商。 第三个促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因素,是尽管官方并不控制甚至也不影响这些协商,但是,所有案例中那些嵌入在正式框架中的协商平台都是由官方自上而下建立的。本文所讨论的国有企业分配住房的案例,就是在职工代表大会框架内进行的,这个机构是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在国有企业里重新建立起来的。村民小组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中央政府决定在去集体化时期保留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以及原来的村民小组。在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则被允许以股份公司的形式保留村级机构和集体财产所有权。在每个案例中,可以由上级政府同意、批准甚至推动而召集特别会议以讨论紧急问题。有关住房问题的协商会议就是企业领导人的创意。讨论城中村如何重建的大型公开会议,就受到了市政府的鼓励(因为他们想解决矛盾),并且是由村/资产公司的领导组织的。村民小组不需要秘密集会去讨论土地再分配问题,因为他们没有理由担心县或镇政府会反对。恰恰相反,农村干部对农民所面对的困难是同情的,所以从恢复家庭农业的头10年,直到1995年,经常是县和乡镇政府官员采取主动,建议村民小组讨论决定是否需要进行土地再分配。到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禁止再分配土地之后,这些官员就不再提出这样的建议了,但是,地方官员也不会刻意干涉土地再分配以表示支持中央的政策,相反,他们选择对村民们的召集小型聚会视而不见。没有哪个村民小组的小组长记得上面曾给过他们什么压力以阻止再分配土地。 这个推动因素同时也揭示了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局限,协商平台需要地方权力部门建立或批准建立,至少是一个默许的协商平台。这是因为官方并不允许在基层以上层面的普通民众之间进行这样的民主协商活动,也不允许这种协商的影响力超越任何地方性事务。 *本文译自《政治与社会》(Politics & Society)杂志2014年第4期(第42卷)。 注释: ①Jan Elster,ed.,Deliberative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1. ②Archon Fung and Erik Olin Wright,eds.,Deepening Democracy: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in 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London:Verso,2003. ③家庭周期,又称作家庭生命周期,指的是一个家庭从诞生、发展直至消亡的运动过程,它反映了家庭从形成到解体的运动变化规律。 ④⑤E.P.Thompson,"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Past and Present 50,No.1,1971,esp.pp.78-79. ⑥James C.Scott,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p.167. ⑦John S.Dryzek,"Democratization as Deliberative Capacity Building",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2,No.11,November 2009,p.1383. ⑧Baogang He and Mark E.Warren,"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The Deliberative Turn in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9,No.2,June 2011,p.278. ⑨Beibei Tang,"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The Dimensions of Deliberative Capacity Building",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9,No.2,July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