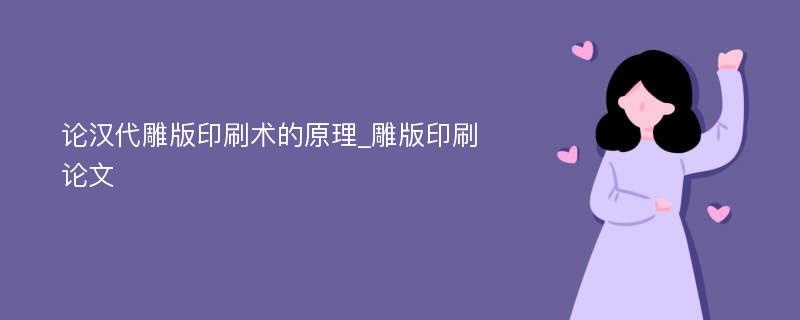
论雕版印刷术原理发明于汉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刷术论文,汉代论文,原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3)03-0113-05
将文字及图案以阳文汉字(图)的形式刻在整块木板上,木板上施墨,覆以纸,再用特制的刷子刷纸,刷完一张再刷一张;如此,则木板上的文图转化为了纸上的正字文图——是谓刷印,亦即印刷。换言之,这便是所谓的雕版(板)印刷术,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历来是学术界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以往的主流观点认为在唐代贞观年间,例如,我国著名的印刷史研究专家张秀民、魏隐儒先生均主此说。近年来“隋代发明说”后来居上,似乎已成定论,例如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在他出版于2001年4月的新著《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中便一改他主编的《中国编辑出版史》(1996年12月第1版)中主张的“唐代发明说”,明确而肯定地认为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于隋代。的确,“隋代发明说”也具有切实充分的理由,因此将“唐代发明说”在时间上提前为“隋代发明说”,现在来看是完全成立的。
魏隐儒先生在其《中国古籍印刷史》之第七章《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中,比较详细地介绍排比了关于雕版印刷术发明时间的7种不同观点。为了说明问题,在此不妨先转录如下。
一、主张雕版印刷始于汉代的,有清代的郑机(字春园,清咸丰同治间人),他在《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卷十二“杂考上·人事”里说:“汉刊章,捕张俭等,是印版不始于五代。”意思是说后汉山阳高平人张俭,因反对当时有权势的宦官侯览,而遭到“刊章讨捕”,到处亡命。什么是“刊章讨捕”呢?元王幼学《纲目集览》卷十二说:“‘刊章’两字,以为印行之文,如今板榜。”这是说“刊章”等于后来通缉犯人的布告。把布告刻板刷印,张贴各地,自然比一张一张的书写要快得多了。
二、主张雕印始于晋成帝咸和年间的,有19世纪末的法国人拉古伯里(Terriende Lacouperie),他根据《蜀志》、《后周书》,认为晋咸和时蜀中成都就已有了雕板印刷的书(转引自向达《唐代刊书考》)。
三、主张雕板印书始于六朝的,有清道光年间的李元复,他在《常谈丛录》卷一说:“书籍自雕镌板印之法行,而流布始广,亦借以永传。然创之者初不必甚难,以自古有符玺,可师其意,正无待奇想巧思也。窃意汉蔡伦造纸之后,当魏晋六朝宜有继起而为之者矣,但未盛行耳。乃谓肇兴于宋,是其不然……”
四、日本岛田翰认为雕板印刷图书北齐以前就已经有了。他说:“予以为墨板,盖昉于六朝,何以知之?《颜氏家训》提到: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夫书本之为言,乃对墨板而言之也。颜之推北齐人,则北齐时既知雕板矣。”(见《古文旧书考》卷二“雕板渊源考”)
五、主张始于隋朝的,第一人是明朝的陆深,他在《河汾燕闲录》中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造,此印书之始,又在冯瀛王先矣。”继其说的又有明朝的胡应麟,清代的方以智,近人孙毓修等。
方以智在《通雅》卷三十一说:“雕板印书,隋唐有其法,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今则极矣。……废像遗经,悉令雕板……”
近人孙毓修在《中国雕板源流考》里,除沿袭了胡应麟的说法外,又说:“按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亦谓隋代已有雕本,是我国雕板托始于隋。”同时又引罗振玉的《鸣沙石室秘录》说:有宋太平兴国五年,翻雕隋刻《大隋求陀罗尼》为据。
六、认为雕板印刷始于唐朝的,《旧唐书·文宗本纪》载:“太和九年(827年)十二月,敕诸道府,不得秘置日历板。”唐梆玭在《柳氏家训》序中说:“中和三年(883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见《旧五代史》卷四十三《唐书·明宗纪》小注引)
孙毓修在《中国雕板源流考》里介绍了《开元杂报》是唐人雕本。1958年方汉奇也为《开元杂报》撰文论述,题为《中国最早的印刷报纸》,发表在《北京日报》上,说是唐朝统治者的宫廷邸报,认为它和清代的宫门钞相似。因为它出版于唐玄宗的开元年间,所以后人就称它叫《开元杂报》。内容大部分是皇帝的言行,如皇帝某日去狩猎,某日接见某大臣等日常生活或国家大事的记录。孙氏曾说:“湖北江陵有个杨姓,家中藏有七张《开元杂报》,叶十三行,行十五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中缝,犹唐人写本款式,作蝴蝶装,墨印漫漶,不甚可辨。”这份杂报不但刻印得早,而且是中国和全世界最早的印刷报纸。英国的学者在《大英百科全书》里也承认《开元杂报》为世界第一份报纸。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资料室藏有仿制的原件。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说:“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耳。《柳玭家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
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三,引宋《国史志》说:“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学小书。”
清王士槙《居易录》卷三十四说:“刻书始于五代,昔人率以为然。予按司空表圣《一鸣集》,有为东都敬爱寺募雕刻《律疏》印本疏云:自洛城□□,乃焚印本,渐虞失散,欲更雕锼”云云。则唐已刻书,此其昭昭可据者。
近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一说:“书有刻本,世皆以为始于五代冯道,其实唐僖宗中和年间已有之……吾以为雕本始于唐。……唐元微之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有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之语。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也说:“夫刻石亦可云摹勒,而作书鬻卖,自非雕板不可,则唐之中叶吾浙亦已有刊板矣。”
七、认为雕板始于五代的,宋王明清《挥麈余话》卷二说:“毋邱俭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孟蜀为宰相,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
明罗颀《物原》说:“周宣王始刻文于石,五代和凝始以梨板刊书。”
明陆深《金台纪闻》说:“后唐明宗长兴三年,令国子监校完《九经》,雕印卖之,其议出于冯道,此刻书之始也。”
明杨慎说:“孟蜀后主,崇尚《六经》,恐石经本流传不广,乃易木板,宋世称刻本始于蜀也。”
清万斯同《唐宋石经考》说:“按五经镂板,《宋史》谓始于周显德,不知唐长兴、晋开运已先有之。世言冯道始镂板,官鬻于世,盖射利也。其射利未可知,而创始之功实被于万世。”
关于雕版印刷术发明时间诸说,又可参阅肖东发先生《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一书中“雕版印刷发明时间各说一览表”。
笔者按:当然,后来又发现了隋大业三年(607年)《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唐《陀罗尼经咒》(四川成都)、唐《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韩国南部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唐咸通九年(868年)《金刚经》等印刷品实物。
魏先生对以上观点作简略分析后的结论是“唐代发明说”。与本文论题具有直接关系者,是他以为:“以为始于汉、晋、六朝的,似乎过早了些,没有什么足够的理由和有力的证据使人信服。假使说后汉已经有了雕版印刷术,为什么对以后的四五百年再也不发生一点影响呢?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作者认为,雕版印刷术是一种具体的科学技术。它的发明完全是一种技术发明。大凡一种技术发明,均不是凭空偶然产生的,总是有其发明的技术原理或技术基础的,并且建立在这上面。研究雕版印刷术的发明,需要特别重视其技术原理的因素及主要材料的因素。这二个因素,正是我们以往忽视了的因素。从上引7种观点来看,基本上都是从文献记载中找资料来论证的,而普遍忽视了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和内在逻辑上予以科学理性的考察。如果我们这样去做,那么,不仅中国雕版印刷术原理发明的年代会大大前提,而且上述这7种观点均将由此而获得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成立。对于任何一种科技发明而言,其科技原理的发明应是其核心的发明。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科技发明应是其科技原理的发明。换言之,没有科技原理的科技发明,就不是真正的科技发明。雕版印刷术作为中国之于人类的一项伟大科技发明,实为一种科技原理的发明。它的科学技术原理,就是人类关于印刷的原理。这一原理,直到现在还没有变。现在全世界的印刷业,基本上还是对这一原理的实际应用。
从材料上讲,雕版印刷术最主要的材料就是“木材”。文字是被雕在木板上的,所以才称之为雕板印刷术。把文图以阳文反字(图)的形式雕在木板上,这是雕板印刷术的核心技术。没有这一核心技术,也就没有雕板印刷术。至于具体雕在什么样的木质(诸如枣、梨、柳等)上,印在什么样的介质(诸如纸、布、帛等)上,以及印成品具体做什么用,这些问题,已经不再是雕版印刷术技术原理的问题了。诸如这些问题,应当属于雕版印刷术的具体应用问题。
正是从这一意义——雕版印刷术科技原理——雕在木版上再施印上立论,本文才认为,中国雕版印刷术原理发明于汉代。再者,过去一直认为套色印刷技术发明于元代,其证据为朱墨两色套印的元代后至元六年(1340年)中兴路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注解的《金刚经》。其实不然,套色印刷技术,在现在看来,也出现于汉代,而且是三色套印,其技术原理完全同于今日之多色套印,而实为其祖。
本文的观点,即雕版印刷术原理及其多色套印技术发明于汉代,主要是立足于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1972~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现。
我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其《中国文明的起源》之第二章《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中谈到了这项考古发现。他说:“马王堆汉墓中还发现几件印花的纱绢。印花技术似乎采用阳纹板(或凸板),但是镂空板印花也是可能的。其中一件金银印花纱,是用三块凸板各印一种颜色,成为三色套板。另一件是印花敷彩纱。这里先用凸板印出藤蔓作为底纹,然后用六种不同颜色的彩笔填绘花纹的细部,如花、叶、蓓蕾和花蕊之类。这几件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印花绢,时代在公元前二世纪之末。”
显然,从这两件印花纱绢的印制工艺来看,完全符合雕版印刷术原理。熟悉中国印刷史的人都知道,即使在中国的唐宋元明清时期,一切雕版印刷的工艺(包括多色套印、饾版印刷、连套带敷),均没有脱离(或超越)这两件汉代纱绢的印制原理。也就是说,无论是我们称之为雕版印刷术者,还是称之为套印、饾版、版画、套敷并用者,其原理乃至具体工艺,均已在汉代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这两件印花纱绢上完全具备。
惟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汉代是印在纱绢上,隋唐及其以后是印在纸上;前者是用于穿着,后者是用于阅读。笔者在前面已经讲过,这一区别是无关紧要的,它并不是科学技术原理——雕版印刷技术原理上的区别,因而也就无妨于这一技术原理的发明及成立。换言之,至于印在什么材料上作什么用,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而不是技术问题了,亦即不是雕版印刷科学技术原理问题了。
雕版印刷技术原理一但获得发明,从理论和逻辑上来讲,凡是需要并且能够用于印制的物质材料,均可以印上去。至于汉晋时代雕版印刷术原理没有在图书出版领域大放光辉,其中原因,主要还得从中国出版史自身去找。这一时期纸的质量及产量问题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一项新发明新技术的广泛采用,总要经过一个过程,这在古代中国尤其如此。即使按“隋代发明说”来讲,不是也直到唐末五代才大放其光辉吗?而整个煌煌唐代,万物并辉,为何偏偏就雕版印刷术默默无闻于“手抄之鼎盛”之下呢?从文化上来讲,从根柢上来讲,这完全是由中国文化——农业文化的保守性所致。
真正的价值在于,雕版印刷技术原理获得发明后,无论是何种原因,一但条件具备,它就必将会在某个相应的领域大放其光辉。这也就是直到唐末五代雕版印刷术原理才开始在中国古代图书出版领域大放光辉的一般原因。只要我们稍具一些中外科技史的知识,就会认为这种情况很正常,而不以为奇。例如,当初科学家研究“克隆羊”,谁会想到“克隆人”及其一系列复杂的人类问题及社会问题呢?水开了自然要顶翻壶盖,又有谁当初会想到瓦特由此发明了蒸汽机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呢?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所以,中国汉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技术原理,这并不妨碍这一科技原理直到唐末五代才在图书出版领域“大放光辉”,而后者也更不能成为“汉代发明说”不成立的理由。
我们从中国科技史话丛书之一《纺织史话》中还可以读到三条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材料。
其一,“马王堆出土的金银色印花纱,是用三块凸纹版套印加工的。有些地方由于加工时定位还不十分准确,造成印纹间有相互叠压以及间隙疏密不匀的现象,但从整体来看定位技术还是比较高的”。
了解并熟悉印刷技术的人都知道,细节一表明的正是套印技术的主要技术特征。直到现在,印刷图书、期刊、报纸、广告(特别是彩印)等,还经常出现这种套印不准的情况。
其二,“凸版印花一直到明清仍然盛行。《墨娥小录》记述着:印花版的花样可以随意雕刻、翻新,当时杭州的雕花版以‘匠人最工’”。
我们知道,从宋代开始,一直到清代,杭州都是雕版印刷和图书出版的一大中心。杭州的雕花版以“匠人最工”,这同杭州的图书雕版技术为天下一大中心,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无论是雕版印制纺织品,还是印制图书,杭州均名响于世,这恰恰证明了这二者所依据的是同一个技术原理——雕版印刷术原理。进一步讲,杭州的雕花板匠人同雕字板匠人,很可能就是同一种职业阶层——甚至就是同一批人。
其三,“14世纪传入欧洲,先是意大利比较盛行,直到17世纪西欧各国才普遍掌握这一技术”。
这同美国学者卡特在其《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这部关于中国印刷术研究的经典名著中所讲的中国雕字(图)版图书出版技术之传入欧洲的大致时间及其走向完全一致。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仔细加以联系思考的既有价值又有趣的契机或课题。究竟是雕花技术先传入欧洲并启发了欧洲人关于雕版印刷术的思维呢,还是雕花技术与雕字技术这一对基于同一技术原理的姊妹技术同时传入欧洲并对欧洲的印刷出版业及纺织印染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呢?在当时的欧洲,这二种具体技术传入后,二者间的相互关系又如何呢?反正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雕花技术的传入,还是雕字技术的传入,其实均表明中国雕版印刷术原理的传入,而这才是最主要的。或者,其实亦即同一种技术的传入。
肖东发先生在其《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中也将“镂花模板、刺孔漏印及凸版印花”作为其“隋代发明说”的支持条件之一。他也认为“凸版印花与雕版印刷基本一致,工序方法出如一辙,所不同的是涂料(前者为色浆,后者为墨)和被印物(前者为织物,后者为纸)”。他还例举了江西省贵溪县渔塘仙岩一带春秋战国崖墓考古发现及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发现。遗憾的是,肖先生并没有充分认识到马王堆汉墓出土上述二件印染品所体现出的完备的雕版印刷术原理,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诸如雕版、套印、用色、连雕带套带印以及镂空版施印这一系列十分重要的技术因素。肖先生只是认为凸板印花技术“正在逐步向雕版印刷靠近,是一种十分难得的中介性技术”。于是,“汉代发明说”与他擦背而过,雕版印刷术原理仍然没有被发现。
赵翰生在其《中国古代纺织与印染》的第六部分《古代的印染技术》中,以赏鉴的笔致向我们展示了长沙马王堆汉墓这二件丝织品令人神往的“印技”: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印花敷彩纱和金银色印花纱,就是用凸版印花与绘画结合的方法制成的。印花敷彩纱是先用凸纹版印出花卉枝干,再用白、朱红、灰蓝、黄、黑等色加工描绘出花、花蕊、叶和蓓蕾。彩纱表面,手绘花卉,活泼流畅,细致入微,凸印花地,清晰明快,线条光滑有力,很少有间断。整个织物用色厚而立体感强,充分体现了凸纹印花的效果。金银色印花纱是用三块凸纹版分三步套印加工而成,即先用银白色印出网络骨架,再在网络内套印银灰色曲线组成的花纹,然后再套印金色小圆点。从整体来看,银色线条光洁挺拔,交叉处无断纹,没有溅浆和渗化疵点,有些地方虽由于定位不十分准确,造成印纹间的相互叠压以及间隙疏密不匀的现象,但仍反映出当时套印技巧所达到的娴熟程度。”
与这二件印染丝织品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批帛书。同一墓中,既然文字可以写在帛上,图案可以印在帛上;那么,将文字也印在帛上,毫无疑问,已经完全具备了一切技术条件,特别是具备了其雕板印刷术之基本原理。
《马王堆汉墓》一书也就此出土文物明确指出:“这在科学技术史和印染工艺史以及雕版印刷史上,都是光辉的创举。”
秦汉时期,中国还出现了“夹缬”印染技术,即“用两块雕镂相同的图案花版,将布帛对折紧紧地夹在两板中间,然后就镂空处涂刷染料或色浆。除去镂空版,对称花纹即可显示出来。有时也用多块镂空版,着二三种颜色重染”。
由于中国的纺织品文明出现比纸文明早得多,因此,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原理自然先在纺织品上发扬其光辉,并在汉代就达到了技术上全面成熟的地步。一直到隋唐时期,由于楷书的达于极致,纸张生产的普及及其质量的符合印刷要求,以及社会对图书的大量需要,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原理方才在图书出版领域中开始得以技术应用,并于宋元明清时期大放光辉。另外,从纸最初源于丝的生产来讲,这一过程也是合乎科技发明及其演进与应用之逻辑的。确实,中国雕版印刷术原理在纺织品上与在纸上的成功技术运用,就像一枝二蕾,绝妙而神奇。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中也明确认为:“马王堆所出泥金银印花纱,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三版套印制品。磨嘴子48号墓中三件草箧裱糊的印花绢,也是用三块镂空版套印的,绛色底上印以绿、白二色的云纹,颇为美观大方。”
由此不难看出,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二件印染品为标志,其雕版、套印、用色、连雕带套带敷、镂空版套印,以及“夹缬”即镂空版印制的一系列雕印技术,比之宋元明清时期的雕印图书技术来,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套完整的雕印技术,虽然是用在纺织品上,然而一但条件具备,移用在纸上,又有谁能不信它必将会取得成功呢?
缘于是,本文认为,中国雕版印刷术原理的发明时间,应定在汉代,而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二件实物为其成熟的标志。当然,如此成熟的技术,其发明过程必非一日,此前(马王堆汉墓时间)肯定就有了,只是因为目前尚没有考古实物或明确可靠的文献记载为证,以是如此立论。
收稿日期:2003-0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