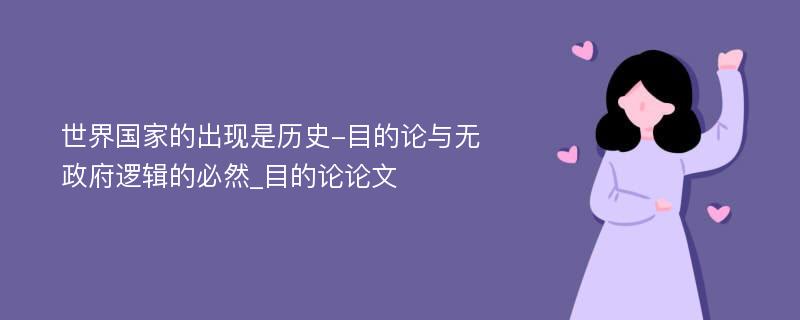
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目的论与无政府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的论论文,无政府论文,逻辑论文,国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政治学面临两个重大问题:世界体系会走向何种终极状态?什么力量推动世界体系走向终极状态?国际政治理论提出了三种终极状态:第一种是自由主义的终极状态,认为世界最终会成为民主国家的“和平联邦”,根基是康德的世界政治学说。第二种是现实主义的终极状态,认为世界最终只能是民族国家体系,战争也不会消失,根基是黑格尔的普世国家学说。第三种是我所说的世界国家。康德和黑格尔都认为冲突是推向终极状态的动力。我也认为如此,但是我的推理与他们有着根本的不同。康德认为冲突使世 界走向民主国家联盟,但没有意识到冲突会导致集体身份的形成。黑格尔讨论了争取承 认的斗争,认为这种斗争会导向普世国家。(注: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Avon Books,1992.)但黑格尔指的是个人之间的 斗争,其普世国家仍然是诸多民族国家的共存状态。我认为争取承认的斗争是在两个层 次上展开的:一是个人之间的竞争,二是国家之间的竞争,(注:Erik Ringmar,“The
Recognition Game:Soviet Russia against the West,”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37(2),2002,pp.115-136;Axel Honneth,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Cambridge:MIT Press,1996.)只有国家之间的竞争才是无政府体系的产物。另外,康德 和黑格尔受到时代的局限,不可能考虑技术发展问题,所以不可能接受世界国家的说法 。(注:Thomas Carson,“Perpetual Peace:What Kant Should Have Said,”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Vol.14(2),1988,p.177;Paul Guyer,Kant on Freedom,Law and
Happines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416-417.)我的观点是: 一个自下而上的自行组织过程和一个自上而下的结构过程之间的互动使世界国家的出现 成为历史的必然。微观层次上争取承认的斗争,加上技术发展的助动,同时受到宏观层 次上无政府性的引导,终将导致世界国家的诞生。
目的论与世界国家
世界国家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目的论。目的论考虑的是一个系统怎样被导向最终目的,即:“X的目的是什么?”(注:Charles Cross,“Explanation and the Theory of Question,”Biology and Philosophy,Vol.11 1991:301-320;Alexander Wendt,“On C onstitution and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8)24:101-117.)其基本陈述是:如果X的发生是为了实现Y ,则Y就是X的终极性原因。世界体系的发展具有目的性,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目的 过程:一是微观或自下而上的自行组织过程,二是宏观或自上而下的结构导向过程。终 极状态产生于这两种过程的互动。
微观层次自下而上的自行组织理论解释了目的过程的微观基础。在一个系统中,虽然组成单位各行其是,结果却产生了某种系统性秩序。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是这一理论的最佳范例。杰维斯的复杂系统理论也具有明显的目的论导向:每个国家针对自己受到的威胁而采取行动,结果却产生了系统性均势状态。(注:Robert Jervis,System
Effects: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宏观层次自上而下的限制条件理论讨论了系统结构的整体性 :整体不能还原到个体,亦即整体大于其组成单位之和。(注: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chapter 4.)整体性产生于宏观层次的限制条件,限制条件可以是生物性的(如DN A),也可以是社会性的(如无政府文化)。整体和部分相互建构:没有整体就没有部分的 身份,没有部分整体也就不复存在。自上而下的因果关系表示系统限制条件控制着系统 组成单位之间的互动。系统整体形成后,限制条件就成为帮助系统生存的因素,制约着 系统单位之间的互动。虽然系统单位的行动是在微观层次上的自行选择,但系统可以通 过限制条件对系统单位的选择进行调控和干预。这就是系统自上而下的因果作用。沃尔 兹的系统理论就是一例。他认为国际系统的无政府结构使国家选择了走向均势的行为: 均势不是国家的有意识选择,国家甚至没有意识到系统具有这样的作用,但国家不知不 觉地就会这样去做。(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Addison-Wesley,1979.)这是系统对于单位的作用使然。
除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因果关系的互动,目的论还需要一个因素。自上而下因果关系所保持的是系统的稳定,无法解释系统的变化。自下而上的因果关系解释的是非线性动因,无法解释系统目的的方向性。因此,还需要一个因素,解释系统整体朝着一个成熟状态的方向运行。(注:Jonathan Jacob,“Teleological Form and Explanation,”in N.Rescher,ed.,Current Issues in Teleology,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6,p.51.)这就是终极性因果关系,亦即终极状态对系统动力产生的导向性引力,使其必然朝着某种结果发展。目的过程就是由三种因果关系构成的:自下而上的因果关系、自上而下的因果关系和终极性因果关系。
使系统向其终极状态运行的动力是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注:Leo Buss,The Evolution of Individual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系统的 限制条件选择组成单位的行为和特征,使其符合维持系统的要求。但这一选择过程并不 是固定的,因为有着许多自下而上的行为路径,因此,在微观层次上许多行为是无法控 制的。这些行为会不断产生威胁系统的力量。系统为了消除这些威胁,会采取扩充自身 结构的方式,以便在更大范围内控制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这样就会暂时稳定系统。这 种暂时的稳定构成了“阶段”吸引因素,或阶段性“终极状态”。但是,随着系统结构 每一次的扩充,微观层次上都会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于是,系统会再度扩充,直至产 生“整体”的吸引因素,或到达最后的“终极状态”。
国际体系必然走向稳定的终极状态--世界国家。我采用韦伯的定义,将国家界定为 在 社会中对有组织暴力具有垄断性合法使用权利的组织。(注: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根据这一定义,如果世界性权威具有对暴力的垄断性使 用权利则可成为世界国家。世界国家的实现,需要现行的世界体系发生三个根本性的变 化。(注:Robert Williams,Hegel's Ethics of Recogni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第一,普世性安全共同体的出现:国际体系成员不能相互 视为威胁,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注:Emanuel Alder and Michael Barnnet,eds .,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第二,普世 性集体安全。如果出现侵略等犯罪行为,体系成员必须做出反应,将对一个成员的威胁 视为对所有成员的威胁。这两个变化会创造一个全球共同权力。第三,普世性超国家权 威机构。这是一个世界社会公认的法治程序,可以就使用有组织暴力问题做出具有约束 力的决定。
世界国家不是世界政府,所以在三个方面表现出权力分散现象:第一,世界国家不要求成员放弃自主性。有组织暴力的集体性使用并不意味着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完全同质。第二,世界国家不需要统一的联合国军,只需要建立一种可以确定和实行对威胁的集体反应。世界国家可以与各个国家的军队同时存在,通过与这些国家军队协议的方式采取行动(如北约模式)。第三,世界国家不需要世界“政府”。政府指一个单一行为体,由行政首脑行使最终决定权。(注: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1977.)只要能够做出约束性决定,世界国家的决策可以是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在公共领域内的议政,而不是首脑决策。(注:Jennifer Mizen,“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手稿),”2001。)总之,只要具有共同权力、合法性、主权和主体性,则不 必预设世界国家的形式。虽然我们距离世界国家仍然遥远,但在区域层次上,欧盟已具 备世界国家的许多条件。如在全球层次上出现类似欧盟的结构,世界国家则具雏形。
争取承认的斗争
世界国家的诞生要求将诸多国家的身份转移到全球认同上来。领土国家组成的世界是不稳定的。国家是局部稳定形式,但国家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全球体系之中,要解决这一不稳定状态,必然导向世界国家的产生。促进这一具有目的性过程的机制是微观层次上的“争取承认的斗争”和宏观层次上“无政府文化”的互动。
争取承认的斗争有着物质性和社会性两个向度。物质性向度关系安全问题,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中人的安全无法得到保证,接受国家提供的安全保证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所以,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多德尼进而认为,国家提供安全的能力是与暴力技术的毁灭程度有关的。毁灭力的提高和技术的发展会使国家的规模加大。(注:Daniel Deudney,“Regrounding Realism,”Security Studies,Vol.10(1),2000,pp.1-45.)中 世纪发明的火药和火炮帮助欧洲君主打败了封建王侯,扩展了领土。后来产生了领土国 家,但在出现弹道导弹和核武器之后,领土国家自身也面临险境。(注:Daniel Deudne y,“Nuclear Weapons and the Waning of the real-state,”Daedalus,Vol.124(2),1 995,p.228.)由于存在这些物质性条件,国家无法继续为其公民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 国家自身也像自然状态中的个人一样易受攻击。于是,出现了“核武器下的世界整体” :自然状态下的个人由于易受攻击而服从共同权力,军事技术和战争日益增强的摧毁力 使国家同样会服从一种共同权力。
多德尼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目的论特征,但他将国家整合的根本原因置于国际体系之外,即外生的技术发展,因而世界国家并非系统内在动力的必然目的终点。(注:Daniel Deudney,“Geopolitics and Change,”in M.Doyle and J.Ikenberry,eds.,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Westview 1999,p.108.)如果 将安全困境考虑进来,就可以表明技术发展也是体系自身的内生因素,这样就使其物质 向度具有了目的性。在无政府状态中,国家被迫以自助方式对付威胁,导致军备竞赛“ 螺旋”,亦即安全困境。由于具有先进武器的国家在战争中占据优势,其他国家就会效 仿,结果将保证基本安全所需要的军事技术水准不断推向新的高度。这样,体系自身产 生了一种向高技术武器发展的动力,使其越来越具有摧毁力,因而也就对国家形成了军 事技术竞争的压力。这是物质性竞争的系统性动力。
也许人们会认为这一物质性动力足以使世界国家成为必然,但事实并非如此。原因有二:第一,在核时代,国家面临的条件与个人在自然状态中所面临的条件是不相同的。(注:Gregory Kavka,“Nuclear Weapons and World Government,”The Monist,Vol.70,1987,p.304.)确保相互摧毁意味着国家无法接受核战争的代价,因此也就意味着国家可能宁愿保持一种核对峙状态而不会相互摧毁,既然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并不像自然状态中的个人那样处于非战不可的境地,国家也就可能宁肯相互对峙也不愿意将主权让渡给世界国家。冷战即是一例。第二,霍布斯证明已有的国家形式可以克服自然状态,但他并没有预测另外一种克服自然状态的国家形式,所以,霍布斯理论是后观性理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将霍布斯推理用做前瞻性理论,就会出现严重的集体行动逻辑问题。从集体的角度来看,个人将自我权利让渡给共同权力可能是理性的,但从个体角度来看,则可能是非理性的。在无政府状态中,人们相互之间无信任可言,集体行动逻辑的问题就会显现。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也是如此。
物质主义世界国家形成理论的缺失是对身份变化的解释。它假定行为体是理性的、利己的、力图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当世界国家出现之后,行为体服从规则的成本和代价会发生变化,但其主体身份和利益仍然不变。康德否认世界国家的出现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即使民主国家可以达成永久和平,它们作为具有主权、实施契约的利己行为体的身份并没有改变。(注:关于康德的永久和平不是稳定状态的讨论,参见Carson,“Perpetual Peace”。)所以,要使世界国家理论得以成立,就需要解释为什么国家身份 的界限会扩展开来,不仅将自己的国民包括在内,而且将所有人民包括在内。这必然涉 及社会性向度。
我的理论属于结构理论。结构理论的动力来自行为体的需求,这样,在微观层次上才会存在追求目标的成分,即意向目的。新现实主义假定人最需要的是人身安全,认为无 政府逻辑意味着争取安全的斗争。人需要安全,但人同样需要得到承认,无政府逻辑同 样意味着争取承认的斗争,这就是社会性向度。争取承认的斗争有两个层次:个人之间 和国家之间。首先,我要讨论一般性的争取承认的斗争。
承认意味着其他行为体(他者)被视为主体:相对于自我来说,他者主体具有合法的社会地位,因此,自我在怎样对待他者的问题上要接受规范性约束。如有违反,则必须申 明理由。没有受到承认的行为体,如奴隶或自然状态下的敌人,不享有这样的社会保护 ,因此可以任人宰割。如若不被承认,生命和生命的部分(如肢体)就会受到威胁,这是 安全问题,是行为体需要追求承认的理由之一。但是,需要得到承认不仅仅是因为安全 ,还因为自我的构成本身就需要得到他者的承认。我们每日每时的身份都可以说明自我 依赖于他者存在的情景:没有妻子的承认就不会有丈夫的身份,没有其他公民的承认就 没有公民的身份。简言之,自我通过他者成为自我:主体性取决于主体间性。只要人们 希望成为主体,就必然需要得到承认。另外,承认理论还有一个重要内涵:承认会构成 集体身份,因为承认使自我得以延伸,使他者成为自我的一部分。(注: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hapter 7.)承认意味着被承认为法治共同体中的 独立主体。得到这种承认,就具有了主权法人的合法地位,而不再被视为其他人的附属 物(如儿童和奴隶),即得到了黑格尔所说的、具有积极社会建构意义的自由。
希望得到承认是指希望他者视自我为独立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我对他者的承认 。所以,承认可以指承认他者的平等地位,也可以指接受他者承认而不予以他者对等的 承认。对于黑格尔来说,合理的国家要具有对等承认特征。(注:John Rawls,The Law
of Peopl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韦伯定义的国家仅仅具有垄 断性使用暴力的权力,可以在不对等承认的情况下存在(如美国的邦联制等)。对等承认 反映了黑格尔的目的论观点:国家的最终目的不是仅仅保护国土安全,而要实现自我的 主体性。这一点只有在所有国家都被承认为主体的时候才可能实现。黑格尔普世国家学 说的独特之处是其成员的相互承认,也就是所有法治共同体中的公民之间的相互承认。 国家具有裁判权,具有确保相互承认的手段:人们违反法律就会受到惩罚。(注:Kenneth Baynes,“Freedom and Recognition in Hegel and Habermas,”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Vol.28(1),2002,p.6.)在这样的国家里,所有行为体被承认的 希望得到了满足,因此这种状态就是稳定状态。各种形式的不对等承认都有一个共同之 处:一个行为体受到承认的意愿得到了满足,但却不给其他行为体对等的承认。(注: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pp.163,182.)在不对等承认结构中 ,那些没有受到完全承认的行为体会继续奋斗。所以,基于不对等承认的社会秩序,从 长远来看,必然是不稳定的秩序。
不稳定的根源既是物质性的,也是观念性的。从物质性角度来看,压制得到承认的意愿代价很高。未获承认者对政权的承认或是假心假意,或是高压之下的不得已行为。有效和稳定的秩序基础是合法性,不是高压手段。没有合法性,维持稳定秩序的代价就会极高。从观念角度来看,则存在长期的威胁。这种威胁的根源在于承认逻辑本身。黑格尔认为完全基于高压的不对等承认(如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秩序,因为不承认奴隶意味着奴隶主自己的主体性出现了危机。(注:Robert Williams,Hegel's Ethics of Recogni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p.63;Erik
Ringmar,“On the Ontological Status of the Stat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2002,pp.120-121.)只有当承认来自有价值的、有尊 严的他者的时候,它才是有意义的。如果奴隶不是有价值、有尊严的人,那么他对奴隶 主的承认最终是没有意义的。(注:参见Williams,Hegel's Ethics of Recognition。) 所以,要想得到他者的完全承认,必须对等地承认他者。这是自由的先决条件:一个人 只有被承认是自由的时候才是自由的,这种承认只有在被自由地给予的时候才是有价值 的。虽然某些因素会加强不对等承认的关系结构,只要不对等结构存在,争取对等承认 的斗争就会继续,这决定了不对等体系的不稳定特征。
无政府逻辑
争取承认的斗争是我的目的论理论中自下而上的向度,现在转而讨论自上而下的向度 ,即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推动体系向世界国家的目的发展。世界国家的形成需要经历五 个“阶段”,推动体系向前发展的动力是无政府性:无政府性通过自上而下的因果动力 ,以两种方式建构了争取承认的斗争:一是使国家可以通过有组织暴力的形式争取承认 ,二是军事技术的发展使暴力的代价越来越无法接受。(注: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an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232.)每一阶段的无政 府文化都会限制全球层次上争取承认的斗争,力图将这类斗争的代价控制在可以接受的 范围之内。所以,每一阶段的文化也就构成了体系发展过程中的阶段吸引因素。但在世 界国家形成之前,所有阶段性吸引因素终将是不稳定的。
第一阶段,国际体系阶段
国际体系阶段是完全不存在承认关系的阶段,也就是霍布斯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的阶段和布尔的国家间体系阶段。这一体系是由三个限制条件构成的:诸多国家的互动,或曰充分“差异”阶段;不存在任何可以强制国家进行合作的机制,即充分无政府性;国家之间相互视为“敌人”,(注: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260-263.)国家没有权利,也没有社会制约因素对国家行为进行限制。因无承认关系,在体系中也无集体身份,这意味着国家没有真正的主体性。
霍布斯阶段是不稳定的,因为它无法在最低程度上满足承认需求。以两个国家之间的互动为例,争取承认的斗争可能产生两种结果:(1)如果一个国家明显地比另外一个国家强大,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征服另外一个国家,将其消灭。于是,两国并存变成一国独立,寻求自我承认的斗争重心会转移到这个扩大了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竞争上去。如果成功的国家继续成功,征服者继续征服,最终就只会剩下一个国家,体系便也不再有无政府状态。但是,如果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不予承认,那么,被征服者终会试图反抗,因之再次出现无政府体系。如若征服者承认被征服者是完全的成员,那么世界国家就会出现。(2)如若两个国家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征服对方,它们就会继续为争取承认而斗争。这并非需要常年不断的战争,但却需要常年备战。致使社会资源消耗殆尽,而战争始终可能发生。这一过程也是不稳定的:或是一个国家终于将对方征服,或是双方在相互耗尽时相互承认。(注:John Burbidge,“The Cunning of Reason,”in R.Hassig,ed.,Final Causality in Nature and Human Affairs,Washington D.C.: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n Press 1994,p.157.)在这种情景中,无政府性对军事技术的 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技术发展会逐步增加战争代价,使得不予承认的政策越来越产生 负面反馈。相反,相互承认则会造就正面反馈,因为它可以使两个竞争国家节省资源并 将其使用到与第三方的争取承认的斗争之中,因而加强了与第三方斗争成功的可能。这 可以被视为导致威斯特伐利亚和平的原因,当今的以巴冲突很可能出现同样的结果。
霍布斯无政府状态是不稳定状态,所以它终将会向一个非霍布斯状态的方向移动。
第二阶段,国际社会阶段
有一种方式可以解决霍布斯文化的不稳定性,即体系向前发展,使国家相互承认主体性,但并不承认相互公民的主体性。这就是布尔所说的“国际社会”,(注:Bull,Anarchic Society.)亦即洛克文化。在这一阶段,有两个限制条件与第一阶段是相同的 :他者性和无政府性。但是第三个限制条件则不同:国家不再相互视为敌人,而是相互 视为竞争对手。(注: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279-283. )竞争对手承认相互作为独立主体的主权地位。取消了相互征服的权利也就限制了国家 的某些自由,但同时也使积极自由和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可能,这在霍布斯世界中 是不可能存在的。国家之间还会形成一定的集体认同,以文化规范为准则限制它们的互 动。不过,这种集体认同是肤浅的,有限战争也为大家所接受。战争可能不会用来消灭 其他国家,但却可以是获取领土和其他利益的合法手段。拉格将其称为“位置性战争” ,而不是“生成性战争”。(注:John Ruggie,“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4),1998,pp.855-885.)洛克文化造 成了两种不稳定状态:第一,即便位置性战争不会危及对方“生命”,但毕竟代价很高 。无政府状态促使国家提高军事技术,战争的代价也就会随着军事技术的提高而逐步加 大。第二,即使国家在位置性战争中不会被“杀死”,但国民是会被杀死的。个人不被 承认为国家之外的另一主体,因而也就不被承认为世界体系中的主体。这就回到国家的 根本目的这一主题:国家不仅要得到承认而且要使其国民得到承认。只要国家还会将国 民送上战场,这一目的就无法实现。总之,个人争取承认的斗争和国家争取承认的斗争 一并成为体系层次的动力,个人要得到完全的承认,就必须破除国家界线的中介功能。
洛克文化不排除战争,不承认个人主体性,所以,它不是终极稳定状态。
第三阶段,世界社会阶段
战争要通过一个普世性的安全共同体加以解决。在这样的安全共同体中,争端是以非暴力形式解决的。这就将全球性承认从国家转移到个人,形成了体系运作的新的限制条件,这就是世界社会。这一体系对其成员自由度的限制更大(成员不能自由发动战争),但同时也将积极自由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包括国家,也包括个人。
但是,这一发展阶段也不是一个终极状态,因为没有针对侵略的集体保护机制。虽然大家都承诺和平解决争端,但无法排除有的国家拒绝接受非暴力行为,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注: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Norton,2001.)原则上有两种方式可以对付这样的国家:一是集中强制措施,二是通过 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实行非集中的强制措施。但这两种方法均难以实施,因为国家具有主 权,且安全共同体的概念本身就与国家概念不符:没有人能够将互助行为强加于具有主 权的国家。所以,要维持一个世界社会,行为体需要一种更加强式的承认,这种承认不 仅要强制其成员实行消极义务(非暴力行为),而且要强制实行积极义务(互助行为)。互 助是世界社会的关键缺失。
因此,世界体系会向一个互助的共同体发展。试想一个由A、B、C三个国家构成的体系。如果A和B构成一个共同体,它们就会经历积极反馈:不再担心战争的发生,双方的集体和个体主体性都得到了承认。现在,假定C作为对B(仅仅对B)的外部威胁出现在体系之中。对于A来说,原来是和平的边界可能会出现一个充满敌意的国家,将和平边界变为战场。这就使A在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将保护B视为自己的利益。事实上,B国被征服的负面反馈增强了A、B两国和平关系的正面反馈。由于这类刺激因素是相互的,所以,A、B两国都会关心相互的命运,结成互助联盟。一旦体系达到了世界社会的状态,使其得以发展的意愿就会进一步推动体系向前迈进。
第四阶段,集体安全阶段
在第四阶段,体系获得了一个新的限制条件:不仅体系成员(个人和集体)相互承认对 方生存和实施非暴力解决冲突的方式,而且体系成员必须实施互助原则,相互帮助对付 威胁。这一体系就是“康德文化”体系,是集体安全或友谊体系。(注: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298-299.)行为体具有全面的集体认同意识, 相互尊重安全,在与集体命运认同中保存自己的差异。在全球范围内,我们仍然距离这 种体系甚远,但在区域层次上(如欧洲),这种体系的优势已显现出来。
全球集体安全体系并不是世界国家。领土国家仍然保留主权,所以,全球安全体系的 运作首先要征得国家的同意。集体安全体系也无法以合法实施暴力的手段强制性地要求 其成员相互承认。集体安全体系是一个自愿体系,所以仍然具有无政府性(世界国家不 是自愿体系)。但集体安全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满足了个人和集体的承认需求。在这 种情况下,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全球集体安全体系呈不稳定状态,促使它继续向前发展呢 ?这是一个难题。
康德意识到这一难题,所以他的目的论在和平联盟的阶段终止了。这也是以福山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者所认识的历史终结点。康德对世界国家的怀疑有三重内容:在全球 范围内无法组织和强制实施政治权威;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将主权让渡给世界国家 ;世界国家会成为暴政。我已经对第一个内容进行了说明:从18世纪以来,技术的飞速 发展使今天的世界可能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强制性权力。但其他内容还没有得到解释,所 以,似乎发展到全球集体安全体系历史就终结了。
但是,集体安全作为对争取承认的斗争的解决方式仍然具有不稳定性。理由之一是集体行动的逻辑,集体行动的逻辑使得集体安全不能作为对抗侵略的充分手段。由于国家依据自我利益采取行动,往往在最需要集体安全的时候,集体安全最难以实现。另外还有两个不稳定源也是难以消除的:第一,由于集体安全是一种基于自愿的体系,国家保留主权,所以,它无法阻止一个国家“退出”集体安全体系,发动侵略战争。(注:Thomas Carson,“Perpetual Peace:What Kant Should Have Said,”pp.179-180.)第 二,集体安全不能充分保证个人和集体争取承认的愿望得以实现。保留主权就是保留单 方的决定权,使国家可以改变政策,收回承认,并在必要时消灭对方。只要不将生杀权 利让渡给一个能够强制实行承认的权威,他者总会受到自我政策改变的威胁。据此,集 体安全体系不可能是稳定的终极阶段。没有受到共同权力强制实行的承认终将不是真正 的承认,因为这样的承认依赖于承认一方的良好意愿和自愿选择。真正的承认是权利, 不是施舍。只有当为他者利益采取行动成为可以得到强制实行的时候,承认才能得到保 证。
大国是世界国家形成的最大障碍。如果形成世界国家,相互承认平等地位,对弱者来 说只有收益,没有损失。大国则不同:它们不像其他行为体那样易受侵犯,它们具有根据自己的意愿对待其他国家的能力,甚至可以独行其是。但从长远观点来看,如果大国坚持保留不对等承认,个人或小国就会继续争取承认的斗争。由于毁灭性越来越强大的武器的扩散,个人和小国使用暴力的能力也会增长,因此也就会越来越威胁到大国的安全。中小国家也有着联合的动机,合力“制衡”大国。在这种情况下,大国超然于全球争取承认斗争之上的能力就会减弱,单边行为的合法性也会受到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对于大国来说,尤其是对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来说,也许假以时日才能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如果大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拒绝承认他者而导致一个威胁日益增长的世界,二是一个他者得到承认因而日趋平和的世界,那么,理性的大国做出何种选择应该是很清楚的事情。
第五阶段,世界国家阶段
世界体系发展的第五阶段是世界国家阶段,也是终结阶段。国家主权转移到全球层次,对个人的承认不再由国家发挥中介作用。当然,国家仍然被承认为主体,也还保留一定的个体性(普世性中的个体性)。个人和国家都不再具有单方使用暴力的负面自由,它们都具有完全得到承认的主体性,因而也就获得了正面自由。(注:Buss,The Evolution of Individuality.)
但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世界国家是终极稳定状态,还是它也会产生不稳定性,最终导致自己的消亡?有人认为,世界国家还可能存在三种不稳定源:一是康德对出现专制的担心。世界国家会成为专制国家吗?似乎不太可能。这里最明显的问题是“民主赤字”,(注:Klau-Dieter Wolf,“The New Raisond'etat as a Problem for Democracy
in World Societ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5(3),1999 ,pp.333-363.)世界国家的巨大规模以及由此产生的公民声音减弱的状态会造成一个国 家与公民之间的鸿沟。(注:Robert Dahl,“A Democratic Dilemma:System Effectiveness versus Citizen Participat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 .38,1994,pp.33-59.)但目前的大型民主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存有内在不稳定性。进而, 如果不走向世界国家,世界只能处于无政府状态,领土国家保留使用暴力的主权权利。 主权的实质是国家可以合法地对非国民实行暴力,这难道不是“专制”吗?美国在科索 沃、阿富汗、伊拉克杀死了众多平民百姓,无论是否正义,谁又追究过美国的责任?世 界国家的民主问题是会存在,但是,对于解决承认问题,世界国家比起无政府状态显然 要强。
二是民族主义对世界国家的威胁。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非殖民化使得体系中的国家数 目增加,民族主义情绪也在增长。但民族主义的增强实际上是支持我的理论的证据,因 为民族主义涉及争取承认的斗争。1945年世界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帝国统治之下,他们并 不被承认为具有完全的主体性。于是,他们展开了争取承认的斗争,并最终获得了自由 。就此而言,民族主义和非殖民化使得以前未被承认的行为体自由参与到体系中来,并 使他们受到超国家权威的制约。争取承认的民族主义斗争远没有结束,新的国家仍然会 被创建。但这类分裂是向前迈进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差异得到承认,更大范围内的认 同才会是稳定的。世界国家绝非压制民族主义,恰恰相反,只有包容民族主义,世界国 家才可能存在。
三是世界国家的一个不稳定原因似乎涉及我的理论中一个内在的矛盾。世界国家必然出现的论点的假定是:自我和他者的对等相互承认。如果世界国家将所有主体都融入一种集体身份,那么它就失去了他者,因而也就不会稳定。这一全球性自我如何保持它的主体性呢?亦即谁来承认世界国家呢?承认的先决条件是存在各种主体之间的差异轴线。 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承认世界国家的是组成世界国家的个 人和集体。部分和整体相互建构,但并非同质,部分和整体之间仍然存在差异界线,所 以部分承认整体是可能的。第二,在领土国家里,争取承认的斗争的特征是成员和非成 员之间的空间界线。世界国家是全球性的,没有外部的他者,因此也就失去了空间性差 异。为了弥补这一缺失,会创造一种时间差异:过去与现在的差异。(注:John Ruggie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Problematizing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4),1993,pp.855-885;Ole Waever,“Scrutinizing and Descrutinization,”in R.Lipschutz,ed.,On Securit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p.46-86.)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历史”成为 他者,世界国家根据历史定义自我。在这个意义上,现在的身份依过去(往往也依未来) 而获得合法性。自我在时间上形成差异使得相互建构成为可能,因此也就使“他者”得 以存在,从而稳定了全球性的自我。
对稳定性的讨论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世界国家形成之后会是什么状态呢?“政治”或是“历史”是否就此终结了?如果“政治”和“历史”意味着无政府状态中的活动,亦即由战争作为手段的争取承认的斗争,那么,这样的“政治”和“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终结了。但是世界国家仍然需要自我再造,所以仍然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世界国家不是一个完全闭合的体系,世界国家仍然会受到诸如分裂活动等暂时的冲击。但是,世界国家与无政府状态的根本不同在于它会将这样的分裂活动确定为犯罪行为,而不是确定为政治和历史活动。世界国家不是历史的完全终结。比较合适的说法是,这只是“一种”历史的终结。历史即使到达了一个目的,另外一个目的又开始显现出来。
结论:世界国家理论的政策性意义
国际体系的终极目的是世界国家。虽然世界国家的出现仍然需要很长的阶段,但这一理论对于宏观战略来说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因为宏观战略需要基于世界发展的正确理论。如若现实主义是正确的理论,无政府性必然导向战争,以利己思维方式定义国家利益并据此采取行动就无可非议,国际法因之无足轻重,国家可以随意采取单边主义政策。如若世界国家的理论是正确的,国家则应试图在未来全球形态中获得最大收益,这就要求国家参与世界国家形成的多边主义过程。也就是说,如果世界国家是历史的必然,最好的战略是参与其中,而不是坐等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