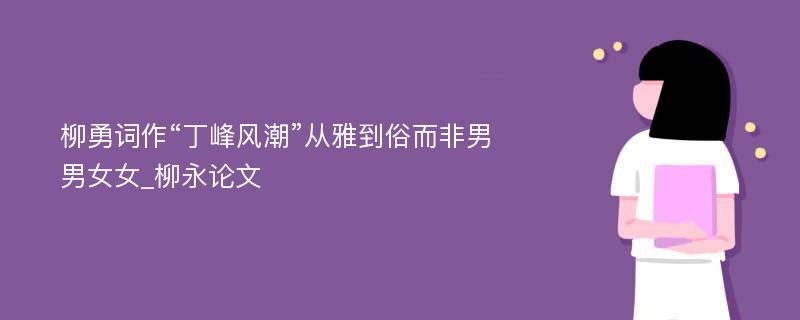
由雅返俗 以俗代雅 由男观女 以女定男——柳永词《定风波》赏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柳永论文,定风波论文,俗代雅论文,雅返俗论文,女定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柳永:《定风波》
柳永的词,据我想来,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是一种在雅俗之间的非雅非俗的文化现象。它不像民间歌舞,完全是非文化阶层的娱乐活动的产物。这类的民间歌舞,其创作者本身并无明确的文艺意识,他们不把创作活动本身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他们的创作活动是不自觉的,只求自己的感觉上的妥贴,不求理性上的合理,因时而变,因情而变,没有完全固定的形态,没有十分确定的作者,就其多数,带有粗糙简陋的特征,在形式上也不会有自觉的革新,但朴素自然,则是任何文人的有意创作所难以企及的。因其不以雅正为标准,所以不论是情歌还是节日歌舞,都具有原始生命力的野性美和粗犷美(这些在文人的搜集、整理和修改过程中有更多的失落);一般的文人创作,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的文艺中,是文人表现自己的才能和思想情趣的手段,他们的创作是有意识的行为,彼此之间也有相对固定的价值标准。因是个人才能的表现,所以它重视个人的风格和个人的创造,文学艺术的发展多赖他们的努力,但相对固定的价值标准又不能不限制着它的革新范围和程度。严格说来,这类的作品是文人写给文人看的,甚至是为了留存后世的,雅正的标准虽然时有变化,但求雅正的目的是不会变的,彼此所争夺的也就是何为雅、何为正这个标准。雅文学的困境在于雅文学的创作者并不一定都是雅正之人,像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这类有雅正之气因而雅正对他们不是一种束缚,自由驰骋而不失其雅正标准的诗人是并不如想以雅正之诗获得文名之人那么多的。一但失却雅正之气而又作雅正之诗,其诗就带上了模仿的痕迹和拘谨逼仄的特征,至其末流,就充满了道学臭气,失去了文艺的基本特征。道学气的诗,究其原因,则在自身的生活趣味不在社会崇仰的目标而又极力伪装崇高,像一个故意摆架子的人,架子摆得越大,庸俗之气越浓,无俗文学的朴素,也无雅文学的雅正之气。在这时,那些不想作伪的知识分子就干脆抛开道学标准,而直接用雅文学的形式去表现自己生活的情趣,就造成了一种非雅非俗、亦雅亦俗的文学。就其形式,它原本属于雅文学的范畴,其创作者也是有意进行创作的雅文学中的作者,他们与雅文学的创作者有着共同的艺术的标准,但其作品的思想情趣则由雅返俗,不再以当时所意识到的严肃的道义精神为支柱。连这些创作者自己,也不认为他们的作品有什么严肃的社会意义,他们是以趣味为中心、以艺术为目的对抗假道学者的虚矫文风的。他们以俗为美,以俗为正,把雅的形式同俗的情趣结合为一体,成为介于雅俗之间的一种独立的文学形态。就其创作者而言,因为这类作品在形式上和语言上与当时的雅文学有着可以共同使用的评价标准,能够让一般文人感受到作者的艺术才能,所以仍然是雅的,但在所表现的情趣上,它又被一般文人所轻视,不被视为高贵、伟大、深沉、严肃的正人君子,而只是常人所不可免的一种趣味,一种人生态度。虽然平庸,但却真实,道别人所不想道、不屑道,经他们道出来,自有不拘一格的自由感,脱去伪装的轻松感,发现别人与自己相同的心理隐秘的愉悦感。因其所表现的情趣的普遍性,这类的诗不再局限在正统文人集团的内部,一个时代的文艺接受者都能与之发生共鸣,而越是过着普通生活、没有自己不能摆脱的社会责任感的人越与之有着更多的共鸣,所以它在当时的社会能获得更多人的喜爱,成为流行最广的文学,特别是在社会和平发展时期,社会的享乐欲望超过了责任的意识,这类作品就有更广泛的市场,在这时,严肃文学和民间文学也往往不是在自己全部的意义上,而是在与这类文学的相同相通的特点上被读者所接受的。但是,这类的文艺也有自己的发展限度。较之民间文学,它们的朴素自然是外在的特征,它们有创作者有意营造的痕迹,是着意显示的朴素自然,这使它们不具有纯民间文学的拙朴美和野性美,精致的形式与所要表现的朴素自然的生活情趣在这类作品中是永难克服的一个矛盾。它们的朴素自然只是所表现的情趣本身给读者造成的印象,而不是由形式本身体现出来的,是经过剪修的朴素自然。至其末流,则会暴露出明显的媚俗性质,如果说道学气的诗流于霸道或虚伪,这类诗的末流则会流于恶滥或妖媚。与此同时,由于作者本身就不把自己所表现的情趣当作一种有社会价值的情趣,所以他们笔下的这种情趣多多少少会带有一些轻佻的性质,并且停留在情欲自身的闪烁表现上。这类的文学只有在严肃文学走到末路,不能满足文艺接受者的需要的时候,才会在整个文坛上独领风骚,并且具有严肃文学的性质,但相对于真正的严肃文学(非假道学的文学),它们有自己不可克服的弱点。真正的严肃文学,像屈原、陶渊明、杜甫等人的诗,曹雪芹、鲁迅等人的小说,其个人的情趣和社会的意义、情感的价值和理性的深度、强烈的欲望与刚正的道义、物质的生活与精神的追求是以不同的形式融为一体的,并不是用生活情趣对抗社会的价值、用俗的对抗雅的,而这类的作品则是以俗抗雅、以俗代雅,情趣和意义、个人爱好和社会责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作者的理解中就是尖锐对立的,它们是在对社会道义的消解倾向中走向个人情欲的表现的,这使他们的作品不但在形式上而且在内质上就不具有崇高的性质。在他们的俗中看不出雅来,在他们的雅中看不出俗来,二者没有可过渡性。柳永的诗歌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学的领域中建立了自己的独立领地的。他有他自己的价值,但他的价值又不能不受到这类文学所能够达到的最高限度的限制。否认他的价值同笼统地肯定他的价值同样是危险的。
在中国古代的这类文学中,性爱的主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爱情诗的一大流派,但这类文学中的性爱主题在其基本意义上并不属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爱情诗。以《诗经》、《乐府诗集》中的性爱主题为代表的爱情诗,是把两性的爱作为一个独立的生活内容被描写和被表现的,在这些作品里我们基本上感不到情爱生活与其它生活有雅谐的区别,不具有排他性质。后来的一些严肃文学作家的爱情诗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但为数极少,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屈原的诗里,实际上也有爱情的内容,其特点是把爱情作为整个人生的象征,求女和求美、求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同情处在同一个意义层次上,在爱情中体验人生、在人生中体验爱情,但对屈原作品的儒家化阐释把屈原政治化、单纯化了,这个传统也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在白居易、李商隐以至《红楼梦》的爱情描写里,这种特征还是保留下来。在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古代的爱情诗中占有绝大多数的作品则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类文学中的作品。这类的诗歌最初的形态是以被冷落的宫女为题材的,这类的诗表面写的是被冷落了的宫女的爱情悲哀,但其实质的内容却是不得志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不被赏识的痛苦,爱情还不是这类诗的基本主题。诗人与宫女之间的认同不是在社会人生的普遍意义上,而是从纯个人的生活际遇上,宫女和作者都需要帝王的赏识才能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这类的诗写的是真情,所以显得亲切生动,但其情是狭小的、卑屈的,不具有人生哲学的意义和平等爱情的性质,以小见小,无法像《红楼梦》中的爱情描写一样从平凡中感到崇高。唐以后,这类的诗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它是与中国官僚知识分子的才子化发展趋向密切相关的。
以唐为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唐以前,中国知识分子是在寻找自己的社会价值的过程中自求发展的。从先秦到唐代这一整个历史时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发挥社会作用空间的政治结构都还没有一个十分固定的标准和确定无疑的方式,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必须通过自己才能的表现而获得统治者的赏识、进入政治集团当中去,以获得自己立身扬名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要展示的主要是自己的才学和抱负,自己能为君、国所用的社会价值,与此无关的个人生活要求尽管也有,但脱离开社会价值的纯个人需要不被作为表现的中心。文学艺术是他们的主要表现方式之一,所以那时的文学艺术浸透着的基本精神是社会的,是个人才能和抱负的表现。与这种入仕精神相对立的是道家的出仕精神,但这种出仕精神也建立在对人生普遍价值的思考上,它不被作为纯个人的生活享乐欲望的满足,从而表现着比入仕文学更高雅的特征。以诗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从唐代开始形成,到宋成为官吏选拔的固定制度,一批一批的青年知识分子不必依靠自己的创作表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只要通过科举考试便可进入官僚集团。在这种考试中,个人的聪明和才华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一批带有才子气的知识分子进入到官僚集团当中来。这批才子以聪明和伶俐顺利跨过唐以前知识分子必须通过自己的社会努力才能跨过的政治的门槛,而一当跨过这道门槛,他们的社会身分与个人生活情趣就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忠君报国、拯世救民、治国安邦,要求于他们的是自我牺牲,是放弃个人的生活享乐,这与他们读书作官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在此之后,仍有许多表现出凛然正气的儒家知识分子,但就其多数,在忠君报国的旗帜下实现的是个人声色欲望的满足,例行的政治生活对他们只是外在的社会责任,从中激发不起真正的创作热情,文艺遂向个人生活情趣方面发展。但这些诗人又不是传统的道家知识分子,他们并不追求田园式的恬淡生活,不追求宁静和高雅,而把生活享乐当作人的最真实、最合理的生活形式,性爱的主题就成了他们最中心的主题,它是作为与迂腐的道德说教相对立的情欲表现而受到他们的重视的。性爱是这些知识分子由雅而俗的重要推动力量,是摧毁道学家思想提坝的情感洪流。唐以后这类文学得到更充分发展的另两个必要条件是城市歌楼妓院的发展和词这种文学形式的流行。这三者实际是三位一体的。从唐代开始,就开始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歌楼妓院的红粉女子的结合。为适应中国官僚知识分子的享乐需要,在歌楼妓院造就了一批文化型的女性,高雅的琴、棋、书、画,歌、舞、弹、唱,诗、词、歌、赋在这种俗世的享乐场所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从而使这些艺术门类由雅返俗,在雅的形式中注入了俗世的享乐欲望,同时也为俗世的享乐欲望赋予了雅正的色彩,构成了一个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市场。这个市场同民间文化、文人文化的纯俗和纯雅不同,它是雅与俗的混血儿,是文人与歌妓的共同创造。这个市场的需要,把在文人之间不可能获得独立发展的文学倾向大大发展起来,性爱的主题在这个市场中成了最主要的主题。歌楼妓院原本就是感官享乐的场所,其性爱是建立在享乐主义基础之上的,既不同于《诗经》中的情歌,也不同于《离骚》当中的爱与美的追求。与此同时,词在唐代开始发展,到宋达于鼎盛。诗的整饬美不适于表达婉转缠绵、流动起伏的情绪,词的长短变化为轻灵跳动的感受提供了更适宜的形式。词原本是用于歌唱的,歌楼妓院为词的演唱提供了有利的场所,这同时也把词的创作同歌楼妓院的生活情趣更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性爱主题在中国古代的词中比在中国古代的文人诗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我想,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中国官僚知识分子这种由雅返俗的倾向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过程。官僚知识分子这个身分的“雅”对于他们与所有人都不能没有的“俗”永远具有一种牵制力量,这使他们向“俗”的发展永远是有限度的,但这里又有一个自我意识的问题。在这个集团当中,声色欲望向来是一个大忌,它对整个官僚集团是一种瓦解力量,当他们在实际的社会政治目标中已经感觉不到兴味、其个人情趣已经世俗化的时候,他们仍然要保持自己高雅的身分,使自己的情欲表现也限制在一个极有限的范围之中,这在艺术表现上并不完全是不好的,如果说儒家传统造成了杜甫诗的沉郁美,道家传统造成了王维诗的空灵美,中国官僚知识分子这种由雅返俗的倾向则首先造成了温庭筠词的朦胧美。但温词的朦胧并不同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朦胧,他的诗不是一个多义的象征体系,而是一种情中见欲、欲融情中的那种朦胧。北宋初年的词,仍有含而不露的特征,一直到柳永,词的格调才为之一变。用我的话来说,柳永在中国这类文学中的作用,起到的是茧破蚕出的作用。在中国文学史上,柳永不能被称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但却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他的杰出就在于他是当时歌楼妓院文化的最典型的代表,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流行歌曲的词作者。在中国流行歌曲的发展史上,他应有极突出的位置。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自我意识的变化问题。这类官僚知识分子,是在一个由君主、歌妓、自我组成的三角关系当中意识自我和确定自我的。君,体现着当时对自我的政治要求、社会要求和道义要求,在文学上体现着当时所谓的严肃文学,这种文学主要在以官僚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人集团当中以传阅的方式进行流通,以君的需要意识自己和规定自己是官僚知识分子的政治身分所要求于自我的;歌妓,体现的则是个人的生活乐趣,是俗世的声色娱乐,在文学上则体现着当时的歌楼妓院的流行文学,其传播方式是歌楼妓院的演唱活动。也就是说,这里体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和艺术观,两种不同的审美趣味,尽管它们同时存在在部分官僚知识分子的身上,但却是他们自身分裂的结果,当社会政治需要不再是在他们的人生体验中自然产生的、而是一种外加的责任的时候,这种分裂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倾向。在这时,君体现的是政治的、社会的但却不是自我的、文学的,歌妓体现的是非政治、非社会的但却是自我的、文学的。一方是社会、政治、道德,一方是自我、生活、艺术。对于他们,二者的对立是根本上的,既想整日混迹于歌楼妓院又想让君主封为忠臣良将。既想让歌妓传唱自己的作品又把它们当作修身教材,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从人生情趣到审美特征完全以自我、自我的生活感受、自我的审美追求为基础进行词创作的就是柳永,他开始脱去道义的伪装,完全以当时歌楼妓院的歌手以自许,这使他基本摆脱了正统文学对流行文学的束缚和限制。他的诗歌的局限性是由这种文学自身的局限性造成的,而不是由它种文学加于这种文学的。可以说,柳永在当时的流行歌曲的创作中获得了自己的自由,同时也把这类文学提高到了更高的艺术境界。郑振铎说:
耆卿词的好处,在于能细细的分析出离情别绪的最内在的感觉,又能细细的用最足以传情达意的句子传达出来。也正在于“铺叙展衍,备足无余”。《花间》的好处,在于不尽,在于有余韵。耆卿的好处却在于尽,在于“铺叙展衍,备足无余”。《花间》诸代表作,如绝代少女,立于绝细绝薄的纱帘之后,微露风姿,若隐若现,可望而不可即。耆卿的作品,则如初成熟的少妇,“偎香倚暖”,恣情欢笑,无所不谈,谈亦无所不尽。所以五代及北宋初期的词,其特点全在含蓄二字,其词不得不短隽。北宋第二期的词,其特点全在奔放铺叙四字,其词不得不繁词展衍,成为长篇大作。这个端乃开自耆卿。(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三册,第486页。)用我的话来说,《花间》的含而不露,在情趣上是情欲的遮掩,在艺术上是诗美的延续,在表现上是由外而内的窥视,而柳永的词,是对情欲的直接叙写,在艺术上是歌词的典型特征,在表现上是由内而外的展示。到了柳永,歌楼妓院文学才具有了自己完全独立的特征。
儒家文学的特征是政治的、道德的,道家文学的特征是自然的、超脱的,歌楼妓院文学的特征是现世的、享乐的。歌楼妓院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普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它从产生之时起,就是畸形的。它的畸形特征就产生于歌楼妓院与官僚知识分子的直接结合上,这使歌楼妓院的流行文化很容易被纳入到官僚雅文化的文化系统中来,这种生活情趣和审美特征也成为官僚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念的审美观念。直到现在,最正统的政治文化往往和最流行的享乐主义文化直接联姻,而对真正严肃的社会文化构成强大的压迫,恐怕是与中国文化的这种传统有密切关系的。它的弊病并不产生在这种文化自身,而产生在对这种文化的把握和阐释上。当官僚知识分子把歌楼妓院文化不只是作为歌楼妓院的流行文化而是作为官僚雅文化的一部分予以接受的时候,当这类诗歌的情趣不是作为在城市市民中流行的一种自然存在的人生情趣而是作为中国官僚知识分子的高雅趣味予以艳羡的时候,它就成了中国文艺才子化和中国官僚知识分子享乐化发展的原因之一了。中国人常说,中国官僚知识分子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这是对的,但是,中国官僚知识分子却不能仅仅是一个一般的人,不能只有七情六欲。他们之被赋予比一般人更高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就理应对中国社会的管理和发展作出比一般人更多的贡献,就理应对中国社会负有更大的责任,个人享乐可以是一般市民的人生观,但却不能是中国官僚知识分子的主要人生观念。我们还常说,文学就应有娱乐职能,这也是对的,但是,文学的价值却不能仅仅由文学的娱乐性来确定,娱乐性是流行文学的主要特征,雅文学之所以被认为是雅文学就因为从中能够发掘出更丰富的社会的或人生的意义,它不能只停留在感官享受的层次。
柳永的《定风波》词在柳永的创作中不是最优秀的,但在理解他的作品的思想艺术特征上则是有重要意义的一篇。这是一篇以性爱为主题的诗,由于“五四”以后爱情主题受到空前的重视,所以我们对中国古代这类诗就不再进行过细的分析,而仅仅从爱情诗的意义来评价它、分析它。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爱情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它不象西方一样把爱情视为人类之间最伟大、最庄严的感情,因而西方诗人对爱情的讴歌就是对人类的讴歌,是一个严肃的文学主题。中国古代大量的性爱描写都不是在严肃文学的内部产生的,而是在中国官僚知识分子这种由雅返俗的倾向中产生的。在这里,首先需要解决的不是它有没有描写两性之间的爱,而是它为什么转向这个主题。只要我们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中国官僚知识分子之转向女性,不是从对女性在整个人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出发的,不是从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关心出发的,而是从男性自身的需要出发的,是男性享乐欲望的向外延展,它联系着女性,因而也开始大量描写女性。也就是说,这种描写,首先是从当时男性的视角出发的,是男性欲望的眼睛中所发现的女性。女性是什么?女性是男性所需要的那个对象,那个形象,是使男性感到愉悦的事物。显而易见,这同时也就把女性在一个方向上观念化了。文学中的形象都是观念化了的,但我们要欣赏作品,则必须知道它是怎样被观念化的。柳永词中的女性,是作为一个温馨的生活环境被观念化的,她们不是可以给男性带来幸福同时也会带来痛苦的具有复杂意义的女性,而是只使男性感到舒适愉悦的女性。通过这样的女性,他所实现的是一种表达:人的生活享乐是唯一真实的生活,其它的意义都是虚幻不实的。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词的上阕,有一个中国读者习焉不察的矛盾,即描写对象与创作主体两个视角所存在的差异。作者写的是一个女子对男子的思念,但在作者和读者眼中的这个女子,却是一个欣赏的对象。在你面前展开的是一幅美女图。这个美女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个充满性感的女性。她有一身温润酥软的皮肤,有一头如云如雾的细密柔美的黑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日上花梢,绿柳依依,黄莺乱啼,一室晶莹的昼光呈现出她裸卧玉床的形象。倦眼轻启,体态厌厌,浓发未整,蓬蓬松松,身下软衾衬出她洁白如玉的身体和这身体的曲线,阵阵幽香从她的身上和衾被之中散发出来。面对这样一幅美女图,你产生的是心旷神怡的感觉,而没有这个女子思念男子时的失落感。甚至连“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也让你感到心灵的愉悦,而不因这个女子的怀念之苦而产生阴郁的情绪。这是这类诗词的一个重要的审美特征,这使它们同真正的爱情诗分别开来。爱情的双方是感同身受的关系,它虽从异性形体美的感受开始,但却具有对异性形体的超越性感受。贾宝玉初遇林黛玉时注意的是林黛玉的形体美,但越到后来,越消失了对她的单纯形体美的感觉,随之而来的是林黛玉情绪对他的情绪的严重干扰,两者有了感同身受的能力。
过去的评论家已经注意到该词的环境描写和人物刻划的矛盾,环境的“雅”和人物的“俗”好象是不相协调的。但这里的问题不是环境和人的描写的真实性问题,而是如何理解所描写的对象的问题。不论从这类文学的总体特征,还是从这首词的具体审美特点,我们都应该看到,它所描写的不是一个家庭女性,而是一个青楼女子。歌楼妓院是雅的,但它的雅是呈示性的,不是精神性的,这种雅给人的是舒适优美的感觉,但却不朴素自然,雅而不亲,正像现在的星级旅馆,你住在里面,比住在自己家里还要舒适方便,但却没有自己家庭的亲切自然。它是为顾客精心布置并精心保护的,却不是布置和保护者的精神需要。这首词里的环境,也是向别的人呈示的,而不是居住者自我精神的外化形式。它的芳草鲜花(《“惨绿愁红”)、莺啭柳舞、香衾玉枕,都是青楼环境的特征,它雅而不素,美而不亲。它的美是感官效果上的,而不是人们精神系念中的。这里的“红”,这里的“绿”,这里的“香”,这里的黄莺啼啭,这里的柳带飘舞,都使你感到感官上的愉悦,但却不是你情意上思念的事物,不像王维笔下的茱萸和李商隐笔下的巴山夜雨。在这个感官化的画面里,出现的是一个感官中的美人,她诱惑着你,吸引着你,但是是以你能享受的对象那样诱惑你,吸引你。也就是说,她是被作者享乐欲望观念化了的女性。
一个被作者的享乐欲望观念化了的女性,不是需要男性征服的女性,而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就能提供给男性以温存、以爱抚、以感受上的满足的女性。该词中的女子对男性的思念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的怜爱而不是引起人们相同的思念,就在于作者是在男性享乐的意义上感受她对男性的思念之情的。他不再有爱情追求中的痛苦,不再有被拒绝的难堪,不再需要为爱情的实现付出自己的努力乃至作出自己的牺牲。但在同时,它也不再有可能对女性复杂的心理内容作出新的发掘和新的探索。柳永的词所描写的女性比李清照所描写的女性更能引起男性读者的怜爱,但却没有李清照词所揭示的女性的复杂多变的心理内容。不难看出,柳永词所写的两性关系,更是才子型的官僚知识分子与青楼女子的关系。在这二者之间,不存在沟通的困难;女性是直接作为男性享乐的对象被提供于男性的,但假若只是赤裸裸的性感官的刺激,男性还是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的,他还需要感情上的联系,需要因两相爱悦给双方带来的心情上的愉悦。所以,他所描写的总是青楼女子与所爱悦的男性的关系。但在这里,两相爱悦却不必经过互相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被商业化的目的人为地缩短了,彼此从相互的需要就可以直接建立起爱悦的关系。如果说爱情是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这里的爱悦就是寻找自己的精神旅馆。它的轻易性带有一种轻薄的意味。它对女性的理解是单纯的:女性需要男性的温存,并且只需要男性的温存;一个她所爱悦的男性就是她的一切。在该词对这个女子的描写里,所表现的同样是她对她所爱悦的这个男人的需要,而并不包括她对这个男子的关心。
上述各种差异性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我认为,注意该词语言表现上的这一特点是十分必要的,即,在男性视角中占有更重要地位的内容,多用具有直感直观上的舒适感的词语予以表现,而在女性视角中占有更重要地位的内容,多用无直感直观性的抽象语言予以表现。“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这里的“惨”,这里的“愁”,是这个女子心中的感受,但对于读者,这种表现方式对愁肠悲感的表现是抽象的,不具体的,你不会因知道这个女子的“惨”和“愁”便自己也“惨”也“愁”起来,而这里的“绿”和“红”则有视觉上的直观性,并且在视觉上产生的是艳丽的感觉。如果说李清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凄凄”传达的是女性作者的心情,柳永的“惨绿愁红”传达的则是男性作者的一个视觉感受,“惨绿愁红”还是一种视觉美;“芳心是事可可”,说的是这个女子的落寞感觉,说的是她对周围事物的淡漠感,任何事物都引不起她的兴趣。但读者却不会感到兴味索然,相反,这个怀春的女子却使我们感到一股暖意,一种趣味,它与其说传达的是这个女子的心情,不如说描写的是这个女子的情态。“芳心”已有美感,一个怀春的女性在女性自身是一种苦,但对于男子则是一种美,一种心灵的慰藉。“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这对于这个女子自身都是一种无意识的表现,但在读者眼里,却是最具直感直观性质的画面。像“暖”、“酥”、“香”、“腻”几乎只是男性的感官感觉,一个女读者不会感到一个女子皮肤的“暖”和“酥”,对女衾之“香”、女发之“腻”也很少有敏锐的感觉。因此,这里的效果主要是男性感官中的感觉。“天那!恨薄情一去,音信无个!”这可能是一个有同感的女子能够感到妙意的唯一一段诗句。但即使在这里,两性读者进入这首诗的程序也是不同的。因为这里的真正艺术效果不是恨,也不是半嗔半爱,而是写的这个女子的可爱。一个男性读者更能体会到柳永的用意。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词的下阕是直承上阕的最后一小段的。人们说这首词用的是“代言体”,实质上只有到了下阕才真正把视角转到了这个女子身上。但在这时,这个女子已经被男性的需要所确定了。这是一个在男性的享乐欲望中被规定了的女性。这个女性的根本特征是要求着这个男子的,并且只作为一个异性要求着这个男子。在下阕中,这个女子的口吻和环境中的事物的色彩有了更大的差异。这里的“雕鞍”、“鸡窗”、“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都是相当文雅的事物,而这个女子的语言和表达的愿望和表现着十分单纯、乃至十分世俗的特征。这仍然说明这个女子是一个青楼女子。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感到柳永这首词的真实性和他对青楼女子心理把握的精确性。在后来的知识分子中,逐渐把青楼女子雅化了。这种雅化实际是中国才子型知识分子自我雅化的需要,他们既需到歌楼妓院寻找生活乐趣,又要维持自己高雅的身分,就自觉不自觉把他们与之交游的青楼女子也完全高雅化了。但是,这类女子的高雅是在歌楼妓院的商业性需要中有意识地被调教出来的,她们在琴棋书画这诸多外部技能上都表现着高雅的特征,但她们的高雅化不是全部意义上的。她们对事、对人的理解上的单纯不但为政治官僚所不及,甚至也为同龄的社会、家庭女子所不及,而这正是柳永这首词真率可爱特征的客观来源。被才子化的官僚知识分子所垂青的青楼妙龄女子,恰恰是最少社会人生考虑的女子,她们的愿望和要求更是从自我直观的感受中产生的。她们对男性的要求更是单纯的两性要求以及由此产生的爱抚的要求。但是,这种要求虽然简单可爱,但却不是一般社会女子的爱情要求。社会上的爱情要求是多方面的,并且更是内在精神上的。它超越于单纯婚姻的物质实利性,但又不同于单纯的两性之间的需要。爱情的排它性主要集中于对同性竞争者的排斥,而不主要表现为异性的社会职能。也就是说,两性性爱关系主要与整个社会争宠,从而把异性据为己有,爱情关系包含两性关系但不等同于两性关系,它主要与同性争宠但不与整个社会争宠,它更希望所爱的对象在社会上获得荣誉。由此我们看到,柳永这首词的基本意义不是表达了对这个女性的爱,而是表达了对当时官宦生活的厌恶。由于这种厌恶,他希望逃回到单纯的享乐生活之中去;而这种希望,他又是通过一个青楼女子对男性的要求表达出来的,是以对这个女性愿望的满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他的女性视角只不过是男性视角的转换形态,最终还是回到了男性的视角之中来。
但是,这里的女性视角也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实际上起到了以女定男的作用。在这首词里,男性的生存价值是用女性对他的需要规定下来的。但是,男性生存的意义并不能全用女性对他的需要来规定,正象女性存在的价值不能仅仅由男性对她的需要来规定一样。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女子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被规定的,但男子仍然离不开女性和女性的爱,当女性被男性束缚成没有主动性的奴隶之后,对女性有所需求的男性则通过自己对自己的束缚而获取女性的爱,这也就开始了男子女性化的过程。中国古代才子型的官僚知识分子,京戏舞台上女扮男的小生类典型人物,都无非是一些女性化了的男人,“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对于儒家道统当然有破坏作用,但却不能认为这就是爱情的追求和正当的人生观念。
1995年9月18日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标签:柳永论文; 文学论文; 定风波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花间论文; 古代文人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爱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