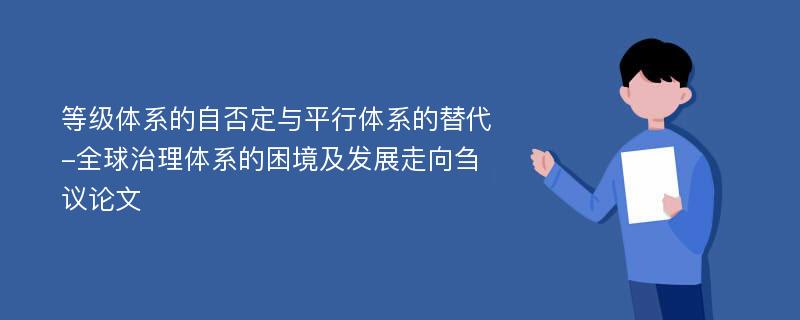
等级体系的自否定与平行体系的替代
——全球治理体系的困境及发展走向刍议
林 海 虹
(中国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8)
摘 要: 近代以来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很大程度上被打上“西方制造”的痕迹,尤其是二战之后,美国主导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制订。然而,时至今日,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已不能帮助西方国家克服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反而使这一矛盾日趋尖锐。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正遭遇自否定的困境。这是因为西方全球治理的等级体系存在以下先天缺陷:自由主义全球体系本质上并不自由;自由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家目标日趋背离,国内政治影响全球治理体系变迁;西方滥用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权,导致现存体系公信力下降。权力转移导致西方全球治理体系的根基发生动摇,全球治理体系正从等级体系向平行体系转化,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保持定力,发挥自身的制度潜能和引领作用。
关键词: 全球治理; 等级体系; 平行体系; 替代
当前,随着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潮流升温,西方国家维系多年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瓦解与重构风险,人类社会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新形势下,全球治理体系亟须“创造性转换”。“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1]260本文拟剖析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诸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若干基本准则。
一、 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遭遇自否定困境
现代世界体系很大程度是由西方主导的,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很大程度被打上“西方制造”的痕迹。尤其二战结束后,在美国主导和推动下,建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一系列国际组织以及相关国际规则。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既反映了国际社会中各个国家谋求发展与合作的共同需要,也包含着西方大国建立制度霸权的考虑。“国际机构常常是反映霸权的需要并保护霸权。它们普及世界权力结构的规范,这种权力结构统治靠支持国际机构自身来维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机构是现状的压舱石。”[2]81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套全球治理体系行之有效,既保证了国际社会的正常运转,也使西方大国以隐蔽方式获得巨大霸权收益。然而,时至今日,这套全球治理体系弊端丛生,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不能从中从容获益。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也开始质疑自己一手打造的国际体系与规制。近年来,西方世界出现的逆全球化、右翼思潮复兴、贸易保护主义、频繁“退群”等种种不正常现象,就是对这套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自我否定。由此,国际社会出现了“西方国家反对西方打造的世界体系”的反常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规则制定者带头破坏规则的现象?说到底,这是因为现行国际体系已无法帮助西方国家解决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反而使这一矛盾日趋尖锐化。
总之,疏血通注射液联合纳洛酮治疗慢性肺心病急性加重期能抑制血浆ET‐1的表达,改善肺动脉压力,具有抗凝的作用,从而有利于提高治疗疗效。
汉娜·阿伦特曾敏锐地指出,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力来保护持续增长的财产[3]29。意大利学者阿瑞吉也提到,资本主义的积累是无休止的。但资本过度积累必然导致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劳动盈余体现在失业率的上升,资本盈余体现为闲置的生产力和货币资本),由此造成资本贬值和经济危机[2]89。因此,资本为了实现盈余,必须不断寻找盈利方式。
第二,托换梁和被托换结构之间结合处理。为保证托换梁和被托换桥墩之间的牢固连接,采用植筋的形式进行处理。首先对原墩界面处理,步骤如下:
泪水盈满了我的双眸,这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知道了结局,却无法改变。我只有眺望远方,看看这江南最后的繁华。
针灸:选用2寸毫针,穴位选择为灵台穴和大椎穴,在疱疹起始部位呈15°角进针,针尖刺病灶中心,反复捻转,在针刺方向使用同样方法,避免疱疹蔓延[1]。
施工材料在工程造价中占有绝大多数的比重,材料的总费用的高低直接影响施工成本的控制情况。一些施工工程缺乏在材料上的精细化管理,领料、用料、购料、余料等方面都缺乏精确的核算和统一的管理,造成材料丢失和浪费严重,无形之中增加了不少施工成本。对劳务队、作业班组、项目部没有统一的用料管理制度,这些部门在施工生产过程中都存在严重的混凝土、建材等方面的消耗。
3.1 传统的数字PCR是进行绝对核酸量化的方法,它基于在有限稀释的条件下将各个分析物分子分配成许多重复反应的绝对核酸定量方法,在大多数反应中产生1个或0个分子。终点PCR后,模板的起始浓度通过泊松分布统计分析确定阳性(含有扩增的靶标)和阴性(未扩增的靶标检测的反应)。数字 PCR比qPCR具有许多潜在的优势。近来,该技术已经商业化,将反应分为纳米级大小的液滴。数千个液滴的快速微流体分析每个样品使ddPCR适用于常规使用,并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实际动态范围(对每个液滴的多个目标分子进行泊松校正)[20]。
然而,金融行业的恶性膨胀导致经济泡沫化,并最终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学者克罗蒂(Crotty)在2009年曾指出,在投资界拿高薪酬的“呼风唤雨者”是系统性风险的根源,后者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系统的崩溃[3]118。更严重的是,在金融业畸形繁荣的挤出效应下,西方国家那些原本解决更多数人就业、给更多人带来福祉的实体经济(机械制造、纺织业等)日益变成“夕阳工业”并逐渐消失。大型超市、餐饮业等服务业的兴起,虽然同样可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但低端服务业收入不高,且以短期临时工作为主。而高端服务业(如电子行业)则需要专业技术特长,只能是少数人的领域。
金融资本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为解决滞胀导致银行盈利能力大幅下降问题,美国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借贷成本,直接增加银行机构的盈利。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纷纷放松金融管制,先后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与《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放弃了对信用违约、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并实现了存贷款利率的自由浮动。金融业成为美国经济中增长最快、最有利可图的部门。金融行业雇员平均工资增长明显领先于其他行业。
因而,新自由主义政策催生了“二元经济”:由FTE(金融、科技和电子)产业组成的高收入产业,以及由半技术、非技术工人组成的低收入产业,夹在中间的则是收入不断缩水的制造业从业者及白领等“中等收入人群”。许多中低收入阶层对现状日益不满,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在经济愈发向金融和金融服务业倾斜的“后工业时代”,自己是被遗弃的那群人中的一员[5]40。总之,西方国家大力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全球治理体系,看似延缓了经济滞涨问题,但又形成了更具破坏力的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制度陷入更加深重的危机。“美国模式”日渐失去了原有的诱人光环。
具体来说,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三大结构性缺陷:
二、 西方全球治理的等级体系存在先天缺陷
全球治理体系通常被认为是由各主权国家组成的平等且多元的无政府社会,但近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可以影响、压制其他国家,形成了事实上的等级体系:在经济层面,因生产体系分工不同而形成了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依附关系;政治上则形成了西方列强集团、中等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分层与控制机制。因而全球治理体系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西方特质,美国则自视为西方文明的“山巅之城”。
一直以来,西方大国依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确立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或权威;二战后,各主权平等国家让渡部分权利形成的契约型权威代替强权成为主流。但契约型权威不具备法理型权威的合法性,需要寻找治理的道义基础,有时甚至需要借助宗教等神性资源,确保权威的延续。因此,全球治理体系从产生开始,主导国的权威就是由两套并行不悖的体系构成的:一方面,主导国的权威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及综合实力基础上,可以强行压制其他国家服从其领导;另一方面,主导国又不是单纯依赖暴力征服,而是通过建立国际规则等方式,低成本维系其霸权统治。
本机制动管减压,平均管、作用管增压,机车制动缸充风产生制动作用。补机接收制动管压力减少的变化,通过DBTV模块停止制动管给辅助风缸充风,并将辅助风缸的风压传送到16TV作用管;补机接收平均管压力增高的变化,通过BCCP给制动缸充风,补机制动
从深层看,全球治理体系是主权国家(特别是大国)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各种力量互动交锋的产物,全球体系的发展路径证明了这一点。在经济繁荣时期,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经济效应会惠及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在这一阶段也显得慷慨仁慈;在经济危机时期,西方国家则会毫不犹豫地否定和推翻其一手塑造的国际秩序,使发展中国家沦为弃子。这样,国际秩序经常呈现出令人迷惑的一体两面:忽而是滥用权力残暴的“帝国主义”者,忽而是彬彬有礼、倡导自由、民主的“西方绅士”。但万变不离其宗,最终目的都是优先维系主导国的利益。换句话说,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先天具有不稳定性,其建立和维系依赖西方大国的推动,其被破坏和颠覆同样取决于西方体系内部的力量。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国联、联合国等,都是由西方大国建立的,这些国际组织的解散或“去功能化”均取决于西方大国的好恶。由此不难理解,特朗普的“退群”和逆全球化举动,恰好体现出对现行国际机制的实用主义态度。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欧美出现了针对现行经济体制和经济全球化的种种反叛举动。2011年美国出现了反对金融寡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6年11月,美国民众又将奉行反全球化的特朗普选为总统。特朗普把自己打造成“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表,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推行了一系列反全球化举措:退出TPP、NAFTA、世界邮政联盟等多个国际机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与中国等多国大打贸易战;鼓励制造业回国建厂;反对非法移民等。这些做法看似乖张,实则反映了美国中下层民众的心声。从更大范围看,特朗普带有“新孤立主义”色彩的内外政策,意味着美国正在着手推翻由自己一手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正遭遇自否定的困境。“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日趋凸显,需要从全球治理体系本身寻找答案。
(一) 自由主义全球体系本质上并不自由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主流范式是资本主义国家引以为傲的自由主义秩序。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全球治理模式强调全球经济建立在市场竞争基础上,国家只扮演辅助性角色。换言之,跨国公司或市场逻辑才是全球治理的真正主角[6]324-325。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自由主义世界体系并非单纯依靠市场竞争原则,相反,它是国际体系中大国实力此消彼长的结果,处处打着“大国博弈”的色彩。
以英国建立的全球体系为例。英国在早期扩张时期,先是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后来与荷兰进行了四次英荷战争,19世纪又击败欧洲陆上强国法国,建立起所谓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维系这套体系,背后靠的同样是空前强大的军事能力和“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国家干预。“它的扩张通过贸易、移民和资本投资等方式来进行,国家也采取行动给予支持和助长。英国为促进资本主义扩张所采取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有一个共同点: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正式的干预和控制,但如有可能,则做出非正式的、代价较小的安排,由可靠的地方政府负责执行规定。”[7]100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随着资本主义全球积累和全球扩张,主权国家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6]324-325。当年英国向世界市场出口呢绒产品,在国内进行“圈地运动”,导致大量贫民出现,英国政府为资本主义市场扩张“背书”,出台了《济贫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则通过建立社会福利政策的办法,运用失业救济和童工、女工救济等社会政策,解决市场扩张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更需要国家提供相应的支持。
测量放线→井点降水→工字钢支护→土方开挖(围檩和横撑一并施工)→设置排水沟→混凝土垫层施工→承台施工→基坑回填(围檩和横撑拆除)→工字钢拆除。
换言之,英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是由“硬实力”和“软实力”组合而成。从“软实力”角度看,英国的目的就是“促进这个岛屿型商业主义国家的利益”[7]127,因此,英国把世界市场奉为衡量政策的首要标准,认为在世界各地自由通商,要比大英帝国的形式重要得多,为此,他们在欧洲推行均势政策,同情和支持其海外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维持欧洲各大国力量均衡,以确保英国对海洋无可匹敌的控制权,获得了道义和力量上的双重收益。英国倡导“自由贸易”原则,说到底是因为英国工业能力强大,可以用高附加值产品交换别国的原材料和初期产品。一旦这一交换关系受阻,英国会毫不犹豫地用武力维护所谓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1840年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就是典型案例。
曾几何时,技术创新变成了资本主义转移矛盾、延缓寿命的重要法宝。二战后,西方国家通过技术革命实现“创造性毁灭”,使资本主义世界实现了持续20多年的快速增长。但到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遭遇滞胀危机(增长停滞与高通胀率并存)。表面上看,这与1973年中东石油战争导致油价飙升,企业生产成本增加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德国、日本经济整体复苏,美国制造业的优势日渐丧失,资本投资收益率降低,资本过度积累矛盾再次凸显。缓慢的经济增长导致国内投资减弱,而通货膨胀则瓦解了银行的传统信贷模式——从客户吸收存款并放贷给投资者。总之,滞胀导致了银行盈利能力的大幅下降[4]105。
美国也是如此。20世纪初,美国大力倡导“门户开放”。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建立了更为开放的自由主义全球治理体系,其本质与英国异曲同工,都是试图借减少国家间阻碍商品、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帮助本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获胜。苏联解体后,美国一些人毫不掩饰地宣称,美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主宰全球的“新罗马帝国”。这个“新”就在于更多采用法律规则、投资贸易、金融体系、知识产权、人权、法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渗透等来征服和扩大全球市场。比如挟持国际组织的权威来支配主权国家,在商业贷款中附加私有化、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要求,用所谓“华盛顿共识”来控制弱小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政治力量,甚至采取“颜色革命”的战术来摧毁主权国家等[8]。就此而言,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秩序并不自由。
(二) 自由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与西方国家的总体目标日趋背离
自由主义全球秩序是主导国国内利益的延伸。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中,企业看似可以不受限制地参与市场竞争,实则需要国家来应对各种不确定现象,有时甚至需要动用军事力量来保护海外权益。这是因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强调以市场竞争为原则,崇尚优胜劣汰,由此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制造出一大批边缘群体。贫富分化破坏了传统社会结构,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自由主义秩序要获得广泛支持,必须借助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政策弥合这一裂痕。跨国公司作为经济主体,不可能把照顾弱势群体作为自己的任务目标,但主权国家政府则必须面对乃至解决由此带来的大量边缘群体。
CT检查:采用西门子16排CT机,层厚0.625mm,螺距0.516:1,常规扫描,观察腰椎间盘位置及形态,测定腰椎间盘密度;除观察椎小关节、椎体、椎弓情况外,对椎管径线、恻隐窝情况做出评价,进一步确定病变情况。
在磷复肥产销会召开之前,东北、鲁东、西南和山西等区域的冬储市场就已经启动,但是受终端需求逐年疲软和原料价格持续高位的影响,大部分经销商对冬储还是持观望态度,备货并不积极,这也导致生产厂家新单情况一般,依旧以发前期订单为主。与此同时,厂家前期的低价原料基本已经消耗殆尽,目前多采取降低开工率、以销定产的方式规避风险。预计本月底或下月初,业内的标杆厂家就会公布冬储报价,届时复合肥冬储市场将会逐渐趋于明朗,厂家也会恢复开工率,加快生产进度。
跨国公司虽然具有超越主权国家的权力独立性,但其活动仍然需要主权国家提供相应的规则、制度、环境、服务机制等配套设施。公司需要生存在主权国家之中,从民族国家的有序性管理中获益[6]324-325。越是全球化的企业,越是寻求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有效治理。也就是说,真正的自由市场秩序是在“国家保姆”的精心呵护下成长起来的。资本与国家本质上是一种共谋关系。反过来看,全球治理体系是西方大国国内政策国际化的产物,它以国内经济扩张为基础,所以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制度往往是主导国国内规则、制度的折射,反映的是主导国的国家利益。近年来,美国频繁利用国内法(如《反海外腐败法》)在国际社会进行“长臂管辖”,刻意打击威胁其经济利益的其他国家公司。这种不正常现象恰好表明,现行国际规范是西方大国国内政策的延伸,由此使西方国家的国内法成为打击异己的手段。
全球体系不仅是国家与资本共谋的结果,还是国家与民众利益协调的产物。当民众利益因国内经济失误或经济危机受损,资本主义国家就通过对外转嫁危机的形式,来平衡和协调资本利益扩张和其他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例如,20世纪初,随着美德新兴工业国的崛起,过剩的生产能力使全球资本主义竞争加剧。各国资本利用国家的力量,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确保本国市场、屏蔽全球化的影响。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为缓解国内阶级矛盾,花费很大力气来建立社会协调机制。在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政府为缓解国内不平等问题,大力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并制定反垄断法,防止资本在市场上形成垄断。后来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直接运用国家手段救助失业群体。德国20世纪20年代建立的魏玛共和国也是运用国家力量来推行社会福利政策。
这些国家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有效缓解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因此,资本力量依赖国家机器这一润滑器,与它的对立面(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达成妥协,社会大众甚至成为资本主义市场扩张政策的重要支持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的战争就得到各国民众的大力支持。这说明,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主权国家可以将资本和劳工力量整合起来一致对外,并通过从落后国家获得资源,来缓和国内日益紧张的阶级矛盾。遗憾的是,资本和劳动力两大生产要素之间矛盾难以调和,因劳资力量在不同时期态势不同,造成政府在资本和劳动之间首鼠两端,对待全球秩序态度前后不一。这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中的常态现象。
从现实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与国家及多数民众的目标日趋相互背离。这是因为资本运作的铁律就是谋求利润最大化,哪里有升值潜力,它就流向哪里。资本的流动又会带动产品生产线的转移。对输入国来说,资本和生产的引入可以增加就业,满足资金需求;但对输出国来说,资本和生产对外转移则会带来巨大冲击,甚至危及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9]3。从现实情况看,在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规律的作用下,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工业资本家主动或被动地将生产企业迁往土地和劳动力更加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日趋金融化,而金融资本扩张加剧了“产业空心化”,由此造成了发达国家税收减少、失业率上升,昔日工业区沦为“铁锈地带”等一系列后遗症。因此,在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中,此时的赢家可能变成彼时的输家。
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内部和谐共处的劳资关系日趋转向分裂与对立:资本和跨国公司支持并推动全球经济扩张,民众却力主国家实行贸易保护,减少移民,保护就业。这些弱势群体把振兴国家以及改善生活的希望寄托于主权国家的力量。正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失意群体的推动下,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和民粹情绪才日趋上升,这些人构成了支持特朗普当总统的重要社会和民意基础。
(三) 西方滥用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权,导致现存体系公信力下降
保障各国平等,实现共同发展,是各国对国际秩序的共识。基于这种共识建立起来的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同和尊重。国际社会对建立和主导这套国际秩序的西方国家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可以为落后国家和地区带来资金和先进技术,最终实现共同繁荣。为此,很多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亦步亦趋,甚至放弃部分主权国家权力,全盘移植来自西方的价值体系、管理方式,接受外来文化的改造。
遗憾的是,西方国家滥用了国际体系治理者的优势地位,将西方价值体系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体系,引导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或利用国际规则谋取私利,或随意毁弃规则,由此逐渐丧失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法性。从实践看,西方主导全球政治治理体系霸权色彩浓厚,全球治理成为“大国治理”乃至“霸权治理”。
美国是当今全球治理体系的建立者和主导者。美国对外政策在滥用权力的“霸道”和“王道”之间反复变动,生动地折射出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始终存在“并行但相悖”的双面属性。
虽然美国自认为是个反殖民主义国家,但其真实历史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帝国扩张史。美国建国后接连发动战争,武力吞并了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等地区。1898年美国又发动美西战争,在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得以扩张[10]125。进入20世纪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日渐走出美洲,向世界扩张。但当时美国的整体实力仍不足以与已建立全球帝国的英国抗衡。因此,美国一面进行帝国扩张,一面举起道义大旗。例如,美国在亚洲标榜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没有像传统帝国那样分割中国领土,而是强调“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均大力倡导“民族自决”原则,借此动摇英国全球统治的道义基础。美国打起反殖民主义的旗帜,和苏联的反帝国主义纲领抗衡,强调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推翻殖民统治的国家,由此激发发展中国家的“共情”感。
在二战后,美国不仅“没有攫取战败国日本的殖民地,也没有占有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关岛附近的海域,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先声,得到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并最终肢解了英国和法国”[10]127。正如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强国英国赞成“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以便进入世界市场一样,20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强国美国,赞成反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目的就是将自己的统治强加在刚刚从英国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民的头上[11]142-148。从二战结束直到冷战结束之初,美国一直奉行多边主义原则,放弃利益最大化,通过多边机制来维护其在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即使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美国通过诉诸北约这一多边机制获得战争授权以及西方盟国支持。“霸权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可以被霸权统治下的大多数人接受。”[12]43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转而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本国,他们强调减少国家管制,弱化政府经济职能,特别是减少国家对劳工群体的扶助政策,主张以市场来解决经济和政治危机。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对强调公众福利的凯恩斯主义的否定,它支持营造一种亲资本的社会氛围[3]104。在国际上,便是倡导自由贸易,号召各国减少管制,构筑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秩序。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一超独霸的超强实力使美国称霸的野心随之膨胀。美国的对外政策日益从多边主义转变为单边主义,把说服改为压制。2003年,美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条件下发动伊拉克战争,“露出藏于正当性的丝绒手套之中的铁拳”[10]185,毫无顾忌地干涉他国内政。美国不需要再给伙伴恩惠换取权威,只要肆无忌惮地使用武力,就可以使其他国家默认或拥护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美国一位外交人员把这一“新帝国主义”转向的本质总结为罗马国王卡里古拉所说的格言“让他们恨吧,只要他们恐惧就行”[10]130-131。同时,美国对它一手打造的国际制度失去耐心,不愿受其约束,从小布什政府开始,就频频退群,拒绝《京都议定书》,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有效核查机制,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甚至还频繁利用国内法律来打击盟友。特朗普“退群”和逆全球化举动,恰好体现出西方大国对现行国际机制的实用主义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和代表性不足,严重制约了全球治理的发展。
三、 从等级体系转向平行体系:世界呼唤新的全球治理体系
从宏观视野和历史纵深来看,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有两套话语体系:一套是西方国家倡导并长期奉行的等级关系;另一套是发展中国家倡导的强调自主性的平行世界观。构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大方向就是从等级性体系转向平行性的全球体系。
(一) 西方全球治理的等级性体系正因权力转移而发生根基动摇
历史历来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现行国际体系是西方国家主导的等级性体系,因此西方国家国力兴衰,直接影响其有效性和权威性。过去相当长时期内,世界权力的接力棒始终在西方国家内部传递(从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从荷兰到英国,最终又从英国转到美国),由此使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以及其所推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长期主宰世界,乃至一度被认为是“历史的终结者”。
但发展不平衡是国际政治的铁律。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大变局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国际力量对比“南升北降”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整体影响力持续下降。美国虽然仍是唯一超级大国,但不少经济指标明显下降。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相对崛起态势明显。2012年,发展中国家GDP总量百年来首次超过西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率为33.2%,居世界首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日趋动摇。尤其在美国频频“退群”,转而奉行“新孤立主义”的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已经到了动能转换、模式更新的十字路口。
何谓“人渣”?当年迅翁未明确界定。但从他所言文坛“人渣”多分析,用他“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的话判断,他说的“人渣”当是那些无良知的软骨头以及“才子加流氓”模样的败类,还有某些不爱学习又不肯用功“留长头发,放大领结”的青年。仅就以上意思,还难以确定“人渣”内涵,但也可看出,现说的“人渣”与当年迅翁说的,无论内涵外延,都更宽泛了。
在总体实力下降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维持等级体系越来越难。等级体系的霸权国需要为体系提供和平与秩序等公共产品,这需要花费精力和投入资金。一般来说,在国际体系稳定期,“各霸权时期的典型特征是‘良性循环’,社会安定、贸易和生产扩张一波接一波。而各霸权转移时期则相反,它表现为‘恶性循环’。国家间和企业间竞争激化,社会机能失调,冲突不断增加,直至整个体系动乱,国家崩溃和社会革命”[13]164。
与此同时,霸权国在建立治理体系的过程中需要让渡部分权力,但国际法律和制度一旦产生,就具有自主性,对制订者有约束作用。霸权国能否遵守规则,决定着治理体系的成败,而体系的领导者遭遇危机,首先放弃的一定是国际体系中的“国际主义”义务。因此,等级体系的建立很难,维持更难,丧失则很容易,这一体系脆弱而短暂,沃勒斯坦此前曾提出:“这样的现实大国霸权时期,即霸权大国将其意志与秩序,强加于其他重要大国的能力,不会遇到严肃挑战的时机,在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上,都是相对短暂的。在我看来,仅仅有过三次,17世纪中期的荷兰,19世纪中期的联合王国,20世纪中期的美国,按照上述定义,它们的霸权各自都延续了25年左右”[14]146。近年来,美国随着国力持续下降,其主导国际体系的意愿和能力都随之下降,尤其是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频频退出各种国际机制,等于自行放弃了作为国际体系维护者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西方国家霸权衰落使其主导多年的国际体系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
(二) 全球治理从等级体系向平行体系转化的呼声日高、动力强劲
当前中俄等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国际政治多极化态势日趋明显。这种权力的扁平化和“去中心化”态势,使全球治理体系更有可能从过去“美国说了算”的等级关系,转向“大家商量着办”的平行式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方向发展。
这是因为,一方面,西方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确实有局限性,但并非完全没有合理性。况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经济和军事领域仍占据较大优势,因此其仍有能力维系这种弊端丛生的全球治理体系。另一方面,俄罗斯、中国等国倡导的国际新秩序虽然更具历史进步性,但由于总体实力难以支撑起一个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多的是一种奋斗目标和愿景,而不是已经变成现实。退一步看,“中国模式”只是中国进行国家治理模式的成功实践,这种模式固然包含了发展成功的共性规律,但也有不少中国特定国情的特殊性成分。在当前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也应该是一体多元、百花齐放的。
具体地说,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应该包括以下两大基本原则。
1. 承认主权国家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最基本行为体。从法理角度看,国际制度、国际规则体系应当是各国合作的共识与底线。但在当前的全球治理实践中,国际规则是体系治理者(西方大国)为被治理者(发展中国家)“量身打造”的,却对自己没有约束力。当前西方力量衰落时,最先强调主权国家利益,破坏全球秩序及规则的首先是“自由民主旗手”美国。自由秩序在西方最引以为荣的经济领域都没有实现,国际政治领域的治理更是阻力重重。这一体系也会因为缺乏规则的随意性而丧失公信力和合法性。因此,与其强调“人权高于主权”等不切实际的规则,不如承认全球政治治理的重要前提是主权国家的前提和利益。即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主权国家仍然是最基本的行为体。中国政府提出的“尊重各国主权平等,不相互干涉国家内政”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是国际社会中各国交往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同样是以主权国家为出发点形成的一种平行国际关系。这也是新型全球治理体系与西方主导的等级性的国际治理体系最本质的区别。
2. 发展是全球治理体系的第一要务。当前全球治理模式应该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要解决困扰各国内部的贫富分化问题,以及国家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这些问题是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造成的。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外围”与“中心”的等级式经济结构。破解这一难题,必须改变“资本至上”、市场万能的迷思,建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努力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更具可持续性的国际经济秩序。进一步说,就是在全球治理中更多注入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
当前,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光环不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已到了新旧交替的混沌期,人类亟需更具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体系。有学者认为,随着西方主导的治理体系的衰落,世界治理正在进入“中国时间”。但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1]514。国际政治生态因复杂多元而丰富多彩,文明间因互鉴交流而相互受益。全球治理体系同样应该是“一体多元”,基于各国认可的最大公约数。中国作为正在复兴的“复合文明型”国家,有义务也有必要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为全球治理体系建构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需要指出的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是个动态、复杂、长期的工程,由此决定了中国必须保持定力和耐力,持之以恒。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2] 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M].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3]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 唐纳德·托马斯科维奇-迪维, 林庚厚.收入不平等、经济租金和美国经济的金融化[J].政治经济学报,2015(5):99-122.
[5] 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M].马 霖,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6] 保罗·赫斯特,格雷厄姆·汤普森.质疑全球化——国际政治与治理的可能性[M].张文成,许保友,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 罗伯特·W·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M].林 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8] 强世功.《美国陷阱》揭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霸凌主义案例[J].求是,2019(12):73-76.
[9] 威廉·格雷德.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M].张定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0] 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M].高婉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11] 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M].苏仲彦,桂成芳,希 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
[12] 西蒙·赖克,理查德·内德·勒勃.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M].陈 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13] 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J·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M].王宇洁,译.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3.
[14] 弗朗西斯科·洛佩斯·赛格雷拉.全球化与世界体系[M].白凤森,徐文渊,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The Self -Negation of the Hierarchy and the Substitution of the Parallel System —On the Dilemma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Lin Haihong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formed in modern times is largely marked by “Made in the West”. Especially after World War II, the United States l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rules. However, the current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can no longer help western countries overcome their internal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but make them increasingly acute. The western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is suffering from self-denial for the inherent defects of the hierarchical system of western global governance: the liberal global system is not free in nature, it deviates from the national goals, and domestic politics influences the change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abuse of the dominant power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by the West has reduced the credibility of the existing system. The shift of power has shaken the foundation of the western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which is transforming from a hierarchical system to a parallel one. In this process, China should stay calm and play its institutional potential and leading role.
Key words : global governance; hierarchy; parallel system; substitution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19)06-0008-08
DOI: 10.13317/j.cnki.jdskxb.2019.063
收稿日期: 2019-08-05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大专项课题(19JZDZ015)
作者简介: 林海虹,副教授,法学博士,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室主任,从事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和国际政治研究。
(责任编辑 张向凤)
标签:全球治理论文; 等级体系论文; 平行体系论文; 替代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