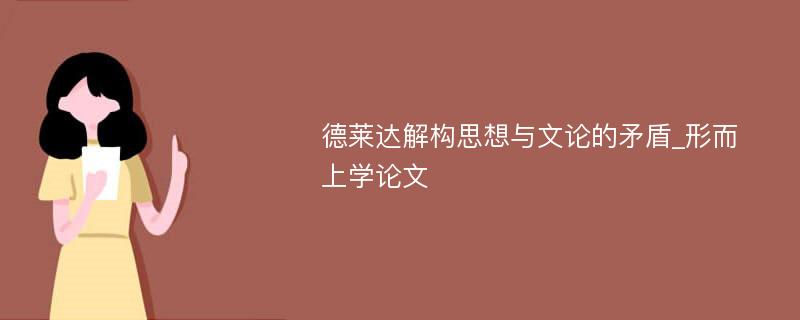
德理达解构思想对文学理论的不洽适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思想论文,德理达论文,不洽适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5—0066—08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德里达在美国以文学批评家和比较文学学者的身份从事学术活动,他总是在文学场域内实施他的解构操作。在国内外文学批评领域,解构也成为批评家们的时尚。但是我们发现,德里达的理论与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不洽适性,有一条根本的裂痕阻止着德里达解构理论直接通达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界应对这一裂痕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场”和“隐喻”是德里达攻击哲学形而上学的两个根本性概念,它们也恰好是文学理论中的两个关键概念。笔者以下就从考察德里达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入手,显示他的立场与文学的立场之间的这一重要裂痕。
一、德里达的“在场”与文学的“在场”
在场就是在现场,就是出席,它表明主体对所指的场合拥有确切经验和亲身经历。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① 一书中指出,形而上学为了证明自身合法性而引入在场机制。在场这样证实自己:“因为当场而且立即独立于主体性事件和活动的理想对象无限地被重复而始终还是同一个对象”[1]95,从而它们既获得即时性,又获得永久性。按理,可重复的东西是不可经验的,是“理想对象”。为了使之可经验(这是在场的关键),必须找到一个现实的物质要素,德里达称之为“中项”。“它(理想对象——引者注)的理想存在既然在世界之外就一无所是,它就应该在一个中项中被构成,被重复,被表达,而这个中项无损于在场和追求它的活动的自我在场:这个中项既保持了面对直观的‘对象的在场’,又保持了自我在场,即活动对自身的绝对靠近……声音就是这种因素的名字。声音被听见。各种语音符号(索绪尔所说的‘听觉形象’,现象学的声音)被主体听见,这个主体在它们的现在的绝对接近中把它们发出声来。主体并不要越到自我之外就直接地被表达的活动所影响。我的言语是‘活的’,因为看来它们没有离开我:它们没有在我之外、在我的气息之外落入可见的远离之中,它们不间断地归属于我,并且无条件地归我所支配。[1]96 也就是说,当主体在讲话时,声响这种物质要素似乎从外面触及主体的感官,使主体处在被触动中,它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因而主体有一种就在现场的感觉。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听觉要素(能指)在随后消失了。“声音的‘表面超验性’系于总是身为理想本质的所指,即被表达的意义直接向表达活动在场的东西。这种直接的在场系于能指的现象学‘身体’在它产生的时刻就似乎消失的东西身上。能指似乎已经属于理想性的因素。从现象学的观点看,它自我还原,它把自己身体的世俗不透明性改造成为纯粹的半透明性。这种可感身体的形式与其外在性的消失,在意识看来就是所指直接在场的形式本身。”②[1]98 如果能指一直是凸显的、可感的和不透明的,意义就一直在我之外,无法归属于我;在触动我之后,语音(能指)必须使自身隐去,而让位于所指,由所指占有能指原来占有的位置。也就是说,当我们听到一种语音时,我们觉得直接就听到了意义本身,在声音和意义之间没有阻隔。这个过程使语音这种物质要素所拥有的真切性的好处被它所携带的超验信息——所指所得到,意义由此有了物质性证据,以证实自己在场。德里达称这种“被听见——说话”的现象为“一种绝对独特类型的自我影响”[1]100 。自我影响(auto-affection)这个词表明一种被动性(自我受到“影响”),同时也表明这种被动性是通过自我作用(auto,自己听见自己)生成的,因而它也被称为“自恋”的行为。③
但德里达揭露道,这种在场实际上是虚幻的。首先,如果作为在场根据的“被听见——说话”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影响”或“自恋”现象,它就并不具有真正的客观性。其次,在场的在场性取决于能指的消失,就是上文所说的能指的隐去。但实际证明这只是一种幻觉。再次,在场所需要的起点是达不到的。如要证明在场,就必须证明存在着最初被我们听到、看到的一个原点,意识或语言是对这一起点的追逐。德里达指出,“被感知的现在的在场只有在它连续与一个非在场和一个感知组织在一起时,即与回忆与最初的等待(持存和预存状态)组在一起时才可真实地显现出来”[1]81,而当意识反身转向被认为是在场的那个瞬间时, 那个瞬间已成为过去,在场在意识中已经被阻断。这种“间隔”现象无限地推迟了对起点的通达,从而令在场落空。最后,在场需通过文本,但文本作为语言的书写,并不具有实体性。德里达称书写为“替补”,即用文字及其运行体例替代非文字的“纯粹在场”(“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德里达补充道)。“无限系列的替补必然成倍增加替补的中介,这种中介创造了它们所推迟的意义,即事物本身的幻影、直接在场的幻影、原始知觉的幻影。”[2]228
德里达揭露“在场”机制对形而上学所起的基础作用,在哲学上无疑是重大发现。那么,德里达意义上的在场与文学意义上的在场的经验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知道,文学追求在场。文学这样做是不是也使自己成了形而上学的呢?
笔者认为,这关键要看文学中的在场是一种什么样的在场,或按德里达的术语,它是所指的直接在场,还是由能指引起、并且能指仍然凸显的在场?
我们来看一个文学在场描写的实例:
当疼痛充满我的感觉神经的最后一个细胞时, 我的脑海里已暂时地把时间、地点和所发生的事情混杂起来,这时我感到左右两旁的深渊更加深不可测,我躺在担架上晃晃悠悠的,好像置身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底座,向绿色的天花板升腾而去。到了这种时刻,我间或也想到:自己莫非已死了,莫非徘徊在痛苦万状的地狱门前,而光束勾画出来的那个门框,对我来说好像是通向光明与良知的入口,一只温厚的手也许会把它打开,因为我自己此时此刻已经像一块石碑一样一动也不能动了,死了,只有从头部伤口放射出来的剧烈的疼痛以及随之而来的恶心呕吐算是唯一的生机。
此后,疼痛又减弱了,好像有人把钳子松开了一点,现实对于我不再是那么残酷可怕:这种有层次的绿色氛围对阅尽苦难的两只眼睛来说是宜人的,这种无限的静穆对备受折磨的两只耳朵来说是舒适的,而回忆对我来说,好像是在看走马灯似的一幅幅与己无关的画面。一切似乎都离得无尽的遥远,然而实际上它们仅仅发生在一个钟头以前。
——海因里希·伯尔《与德林重逢》
伯尔写的是二次大战中的一个场景。故事中的“我”在战场上被炸成重伤,失去知觉后被抬到一个农舍。故事从“我”在这间黑暗的农舍中醒来开始,直到意外地在这农舍中发现自己儿时的伙伴德林,他也身受重伤,躺在这里。在这段文本中,伯尔通过充满“感觉神经的最后一个细胞”的疼痛、“头部伤口放射出来的剧烈的疼痛”、导致“恶心呕吐”的头部疼痛,以及“钳子”钳肉体似的疼痛,写出了疼痛的强度。伯尔还写出了随疼痛程度的变化而变化着的意识状态:“当疼痛充满我的感觉神经的最后一个细胞时……我感到左右两旁的深渊更加深不可测”,此时脑子只有“自己莫非已死了”的简单念头;而当疼痛减弱时,现实便“不再那么残酷可怕”,“我”能感到“有层次的绿色”,眼睛有了“宜人的”感觉,头脑甚至能够回忆。这些描写令读者感同身受。
这种疼痛是不是在场?巧合的是,疼痛也是胡塞尔现象学理论中的经典例子,而德里达对胡塞尔关于切身体验的这种解释持批评态度。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的第三章指出,胡塞尔实际上已经发现:“当我听他人讲话时,从根本上讲,他的体验并不‘亲自’对我在场”[1]48。因此,当一个人说他疼痛时,语言符号并不能直接传达这种疼痛。德里达指出,胡塞尔把表达的间接性视为缺陷,他试图诉诸现象学还原,排除表述所不可避免的外在性,悬搁存在于读者与作品人物(例如德林)之间的关系,通过“自我影响”使他人经验内在化,“重新获取纯粹的表达性”[1]50,这就可以达到对例如德林的疼痛的在场直观。德里达认为, 摆脱这种非直接性的愿望只能是一种幻想。伯尔的叙述虽然针对德林的疼痛,但是作为替换,语词链只会围绕而不可能达到这疼痛,疼痛在叙述中只会被无限地推迟。
我们可以认同德里达,认为这是我们从伯尔的描写中看到的在场的情况,伯尔写出了在场的疼痛经验。这种疼痛虽然并没有传达到我们的感官,但我们能够从意义上理解这种经验。而导致这种理解的原因,既不是伯尔拥有比我们更多的疼痛经验,甚至也不需要伯尔曾经在这样一个农舍中呆过,而是伯尔对于能够引起人们智力和想像力足够敏感的句式和词语的天才操作。所以,文学所给出的在场无疑是语言层面上的在场。就这个意义而言,文学的在场经验本身就是反形而上学的,它可以成为延异的场域和例证。德里达并不一概弃用“在场”这个词,德里达反对的只是“纯粹在场”的假设。相反,他把在场看作是一种书写的在场、替补的在场。他说,写作“是对在场的重新占有”[2]208,因为它把自己交托给替补,替补则是“彻头彻尾的在场,它将在场堆积起来,积累起来”[2]209。
然而,当我们用“疼痛是否纯粹在场”这样的思路来谈论《与德林重逢》时,我们是在对作品作哲学反思。德里达谈论在场是由于胡塞尔现象学未能摆脱形而上学的陷阱,因为他设定了一个理想的原点——在场,从而陷入了一种对固定不变的意义的允诺;海德格尔虽以清算形而上学为己任, 却执著于对始源的追踪,赋倾听以特权,陷入了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这一形而上学窠臼。德里达的视野中没有文学的在场这个课题,文学对于他只是有助于哲学论证的要素。他曾说他对文学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兴趣,是因为文学一直是一种书写的形式,而“书写”是他解构语音中心主义乃至整个形而上学的特效武器。“我常常是在‘利用’文学文本或我对文学文本的分析来展开一种解构的思想。”[3]20 德里达最喜欢的几位作家都与他的解构理论有关:马拉美敏感地注意到诗是语言写就的,他关心能指,“马拉美的所有文本,即使在它组织得最强有力的地方,意义仍然是不确定的,从此,能指不再让自己被横穿过去,它坚守,抵抗,存在,把注意力引向自己”[4]328,他也关注“间隔”,甚至否定在场(“总是没有在场,不——不存在在场”[4]326);乔伊斯的作品提供了诸多对所指事物和意义的延宕、推迟的例证;卢梭则使用“替补”一词表示他写作的方式。
文学并不关心哲学的争议。作家无须关心诸如使用“切身”这个词是不是意味着掉入了形而上学的陷阱之类的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把写出的事实等同于前语言的事实,他甚至从来不考虑是否存在前语言的事实这回事儿。当运用在场式写作时,文学关心的仅仅是能不能写出一种切身在场的经验,即作家以“写得跟真的一样”为目标。王国维有“隔”与“不隔”之别说。所谓“隔”,就是在词语和意义—场景之间有隔阂,不能一目了然,就是绕弯子,不爽快;而“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5]211。这体现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这个中国诗学的重要主题。不过,这个主题并不是有关纯粹在场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的下文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王国维引用的“不隔”的范例)引发了某种意义或曰感受性,这意义系于语言,但又难以言表,故尽在言外。“如在眼前”表达了诗的追求及其所达到的效果;而“见于言外”除了对诗的效果的描绘外,客观上还道出了语言本身的限度,即语言的非透明性。诗的写作存在于语言中在场与限制之间的张力,“不隔”实际上是对形象写作的一种表述。所以,王国维在此要探讨的问题不在“纯粹在场是否可能”这一语境中,这一语境对于它实在是太大而化之、不着边际了。它只是追索,即在用语言引发场景的想像力方面,哪一种写法更好。可以推测,德里达在见到王国维的观点时并不会贸然批驳说,不隔是不可能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臆想,间隔才是语言的本义;“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这种写法应该被具有隔阂效果的“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取代,因为后两句推迟了意义的来临,因而更具有反形而上学的意义。德里达清楚,类似的判断针对的是哲学形而上学,而不是文学的在场描写。
二、德里达的“隐喻”与文学的“隐喻”
隐喻是德里达用于批判形而上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恰好也是诗学(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我们进一步考察在这个概念上两者的重大差异。
在集中讨论隐喻问题的长篇论文《白色的神话》中,很引人注目的是,德里达压根儿没有把隐喻当作一个诗学的概念。“修辞学来自哲学”,德里达在文中开门见山地说,“哲学文本中有隐喻……隐喻看起来完全卷入到哲学语言的使用中去了,在哲学话语中,隐喻的使用决不比所谓自然语言对它的使用少,也就是说,自然语言的用法就是哲学语言的用法”[6]209。
亚里士多德把“隐喻”定义为“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他物……其应用范围包括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和彼此类推”[7]149。德里达认为,虽然亚里士多德不是第一个使用“隐喻”一词的人,但他第一个提出了隐喻的系统定义,这定义“无疑是最清晰、最精确,并且无论如何是最普遍的”[6]231。这一定义反映了隐喻对哲学形而上学可能产生的两个主要作用。首先,它似乎支持了形而上学预设,尽管实际上做不到。这个定义直接表达了用语词捕捉到物(“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他物”)以及真理这个哲学形而上学的主题。亚里士多德只承认名词和名词性的实词为隐喻词,而人们通常把隐喻也分成两类:表示物质的、动物的、生物的隐喻, 以及表示技术的、人工的、经济的、文化的隐喻。这一切,实际上都旨在进入到一个回归的运动,即通过隐喻回归初始的存在。就这个意义而言,隐喻和在场的允诺是一样的,它们都保证能够达到对一个初始的起点的回归。不同的是,在场可以把起点归结为物质性的存在(声音),而隐喻则只能归结为词,即词的字面意义。但德里达揭示道,回归只是一种幻想。“原始意义,最初的、并始终是感性的和物质的表征符号(英译用figure,这个词有图像表达、图形、修辞格、符号等多种意义——引者注)并不恰好就是隐喻。它是某种透明的表征符号,相当于一个字面意义。当哲学话语将它投入流通时,它才成了隐喻。与此同时,第一个意义和第一个替换就被遗忘了。该隐喻不再被注意到,它成了专用意义。这是双重的消抹。哲学可以说就是这一隐喻化的过程,它合其本意地被掠走。从根本上说,哲学文化始终是一种擦抹着的文化。”[6]211 德里达用了一个英译者感到无法翻译的法语词usure来表示这种哲学文化的擦抹用法(usage)。Usure同时具有两个相反的意思:超额获取和贬值。德里达援引法朗士小说《伊壁鸠鲁的花园》中波利斐勒斯的比喻对此进行说明。在那部小说中,波利斐勒斯发现,形而上学者在制造一种相应的语言时,总是用所指原本有限的能指去指称形而上学本体,这很像贫困的磨工们做的一件活儿:他们把硬币上印有币值和图像的一面用磨刀石磨去,然后说,它们不只值五先令了,它们价值无限。但是,这些可怜的磨工并没有制造出真正的增值,他们只是制造了增值的幻觉,一种真正的贬值。形而上学者也通过隐喻的方法磨去了词的有限性,结果这些词大而无当,什么也值不了。哲学通过隐喻承诺对真理的占有,它所承诺的东西却总是远远超出它所能兑现的。德里达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白色的神话”:其承诺是神话,其兑现力是贫乏的、苍白的。其次,“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他物”表明,那个“他物”是达不到的,因为所用来表述的词原本并不属于那个“他物”。按德里达的说法,亚里士多德定义的四种隐喻都可以归结到“彼此类推”一种。隐喻本质上就是“彼此类推”,它的根据是相似性。但相似性不是同一性。这就意味着隐喻永远无法达到它想要达到的目的,永远只在他物周围游荡,成为一种始终无法达到他物的绕行(detour)。隐喻的这种悖论在哲学阵营里引起了对它既爱又恨的态度。“哲学对隐喻的评估总是模棱两可的原因是:隐喻对于直觉(视觉或触觉)、概念(对所指的领会或所指的确切在场),以及意识(临近或自我在场)总是危险的和外在的;但它与它所危及的东西是同谋,在下述意义上它对后者是必需的:绕行成为一种在同一律法则下由相似性功能所引导的回归。”[6]270
如果说绕行对于形而上学来说是一种遗憾的话,对于德里达,它恰好是解构哲学的一个战略。德里达认为:“隐喻并不只是注解了被如此描绘的一般可能性。它冒着搞乱它本应隶属的语义完满性的危险。通过显出转折和绕行(这时意义可能看起来是在独自冒险),隐喻在从它所瞄准的事物中解放出来,从它被迫调整自己以适合于它所指称的真理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启动着语义的流浪之旅……凭借其隐喻替换的力量,意指过程处于某种有效状态,介于无意义的前语言(语言是有意义的)与语言的真理(它把事情说得跟真的一样)之间。这真理不是固定的。”[6]241 这是一种延异的过程。德里达在此看到了隐喻的积极面。
由此可见,德里达关心的是:隐喻击中了还是绕开了形而上学本体?在企图击中那本体的过程中,围绕着语言发生了什么?与在场一样,德里达关注隐喻概念,首先是因为这个词反映了形而上学哲学对思想目标的误解。德里达并没有从文学写作的立场看待隐喻游戏。
对于隐喻,文学从不怀有形而上学的臆想,它关心的只是其描写能力和创新能力。“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他物”是一种生动的描写,其目标不是捕捉住某物,而是使某物有另一种说法。文学因事物各种不同的说法的诞生而称心如意。什克洛夫斯基因而称文学的使命为将“熟悉事物陌生化”,他以托尔斯泰小说为例,认为陌生化的描写可以令事物以新鲜的方式被重新感觉:“在描写事物时,对它的各个部分不使用通用的名称,而是使用其他事物中相应部分的名称”,或者“不说出事物的名称,而是把它当作第一次看见的事物来描写”[8]10。这种方法恰恰正是亚里士多德定义中的隐喻。但在这里发生的不是对事物本义的回归,而是因感觉不断更新所要求的词义的无限生发。文学隐喻早就在进行着德里达所谓的“绕行”,并以之为己任,而从未为自身设置一个回归的任务。现代阐释学者保罗·利科尔认为,科学言语追求效率,其要义在于确保词的一词一义,消除词的歧义现象;相反,诗歌则通过隐喻保留和创造歧义,并享受由词的歧义带来的语言的盛宴,诗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歧义的游戏[9]。
在诗歌中,隐喻不仅表现在上述词义的替换上,而且表现在语音之间的共鸣所产生的语义互渗上,这种德里达几乎未提到过的语音隐喻其实更具有诗学的价值。与散文不同,诗歌文体特别注重各种语音效果,如通过整齐的音节排列、规则的声调或平仄起伏、韵脚等等,增强语言符号的可感知性,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语言的能指,使诗歌成为一种能指的游戏。在诗歌中,音响阻碍了能指与所指的“必然”联系,把能指引人注目地强烈凸显出来。而且能指间通过语音的联结更进一步使语义模糊化和重新配置。雅各布逊指出,话语成为诗,原因就在于它“把对应原则从选择轴心反射到组合轴心”[10]182。 选择轴心和组合轴心的概念来自于索绪尔的联想关系和句段关系理论。在语言中有两种关系:联想关系表现为选词,“把不在现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11]171,从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词,其原则是对应性,词与意义相对应,雅各布逊把这称为隐喻;另一个是句段关系,各个语词要素相组合,呈横向展开,这种关系的原则是毗连性,雅各布逊把它称之为换喻。通常的言语(parole)是选择轴心和组合轴心的同时交叉构成,既选词(对应意义),又造句(连接成句)。但雅各布逊发现,诗歌言语使用特别的构成:在成句时不用毗连性原则,而用对应原则。正是这一点使话语成为了诗歌艺术。对应是隐喻的原则,对应不仅形成语音之间的相对关系,而且也因为语音的相互唤起和呼应,深刻影响词语的意义。保罗·利科尔说:“(诗歌中)响亮的声音形式的再现影响了意义,在那些由相同形式的周期重现弄到一起的启示词汇之间,产生了密切的关系——语义的联系。例如,如果同一诗歌启示引起了‘孤寂’(solitude)和‘抛弃’(désuétude)的共鸣,那么这两个词通过其形式上的类同而维持着一种语义上的交感。孤寂将似乎被抛弃,而部分地耗尽的东西似乎是被弃置了的。宽泛地说,由响亮的声音的相同形式的周期重现引起的这种含义的交感,可以称为‘隐喻’。意义已经‘被置换’、‘被转移’:词语在诗歌中所意指的与它们在散文中所意指的完全不同。一种意义的光环萦绕在它们周围,这时它们由于响亮的声音形式再现而互相被迷住。”[9] 例如,诗歌中的韵脚不仅令诗歌具有节奏,而且也使得占据韵脚的词语之间产生意义共鸣。
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声音的隐喻游戏一方面带来了文学的快感、意义的创新;另一方面,在词义的确定性方面,它带来的是灾难,比起替换隐喻,它更少依赖于所指,产生的歧义更漫无边际,更不符合形而上学理性。这一层面本应成为德里达展开解构思想的一个有力证据。但德里达似乎只对替换隐喻有兴趣。这无非出于以下原因:第一,这是一个只有在诗歌中才应用的隐喻模式,并不常见于其他话语,特别是不会出现于哲学文本中。第二,德里达对语音这一因素特别警惕。我们已经看到逻各斯中心主义正是通过赋予语音以特权而成为在场的物质证据的。在这种情况下,要肯定语音隐喻,显然得重新思考他的那些重要发现。第三,更根本的是,对于隐喻问题,德里达真正感兴趣的是它的及物允诺和不及物实质之间的张力,因为这才能体现反形而上学的主题,语音隐喻由于缺少物或原点这一环节,不具有典型性。德里达对隐喻的关注与文学的旨趣并不相同。
三、小结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德里达对“在场”和“隐喻”这两个词的兴趣来自于他独特的哲学关注点,他通过这两个词看到了哲学形而上学的支撑点和颠覆机制,他关心的实际上是对现象的定性: 纯粹在场或隐喻是否可能, 那些被说成是纯粹在场和隐喻的现象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但这绝对不是文学在这两个概念上关心的问题。德里达的“在场”和“隐喻”只有在他的哲学语境中才能最直接有效地发挥作用。文学不关心它们的定性,只关心怎么把在场和隐喻游戏做好,而这又恰恰是德里达不关心的。在德里达的在场、隐喻与文学的在场、隐喻之间存在着某些重合的方面,例如德里达把书写(当然包括文学写作)视为“对在场的重新占有”,从而有条件地沿用了“在场”概念。但甚至在这些重合之处我们也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根本的裂痕。德里达沿用“在场”只是要表明不存在实质性在场,只有语词在场;而文学只是做这种在场的语言游戏。两者之间的根本裂痕向我们表明,并不存在把德里达解构思想应用到文学研究的直接通道。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同意当代美国学者马克·爱德蒙森在《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中所表达的下述观点:不能听任哲学化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畅行无阻。
[收稿日期]2006—03—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99BZW002)
注释:
① “声音”在此指言说(有声语言)。此书英文名为Speech and Phenomena。
② 德里达在这里提到了现象学,因为在《声音与现象》这本书里,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揭露就是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靶的的。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在场形而上学以及语音中心主义的典型例证。
③ 也可以把“auto-affection”称作“自恋”,“affection”是多义词,除了“影响”、“特征”外,也有“情感”的意思。让它同时具有多种意义,是德里达用这个词的用意之一,在分析卢梭《忏悔录》时,他把这一概念与自体性行为(如手淫)等量齐观。他说:“自体性行为,即一般意义上的自恋,既不开始于也不终结于手淫这一名称所涵盖的内容。”见德里达《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2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