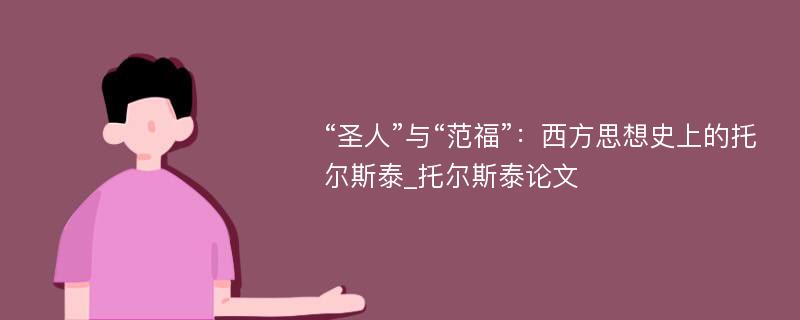
“圣愚”与“凡夫”:西方思想史中的托尔斯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凡夫论文,托尔斯泰论文,思想史论文,圣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1)03-0198-05
“狐狸知道很多件事,刺猬只知道一件最重要的事”。
——古希腊诗人阿基洛克斯(Archilochus)[1]3
重读托尔斯泰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已被述说得太多了。中国人解读托尔斯泰难上加难,在语言和文化的隔膜之外,还隔着意识形态以及欧洲人的各种解读。自1906年托尔斯泰被译介到中国,他就被不断地意识形态化。不论五四时期被当作道德的化身,还是建国后强调他的社会批判精神,托尔斯泰的名字长期以来和“伟大”紧紧关联:他的作品大多是鸿篇巨制,几乎是俄国社会和历史的百科全书……更有意思的是,尽管很多人,比如福楼拜、阿赫沙鲁默夫,都讨厌托尔斯泰满口哲学,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却是位拙劣的思想家,托尔斯泰本人还是更乐于以人类的精神导师自居。他的研究者米克洛夫斯基(N.K.Mikhaylovsky)也曾强调托尔斯泰的“右手”(思想家的才能)并不亚于他的“左手”(小说家的天赋)[2]274。既然如此,从现代西方思想史的视域来理解托尔斯泰也许是更为贴近的方式。
“圣愚”:俄国思想中的道德纯真
大多俄国艺术家都迷恋道德纯洁,这一点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和托尔斯泰的《复活》等作品里都表现得特别清晰。按照以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说法,这是刺猬型的一元主义的人生观使然。他比较了法国人和俄国人对艺术家的不同态度。在法国,艺术家的任务是提供作品,他们的私生活不是公众所关心的,而作品的优劣与作者的道德品质无关。在俄国则不然。由于俄国素来有东正教传统,大家都喜欢用宗教道德来评价事物,纯洁往往与高尚联系在一起。道德提升需要不断自省、超拔于世,因此,在常人看来,那些格外执着于道德纯洁的人显得非常“异类”。汤普逊(Thompson,Ewa M.)曾专门考证过俄国文化中的“圣愚”现象。从欧洲医学的角度,所谓“圣愚”不过是一些疯子。但俄国人却把某些出身比较高贵,或者曾经做过神职工作,或者曾经偶然被人发现有所谓“灵异”行为的疯子称为“圣愚”,甚至国家还授予证书,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层。然而到了19世纪,“圣愚”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必须有相当的名声,受人崇仰;另一方面,政府和教会经常会把这样的帽子扣到他们排斥的人身上,而这些人很多都是反对专制、心性纯良的知识分子[3]72-73。我们发现,托尔斯泰特别具备当“圣愚”的条件:既有极大影响力,又坚决反对任何有组织的宗教、国家观念和暴力行为[4]600-605。托尔斯泰本人也乐得落下这样的名声,他的《童年》(1852年)就是最好的证据。这篇小说的第五章的标题即为《圣愚》,里面描写了一个有真实原型的“圣愚”形象。他笔下的“圣愚”住在粗陋的乡间茅屋之中,却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大智慧。他游离于所谓的“正常的生活”和社会极权结构之外,却与俄罗斯的土地血脉相连,受人爱戴。不难看出,这是托尔斯泰的自画像。在英国学者莫德(Maude,A.)的《托尔斯泰传》中,那些半癫的圣徒,构成了托尔斯泰生长环境中的重要部分,当时他们遍布俄罗斯。托尔斯泰在他的回忆录里也作了如下记载:
“格利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在我们家里有很多这样的半癫的圣徒,家里的人教我对他们特别敬重。即使他们当中有些人是不真诚的,或者他们有过意志薄弱和不真诚的时期,可是他们生活的目标,虽然事实上是荒谬的,却非常崇高,因此,我从小就不自觉地学着了解他们的目标的崇高。渴求人世的光荣,是那么有害,而不是那么不可避免,它常常玷污良好的行为,因此我们不得不同情这种不仅是避免赞扬,甚至还会引起轻蔑的努力。我妹妹的教母玛丽亚·格拉西莫芙娜、半白痴的叶夫多基木什卡和在我们家里的一些旁的人,正是这样的人。”[5]27
“圣愚”现象反映了19世纪俄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对精神高贵的普遍崇仰。“托尔斯泰主义”似乎是后人对这种高贵精神内涵的典型总结。它包括“爱一切人”、“勿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等。托尔斯泰觉得自己具有高于所有人的道德评判资格,高尔基甚至戏称托尔斯泰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上帝的兄长”。然而,在世俗社会充满着人的劣根性以及当时俄国的历史背景之下,“托尔斯泰主义”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又不免有道德理想主义的倾向。瞿秋白曾经把《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形容成一个幻想式的哲学家:“彼埃尔命运不佳,精神的力量却很伟大,可惜不能运用,不能对于自己和亲人有所成就或补助。基督教义和现实的恶象之间的矛盾,使他不得不厌恶生活。”[6]44
瞿秋白此语点破了一个事实:对精神的过分注重也必然引来对现世生活的怀疑和距离感。托尔斯泰把他的道德理想主义主要往两个方向延伸开来:政治观和生活方式。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两种非现实的西方社会思潮在俄国特别流行:德国浪漫主义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在托尔斯泰的时代,俄国已经流行起了所谓的“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被人称作民粹主义先驱的赫尔岑始终坚持俄国可能在尚未破坏的、自然的农村公社中得救,即所谓“村社社会主义”。其实,赫尔岑本人也意识到它带有空想性质,因为村社并非个体,同样有可能产生专制。而且,农村村社为什么会成为解救俄国最终的、唯一的道路,为什么这种制度会又会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符合俄国国情的捷径呢?甚至为什么俄国必须走向社会主义?这些本身就与赫尔岑所信仰的多元主义产生冲突。
比赫尔岑更进一步,托尔斯泰提出要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与专制组织,尤其是“国家”。他认为只要存在国家,就存在最大的暴力和滥杀。托尔斯泰也幻想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取得和平和民主。他在1890年10月写成《天国在你的心中》(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这是一部呼吁俄罗斯人民基于基督教教义,不服从、不合作地负起个人的政治责任来反抗沙皇残暴统治的著作。他提出一系列破坏政府的办法,比如不参与一切政治活动、拒绝服兵役和纳税等等。
托尔斯泰的空想社会主义还表现在主张废除私产制。他晚年为了表示自己对下层民众的关心,愿意放弃自己的财产,但是遭到家人的激烈反对。他的妻子甚至到政府部门,请求宣布托尔斯泰为精神病,从而取消他的一切财产支配权[7]31。俄国有强大的贵族社会和专制传统,很大程度上托尔斯泰的想法与世不融,的确可以被当作疯子的异想,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又是地道的“圣愚”。
作为“圣愚”的托尔斯泰一生都在追求最接近自然的生活状态。正是这一点使他与卢梭的思想达成了默契[8]401-425。他曾说:“我读过卢梭所有的作品。我不只是对他非常热情,我还崇拜他。我在十五岁的时候,贴身佩戴了一个有他的肖像的纪念章,以代替东正教的十字架。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地方我都那样熟悉,以至我以为一定是我自己写的了。”[5]56在另一篇论文中,他说:“路德主张从希伯来原文教授《圣经》,而不主张从教会神父的注释教授《圣经》。培根告诫应从大自然研究大自然,而不应从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去研究大自然。卢梭主张按照他自己的理解,从生命本身讲授生命,而不从过去的试验讲授生命。”[5]291
卢梭身上带有强烈的浪漫气息,他厌弃工业文明,提倡回到原始大自然和蒙昧状态中。托尔斯泰也特别喜欢自然和乡村生活,他晚年经常和农民一起劳动。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中激烈批评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托尔斯泰也特别强调社会正义和平等,主张取消私有制。卢梭提倡个人主义,托尔斯泰也关注个人,他认为战争中每个个体所关心的和民族国家所关心的东西其实很不一样,不能用虚假的大历史把“个人”完全掩盖了。卢梭强调自我道德反省、剖析和完善,始终与现世生活保持距离,托尔斯泰同样如此,他追随着卢梭的名著《忏悔录》,写了一部同名自传,并坚持写日记。他的日记非常坦白地记载着内心,包括对妻子和至友的怀疑和抱怨以及人性最卑劣的欲望,这使得负责誊抄他全部作品的妻子经常暗地寒心。托尔斯泰和妻子的最大分歧除了是否保留私产,就是教育问题。1859年革命高潮的时候,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庄园里开办农民子弟学校,鼓励学生顺从天性,想学就学,自由选择学习内容。他还要求他的妻子根据卢梭在《爱弥儿》中的主张来实施对孩子的教育。他希望他的孩子们爱好大自然[5]293。
凡夫:来自“共同世界”的反抗
除了宗教般的道德自律和理想主义,托尔斯泰又表现出极为凡俗的一面,尽管他自己努力掩饰。作为“圣愚”的托尔斯泰关注一元论,始终有自己明确而坚定的价值目标,而作为凡夫的托尔斯泰有很多常人的局限、矛盾,他的精神世界是多元、富有张力的。在伯林的笔下,托尔斯泰其实是一只想做刺猬的狐狸。伯林写道:“托尔斯泰的同时代人马克思坚持在资产阶级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我欺骗’,与马克思不同,托尔斯泰除了保留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外总是从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一切,他的中心论题是,人类生活中存在着一种与自然界规律相同的决定论的规律;但是由于人无法忍受这种过程的无情,所以总是想将之看作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过程,从而追究那些作为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责任,这些当事人被他们称为‘伟大人物’并赋予英雄的美德或恶习。什么是伟大人物?他们也不过是无知的愚蠢的想要为一定的社会生活承担责任的普通人,是一些与其说是认识到在那不顾人们的意志和理想而只追求自身实现的宇宙洪流中他们自己的虚弱无力和无意义的人,不如说是为所有的残酷行为、非正义和以他们的名义出现的灾难而承担责备的个人。”[9]48-49可见,伯林赞成托尔斯泰不对历史做任何硬性的解释,从而有别于启蒙时代的英雄史观。
托尔斯泰有深重的怀疑精神。许多人认为保守、坚持信条才是俄国思想的特点,其实自我否定和狐疑同样也是。这种狐疑可能来自于俄国知识分子深刻的“无根基感”[10]25。托尔斯泰在《忏悔录》草稿中有这样一段:“我记得我在大学里第一次考试的那天,走近黑湖的时候,我祈求上帝使我能考试及格,而在默记教义问答里面的字句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整个的教义问答都是虚伪的。”[10]48
基于对理论和信仰的怀疑,托尔斯泰相信,日常生活中能验证到的结果而非神学或形而上学的解答才是唯一可靠的。于是他乐于打破一切大而无当、对现实漠视不顾的种种理论,尽管他本身又不足以提供一个基础,来对事实做更圆满的通诠。伯林认为,现实的真相与圆满的通诠无法兼得,可能就是“二元论”之根。托尔斯泰强调实实在在地描写客观事物(关于托尔斯泰对事件的人体写生式的细部描绘,另有研究者强调过[1]436-448)。他反对把历史当作社会学来进行解释,而念念不忘地想写历史小说,要写个人和群体的“真实生活”。他最终完成了《战争与和平》,这是部充满了活生生复杂人性的作品,完全颠覆了历史决定论。
相比赫尔岑,伯林对托尔斯泰的态度是既认识到他理论和人格的许多弱点与自相矛盾之处,又很同情和欣赏他骨子里的“狐狸”气质。伯林的多元强调是多种价值的宽容、共存,而托尔斯泰的多元是建立在怀疑所有之上的。托尔斯泰既反对社会主义又痛恨自由主义。也正因为如此,许多托尔斯泰的研究者说他最终走向了“虚无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林称托尔斯泰从不去与任何“真理”正面相照,他最大的天才“在于破坏”[10]91。
对道德纯洁的追求使俄国知识分子一直警惕人格上的多样性、矛盾性和劣根性,这种警惕又使他们中很多人从常人的“共同世界”中剥离出来。但是超脱同样又反过来加深了别尔嘉耶夫强调的“无根基感”。真正的托尔斯泰可能远比伯林的描述更为复杂。舍斯托夫(Lev Shestov)更尖锐地指出了托尔斯泰作为凡夫和狐狸,与那个作为圣愚和刺猬的他相交时形成的痛苦。舍斯托夫认为,托尔斯泰狐狸般的怀疑源于他对生命的恐惧,他最大的弱点就是怕死。托尔斯泰对宗教的信仰,他的怀疑精神和反省、禁欲意识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这个根源[12]79,104。舍斯托夫和伯林的看法很不一致,他认为托尔斯泰的思想源于康德的道德本体论,是逃避此在的无根基的说教。这种道德说教源于托尔斯泰面对生活中的悲剧和苦难时感受到的软弱和绝望。托尔斯泰对死亡的恐惧使他难以承受,他不得不走向宗教,求助于至高的善的观念,以此维护精神的平衡。也正是这种对死亡的恐惧,舍斯托夫强调,使托尔斯泰开始学会平凡和中庸地生活,他确信只有这样的生活能建立起一堵墙,这堵墙哪怕不能永远,至少可以长久地使眼睛避开可怕的疑问(怀疑),从而平静下来。舍斯托夫把托尔斯泰描述成用道德的至高性来粉饰内心和现实危机的人,他的学说似乎也能解释得通托尔斯泰晚年离家出走的行为动机。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把托尔斯泰描绘成精力过于旺盛、始终无法克制情欲的人。他的焦虑并不来源于舍斯托夫所言的对死亡的恐惧、信仰与共同世界之间的矛盾,而是对自身存在无尽欲望且不可能完全克服的无奈[13]152-153。在《谢尔盖神父》中,主人公隐居乡间苦修,抵制住了贵妇的爱情,却经不起妓女的诱惑。相对于宗教,俗世生活永远有变动不居的神秘特性。茨威格并不想对托尔斯泰进行攻击。他只是想解释,托尔斯泰之所以斋戒、翻破了福音书,到处宣传禁欲,晚年生活得像个苦修僧,正因为他认识到自己有不同于常人的欲望,而且对这种失常感到恐惧。
保罗·约翰逊(Johnson,Paul)有些哗众取宠的传记更为极端。他把托尔斯泰看作人格分裂、伪善的人,伟大的外表和渺小的内在同时存在,折磨着他。托尔斯泰一直喜欢“做戏”。他最大的爱好是赌博和酗酒,为此变卖了好多家产,向朋友借钱却有借无还。他声称力图展现人物和事件最真实的一面,但从日记和书信里看出,他的人物完全受他摆布。他对周围人十分冷酷,多次离家出走,等家人疲惫不堪地找来。他两个哥哥重病,其中一个托尔斯泰只在临终前看了一眼却拒绝参加葬礼,另一个干脆不闻不问,对方只好自己跑过来死在他怀里。托尔斯泰夫人提出:托尔斯泰强调的宗教般“爱一切人”是概念的人类还是具体的人?因为他没有真正具体爱过一个人,除了自己。托尔斯泰许多朋友也深受他的伤害。比如屠格涅夫,当他兴致勃勃把费尽心血创作的《父与子》拿给托尔斯泰时,他没看几行就睡着了。有一次两人激烈争吵,屠格涅夫率先道歉,托尔斯泰却得意地说对方惧怕自己。屠格涅夫死前想再通封信,尽管托尔斯泰在对方死前两个月就收到了,却没有任何回应。等人家死了之后,托尔斯泰却在回忆录称颂他[14]32-35,67。
正如托尔斯泰夫人所注意到的,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和真正的友谊,托尔斯泰都不具有。他具有的只是知识分子的习惯,他们写任何文章时都会考虑到将来发表,所以托尔斯泰不会放过任何为自己辩护和做宣传的机会。他在日记中披露:“廖瓦契卡得知我抄他的日记,开始不安起来。他想把他过去的日记都销毁,而只以家长的面目出现于孩子们和广大读者面前。现在他的虚荣心还这么强!”[15]85
约翰逊极具戏讽地描写显然有过于夸大事情的一面,然而托尔斯泰确实比较重视人间享乐,比他的作品多了好几倍烟火气。这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形容他的“波良纳”庄园中可以得到印证[16]59。
结束语
百年来,诸多西方思想家一直努力丰富甚或颠覆以往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托尔斯泰形象:一个“圣愚”、精神之父、俄罗斯的道德导师,一个被宗教执信而折磨得无法感知到真实生活的人。我们现在看到的托尔斯泰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他甚至有着比凡人更多的欲望,有着人性通常具备的一切弱点。
然而,在不同的思想家和传记作者笔下,托尔斯泰被还原的路径及效果却大不相同,这源于不同视角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者们对俄国知识分子及俄国文化的不同感受。比如舍斯托夫,他终生抨击传统形而上学并跟随基督教神学,他坚持的偏见是:“维护圣经真理的自主性,拒斥希腊哲学的理性形而上学,主张不寻求理性证明、也不可能得到理性证明的信仰——圣经的信仰,才是真理的来源。”[17]30-31因此,对于舍斯托夫来说,一切来源于实践与生活(而不是来源于圣经)的对人性的反省、对生命价值复杂性的认识都是屈服于希腊理性及伦理标准的怯懦表现。因为希腊精神本身是源于认识论的,它承认人欲和俗世的平衡原则,并非不证自明的信仰,这与俄罗斯精神中坚韧的宗教自律和道德理想主义差距甚远。所以托尔斯泰在他的眼中,充满生之恐惧与欲之局限。
与舍斯托夫同时代、同被归属于“新精神哲学派”的别尔嘉耶夫,一方面肯定舍斯托夫的存在主义式的哲学,另一方面又尖锐批评他的极端非理性。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没有信仰,也不在于不注重现实,而是在于精神上的“无根基感”。这种概括道出了白银时代俄国思想界的普遍焦虑。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东正教传统与现代理性精神;根深蒂固的贵族专制、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各种思想的争鸣,或者别尔嘉科夫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精神”与“共同世界”(日常俗世生活)的矛盾在托尔斯泰创作和生活中都体现出来。和别尔嘉耶夫接近,梅列日科夫也观察到俄国思想界“两个真理”(基督教的牺牲精神与多神教的追求个性确立)始终折磨着知识分子的心灵。这种矛盾逐渐演化为“天上的真理”与“人间的真理”、灵魂与肉体需求的对立。梅列日科夫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描述托尔斯泰在“波良纳”庄园的生活。
约翰逊和汤普逊,均从英美的经验主义传统中理解托尔斯泰。汤普逊关注到俄国文化中对道德纯洁的狂热追求,这种道德纯洁与俄国广大的乡村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变得天真超脱、愚钝而近乎自虐,这在英美经验式的实用理性背景中是很难理解的。工业文明的兴起以及由此带来的阶级斗争等社会问题,在俄罗斯这个尚未解决一元主义还是多元并存的社会里显得过于前卫。如果说汤普逊在努力贴近俄国传统,约翰逊的理解则过于像小说家式的爆料,脱离了严肃思想史的求索。他的预设是:托尔斯泰既然是俄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标签、社会的良心,他就理应只是个伟大的“圣愚”,怎可有“凡夫”的自私与虚伪?
还是回到伯林,他出生于俄国却游走于西方的特殊文化身份注定了其视角和价值的宽容多元。当人们或想把托尔斯泰树为伟人,或愤愤不平地批判他的所谓“恶行”时,伯林都机智而平和地会心一笑,告诉我们其实不必太在意主人公到底是刺猬还是狐狸,因为这两个概念并不绝对。如果伯林为我们真正提供了某些洞见,恰恰因为他能用类似于心理学的角度去体会思想家本来的精神世界,他对我们的最大启发或许在于:圣人因为不完美,才显得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