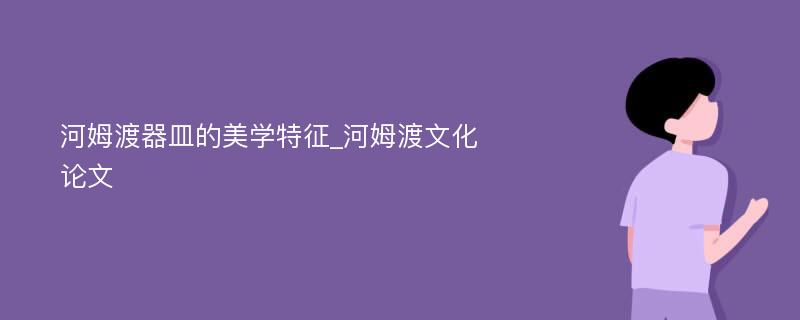
河姆渡器物的审美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器物论文,特征论文,河姆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人,在距今4000到7000年以前,就已经有了较为精细的器物创造。其精湛的雕刻工艺,生动逼真的陶塑,优美的刻划装饰与人体的装饰和佩饰等,创造了辉煌的原始艺术,有力地体现了河姆渡人审美意识的觉醒。① 除了部分的佩饰等是专为审美而创造的以外,绝大多数既是实用对象,又是审美对象,体现了河姆渡人自发的审美意识,在中国远古时代审美意识的发展历程中起着桥梁作用。从器物的创造中,河姆渡人展示了自己的审美趣味和创造力,体现着当时长江流域湖沼地带的自然环境和农耕稻作文化的特点,我们可以从器物的造型和纹饰推测他们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
一、审美创造的生成特点
河姆渡人在器物创造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实用到审美的过程,从中显示出因物制宜的特点,而工具的进步则给他们的审美创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有力地促进了审美意识的深化和发展,并在器物的创造过程中尤其重视观赏者的感受效果。
首先,河姆渡人的器物创造体现了从实用到审美、艺用不分的原则。河姆渡的器物就是他们的艺术品,他们把艺术性的理想表现在实用和装饰品上,反映了当时艺、用不分的特点,是他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写照,同时表明他们已经有了专门的器物生产者和创造者。“从河姆渡艺术本身所反映的情况看,当时已经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萌芽。而这种最初的脑力劳动者,就是创造了精神财富的原始艺术工作者,或称之谓原始艺术专门家。”② 从完全的实用到艺、用不分,并由用而形成独特的审美趣味。如加炭化的植物碎屑制作的黑陶,原先为着防止开裂、提高耐热急变性能和耐用,后来则因物而形成独特的审美趣味与要求。到二期陶器的镂空装饰,则主要是为了审美了。骨器也是因骨制宜,利用骨的自然形态,因骨而赋形,大都在骨尽其用的基础上追求审美的效果。三足陶器的三足本来是受着禽足的启发,为着烧煮的实用目的,由起着固定、稳固作用的支架演变而来,形制的变化中有实用的烙印,后来竟成了一种审美的趣味了,到了三足的陶釜已经很规整,且富于变化。许多器物的造型和纹饰是在日常活动中,不经意间发现的,无论是手拿陶器留下的指纹压印、拍打的绳纹,还是贝壳、稻粒的印迹,都是由不经意间的效果得到启示,再自觉为之的。这些陶器上有的是已干后的刻印,有的则是未干时的压印,它们都是器物成形后装饰在上面的,与后来青铜器固定在模子的纹饰有很大的不同,有着随意性和即兴创造的特征。陶器上的绳纹,也是由制陶工艺中由缠绳的拍子拍打的痕迹,渐渐转化为纹饰的。斧柄等工具的把柄上用两侧排列整齐的斜杠夹成的夹角纹,或加上绳纹,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防滑、增加摩擦,便于手拿,后来渐渐讲究规则和美观,进而也累积为审美创造的经验了。木船浆的柄部所刻画的几何形纹饰,也同样是由防滑实用的需要演化而来。漆的发现和使用,是防腐实用和美观的统一。这些实用与审美的融合,说明这时已经有了自发的审美意识。
其次,工具的进步促进了审美传达能力的发展。工具作为人的器官的延伸,带来了技术上的进步,给器皿的创造带来了质的变化,使艺术的精美程度产生了飞跃。审美理想的深化、审美能力的提高,是一个逐步积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它与人的创造力及其物化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器物的创造过程中,河姆渡人继承了旧石器时代钻孔、染色、磨光和简单刻划等手法,并加以发扬光大。河姆渡器物的纹饰主要靠雕、塑、刻等手法有机协调,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创造能力,特别是其中的划画,如压印、拍印等以及捏塑和堆贴方式,起到装饰性的功能。随着工具的进步,审美趣味也随着创造力的增强而日益深化。河姆渡的陶器已经开始了泥条贴筑和慢轮修整,且常用木拍、鹅卵石压光,用竹木和尖锥具雕刻,使陶器的器型更光滑、更规则,纹饰也更精美。陶器的套接,如分段筑迭、直迭和盘类斜迭等,也因方法的不同而影响到器皿的造型。当时的陶豆已经很规整,从中可以看出轮制的特点。饮食陶器用竹片和卵石等在陶胎上的刮削打磨,使其烧成后会墨黑发亮。玉器也是如此,随着玉料的采掘和加工能力的提高,由征服能力而实现自己的创意,由适应而征服。玉玦中的同心圆孔、玉环中的偏心圆圆孔,不仅证明当时在器物制作上已经有了类似砣机的器械,而且反映了在审美趣味上的多样化。
第三,河姆渡人的器物创造重视欣赏者感受的效果。河姆渡器物的纹饰常常位于器物表面的显眼部位,为的就是便于感受。它们常常位于盘盆敛口的口沿、器座的底座等显眼部位,且常常在不易磨损的地方。与商周以后的有些纹饰为着某些宗教意图,而放在一些不显眼的地方有着根本的区别。一些陶釜侈口边缘的纹饰,充分考虑到俯视的整体效果。一些动物形象,从木器到石器、到象牙骨器等,常常体现了动态的感觉。纺轮的制作也开始注重动态的效果。纺轮上用弦纹、旋转纹,虽然静态效果未必明显,甚至显得零碎,但在旋转时视觉效果好,有的一个点旋转起来就可以变成一道线,有动态的完整性。同时,为着对象审美价值的持久存在,河姆渡人还重视欣赏的久远性,耐用品和固定器物,其纹饰就多而精细,而耗蚀品则很少纹饰,甚至不用纹饰,目的在于利于欣赏,便于流传。
二、审美创造的表现方法
河姆渡人在器物制造的过程中,既体现了实用的要求,又反映了他们的游戏心态,更为精细的工具的使用,使得所创造的器物在实用和美观效果方面都有了提高。审美活动和创造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也在逐步深化中得到升华。
首先是它体现了仿生的特点。河姆渡人已经开始重视通过仿生来进行器物的创造,河姆渡器物的表现形态大都即目所见。这些器物的装饰,常常以人为参照,上重下轻,体现生命意识。如口、颈、肩部装饰精细,腹、底、下沿就相对较差。特别是陶器的装饰,大都在口沿和肩部。敛口器物的创造,甚至受到了男性生殖器官龟头的启发。
生活场景在他们的心灵中深深地打上了烙印,器物表面描写刻画的物象是驯养的家畜及生活环境中非常熟悉的动植物等,以及日常生活中场景的描述,是器物制造者生活情趣的表现,常常还体现着他们的祈望。生活环境中的动、植物形象,影响着他们对器物造型和纹饰的摹拟和创造。作为鱼米之乡的河姆渡,在他们日常的“饭稻羹鱼”生活中,作为主食的稻作和农耕时代的其他植物,猪、狗等家畜,水中的鱼儿,空中的鸟儿都是他们常见、常用的,所见所想,都离不开这些,都启发了他们器物创造的灵感,故加以摹拟和表现,造型优美,栩栩如生,从中体现了仿生的特点。
猪纹陶钵形象介于野猪和家猪之间,猪纹的神态逼真、鬃毛直竖,猪头前伸低垂,两眼圆睁,四足蹒跚,长嘴高腿,野性尚存,好似在寻觅食,笔触流畅,能传神达意,是原始畜牧业的艺术缩影。特别是水稻,从禾叶纹,到稻穗纹,再到谷粒纹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在河姆渡器物的纹饰上占有一定的比例,足见稻谷与南方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在他们生活中有着重要地位。其中,鸟和太阳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对鸟的摹写,说明他们爱鸟、崇鸟,表达了河姆渡先民们对鸟能自由翱翔的好奇与羡慕,是对鸟的礼赞。“双鸟朝阳”中双鸟对太阳的好奇心态,正是人类童年自身心态的表现,有很浓的娱乐成分。由木、石、骨、象牙等材料制作的蝶形器,也反映了他们的即目所见,和对飞蝶美丽与飞动的好奇与羡慕。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已经有了蚕纹。
其次是具象与抽象的统一。纹饰中既有具象的实物摹写,也有抽象的几何形,这是中国古人在观察、描写物象过程中向具象和抽象即几何和写实两个方向发展的基本规律。纹饰的变迁也与摹仿能力、写实能力和创造能力相关。器物的外形也有更多的写实造型,它们古拙而生动,主要有陶猪、陶羊和陶狗等家畜形象和陶鱼等。陶猪的憨态可掬,颇为传神,陶羊以夸张的后臀突显它的肥壮,陶狗则以卧地小憩的静态作为器盖,放在显眼的顶端。陶鱼两鳍竖起若翅,表现其动态的游动、飞跃,表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另有木雕鱼周身阴刻有大小不同的圆状纹,也同样显得形象生动。这些动物器型大都造型优美、栩栩如生。在具象的写实纹中,在写实的鸟、猪等图象中,显示出高度的模仿能力。如猪身上的涡毛或竖鬃,刻画得非常生动。而连体双鸟纹骨匕,其背翼、蹼足,利钩似的喙,炯炯有神的双眼,以及飘逸的羽冠,生动地刻画出了神态逼真的形象。河姆渡的器物中,常常以曲线描摹物象的外形与内在神情,已经是一种抽象了。几何纹饰如骨笄中的几何图案等,更是有相当抽象的成分,反映了人们思维能力的提高。它是由繁到简,由具体到抽象。从简单的压印、拍印纹,到抽象的线条,特别是其中的叶芽纹,开始了有规则的连续和重复,其抽象的装饰能力更加明显,从中也体现了对称和节奏感。
第三是构思的整体性。陶器表面的形象刻绘,如自然界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鱼藻纹、稻穗纹、猪纹、五叶纹陶块,已经初步讲究整体的构图。其构图在重视形式规律的基础上,体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巧妙的构思能力。在形式规律方面,从旧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均匀、规整和光滑等特点,在这时的器物创造上得到了发展,其中尤其重视对称等形式规律。这是由对客观规律的体悟带来的形式规律的自发意识。如在长方形的陶钵上,有一对对称的猪;“双鸟朝阳”以太阳为中心,两鸟左右对称,具有均衡稳定的视觉效果。双鸟对称等首先来自古人对自然法则和生殖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并被运用到构图的形式规律中。这种对称的法则,显示出其整齐、稳重和沉静。河姆渡器物中的许多雕刻图案,都在讲究对称或均衡。陶钵上的纹饰反映了当时人构思的精巧和想象力的丰富,具有浪漫气息。夸张的使用也别具特色,如对变体怪异鸟的创造。骨匕柄上雕刻的连体双鸟纹,因物而赋形,巧妙地借形构图,前后两个小孔作鸟的眼睛,中间稍大孔成为双鸟身体的连接点,并以连接点为对称面,两侧对称,使装饰与实用有机结合。在鱼禾陶盆中,鱼在游动,禾苗在水中静立,动静相合,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陶鱼的两鳍成翅膀状,以管戳成的圆圈为为鳞,表现出游鱼飞翔腾越的动态。浅浮雕以飞、禽、虫、鱼为表现素材,强调其神态和姿势。这些刻绘从描摹、构图及其设计、变异等,乃至器物部位的选择,都显示出当时艺术家的独具匠心。我们现在管中窥豹,从出土器物的一鳞半爪中,可以推测到当时的陶艺工作者的良苦用心和训练有素的技巧。
第四是表意性。河姆渡器物的造型和纹饰已经有了很大的表意性。河姆渡器物上的纹饰,无论是具体写实的,还是抽象表意的,都有了写意的意味。写实之中包含着写意,夸张也是为了写意。禾叶纹也多有写意的成分,并且有了丰富深刻的寓意。少有的彩陶也显示了它的写意性,如尖细的蔓草、浓彩重笔的阔叶,栩栩如生,错落有致。在一些陶塑动物中,为了突出其具有特征性的部位,河姆渡人常常在创造形象时使用夸张和变形等手法,如陶鱼的嘴、双鳍和腹部陶狗昂起的头脖等,以达到传神表意的目的。有的刻有动植物图案的黑陶盆,甚至看上去像是后代的一幅写意画的画面。反过来也可以说,后代的写意画实际上多少是承续了这些器物刻绘所积累的一些探求。这些日常生活场景的描摹,特别是禾叶纹、稻穗纹和猪纹等图案,既是通过描摹读自然的礼赞,也表达了他们对家畜和丰收的祈望。至于一些几何纹饰,除了承载着演化前的实物韵味引发联想外,间接的寓意更为丰富,甚至具有朦胧多义的象征意味。在河姆渡器物中,已经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几何纹饰,说明其有了更多的自觉性,表意性也更强了。
三、独特的南方风格
河姆渡温暖湿润的气候,以及鱼米之乡的生活环境,对器物的造型和纹饰的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那些鱼、鸟、禾苗、稻谷等内容上显示出南方生活的画面,而且在形态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木质朱红色漆碗呈椭圆瓜菱形,敛口,底有略外撇的圈足,这类技术和文物,是仰韶文化所不具备的,对后世碗的造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陶器则因当地的土质和保存环境,决定其陶器的质地和形态风格,其线条也多流动、变化,柔和、轻巧。康育义为此提出,中国南北艺术的差异“就目前认识应当上溯到仰韶和河姆渡”,是非常有见地的。他通过半坡和河姆渡艺术进行比较,指出:“前者喜欢对粗犷直线的追求,表现剽悍豪爽的性格以及对浓烈色调的偏爱,后者喜欢对柔和曲线的追求,不尚色彩,表现出温和潇洒和内含的性格,和对清淡素雅风格的喜爱。”③ 南方文化和南方艺术求精求细的特点,南北艺术的差异,在河姆渡文化时代就有了端倪。
河姆渡南方艺术的风格主要表现为线条明快、图案简洁,器面光滑。与半坡遗址中的彩陶浓墨重彩不同,河姆渡人的陶器中很少见到彩陶,而多黑陶,其装饰相对多白描、素雅,显示出他们在周边自然环境的影响下所形成的情趣,显得含蓄、隽永。河姆渡的玉器大都造型简约、风格质朴,但其工艺的精湛,玉质的精细、典雅、柔和,更能体现出南方器物的温润、阴柔的风格。玉璜、玉管等大都器、表光洁、圆滑。“双鸟朝阳”表现的对象复杂,构图却相对简洁、明快,线条也较娴熟、流畅,这不仅是熟练的表现,而是久而久之所形成的精细、圆润、别致的风格。象牙圆雕鸟形匕上单线阴刻,简洁概括地表现了猛禽的静态特征。
例外的是木质漆碗的朱红色漆类涂料鲜艳夺目,虽然只有孤零零的一只,却让我们看到了朱红色在中国一直流行的源头。如果说,生活在近两万年以前的山顶洞人用赤铁矿染过穿戴、在尸骨旁撒红粉对红色还更多的是动物性的生理反应,那么对红色的重视、并且赋予红色以审美的一味至少从河姆渡人就开始了,后来形成了中华民族用色的传统特点。
纹饰中常常反映出河姆渡人对线条更为重视,色彩则相对较少,但比起色彩更具有表现力,这既有时代的原因,更有地域的原因,南方风格由此发展。对线条的充分感受与传达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特点。李泽厚说:“如果说,对色的审美感受在旧石器的山顶洞人便已开始;那么,对线的审美感受的充分发展则要到新石器制陶时期中。”④ 吴玉贤也说:“河姆渡的艺术作品线条多而色彩少, 表现了一种明显的时代倾向,这是积极的因素,说明了手法上的进步。”⑤ 而河姆渡人对线条更为重视,也更有自己的特色,这就不仅是时代的特征,更有着地域的特点了。与仰韶半坡遗址相比,河姆渡的器型及纹饰早期以直线为主,晚期则更多圆润的曲线。河姆渡的刻画艺术则更多曲线,在生动、传神中体现出南方风格的细腻、柔和、安详等。在陶器的装饰,刻画中,线条艺术别具特色。仰韶半坡遗址的器物多直线、粗硬、多曲折、圭角,粗犷、刚劲。而河姆渡人则在线条中传达着情感,如卷曲线、短线、弧线、圆圈线、波曲线等,使得纹饰的笔触比较流利。
河姆渡器物的造型、纹饰及图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骨匕中的圆心对鸟图案,我们至今在苗族刺绣上还能见到与它惊人相似的图案。其中的鸟和枝叶、花瓣等植物的纹饰,可以看成是中国花鸟画的最初源头。河姆渡色彩缤纷的玉玦、玉璜、玉珠、玉坠等玉器,对后世的玉器造型和纹饰也产生了影响。造型生动、周身阴刻着圆状纹、且刻纹流利的河姆渡木雕鱼,对后世的木雕艺术的影响也尤为深远。
注释:
① 河姆渡遗址材料参见《河姆渡遗址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② 龚若栋:《河姆渡原始艺术的地位和价值》,《民间文艺季刊》1988年第1期。
③ 康育义:《论河姆渡原始艺术的美学特征——兼论中国绘画南北差异之起源》,《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④ 李泽厚:《美的历程》,见《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第35页。
⑤ 吴玉贤:《河姆渡的原始艺术》,《文物》1982年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