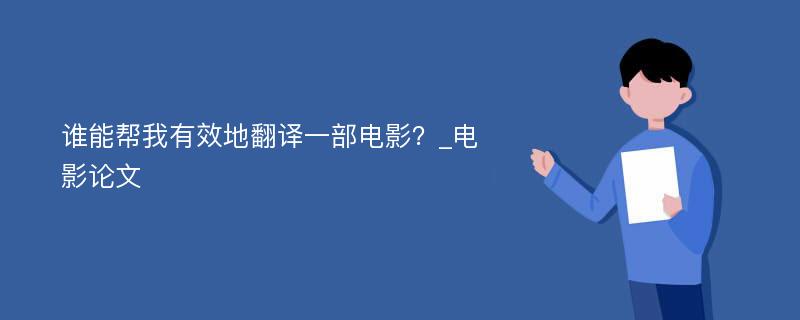
谁能帮我有效解读一部电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帮我论文,谁能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电影理论的普及道路并不畅通,这反映在市场的出版物上。我们看到的电影书多为两种,一种过于高蹈,另一种则过于下流。前者多是学院里的高头讲章,他们缺乏新的感性材料的加入,后者则是多发掘电影人的私生活,电影本身则被贬低为一次传播流言的契机。而报章杂志上的电影评论,也可粗分成两种,一种是主题性评价,就专门总结电影的故事内容;一种是影迷式的评价,文章是“震撼”、“感动”之类词的堆砌物。这样的评论者只敢讲述电影所具有的私人意义,这也许是因为他不敢下一个有公共意义的判断,他们对于电影的形式风格完全缺乏解读的能力。
我为什么看电影?
电影是最能制造流行文本的艺术类型,一个有潜力的流行文本往往能在一段时间内重塑生活的形式。伍迪·艾伦在电影《好莱坞大结局》中说过一句话:生活模仿艺术。这句话在新形式被无限推崇的时代尤为应验。生活的本质是永恒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缺少变化的生活并不使人觉得安稳、愉快,而是觉得沮丧。新时代的人需要新电影,新电影往往是开发生活新感受力的先锋。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被流行文化建筑起来的,这其中包括物质性的,也包括非物质性的。我们接触到的许多商品,价格里文化性占有一定比例,如果我们不能体会到其中的文化秘密,就不能让物尽其用,而不能发现文化秘密的人走在大街上,有时候会面临一种枯竭和惊慌之感,这条街的装饰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变迁。
非物质性的存在,比如语言,我们每天与身边的人进行话语交流,许多词汇来自于流行文本,一句香港电影的台词有时候只是增加生活中的噱头,但往往也颇具洞见,有益于心智的启发。而电影更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力量,这种力量有点类似于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全国人民都被它联系着,大众文化观念被它进行着一种统一化的塑造。电影目前也许不会具有那么大的凝聚力,但是我们会在办公室里一起评说前天观看的《无极》,这部电影也许只是华丽的垃圾,但是人们找到了共同的话题。如果你没看过,你就不能获得交流的乐趣,你就不能进入交流场,你就在这场谈话中被边缘化了。
我并不是危言耸听以此要挟别人重视电影,我也厌烦这些潮流的追赶者,我在此只是陈述现实之一种。试想我们身边是不是有很多人争先恐后地去看一场电影,仅仅因为它被太多的人提起?如果你是一个有着强大精神力量的人,你就不会这样做,因为你自身就是一片坚固而自足的大陆。我们无法希望所有人都能这样精英化地对待电影这种流行文化,也不敢要求别人一定在电影欣赏中得到一种伦理的规范和灵魂的升华,但我们至少希望自己在文化上有自己的选择能力,他在电影中看出了热闹,也看出了门道,他能够获得更深邃更全面的快感。
以前中国的电影市场是计划经济的,自上而下的灌输带来强制性的繁荣。而今电影的局部市场化,加上获得电影碟片渠道的“畅通”,电影又以DVD的形式逐步走入人们生活,人们与电影的接触形式,已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是民间化力量的自行审查与吸收,所以一种健康品位的形成,一种电影市场的健康循环,就有了实现的可能。
看电影需要指导吗?
电影忽然与我们的关系紧密起来,虽然国产片目前远算不上繁荣。我们如何建立电影的关系?我们能够阅读电影像阅读一部小说那样吗?对于文字的阅读,我们一般不会感到紧张,我们与文字有着一种简单平易的关系,但我们看电影就可能会紧张,觉得没有把握感,这与电影特殊的材质和创造手段有关。
虽说就是学龄前的孩子睁开眼睛就可看电影,但我相信更多的,他是在看单个画面,而无法在画面之流中组织出电影的深层意义。德国导演文德斯希望自己制造一种简单的张开眼睛就可以看的电影,但是他的电影却并不比别人的电影好懂。我知道,电影的实现在最初主要还是依靠人类的本能,我们也许不需要训练,或者只需要对以前艺术形式比如戏剧的既有涵养,就能够不仅仅可看单个画面,也能看懂剪辑组织的蒙太奇。导演帕索里尼说:“如今通过诗歌和哲学进行的交流已臻完善,但作为电影语言的基础的视觉交流却非常原始,需要依赖本能。”他说这话已经是几十年前了。如今的电影正是在这些导演的努力下,一些电影已高度“文明化”,或者说有的电影过度符码化了。这也许对于电影成为一个强大的艺术形式有帮助,但也为难了一些懵懂的观众,如何破解电影暗语,几乎成就了一门解读的产业。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电影有时被特权化了。比如导演蔡明亮的电影几乎每个片子都有四处漏水的场景,台湾的大学的教授解读说,这水代表着欲望的意思。水与欲望的联系,中间真的需要几道环节,没有受到训练的观众也许很难看到其中关联。不仅如此,在无法逃脱的后现代的文化状况里,电影越来越“互文”化了。比如美国导演贾木许的《天堂陌影》,里面出现对流行文化的众多戏仿,不熟悉美国文化的中国观众往往难以充分解读。《情癫大圣》里当唐僧说:“曾经有一份爱摆在我面前……”孙悟空说:“不要说了,这句话大家都会背了”。如果此前没看刘镇伟的《大话西游》,几乎就体会不到其中幽默。郝建曾对此引用了一个前卫艺术里的词语叫“完熟”,即对流行文化现象的烂熟于胸,不如此,后现代文化就无法完成循环。
电影技术推动电影艺术,这一点电影与任何艺术类型不同,它是工业化的产物。电影的创造过程也是所有艺术类型中最社会化的。它不像文字的写作那样自然或本能,所以电影创作过程里,自觉意识是最明晰、最强烈的,而文艺作品中最可贵的无意识力量是最难在电影中被发掘出来的,电影作品的作者论至今还有人怀疑,因为一部电影的署名权往往不是被一个人独有,制片人、导演、编剧也许都可以是主要作者。由于电影创作的社会化程度以及人造痕迹过于强烈,所以电影携带着混杂的意识形态,同时有着强烈的约定性。这种约定性就像一种编码,你要解码就需要懂得编码的程序。电影是视觉流,其流淌是有速度和时限的,因此它对人的侵犯性最强,电影里的技术手段也携带着强烈的观点性,例如机位、摄影机运动与观众的身份塑造存在着某种关系。因此,电影是一种魔术与游戏,要想有质量地参与这游戏最好要了解电影的本体论与电影的文化内涵,然后我们才能在观看时占取有益的位置以建构自我的主体。
让理论有效,让理论照亮作品
艺术创作者多反感理论的侵扰,也有论者认为,电影的学问化乃是电影观众的灾难。因为理论是反娱乐的,而电影是生活的一个余数,是承担休闲的功能的。这种担心并无道理,因为一部好的电影总是能提供不同的解读空间。浅显者看得浅显,深刻者看得深刻,好的电影总能揭示繁多的层次感。大卫·波德菲尔认为电影理论其实只是借鉴了其他艺术理论,自己的创新性不足。这是在呼吁体现电影个性的理论,当然非常好,但同样,其他艺术理论在电影里的应用也可以继续发扬,只要它有助于智性发展,能够开启观众的领悟力。
有一位作家朋友告诉我,说他看国外的电影看不懂,跟不上节奏,里面的人走来走去,而这位朋友却无法看到它们之间的前后关系。我相信这现象一定很普遍。目前电影理论的普及道路并不畅通,这反映在市场的出版物上。我们看到的电影书多为两种,一种过于高蹈,另一种则过于下流。前者多是学院里的高头讲章,他们缺乏新的感性材料的加入,后者则是多发掘电影人的私生活,以迎合多年来因信息不足而出现的强烈窥视欲,电影本身则被贬低为一次传播流言的契机。
而报章杂志上的电影评论,也可粗略分成两种,一种是主题性评价,就专门总结电影的故事内容,而忽略其他;一种是影迷式的评价,文章是“震撼”、“感动”之类词的堆砌物。这种评论不仅在网上传播,还结集出版,他们主要把看电影当作一种优雅品位的象征。“那天我在影院看《千里走单骑》,手里拿玉米花,外边下着雪,我正在失恋中……”这样的评论者只敢讲述电影所具有的私人意义,这也许是因为他不敢下一个有公共意义的判断,他对于电影的形式风格完全缺乏解读的能力。
当然上面所叙述的解读方式也并无不妥,我们提倡多种方式的阅读,只是如果这类解读方式占的比例过大,就暴露了我们与电影的隔膜。苏珊·桑塔格多年前在写她那篇著名的《反对阐释》的时候,主要以电影文本为例进行发挥的,认为对于文本的无限阐释将增加这个文本泛滥时代的负担,且阐释是对文本的贬抑,是为文本制造一个替代品,因此她提出了一种“艺术的色情学”。她说,批评的功能不是要指出“艺术作品意味什么”,而要说它“本来是什么”。“艺术的色情学”提倡消解深度模式,只在乎文本的形式快感,这样做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注意电影艺术的独特形式,发掘电影的独特魅力。但是桑塔格同时反对电影的“思想性”解读,这却完全没有必要。快乐的形式有很多,有感官的快乐,也有思想的快乐,而后者往往是更深沉持久的快乐,如果艺术文本提供了思想的契机,我们为什么一定将之抛弃?
而只提倡注重文本自身,注重揭发电影文本的秘密,其实有一种本质主义的嫌疑,那就是认为有一个确定的“文本自身”这种东西,认为文本乃一个固定不变的事物,它不能跟随观众主体的变化而流动,这就忽略了观众主体在电影循环中的建设能力。阐释者有时候在解读过程中投入自己的经验,选择了对自己有效的视角,如果这个解读很深刻,强化了自己的运思能力,那么这也是一件好事情,而这其中所体现的,同样是电影的能量和潜力。
所以理论不是贬低感官,而是开发感官,还与启迪智慧并重,理论是让我们全面获得电影的快感,因此目前理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最需要的不是一般理论,而更是理论的实践和落实,是要理论把具体电影的感性材料照亮。现在有些地方的中学生都在参加影评培训班,专门学习写影评,如同以前的美术培训班一样,这一现象说明了电影与我们的关系在加深。影像在我们身边晃动,如果我们无法主动把握它,就将感到社会的异化力量。如今在电影作品与电影观众之间,尚有一片巨大的空虚,这空虚之处的填塞和充实,将带来心灵的润泽和文化的富足,因此我们该努力促进这一事业。
标签: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