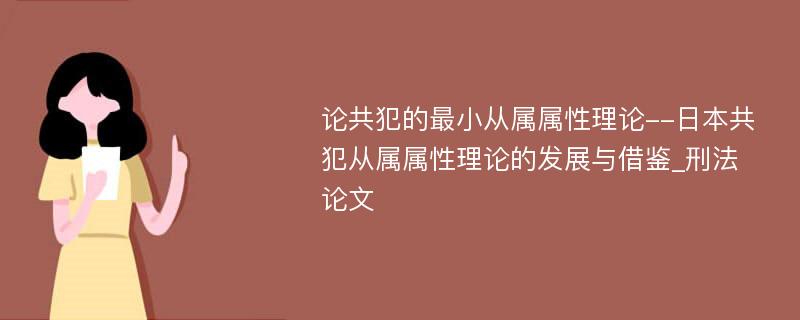
论共犯的最小从属性说——日本共犯从属性理论的发展与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从属性论文,共犯论文,日本论文,最小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共犯的性质,大陆法系国家一度存在独立性说与从属性说之间的对立,但随着主观主义刑法理论的衰退,从属性说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①但从属性说内部也有纷争,主要是关于从属性的实质内容,尤其是要素从属性的内涵。要素从属性又称共犯的从属性程度,是指要成立共犯,正犯行为必须具备犯罪成立要件中的哪些要素。对此,德国刑法学家M.E.迈耶(1875~1923)总结出夸张从属形式、极端从属形式、限制从属形式、最小从属形式等四种从属形式。当今的德日刑法理论通说采取限制从属形式,主张限制从属性说,认为要成立共犯,正犯行为虽无需具有有责性,但须同时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但随着日本刑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共犯的从属性问题上,最小从属性说的影响日益扩大,该说采取最小从属形式,主张作为共犯的成立前提,正犯行为只要符合构成要件即可,既无需有责性也无需违法性。而我国学者对共犯问题的研究大都忽视了这一点,这既导致在共犯一些理论问题上产生矛盾,也不利于指导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相关问题。
一、限制从属性说在日本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日本刑法》第61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科以正犯之刑。”极端从属性说以此为根据,提出所谓“犯罪”正是指该当于构成要件、违法且有责的行为,因而要成立教唆犯,正犯就必须同时具备这三个要件。该说受到学界的诸多批判:第一,按照其观点,凡通过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均只能作为间接正犯来处理,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利用具有规范意识的未成年人的行为并非间接正犯,应构成教唆犯;②第二,第61条并非决定性根据,具体而言,第38条规定,“没有犯罪故意的行为,不处罚,但法律另有特别规定的,不在此限”,对此,一般认为,该条之“犯罪”是指仅该当于构成要件的行为,而并不一定是指该当于构成要件的违法且有责的行为,同样,第61条中的“犯罪”并无理解为有责性行为的必然性,也可认为是该当于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③第三,该说的最大弊端在于有违近代刑法的个人责任原则,根据该原则,各行为人的责任应基于其本身固有的情况独立判断,共犯不应从属于正犯的有责性。为此,极端从属性说逐渐为限制从属性说所取代。
限制从属性说之所以要求正犯既符合构成要件还必须具有违法性,其最大理由在于:对于参与他人的合法行为的共犯并无处罚之必要。例如,在甲出于杀害乙的目的而向乙袭来之时,丙催促浑然不知的乙说,“甲来杀你了,快杀了他!”,感受到生命危险的乙为保护自身安全转而杀死了甲,大塚仁就此指出,既然乙的行为作为正当防卫可阻却违法性,劝说乙杀害甲的丙的行为也自然缺乏违法性,因而针对缺乏违法性的行为并不存在教唆犯与从犯。④对此,木村光江认为,在此种情形下,正犯的违法阻却事由虽然形式上不能及于教唆犯,但若对教唆犯的当罚性作实质性考察,则不得不说,将刑法中并不能归责于正犯的结果归责于共犯,这并不合适。⑤山口厚则从另一视角提出,正犯是“第一性的责任类型”,而共犯是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的“第二性的责任类型”,只要不能认定作为“第一性的责任类型”的正犯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就并未发生需要刑法介入并予以禁止的事态。因而要成立作为“第二性的责任类型”的共犯,正犯还必须具有违法性。⑥
随着违法的相对性理论的提出,不少学者开始对限制从属性说的理论基础,即“违法连带作用、责任个别作用”这一原则提出质疑,并进而主张最小从属性说。以此为契机,围绕限制从属性说的当否这一问题的争论也逐渐活跃起来。平野龙一率先于上世纪80年代对此提出质疑,相继得到前田雅英、佐伯仁志等学者的支持。如平野龙一指出,若正犯的行为与结果均不违法,共犯亦无须对此承担罪责,限制从属性说的观点原则上是正确的,但也不能排斥正犯行为合法而共犯行为违法这种例外。例如,假定构成正当防卫以存在防卫的意思为必要,若正犯具有防卫意思而共犯并无此意思,就属于例外情形。因此,严格地说,共犯只从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该当行为,至于是否违法应个别探讨,故最小从属性说最为合适。⑦前田雅英支持最小从属性说的理由在于:委托他人杀害自己者并不具有同意杀人罪(日本刑法第202条)的违法性、命令刑事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也并非一定构成共犯。⑧佐伯仁志也主张,有无违法性阻却事由,应遵循该事由本身的旨趣,就各行为人个别判断,也会出现虽然正犯阻却了违法性而共犯依然可罚的情形,因而在共犯成立要件这一意义上,以最小从属性说最为合适。⑨上述学者是立足于结果无价值论主张最小从属性说,而大谷实则以违法二元论作为其理论根据事实上也采取此说。大谷实认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通过正犯的实行行为而间接地惹起了法益侵害或侵害危险,因而共犯的成立要件在于:正犯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其实行行为惹起了法益侵害或侵害危险,而并不一定需要正犯具有违法性。⑩
近年来,面对上述质疑,限制从属性说内部也开始出现松动与分化。具体而言,该说不再一味坚持“正犯合法则共犯合法,正犯违法则共犯违法”,而是普遍认为,“正犯违法并不能直接导致共犯违法”,(11)违法的连带性仅具有“正犯不违法,则不成立共犯”这一消极性意义。如有学者提出,“这里所谓限制从属性说,是认为要成立共犯,正犯的行为必须该当于构成要件且具有违法性,而不以有责为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正犯的行为该当于构成要件且具有违法性,便总能成立共犯。在此意义上,正犯的行为该当于构成要件且具有违法性,这虽是共犯成立的必要条件,却并非充分条件”;(12)再如有学者认为,“肯定违法的连带性,并非一定否定违法性阻却事由的个别性”,“即便正犯的违法连带地作用于共犯,也尚未达到完全确定共犯的违法性而不允许存在共犯行为正当化的程度。”(13)
二、最小从属性说与限制从属性说的主要争论
如上所述,限制从属性说虽属于德日刑法学通说,但其本身仍存在诸多问题。归根结底,该说与最小从属性说之间的争议焦点在于是否承认违法的相对性。违法的相对性是指正犯与共犯之间的违法性评价可否不必一致:是否存在正犯违法而共犯合法、正犯合法而共犯违法的情形。这是对“违法连带作用、责任个别作用”这一原则的质疑,既涉及对共犯从属性本质的认识,更涉及对违法性本质的认识。最小从属性说的核心也正在于不仅肯定责任的个别化,也肯定违法的相对性。也就是,不仅应个别判断正犯与共犯的责任,还应分别判断其违法性,因而作为共犯的成立前提,正犯的实行行为只要符合构成要件即可,而不必一定要具有违法性。
首先,我们探讨共犯的从属性,首要问题在于弄清共犯究竟从属于正犯的哪一部分。现在,无论是犯罪共同说还是行为共同说,均基本认为在构成要件相互重合的范围之内成立共犯,也均要求是构成要件行为的共同。(14)显然,构成要件行为只能是实行行为,无论采取何种从属形式,其前提均在于正犯实施了实行行为。因为,所谓该当于构成要件,无非是指实行行为该当于构成要件,所谓违法性,也无非是指实行行为具有违法性。因此,共犯最终从属的是正犯的实行行为,没有正犯的实行行为即无共犯,至于正犯是否必须具有违法性则属于下一理论层次的问题。这也是共犯从属性说的根本之所在。
其次,有关违法性的本质,一度存在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之间的对立。行为无价值强调行为本身之恶,认为违法性是指行为本身的违法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一般称之为行为无价值一元论;结果无价值则强调结果之恶,认为违法性的实质在于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行为无价值一元论割裂了与结果无价值之间的联系,片面强调行为人的主观性,“会陷入心情刑法而有违罪刑法定主义的精神”,因而在日本已无人支持,学者多主张违法二元论。(15)违法二元论认为,违法性的本质虽首先在于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但仅此尚不能准确评价违法性,应在此基础上同时考虑行为无价值,强调不可避免地会对行为的违法性产生影响的主观违法要素。因此,现在主要是违法二元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对立。(16)笔者赞同前者,认为违法性的本质在于“违反国家性、社会性伦理规范,给法益以侵害或威胁。”(17)理由有二:第一,“结果无价值论致力于将违法性的概念客观化,但过于拘泥于此,而有忽视对事态的朴素认识之嫌。例如,就故意杀人行为与过失致死行为而言,在结果无价值论看来,二者在侵害被害人的生命这一点上理应毫无差别,这明显有违我们的法律情感”,(18)并不能准确揭示违法性的实质;第二,无论日本刑法还是我国刑法,对未遂犯(障碍未遂)均采取得减主义,可与既遂犯作相同处罚。由此可见,未遂犯之所以值得与既遂犯作相同处罚,是因为行为人的实行行为在危害性方面有时具有等价性,也会产生与既遂相匹敌的危险(行为无价值),而绝非仅在于是否已发生法益侵害结果(结果无价值)。
违法二元论承认主观违法要素,认为违法的相对性是违法性的固有属性,而主观要素又为各个共犯本身所固有,理应可独立于正犯个别具体地评价共犯的违法性。因此,是否阻却违法,应以该行为人的具体情况为基础,权衡各种相互对立的利益,个别地、实质性地判断违法性的有无及其程度。(19)这一点在行为人有意创造出“利益纠葛状态”之时体现得尤为突出。以正当防卫为例:在X教唆Y去杀Z,同时又教唆并不知情的Z利用正当防卫杀死Y之时,因Z具有防卫的意思可构成正当防卫阻却违法性,而X并无防卫意思不能构成正当防卫,其行为并不因Z不具有违法性而随之丧失违法性,因而正犯合法并不必然带动共犯合法。反之,正犯违法也并不必然导致共犯违法。同样以正当防卫为例:甲发现乙意欲杀丙,且正持刀扑向丙,为保护丙的生命安全,甲教唆丙杀乙,但丙在并无防卫意思的情况下(正好也要去杀乙)杀死了乙,构成偶然防卫。在此案中,丙的行为尽管客观上起到了正当防卫的效果,但并无防卫的意思,其行为当然具有违法性,而丙的违法性显然并不能连带作用于甲,并不能由此认定甲构成杀人罪的教唆犯。因为,甲虽客观参与了丙的犯罪行为,但就其实质而言,甲的行为仍属于“面对急迫不正的侵害,为了防卫自己或者他人的权利,而不得以实施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因而并不具有违法性。由此可见,违法性及其阻却事由均具有相对性,成立共犯也就并非一定以正犯的违法性为要件,因而并非不可采取最小从属性说。
不过,限制从属性说学者也对最小从属性说提出了批判:若成立共犯并不要求正犯具有违法性,则教唆医师实施正当外科手术行为、教唆家长对子女实施正当惩戒行为的也应构成教唆犯,这显然不合常理,(20)“只会不当地扩大共犯的处罚范围”(21)。然而,在笔者看来,根据最小从属性说,医师的外科手术行为、家长的惩戒行为在“形式上”已经伤害到患者、子女,已属于实行行为,只是因属于正当职务行为、具有社会相当性而才“实质上”阻却违法性;同样,也应单独评价教唆人的教唆行为,通过认定其具有社会相当性而阻却违法性,并非一定构成教唆“犯”,最终结论与限制从属性说并无不同,因而这种批判并不能成为采取最小从属性说的障碍。
尽管限制从属性说与最小从属性说就此问题的结论并无不同,但并不能由此忽视二者的根本区别:是否承认“利用合法行为的违法共犯行为”?限制从属性说虽肯定存在“利用合法行为的违法行为”,但并不承认“利用合法行为的违法共犯行为”;而最小从属性说对此持肯定态度。其间差异具体体现在如何处理利用他人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问题上。对此,限制从属性说以“能认定利用者自身存在直接的规范违反”(22)为由,多认为应构成间接正犯,相反,正如后述,最小从属性说则认为可构成教唆犯。
三、我国刑法学应当坚持共犯的最小从属性说
那么,我国刑法就从属性理论的研究现状如何呢?我国刑法学界虽普遍肯定共犯从属性说,但在实际判断是否成立共犯之时,往往只是以相关通说观点为其理论根据,而鲜有学者结合我国刑法规定深层次地探究要素从属性问题,而忽视了对共犯究竟从属于正犯的哪一部分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探讨,(23)其结果就是不可避免地给理论与司法实务带来后述诸多问题。因为,共犯行为本身并非实行行为,只有通过正犯的实行行为才能实际引发法益侵害的客观性现实性危险,作为共犯的成立要件,正犯行为必须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中的那些要素这一问题更是直接决定共犯成立与否及其成立范围。具体而言,我国《刑法》第29条第1款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是教唆犯,对此,我国通说认为,该款中所谓“犯罪”,就是符合所有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且教唆的对象限于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24)另外,就刑法第25条规定的共同犯罪概念,我国通说认为,共同犯罪的成立以各共犯均符合犯罪构成为前提。(25)这与日本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极端从属性说的观点是一致的。尽管尚无学者正面提出我国采取的是何种从属形式,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国可以回避此问题,按照上述通说观点,正犯就一定是具有违法性、有责性的犯罪人,这无疑就是承认极端从属性说。事实上,不少学者提倡处罚的从属性,(26)正是该说的具体体现。
日本与我国一样采取二元论的共犯体系,《日本刑法》第61条就教唆犯概念的规定也与我国并无实质性不同,且未以立法形式解决采取何种从属形式的问题,仍有赖于刑法理论来确立,因而,其从属性理论理应对研究我国的共犯性质具有借鉴意义。但从上面对日本的从属性理论的阐述中不难看出,就此问题,日本也曾经历过与我国理论现状相同的研究阶段,我国是否有必要再重复日本刑法理论已经走过的老路呢?显然,借鉴其最新理论成果对研究我国的共犯性质问题,发展我国的共犯理论更有意义。笔者认为,忽视对要素从属性的研究,只是简单地依据我国相关通说观点就共犯的性质采取极端从属性说,不仅会造成共犯理论上的混乱,也无法合理解决我国司法实际中的相关问题。
其一,采取极端从属性说会造成且已经造成共犯理论上的矛盾与混乱。
首先,我国虽对帮助犯采取从属性说,但对教唆犯性质仍存争议,以“二重性说”为通说。(27)在我国已例外规定正犯行为本身不具有刑事可罚性的引诱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刑法》第 359条)、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刑法》第353条)等独立教唆罪的立法现状之下,一方面采取极端从属性说,主张处罚的从属性甚至“犯罪性质从属”(28),一边又认为教唆犯具有二重性,第 29条第2款规定的是独立教唆犯,这之间显然潜藏着理论上的冲突。
其次,极端从属性说认为要成立共犯,正犯必须具有有责性,这有悖于近代刑法的个人责任原则。刑事责任是就违法行为而针对行为人本人的法律谴责,取决于行为人自身的生理、心理状态,即便以同样的违法结果为基础,对共犯的法律谴责的有无及其程度也各不相同。而且,同样是教唆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犯罪,我国通说认为,若所教唆之罪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八种犯罪,应作为教唆犯从重处罚,若不属于这八种犯罪均构成间接正犯。(29)之所以有此差别,其理由显然不在于被教唆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因为就同一被教唆人而言,我们不能说,被教唆人犯“八种罪”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犯“八种罪”之外的任何罪时则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更多的是基于第17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与刑事政策的考虑。极端从属性说对此难以做出合理解释,因此,是否有必要将正犯的有责性也作为共犯成立要件,对此有必要重新审视。
再者,正如前述,我国之所以只能采取极端从属性说,其主要根据在于第29条第1款的“教唆他人犯罪的”中的“犯罪”这一用语。对此,我们是否只能着眼于“教唆‘他人犯罪’的”文义理解,而不能着眼于“‘教唆他人’犯罪的”文义理解呢?作为一种理论探索,若可以着眼于“‘教唆他人’犯罪的”,即认为教唆犯的核心在于“教唆他人”而非“他人犯罪”,则更无必要采取极端从属性说。
其二,极端从属性说否定违法的相对性,不符合我国的司法实际。
就违法性问题,我国更多的是研究违法性的认识,而鲜有学者探讨违法的相对性。但事实上,我国司法实践并未一概否定违法的相对性,这在以下几点中可得到具体体现。第一,“陷阱搜查”即可说明违法的相对性。例如,警察A隐瞒其身份诱使毒贩B向其出售毒品,虽然B构成贩卖毒品罪(《刑法》第347条),但若A是出于犯罪搜查之必须,并履行法定程序且手段具有相当性,当然应认定该行为属于正当的职务行为而阻却违法性。第二,部分对向犯中的共犯行为不可罚的理论根据正在于违法的相对性。例如,第364条的传播淫秽物品罪并不处罚传播对象,也就是,虽认为传播者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但并未籍此认定传播对象的行为也具有违法性,构成帮助犯甚至教唆犯。第三,法益主体要求对方杀害或伤害自己的行为不可罚,其理论根据也在于此。例如,甲试图自杀,但自己不敢下手,转而委托朋友乙杀死自己,乙实施了杀害甲的行为,但未能成功归于未遂。无疑,乙的行为仍构成杀人未遂罪。若一概否定违法的相对性,认为甲也得构成杀人未遂罪的教唆,这显然不合适。因为甲是法益主体,对其自身而言,并未造成侵害结果或侵害危险。第四,若否定违法的相对性,便无法就共犯的脱离问题展开研究,因为只要剩下的共犯完成了犯罪,脱离人就应连带地具有违法性须就既遂承担罪责;进一步而言,若机械地坚持违法的连带作用,在共犯的场合,更无法解释中止行为的一身专属性,因为,中止人基于自己的意思中止犯罪之时,其主观违法性虽得以减少,但其主观要素仅对其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强弱产生影响,并不能就此说,整个共犯现象的违法性也随之必然减少,也就是,并不必然连带地减少其他共犯行为的违法性。第五,在处理有关共犯与身份的问题之时,就同一犯罪行为,因主体身份不同而分别定罪量刑,就正是从另一层面对违法的相对性的肯定。
其三,采取极端从属性说无法合理解决司法实际中的相关问题。
例如,A教唆15周岁的未成年人B实施盗窃,我国通说认为应成立间接正犯。在此,首先有必要厘清间接正犯成立与否与要素从属性之间的关系。从结果上看,似乎二者密切相关:共犯对正犯的从属程度越小,教唆犯的成立范围越广;从属程度越大,间接正犯的成立范围越广。然而,笔者以为,对结果承担第一性罪责的原本是正犯,共犯只是作为处罚扩张事由承担第二性的罪责,因而在数人一同参与犯罪之时,首先应探讨是否成立包括间接正犯在内的正犯,只有在不成立正犯之时才可退而探讨是否成立共犯,而要素从属性完全是有关共犯成立要件的问题,二者本属于不同理论层面。事实上,在正犯行为缺乏有责性之时,限制从属性说或最小从属性说只是认为也可成立共犯,并不必然排斥间接正犯的成立;反之,极端从属性说则认为只能成立间接正犯,并无成立共犯的余地。因此,在本案中,即便坚持A应成立间接正犯,也并非采取极端从属性说所至。
但笔者仍以为,对此一律认定成立间接正犯,不无过度扩大间接正犯的成立范围,有违其理论旨趣之嫌。因为,B显然已具有规范意识,至少具有“盗窃犯法”这一朴素的法律情感,不能否定其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只是基于《刑法》第17条第1款的规定而不予处罚,因而A完全有可能与B形成共犯关系,并不一定成立间接正犯。
同样,就利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行为的情形,即教唆人故意创造出“利益纠葛状态”的情形,与极端从属说的观点一致,我国通说认为也应构成间接正犯。(30)
对此,笔者赞同最小从属说的观点,主张构成教唆犯。理由在于:第一,既然我国也不能一概否定违法的相对性,正犯合法并不必然导致共犯合法,那么,在正犯行为合法的情形下,认定具有违法性的教唆人构成教唆犯,这在理论上也并非全然不可行;第二,教唆他人实施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行为时,尽管正犯可阻却违法性,但其实行行为仍产生了侵害法益的结果,教唆人应从属于此实行行为,原则上仍应构成教唆犯,至于是否值得处罚,则另当别论;第三,运用教唆犯这一“法律概念”即可解决此类问题,本无需适用间接正犯这一“学理概念”;第四,利用人是出于教唆的意思实施利用行为,并无亲自实施犯罪这一正犯意思,若将此类行为一律认定为间接正犯,无疑是将本可认定为教唆犯的行为也认定为正犯,既难言符合间接正犯的成立要件,也不无扩大正犯成立范围、置被告人于不利益之虞,如此,也有违“存疑从无”这一刑事审判的“金科铁律”。
进一步而言,若按照极端从属性的观点,以利用人的行为作为间接正犯实行的着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未遂犯的处罚时点过早这一问题。如在上例中,A命令B盗取C放在身边的提包,但 B中途被同学叫住而未执行命令,对此,若认定A构成盗窃未遂的间接正犯,这不仅有悖未遂的处罚根据(尚未发生C的提包马上就要被盗这一现实性客观性危险),其结论也与共犯独立性说并无不同。相反,若按照限制从属性说或最小从属性说的观点,限定解释第29条第2款,则A属于教唆的未遂,并不具有可罚性,这样处理无疑更为合理。并且,若A并非教唆而是帮助B实施盗窃,极端从属性说只能认为不构成犯罪或者极其“勉强地”认定A构成间接正犯,这显然不如限制从属性说或最小从属性说直接将A认定为帮助犯这一结论更为合理。
总之,是否构成间接正犯,不能仅以对方是否具有违法性、是否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为根据,这取决于对间接正犯性质的理解,应该基于间接正犯自身的理论来判断,而与采取何种从属形式并无直接联系。
为此,笔者提倡我国刑法学有必要从极端从属性说转向最小从属性说。
我国采取最小从属性说的最大难点在于:通说认为,共同犯罪应该是所有共犯均构成犯罪。因为,按照此说,本不应存在正犯合法而共犯违法、正犯违法而共犯合法的情形,利用他人的合法行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均应构成间接正犯。此问题既事关对共同犯罪概念的认识,也涉及到我国与德日等国在犯罪论体系上的差异,笔者在此无意探究我国犯罪论体系是否必须重构的问题,只是认为完全排斥对要素从属性的研究似乎并非科学的态度。
其一,德日刑法虽未就“共同犯罪”概念作出明文规定,但与我国刑法第25条的差别仅在于是否将共同犯罪明文限定于“故意犯罪”,但仅此并不能成为我国探讨要素从属性的桎梏。事实上,就如何处理通过教唆他人实施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行为而实现犯罪或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这一问题,其间差异主要源于对共同犯罪以及教唆犯概念中“犯罪”的含义的不同理解,实质上仍取决于如何把握共犯从属性的内涵即是否认可违法的相对性。具体而言,其差异在于:如日本早期刑法理论那样,采取极端从属性说,要求被教唆人的“犯罪”必须符合构成要件且具有违法性与有责性,即完全符合我国的犯罪构成要件,对上述行为原则上作为间接正犯处理;如德国现行刑法第26、27条以及当今日本通说那样,采取限制从属性说,被教唆人的“犯罪”不必具有有责性,一般作为间接正犯处理,但对教唆具有规范意思的刑事未成年人的可作为教唆犯处理;采取最小从属性说,只要求符合基本构成要件即可,原则上作为教唆犯处理,但对教唆不具有规范意思的刑事未成年人的行为可作为间接正犯处理。
其二,如一般采取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这种“三段论式”的德日犯罪论体系那样,我国也不否认存在违法阻却事由、责任阻却事由,理应有研究要素从属性的余地:正犯必须具备全部构成要件要素,还是也可不具有有责性,抑或只要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即可(例如,杀人罪中的“杀人”行为)?具体而言,尽管多认为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正是“具体犯罪的基本的构成要件”,(31)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也是以总则为前提,并非简单地归结为“只要杀人就是犯罪”,仍须进一步探究行为人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第14条、第15条)、是否属于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第16条)、是否属于正当职务行为、正当防卫(第20条)、紧急避险(第21条)等违法性要素(违法阻却事由),以及是否具有责任能力(第17~19条)、有无期待可能性等责任要素(责任阻却事由)。我们判断实施杀人行为者是否构成杀人罪、教唆他人杀人者是否构成杀人罪的教唆犯、帮助他人杀人者是否构成杀人罪的帮助犯的前提仍在于,无论该实施杀人行为者最终是否构成犯罪,其行为形式上仍须符合“杀死他人”这一杀人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尽管我国采取的是平面的犯罪构成体系,强调犯罪行为是主客观的统一,但要判断某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也不可能“一气呵成”,也必须首先把握是否存在“杀人行为”等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实行行为),其差别无非在于:先探讨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以及在哪一阶段探讨违法阻却事由、责任阻却事由。因此,较一味强调“共同犯罪应该是所有共犯均构成犯罪”而言,在发生法益侵害或危险的情况下,以实行行为为中心,在认定正犯实施了诸如“杀死他人”等实行行为之后,再考虑其他主客观要素,进而分别判断正犯、共犯最终是否构成犯罪,这并非全无意义,相反更具可操作性。
其三,从上面的论述中还不难看出,我国对共同犯罪、教唆犯概念的通说观点也并非“完美无瑕”,对此作出一定的修正,更符合司法实务的要求。而且,既然采取极端从属性说会出现诸多弊端,因而也并无将共同犯罪限于“所有共犯均构成犯罪”、将教唆的对象限于“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的必然性,也存在探究间接正犯或教唆犯何者更为合适的余地。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以为,采取何种从属形式与采取何种犯罪论体系并无必然联系,在肯定共犯从属性的基础上,我国有必要采取最小从属性说。
四、结语
综上所述,完全遵循我国关于共同犯罪与教唆犯的概念、教唆犯的性质的通说观点,对共犯是否采取从属性说莫衷一是,这不利于服务并指导司法实践;而且,即便就第29条第2款规定的教唆的未遂之外的其他共犯形态采取从属性说,也似乎只能采取极端从属性说,这既不符合我国的司法实际(因为我国并非一概否定违法的相对性),也有违近代刑法的个人责任原则(共犯的成立并不以正犯具有有责性为前提),这种“大一统”的观点更是只会禁锢刑法理论的发展。其直接反映就是我国鲜有学者探讨从属性的内涵,甚至有过度“仰仗”间接正犯这一学理概念,而轻视教唆犯这一法律概念之嫌。(32)
如果借鉴日本的共犯从属性理论,倡导最小从属性说,可以更加明确共犯的成立要件。例如,可对陷阱教唆、共同犯罪中的中止行为的一身专属性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不限于此,对于司法实践中如何处理利用刑事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利用他人的正当行为(例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正当职务行为等)实现犯罪的情况,更是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对此类问题一律认定构成间接正犯,既不符合个人责任原则这一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也往往只会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判决。反之,若能对我国的相应通说观点加以反思,采取最小从属性说,肯定责任的个别化与违法的相对性,严格区别教唆犯与间接正犯,只有在运用教唆犯理论不能解决的前提下,才例外地适用间接正犯解决问题,则不仅有助于达到个别预防的目的,也有利于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最终彰显刑法的公正性。
注释:
①张明楷教授就此作了详尽论述,但遗憾的是并未进一步论及共犯从属性的内涵。参见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331页。
②[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有斐阁2005年第3版增补版,第272页;[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成文堂2007年新版第2版,第409页等。
③[日]松宫孝明:《刑事立法与犯罪体系》,成文堂2003年版,第262页。
④[日]大塚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有斐阁1982年版,第356页。另见[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总论》,创文社1990年版第3版,第383页。
⑤[日]木村光江:《刑法》,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2版,第147页。另见[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4版,第425页。
⑥[日]山口厚:《刑法总论》,有斐阁2005年补订版,第266页。
⑦[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Ⅱ》,有斐阁1975年版,第358页。
⑧[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4版,第424~425页。
⑨[日]山口厚、井田良、佐伯仁志:《理论刑法学的最前线》,岩波书店2001年版,第236页。
⑩大谷实自己将其主张定位于最小从属性说与限制从属性说之中间位置。参见[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成文堂 2007年新版第2版,第409~410页。
(11)[日]林干人:《刑法总论》,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初版,第430页。
(12)[日]内藤谦:《刑法讲义总论(下)Ⅱ》,有斐阁2000年版,第1353页。
(13)[日]堀内捷三:《刑法总论》,有斐阁2004年第2版,第275页。
(14)同上注,[日]堀内捷三书,第253、276页。
(15)[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成文堂2007年新版第2版,第242页。
(16)张明楷教授主张结果无价值论,并就此问题作了详尽论述。参见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52~197页。
(17)同前注②,[日]大塚仁书,第338页。
(18)同前注②,[日]大塚仁书,第350页。
(19)[日]十河太朗:《共犯从属性概念的再构成(一)》,载《同志社法学》2004年第302号,第16页。
(20)同前注(12),[日]内藤谦书,第1354~1355页;[日]福田平:《全订刑法总论》,有斐阁2004年第4版,第257页。
(21)[日]高桥则夫:《共犯体系与共犯理论》,成文堂1988年版,第144页。
(22)[日]川端博:《刑法讲义总论》,成文堂2006年第2版,第532页。
(23)如张小虎教授在介绍共犯从属性说的具体内涵以及这四种从属形式的基础上谈到,“目前限制性从属形式为多数学者所采纳,从而凸显出教唆犯的相对独立地位,但仍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遗憾的是既未具体阐述批判限制从属性说的理由,也未结合我国共犯理论予以展开。参见张小虎:《犯罪论的比较与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593~594页。
(24)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347页。
(25)同上注,张明楷书,第317、324页;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11页。
(26)马克昌:《共同犯罪理论中若干争议问题》,《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陈兴良:《共同犯罪论》,《现代法学》第23卷第3期;魏东:《教唆犯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李兰英:《论教唆犯的几个问题》,《现代法学》第25卷第5期。
(27)“二重性说”认为,第29条第1款与第2款分别规定的是构成共犯关系的从属性教唆犯、不构成共犯关系的独立性教唆犯。参见同上注(26),马克昌文。
(28)如张小虎教授主张,“教唆行为、帮助行为的具体性质,依赖于正犯实行行为的具体性质,教唆犯、帮助犯的罪名从属于正犯的罪名”。参见张小虎:《犯罪论的比较与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6页。
(29)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2~563页。
(30)同前注(29),马克昌书,第548页。
(31)李希慧:《罪状、罪名的定义与分类新论》,《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
(32)例如,我国甚至有学者主张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的是间接正犯。这就将本只应承担第二性罪责的教唆犯直接“升格”为必须承担第一性罪责的正犯。参见何庆仁:《我国刑法中教唆犯的两种涵义》,《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
